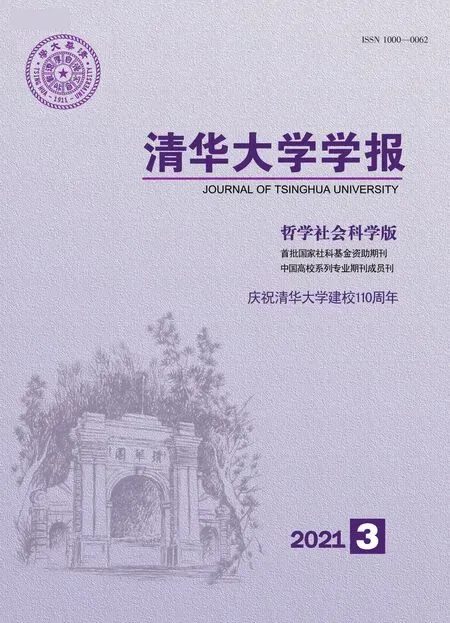论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创构与文化实践
郑倩茹 杨庆存
文道观是决定作家创作风格与艺术境界、引领学风文风与文化建设的关键。对于“文”“道”关系的思考与认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坛反复讨论的热点问题,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欧阳修对文章形式与思想内容关系的深入思考并逐渐生成构建的“文道观”,不但奠定了其文坛盟主的坚实基础,而且直接促进了宋代文化建设,既有力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又给后世以深刻启迪。以往研究大都侧重于文道观内容的理解与阐释,很少就欧阳修文道观生成的创构过程、文化环境和实践策略,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动态考察。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力图在还原时代历史语境的过程中,揭橥其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创构与文化语境
任何理论的产生与传播,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诸如首创者的综合素养、表述方式,接受者的层次范围、传播途径,乃至社会环境、文化思潮等。而首创者在建构话语体系时,也会受到文化资本、社会声誉、政治权力、士人群体、审美情趣等多种要素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并非纯粹认知性的知识形态,而是包含多重文化因素,是具有鲜明思想性、专业性、政治性、社会性与引导性的文化综合体。理论主张既与文人阶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角色紧密相联,也与士人群体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其背后依托的乃是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理想。如果将欧阳修的文道观仅仅理解为诗文风格或文学主张,就忽略了其文论话语产生的复杂性,遮蔽了文道观在文化内涵上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忽视了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我们尝试“把古文论的资料放回到它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去考察”,①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探讨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与构建。
欧阳修文道观的重要论述,大都集中在写给学人的书信中,诸如《与张秀才棐第一书》(1033)、《与张秀才棐第二书》(1033)、《与乐秀才第一书》(1037)、《与荆南乐秀才书》(1037)、《答吴充秀才书》(1040)、《答祖择之书》(1041)等等。这些文章写于景祐元年(1034)到庆历五年(1045)前后,是“欧阳修政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又一重要时期”。②王水照:《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见氏著:《走马塘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0页。在此期间的三段经历:西河幕府彰显文人身份;被贬夷陵赢得士人认同;任职馆阁成为文化精英,不仅促使欧阳修的文化资本迅速积累,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文学话语权力,为文道观的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次年任西京留守推官,当时的文坛宿老与新秀,如钱惟演、梅尧臣、尹洙、苏舜钦、张先等都汇聚于此,欧阳修《寓随启》称“西河幕府,最盛于文章”,③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五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90页。下引均据此本,仅随文夹注。是宋初文坛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他们主导了文学的主流话语,引领了社会的文化风向,并在文化因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阳修深受熏陶,“专以古文相尚,天下竞为楷模,于是文风一变,遂跨于唐矣”。④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六》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379页。其好作古文的文学志趣与审美风格,得到了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不少学子慕名向他投师求学。明道二年(1033),来自河中的张棐秀才献上诗赋作品,但欧阳修不予认可,《答张秀才棐第一书》批评他“持宝而欲价者”的钻营行为,谦称自己“官位学行无动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第977页),拒绝了张秀才的举荐要求。从话语表述中可以发现,欧阳修对自己此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有着清醒认识,因为决定文学话语的根本因素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显然这时他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景祐三年,欧阳修因贻书责备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虽然在政治上遭受了打击与挫折,但他仗义执言、不畏强权的精神品格,反而赢得文人同气相求、正义相惜的心理认同,得到士人群体的广泛支持,使他在文学领域的声誉不降反升。石介、苏舜钦等大批雅士纷纷寄诗慰问,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高度赞扬他嫉恶如仇、临难不避的文人气节。此诗一出,天下争相传颂,“布在都下,人争传写”,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进一步扩大了欧阳修的社会影响。欧阳修《于役志》记载自己即将离京之时众多文人分批前来送行,被贬途中也有大量雅士结伴同游、赋诗赠答,行迹所至均有士人迎来送往,如行至楚州先后与田况、刘春卿等人饮酒弈诗,至南京有石介相邀小饮于河亭,不一而足。文人群体的种种文化行为,充分表达出对欧阳修文化地位、士人品格以及精神追求的全面认同,也说明他此时文化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被贬期间的欧阳修要求自己“慎勿作戚戚之文”(第1897—1905、999页)。不仅文章琢磨愈精,而且首倡疑经惑传,开经学研究新风。欧阳修还与尹洙商议合撰《五代史》,在史学领域有所建树。欧阳修此时广泛涉猎文学、经学、史学等领域,奠定了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基础,正如庄有恭诗言“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⑥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05页。这段贬谪经历让他对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体悟,《与乐秀才第一书》说:“官仅得一县令,又为有罪之人。其德、爵、齿三者,皆不足以称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为惭。”(第1023页)此话虽是自谦之语,却透露出只有在世俗社会政治权力的主导下,文化资本与文学话语才能得以彰显的事实。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举荐欧阳修为陕西经略府掌书记,其《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说:“臣访于士大夫,皆言非欧阳修不可,文学才识,为众所伏”,⑦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卷一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足见当时欧阳修的文学声望日隆。欧阳修六月被召还京师,复任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重新回到政治文化权力中心,并与晏殊、宋祁等权贵显达、文章宿老宴集唱和。任职馆阁标志着精英士大夫身份的确立,馆阁是培养和储备治国精英的文化机构,位于宋代政治最高端,欧阳修在《又论馆阁取士劄子》中说文臣均是“有文章,有学问,有材有行,或精于一艺,或长于一事者”(第1728页),像晏殊、黄庭坚、秦观、苏轼、王安石等一流学者才能进入馆阁,他们代表着精英人才的最高文化品位,掌控着文坛的主流话语权,扮演着文化创造者、政策制定者和思想传播者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馆阁文臣在国家科举考试中负责具体考务,与翰林学士一起为国家选拔人才,是文化的实际“立法者”,更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者。在此时期许多学人入京进谒,欧阳修自称“过吾门者百千人”,①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见陈杏珍等点校:《曾巩集》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4页。可见他的精英身份与文学趣尚,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文化思潮与社会审美风尚的旗帜。而欧阳修对此始终保持着理性、谨慎的态度,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第663—664页)谦称自己的天资、官职、荣誉、才能不足以奖掖后进,但此语恰恰说明他深知自己“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②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5页。后辈士子的拜谒行为,也是看重他所占据的政治地位和拥有的话语权力。对吴充秀才来说,一旦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或举荐,他的文学生涯和社会地位将会发生巨大转变;对欧阳修而言,超越文学意义的馆阁身份,促使他思考着如何引导文风、砥砺士风。以上所述,都为欧阳修酝酿文道观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和气氛。
二、欧阳修文道观的表述媒介与内涵创新
宋代文学众体皆备,吕祖谦《宋文鉴》将文体分为58类,与人际交往相关的有问答、对、说、记、论、书等体裁。而欧阳修对文道观的理论建构与话语论述,几乎全部集中在与学人的交往书信中,则是他精心选择的一种表述形式。与普通学人相比,欧阳修显然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而表述媒介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一种标志着更深层次权力关系的符号形式,其中不无文化权力运作的支配性力量。学人借助“去信”表达自己的文化意图,即渴望凭借欧阳修的文化权威获得文化地位的提升。而欧阳修则通过“回信”阐述文学思想,传递给后进士人,引导他们的文化实践,传播自己的文化思想与理论主张。作为一种话语权力由高到低的传递方式,回信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满足求教者的心理期待,更益于自己的话语论述得到全面认可与接收,也更容易引导并改变学人的知识表述与心态结构。
欧阳修对回信这种传播媒介的认识是逐步明晰并加深的。《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一改之前的嘲讽态度,对他多有肯定和赞美,如“言尤高而志极大”“甚有志”“多闻博学”(第978页)等等,所述内容不仅包括自己对治学的理解,而且阐发了对文道关系的思考。欧阳修前后态度的显著变化,以及书写内容、言说方式的明显转变,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张秀才在文学话语上的不平等关系,可以通过“回信”这种表述形式将文学思想传递给广大士子,通过一个又一个学人的具体文化行为,让自己创构的理论主张获得更广泛的群体认同,并逐渐形成规模性的文化思潮。被贬夷陵期间,欧阳修对回信的传播力度之大和接受程度之高已然深有体悟。《与荆南乐秀才书》虽然对乐生所问“举子业之文”略有不屑论之的意思,但又担心误导和打击他,故而挈出“顺时”二字告之,将其为学困惑与文坛乱象结合起来,指出这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普遍现象,并且说自己在创作中也存在这种状况,“其前所为既不足学,其后所为慎不可学”,鼓励他树立信心,还以“齐肩于两汉”期许乐秀才(第661页)。清代文评家王元启说此文“措辞微婉,不作伉直语,较为可味”,③王元启:《读欧记疑》卷一,见《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47页。正是看到了欧公一改往日直白晓畅,措辞变得委婉善诱,反映出他越来越重视回信这种话语传递形式,也更加注重言辞表达的谨慎性以及思想论述的启发性。
欧阳修任职馆阁时所作的《答吴充秀才书》与《答祖择之书》,无论是内容要义还是表达方式都更为朴实,因为此时他已经位于政治空间的较高位置上,并成为文坛风气的引领者,可以更加坚定、直接地表述自己的文道观理论,也更利于学人顺利接受并迅速掌握。如《答吴充秀才书》以自己的作文经历为例,“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第663页),使吴充秀才更容易理解并接受启迪,话语表述体现出普适性、引导性与启发性。同时也更加注意回复内容的典型性和针对性,面对文士为求利禄而尽心于文字的现象,《答吴充秀才书》指出学人必须走出书斋,在社会现实中行道;针对当时士风堕落的现象,《答祖择之书》提出“师经”重道、重振儒学的主张。两封回信彰显出嘉惠后学、奖掖后进的领袖风姿,透露出精英文人的身份使命和责任担当,与此同时欧阳修也建构着自己的文道观话语系统。
首先,欧阳修将“圣人之道”作为文道观的灵魂。宋初,柳开、石介等人推尊韩愈,提倡“行古道作古文”,但只取其道统而忽视文。柳开认为“文章为道之筌也”,①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见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3册,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82页。将文学视为道的工具与附庸,之后石介接过复古大旗,其《尊韩》提出只要将“布三纲之象,全五常之质”②石介:《上蔡副枢书》,见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15册,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196页。的传道内容贯彻到文章中,文采形式可以略而不计,表现出重道轻文思想,导致文坛出现偏离现实、轻视实用的怪诞文风。欧阳修结合当时文坛状况,梳理儒学本义与传承,强化儒家之“道”思想内涵,建构“圣人之道”话语体系,并针对当时文风险怪乱象,赋予“道”新的时代内涵,严厉批评“诞者之言”,遏止其蔓延,使复古行道的儒家精神重新得以弘扬。
《与张秀才棐第二书》是欧阳修文道观最为集中、最为充分的展现。这封书信以评论张棐文章为引子,从六个方面,层层深入地阐明了自己的“文道观”思想,如“圣人之道”与“诞者之言”,“知道”“明道”“为道”“务道”“王道”等等,构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全文突出六大重点:一是由评论张秀才的“古今杂文”提出问题。欧阳修认为大部分“言尤高而志极大”,意在“闵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作了基本肯定和鼓励。同时也严肃指出其“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错误。由此引出“文”“道”关系的重要话题。二是分析“文”与“道”的关系,突出其重大意义。欧阳修先着眼于“道”,讲述“君子之于学”的目的在于“务为道”,进而指出“为道必求知古”的路径,再说“知古明道”的用途,在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即躬身实践、应用于现实社会,然后体现于文章,流传于世,启迪后人,实现“行道”“传道”的目标,促进人类的文明发展,而最后落脚于“文”。作者在讲清读书学习、知古明道、履身施事、见于文章、以信后世这五者之间内在逻辑与密切关联的同时,突出了用古代儒家之“道”来指导现实实践并体现于“文”的核心思想,着眼点与落脚点始终围绕阐发“文道”关系,而以“好学”“知古”“明道”“务道”“为文”五大支点为轴心,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三是界定“道”与“文”的内涵特质,突出文化传承。欧阳修明确指出,“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这不仅具体诠释了“道”与“文”的规定内涵,而且明确了儒家思想之“道”可“履而行之”与儒学经典之“文”能“至今取信”的根本性质。与此同时,欧阳修还总结了“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重要特征。这与“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的“诞者之言”形成鲜明对比。四是强调“圣人之道”的“可得”“可行”“可学”。欧阳修以孔子“道不远人”的名言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观点,说明“人”与“道”的密切关系;以《春秋》为书“以成隐让”“信道不信邪”等,说明“文”“道”本为一体;指出“圣人之道”能“履之于身,施之于事”,此非“诞者之言”所可比。又以《尚书》“稽古”、孔子“好古”,说明“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既具体实在又不虚不诞,“宜为君子之所学”。五是倡导为文“切于事实”而不务“高言”虚语。欧阳修以“孔子删《书》断自《尧典》”,其学则曰“祖述尧舜”为例,说明儒家明白“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的道理,故“弗道其前”,不说尧舜以前的事,体现着学风的扎实与文风的严谨。对于当时“舍近而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不良风气,欧阳修给予了严厉批评。此后,又举《书》为例,称“唐、虞之道为百王首”,而所书“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以此说明“道”在“事”中。欧公认为“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而“孟轲之言道”“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也是不务“高言”。六是批评“诞者之言”“无用之说”,以遏止与矫正不良文风。欧阳修批评“今之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指出“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这不是“学者之所尽心”的事。并针对张秀才文章“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弊病,劝其“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第977—979页)。由上述六点可知,欧阳修以正本清源的方式,重新举起复兴儒道与古朴文风的大旗,在建构文道观的话语体系时,不仅选择了广大士人最为熟知的“文”“道”概念,而且使用表达精准的“圣人之道”“诞者之言”一类不易产生歧义的词语,易为广大学人所接受。
其次,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建构过程。其《与乐秀才第一书》对广大学人最为关心的“文”作了深入阐释,进一步丰厚了文道观的理论内容。欧阳修指出往圣前贤“为道虽同”而“辞皆不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第1024页)的现象,不仅揭示了“文如其人”的个性化规律,而且说明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必然性。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内在修养有差异,却始终遵循儒家之“道”,尽管文章的形式风格与表述方式各具风貌,而在思想内容方面,都体现着关心社会、关注现实、关切民生的人文情怀,承载着重要的道德价值和文化意义。欧阳修视“文”为“道”的集中反映和表现载体,将儒学之“道”与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引导学人追求“圣人之道”,进而带动“圣人之文”在知识论述和文学表达上的转变,为广大士人指出了一条既能实现政治功利性,又能达成文学审美性的努力方向。
再次,欧阳修在厘清“圣人之道”的文化定位以及“文道”关系的基础上,又为建构文道观话语体系赋予实践意义。《答吴充秀才书》提出“道胜文至”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由此进一步指出“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第664页)。欧阳修认为,孔子著述整理六经只花了数年时间就得以完成,是因为他周游列国并实际考察,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认识深刻,思想与文化积累深厚。当今学人要想写出“圣人之文”,就要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践行其“道”。圣人之“道”是具体的、实在的、充满人情人性的,既在于“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的纲常伦理,更在于社会生活“百事”的方方面面。“务道、行道”就是要身体力行地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实践,积极承担社会道义和现实使命。欧阳修将抽象的“道”创新为一种可知可行的话语体系,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与质变,使其文道观话语体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行为上的可操作性,对现实生活有实际的指导价值,因此获得了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与普遍接受。
第四,欧阳修将“圣人之道”升华为士人阶层实现人生理想的坚定信念与践行准则。他在《答祖择之书》中指出,社会中存在着“今世无师”“忘本逐利”等败坏风气的现象,造成这种乱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文化的式微。于是他告诉学人,“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毅”,要求士人向真正代表“圣人之文”的“六经”学习,以“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价值,将“道”的精神实质内化在濡养德性的人格修养中,“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第1010、661页),注重对自身德性修养的锤炼,从而达到“道纯中实”的有德境界,体现在文章中自然会富有光彩。欧阳修将儒者终生追求的道德理想纳入“圣人之道”的评判维度,将“道”升华为士人阶层的核心文化价值和最高精神追求,体现出其文道观的社会良知与思想价值。
以上考述了欧阳修文道观及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其根本实质是欧阳修对儒家思想的殷服,是对修身养性圣贤品格的企慕,代表着士人阶层的文化品格与精神价值。欧阳修呼唤并创明“圣人之道”的话语论述,恢复儒学精神,回归圣人原旨,体现出强烈的古道意识以及“我注六经”的创新意识,有宋一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与诗文风格都是在“圣人之道”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
三、欧阳修文道观的文化实践与革新策略
宋初以杨亿、刘筠等为首的“西昆派”承袭晚唐五代文风,创作用事精巧、词藻华丽的四六文,重新煽起浮靡文风,随后晏殊、宋庠、宋祁、王珪等“后西昆派”又将骈文大量运用于制诰、奏议、碑册、谢表、笺启等应用文体中,四六“耸动天下”,①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盛极一时。宋仁宗自天圣三年至明道二年间,多次下诏申戒浮华,尹洙、王禹偁、穆修等文人也极力提倡古文,尽管朝廷遏制与古文派上下呼应,但似乎还是没有引起文坛的巨大响应。一方面是因为古文家对骈文、散文非此即彼的绝对态度,在四六文风头正劲之时,要“以散代骈”必定阻力重重;另一方面,古文家们并没有创作出超越前人的优秀作品,也没有出现能够折服文坛、号召与凝聚文人群体的领军人物,故不会得到广泛认同。
欧阳修走向文坛并逐渐崭露头角时,四六骈文早已是成熟的文体,具备了自成系统的话语风格,要想革新,并非易事。否定四六文体的话语形式,改变士人长期以来僵化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态,尤其是四六在科举取士中颇受重视的情况下,正所谓“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②叶适:《宏词》,见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28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难度之大不言而喻!面对朝廷申戒浮华的现实政治压力,如何恢复上古文风,让散体古文成为主流,这是古文派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变革文风的重大机遇。对欧阳修而言,这一时期是他引领文坛并树立盟主形象的重要阶段,文体改革的成败会影响甚至改变他的话语权力与政治地位。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策略才能确保文风改革成功,是他必须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欧阳修选择既有因循又有创造的策略,借鉴前人创新经验,选择“破体为文”的方式,在“尊体”与“破体”中突破了“文各有体”的藩篱,通过“以文体为四六”的话语创新方式,③陈善:《扪虱新语》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巧妙化解了骈体、散体看似完全对立的矛盾话语体系,创造出能够兼容古文而自成一格、独具风神的“宋四六”,探索到一种既维系时文功利性又含纳古文审美性的均衡模式,从而取得了宋代文风革新运动第一战役的巨大成功。
首先,欧阳修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海纳百川的胸怀,用理性、包容、通达的态度看待四六。其一,宋代建国至欧阳修主盟文坛之前70年间,四六创作十分繁荣,有历史的必然性。宋初万象更新、文治武功、国威扬厉,自然需要典雅庄重、富丽堂皇的骈文来歌功颂德、润色宏业,属对精切、形式优美的骈体,契合安稳平和、雍容醇正的审美风尚与文化心理。“兴文教,抑武事”的治国方略,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4页。表现出统治者尊重知识、优渥文人的政策倾向,不少士子因献赋获誉,如开宝九年(976)正月,扈蒙上《圣功颂》“述太祖受禅、平一天下之功,其词夸丽,遂有诏褒之”,⑤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239页。又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白献《平晋颂》而擢为中书舍人。此类例子,体现出政治权力对文学话语的规范要求,而文人通过创作四六迎合圣心,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意愿与权力诉求。因此可以说四六是政治集权和文化专制状态下,文人选择的集体书写形式,受到特定时代的影响。其二,四六确有无可取代的文体价值。欧阳修《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说:“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第662页),透露出四六能为士子提供文学话语与政治权力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功利性;此外还具有“上至朝廷命令、诏册,下至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的广泛性。①洪迈:《容斋四六丛谈》,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其三,四六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欧阳修《谢知制诰表》称:“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谟;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第1319页),充分肯定骈文端庄严肃的文体优势,以及用典精当、对仗工整等形式美。其四,从欧阳修早年的创作经历以及他与四六大家的密切交往关系来看,欧公“早工偶丽之文,故试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②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6页。足见其四六创作的功力;欧阳修在文学上与“西昆派”有一定渊源,钱惟演是西河幕府的主人,洛阳的文学经历影响了欧公文学思想的形成,他在政治上又受到晏殊等人的提携举荐,欧公自己也赞赏西昆诸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③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0页。更称杨亿为“真一代之文豪也”,④欧阳修:《归田录》,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故他并不全盘否定四六文。其五,欧阳修对文学发展规律有清醒认识。四六发展至杨、刘已达高峰,物极必反,后期似乎再无出路,而陷入隶事晦涩、堆砌典故、形式僵化的泥淖,导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⑤穆修:《答乔适书》,见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8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412页。士人沉迷于内容空虚、浮艳纤弱的时文不可自拔。欧阳修于此时提出“以文体为四六”的主张,为骈文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使四六的长短及节奏变化,服从于议论说理的需要;同时又借助古文的气势与笔调,使骈文自然流畅、情文并茂,从而提高了四六的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⑥孙梅:《四六丛话》,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5册,第4955页。重新焕发了鲜活的生命力。
其次,欧阳修始终将“圣人之道”作为核心思想贯穿于文体改造中。四六文最大的弊病就是片面追求语言工整,限制思想的自由表达,容易造成说理不清和叙述不畅,内容空泛显然无力承担载“道”使命,与“圣人之文”标准相去甚远。“以文体为四六”的文化策略,改变了刻意追求对偶、堆砌辞藻的僵化形式,有利于自由灵活地表达儒家礼乐的政教内容,改变了士人群体文化资本趋于世俗化的局面。欧阳修甚至直接将“圣人之道”的儒学精神贯注于新四六中,《上执政谢馆职启》直接以六经入文,但又叙事明白、娓娓道来,堪称“变革为文”的经典,不仅从文体形式上恢复了叙事议论的先秦古文传统,而且从思想内容上突出了“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第1446页)的社会功能,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为四六注入了一股源头活水,体现出欧阳修复兴儒学的精神实质。这才是纠正浮靡文风、净化文化环境最有力度的话语重塑与变革方式。
其三,欧阳修“众莫能及”(第2704页)的文章模范,以及文人的文化意愿与创作实践,促使“以文体为四六”获得普遍认同与广泛传播。首先,欧阳修的四六创作代表了“宋四六”的最高成就。他的文集中有7卷是四六骈文,大多为表、奏、书、启等,陈师道说“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⑦陈师道:《后山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10页。指出欧阳修骈文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艺术成就仅次韩愈。他本人的艺术才力超群,使他能将两种文体的章法、结构、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其《谢襄州燕龙图肃惠诗启》“佳在不作长句”,⑧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9页。《上随州钱相公启》“言情运事皆佳”,⑨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22页。他的四六创作异于流俗的文学形式,为广大士人钦服,“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第2670页),对变革浮华文风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其次,欧阳修作为文坛盟主,其文学主张获得士人群体的积极响应,前有二苏、王安石、曾巩等人,稍后有苏门四学士、陈师道等人,交相呼应,创作出了许多出色的宋四六作品。其中苏轼与王安石的四六创作最具代表性,“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⑩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二,见曾枣庄等编:《宋文纪事》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苏轼四六独辟蹊径,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说他的骈文“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①邵博:《闻见后录》卷一六,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第10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1页。其《量移汝州谢表》《孙觉可给事中制》等,笔调轻快雄健、句式自然妥帖。王安石的骈文自守法度,如《贺韩魏公启》《辞拜相启》等文章,笔力雄健、深厚典雅,展现着文风改革之后“宋四六”的新风貌。
其四,“以文体为四六”的改革策略其实是文学、政治与社会多方互动、彼此妥协的产物。欧阳修凭借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力,已经获得文人群体的广泛认可与普遍支持,士人承认、服从并认可他的文化权威与领导,团结了如梅尧臣、苏舜钦、范仲淹等同道,奖掖推荐了苏洵、苏轼、王安石等人。但当时的欧阳修,在国家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并不足够大,无法直接抗衡具有根深蒂固社会基础和现实政治权力的四六文。何况骈文还是当时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承载着一定的政治使命与服务功能,是文学形式与政治权力交织的产物。故欲变革文坛风气,只能通过“委婉”的文化创新策略来实现,在悄然渐变中完成。这里不妨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作比较,更能突显“破体为文”的思想智慧。嘉祐二年(1057)前后,欧阳修接连被授予翰林学士权知礼部贡举、右谏大夫、判尚书礼部、判秘阁等八种官职,宋仁宗还亲赐“文儒”二字,标志着他获得了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全面认可,掌握了实际话语权。欧阳修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知贡举,黜落僻涩险怪的太学体,“凡如是者辄黜”,②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九,第10378页。象征的是政治许可与权力意愿对文学形式与知识论述的甄别、筛选,所以短时期内就获得显著成效,“时体为之一变”,③沈括著,金良年校点:《梦溪笔谈》卷一九,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58页。沉重打击了太学体,让古文传统重获新生。欧阳修在改造骈文的第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时,并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亲自授权,更没有文学领域的绝对话语权力,所以面对变革四六文风的历史任务,他不具备彻底否定的资本,而只能通过矫正四六文的弊病,更新骈体的话语形式与论述方式,使之发生改变,“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④张:《明嘉靖玩珠堂刊西昆酬唱集序》,见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0页。而这正是欧阳修在变革文风过程中受到较少阻力,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欧阳修采取“以文体为属对”的文化策略,领导了宋代第一阶段的古文运动并获得成功,是他对文坛风向、政治权力和士人群体三者复杂关系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文学话语的创新性表述,才取得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终胜利。
欧阳修赋予“宋四六”新的生命与风骨,不仅古文家欣然接受,而且专精四六的骈俪名家如王畦,风格也为之一变。新式四六在南北宋之际及南宋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人彭元瑞在《宋四六选·自序》说:“洎乎渡江之衰,鸣者浮溪为盛,盘洲之言语妙天下,平园之制作高禁中,杨廷秀笺牍擅场,陆务观风骚余力。”⑤彭元瑞:《恩余堂辑稿》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46页。南宋文人汪藻、洪适、周必大、杨万里、陆游等人将这种新文体发扬光大,创作出了耸动人心、传诵人口的名篇。欧阳修“破体为文”的文化创新策略,为文学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健康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扭转了“论卑气弱”的文坛态势,营造了救时传道的文化环境,也创造性地弘扬和建构了中华文明发展的优秀文化传统。苏轼《六一居士集叙》称欧阳修为“今之韩愈”,“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⑥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页。正是对欧阳修亲身实践“圣人之道”与“圣人之文”文道观的最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