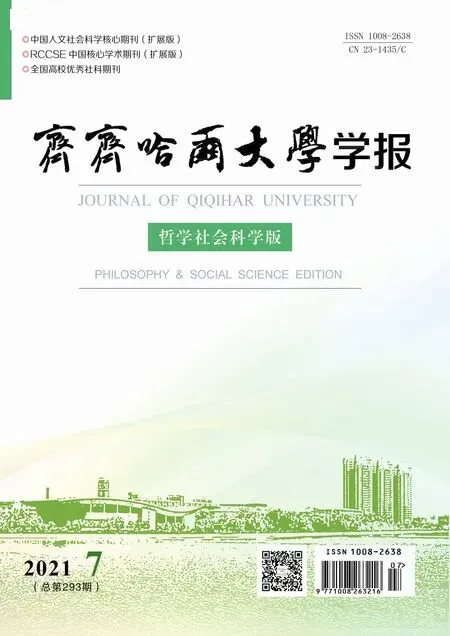记忆·符号·认同:电视剧《山海情》的乡土文化
刘晓燕,陈接峰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截止到2020年11月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认识不能仅停留在目标实现层面,更应该重视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至关重要,如何讲述脱贫攻坚事业的“中国故事”也不可忽视,其中叙述脱贫攻坚的发展历程具有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意义。新时代的中国电视剧涌现出了一批优质的脱贫攻坚作品。其中《山海情》具有现实观照、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内容层面上,影像是乡土文化的记忆与重构,形式层面上,以影像为载体的脱贫攻坚电视剧建构了受众的乡土认知。国内影视市场渐涌出一批以《山海情》为代表的礼赞“脱贫攻坚”的优质剧。电视剧《山海情》之所以取得极高的传播影响力和广泛的好评,与其奉行深耕细作的创作原则有着密切的关联,创作者秉持工匠精神,从现实生活出发,建构乡土记忆和文化的时空坐标。影音符号的运用使仪式性场景、仪式性动作和语言得以再现和表述,传播出乡土中国的社会记忆,剧集通过典型的中国人物和中国故事扩展了乡土文化的表达空间,着力展现中国脱贫攻坚事业,从而建构出国家和民族的认知。
一、乡土记忆的文化机制
在脱贫攻坚现实背景下,电视剧《山海情》的制作团队,描绘出乡土记忆和文化的时空坐标,绘制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图谱。电视剧《山海情》的创作者,以西海固干沟乡涌泉村为乡土记忆的空间载体,将移民吊庄作为叙事空间起点,把闽宁镇金滩村作为叙事终点。这一迁移历程,揭示着乡土空间的变迁,诉说着浓浓的乡情,描绘着山乡巨变的情景,折射着社会的变迁、文化的迁衍和文化记忆。“记忆的生成需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根植于特定的情境之中”。[2]20世纪90年代的涌泉村处于穷乡僻壤中,村民在贫瘠的黄土高坡上开垦土地,顿顿只能以土豆为食,因食物的缺乏政府发放八十一只扶贫珍珠鸡仅剩一只,兄弟三人只能共用一条裤子……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了西海固地区的贫穷。正是《山海情》中创作者对于西海固地区自然环境的真实打造为观众乡土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有力支撑,继而实现了观众集体共识的凝聚。“当今人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并列共存的空间时代,我们的时代焦虑也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3]西海固村民要想彻底改变“干沙滩”的面貌,彻底摆脱贫困就要面临吊庄移民的问题,然而整村移民遭到老一辈的强烈抵触。“作为一种共同体,村落有地域的共同性,正是因为村落共同体内的各家各户是长期生活于整个时空场域之中,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4]因此,涌泉村整村搬迁,在生于此、长于此的村民心中意味着对故土的割舍和脉源的断裂,而接受过现代知识教育的马得福则坚持认为整村搬迁是摆脱祖辈穷苦和走出大山荒瘠的利好机遇。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人之间产生的群体对立是西海固与闽宁镇两个并存空间的对立冲突,寓意着时代前进与历史固守的现实对抗,是那个年代先进社会思想与传统历史观念激烈碰撞的真实写绘。在当今精神世界极其匮乏的现代社会,村落对乡土记忆的展现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电视剧《山海情》将带领观众开启一场寻根之旅。
剧集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创作团队的创作理念,每一次的告别都蕴含着中国脱贫攻坚的乡土记忆,在记忆中讲述中国脱贫故事,在故事中弘扬中国脱贫攻坚精神。闽宁镇金滩村作为移民吊庄的终点,最初呈现空间环境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常年风沙漫天:“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但是闽宁镇离包兰铁路近,周边有国营农场,靠近黄河西干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带给西海固广大人民脱贫致富的希望。戈壁荒滩恶劣的自然环境无形中加剧了创作团队拍摄的难度,但是为让观众感知电视剧外部形态的真实,创作团队秉持工匠精神,从现实生活出发,扎根闽宁镇和西海固地区,与艰苦工作的基层干部群众深入探讨交流。正是由于创作团队深入西海固实地采访调研,使吊庄移民故事得到集中展现,从而让这部剧更为鲜活。剧中演员发表评论:“从地窝子到土坯房,既是闽宁村的成绩,也是《山海情》主创团队的突破,我们都是《山海情》当中的一个元素。”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审视,电视剧《山海情》不是呈现创伤记忆的修复和疗愈,而是蕴含着新时代的乡土记忆。作者以闽宁镇脱贫致富道路的呈现唤起无数人们对乡土记忆的感知,潜移默化中加强观众对乡土记忆的表达,闽宁镇成为观众记忆的追溯,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海固群众得到了国家扶贫政策的引导和福建对口扶贫的支持,通过艰苦奋斗在贫瘠的土地上建设新的家园。其中创作团队以教育帮扶、科技帮扶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重要内容进行呈现,一定程度上使年轻受众群体加深对电视剧《山海情》的接纳和认同,更好地理解国家扶贫政策的文化精髓。白校长和福建援宁教师郭闽航给荒漠戈壁上的孩子们带来了知识,知识打破了阻碍脱贫的障碍,让希望之光照亮整个西海固大地。凌教授在西海固土地上教村民种植菌草蘑菇,说服村民出资建棚,遇到蘑菇滞销问题时亲自跑销售,建冷库,自掏腰包垫付款项。当凌教授再次启程去帮扶新疆时,玉泉营的所有村民手捧自己种的枣、拿出家里的鸡蛋……赶来送行。2020年11月16日,西海固地区全部脱贫,闽宁对口扶贫贫致富的背后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式脱贫致富的成果,是世界脱贫事业的探路者。
二、乡土仪式的文化传播
“媒介是标准的制造者,作为传播和塑造意识形态的媒介,可以通过塑造标准化的展示方式来规范事物的内涵,促成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短期模式和长期习俗”。[5]电视作为文化传播媒介,往往具有构建国家品牌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功能。“没有媒介的记忆是无法想象的”。[6]电视剧《山海情》借助电视媒介实现乡土文化传播,可将其艺术化的制作和播出视为一场仪式活动。“仪式的形成有赖于形成创造者选择与他们有情感关联的对象,并通过具有严格规范的活动使对象依然活跃于现实中,或者说将其现时化”。[7]在电视剧《山海情》中,文化的仪式感是通过视听符号使仪式性场景、仪式性动作和语言得以再现和表述,仪式变成了文本,文本成为大众仪式想象的媒介。詹金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性并不是在于信息的获取,而是在于某种戏剧性的行为”。[8]在这种戏剧性行为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信息效果或功能问题,而是在观看电视剧《山海情》中呈现和介入在建构观众生活与时间中所扮演的角色。
电视剧《山海情》的观众在“身体操演”[9]中参与到脱贫攻坚这项纪念仪式之中,这种纪念仪式是通过情感互动参与到剧中,其中导演对于色彩的运用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感受的同时实现了电视剧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互动。色彩有“第一视觉要素”之称,[10]直观的表达画面符号所传达的信息。“人类对色彩的最高层次的认知是寓意于色,就是赋予色彩某些符号化、象征化的意义,而探究和挖掘色彩的象征意义就是人们基于色彩的运用最重要的部分。在人类的情感领域,色彩符号被赋予象征意义之后能够深刻而又贴近地表达人们的信仰和观念,生成色彩情感”。[11]电视剧《山海情》中色彩运用真实还原了黄土地上村民形象,将一位普通却又不平凡的西北人民刻画的淋漓尽致。黄轩在《山海情》中饰演一位年轻扶贫基层干部——马得福:宽厚淳朴的西北方言,被黄沙沾染得泛黄的头发和衣服,古铜色脸上有两团高原红,干燥气候下粗糙皲裂的黄色皮肤、大风吹后在皮肤上留下的纹路都清晰可见。人物形象的真实描绘、浓厚地域文化的呈现使观众将剧情引入到自我情感之中,实现电视剧与观众之间的共情,完成脱贫攻坚纪念仪式的“操演”,赋予电视剧创作以活力。
电视剧《山海情》中对仪式性的场景描绘和仪式性的语言的运用拓展了观众的情感表达的空间,艺术化的表述让使西海固地区脱贫图景更加鲜活,实现了仪式感和高尚感的叠加。
贫困之苦、脱贫之难是西海固百姓最真实的写照,移民在吊庄途中遇到沙尘暴,一阵疾风后漫天黄沙,行李被风沙卷起导致村民身体受伤孩子受到惊吓,这更是构成了西海固“干沙滩”的典型性场景。电视剧《山海情》中西北方言和福建方言的使用使人物塑造富有感染力,起到了活跃剧情的作用。“流行的文化产品具有“文化吸引器”的作用,也就是通过文化产品可以把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观众召集到一起,并使这些观众相互之间产生价值的认同”。[12]在剧集的第一个章节,马得福和张主任在涌泉村召开集体大会,动员大家移民吊庄,面对村民对吊庄移民的抵触老支书说:“我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了,我知道咱涌泉村穷,可是再穷,也不能把骨头穷没了是吧……这又能打工又能挣钱这算啥苦嘛?有奔头那就不算苦,没奔头那才叫真的苦……在咱这儿活不好,咱换个地方活有啥不好呢,张同志你放心,咱涌泉村不会给全县丢人,不会扯全县的后腿。”年迈的老支书一口浓厚的西北方言,句句铿锵有力,言语间突出了西北人民淳朴、善良的特质,扩展了人物情感表达的空间,加深了受众对于电视剧的接纳和认同。剧集中福建方言采用的是福建普通话,福建省扶贫领导吴月娟在给扶贫干部开会时,一口浓厚的福建普通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922年到现在,七个村四千人,从吊庄区发展成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规模,这也证明这种移民方式是可行的,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要把这种模式发扬光大,一方面我们让原住地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和重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异地建设我们要从根源上帮助老百姓来解决贫困问题。”话语间的停顿加深了语言的感染力,使观众感受到了福建政府带领宁夏人民脱贫致富的决心,这其中也包含了两地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因此,方言版《山海情》立足于本土化特色,对方言深入的探索展现了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演员演绎方式的变化催生了喜剧性,打破以往电视节目中人物形象概念化的局限性,使观众领略到语言在主流题材影视作品中的独特魅力。
三、乡土中国的文化认同
电视剧《山海情》仪式性的表达方式之所以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并能够成为他们脱贫攻坚记忆中的一部分,是因为其剧集本身蕴含着劳动人民的乡土情怀,这种情怀建构了城市寓居者和年轻观众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成为一代人乡土文化记忆的载体。“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形成的“回不去的农村”的思潮一样,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乡愁”次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思潮。越来越多原本寓居在乡村的人口转而以城市作为生活的据点,失去了与亲情和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这部分人口分布在急遽扩张的城市里”。[13]他们成为乡村题材电视剧的拥趸,在电视情节的推进中思考时代的变迁,脑海中浮现的是对故土家园的乡愁,内心深处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情再次被唤醒。乡村题材电视剧《山海情》中对脱贫攻坚道路上农民和知识青年形象的塑造使城市寓居者产生了强烈的身份和文化的认同。
农民作为乡土社会的主体,主要依靠农业来谋求生存,他们始终与土地有着紧密的关联,依赖于土地并且受制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14]剧中所刻画的农民形象大有叔,村支书马喊水,他们对于美好生活有着不懈的追求,并为脱贫攻坚而努力奋斗,在参与和互动中唤起了千万人对于自己家乡无限的回忆和思念,从而完成了年轻人对家乡脱贫攻坚记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记忆。“我们保存着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15]在剧集《山海情》所塑造的一大批为脱贫攻坚事业而奋斗的村民中,很多都是受到过高等教育、具有知识身份的年轻人,他们投身于家乡脱贫工作当中,承担起脱贫地重任。剧中的基层扶贫干部马德福,当年农校毕业后,参加工作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追回参加吊庄的村民,动员西海固贫困地区的百姓搬到宁夏附近的平原,建设新家园。马德福的扮演者黄轩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演一个农村人,我觉得中国扶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且有正能量的事情,是值得歌颂的。马德福是一个基层干部,他非常简单纯粹,并且带有一些执拗,却从不抱怨,就是积极为大家解决问题,真心希望大家能够脱贫致富。”[16]剧集中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包含更多的温情,热依扎饰演的李水花,以素颜呈现在荧幕之上,辍学后的水花被她父亲以一头驴、两只羊、两笼鸡的价格卖到邻村,她选择反抗最终向现实低头。这不是简单的认命,而是勇敢坦然的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丈夫因为建水窖致残后,她又独自撑起整个家,勤奋好学,向凌教授学习种植蘑菇的经验。《山海情》为观众呈现一个具有女性自觉意识的荧屏女性形象,成为玉泉营其他女性精神上的引领者。年轻人参与扶贫投身于家乡脱贫攻坚事业,他们给贫困地区带来的除了一些硬性的政策支持以外,更多的还是他们的年轻、朝气和锐气,他们打通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文情怀,给贫困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随着西海固百姓和基层干部的不懈努力,贫瘠的黄土地变成了塞上江南,踏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现如今山河壮丽,国富民强。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践行,并对这一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17]着眼于中国大地上涌现的优秀剧目,在提升文化自信、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电视剧《山海情》以全新的形式诠释文化自信,打通了剧集中蕴含的人文情怀,充分利用具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完成宏大国家叙事的呈现,为民族记忆的传承给予更多力量,将观众带入一段跨越山海的真实奇迹。建设新家园的西海固百姓、投身家乡脱贫事业的年轻人、勤政为民的基层扶贫干部、助力脱贫的专家以及各行各业在脱贫攻坚一线上默默奉献的人民,都是脱贫道路上平凡而又伟大的乡土人物,他们使城市寓居者产生身份认同,建构年轻观众关于中国脱贫攻坚的记忆,唤起观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扩展了文化的表达空间,赋予电视剧创作以活力。沿着精准扶贫的道路,掀起了知识精英、青年群体返乡的热潮,使具有历史厚重感的中国乡土文化焕发出生机。
总之,在大众传媒时代语境下,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具有现实观照、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其中剧作《山海情》一方面通过乡土记忆空间性和时间性表征地域文化的方式来传播乡土中国的记忆;另一方面融合期待视野和视界,唤起观者与对乡土中国的文化认同,蕴现出真情融入现实关照、真心凸显时代意义以及真实镌刻社会价值的创作情怀,再加之作者生命体验的温情流露和中国乡土大地的深入聚焦,得以使其成为一部影射乡村振兴时代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的优秀荧幕作品。因此,这部集聚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同时注入乡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主旋律扶贫剧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