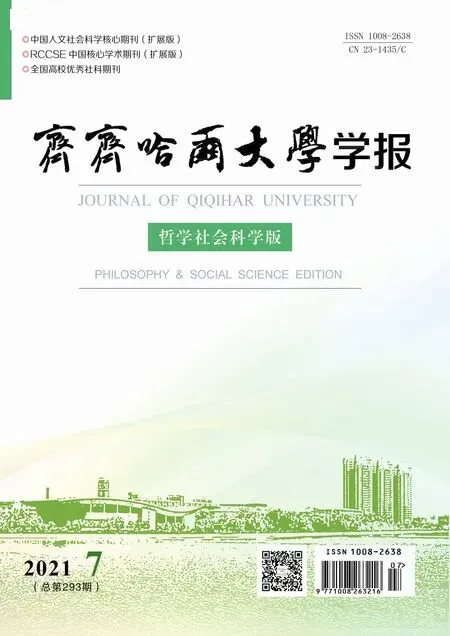论牛汉诗歌的生命形态
乔军豫
(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在牛汉的诗歌中,生命体验、生命哲思通过艺术巧妙处理转化为诗歌的审美特质,成为与众不同的诗学品格。诗人塑造的生命形态十分鲜明,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气息,迸发出强大的生命潮流,令人为之惊心动容。我们向牛汉营造的诗歌艺术境界攀登,领略到他书写的生命形态的别样风采,并从中发掘其诗歌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一、走近“绿色”:植物生命形态
牛汉的诗是生命之歌,展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景象。在绿色的生命世界里,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个独具特色的生命形态。它们是饱经风霜的诗人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创造的,正如牛汉所说:“我是凝结着全部的精气、心血和生命写诗。”[1]因此,寄寓着诗人一生不同时期的生命哲思和生命理想。1940年代初创作的《鄂尔多斯草原》足以说明问题。诗人以“绿色”确立为自己的言说姿态,使诗具有浓厚的生命意识,表现出独特的生命意蕴。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生命底色的渴望和赞美:“我歌颂绿色的鄂尔多斯/歌颂北中国绿色的生命的乳汁/绿色的生命的海/绿色的战斗的旗帜。”(《鄂尔多斯草原》)牛汉创作这首诗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民的前途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又在何方?促使诗人不断思索和探寻。诗人在黑暗的现实很难看到光明的未来,落寞和苦闷的情绪就油然而生。为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诗人走向了大自然的怀抱,在与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亲密接触中,生命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仿佛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诗人获得写诗的契机与灵感。绿色的草原抚慰牛汉痛苦的心灵,绿色的草与向往“绿色”的心达成和谐默契,诗人的精神世界得以“还乡”。牛汉憧憬一个广袤高远的绿色视野,绿色的鄂尔多斯大草原就自然充当了这样的一个生命载体。诗人在鄂尔多斯大草原那里找到情感的对应物,并且坚信作为生命底色的绿色就是当时国家数亿万生命的期待和希望:“静静地/茁壮着明天的生命力。”(《鄂尔多斯草原》)显而易见,“鄂尔多斯草原”就是“生命”或“生命理想”的代名词,一时占领牛汉的诗歌审美空间,大放艺术的光华。
牛汉的诗歌有温度。读之,总感到有一股生命的暖流奔腾而来,隐含着生命被埋没被压抑后仍对生命抱有的热切守望,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命在困境里坚韧挺拔,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二是对受侮辱受损害的生命持“理解之同情”、欣赏与热爱的态度。诗人将植物生命形态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作对照,我们能从中深切体味到他的生命底蕴、生命本质及其倡导的生命主张。1970年代牛汉将埋藏于地下毫不起眼的“根”纳入“麾下”,于是,一首首关于“根”的诗就这样诞生了。《毛竹的根》写毛竹面临严酷的环境:干涸的荒山、发烫的黄土地、坚硬的岩石和网状草根纠缠的周边世界,但它不惧,却能“迂回曲折”找到“生命之湖”,将汲取的生命的清泉再“反哺”给干渴的荒山。《根》采用第一人称抒写道:“我是根/一生一世在地下/默默地生长”,它听不到“枝头的鸟鸣”,感觉不到和煦的“微风”,不去跟高高在上的“枝叶”攀比,相信“地心有一颗太阳”(《根》)。“根”朴实一生默默一世,用“枝头”沉甸甸的果实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巨大的块根》的生命形态奇特,“灌木丛”年年长又年年被砍斫,生长了几十年却没长成一棵大树,但顽强的生命“凝聚成一个个巨大的根块/比大树的根/还要巨大/还要坚硬”(《巨大的块根》),不停地聚集热能,期待“人们把珍贵的根块架在火塘上面”(《巨大的块根》),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江南阴冷潮湿的冬夜。《伤疤》叙写一棵生长了数个世纪的大树被伐倒后,地面上留下触目惊心的巨大的“伤疤”。随着岁月的推移,泥沙和灰土掩埋住了“伤疤”,但这棵大树的根却深扎于土底下。大树的根能繁衍它的子孙,长出新的枫树来。“根”是生命的支撑点,也是牛汉的一个显著的诗学坐标。“根”让牛汉产生特殊的感情,他在《学诗手记》里坦言:“我从根的品性、姿态、苦难,获得了难以抗衡的精神力量,其中有无言的慰藉,也有高远的启迪。”[2]“根”作为生命形态,自身带有谦卑、低调、淳朴、隐忍的生命气象,与恶劣的现实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加深了读者对“根”的理解和认识,给读者带来一种阅读的快意。
牛汉自称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3]这一下子点名他的诗歌发生学原理——根植于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诗人的主观情感和客观对应物融合统一后,诗中的具体形象就产生了超出其原有的客观意义之外的另一层涵义,它们烙印着诗人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4]牛汉的诗常常流露出生命的爱意,如《野花》、《车前草》、《第一朵花》等。在诗人看来,即使一朵寻常的野花,“也有母性的温柔/在分娩的前夕/它们的生命也流溢着快乐与甜蜜”(《野花》)。野花在即将凋零的时候,会突然散发出一些奶汁样的气息,值得人们喜欢和珍爱。牛汉也对另一种平凡的生命——车前草——怀有深深的敬意。诗人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默默无闻甘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生命形态:“生长在乡间小路上/生长在牲口的蹄印里/生长在旅人的面前//几张椭圆的叶片/布满了厚厚的尘土/低低地贴着地面/远远望去/像一块块踏脚的石头。”(《车前草》)诗人饱含深情歌颂了车前草“默默地埋在脚印里”的生命风范。“第一朵花”是春天的信使,向人们报道春天的讯息。诗人夸赞道:“几片白里透红的花瓣/支楞起来/像婴儿透明的耳朵/谛听着远方/听到了候鸟的羽翼拨动冻结的天空/天空也将蓓蕾般绽开。”(《第一朵花》)“第一朵花”预示一个草长莺飞姹紫嫣红的春天已经到来,给读者留下美好的想象和联想。
《半棵树》这首诗呈现出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生命形态,一棵完整的树被雷电“齐楂楂劈掉了半边”,诗人将其命名为“半棵树”。虽然它不幸地失去了“半边”,但仍然顽强不屈地活了下来,“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虽然它遭受无情的重创,但仍然“还是一棵树那样伟岸”。“半棵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残疾”只是“身体”的某种极端而已,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心灵的健康和灵魂的健全。生命的悲壮美和崇高美在这“半棵树”上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交代了枣子早熟的原因,这棵枣子因受到虫子的噬咬而感到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在凋零之前,它期待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于是便在弥留之际“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早熟”是这颗枣子遭虫咬而作出的无奈的选择,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无限的悲怆:“我憎恶这悲哀的早熟/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全诗以乐景写哀情,让读者更觉悲哀和凄凉。《虔诚的头颅》这首诗从题目来看,巧设悬念,发人深思。“虔诚的头颅”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向日葵的生命形态。诗人选取向日葵这种植物生命历程中数个关键节点,用特写的镜头将数个关键节点组合在一起。诗中形单影只的向日葵自始至终低垂着它饱满的头颅,虔诚地“完成了它的一生”,“从冰冻的土地里挖了出来/它的低垂的头颅多么沉重啊/数不清的生命的籽粒洒落着/像一串串命运的泪滴”(《虔诚的头颅》)。牛汉怀有一颗虔诚的心在为虔诚的生命——向日葵——画像。《一盆小石榴》更是立意新颖,小石榴“在瓦盆里弯来弯去/处处碰壁”,但不甘服输,不安于现状,执着地梦想能够找到“遥远而广阔的母亲大地”(《一盆小石榴》),“一盆小石榴”传达了一个被压抑被扼制的生命对自由和博大的生命境界的憧憬与追求,呈现了另一类不幸的生命形态。
牛汉走近“绿色”,在那里寻找生命的底色和内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植物生命形态,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为诗歌艺术长廊增添一道道迷人的风景——鲜明生动的植物形态。成功之处在于他的生命诗学的运用,其诗歌创作过程就是其体验生命、感悟生命的过程,他的诗歌恰恰所传达的正是他的生命体验与感悟。[5]只有用生命和心灵去贴近牛汉那冒着生命热气的诗歌,去领悟他那有一定海拔高度的诗歌,我们才能感受到他诗歌里生命的呼吸、痛哭与微笑,才能获得他诗歌里生命的信息和能量。牛汉真诚地“写作生命”和“为生命而写作”,其“写作姿态”和写作目的令人敬佩。真正能像他这样做并达到他那种水平的还不多见。论及“生命写作”,有人误认为是青春的挥洒、激情的宣泄,有人误认为是简单的抒情。其实,生命体验的深刻与浅薄,主体人格的高大与渺小,语言表达的精准与偏颇,写作态度的真诚与敷衍,是能否达到“生命写作”这一境界的关键之所在。牛汉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创作基础,给生命以关怀,真诚地去“写作生命”和“为生命而写作”,这是牛汉区别于其他诗人的主要标志。
二、凸显刚烈:动物生命形态
牛汉的诗歌塑造了大量的动物生命形态,一般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这些动物大多是受害者、伤残者,处于生命的低谷;二是它们身上都有着坚韧不拔、顽强不屈、敢于挑战和斗争、誓死捍卫生命的尊严的精神与意志。我们选取几个典型来做具体分析。首先我们从“鹰”入手,《牛汉诗选》里写鹰的诗有五首:《山城与鹰》、《鹰的诞生》、《一只跋涉的雄鹰》、《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鹰的归宿》等。鹰是诗人倾注心力较多的动物。无论何种类别的鹰,无一不是勇猛、强悍、刚烈的象征。“鹰”引起诗人强烈的生命反应,与诗人结下了“缘分”。诗人创造了一个融客观物象与主观心境为一体的动物生命形态,借以传达生命的体验与感悟。“鹰”将诗与生命深度契合,诗代表朝气蓬勃的生命,悲壮崇高的生命也化为壮丽的诗篇。《牛汉诗选》里关于鹰的五首诗,催生了几个生命哲学问题:什么是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处在困境中的生命如何进行自救以及生命如何进行救赎?[6]
在《山城与鹰》中,鹰是山城哺育的,不惧山城天气条件的险恶,依然渴望在山城的弥天大雾里飞行。鹰的英勇无畏的行为在向人们宣告:“自由飞翔才是生活……”(《山城与鹰》)鹰的诞生是异常艰难的,“鹰的蛋是在暴风雨里催化的/隆隆的炸雷/唤醒蛋壳里沉睡的胚胎/满天闪电/给了雏鹰明锐的眼瞳/飓风十次百次地激励它们长出坚硬的翅膀/炎炎的阳光/铸炼成它们一颗颗暴烈的心”(《鹰的诞生》)。诗中以“暴风雨”、“炸雷”、“闪电”、“飓风”、“炎炎的阳光”等作为参照物,渲染了鹰诞生条件的“非人道”,烘托出鹰生命的强悍和刚烈。《一只跋涉的雄鹰》里一个“雄”字明显流露出诗人对鹰由衷的歌颂。一只雄鹰不幸跌落在“干热而焦渴”的荒漠,如同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噩梦”,九级风暴铺天盖地带来死亡般的恐怖和威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鹰一步一步在跋涉/生命最强悍有力的羽翼/支撑住被旋风围击的躯体/使之不摇颠/不偏斜/不倾倒”(《一只跋涉的雄鹰》)。即使凛冽的旋风拔去它所有的羽毛,甚至舐去一层皮,使它变成一只流淌着鲜血的秃鹰,但它的雄心依然不改,搏击长空的英雄本色促使它扑扇着翅膀重又飞入万里苍天。《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揭示了鹰知命安命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采用第三人称来表达:“它的一生/只能在广阔的天空/不停地翱翔/唱着自己悲壮的歌。”(《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鹰的归宿》又是一曲唱给生命的赞歌。鹰在“风云变幻”的天空快要过完“壮丽的一生”,在向大地作永远的告别前,不是“从高邈的天空坠落”,“而是幸福地飞升/在霹雳中焚化/变成一朵火云/变成一抹绚丽的朝霞”(《鹰的归宿》)。《鹰的归宿》以近乎冷酷的笔调描写了鹰“向死而生”的壮举,涉及生命哲学问题。对生命终结和重生的叩问,对生命的美丽和辉煌的礼赞,对生命至境的神往,都体现在“鹰的归宿”这一深邃的命题上。鹰的生命从有限上升到无限,从短暂化为永恒,诗人似乎在这里找到生命哲学问题的答案,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完成了生命的自我拯救和救赎。
在动物生命形态中,“华南虎”非同寻常,体现生命的高贵、刚毅和尊严以及极端困境下的决绝抗争,是诗人重点关注和抒写的主体对象,有着极为重要的原型意义。[7]《华南虎》描写一个遭囚禁的“受难者”形象。它受尽了屈辱和磨难,它的趾爪全是破碎的,凝结着厚厚的血痂,还遭捆绑,牙齿被钢锯残忍锯掉。
有人用石块狠狠砸它,有人厉声呵斥它,还有人居心叵测劝诱它。但是,它对这些野蛮行径“一概不理”,甚至连正眼也不眨一下,以致对手“胆怯而绝望”。它又长又粗的尾巴在悠悠拂动,健壮的腿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像是鞭击那群可怜的对手,又像是梦见苍茫辽阔的山林,企图冲破牢笼重新获得自由和解放。铁笼里和灰灰的墙壁上有一道道血淋淋的沟壑,闪电般耀眼刺目,“像血写的绝命诗”(《华南虎》)。最后,诗人听到“石破天惊的咆哮”——“一个不羁的灵魂”腾空而去。
《华南虎》创作于1973年6月,正值“文革”时期,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生命遭戕害,人性遭扼杀,无数生命岌岌可危,难以保全。诗人强烈感受“文革”给无数生命带来的痛苦与悲哀,并与他们“同病相怜”。同时,也十分敬佩每一个血性的生命为摆脱囚禁获得光明和自由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华南虎”被诗人赋予“人”的性格和特征,成为一个刚强的生命和不羁的灵魂的鲜明的符号。铁笼代表邪恶势力和强权,严重伤害活泼的生命和扭曲自由的生性。然而,伤害和扭曲会产生极大的反作用力,让“华南虎”爆发巨大的生命力量。“华南虎”象征的生命之火在“文革”的暗夜里显示出更加璀璨的光辉,“华南虎”象征的灵魂之光在苦难中得到升华的源泉。牛汉把生命体验、生命哲思、丰富的想象寄寓华南虎这一独特的生命形态上,运用隐喻、象征、对比等艺术手法,将现实的“丑恶”衬托出其相对应的崇高美,显示出他诗歌艺术创造的本领。诗人忠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华南虎为意象抓手真实记录了一段生命的受难史,饱含他对生命及其命运的深度关切和忧思,有沉甸甸的历史痛感和较大的警世意义。
牛汉笔下的“荒原牛”、“雨燕”、“海鸥”、“黄河鲤鱼”等生命形态也给读者留下过目不忘的印象。“荒原牛”富有美德,集坚韧、勤劳、善良于一身,但还是陷入孤独饥渴的境地,奋力挣扎后倒在茫茫的沙碛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从来没有进攻过世界伤害过世界的尖角和仅剩下筋骨的腿脚;更能打动人心的是,“一个个没有干瘪的乳房/还是棕黄色的/还是湿润的/从陷落的命运深处/群峰一般耸立而起”(《为荒原牛塑像》)。“雨燕”富有灵性和“敢性”。它的翅膀尖锐有力,急速穿越密布天空的乌云,“飞得快/像箭矢/像电光”,“搅乱厚厚的乌云”,不停地“呼唤风雨”,“招引来一阵阵霹雳”(《雨燕的话》)。即使如此,它的穿越行动仍不停止。“海鸥”富有刚烈的意志和牺牲的精神。它蔑视黑暗寻找光明,扑向灯塔的亮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连灯柱上也燃遍了斑斑的血迹”(《海鸥的坟》),自己化为一道亮光,与光明同在。“黄河鲤鱼”富有生存的智慧和倔强的性格。“倔强的鲤鱼/经过千千万万代死死生生/学会了在泥浆似的激流里/睁着圆圆的眼睛/一眨不眨/学会了在恶浪与恶浪的隙缝中/从容地呼吸/学会了迎着你的逆流冲刺/”,“向太阳飞跃”(《黄河与鲤鱼》)。
牛汉塑造的动物生命形态大多采用写实和英雄式的浪漫抒情相结合的手法,但一小部分诗作运用写实与平民式的梦幻抒情相结合的方式。《蝴蝶梦》便是后一种方式运用的典型。诗人在《蝴蝶梦》里写道:“那些年/多半在静静的黎明/我默默地写着诗/又默默地撕碎了/撕成小小的小小的碎片/(谁也无法把它复原)/一首诗变成数不清的蝴蝶/每一只都带有一点诗的斑纹。”诗变成翩翩起舞的蝴蝶,乘着风飞向远方。在这里,我们驻足思考,蝴蝶象征什么?远方又象征什么?联系当下较为流行的一句诗: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产生了新的认识。远方有诗,是富有诗意的远方。在诗受冷落生命遭压制的时代,富有诗意的生命是活跃、飘逸的,像自由飞翔的蝴蝶。诗的生命与诗人的生命是相辅相成的,诗的生命就像诗人的生命一样,向往着远方,憧憬着未来,渴望着“神与物游”。在诗里,蝴蝶变成诗人心灵的信使,展开灵动的翅膀,划出美丽的弧线,飞得很高很高。天气晴好也罢,雨暴风狂也罢,都勇敢无畏地在海上飞翔,耐心寻觅萌动着诗意的远方。蝴蝶在海上跳着曼妙的舞步发出悦耳的歌唱,让大海着迷,海水变得异常柔媚起来。蝴蝶看似弱小,实则刚强而勇毅,不惧大海的威力而征服了大海。在蝴蝶的身上,我们看到富有诗意的生命所具有的“弱德之美”和刚烈之勇。
三、对照自我:“他者”生命形态
“他者”生命形态是相对诗人自己生命形态而言的,在对象的选择和创造上有显著的特征和路径。这与诗人曲折的人生、坎坷的命运、丰富的阅历以及鲜明的性格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他者”生命形态与诗人的主观世界一脉相通,有思想的照应和情感的共鸣,所以诗人的生命就打上了“他者”的思想情感的烙印,或者说,诗人的思想情感在“他者”的生命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诗人凭借这些与自己生命息息相通的“他者”生命形态,来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生命的“栖息地”,消解自己的苦痛,净化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生命塑像。可见,这些与诗人生命对应合拍的“他者”生命形态,给诗人发挥了良好的心理调节作用。反过来,诗人在塑造“他者”生命形态时,也倾注了大量的智慧和心血,挖掘出与自己相似的生命意志、生命理想、生命追求,使之成为一个个卓然挺立于诗坛的难以磨灭的塑像。同时,也走进读者的心中,成为一座座不褪色的丰碑。我们从“他者”生命形态源源不断地汲取精神的动力,增强战胜生命困境的信心和勇气,以便更好地守卫生命的尊严、圣洁、崇高,更好地追求理想的生命境界,更好地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8]
牛汉将诗歌艺术的视角直接对准“他者”生命形态,实质上是对准自己,留下了自己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背景下的生命形态。这是诗人自己命运的倒影,是诗人自己心灵真实的倾诉,也是诗人自我写照和真实的塑像。《雪峰同志和斗笠》、《关于脚》、《把生命化入大地——忆孟超》等三首诗都是创作于没有诗意的时期,[9]真实描述了“他者”生命形态。冯雪峰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曾热情参与了1930年代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可是在“文革”时期,“空白论”和“新纪元论”盛行泛滥,肆意攻击和诋毁“三十年代文艺”。冯雪峰自然也牵连其中,遭受迫害。恰恰那时牛汉也遭批斗被下放到农村,与冯雪峰同在湖北咸宁文化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牛汉近距离接触了冯雪峰,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先驱者的高风亮节和赤子情怀所熏陶和感动。通过对“斗笠”的描写,讴歌了冯雪峰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坦荡的革命精神。《关于脚》特写了历经沧桑的冯雪峰的脚——“干干瘦瘦”、“青筋弯曲而隆起”——看起来让人心疼。脚上面不仅有革命岁月里敌人的“铁镣啃的伤痕”,还有因“四人帮”迫害使“脚掌布满了厚厚的茧”。这双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脚”是阶级敌人和“四人帮”铁的罪证。冯雪峰却认为它们“像手一样美好”,“比脸面重要得多”。在炼狱般的日子,冯雪峰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牛汉在诗里抒写了冯雪峰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丹心和赤诚,也表达了自己深受教育的心声:“雪峰同志的话/像碧清的河水/洗涤着我的心头。”在《把生命化入大地——忆孟超》里,诗人对友人孟超深情的回忆。孟超在1960年代初因与人合创历史剧《李慧娘》而遭“杀身之祸”,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诗人联系自己的遭际,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时光可以无情地流逝,但孟超高大的形象却永驻诗人心中。生前的孟超“被时间的风雨冲刷得异常的简洁”,“只剩下弯曲的骨骼和不弯曲的心灵”,“他的生命洗练得不能再作一点删节”。诗人抓住关键词勾勒出孟超至纯至简的形象,使其跃然纸上。读之,唯有思念和敬意在我们心中蔓延开来。
牛汉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和遭际与“他者”生命形态融合,选择自己熟悉并与自己“同病相怜”的生命形态作为创作对象,通过对其悲惨生命的描述,达到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历史的悲剧造成个体生命的悲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些受难的生命形态直刺人心使人无法淡忘。《阳光恋——一个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一个蒙冤的“囚徒”身在囹圄心却向往阳光和自由的故事。这个与诗人有着相似命运的囚徒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连享受一下阳光的权利也失去了,他的遭遇让诗人感慨:“生命像发了霉/面颊上手臂上长出了块块灰斑。”(《阳光恋——一个真实的故事》)诗人也爱莫能助,只好用诗句来表达惺惺相惜之情。“囚徒困境”如何破除还得靠囚徒自己。他不断地寻找阳光的照拂,发现一年之中约摸有二十多天,太阳会“擦”着他的囚室而过,他能够从“两尺见方的天窗”看见久违的阳光。无奈天窗过高,阳光只能照射到高高的墙壁上。他多么希望能得到阳光的温暖,于是开动脑筋仔细观察精心度量,用指甲在水泥墙壁上标记着阳光走动的轨迹。当下次阳光照来时,他马上脱掉衣服,拼命向上跳跃,去亲吻这只有二十多分钟的光芒。更令人心酸的是,这个囚徒被释放回家后,多年仍保持向阳光纵跳的习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囚徒和阳光的故事曾感染无数的人。寻常的阳光在他那里如同救命的稻草,折射出他清醒的生命意识和活下去的决心。显然,牛汉在借“他者”的酒杯,在抒发自己对生命的热爱和陶醉。
路翎同牛汉一样属于“七月诗派”,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生命。《路翎和阳光》描述诗人路翎的不幸遭际。路翎遭迫害精神上深受刺激,行动上发生异常,刻意避开“所有的阴影/连草帽也不戴”,“独自在阳光里行走”(《路翎和阳光》)。他记忆力也变差了,忘记了来路,“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他的女儿怕他走失,只好“眼泪汪汪/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边”。散发着历史痛感的诗句表明了路翎身心受到的摧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歌者》塑造了一个经过“悲壮的颤动”失去歌唱权利的“歌者”生命形态。他是诗人的一个“同龄朋友”,他的遭遇引起诗人心灵的共鸣。歌者虽然失去表演的舞台,但仍寻找人生更大的舞台,最后来到黄河边面对滔滔河水一往情深放歌一曲。“他唱的时候/嘴张成扁圆形/我看见他那仅有的两颗门牙/不住地摇颤//他的胸骨/一起一伏地颤动着/眼角的泪珠颤颤地流淌/太阳穴弯曲的蓝色脉管/跳得像黄河的波浪”(《歌者》)。牛汉着力塑造了这个美丽的“他者”生命形态,从中可以看到“歌者”生命活力的迸射和艺术生命的复苏。“歌者”找到人生大舞台时的喜悦和激动与牛汉重获人格尊严和创作自由时的生命体验何等相似。
牛汉的创作视野不断扩大,还将“镜头”对准一些和他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命运的世界级文学大师、文化名人。不惜笔墨刻画出一个个敢于挑战命运、创造奇迹的强大伟岸的生命形态。《冰山的风度》塑造了一个肉体和灵魂遭受战争的重创,依然用笔作武器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强者”。“谁都担忧你膝盖上那个创伤/可你偏偏用这条腿/站立着写字/一口气写一个短篇/你的头颅是坚固的/(即使有裂缝)/它硕大浑圆永不变形/颅腔里有另一个广阔的世界/幻梦如雄狮野马/奔驰在四度五度高耸的境界”(《冰山的风度》),表现了一代文学大师海明威的生命风姿。《贝多芬的晚年》赞美音乐家贝多芬在垂暮之年忍受失聪的巨大麻烦和痛苦,依然在无声的世界里凭借“灵敏的感觉”而谱写出伟大的乐章的生命壮举。《最后的形象》定格了天才画家梵高的最后的生命形态,“苦痛把梵高鞭笞到爆炸点/他的头发眉头眼瞳/看不见的突然上升的血液/血液里的梦想/还有四周的天地/都飞腾起了蓝色和黄色的火焰/这就是梵高最后的形象/永不熄灭的火焰”(《最后的形象》)。大而言之,《冰山的风度》、《贝多芬的晚年》、《最后的形象》塑造的是世界级文学大师、文化名人的生命形态,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类生命的顽强和人类精神的崇高;小而言之,三个“他者”生命形态也是牛汉生命形态的自我写照,从中可以感受诗人的“别有用心”。
总之,“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10]尼采的这句名言强调和概括了生命和艺术的血肉联系。对诗歌而言,也是如此。从生命的本能出发,探索生命的真相,思考生命的本质,诠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完成“生命的最高使命”。诗歌创作是生命本能冲动和激情的升华,从本真的生命里流淌出来的文字,才含有真诚的内容,才含有生命的“活气”。诗歌是“一种生命的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饰,一定要把生命写进去”。[11]牛汉言必行,行必果,把生命写入诗歌,同时,也带着生命写诗。一路风雨兼程,心底“蓄积着极痛烈而且深刻的许多伤害的。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12]一路奏响生命的进行曲。因此,诗人获得诗歌创作的源泉。牛汉发掘生命的潜能,“寻找生命与精神上的应和”,[13]用心塑造不同种类的生命形态,找到自己诗歌创作的立足点和生长点。
牛汉在诗中为我们塑造了大量的植物、动物、“他者”的艺术形象,显示出三类不同的生命形态。诗人亲近这些生命形态,并称之为“相近的生命的邂逅”,很快发展成为“诗伴”。因为植物生命形态和动物生命形态融入了诗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构成一种“主体间性”,在主体间性中,主体彼此之间通过交流、对话、相识、理解、同情融为一体,所以也就带上了“人”的性格和特征,具有了“人”的属性,成为“人化”的生命形态。同时,三类不同的生命形态又具有客观性、纪实性,在此基础上完成由自然世界向诗歌艺术世界的转化与升华,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和艺术之美。
诚然,牛汉的诗歌创作也似乎存在着塑造生命形态时“心事太重”,表现欲过强,围绕个人的生命经历书写太多,陷入个人语境导致私人气息太浓,表现的主题多有雷同等问题。如何超越一己的生命体验,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天地,显出更大的生命气象和格局,如何增强生命的内蕴和涵养生命,时刻保持生命的博大与鲜活,如何避免过于个人化的书写,突破“小我”的局限,将个人书写转化为人类书写,如何将“小我”融入到“大我”的世界中,个体生命融入到整个人类生命中,使诗歌创作既源于个人生命体验又超越个人生命局限而对整个自然和人类进行人道主义关怀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