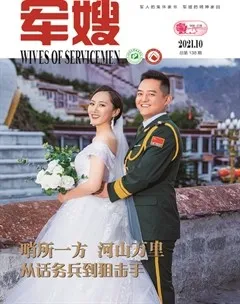母亲吴瀚,一生无憾
吴瀚,1914年3月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33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历史系学习。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4月入党,1941年8月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在苏南妇联、华东妇联工作,后任上海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副主任,上海华东医院副院长、党总支书记,山东省科技情报所所长,中央监察部驻高教部教育部监察组监察员,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等职。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称号等。2021年9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107岁。

2021年9月16日,母亲吴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她一生听党话、跟党走,无怨无悔。
踏上革命征途
母亲1914年3月8日出生,祖籍江苏常州。她自幼便随外公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生活,饱尝矿区生活的艰辛。母亲13岁时,安源煤矿大裁员,外公失业,一家九口不得不回到常州,靠族亲接济生活。
母亲受新学启蒙,从小立志读书报国。1933年,她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时任清华教授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曾在日记里记载“吴瀚申得清寒学生助学金”(见《三松堂日记》)。
在清华园,母亲一边坚持学业,一边服务社会,参与赈灾济贫、助学帮困等。
1935年底,“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爆发,母亲数度与同学走上街头向当局抗议示威;还在街头、在校园内,冒着愈演愈烈的危险,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不分昼夜掩护学生领袖与进校搜捕的军警周旋,直至自己也面临追捕被教授们藏匿于家中……
当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怒潮席卷全国时,12月25日,母亲再次挺身而出加入清华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一路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宣传抗日。
母亲到沧州时就开始发烧,但她始终瞒着大家,强忍病痛坚持跋涉。到达德州,她被送去医院检查,诊断患了白喉,不得不隔离住院。但一周后,她用姑父送来的回校盘缠,继续乘火车南下追赶队伍。最后,全部队员被南京国民政府派军警悉数武装押解回北平。
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局势突变,爱国学生却众志成城,临危不惧。后来,队员们每人从名字中各取一字,集字成联以纪念当时的血性拼搏:“坚琦照新瀚,仁德振威荣;长城如海龙,雨仕让金山。”联中的“瀚”就是母亲,她是千里突骑中唯一的女性。
1936年4月,母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全校师生中的42名党员之一。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她始终秉持“一二·九”运动精神,不畏艰险,矢志不渝。
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7月,母亲从清华大学毕业,前往汉口懿训女中任历史教员。
母亲接上组织关系后,由中共湖北工委派到汉口江汉路支部做地下工作,我的父亲刘季平时任支部书记。
由于母亲胆大心细,湖北工委委派她作为特别交通员,前往大别山七里坪给时任工委宣传部长彭康送信。那里是中国工农红军唯一坚持武装斗争达十年之久的革命老根据地,正在组建新四军实力最为雄厚的四支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敌我斗争的前沿。信送到后,母亲曾向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高敬亭请求参加新四军,但被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解释开展城市斗争的重要性说服,而未能如愿。
当日军疯狂进犯华北华中腹地,战火逐步逼向武汉时,母亲承担起更多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工作。她在硚口工人区开办女工夜校扫盲班,训练妇女救护技能;参加组织全国女青年协会乡村服务队,一干数月;组织安排进步青年前往延安等。1938年7月,母亲受党组织指派,与陈维清创办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并担任团长,带领近百名姐妹深入各医院救死扶伤、忘我奋战,坚持到武汉失守的最后一刻。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母亲随组织转移至桂林,以从教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桂林,母亲与父亲结成并肩战斗的革命伉俪。当我的大姐出生不满百天时,父亲接到秘密撤退到皖南新四军总部的指令,而母亲正遭受不明原因的日夜腹痛的折磨……父亲咬牙别离奔赴苏皖,母亲留下作掩护,每天桌子上放着一包烟、泡上一杯茶,来人便佯称:“老刘刚刚出去……”
母亲的腹痛日益严重。她的大妹靠卖血在贵阳的湘雅医学院求学,母亲去贵阳找大妹求助,被确诊为卵巢囊肿。她腹部肿瘤切除手术伤口刚愈,又接党的指令动身前往苏中新四军根据地。
母亲只身怀抱不满周岁的大姐,经柳州往南翻越十万大山前行。她们身上没有钱,饥渴交加。正举目无望时,巧遇汪达之先生带领新安旅行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革命团体)路过,母亲得以随团同行。
一路出广西到湛江,从湛江到香港,经海路到上海,过江到苏北,历时4个多月,闯过国统区、沦陷区,总行程约3800公里。1941年8月,母亲终于到达新四军一师和苏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苏如东栟茶镇,成为新四军的一员,从事机要工作。
不改革命本色
母亲被誉为苏中根据地“三位女杰”(另两位是钟英、张云)之一。在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和残酷激烈的武装斗争中,她不仅像其他战士一样时刻要突围、转移、埋伏,遭受战火考验,而且因为带着孩子,境地更加危险。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华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母亲所在的黄河大队(1946年6月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战略转移的新四军番号)北撤转移。黄河大队包括大队部、参议会、银行、财粮、医院、干校、新安旅行团、印刷、报社、剧团、家属等20多个中队,共2000多人。其中,还有60位孕妇组成产妇队。我的父亲任黄河大队政治委员,负责大队北撤行动。队伍从江苏淮安经鲁中地区,过黄河,进驻冀南地区故城县郑家口大杏基村。
1947年2月1日,新四军与华中野战军、八路军一部、山东野战军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应对蒋介石的进攻。蒋误认“黄河大队”是“陈毅所部溃败,向西渡河逃窜”,下令在黄河渡口加以全歼。所以,黄河大队起到了在战线西侧钳制敌人的作用。情况紧急,军队命令,轻装前进,每人负重不得超过10公斤。
行军中,母亲要背负机要文件、军事地图等,还要携带枪械,而减负的最大问题是身边的孩子。当时,母亲不仅即将临盆,而且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7岁的大姐、4岁的我和2岁的大弟。
由于军情紧迫,在途经山东沂水马家崖村时,母亲果断将我和大弟送给老乡。因革命妈妈朱姚竭力反对,我们又被父亲接回。别子之痛,生离死别,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母亲在危难之时的抉择,践行了她的入党誓言。
1947年2月20日,母亲在行军途中生下二弟的当晚,华东野战军发起的莱芜战役打响。这场大规模战役经过精密部署,连非战斗部门也被派上战场发挥诱敌作用。母亲随队伍在战火缝隙中穿行20天。战友黄希珍生下双胞胎女儿雷豪、雷杰,因身体极度虚弱,没有奶水。母亲二话不说,就把体重不足2公斤的小雷杰带到身边一起喂养。黄阿姨曾在《忆双胞胎女儿的幸存》中写道:“一个妈妈哺育两个孩子,我的精神、心理、体力的重负全压在了吴瀚同志身上,多么可亲的战友呀!”
战争的残酷没有令母亲退缩,反而意志更加坚定,她在充满战火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并最终从战争中走了过来。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从事过政权初建中各种应急事务,以及妇联、民政、科技情报、人民信访、纪检监察等基层工作。她始终信守教育情怀,与父亲一起参与传承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文革”后,组建陶行知研究学术团体和领导机构,使研究会在各地落地开花,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大、中、小学陶行知教育育人基地。
严于律己,是母亲坚守的人格品质。她要求全家不沾父辈的光,不取浮华虚名,个个下得基层,知恩图报。母亲年逾百岁高龄后,每周在“家庭视频会议”上与家人相聚,用目光凝视我们这些在各地扎根锻炼过的子女,她神闲气定,对儿孙的寄望尽在不言中。
母亲离休后,受到组织关怀。这两年,她在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又得到了年轻战友的关爱,安详地度过虚岁108岁生日(“茶寿”)。母亲有幸光荣在党85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中国!
母亲,安息吧!您的一生是真真正正的无憾!您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初心,一定会由后代传承!
(作者为原中国国防工业工会巡视员、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退休干部)
编辑/贡伟(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