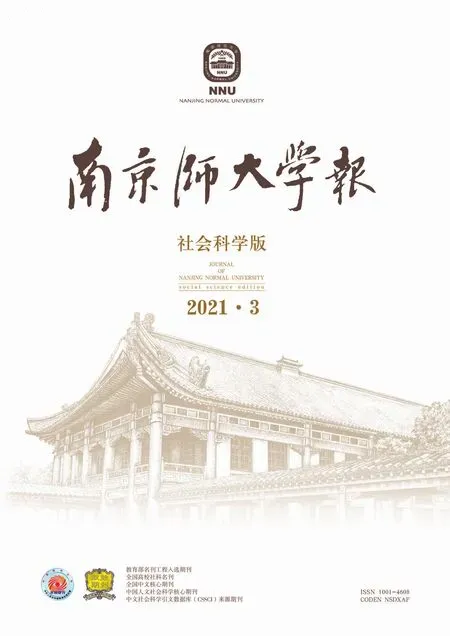媒介变迁视野中的网络民族主义:兴起、演进及反思
邹 军
网络民族主义常常被视为“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民族主义思潮”。(1)邹军:《看得见的“声音”——解码网络舆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第30页。在中国,伴随网络社会的崛起和“网络化生存”成为常态,网络民族主义作为网络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早已溢出网络,成为公众话语,进而对社会产生持久影响。与此对应,有关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议题涉及网络民族主义的生成与扩散(2)王军:《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倾向与特征(3)赵金、闵大洪:《网络舆论,民意表达的平台》,《青年记者》2004年第10期。、功能与引导(4)卜建华:《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以及对内对外影响(5)王军:《网络民族主义、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等等。以2016年1月“帝吧出征”为标志,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吸引公众目光,也引发了从媒介和传播角度对其动员机制、传播形式和话语符号等问题的探讨,特别是传播技术的影响问题。(6)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但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民族主义作为依托于网络媒介滋生和传播的思潮,它与网络应用的发展一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流变。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的变迁同媒介演进关系密切,但现有研究对此尚未加以充分讨论。本文将通过整理与爬梳既有文献和经验材料,力图呈现网络民族主义在互联网应用演进与社会思潮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特征,并从媒介化的视角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对现有研究予以反思。
一、 “网络民族主义”:概念的提出和现象的出现
“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往往被用来指称民族主义思潮在互联网时代所呈现出的新发展与新形态。从词源上看,“网络民族主义”产生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尽管“民族”二字古已有之,但并没有产生“民族主义”这样的词汇。此外,许多学者认为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而非“自觉”的民族实体,而古文中所谓的“民族”往往只是泛指人民的模糊性概念,也不是用来表示族群之间边界的词汇,因而古代中国没有所谓的“民族主义”。(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近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正式形成,往往被认为同18、19世纪欧美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关。当然,亦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可追溯到西欧社会更早的历史时期。(8)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代序言》,[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尽管“民族主义”是西方“nationalism”的舶来词汇,但“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却似乎是一个本土的产物。一般认为,中文语境里“网络民族主义”的表述最早见于2003年。(9)罗迪、毛玉西:《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是时,北大在读博士李颖关注到八万多人次参与到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技术的网络签名活动,遂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一篇名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新闻评论,率先提出“网络民族主义”的说法,并批评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种局限性的民族主义,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可以宣泄口号而无责任约束,可以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可以言行不一”。(10)李颖:《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2003年7月31日,http://news.sina.com.cn/c/2003-07-31/18101452251.shtml,2021年2月5日访问。
尽管“网络民族主义”的提法直至2003年才出现,但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在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不久就现端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高校学生群体为先锋的“第一代网民”开始活跃于早期的网络论坛和校园BBS(如“水木清华”“小百合”)等交流平台,表达民族主义情绪与爱国主义情感。如在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骚乱后,中国网民在一些中文站点、讨论组中抗议排华暴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表达华人社会的愤怒与民族主义情感。(11)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1999年,因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引发网民集体抗议,直接催生了人民网“强国论坛”前身——“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以此为标志,中国民众不仅开始拥有了进行网络民意表达的正式渠道,也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抗议活动固定成为中文互联网空间的独特“剧目”,不时上演。
对应中文语境中“网络民族主义”一词,通过以“Cyber Nationalism”“Internet nationalism”“Online Nationalism”等为关键词在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SAGE及其他非学术资料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在西方社会和学术界早期的文献资料记载里,并没有“网络民族主义”的说法。尽管当时互联网空间中库尔德人、马其顿人、亚美尼亚人、苏格兰人、加泰罗尼亚人等等都开设了民族主义内容的网站,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网络政治(12)R.K.Whillock,“Cyber-politics:The Online Strategies of ’96”,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0,No.8,1997,pp.1208-1225.(Cyber Politics)、网络文化(13)L.Back,“Aryans reading Adorno:Cyber-cultur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racism”,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5,No.4,2002,pp.628-651.(Cyber Culture)对西方既有民族国家格局潜在的影响和冲击,但绝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将关注点放在网络对民族主义的变革性意义上,而仅仅将网络视为传统民族主义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英文文献中,“网络民族主义”(Cyber Nationalism)的概念最先见于由华人学者Xu Wu在2005年所提交的博士论文(14)X.Wu,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How China’s Online Public Sphere Affecte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Florida,2005.,而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的也是中国自接入互联网以来所产生的大规模网络民族主义传播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空间上最先形成规模的现象,并通过互联网的跨境传播,为国际社会所关注。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演进与现实政治的改变,网络民族主义本身也不断发生变化。从媒介演进与传播变革的角度看,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在互联网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由精英到公众、从公共到社群的变化。
二、 从精英取向到公众话语:互联网大众化与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
自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到2003年“网络民族主义”被正式提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基本对应着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第一个十年”(1994—2003)。它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以高校在读学生(甚至包括一些青年教师)为主体的“精英主义”民族情绪表达,逐渐转变为存在于互联网虚拟空间,却能影响到社会现实的一种公共舆论。
(一) 精英化: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早期特征
相比于传统的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互联网这一媒介渠道和传播方式。早期互联网的应用服务普遍具有原始的粗糙性和明显的工具性,第一代互联网的用户们大多只能通过互联网来查看网页、下载资料及收发电子邮件。而BBS的兴起真正使人们在虚拟空间上有了自由交流的可能,参与网络表达的人数大幅增加。曾有学者一度认为,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会使“理想的言语环境”——“网络公共领域”成为现实。(15)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第279页。
当技术条件成为现实后,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还需要有行动者的参与和互动。虽然早在1994年中国就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可当时只有不到2000人能够上网,其中大多数是国家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者。(16)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1994—1996年)》,2003年10月22日,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3/10/22/1003.htm,2020年12月20日访问。互联网真正向社会开放则等到了1995年,虽然开放商用后用户有了大规模增长,如到1997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达62万,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社会群体了。但这一数字相对于中国人口总量来说依然很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能上网代表着他们属于某种程度的社会精英。而且,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在1990年代末的几次统计均显示,当时的互联网用户85%以上是男性。
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初衷之一是用于科学研究和发展教育事业。受“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项目的影响,早期深具影响力的网络论坛主要是校园BBS,用户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水木清华BBS”就曾是中国内地最具人气的BBS之一。尽管CERNET早期对校园BBS上的讨论帖有“仅限学术交流”的规定,但当时高校里的在读学生仍然经常性地讨论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与现实社会问题。(17)X.Wu,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How China’s Online Public Sphere Affecte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p.184.1996年,台湾政局变动、中美关系紧张,加上发生了日本右翼组织在钓鱼岛挑衅等一系列事件,这些活跃于校园BBS的青年学生发表了许多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网络言论,并试图通过发布帖子来进行抗议动员。但受限于使用群体的数量,加上官方的有力干预,这些早期的网络民族主义动员并没有对线下的现实社会造成大的冲击。
同样在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成为中国图书市场的畅销产品。有学者认为,这本书的畅销标志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精英民族主义在日渐商业化的环境中走向“大众化”,草根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特征。(18)S.Zhao,“Chinese intellectuals’ quest for national greatness and nationalistic writing in the 1990s”,The China Quarterly,No.152,1997,pp.725-745.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镜像,受现实社会思潮的影响及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网络民族主义也逐渐开始从“精英主义”取向转变,变得越来越具有“草根色彩”。
(二) 民间表达:进入公众话语的网络民族主义
无论从表达主体的“草根性”,还是从议题的民意特质,以及呈现出的民粹主义、非理性等特征,中国的网络舆论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民间表达”。(19)邹军:《看得见的“声音”——解码网络舆论》,第18页。网络民族主义正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成为网络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1998年,中国网络媒体整体起步,在传统媒体(如《人民日报》网络版的上线)与商业网站(如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开始提供新闻信息)的合力下,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显现。1998年,印尼爆发排华骚乱,虽然国内传统媒体并未对该事件做过多报道,但《人民日报》网络版推出的“印尼五月暴乱”专辑、一些中文BBS站点上暴行目击者的亲述和贴图以及海外媒体电子版的专题报道,传播了事件真相,并为人们提供了表达愤怒的渠道。一个华人社群的“跨国性公共论坛”似乎在该事件中得以形成,并且共同地表达他们关于“中华民族”的想象。(20)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第287页。网络民族主义在这一事件后,开始逐渐具有了舆论的“公共性”特征。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人民日报开通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一个月后,论坛改名为“强国论坛”,转型成一个由传统媒体创办的电子时政论坛。虽然早期改版以后的强国论坛拥有读书论坛、英文论坛、生活聊天区板块,但在“强国论坛”开通的一年内,论坛内的讨论焦点仍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海局势等方面的话题。(21)洪兵:《〈强国论坛〉:新的平台及其前景》,《新闻大学》2000年第3期。直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强国论坛上的内容还是主要围绕这些话题展开。自“强国论坛”起,网络上广泛存在着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正式借由网络舆论的形式来进行表达。而“强国论坛”平台的出现也被看作是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在中文互联网上固定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节点。(22)束凌燕:《从“情绪发泄”到“理性出击”——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图景呈现》,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新闻学专业,2010年,第16页。
2003年被媒体称为“中国网络舆论年”。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以博客为主要形态的Web2.0服务兴起,网络舆论在SARS疫情爆发、孙志刚案、刘涌案等事件中都彰显出强大的现实影响力。虽然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但因为用户基数的扩大与社会环境的复杂,互联网空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言语环境”。闵大洪曾提出,当时的网络舆论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倾向:对内表现为批判现实主义,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23)赵金、闵大洪:《网络舆论,民意表达的平台》。而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这一阶段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愤怒”,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行动者也常常被称为“愤青”。网络民族主义的关注焦点也从中美冲突扩展到中日矛盾等其他对外关系,如在日本人珠海买春案、西北大学反日本留学生事件、“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线上签名活动等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中,网络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激化——网民在“爱国者同盟网”“9·18爱国网”“龙腾中华网”等站点和SNS平台上以新闻跟帖、论坛上帖的方式,通过愤怒化的网络语言表达,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并发起多次线下抗议动员。
也正是在2003年,李颖在《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正式提出了“网络民族主义”的概念,并对其过于偏激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以此为标志,国内网络民族主义的早期发展经历了从主要由精英群体的言论表达与集体行动,发展为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社会舆论的演进历程。
三、 走向社群: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民族主义的重构
进入2003年后,以“用户创造内容”为主要特征的Web2.0应用兴起。时值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因中国同个别邻国关系出现波折而呈现出激化趋势,国内学术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对网络民族主义问题给予大量关注。有学者曾提出,网络民族主义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是因为Web2.0时代贴吧、博客及即时通信应用或群组等传播方式,为民众自下而上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而这些新的传播方式也塑造了国家与公民意识自下而上生成的新路径。(24)吴学兵:《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念、话语和行动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市民社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崛起,更反映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在互联网传播技术推动下的民主化发展。(25)郑智斌:《事件、观念、共变:中国互联网事件二十年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7年第1期。从政治社会属性和作用的角度来看,尽管官方存在着类似强国论坛这样重要的传播渠道与平台,但对互联网的认知、运用和引导不及民间,民众力量是互联网事件传播与舆论生产的主要贡献者。(26)郑智斌:《事件、观念、共变:中国互联网事件二十年研究》。在2005年反对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网络抗议和2008年反击西方部分媒体对西藏骚乱歪曲报道的网络运动中,以民间为主的集体动员在网络民族主义表达中表现出了强大力量。
(一) “文化政治”兴起:网络民族主义生成逻辑的重构
Web2.0开启了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时代,推动了话语权对普通网民的下放,但博客本身的精英取向限制了个体网民的传播影响。2008年后,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应用崛起,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移动传播融入日常生活,社会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网络社会”开始和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强关系”与“弱关系”联结的方式创造了社会群体的共同在场,构成了一种“真实与虚拟间杂的网络世俗生活”。(27)郑智斌:《事件、观念、共变:中国互联网事件二十年研究》。网络舆论在社交媒体的圈层化传播中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国内网络民族主义也从“一致对外”,发展为身份认同差异所带来的“文化政治”论争。原本同民族主义并不相关的思维和逻辑开始加入到了网络民族主义的观念中来。(28)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69圣战”的大规模集体网络行动即反映了国内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转变。2010年韩国演艺团体Super Junior到上海演出,由于主办方的原因,大量聚集的歌迷粉丝迟迟无法入场,引发不满。以“魔兽世界”贴吧、天涯、猫扑等有“反哈韩”倾向的小众圈层社区为发源地,一些网民不仅在国内对Super Junior的中文贴吧与粉丝社群进行网络攻击,还联合“中国红客联盟”等黑客组织对韩国SJ论坛及部分韩国明星的网页发动攻击。凤凰网对此发起了一项网络调查,显示约有92.2%的网民视这一行动为“爱国行为”。这是国内网络民族主义同商业消费环境下的粉丝文化逻辑相挂钩的重要标志。
与上述案例相似的是2008年和2011年《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上映在中文互联网空间中引发的“文化民族主义”争论。(29)肖珺、郑汝可:《网络民族主义:现实与想象的冲突——中国网民关于抵制〈功夫熊猫〉的争论启示》,《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6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229页。当时的网民普遍认为《功夫熊猫》虽然运用了大量中国元素,但它本身是出自好莱坞的美国文化产品,本质上还是一种美国文化观念输出,因而在相关讨论中频繁出现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这些现象的出现清晰地告诉人们,在互联网传播方式的演进与现实社会的代际更替过程中,网络民族主义的抗争从公共性、严肃性的国际政治冲突,转向全球化背景下商业文化消费中的身份认同冲突。换言之,网络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文化政治”现象。(30)张爱凤:《网络舆情中的文化政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
(二) 从新媒体事件到日常化传播:网络民族主义传播形态的重塑
2016年初发生的“帝吧出征”事件可被看作是90后乃至00后“迷妹”“小粉红”群体主导下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第三波浪潮。(31)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2016年年初,以“周子瑜事件”为导火索,在大陆网民中有着“帝吧”之称的“李毅贴吧”网民发起组织和动员,号召网友“出征”Facebook,主要以“表情包大战”的形式表达爱国主义情绪和实现两岸统一的诉求。
但与此前网络民族主义抗争的新媒体事件不同,“帝吧出征”的集体行动有了高度的组织性与规模性。在“帝吧远征军”的内部,组织方明确提出了两条行动规范:反“台独”而不反“台湾”;行动的基本原则与目的是文化交流。此外,组织“帝吧出征”的行动者们还进行了细化的分工安排,如以“鬼畜视频”抗议台独分子恶劣行径,用表情包“灌水”台独博主的Facebook主页,发表两岸友好沟通交流贴等等。(32)李兰:《网络民族主义行动的新面相:“帝吧出征”事件的逻辑、组织与行动方式》,《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9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4-205页。对此,刘海龙曾提出,如果说早期以“60后”“70后”民族主义行动者为主体的网络民族主义抗争还只是将网络传播的方式整合进传统的民族主义抗争中去,那么“帝吧出征”事件以来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则完全是一种原生于互联网媒介环境下的文化政治。对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80后”“90后”来说,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集体、公共及严肃的政治性事件,而成为了同追星、游戏等娱乐活动相似的身份认同表达。(33)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首次“帝吧远征”事件发生后,“帝吧”网友在Facebook上创立了“帝吧根据地”“帝吧中央集团军”等群组,在后来的维珍航空事件、日本APA酒店事件中形成了一股网络力量,时刻关注与捕捉世界上发生的各种“辱华”事件。2019年8月,“帝吧”正式在新浪微博网站开设微博帐号,并形成“帝吧官微”“帝吧爆破组”“帝吧出征参谋部”等微博传播矩阵,动员“90后”和“00后”的所谓“迷妹”正式集结起“饭圈女孩”参与到“守护阿中哥哥”的网络动员中。在新冠疫情期间,“饭圈女孩”还积极参与到抗击疫情的志愿捐助与谣言澄清上,对与中国官方抗疫政策相左的言论与行为进行反击。
总体上看,社交媒体已然重构了民族主义的逻辑。在今日圈层化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下,新一代的民族主义行动者通过使用新的象征符号,在日常化、碎片化、即时性的传播活动中,固定化地动员组织新一代民族主义的网络传播实践。在消费文化影响下,今天的网络民族主义甚至呈现出某些更具女性主义气质的趋势。
四、 媒介化与网络民族主义再审视
雷蒙·威廉斯指出,小小的词语变化实际上蕴含着重要的社会变迁讯息。(34)杨国斌:《转向数字文化研究》,《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基于上述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历时性梳理可以发现,相比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多了“网络”二字的“网络民族主义”实际上反映着“民族主义”的思潮本身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
从媒介与传播的视角来看,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观念的产生,本身就离不开媒介技术与传播变革的影响。西方研究者普遍认同,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产生往往被认为与工业社会机械化的“媒介化”进程紧密相关。麦克卢汉较早对媒介技术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提出,“前现代”群体主要是以口语传播为特征的血亲家族式部落,而印刷术的出现则改变了以往的文化边界和模式,口语和语言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作为现代性的社会群体形式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因此得以催生,印刷术可以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3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5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安东尼·吉登斯等也曾指出,现代民族(nation)的意识形态是以印刷资本主义对社会语言的标准化改造,以及对时间观念的“空洞同质化”改造为条件的。(3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9页。
民族主义的成熟与发展同样一直伴随着媒介化的影响。20世纪以来,随着报纸的普遍大众化,电报、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技术逐渐成熟,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传播。安东尼·史密斯曾分析指出,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从欧洲内部扩散到东北欧、再扩散到亚非拉地区的传播过程,有赖于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大范围、远距离跨地域的传播能力与文化建构力。(37)[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2-93页。值得一提的是,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大众媒介带给民族主义一个特殊的结构性改变就是让“媒介事件”成为可能。霍布斯鲍姆就曾以始于1932年的英国皇家圣诞广播为例,对这一点予以说明。在他看来,这样的大众传播可以有效地将私领域的人民同公领域的民族关联在一起,把民族象征融入日常生活之中。(38)[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171页。比尔格(Michael Billg)也曾以好莱坞电影及美式摔跤比赛电视节目等为例,说明各式各样携带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是如何通过传媒的方式,在美国范围内建构起“平庸的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39)M.Billig,Banal Nationalism,London:Sage,1995,p.6.
而“网络民族主义”的现象,在此视角下就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时代传统民族主义的延续,是数字媒介浪潮下民族主义自身转型的产物。随着今日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在世存有”(40)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现实社会已经无法完全分割,基于网络的民族主义表达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形态。
理解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包含着中国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同“他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更包含着“他者”如何就“我者”的这种理解是怎样认识和互动的。(41)李红梅:《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帝吧出征事件分析》,《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网络民族主义尽管是最先大规模出现于中文互联网的独特现象,但也广泛存在于国际互联网中。从国外研究情况看,在互联网普及和推广的初期,互联网中确实出现了“赛博国家”(Cyber-Nations),如韦奇伍德(Ruth Wedgwood)就较早关注过这一现象。由于真实社会中种族群体间的复杂关系、政府治理边界及殖民地(或争议领土)归属问题等因素的不稳定,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并不总是能够促成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而导致了在千禧年前后诸如“洛马共和国”(Republic of Lomar)等所谓“赛博国家”的出现,并在互联网传播中通过话语表达来争夺政治权利或谋求国际认同,创造出基于互联网的新的“民族国家”(42)R.Wedgwood,“Cyber-Nations”,Kentucky Law Journal,Vol.88,No.4,2000,pp.957-965.,马其顿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巴勒斯坦人都曾试过以使用(或申请)互联网域名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虚拟国家”。(43)P.Bakker,“New nationalism:The internet crusade”,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jsessionid=214F9565F2B8E70145F38C843A74E496?doi=10.1.1.101.3066&rep=rep1&type=pdf,2021-02-26.
到了web 2.0时期,线上少数族裔群体的民主化动员兴起,转型国家移民群体的民族认同问题凸显。桑德斯(Robert A.Saunders)等就中俄海外移民的网络社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非对所有移民群体的民族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华人社群的互联网话语推动了其民族认同的强化,而后苏联时代的散居俄罗斯人则在互联网表达中体现了一种“去民族主义”的势头。(44)R.A.Saunders & S.Ding,“Digital dragons and cybernetic bears:Compar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near abroad Russian web communities”,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12,No.2,2006,pp.255-290.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身份认同抗争为特征的网络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伴随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移动传播同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以Twitter、Line、Instagram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构筑了一种多重场景并置、多重角色共在、多重关系同时展开的“中介化场域”。在“节点-网络”的传播模式中,碎片而多元的个体认同被更加突出强调,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理论中强调“政治和民族的单位保持一致”的民族主义原则开始被打破。网络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人们展开身份认同抗争的一种传播手段。如在土耳其(45)L.Szulc,“Banal nationalism and queers online:Enforcing and resisting cultural meanings of .tr”,New Media & Society,Vol.17,No.9,2015,pp.1530-1546.、加泰罗尼亚(46)M.Iveson,“Gendered dimensions of Catalan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Twitter”,Discourse & Communication,Vol.11,No.1.2017,pp.51-68.和一些前苏联地区(47)D.T.Kudaibergenova,“The body global and the body traditional:A digital ethnography of Instagram and nationalism in Kazakhstan and Russia”,Central Asian Survey,Vol.38,No.3,2019,pp.363-380.的性少数群体因被其国家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采取线上表达的方式申请“酷儿”(queer,性少数群体的一种类型)顶级域名,以此传播实践来“驯化”国家对他们的接受程度。此时,网络民族主义已不再是只有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才出现的现象。如英国学者罗伯特·托平卡(Robert J.Topinka)发现,在社交新闻站点Reddit的子版块“#ImGoingToHellForThis”中,某些网友故意以“黑暗、冒犯及扭曲式幽默”的方式调侃强调“政治正确”的网络社群(48)R.J.Topinka,“Politically incorrect participatory media:Racist nationalism on r/ImGoingToHellForThis”,New Media & Society,Vol.20,No.5,2018,pp.2050-2069.,反映了欧美主流社会以“白左”为特征的狭隘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而这在特朗普执政时的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杜赞奇所言,民族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概念,它是一种呈现竞争性的场域,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话语权。(49)P.Duara,“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0,1993,pp.1-26.整体上来看,在媒介与传播变迁的视野下,网络民族主义不再像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理论描绘的那样,始终强调“政治与民族的单位保持一致”的原则(50)[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它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由民族的成员所共享的“同种文化”(51)[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第9页。。在互联网世界中,“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在世界上存在,证明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一条边界及纽带。(52)胡翼青:《对于学术,概念意味着什么》,2020年11月16日,https://mp.weixin.qq.com/s/jORQwho4oJRLDv5fLeRxWQ,2020年12月1日访问。阐释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力不再集中在政府、官方机构及主流的社会群体手中。即便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也开始拥有了他们自己对于民族主义的解读框架和表达权力。在社交媒体为主导的网络传播逻辑影响下,今日的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更多呈现出个体化、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
五、 结语
互联网产生以来的社会实践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独特的事件史、观念史。以网络民族主义为例,它反映了从精英到民众丰富的知识、多元的思想与信仰,更反映了互联网传播变革下民族主义观念的转型与变迁。(53)郑智斌:《事件、观念、共变:中国互联网事件二十年研究》。从媒介与传播的角度看,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是一个随着网络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一种社会文化政治形态。以互联网的早期普及、Web2.0应用的兴起以及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为线索,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走过了一个从“精英”到“草根”,从“公共”到“多元”,以至“社群化”“泛娱乐化”的发展历程。而西方的网络民族主义演变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总的来看,社会化传播的条件及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让人们的民族主义观念变得模糊,群体基于“政治一致性”原则的国族认同更多地被多元化的个体身份认同所超越。不同价值观取向的网络行动者们往往“因事聚集”(54)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通过他们的具身性传播实践,一方面与认同相近者结成“无组织的组织”,另一方面则在互联网提供的跨国空间中应激式地找寻和树立认同不一致的“他者”,并能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和传播动员。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在当下呈现出一种“政治多元性”的特征。随着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和进一步网络化,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路口,重思网络民族主义的变迁和未来,就有了更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