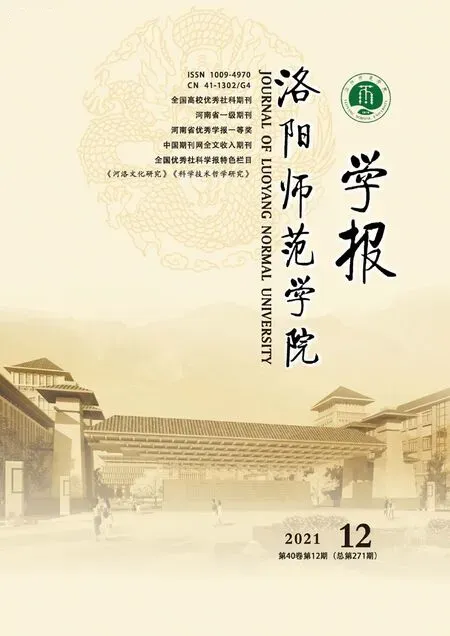论罗伯特·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反独白”叙事
张凤梅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有不少学者曾指出,勃朗宁的名作《我的前公爵夫人》描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少女露柯蕾西亚14岁嫁给阿尔方索公爵,17岁即被秘密处死。诗作通篇都是以公爵一个人的口吻进行独白,露柯蕾西亚只以画像身份在场,未发一言。本文试图借助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来揭示《我的前公爵夫人》这一戏剧性独白的代表作所独具的“双重声音话语”结构。
一、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双重声音”
戏剧性独白是英语文学中的一枝奇葩,它萌芽于英国中世纪末期,在维多利亚时期开出灿烂花朵,到20世纪已深入人心,并对后世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维多利亚时期戏剧性独白的杰出代表当数罗伯特·勃朗宁,他将自己的多部诗集冠以“戏剧性”称号:如《戏剧性抒情诗》(DramaticLyrics)、《戏剧性浪漫传奇》(DramaticRomances)、《戏剧性田园诗》(DramaticIdylls)、《戏剧性研究》(DramaticStudies)以及《戏剧性代言人》(DramatisPersonae)等。此外,他还有一部诗集直接命名为《独白戏剧》(Monodrama),因为他认为这些诗本质上更接近于戏剧。
勃朗宁所谓的“戏剧性”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他的戏剧性独白具有真正的情境。像一出真正的戏剧一样,他笔下流动的这些诗句不是空泛的情感宣泄,而是一段连续的戏剧情节,时间、地点、人物都有明确的提示。《夜晚幽会》是一首戏剧性抒情诗,描写的是夜晚两个相恋的年轻人秘密约会的欣喜之情。全诗没有出现一个“爱”字,而是由恋爱中的男子叙述了与心上人见面的经过。他乘船渡海,上岸后又越过原野,终于来到爱人居住的农舍旁,轻敲一下窗子,屋内“嗤”地划亮一根火柴,随即传来“啊”的一声轻叫,两颗砰砰直跳的心便碰到了一起。这一段叙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段戏剧情节,读者随男子的行踪仿佛能看到波涛、海岸、小船、村舍和屋内跳动的火焰,能听到屋内人又惊又喜的叫声,以及见面后两个年轻人的心跳声,这样的情节设置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勃朗宁写有一首《在英国的意大利人》的政治独白诗,讲述一个意大利士兵在抗击奥军时遭到敌人追捕,逃往英国,后被一位农妇搭救的故事。革命处于低潮,主人公被迫远走他乡,虽然他儿时的伙伴及农妇的丈夫等许多人都背叛了革命,但是素不相识的农妇的搭救使他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念。这首诗以抗奥战士的视角进行独白,跌宕起伏,也充满戏剧性。其二,他的戏剧情节的设置促成了叙述者与作者的分离。从上述两首诗可以看出,那名恋爱中的男子与抗奥战士并非作者本人,因为作者并不具有这样的经历。下文要分析的《我的前公爵夫人》中的公爵更是与作者本人有着天壤之别。勃朗宁在他的第一部戏剧性独白诗集《戏剧性抒情诗》的宣传语中写道:“这些诗虽然在表达上是抒情的,但在本质上却是戏剧性的,因为如此多虚构人物的话并不是我说的。”[1]70可见将主人公与作者分离是这类诗歌的重要特征。但是很明显,上述两首诗中的主人公都带有作者的影子,作者分别借两位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歌颂和对意大利人民抗击奥地利帝国的支持。《我的前公爵夫人》一诗却不同,作者不仅没有与主人公一致的声音指向,甚至还与主人公唱反调。那么在主人公一人霸权话语的背后,作者的意图是如何表达的呢?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故事中的主人公虽然是戏剧人物,他因与作者相分离而获得更大的言论与行为自由(他的行为构成戏剧情节,他的话语构成整个诗篇),但是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天马行空,只能限于作家艺术构思的范围之内。主人公就好比飞向天空的风筝,虽获得了自由,但终究挣脱不了作者手中的那根线。不难发现,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其实具有巴赫金在复调理论中提出的“双重声音话语”结构[2]30,即在同一个语境范围内,有两个说话的中心,两套话语体系,一个是作者话语,一个是人物话语。读者在诗中其实能听到两种声音,一个是以第一人称说话的声音,另一个是作者以各种方式间接表达的隐含评判的声音。批评家通常认为,优秀的戏剧性独白的精彩之处不在于主人公要传达的信息,而在于他无意间性格的暴露和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或者他灵魂深处隐秘的揭示。那么,巧妙并悄然完成这一使命的正是双声语结构中退居台后的作者的声音。
复调手法具有不同的声音指向,主人公的声音若是与作者的声音指向一致,那么整个诗歌的走向便是单一的,作品的主题也一目了然,如《夜晚幽会》和《在英国的意大利人》都属于这一类。巴赫金称这种手法为“仿格体”[3]260-261,即主人公的讲话,只需保持本来面目,作者不必把自己的态度向人物语言内部渗透。但是如果作者的声音与主人公的声音有着不同的指向,戏剧性独白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主人公受自己的身份地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影响使得自己的声音有着既定的轨迹。另一方面,作者出于写作目的要扭转这一方向,那么他就要“赋予这个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人相抵牾,发生了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语言成了两种声音争斗的舞台”[3]266。在《我的前公爵夫人》中,虽然自始至终读者听到的是公爵一个人的声音,但作者的声音却贯穿其中,暗中不断地对其实施破坏与颠覆。换句话说,作者的声音扮演的是一个“反独白”的角色,正是这一隐匿的声音破坏与颠覆了公爵堂皇的话语而使虚假的东西被揭穿,真相得以昭示。一直被公爵的霸权话语所蒙蔽的读者只有体会到这一层才会恍然大悟。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作者是如何使用这一技巧来揭示前公爵夫人被暗杀的真相的。
二、《我的前公爵夫人》中的反独白叙事
从某种程度来说,勃朗宁是个写实的诗人,他总是从历史的烟尘中挑选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或小事件做题材,他的作品中或明或暗都有关于背景的暗示。通过“法拉拉”这一地点及公爵身份的暗示,学者们很快发现,独白者正是意大利法拉拉领地公爵——阿尔方索二世。他的前妻露柯蕾西亚1561年去世时年仅17岁,1564年公爵又与一伯爵的侄女(文中为伯爵的女儿)开始谈婚论嫁。故事就从公爵在自家府上与伯爵的使者商讨嫁妆的多少开始,正事似乎已谈完,公爵顺手拉开画框上的布帘,想让来使一睹他收藏的艺术品。
“墙上这幅画是我的前公爵夫人/看起来就像她活着一样。”[4]139独白以这样平淡的口气开始,读者得到的信息是:公爵夫人已死,墙上是她的遗像。很自然就会在心里泛起疑问:她年纪轻轻因何而死?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所有对她生平的猜测也就集中到了这幅画像上。公爵接下来大赞这幅画为奇迹,因为画师潘道夫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这幅杰作。这不免又会使读者生疑:面对亡妻的遗像,公爵不但没有流露出半点留恋与怀念之情,反倒对画师赞赏有加,好像画上的人不是与他同床共枕的妻子,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这是何故?这些看似自然产生的疑问其实都是作者的暗示,当然答案也潜伏在下文中。
公爵与使者的谈话继而集中到了画面最抢眼也最触动观众心灵之处——夫人脸上的笑容。画面上呈现的不是一个冷若冰霜、面带威严的贵妇人,而是一个洋溢着青春与热情的少女形象。她眼里透着一股真挚、深邃的热情,腮边因欢笑布满红晕,这种快乐深深打动着每个观赏者,画师也正是抓住了夫人爱笑这一特征并将其传神地描绘出来,才使得这一画作成为精品。细心的读者能够体会到画像上夫人灿烂的笑容与她已香消玉殒的事实是多么凄凉的对照。那么,公爵夫人是因何缘由露出灿烂的笑容的呢?原来是因为在绘画过程中画师说了一两句俏皮话。他说夫人的披风盖住手腕太多,夫人不好意思地两颊变红了;画师又说这红晕向颈部散去,任何颜料都画不出来,夫人因此笑得更加灿烂了。这件在一般人看来平淡无奇的小事却激起公爵心中的怒火,画师是何等卑微的人物,公爵夫人却毫无顾忌与他谈笑风生,这有失身份。也有论者认为公爵心胸狭窄,怀疑夫人与画师有私情,因而妒火中烧。总之在公爵眼中,夫人太缺乏贵妇人的气质与威严。说到这里,他不禁又回忆起一些往事:
她胸口上佩戴的我的赠品,或落日的余光,
过分殷勤的傻子在园中攀折
给她的一枝樱桃,或她骑着
绕行花圃的白骡——所有这一切
都会使她赞羡不绝,
或至少泛起红晕。[4]140
这一段白描复活了夫人生前的一些生活片段:她喜欢在胸口佩戴些饰物,喜欢观赏落日的余晖,喜欢和仆人嬉戏,喜欢他们在花园里折给她的一枝樱桃,喜欢骑一匹白骡在花圃边散步。无论身份尊卑她都一视同仁,对别人的善意心怀感激。但她的善良在公爵眼中却一无是处:“谁愿意屈尊去谴责这种轻浮举止?即使你有口才(我却没有)能把你的意志给这样的人儿充分说明……我也觉得有失身份。”[4]140显然,从他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夫人十分不满,他眼里的公爵夫人不过是个粗俗鄙陋、不知好歹、毫无教养的野丫头,不懂得夫家门第的尊贵,不知道成为公爵夫人是何等的荣耀,亵渎败坏了他的家风。然而细读上述文字,读者却会发现这分明是个纯真无邪、活泼开朗的少女形象,她对新奇事物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对爱护她的人心存感激,没有等级观念。“她看到什么都喜欢”[4]140,“她对什么都一样”[4]140,“她总是在微笑”[4]141。她的快乐像一盏火炬照亮这森冷的府第,给人带来惊喜与温暖。这一段描述显然是作者的声音在“从中作祟”。
公爵夫人不懂掩饰的欢笑被技艺高超的画师捕捉,巧妙地记录了下来,她在现实中的命运如何呢?虽然公爵口口声声不愿去计较,暗地里却采取了残忍的手段:“——我下了令,于是一切微笑都从此制止。”[4]141据学者们考证,露柯蕾西亚是被毒死的,作者却没有让公爵道出夫人被害的详细过程,只是淡淡地说:“她站在那儿,像活着一样。”[4]141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其实蕴含着潜在的意义。第一,它暗示了公爵夫人早已死去,面前是她的遗像。第二,这句话与诗的首句遥相呼应,“墙上这幅画是我的前公爵夫人/看起来就像她活着一样。”[4]139读者绕了一圈,又被带回了原地。先前产生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她是个纯真可爱的少女,却被无辜谋害致死,公爵大赞画师是因为她的生命在他心中轻如鸿毛,他更多关注的是画像的经济价值,哪管画的是谁呢。其实这正是作者设计的一个“巧妙的循环论证(Circular Conclusion)”[5]序,这种A—B—A的结构不仅使整个作品显得浑然一体,更是在B部分巧妙地用“话中话”颠覆了公爵所描述的夫人形象,反倒将他自己残忍无情又附庸风雅的本性暴露无遗。
前公爵夫人的故事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是作者似乎担心读者还不能体会他的良苦用心,又用两个细节进一步勾画了公爵的嘴脸。一个细节是他就伯爵女儿的嫁妆问题讨价还价,另一个是他展示的一尊青铜像。赏画对公爵来说不过是个小插曲,就嫁妆多少进行谈判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在起身陪客人下楼之前,他又向使者叮咛道:“我再重复一声:你的主人——伯爵先生闻名的慷慨大方足以充分保证:我对嫁妆提任何合理要求都不会遭拒绝。”[4]141按照当时的习俗,嫁妆的多少在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就要确定,并尽快汇到丈夫名下。嫁妆的多少也决定了出嫁女儿在夫家的地位,而作为嫁妆受益者的男方,这笔钱会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财源[6]277。也就是说,公爵夫人之死不但未给公爵造成什么损失,还给他创造了又一次敛财的机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面对亡妻的画像时毫无伤感。既然新娘不过是嫁妆的代名词,婚姻不过是商品,那么新公爵夫人——待嫁的伯爵女儿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公爵说:“当然,如我开头声明的,他美貌的小姐才是我追求的目标。”[4]141(Though his fair daughter’s self, as I avowed/At starting, is my object.)这里,作者又巧妙地使用“object”一词颠覆了公爵的话语。“object”是双关语,既可以指追求的“目标”,又可以指“物品”。显然作者暗示即将出嫁的伯爵女儿又将成为公爵的一件物品,就像前公爵夫人一样。
走到楼梯口,公爵又把一尊雕像指给使者看——克劳斯以公爵本人为模特为他特制的青铜铸像——海神尼普顿驯服海马。这一雕像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那凶神恶煞般的海神尼普顿正是公爵本人的化身,公爵与夫人的关系正如同尼普顿驯服海马一样,要将她的个性抹杀,使她变得服服帖帖。如今,前夫人的确是变得“服服帖帖”了,公爵说:“除我外再没有别人把画上的帘幕拉开。”[4]139他终于拥有了对她百分之百的控制权,夫人的微笑也再不会随意为他人所见,即使这一特权的获取是不惜采取谋杀的恶劣手段。
三、结语
勃朗宁用短短的五十六行诗句不仅揭穿了公爵谋财害命的丑恶嘴脸,也勾勒出了露柯蕾西亚这位年轻女性的风采以及她悲惨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戏剧性独白——只容许一人发话这一形式本身便剥夺了女性说话的权利。公爵把持着话语权,他可以随意歪曲夫人的形象和事实真相,而以画像身份出场的前公爵夫人,脸上虽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生命却早已枯萎。她不能开口,不能争辩,对任何污言秽语她只能报以那永恒明媚的笑容。在不明真相的观赏者眼中,那笑容诉说的是幸福,是她嫁入豪门后尊贵的丈夫对她的爱与呵护。殊不知她的笑容早已被鲜血淹没。显然,这篇戏剧性独白若由露柯蕾西亚本人来叙述,情况会大大不同。真相很容易揭示,读者也不用猜谜般费尽周折。但是生活在父权时代的她怎么可能掌握话语权呢?她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权力,她不过是公爵娶来装饰门面的花瓶或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公爵的要求和当时的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说,勃朗宁这一手法的巧妙运用正暗示了男权时代女性的整体命运,甜蜜笑容假象的背后掩盖的是其卑微的身份和凄苦的命运。
——勃朗宁武器公司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