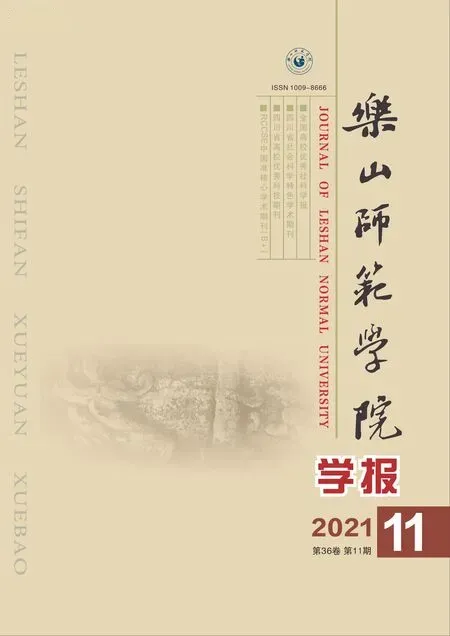从寇准的形象看民间视域对史传的偏移与简化
郑增乐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对于中国历史的记述,历来存在两个传统:一是史传传统,二是小说戏曲传统。受不同传统的影响,相同的材料可能会被引入不同的阐释方向。在史传传统下,从《史记》开始,“实录”就是史官的美德,“不虚美,不隐恶”即是一种标准,而小说戏曲传统下的历史材料则受“实”的影响相对较小。尽管历史演义这一支经常标榜“羽翼信史”,然其往往一边宣扬“据实指陈”,一边在正文中加入具有民间色彩的情节。正统史传与小说戏曲往往对同一事件采取不同记叙策略,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作者与作品背后的读者群——主流士大夫与中下层平民之间思想、思维、诉求的差异。本文拟以宋代史传为参照系,以士大夫视角为坐标原点,以通俗小说中出现较多的寇准为核心,对其本人经历,及其所处的宰辅团队内部斗争进行梳理,再对比小说戏曲中寇准的形象变化,来探求其偏移于史传的表现与原因。最后,本文通过两个寇准的对比,指出一种评价人物形象的传统观点——史传上呈现的人物枯燥干瘪,小说戏曲塑造的人物则生动丰满,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一种认知误区。相对于史传的多角度呈现,小说人物的性格往往片面化、纲要化。建立在人物性格基础上的政治生态、民族矛盾也随之被简单化处理。鉴于此,“羽翼信史”这种小说评价标准或需重新反思。
一、史传中的寇准: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中心
寇准为名门之后,《宋史·列传第四十》记载:“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也。父相,晋开运中,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1]9527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进士及第,早年曾在巴东做过县令,后慢慢进入中央任职。[1]9527寇准第一次出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是在雍熙元年的李继迁事件中:“时寇准为枢密副使,上独召准谋。”[2]586从此开始,一直到景德元年签订澶渊为止,可以说是寇准与宋朝两位皇帝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里寇准与皇帝的关系相对亲密,其对皇帝与朝廷的影响力也很大。
寇准为官时期参与了宋王朝诸多核心决策,其对于太宗、真宗的影响力极大。前面已经提到的宋太宗“独召准谋”就颇见端倪,而更生动的,就是废立东宫之事。太宗认为太子“所为不法,他日必为桀、纣之行”,因此召见寇准,与其商议废储之事。寇准建议“某月日令东宫至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卫皆令从之”,随后搜查东宫,太宗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2]598-599
在立太子这件事上,太宗同样信任寇准:
上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诚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宦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对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太子。[2]818
在立储的问题上,寇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或许也是因为此,寇准赢得了未来的真宗皇帝的强烈信任。
寇准其人以“诤臣”而闻名,为官刚硬是其本色。这正是他生命中最有传奇色彩,也是最为小说家所喜爱的部分。
其一为太宗时犯颜直谏。端拱二年(989),寇准向太宗奏事。“准尝奏事切直,上怒而起,准攀上衣,请复坐,事决乃退。”事后,太宗还高度夸赞寇准道:“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也。”[2]818-819
其二为王淮受贿案件。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发生了祖吉、王淮两桩受贿案件,最终情节较轻的祖吉被处斩,而大量受贿的王淮却逃过一死。淳化二年(991)发生了一次旱灾,寇准借此机会,向太宗进言,力陈王淮因与参知政事王沔有亲戚关系而免于一死,“上大悟,明日见沔,切责之”[2]713-714。
第三,在对契丹的态度上,寇准是坚决的主战派,同时他对军事行动也有深厚的理解。早在端拱二年,寇准就“承诏极言北边利害”,并且获得了太宗的赞赏。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侵,王钦若、陈尧叟提议迁都。寇准则坚决主战,并且建议真宗御驾亲征。
“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1]9530
事实上,真宗在军事上对寇准的倚仗也十分明显,《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五十七卷记载:
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乡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2]1257
对寇准、毕世安等人在军事上的倚重,已经让真宗直接绕过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率先与寇准等人商议了。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真宗最终御驾亲征。“琼即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1]9531最终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这几乎是寇准为官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具备较强的民族色彩,御驾亲征这个事件也被后世津津乐道。
然而危机同样在巨大的成就背后潜伏,这就是真宗朝宰辅机构内部的政治斗争。寇准为人刚硬,与王钦若、丁谓等人不和。如在面对辽国进攻的问题上,当王钦若提出迁都金陵、陈尧叟建议迁都成都时,寇准对此激烈批驳:“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2]1267以这样严厉的态度批驳,自然会遭受王钦若的怨恨。回朝后,王钦若就开始打击寇准。景德三年,此时的寇准已经“颇矜其功”,而王钦若则在真宗面前发表了一番“城下之盟”“孤注一掷”的言论:
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
且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2]1389
在王钦若的鼓动下,真宗对寇准开始渐渐疏离。正是在寇准达到事业顶峰之时,他与真宗之间的裂隙开始显现。随后,寇准罢相,外出陕州为官。从此,寇准基本远离了权力中心。之后虽又在天禧三年任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但不久又遭贬谪。[1]9532-9533
寇准的刚烈亦有其负面作用,这一点在《长编》中也有反映。吕端与寇准同列之时,即“先任宰相,虑准不平”[2]812,主动请求让寇准与他平级。再如前文中提到的李继迁叛乱事件中,宋太宗捉住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后,计划将她们处死,太宗独召的寇准竟然也同意了这个主意。这件事情也能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寇准过于锋芒、刚硬的特点。这次事件同样是由吕端来收场,他阻止了太宗的这个计划。
景德二年,年仅14 岁的晏殊与12 岁的姜盖参加殿试,“殊属辞敏赡,上深叹赏”,寇准却以晏殊为江左人士为由,“欲抑之而进盖”。[2]1341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寇准性格中固执与偏狭的一面。《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四十卷亦载:
先是,郊祀行庆,中外官吏皆进秩,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者及不知者,即序进焉……拯尝与准有隙,故准抑之。惟节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衔皆如旧不易,准怒,以中书札子升惟节于拯上。切责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阅万机,宁察见此细事?盖寇准弄权尔。”因上疏极言……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于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准性刚强自任,臣等忝备大臣,不欲忿争,虑伤国体。”[2]846-847
这是官员之间一次比较激烈的矛盾,在矛盾之中,寇准之“率意轻重”“除拜专恣”“刚强自任”的性格有明显的显露。而寇准之刚强乃至固执所引发的矛盾,在其官吏生涯后期更为多见。
景德三年,真宗批评寇准“轻诺寡信”,吕蒙正亦评价寇准“轻脱好取声誉”。[2]1434《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八十四卷记载,面对真宗“天下事付之谁”的问题,王旦答道:“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真宗却以“准性刚褊”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2]1923《长编》第九十五卷则记载了寇准与李谘的矛盾,“准性强固”在这一事件中也有所暴露。[2]2283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中关于寇准的记录,我们可以相对全面地总结出寇准之为人。简言之,寇准正直刚硬,有些固执偏狭。正是他的正直与刚硬,为他赢得了诤臣的美誉,促使他在辽国进攻的时刻提出御驾亲征的建议。这无疑是其生命中的闪光点,同时也是其在后世受到小说家青睐的核心因素。但是偏狭和固执又成为他在澶渊之盟后被排挤出政治中心的一个导火索。站在人的角度,寇准既有优点又有不足是无可非议的,而史传也对作为官员的寇准进行了相对全面的呈现。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小说、戏曲中的寇准相对于史传里的寇准发生了哪些偏移,以及发生这些偏移的原因。
二、小说、戏曲视域下寇准形象的偏移
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例如尚奇、尚趣。作为历史人物,寇准的形象进入民间文艺的范畴中后,自然也会进行这方面的偏移。同时,小说戏曲中的人物形象也寄托了市民、游民等群体的希望与诉求,这在寇准的民间文艺转向中也有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以“羽翼信史”作为小说评价的一个尺度。如蒋大器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作的序中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3]233所谓“庶几乎史”正是衡量历史演义之品格的重要尺度。修髯子亦评价其“羽翼信史而不违”。[3]234在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下,一些提到寇准的小说,其情节与史传的记叙极其相似,甚至是直接照抄史传原文。这个传统一直绵延到民国时代,例如在民国时期李逸候的《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中,有关寇准攀衣直谏太宗的情节就几乎是《宋史》的白话文翻译版。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来说,这样的情节自然是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的。
小说、戏曲之寇准形象的偏移,主要通过强化、淡化、颠倒与无中生有四个方面来展现。所谓强化,即将寇准的某些品质突出表现,比如寇准的刚硬正直,其对于辽国的坚决抗争态度;淡化则相反,把寇准的某些特征(主要的负面品质)消弭掉;颠倒则是将本来的特征改写成此特征的反面,在寇准身上最突出的就是奢侈与勤俭的问题;无中生有,则属于全面的虚构,比较突出的是杨家将系列中寇准审问潘仁美的情节。
以寇准为主要人物的小说主要是杨家将系列,戏曲则有《清官册》《寇准背靴》《寇准罢宴》等,本文即以上述作品为中心进行这一部分的讨论。
(一)强化:诤臣情节与民族情绪的投射
犯颜直谏与坚决主战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较高。清代西湖居士之《狄青演义》第三回即用大量篇幅描写寇准请求御驾亲征。[4]而同属狄青系列的《五虎平南》则在第一回里追忆了“当日若无寇准之才智,劝主亲征,国家几乎亡灭”[5]。陈忱《水浒后传》第二十三回也有种师道对钦宗追忆寇准力劝亲征的桥段[6]。甚至冯梦龙《喻世明言》之二十二卷也曾提及“宰相寇准有澶渊退虏之功”[7]。根据笔者的统计,《喻世明言》中应该也只有这一处提到寇准。
由此可见,小说家与小说的读者们对寇准犯颜直谏御驾亲征的故事是存在偏爱的。究其原因,大概至少包含三点。
首先,“奇”与“趣”向来是民间文艺的追求点,而寇准之劝亲征,其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既是为人所不敢为,也是为人所不能为。
其次,这件事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宋朝从建立伊始就处在外族政权的威胁下,军事斗争长期失利,南宋更是直接让去半壁江山。至元代,民族压迫达到一个顶点,处在下层的民众在国家军事连连不利的情况下,将情感寄托于小说家言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寇准强谏亲征的民间接受与岳家军之于金、杨家将之于辽,乃至《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宋江抗金情节是一致的。于宋江,是国家不济,“转思草泽”[8]。于寇准,则是现实不济,诉诸历史。简言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背景下,主战的寇准确实更容易为民众所偏爱。这自然也是导致王钦若成为民间文艺之大奸臣形象的一个因素。
最后,民众对诤臣有习惯性的偏爱。这是普通平民利益诉求与个人梦想的投射,这种投射可分为两类:一是寄托于自身的发迹变泰,二是寄托于明君贤臣侠客保佑。于前者,就是自话本小说以来的各种发迹变泰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无一不是早期落魄而终以富贵,如《史弘肇龙虎风云会》中的史弘肇与郭威。甚至强行改变人物的出身,如《说唐》系列中的秦琼、程咬金,历史上本为世家,但是小说却将其出身改为游民。早期的发迹变泰故事主角多为游民武人,后书生也慢慢参与进来,这些角色出身于底层,与故事的接受者们出身类似,史弘肇们飞黄腾达的故事也正是普通平民对于其个体人生的梦想。而于后者,人们则普遍希望在清官、明君的庇护下生活,清官成为他们生命的一种重要寄托,在平民的意识里,敢于犯颜直谏、刚硬、正直是清官的重要标准,因为这样清官才能“为百姓做主”。寇准、包拯、海瑞等无不如此。在这样的受众心理下,寇准以刚硬与主战而进入民间视域,并且在这个视域里不断放大自己的刚硬与主战。
(二)淡化:诉求的差异
通俗文艺下寇准形象相对于史传中的淡化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通俗文艺不关心的点,一种是寇准本人性格中的一些不足。
所谓通俗文艺作品不关心的点,首先是趣味性和传奇性不强,其次是与普通百姓联系不紧密,反映在寇准身上就是立太子之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寇准的多数互动都在他与太宗、真宗之间。寇准所考虑是赵宋皇室的利益和朝廷的稳定,按照权力对其来源负责的原则,这是无可非议的。立太子之事在皇室和官僚系统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是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来说,这与他们距离遥远,利益关联度较低。恐怕这是寇准劝立太子之事在民间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
而寇准性格之不足被消弭则是民间二元对立思想、通俗文艺之“扁型人物”塑造模式、民间清官幻想的综合表现。寇准性格里的偏狭、固执在民间文艺作品中鲜有表露。相反,通俗文艺中还增加了一些表现寇准机智聪慧的桥段。随着寇准固执偏狭品格的消弭,由其固执偏狭影响的一些政治矛盾也被简化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进行讨论。
(三)颠倒:清官崇拜的体现
奢侈与节俭的颠倒是寇准之民间形象塑造的又一关键点。关于寇准钱财观的记载并不见于正史,但是在一些笔记中有所涉及。如《归田录》: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9]
《石林燕语》亦云: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醆。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醆方毕。[10]
尽管亦有史料记述寇准“不置私第,不营田园,所得俸赐,皆分给宗党故旧”[11]。不过联系宋朝官吏之优渥待遇,加上寇准本人好客善饮,在宴饮时铺排豪奢也是合理的。宴饮豪奢不蓄私财似可以共存。[12]
然而在民间意识里,清官不允许有豪奢的行为,有时甚至苛刻到必须一贫如洗才算清官。这种刻画也发生在寇准的身上,在戏曲《清官册》中,寇准被外放做县令的经历被着重介绍,这里的寇准不但爱民如子,原本三年一任的任期生生被当地百姓留了十二年。寇准还十分廉洁,府中只有两人居住,这就是民间对于清官幻想的一种集中表现。另一出著名戏曲《寇准罢宴》讲述寇准受到启发决定撤掉奢华宴席的故事,与民间对官吏的清廉诉求亦有契合处。
(四)无中生有:奇与趣的追求
所谓无中生有,也就是小说戏曲中的虚构,而虚构的方向就是趣味性与传奇性,这既是民间作品娱乐性追求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商品性特征。
关于寇准的虚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杨家将》系列小说与戏曲中审问潘仁美的桥段。杨家将故事大多违背史实,甚至荒诞不经,寇准审潘仁美自然也是向壁虚造。在明代秦淮墨客的《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中,寇准设计灌醉潘仁美,又套出其害死杨继业、射杀杨七郎的供词,读来颇有趣味。在戏曲《清官册》中,寇准则利用潘仁美迷信的性格,假装阎王夜审潘仁美,其趣味性和传奇性相对小说又有强化,这一桥段至今仍在戏曲和评书艺术中被不断搬演。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小说戏曲中的寇准对史传记载的偏移,我们可以总结出寇准刚硬正直之强化、固执偏狭之消弭、清廉形象之构建等等。这些都与下层平民的审美情趣、利益诉求乃至生活幻想息息相关。
三、丰满还是简化:对“羽翼信史”的反思
前文中已经提到,古代小说长期处在“羽翼信史”的评价体系中。其实早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就已经做出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13]的判断,这都是立足于“求真”。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通俗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的作者和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追求“真实性”,对于一部小说的正面评价,往往是其可以作为史书的补充。实际上,不仅通俗小说这一支,一些历史题材的戏曲作品也往往会通过宣称有史可依来抬高自身地位,扩大影响力。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羽翼信史”的辐射范围实际上是以通俗小说为核心,波及戏曲等其他文艺形式。
但是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已经触及一个问题,寇准形象在民间视域中有强化优点、弱化缺陷的偏移,这样很容易把人物“压扁”,甚至使人物符号化。从丰满程度的角度看,很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要逊色于史书的(当然精彩程度就是另外一个范畴了)。而这只是简化的一种初级状态,更严重的是,很多官吏集团内部的矛盾在小说和戏曲中被简化为忠奸斗争,好人全好,坏人全坏。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寇准与其同僚的矛盾记载并非个例,由于寇准的偏狭而引发的矛盾,在小说之中随着寇准偏狭性格的消失而消失了。寇准在政治上最大的政敌当属“五鬼”,但是对于寇准和“五鬼”之性质的判断,类似《狄青演义》中那种“忠心贯日的贤臣”“相济为恶,聚敛害民”[14]的评价恐怕还是过于片面。事实上,五鬼之于宋王朝也并非就是全恶,其在文化建设、经济和财税等方面也颇具贡献。寇准的失势如果只用王钦若的谗言来解释恐怕也略简单,真宗建立完善文官体系的需求也许亦是一条线索。[15]但是这些在小说和戏曲中是不会出现的,传统戏曲本身就是脸谱化的艺术,一般的古典小说同样如此。这样,纷繁的政治斗争就被正邪二元对立取代了。更有甚者,纷繁复杂的时代也可以被简化为因果报应的轮回,譬如《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中的司马貌断案情节,或者《说岳全传》第一回金翅大鹏鸟与女土蝠、铁背虬王之间的恩怨。
两国之间的战争在小说戏曲中则往往被简化为意气之争,其套路往往是外国使臣来朝,皇宫内公然挑衅,或是当场比试才艺,或是下战书。之后两国开战,而战争的经过,就是诱敌、劫营、斗阵和武将之间的单挑。
其实这些偏移都是民间审美情趣的反映,矛盾和线索的简单化也适应了市民阶层、游民群体和一部分商人的思维水平。同时,这些简化和扁化也是通俗小说和戏曲商品属性的反映,对利润的追求使得书商们必然走向增强作品通俗性、削弱思想性和叙事复杂程度的道路。
现在回到我们这一节要讨论的问题,通俗小说相对史传的书写,其偏移很多时候表现在简化历史上,例如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将政治斗争变成正邪对抗。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羽翼信史”更像是一种以小说攀附史传的宣传语,而非真实情况。对于史书,很多小说非但没能丰满历史,反而将它简化成了一条一条的“纲要”。
这也是古代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困境,在求真的立场上,小说的“羽翼信史”功能其实并不称职。而虚构的立场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没能彻底占据主导位置(特别在历史演义中),很多小说家也没有重视虚构的作用,如袁于令、金圣叹这样具有虚构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从创作论的角度上来说,这种长期处于求真与虚构之间的摇摆,或许也是明代大批平庸小说诞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