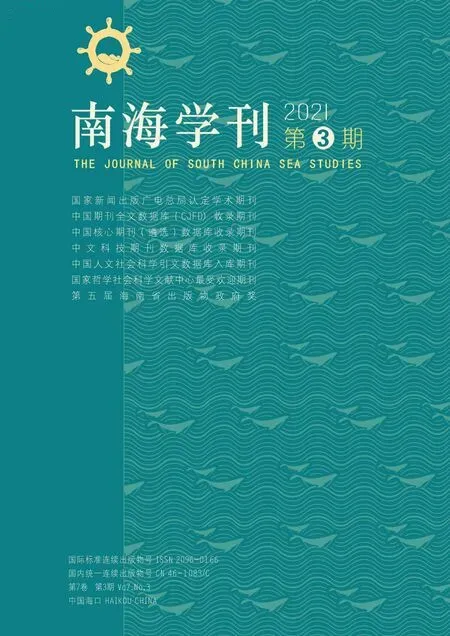文明互鉴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文明人类学的视角
王利兵
(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文明多元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和基础。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虽然对文明多元以及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进行新的交流和对话创造了条件,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接触、联系不断增强,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并就如何加强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提出4点主张,即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注]《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9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5/15/c_1124497022.htm。。文明交流互鉴是对文明理念的一次深刻阐释和解读,进一步丰富了文明概念的思想内涵。
一、文明的含义与本质
“文明”一词出现时间相对较晚,其含义经历了许多变化。在18世纪早期,“文明”是作为一个法律用语出现的,主要指示一种正义的行为或是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诉讼的审判。18世纪中期,“文明”逐渐发展为“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之意。18世纪末,“文明”开始被用以指代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其背后潜藏着启蒙主义的一般精神,即强调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注]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92-94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明”都是作为一种单数形式在使用,其背后暗含这样一种含义,即文明只是少数特权集团(即精英)所拥有的东西,这种文野有别的文明观点在西方发展殖民主义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19世纪中期之后,“文明”一词开始出现复数形式,如西方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文明等,由此文明逐渐成为一个相当中性的词,指涉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注]同①:第96页。。
文明发展至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接受“文明”的单数形式,因为它暗含一种不好的价值判断和观念,具有鲜明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不过,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使用单数形式的文明,“单数形式的文明在今天确切地说是指某种为所有文明所共享却不可均分的东西:人类的共同遗产”[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8页。,比如,文字、火、算术、工业技术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正在使世界均一化。与此同时,布罗代尔还认为,文明的传播和整合只是局部现象,从西方输出的“工业文明”仅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诸多特征之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工业文明但并非意味接纳西方文明之整体。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文明”一词仍将既用作单数形式又用作复数形式。需要强调的是,文明无论是以复数形式存在抑或在未来趋向单数形式,其历史皆告诉我们,文明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相互借鉴、交流、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正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注]杰克·古迪:《偷窃历史》,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页。在有关西方文明研究中指出的,西方的很多文明(如民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爱情等)都是从东方“偷窃”来的。换而言之,文明并非是西方的发明,它是在历史的联系和交流中产生的。
进入20世纪之后,频繁的战争和危机让文明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重要研究对象,他们都希望能够从对文明的研究中探索出世界和平之道。然而,学者们对于何谓文明始终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在《历史研究》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将文明视为历史的最小研究单位,“它是指有一定时间和空间的某一群人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一般包括若干同样类型的国家,是这些地区或民族国家构成的群落”[注]阿诺德·汤因比著,D·C·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上卷),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页。。汤因比认为文明形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其中文化是文明的核心,并据此将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区分为21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代表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将文明界定为一个包含个人心理与自我行为表现以及社会组织完善的过程,强调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在有关文明研究中,引起人们讨论最多的学者应该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内容宽泛的文化实体,包含宗教、语言、生活方式、价值、体制和社会结构等众多内容,其中宗教是界定文明的最重要因素。据此,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划分为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1-26页。。然而,人们在谈论亨廷顿的文明论时,都将其与“文明冲突论”画上等号,却忽略了“文明冲突论”背后的另一层含义,即化解文明间冲突的根本途径正是在于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法国年鉴学派对文明亦有较多讨论,比如,布罗代尔将文明看作是一定时期或一个群体的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不同文明之间也许会相互排斥或拒绝,但更多的是彼此借鉴和吸收,并强调文明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第33-40页。。值得指出的是,布罗代尔的文明论明显受到作为其前辈的法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
莫斯对于文明的本质问题曾有过深入研究。莫斯对文明的关注和研究源于20世纪早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和战争,其时欧洲笼罩着战争阴影,莫斯透过这个阴影看到历史断裂带来的社会危机,认为其中民族国家是导致矛盾的首要原因。莫斯认识到限于国族之内的社会学研究存在很大问题,于是他从“文明”概念出发,试图寻找一条通往“超国族文明”的道路。1913年,莫斯与涂尔干合作发表一篇题为《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开篇即指出社会学只去研究国族之内的社会现象存在不足,因为还存在一个社会学尚未意识到和无法知晓的更高等级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不那么严格地归属于确定的社会有机体,它们在空间上超越了单一国族的领土范围,在时间上超出了单一社会存在的历史时段。它们的存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超国族的”[注]莫斯等原著,施郎格编选:《论技术、技艺与文明》,蒙养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37页。。这些超越单一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象被莫斯和涂尔干称之为“文明”。涂尔干辞世后,莫斯又相继发表《国族》与《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两文,更为系统地阐发了文明的概念和内容,并对文明的定义、特征、形式和区域分布等内容做了有具体设想和现实意义的展望和研究。在莫斯的定义中,文明是一种超社会体系,这些具有超社会属性的文明现象广泛存在于物质文化、语言、宗教和制度等领域,如神话、传说、货币、贸易、艺术品、技艺、工具、语言、词汇、科学知识、文学形式和理念等现象[注]同②:第63页。。莫斯通过对大量民族志和史前史材料的阅读和分析指出,文明的首要特征是传播,传播借鉴和交往对于文明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过文明的传播并非没有限制,而是有其特定的地理空间限度。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文明容易沾染民族主义和国家的色彩,但这并不能否认文明的传播性特征,文明在本质上依然是超社会性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简言之,文明是交流互鉴的产物。
二、作为“超社会体系”的海洋文明
王铭铭在莫斯的“文明论”基础上对文明现象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并将其统称为“文明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civilizations)。王铭铭指出,作为超社会体系的文明是先于国家和社会而存在的,文明现象所表现出的“超社会特征”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乃是一个新的“超社会体系”替代既有“超社会体系”的过程,而非“社会体系”替代“超社会体系”的过程[注]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1页。。因此,文明人类学不仅代表一种对于人的活动及其文化的重新理解,而且对于反思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现实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王铭铭的文明人类学论述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反思,也就是说他所讨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诞生于陆地上的文明现象及其超社会特征。其实,文明现象所表现出的超社会特征不仅可以在陆地社会上寻找到,在海洋社会里体现得更加明显,甚至可以说,海洋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俨然就是一个超社会体系的发展史。
相比陆地社会而言,海洋社会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海洋文明也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文明[注]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黄彦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0页。。与农耕社会中农民“半身插在土地里”不同[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依海而生的海洋族群所面对的社会生态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离乡离土的途径和条件,使他们能够游离于乡土之外,进而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方面呈现出许多非乡土特色[注]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4-213页。。流动性始终是海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人员的流动、物品的流动、信息的流动、观念的流动等,流动性将来自不同地区的海洋族群和社会进一步塑造成为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体系或网络,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区域文化格局和海洋命运共同体[注]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简言之,文化交流、族群互动和文明互鉴是海洋文明形成的基础,也是海洋文明的本质所在。下文将以太平洋文明为例,通过对人类学研究文献的梳理,试图呈现和说明文明互鉴之于海洋文明形成的重要性。
太平洋文明是人类海洋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洋文明是一个包含诸多社会的区域系统,本文所言“太平洋文明”之地理范围主要是指以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为主的大陆沿海社会与岛屿世界,是“太平洋文化圈”的中心地带,这些社会及其所涵盖的文明现象之间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一致性,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塑造出太平洋文明这一整体。太平洋岛屿世界及其文明体系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区域和研究对象,其间诞生过许多著名的民族志和理论,比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对美拉尼西亚社会“库拉圈”的研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南太平洋诸岛土著文化之意义图式的研究,等等。莫斯在分析文明的形式时,也曾专门以太平洋文明为例进行说明。
对我来讲,我从很早就主张在太平洋沿岸及岛屿可能存在一个很古老的文明。在这个分布非常广泛、扩散的文明里,我们似乎又可以或者可能划出一个太平洋南部和中部文明。在太平洋中部,又可以发现马来-波利尼西亚文明、波利尼西亚文明、美拉尼西亚文明和密克罗尼西亚文明。基于这四种文明的关系,或者它们与奥斯特罗尼西亚、澳亚和亚细亚文明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建立所有类型的文明的建构。事实上,在这个巨大的范围内,这些文明之间又有极大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其中又有些令我们深信文明最初的统一性,即使其内部有种族的多样性,例如:黑马来尼西亚人和浅黄波利尼西亚人。相反,这些一致性又让我们相信在相对统一的语言下又存在着多样性,例如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排除巴布亚因素)。蒌叶、醉椒、弓、马刀、胸甲、栅栏和干栏式建筑等传播的局限允许我们将文明分类甚至可以推进关于它们系谱的假设。同时,语言的分支或相似也是证明人类群体关系的最好方法之一[注]莫斯等原著,施郎格编选:《论技术、技艺与文明》,蒙养山人译,第63-64页。。
虽然莫斯在这里对太平洋文明的论述十分简短,却从宏观上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清晰的关于太平洋文明的整体图像。莫斯曾将借鉴和贸易定位为文明史形成的核心内容,两者都属于交换性质的活动,而交换是社会和文明生成的条件。“文明的影响,用外行的话来说,就在于规范、扩大和推广贸易,把它从偶然的或者仪式性的贸易,转换到自由的物物交换,从物物交换再到买卖,从买卖到市场经济,从殖民地的或国家的市场到世界市场。事实上,国族的经济现在已经如此开放,以至于它们不仅仅互相依赖,而且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它们变得绝对依赖于世界市场行情,特别是通过贵金属或者标准价值进行的贸易更是如此”[注]同①:第48页。。莫斯认为,贸易最初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巫术、宗教物品、货币和手工艺品,而那种限于消费物品和经济范畴之内的贸易活动则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象[注]同①:第46-47页。。与此同时,莫斯也指出,我们不应该将贸易想象为近代欧洲国族的独特创造,更不应该设想欧亚大陆才是文明的摇篮,诸如澳洲、大洋洲的土著人群早就致力于远距离贸易,并已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贸易交换体系,也早已形成属于自己的文明。实际上,在现代机械交通工具诞生以前,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海洋社会间的交流互动远比陆地社会更加频繁和便利。
萨林斯在其太平洋文明研究中曾指出,太平洋文明是我们了解世界体系历史进程的一个绝佳场所。他认为,现代全球秩序的建立一直受到所谓的“边缘人民”的决定性形塑作用,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太平洋群岛及毗邻的亚、美大陆的人民便以互惠方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冲击”,从而也塑造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注]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4-365页。。其实,边缘与中心(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早在资本主义诞生和扩张之前的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就已经大量存在,林惠祥关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以及凌纯声关于“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等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这种关联性的早期存在提供了支持。
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两篇重要的考古学报告中开始注意到中国华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太平洋群岛之间在土著新石器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注]林惠祥:《福建武平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林惠祥通过对印纹陶遗存的研究,提出将大陆东南地区看成文化史上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并具体论证了印纹陶文化在亚洲大陆东南海洋地带的空间分布特征,比如“武平陶器的曲尺纹陶也见于马来半岛的陶器上,有段石锛多见于台湾、南洋各地而武平亦有,由此可见武平的石器时代文化与台湾、香港、南洋群岛颇有关系”[注]林惠祥:《福建武平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同一时期,凌纯声教授提出了一个与林惠祥“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相近的概念,即“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在“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理论中,凌纯声详细阐述了中国东南地区与东南亚以及西南太平洋群岛间的土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指出了西方人类学研究中有关“南岛语族”分布范围的错误和不足[注]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343-344页。。凌纯声十分重视人类学的文化分析,他在克虏伯(A. L. Kroeber)“东南亚古文化区”一说的基础上,通过对亚洲地中海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龟祭文化、铜鼓、猎头习俗、父子连名制、文身、少女房、蛇图腾、龙船、弩箭等文化特质的考察,认为东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存在文化上的统一性,并据此认定环太平洋古文化起源于亚洲大陆沿岸,将“亚洲地中海文化圈”中的“南岛语族”归于远古时代以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以“珠贝、舟楫、文身”为特点的海洋文化远航的结果[注]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继林惠祥和凌纯声之后,张光直教授提出“南岛语族”的“闽台起源说”,认为南岛语族的源头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注]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澳洲知名考古学家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综合考古学与语言学研究,系统论述了南岛语族从闽台渐次向海岛东南亚地区再到太平洋群岛地区的扩张过程[注]Peter Bellwood,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7, pp.117-119.。结合上述研究,吴春明进一步指出,“南岛语族与华南土著同属一个人文系统,学术文献中的华南土著与南岛语族间并没有真正的文化内涵与族群系统差别,华南土著地带与南岛语族地带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共同体内在的互动与整合的关系”[注]同①。。近些年,分子人类学从Y染色体、古人类DNA和全基因组芯片等方面对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所得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林惠祥等人的观点,即包括台湾土著人群在内的南岛语族和侗台语族具有遗传亲缘关系,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是在华南地区[注]范志泉、邓晓华、王传超:《语言与基因: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也就是说,南岛语族和侗台语族的先民都是来自新石器时代的亚洲大陆东南沿海的土著民族,他们共同组成了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是早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古代太平洋文明主要是一段族群迁徙史和技术传播史,那么近代以来的太平洋文明则是一段伴随着大航海时代和西方殖民者而来的以贸易为载体的区域互动史,其内容除物品流通与贸易往来之外,亦有大量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关于近代以来太平洋世界的贸易发展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围绕以中国为中心所形成的中外贸易史研究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其中尤以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朝贡贸易是指王朝时期中国与东亚以及东南亚世界之间的一种区域合作制度,它以贸易作为相互联系的手段,目的是维系区域关系和秩序的和谐稳定。滨下武志强调朝贡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商业贸易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朝贡贸易网络,后者具有多重结构的性质[注]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是一种核心的贸易往来,而各个朝贡国之间则是另外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贸易关系,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网络由里向外逐层展开,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有别于以国别为单位的传统亚洲研究,滨下武志的研究强调一种亚洲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突出亚洲整体地域的主体意识,注重亚洲内部的网络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与前近代的内在连续性[注]李长莉:《海洋亚洲:网络化的地域史》,《读书》,2002年第7期。。基于此,滨下武志提出针对亚洲区域内部开展的“地域圈”研究的四种模式,即海域模式、网络模式、腹地模式和港口模式,这四种模式皆以海洋为媒介展开。滨下武志认为,“从海域的观点来看作为空间的亚洲,让人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亚洲”[注]川胜平太:《东亚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亚洲间竞争的500年》,沟口熊三、滨下武志等编:《在亚洲思考·卷6·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转引自翟意安:《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虽然滨下武志的“海洋亚洲”论更加侧重将亚洲海域看作是一个互联互通的贸易网络,但同时这一网络也是各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交流的平台以及宗教、文化和技术传播的媒介。从本质来说,海洋亚洲形成的重要基础乃是文化纽带,文化交流使得亚洲海域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形成特殊的交往结构,进而将其串联成一个具有独特人文底蕴的命运共同体。风帆时代,船舶是海域社会交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工具,日本学者松浦章从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众多的历史文献出发,通过对风帆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发现,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东亚世界的一笔重要财富[注]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麻国庆在关于环南中国海的研究中同样认为,海洋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阻碍,相反是以海洋为中心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形成的重要通道和基础[注]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在海洋亚洲的文化交流史上,宗教信仰的传播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如海洋神灵妈祖在东亚海域的传播就很好地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间的文化交流[注]王小蕾:《妈祖信仰在亚洲海域的传播与流布——以“海洋亚洲”论为视域的考察》,《南海学刊》,2016年第2期。。妈祖是起源于福建莆田的一个地方性女神,后在政治的加持之下逐渐上升为享有重要地位的全国性神灵。与此同时,伴随着东南沿海人群的跨海流动迁徙,妈祖信仰又进一步传播至亚洲海域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以妈祖信仰为核心,包含沿海城市、周边岛屿、半岛等重要节点的海洋宗教信仰网络。如今,妈祖信仰已然成为华人世界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是维系华人认同和联系的重要纽带。妈祖信仰在亚洲海域世界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固然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但同时也折射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上的差异,体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包容和接纳。从流动性的视角来看,诸如宗教等文化现象的传播以及海洋族群的跨海流动与互动皆是塑造区域海洋网络的重要力量,是海洋文明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20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劳工和商品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愈发频繁,区域海洋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要想充分理解和认识海洋文明的本质,就必须对其所涵盖的宗教、文化、自然、族群和市场等因素展开更加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而这无疑也是在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三、文明人类学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海洋作为联通世界的重要通道,在不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海外商贸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桥梁。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目的同样是为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互联互通与合作,推动海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共同促进海洋文明的发展。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概念和理念,他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注]《共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19年4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23/c_1124406792.htm。。“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揭示了海洋作为公共物品和人类共有遗产的本质属性,强调海洋合作与海洋资源共治共享的必要性,又突出了海洋作为联通世界的通道和桥梁的重要性,是在深刻理解海洋文明本质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也是中国为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与发展贡献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文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潜力,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构建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诸多阻碍。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困难与挑战。
一是海洋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中国是一个海岸线漫长、海域面积辽阔的海洋大国,海上邻国众多且族群关系复杂,彼此间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性明显,对于中国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形成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化逐渐接管了文明的内涵,地方文化得以充分展示和消费,文化多元主义成为时下人们普遍接受的口号。在文明人类学看来,“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心在于交流、借鉴与共享,而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对差异性的理解与尊重。世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并不是不同国家与人群之间交流的障碍,相反是彼此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以环南中国海为例,环南中国海的人文地理分布十分复杂,其周边居住和生活着众多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民族,但是这种复杂的分布格局并没有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历史上的环南中国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频繁的区域[注]麻国庆:《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今天,我们重新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正是希望在继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我们尤其应加强对区域民间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深化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然而,民间文化交流的实现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知识的生产和推广。人类学擅长于对异文化的调查、描写和记录,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是理解和认识不同族群和文化的重要知识来源,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早期殖民主义发展史中乃至今天的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注]高丙中:《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早期人类学的许多经典民族志都是关于岛屿社会和海洋族群的研究,如《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和《萨摩亚人的成年》等,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为学术界贡献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和理论,而且至今仍是我们认识太平洋文明和印度洋文明的重要知识来源。有鉴于此,我们应该重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借助和利用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加强对于周边族群和文化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尤其是海洋民族志的调查与书写,增加关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知识积累和推广宣传,提高大众对于他者及其文化的认识,进而在理解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真正做到费孝通先生所言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对流动的限制。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位于边陲地带的海洋很少进入国家的统治范畴,而是更多地被视为联通世界各地贸易的通道和桥梁,甚少有国家和统治者对海洋提出要求或主张。进入民族国家之后,声张主权和划定边界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基本特征,因此对于海洋提出主权性要求也就成为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海洋秩序的国家构建由此也开启了序幕。从本质上说,民族国家下的海洋秩序构建实际上是一场对于海洋权益的争夺战,是一场“蓝色圈地运动”。这种争夺势必会引发民族国家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比如海洋边界划分和岛礁的主权纠纷等,进而对海洋的流动性制造了许多限制。目前,中国与多个海上邻国存在海洋争议,其中尤以南海海域的争议最大。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先民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生产生活,形成了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性权利。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在民族国家理念的号召之下,纷纷对南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性要求,由此导致与中国之间发生一系列不间断的海洋争议,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更进一步加剧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海洋争端与分歧,使得南海问题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不仅如此,部分海洋权益纠纷甚至还和沿海国的国内政治局势、地区战略格局、大国政治博弈发生关联和耦合,成为国家内部、地区甚至全球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注]黄任望:《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初探》,《海洋开发与管理》,2014年第3期。。
文明人类学强调将诸种文化现象置于“历史文明”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其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海洋世界的流动性特征以及民族国家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利于提高海洋治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比如,有关南海渔民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作为区域的南海既是南海渔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他们跨界互动交流的纽带[注]王利兵:《制度与生活:海洋秩序的渔民实践》,《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然而,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海洋逐步疆界化,争夺海洋领土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渔民自由流动作业的传统以及渔业资源自身的流动性特征在民族国家框架之下则被有意遮蔽或忽视。如此一来,渔民的流动作业自然容易引发所谓的“跨界”“非法”作业问题,进而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渔业纠纷和冲突,近些年中菲海洋争端频发以及海南渔民频繁被抓扣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南海渔民渔业问题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即并非所有的海洋资源都可以置于民族国家的管辖之下,而此类问题的解决也并非能够通过某一个国家的海洋制度化和实践可以完成。也就是说,当前的海洋治理必须要考虑到渔民和渔业资源的流动性特征,重视渔民基于资源、生计和历史而形成的渔业生产传统和文化,充分尊重渔民群体的文化传统与海洋实践,进而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层面的对话与合作,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的共享共治。
三是海洋问题的区域化与治理的国家化之间的矛盾。当前,海洋问题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明显,但应对海洋问题的行动和海洋治理的主体主要还是以国家为主。海洋问题的突出表现是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加。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而言的,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指以海洋为活动空间,以政治、军事之外的目标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威胁,其主体较之以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安全更为多元化,对海洋安全的危害更具区域性和全球性[注]宋红红:《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国际合作:理论、行为及机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8-10页。。比如,南海地区是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较为集中和明显的海域,涉及问题包括海盗问题、海上恐怖主义、海上偷渡、区域海洋环境污染以及海洋自然灾害等。虽然这些问题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发展造成了诸多影响,但同时也为南海区域合作提供了动力和机会。以海盗问题为例,南海历来是海盗群体的渊薮,其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注]安乐博:《南中国海海盗风云》,张兰馨译,上海: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4年,第76页。,时至今日,南海海盗问题依然是世界海盗行为最为猖獗的海域之一。有关统计数字显示,1991—2014年间南海及其周边海域所发生的海盗事件占据全球海盗事件总数的50%以上[注]林亚将:《护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海盗防范区域合作法律机制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虽然南海海盗问题对于沿海周边国家的国家安全及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但不乏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比如促进区域海洋合作和海洋制度的建立[注]许桂香、司徒尚纪:《南海海盗文化的历史演变与价值》,《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如果说海洋传统安全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安全”以及民族国家个体层面的行为实践,那么海洋非传统安全则更加强调“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认为海洋领域的任何安全问题都有可能造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安全影响,因此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有赖于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注]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尽管当前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治理问题上立场观点不同、利益诉求各异,但是为有效应对一些频繁发生的共同海洋问题,还是有必要深化区域合作,一个典型案例是东盟国家在处理海盗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次区域合作走向区域合作的历程[注]王光厚、王媛:《东盟与东南亚的海洋治理》,《国际论坛》,2017年第1期。。其实,东盟成员国在打击海盗问题上的合作经验完全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比如海洋灾害救助等,如此可以有效增加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同抵御海洋风险的能力。近几年,笔者在海南东部沿海开展田野调查期间,经常听到当地渔民谈及他们与东南亚渔民互动往来的历史传统以及在发生海难时互帮互助的真实故事,这说明在渔民群体层面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互助合作的精神传统。这种来自民间层面的合作传统无疑为国家层面的海洋合作提供了借鉴和基础,而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又可以适度缓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困境和局势,从而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构建南海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帮助。
四、结 语
海洋文明的本质是一种关系与融合,是对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文明论”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正如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在其文明研究中指出的:“文明是最崇高的联系纽带,人类在文明的旗帜下聚集在一起,虽然这种聚集是精神上的而非领土上的。文明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存在理想。”[注]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5页。在上文中,笔者以太平洋文明为例,将海洋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置于文明人类学的视角之下进行考察,认为海洋文明的生成是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产物,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必将是一个文明互鉴与求同存异的过程。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日益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各类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涌现又说明海洋问题的紧迫性,本质上是对海洋文明的一种挑战和背离,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疑是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一种有效途径。作为公共产品和人类共有财产的海洋,其独特性质决定了海洋问题的解决以及海洋空间的开拓必然会涉及众多不同类型的主体,需要不同国家、地区、组织和族群的共同参与和平等合作,需要我们从文明的视角出发重新认识海洋的历史与本质,如此才能实现海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概而言之,今日海洋之存续和世界之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明之间的借鉴、交流和共享,而非封闭、对抗和自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海洋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