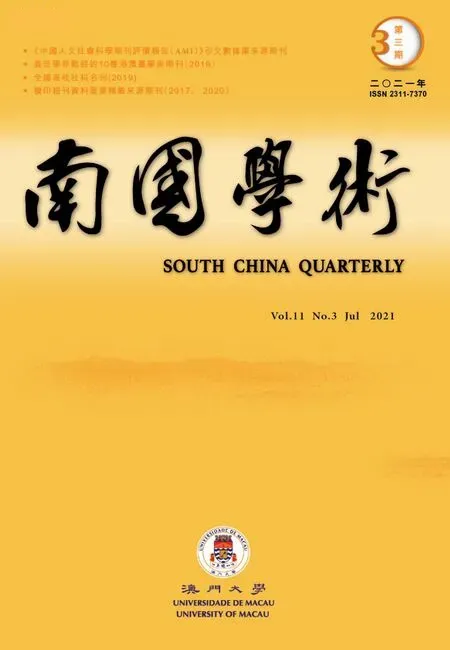臺灣﹑香現當代文學與圖像關係史論
黃萬華
[關鍵詞]臺灣文學 香港文學 文學與圖像關係史 文學思潮 社會媒介
在當今中國文學界、藝術學界,文學與圖像的關係日益受到關注,已從文圖關係史的梳理①2020年12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趙憲章任總主編的《中國文學與圖像關係史》(8卷10冊),可以說是該領域研究的重大收穫,但尚未包括中國現當代文學部分。、作家畫家個案研究、文圖關係理論建構三個方面展開。而如何避免以往理論優先於實證的弊端,是目前中國文學與圖像關係研究中需要重視的問題。因爲,“文圖關係”是作爲20世紀以來現象學、存在論等西方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影響的,因此,從梳理、分析中國文學與圖像的材料和文獻出發,細緻辨析包括文學圖像元素、圖像形式、圖像譜系等的史料,不僅有可能抵達以往單純的文學研究未抵達的廣度和深度,也會以中國文學與圖像關係的豐富資源展開與西方現代文圖理論的平等對話,從而進一步建構、豐富現代文圖理論。從這意義而言,對文圖關係史的梳理將是文圖關係研究的基礎。這正是本文梳理臺灣、香港地區現當代文學與圖像關係史的出發點。②筆者也曾詳盡梳理過澳門文學的史料。明清時期澳門文學的源頭及其後的舊體文學都有詩畫交融,澳門現當代文學在1950年代也開始孕育地域文學的本土性,但1980年代前文學作品的發表、出版等對香港文壇依附性大;1980年代後,澳門文學在澳門本地發展很快,其文圖關係在展示保存東西方古典風格的城市與周圍多未開發而充溢大自然元氣的小島的豐富圖景中展開,但仍較爲單一。整個澳門現當代文學還較難提供足以構成“文圖關係史”的資源,故此,澳門文學暫未納入本文。
臺灣、香港文學的歷史以現當代文學狀態爲主,其文學圖像種類豐富,包括圖像詩、詩配畫(水墨畫、銅版畫、油畫等)、文學雜誌插圖、小說等文學作品插圖、戲劇戲曲圖像、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文學(家)紀錄片、現代傳媒(攝影、廣告、電子媒體等)中的文學圖像、跨藝術媒介文學圖像(如與舞蹈、時裝設計等合作的詩歌)、其他語圖合一的創作(如繪本)等,既有大量以文本造型爲主的文學圖像,也有衆多由文本轉化爲圖像藝術的圖像文學;在內容上,既有中國古代文學圖像的現代再現(尤其是現代影視對古代文學名著的改編),更有臺灣、香港社會百年歷史和現實生活的豐富呈現。它們將文學帶入了更廣闊的藝術變革天地,也提供了豐富的現代文圖經驗,孕育着現代文圖理論的中國形態。
一 臺灣﹑香現當代文學圖像與中國古代文學
中國文學與圖像的關係有着自身的演變,這種歷史延續性使得每一個時期的文學圖像都有着此前文學圖像的重現,既表現出這一時期文學與此前文學的聯繫,也反映出文學在新的文學思潮、新的媒介傳播形態中的變化。中國古代文學透過臺灣、香港現當代的文學圖像媒介環境得以重新表現的內容極爲豐富,不僅呈現了臺灣、香港文學與中華文化傳統的血脈聯繫,也奠定了臺灣、香港現當代文圖關係、文圖理論的一塊重要基石。
臺灣、香港的中國古代文學的現當代圖像呈現極爲豐富。以香港爲例,早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人筆下便已經出現‘香港’這個名稱了”③葉靈鳳:《香港的失落》(香港:中華書局,2011),第175頁。,而“香港”恰恰首先是通過舊體文學進入中國文學的。香港被割讓十餘年後,逐漸形成商業城市,途經香港的文人士子,如魏源、黃遵憲、何紹基等都曾以“香港”爲題賦詩作文。同治元年(1862),爲逃避清政府通緝而居住香港二十年的王韜(原名王利賓,江蘇長洲人)則是第一位內地居港的文人,也是香港開埠後第一位漢語寫作的作家,“被封爲香港文學的鼻祖”④黃仲鳴 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 •通俗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第47頁。,其舊體詩文和傳統筆記體小說開啓了香港文學⑤黃萬華:《百年香港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第2頁。。之後,香港舊體詩文創作綿長而豐碩。據不完全統計,香港寫作舊體詩文的人數超過1700位,至少514位作者出版了808種舊體詩文集。⑥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第9頁。而詩社興盛的局面使舊體詩文的傳播始終有着一定的空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海外吟社、香海吟社、北山詩社、正聲吟社、香港書畫文學社、千春社等著名詩社互相唱酬,到戰後的碩果社、健社、嶺梅詩社、青社、風社、春秋詩社、披荊文會、南薰詩社、錦山文社等諸多詩社前後呼應,結社唱和風氣始終不減,一些詩社壽命之長,令人驚訝。例如,成立於1950年的健社一直活動至21世紀初。詩社的中堅力量,從南來文人爲主轉變到香港本土詩人,而1980年代後“活躍於香港古典詩詩壇的人,有不少是二三十歲的後起之秀”①鄧昭祺:“雕磨璞玉 剖析毫釐——讀董就雄《聽車廬評點璞社詩》”,《文學評論(香港)》44(2016)。。由此反映出,以舊體文學創作倡導傳統文化,始終延綿不斷。即便在新文學崛起之後,舊體文學也始終能在香港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②黃萬華:《百年香港文學史》,第13頁。。這自然密切了香港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係,古代文學的圖像再現成爲香港現當代文學圖像的重要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0年代,是香港文學開始自立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在“冷戰”背景下,香港左右翼陣營對峙分明,然而,“左右兩派文人,卻同有濃厚的中國情懷,左翼着眼於當前,右翼着眼於傳統,但同樣‘根’在中華”③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 等:《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 •三人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第18頁。;到1960年代,右翼堅持的民族意識與左翼提倡的愛國情操交匯合流,“超越了美蘇的意識形態”④古蒼梧:“美雨蘇風四十年——也是一個體驗層次的回顧”,《八方文藝叢刊(香港)》7(1987)。;一些本土出身的作家更超越左右翼對峙政治的層面,追求國家、民族、本土的文化建設。這使得戰後二十多年中,香港取代了中國大陸扮演了“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承的角色”⑤潘碧華:“香港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1949—1975)”,《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2000)。。例如,當時被視爲右翼文化陣營的重要文化刊物,包括創辦於1953年的《祖國週刊》,針對學者和大學生的《大學生活》,以青年文學愛好者爲對象的《中國學生週報》,少兒讀物《兒童樂園》,都無一不以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爲重點。其中,影響廣泛的《中國學生週報》一向被視爲“美元文化”的產物,但實際上它一開始就自覺定位於“發揚中華文化,闡釋民族大義,承續三四十年代的文藝傳統,與讀者共同體認文化民族的血緣關係”⑥本社:“負起時代責任”,《中國學生週報》1(1953):25。,而它“爲海內外全體中國學生服務”⑦盧瑋鑾:“從《中學生》談到《中國學生週報》”,《香港文學》8(1985)。的宗旨,使它不會被東西方對峙的意識形態牽着走,堅持傳承、弘揚的“是一種殖民地教育所欠缺的愛國精神。不是狹隘的愛國,不是時髦的愛國,而是深植於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血脈關懷”,甚至其政治立場也決定於此。很多南來文人還紛紛參與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寫,並且“每年都檢查我們的教科書,看看裏面有沒有殖民地的奴化教育”,“認爲沒有英國那些奴化教育……而且有教一些中國文化,這樣纔比較放心”⑧熊志琴:“黃震遐與沙千夢——黃百合憶談父母”,《文學世紀》40(2004)。。這種中國文化情結,成爲香港文學自立的重要基礎,也必然讓中國古代文學在香港得到多方面的現當代圖像呈現。
臺灣文學也是如此。舊體的漢文詩在臺灣被殖民時期始終不絕如縷,並開啓了臺灣新文學的先聲。新文學興起之後,古典詩文在整個日據時期一直保持強盛之勢。⑨黃萬華:《多源多流:雙甲子臺灣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第1—5頁。臺灣光復後,大部分作家始終抱持臺灣與大陸血緣史緣皆不可分的信念,中國文化傳統得到較完整的傳承。
古代文學的現當代圖像呈現往往採用新的媒介形式,其經典性圖像首先在漫畫和電影中呈現。前者依然是個人繪畫作品(圖文體),後者則完全是新媒介表現的成果。而正是它們,開啓了面向香港、臺灣民衆的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現當代圖像呈現。
源自日本的漫畫在1920年代就被臺灣畫家採用,到1940年代中國漫畫成熟時,香港、臺灣的漫畫不約而同進入了兒童文學領域。1941年,留學美國獲教育學博士學位的曾昭森在香港創辦《新兒童》半月刊,實踐其“兒童爲中心”的現代教育理念⑩霍玉英 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 •兒童文學卷》,第48頁。,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停刊,1946年在港復刊,成爲當時影響很大的兒童刊物。1947—1948年,《華僑日報•兒童週刊》《大公報•兒童週刊》《星島日報•兒童樂園》等衆多兒童副刊紛紛在香港有影響的報紙創設,所刊漫畫突破了傳統童趣詩畫的成人觀,也走出了1920年代後中國漫畫的“政治趣味”“社會趣味”,努力走進兒童的心靈世界。例如,《星島日報•兒童樂園》所刊豐子愷的《爸爸吃蛋糕》《西瓜藝術》《山歌》《小弟弟遠足》《我愛人,人愛我》等具有連環畫性質的漫畫,都在十足的兒童趣味、兒童想象中,將漫畫的人神交遊、幻想與現實同存中而產生風趣、幽默、詼諧的藝術效果發揮得淋漓盡致;其文字也根植於兒童世界,讓兒童在自己的世界中認識生活,深受兒童喜愛。這種成功,使一些漫畫家開始嘗試兒童文學與古代文學經典的“互文”。1951年左右,兒童漫畫開始在臺灣流行。1953年,《學友》刊出臺灣第一部長篇連載兒童漫畫《三藏取經》(作者泉機,本名陳定國),廣受歡迎,被視爲“首開兒童文學與文學經典的互動”。此前,王朝宗已出版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爲內容的漫畫連環畫,由此被稱爲“臺灣漫畫的第一人”;而此後,陳定國、錢夢龍、葉宏甲、劉興欽等都致力於兒童漫畫連環畫創作,陳定國、錢夢龍兩人更專注於古典文學的兒童漫畫呈現,其不同的繪畫風格、繪畫技法、漫畫角色和所配文字均“返歸”兒童心理、趣味和視野來呈現圖文互涉,在兒童本位中表達文學關懷。這股兒童漫畫創作潮流昭示出,古代文學的現當代圖像呈現往往發生於現代理念與新的圖像方式匯合中。
自然,漫畫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圖像呈現並不限於兒童漫畫,所體現的現代理念也不限於兒童教育理念。例如,陳定國長篇連載漫畫《呂四娘》(1953)、《孟麗君》(1954)等被稱爲“女性漫畫”,表現女性的觀念類似現代女性文學,圖像呈現上讓文、圖充分互補,發揮各自的藝術表現之長。以《孟麗君》爲例 ,幾乎每幅畫面都配以較長篇幅的人物對白、旁白,讓文字的聽覺想象與畫面的視覺形象相得益彰。孟麗君的故事原本出自清末才女陳端生的彈詞作品《再生緣》,陳定國漫畫首創鳳眼美女的造型用於《孟麗君》,凸顯其嫵媚中的英氣、俠義,所撰對白、旁白令人“如見其人”,兩者呼應,清晰、生動地講述了孟麗君抗衡權貴,女扮男裝,五度成功隱瞞女性身份,最終實現了自己的追求的故事,將孟麗君勇氣、機敏過人的性格和巧思妙想、能言善道的言行表現得栩栩如生,成功塑造了一位獨立自主、智勇雙全、情義皆深的女性形象。
更大規模的古代文學的現當代圖像呈現發生在電影故事片這一新媒介中,通過電影,中國古代文學母題在臺灣、香港語境中得以延續、豐富。1950年代,香港“取代”上海成爲華語電影中心,而20世紀四五十年代正是中國電影的成熟時期。此時期,南來電影人在香港電影界佔主導地位,其情感傾向、價值尺度都使他們青睞中國古典題材。從1950年代的《貂蟬》《江山美人》等,到1960年代的《楊貴妃》《白蛇傳》《王昭君》《梁山伯與祝英台》等,這些當年轟動華人世界、如今可視爲經典電影的作品都出自以趙樹燊、李翰祥、胡金銓爲代表的南來電影人創作。由此形成的古裝戲電影浪潮,還直接影響了臺灣電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圖像呈現。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臺灣就有了第一部紀錄片電影,但劇情片的拍攝則遲至1940年代,而其高潮正是在受到香港古裝戲電影浪潮衝擊,從而開啓古典題材的改編中來到的。李翰祥、胡金銓分別於1963年末和1967年來到臺灣,與臺灣同行共同從事古裝電影創作。他們與後來的王菊金、侯孝賢等,通過中國古代文學的電影影像成功進入世界影壇,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也爲中國古代文學的現當代圖像呈現提供了珍貴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於古代文學的現當代圖像呈現採用了電影這一新的媒介形式,古代繪畫的影響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古代繪畫畫類、技法等的延續,而表現爲古畫審美趣味、藝術韻味等的影響;這種影響又總是整體的、深層的,電影人往往會通過古代繪畫去感受、瞭解古代,這直接影響到他們對“古代”觀念的形成、變化,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構圖方法、風格,成爲一部古裝戲影片最重要的古代背景,而觀衆也往往通過由此產生的影片風格、情調去遙想古代。
李翰祥早年在北平藝專時專攻西洋畫,卻對中國古代文人畫情有獨鍾,格外欣賞。他對中國古代的許多觀念,“是從古畫而來,枝葉掩映,山澗松泉,雕欄園林的趣味,基本在中國文人畫中散發出怡人的韻味”,“這種國畫的幽情”在李翰祥的“電影中發展出抒情的構圖風格”。①焦雄屏:《改變歷史的五年》(臺北:萬象書局,1992),第83—84頁。從李翰祥在香港執導的《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第二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獎),到他赴臺後拍攝的《七仙女》(1964)、《西施》(1965,第三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等,這種抒情的構圖風格得到多方面的發揮。其電影修辭手法多是詩畫融合,巧妙而成功地借鑒了古代文人畫,尤其是山林雅集圖式。
胡金銓從小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全面而系統,其創作和構圖風格指向了道家、禪宗,由此溝通了胡金銓影片與中國繪畫的深層次聯繫。因爲,中國畫論、繪畫從哲學到方法,都傾向於道家、禪宗。取材於《聊齋誌異》的電影《俠女》(1975,臺灣上映時分上下集,下集曾改名《靈山劍影》,2015年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爲“百部不朽電影”之一),不僅在劇本寫作上融入了原著未涉及的禪之意涵①梁秉鈞:“胡金銓電影:中國文化資源與六○年代港臺的文化場域”,《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2007)。,更在影片構圖上傳達出禪韻。它獲得第28屆戛納電影節“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就是因爲影片處理畫面的成就得到了世界影壇的承認。在影片中,抒情場景如月夜彈唱等,有如一幅幅中國傳統山水畫;寫意和留白,使空間感充滿幽遠玄妙的古意;武者相鬥的場景,常常處理成空靈甚至抽象的畫面;竹林飛舞的實戰畫面,更拍成天機乍現、高僧飄然而下;在鄉野文人、民間義士所代表的儒、俠之外,爲劇中人指點超塵入聖的出路。全片絲毫沒有日本武士片的陰鬱,卻充滿東方藝術超凡脫俗的精神。《空山靈雨》原本就取材於禪宗六祖慧能的故事,影片中那段老住持智嚴以“打水”考三個弟子,三弟子慧思坦言“心清水自清”的戲,顯然化用了六祖慧能“菩提本無樹……”的禪宗典故。而在將五祖弘忍傳衣缽予樵夫慧能的故事改編成一個圍繞衣缽和經書的爭奪,佛門內和江湖上都充滿鉤心鬥角的武俠影片時,胡金銓糅合傳統繪畫與現代影像處理動靜關係的手法,讓畫面在武鬥之動與禪理之靜中傳達超越一切世俗價值觀的精神。例如,在刀光劍影的爭鬥場景後,老住持將衣缽傳給外來流犯邱明,而人品、學識都理當繼承住持之位的慧思卻欣然坦然地爲邱明披上袈裟,畫面動靜傳遞之中呈現“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禪境。胡金銓通過電影影像讓中國古代文學走向世界,1987年入選美國《時代週刊》“國際最出色50位導演”,從而在國際影壇上被視爲同代華人導演中成就最高的一位。
中國古代文學的現當代影像呈現在臺灣1970年代後的“新電影浪潮”中得到延續。王菊金執導的《六朝怪談》(1979)取材於《搜神記》等,成爲中國第一部參與奧斯卡外語片競賽的影片。“新電影浪潮”中最有影響的侯孝賢,拍攝故事片時與作家密切合作,其《海上花》(1998)、《刺客聶隱娘》(2015,第68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改編自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唐傳奇《聶隱娘》,充分體現出“新電影”專注人文關懷、創新電影表現手法的特點。例如,《刺客聶隱娘》在大幅度改寫裴鉶原著內容時,刪除奇幻、道術等場景,以寫實的影像風格表現聶隱娘孤寂中的命運。在拍攝上,發揮“長鏡頭—蒙太奇美學”技巧的長處,巧妙轉化文學意象。例如,在原著中聶隱娘與磨鏡人相遇的情節基礎上,強化唐傳奇中的“鏡子”意象,包括由長安遠嫁的嘉誠公主對聶隱娘講述“孤鸞照鏡”的故事,其孿生姊妹嘉信公主卻是帶聶隱娘習武復仇的道姑,最終讓聶隱娘走出孤絕的磨鏡少年是僑居的倭國工匠等情節,都有含意豐富的“鏡子”意象,通過長鏡頭的多種組合,將聶隱娘掙扎而走出“刺客”的孤絕這一過程表現得起伏跌宕、發人深省,引發觀衆思考人如何面對寂寞、孤獨。
即便限於篇幅,不再述及電視劇、多媒體等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圖像呈現,也足以揭示臺灣、香港現當代文學圖像與中國古代文學的密切聯繫。這種聯繫多層面的滲透,使得臺灣、香港現當代文學圖像的呈現背靠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而向現代開放,甚至可以進入東方美學精神的境地。
二 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早期的香文學與圖像
如果將臺灣、香港現當代文學的歷史和傳統置於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背景中審視,大致可分成三個時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前的“早期”,194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的戰後時期,1980年代後的三十餘年。②參見黃萬華:《多源多流:雙甲子臺灣文學(史)》《百年香港文學史》。這三個時期,大致對應了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的三個時期(即民國、共和國頭三十年和後三十餘年),但更反映出臺灣、香港文學自身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傳統。
臺灣、香港的舊體文學一直與新文學相容共存,傳統的詩畫關係也得以延續。例如,《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 •舊體文學卷》就收有題畫詩,臺灣日據時期衆多漢詩社所留詩作以山川風物爲主,也時見題畫詩。但對於臺灣、香港而言,更有意義的文圖關係發生在白話新文學的誕生與圖像的現代變革幾乎同時產生中,於是有了文學與圖像變革的共生現象。
這方面首先值得關注的是詩畫互文衍生①臺灣學者須文蔚在討論臺灣當代文學與圖像關係時提出,文學研究上探討“互文”現象,通常描述的是前後發表的文學作品之間,有着相互承繼與影響的文本交互現象。而在探討文學與圖像關係的歷史時,可將文本的互文關係,擴大到文學與美術作品之間,更能呈現文學發展的歷史與現實因素。。在現當代文學發生、發展進程中,尤其是文學轉型的重要時期,作家、畫家處於同一種文化思潮中,互相探討新的美學觀念,互相激蕩出新的藝術探索,詩與畫各自從對方吸納藝術元素、交互影響從而產生新的詩畫。這種詩畫互文衍生主要發生在一些“棲身”於文學和繪畫兩個領域的創作者(包括美術出身的作家、文學創作出身的畫家以及詩畫都擅長者等)的詩畫創作、作家所寫畫論等情況中,也發生在文學界與美術界的諸種直接交流、互相聲援中。這些都直接密切了文學界與繪畫界的聯繫,甚至結成了文藝同盟,文學變革與美術變革同時推進。
這種“同盟”關係在臺灣日據時期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一時期,臺灣現代文學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發生、發展,其殖民語境中的命運凸現了保存民族文化、維繫民族血脈的至關重要性。日據時期,臺灣現代文學的中心課題表現爲“鄉土文學”創作的展開。臺灣新文學誕生後,“鄉土文學”被作爲對抗日本殖民“同化”政策的“臺灣”想象共同體提出,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現實批判精神,在二三十年代又明顯具有左翼思潮傾向。而恰恰在這一文學命題上,臺灣作家與畫家結成最密切的同盟。
1920年代,臺灣第一批新文學作家登上文壇之時,臺灣畫壇也有了第一批接受包括西洋畫、東洋畫在內的現代美術教育的新美術創作者。作家、畫家不僅以各自的藝術形式呈現地方鄉土特色的臺灣人事圖像,以此表達現實主義精神,而且有組織地展開交流,互相從對方的藝術觀念、美學追求中汲取營養,促進自身創作。從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臺灣新文化運動興起後,這種新文學與新美術的交匯就已經開始。到了1930年代,新文學作家與畫家結盟的自覺、密切已經是中國文學史上少見的。畫家用西洋美術(風景寫生、雕刻、油畫等)技法創作臺灣地方風情、習俗、景物、人物的美術作品,在1920年代初就有了“成功”之作②1920年,二十五歲的黃土水創作的原住民題材雕刻《蕃童》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之後出現了一大批表現臺灣人生活,具有熱帶海島特色的美術作品。,或者可以說,臺灣美術界表達對臺灣“鄉土”的情感認同早於新文學界。但從1920年代臺灣第一個統一的現代畫社“赤島社”(由臺北的“七星畫壇”與臺南的“赤陽社”合併而成)自覺地以“藝術”展現“鄉土臺灣島”之“生活就是美”③葉思芬:“英雄出少年──天才畫家陳植棋”,《臺灣美術全集•陳植棋》(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5),第14卷,第34頁。的努力開始,他們就面臨被殖民體制納入“地方特色”“異域情調”的困難局面。美術作品需要通過畫展得到承認,而臺灣畫展被掌握在殖民者手中④臺灣畫展始於1927年的“臺灣美術展覽會”,到1936年,已舉辦十屆,主辦單位和主要成員都有臺灣總督府的官方背景,1937年後更改名爲“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削弱了美術界對殖民政治的抵抗性。著名畫家陳澄波當時曾發表《將更多的鄉土氣氛表現出來不可僅熱衷於大臺灣畫壇回顧》一文⑤顏娟英 編:《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510—511頁。,就是呼籲畫家們走出官方美展,去表現臺灣“鄉土”。在這一背景下,臺灣美術界與反抗性強韌而豐富的新文學界的聯盟更爲迫切。1930年,王白淵、張文環、吳坤煌、巫永福、翁鬧、施學習、吳天賞、賴慶、王登山、吳希聖、楊基振等重要臺灣作家和畫家參與創立的臺灣藝術研究會及其刊物《福爾摩沙》,是第一次跨藝術的聯盟(重要發起人王白淵是畫家出身的詩人,後又以美術評論聞名),“不俯順褊狹政治和經濟”,創造“真正臺灣人”所需要的“鄉土藝術”①《福爾摩沙》(フォルモ—サ)創刊号發刊詞“檄文”,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69—70頁。,成爲文學與美術的共同追求。1934年成立的臺灣文藝聯盟,聚合了臺北、臺中、臺南幾乎全部有影響的作家,也囊括了當時臺灣本土美術界重要的優秀畫家(包括“臺陽美協”“七星畫壇”“臺灣水彩畫會”“赤島社”“栴檀社”“六硯會”等重要美術社團的主要成員,不乏臺灣現代繪畫名家大家)。該聯盟的機關刊物《臺灣文藝》(1934—1936年共出版15期)每期刊出的繪畫和畫論之多,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時期刊物中都是少見的。而此時,正是臺灣文學界鄉土文學倡導和討論取得共識之時,這場日據時期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學論爭(1930—1934)寓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現實批判精神,推動了臺灣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形成。而當臺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詩畫聯盟”出現於《臺灣文藝》時,表現“這個島最赤裸真實的面貌、發揮鄉土特色”②編輯部:“二言•三言”,《臺灣文藝》7(1935)。的創作,成爲作家和畫家共同的不二選擇。活躍於《臺灣文藝》上的是賴和、楊逵、張深切、張文環、巫永福、翁鬧、朱點人、呂赫若等最有影響的臺灣作家,《臺灣文藝》刊出的繪畫則出自陳澄波、李石樵、廖繼春、顏水龍等著名畫家。他們互相呼應,共同抗衡殖民者“地方色彩”的藝術導向(削弱變革現實訴求,粉飾“太平盛世”,頌揚殖民文治等),強調以臺灣在地的主體意識,表現具有臺灣時代性的鄉土人事。相關的論述自覺地將文學與繪畫相連,如《臺灣文藝》第2卷第2號的《編輯後記》就論及近期《臺灣文藝》的文學創作呈現鄉土色彩的走向,而對此支持的畫家們也都畫出臺灣的風景。③“編輯後記”,《臺灣文藝》2(1935)。
這裏還需指出的是,“鄉土”作爲殖民統治下被殖民者對養育自己的家園土地的守護,超越了當時左右翼政治的分歧,成爲日據時期現實主義文學藝術的核心價值。臺灣的反殖民政治鬥爭,一直存在左右翼政治的歧異。但不管是左右翼政治力量聯合時期還是分裂時期,文學界、美術界自身或聯盟在深刻表現“鄉土”這一題旨上始終是共同努力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和美術取得的成就,就是從此出發的,而詩畫互文衍生也發生在這種現實主義文學藝術思潮中。
文學與美術“結盟”的詩畫互文衍生的意義在於,文學與美術兩大類別的互相滲透、吸納。對於文學與圖像的關係,歷來有“異質”和“相通”兩種認識。詩畫互文衍生在“詩”與“畫”的直接交流中,“詩”與“畫”各自從對方藝術探求中獲得啓發,吸納變革因素,揚長避短,豐富自身,發展出同一藝術變革潮流中的不同面向,會不斷推進人們對文學與圖像“相通”和“異質”的認識。這種自覺的交流又往往發生在同一社會思潮、文化思潮中,或爲求得藝術的變革、突破,或爲應對生存、發展的壓力,其結果必然使文學在變革、提升中更深地介入了“人”的生活。
正因爲如此,日據時期臺灣的文圖關係還從文學形態的兩端——大衆性的通俗文學和實驗性的現代主義文學展開,與現實主義的“鄉土文學”一起開啓了臺灣現代形象的建構。
臺灣通俗小說的興起,與日據初期臺灣報刊等大衆傳媒的發展密切關聯,自1896年6月《臺灣新報》創刊後,一些重要報紙都有漢文專欄連載小說。這些小說“大抵使用淺近文言爲之,且多採用章回體書寫”④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化想象》(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第249頁。,作者皆爲傳統文人,其插圖等類似傳統章回小說。1937年,臺灣殖民當局實行戰時體制後,漢語的新文學都在查禁之列,唯有傳統文人所辦的通俗刊物《風月》還能刊行,而《風月》延請新文學作家(徐坤泉等)加盟,又聘請現代畫家(林玉山等)爲連載小說作插圖,成爲“囊括並接收新舊文學與書畫藝術的創作者與讀者市場”。⑤柯榮三:《雅俗兼行——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概述》(臺南:臺灣文學館,2013),第34頁。此時的插圖尋求現代社會讀者喜聞樂見的漫畫、速寫等多種形式,與通俗小說的敍事相呼應,將民間傳說、言情故事等的現代意味(例如,社會嘲諷)表達出來,有了許丙丁《小封神》那樣圖文並茂的成功之作,也成爲殖民統治下民衆心聲的抒發。①許丙丁的長篇《小封神》曾於1931年、1938年兩次連載發表,後又於1951、1956、1959、1987等年份多次出版。其“構作內容,概取臺南諸寺廟及街談巷議”,將臺南大上帝廟、小上帝廟、媽祖宮、關帝廟等供奉的神明串在一起,鋪衍成這些臺灣民衆所熟悉的神仙的“現代”遭遇,故事情節“推陳出新”,詼諧幽默,趣味十足,敍事中圖畫性描述與可視性塑形比比皆是,而小說卷首的八幅漫畫,以惟妙惟肖的小說人物形象,配以簡潔生動的敍事語言,提綱挈領地將整部小說情節的起伏與轉折、小說主題的諷喻及刺虐展露無遺。
對於現代文圖關係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現代主義文學引發的變化。以往人們忽視的是,中國現代派小說最重要的成員之一劉呐鷗在臺灣一向被視爲臺灣作家②劉呐鷗1905年出生於臺灣,中小學教育完成於臺灣,學成於日本後赴上海,三十五歲離世,迄今最完備的《劉呐鷗全集》(6卷)也是在他家鄉臺南出版的。,他也是最早與電影結緣的現代作家,從1928年開始大量發表關於電影藝術的論述和譯作,到1936年加入“中電”,編劇,拍攝電影,其對電影的投入甚於小說,而其小說創作也成功地以電影手法速寫現代都市的超現實美感。劉呐鷗的現代派小說創作源頭與臺灣日據時期現代主義文學的源頭一樣,主要來自留日求學經歷。不同的是,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出現與殖民統治下的寫作狀態密切關聯。臺灣現代主義詩潮開啓於臺南的風車詩社(1933),而其發起人楊熾昌就是留學日本時接受法國超現實主義詩歌影響,而當他回到臺灣從事詩歌創作時明確意識到,“將殖民地文學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寫出”,臺灣文學纔能“開花結果”。③楊熾昌:“回溯”,《聯合報•副刊》1980-11-07。他連連發表詩論,較系統地提出了追求詩美,強調詩的探索性、主知性、世界性和語言、意象的新鮮性的現代詩主張,其中包含了溝通“詩美”與“繪畫美”的真知灼見。這纔有了臺灣現代詩對“主知”的追求,電影蒙太奇手法等也引入詩歌,呈現殖民地文學的“隱喻”世界。楊熾昌這一時期的詩集《熱帶魚》(1931)、《樹蘭》(1932)等往往以富有東方精神的語象構成別具一格、想象豐富的文學圖像,在意義的沈潛中表達詩人的心聲,讓人充分感受到現代主義詩潮對現代語圖關係的深化。
幾乎同時,現代詩看重知性而引起的文圖關係變革也在香港文學中發生,衹是香港文學更自覺地藉助現代都市媒介建立文圖關係。從文學創作層面而言,現代文學中的文圖關係,首先值得關注的是藉助圖像的視覺形象來傳達詩的知性感受。詩從浪漫抒情轉向知性表達,是中國新詩現代化進程中極其重要的一環,而以圖像的視覺形象增強詩的知性感受的嘗試發生於香港詩人的創作中,無疑與現代印刷術代表的都市媒介的影響密切關聯。鷗外鷗是香港早期詩人中最有創作實績的,他成就了香港新詩傳統的最初形成,而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他也被視爲“現代中國最具藝術個性和前衛意識的詩人之一”④嚴家炎 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50頁。。鷗外鷗將自己1930年代的重要詩作分別命名爲“香港的照相冊”“桂林的裸體畫”,表明其讓文學與圖像結緣的創作意識是非常自覺的,而這種結緣首先是對都市媒介的自覺。鷗外鷗詩作《第2回世界訃聞》(1937)、《被開墾的處女地》(1942),如今都已成爲香港新詩名篇。這些詩作正是藉助於媒介因素(如印刷字體的變化組合、廣播聲音的戲擬借用等),使文字(文學)具象化(圖像),提供了香港的第一批具象詩。鷗外鷗的這種具象詩(文字圖像詩),推動了詩從浪漫抒情轉向知性表達,也開啓了香港文學創作中的文圖時代;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語圖作爲現代性因素的影響介入新詩創作,避免了中國現代詩歌進程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可能發生的中斷。
鷗外鷗的詩歌也已明顯引入了電影視覺元素。例如,《軍港星加坡的牆——香港照相冊》(1936)在呈現香港城的面貌時,就“建立了引人入勝的頗具電影感的情節結構”⑤鄭政恒:“香港詩歌與半唐番城市生活”,梁秉鈞等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1),第190頁。,畫面感強,“鏡頭”式剪接自然,而且整節詩就如一部戰爭間諜片的開始,在日本人南侵和英國人防守的情節性對照中,不無懸念地呈現了香港這座原本充滿生命力的都市海港面臨戰爭時變幻莫測的命運。非詩意的現代語言在電影情節性畫面的展現中發人深省,從而產生詩意。而香港得影視風氣之先,從1920年代開始,就有文人投身電影創作,也較早發生了文學圖像向電影圖像的轉換。被稱爲“香港新文學作家中真正具有‘文學史’身份的第一人”①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第3卷,第231頁。的小說家侶倫就早早開始了電影文學劇本創作,他的小說成名作《黑里拉》也在1941年被他改編拍攝成故事片。電影形式的外來性,使侶倫小說改編成電影后更表現出外國文化的混雜性,而這正是香港文化的重要特徵。
三 戰後臺灣﹑香文學與圖像
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早期的香港文學與圖像關係,凸現了現當代文學與圖像關係中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文學(界)與美術(界)處於同一文化思潮中發生的詩畫互文,二是新的媒介介入。這兩個因素引起的文學與圖像關係的變化,構成了現當代文學與圖像關係史的基本綫索。
戰後至1970年代是臺灣、香港現當代文學發展極爲重要的時期,其文學與圖像關係也得到了深入展開。這裏試從從“思潮”與“媒介”兩方面擇要敍述如下。②黃萬華:《跨越1949:戰後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文學轉型研究(上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9)。
作家與畫家之所以結成同盟,或者說,之所以要關注詩畫互文,是因爲文學的變革不是隔絕而自足的。當它與各種視覺藝術、聽覺藝術在同一種文藝思潮中交互影響、相向而行,卻又發展出同一變革潮流中的不同面相、類型時,往往可以推進人們對人類藝術及其思潮的認識。而重要的文學轉型往往是在文圖關係的變革中得以完成、深化的。日據時期臺灣詩人與畫家恰恰是在臺灣現代文學的核心話題“鄉土創作”上結成同盟,共同推進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而戰後至1970年代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香港文學在這時期佔有重要地位。這時期香港文學所湧動的現代主義藝術思潮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意義重大,其中的詩畫互文更值得關注。
1950年代之後的香港現代主義藝術思潮是由兩股力量推動的。首先是從上海南來的文人,現代都市文圖媒介融合的文化環境養成了他們的藝術修養,一些人還積累有出入於文學、繪畫、電影等多個領域的經驗,如葉靈鳳、馬朗、劉以鬯、李維陵、羅斌等。他們自覺於以現代主義的開放性、自由度打破“冷戰”下的“政治掛帥”的“封閉性”,也以此提升文藝的品質。而他們倡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時,又自覺於“在推動一個新的文藝思潮之時,需要借鏡者甚多”③“編輯後記”,《文藝新潮》2(1956)。,重要的“借鏡者”就是打破常規,着眼於構圖、色調等所表現“無拘束範圍的完全自由,那絕不是強權所詆毀的墮落,而是現代藝術最升華的造詣”④馬朗:“封面畫家介紹:保爾•克列”,《文藝新潮》5(1956)。的現代畫。他們創辦或積極參與的《文藝新潮》(1956)、《香港時報•淺水灣》(1961)等,成了詩畫互文的園地。在這些文學刊物上,文論與畫論互相切磋,詩文和畫作圍繞現代主義藝術同一個話題同期刊出,甚至畫家出身的創作了廣有影響的現代主義小說(如李維陵的小說《魔道》),詩人出身的轉向現代繪畫(如王無邪)。《文藝新潮》等實踐現代主義文藝的水平之高,從日後人們“在街頭購到《文藝新潮》的舊刊”,都“驚訝之前香港有這麽高水平的文藝雜誌”⑤也斯:“現代漢詩中的馬博良”,《城與文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第187頁。,甚至被香港文學研究者認爲之後“四五十年過去了,還是沒有一本文藝雜誌可以比得上它的水平”⑥何杏楓、張詠梅:“訪問崑南先生”,《文學世紀》34(2004)。,可見詩畫互文的成就是其水平之高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進程中,還有一股力量得以成長、介入,那就是香港本土作家,尤其是青年一代作家。當時被稱爲“三劍客”的崑南、葉維廉、王無邪,一方面在《文藝新潮》《香港時報•淺水灣》等刊物上發表詩畫互文之作(例如,崑南注重空間性、凸現現代視覺形象的小說,葉維廉注重空間層次豐富、廣袤的現代詩等),三人合作的詩畫(往往是崑南、葉維廉作詩或譯詩,王無邪配以抽象表現主義等現代畫)更開啓現代主義詩畫互文的新形式。另一方面,他們又與香港本土青年同人盧因、蔡炎培、李英豪等創辦《詩朵》(1955)、《新思潮》(1959)、《好望角》(1963),成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1958),以青年人追求文學理想的熱情和銳氣展開反叛既有創作、突破傳統的現代主義文藝活動,其觀念和實踐都有包容“詩”與“畫”的自覺。例如,崑南認爲,存在主義的活力開拓了戰後西方文化的新天地,因此,“繪畫的抽象表現,漸達巔峰”,“戲劇與小說對於人性心理的刻畫,淋漓盡致,收穫不淺”,詩與畫都得到發展;他創作的小說,日後成爲香港小說中最具有先鋒性的。而葉維廉的現代文圖理論,萌生於他1950年代與後來成爲著名現代水墨畫家的王無邪展開現代主義詩畫“互文”的創作實踐,使他在中國傳統美學與西方現代理論的平等對話中成爲中國最早系統提出現代文圖理論的學者①黃一:“比較詩學視野中的葉維廉文圖關係理論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020)。。崑南、葉維廉、李英豪等成長於香港已開始形成的都市媒介、都市文化環境,他們的活動早於《文藝新潮》等的創辦,前後延續的時間又大大長於《文藝新潮》等的存在,表明其詩畫互文更深根植於香港土地,成爲香港文藝傳統的重要內容。
臺灣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湧動起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成爲突破國民黨主導的“戰鬥文藝”的主要途徑,且與香港的現代主義思潮“互援互助”。臺灣現代主義思潮濫觴於美術界②從1950年臺北“廿時間社”成立、創刊《新藝術》,1952年“新藝術研究所”在臺北成立,臺灣開啓美術現代化運動,倡導超現實主義繪畫創作和理論,要早於戰後臺灣現代詩運動。參見蕭瓊瑞:《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1945—197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從1950年起,臺灣有影響的報刊《聯合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文藝月報》等頻頻可見介紹西方現代畫派的文章。1957年創刊的《文星》在1960年代初掀起的那場關於現代主義文化的大討論,也是從美術領域開始而波及藝術各個領域。而臺灣作家與美術界“結盟”的狀況更爲引人注目。臺灣戰後第一個現代美術團體“東方畫會”與臺灣三大詩社中最早的現代詩社同在1956年成立,現代詩社的發起人紀弦則是美術出身,其現代詩派宣言糅合了現代詩學和現代畫論。翌年,在臺灣美術界最具前衛性的“五月畫會”與三大詩社中的創世紀詩社又同年降生,兩者成員社會經歷背景也相似。之後,這些臺灣最有影響的詩社和畫會直接結盟之密切、互動之頻繁在中國藝術史上極爲罕見,在那個年代則有相濡以沫之意味。例如,兩個畫會從1957年開始持續舉辦年度畫展,十餘年間得到詩社成員強有力援助,詩人寫畫論、評作品,與畫家合作詩畫作品,在畫家、畫作、畫展遭到政府、社會壓力時更是挺身支持現代畫壇。而詩人也從現代派畫中汲取藝術,提升自身,甚至由此完成自己的藝術蛻變。例如,余光中1960年代寫過數篇有影響的長篇畫論,探討梵高(V.W.V.Gogh,1853—1890)、畢加索(P.Picasso,1881—1973)、布拉克(G.Braque,1882—1963)等西方現代畫家的形式開創和藝術觀念,被視爲“余光中走向現代的開端”③徐學:《火中龍吟:余光中評傳》(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第110頁。。同時,他又針對五月畫會的畫展撰寫大量評論,在評介五月成員糅合國畫和西畫藝術元素中創作的抽象水墨畫是“回到東方”而又走向“現代”④余光中:“樸素的五月──‘現代繪畫赴美展覽預展’觀後”,《文星》56(1962)。。而余光中在文學創作中也有效展開詩畫互文的實踐,他自言其詩歌句法“同工”於繪畫“畫黑留白,不畫如畫……黑呼白應,如魄附身,充分把握住了東方玄學的機運和二元性”⑤余光中:“偉大的前夕──記第八屆五月畫展(上)”,《聯合報》1964-06-17。,他在散文寫作中更直接採用了現代畫與其文相配的形式。
現代主義思潮所推動的文圖新關係在臺灣小說、戲劇等敍事領域也得以推進。臺灣現代派小說中的兩名最重要成員白先勇和王文興,前者早早與“五月畫會”成員密切交往,其小說開創了一種獨特的“圖像寫作”——有着豐富的意指,將自我鏡像從“圖像”轉化爲文學形象的創作,由此走出傳統寫實主義,將小說導向更爲深邃的意指空間⑥陳雲昊:“論白先勇小說的圖像寫作”,《華文文學》2(2018)。;後者的長篇小說將漢字的形象、書法、音韻等充分調動,來開掘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出現代主義的形式追求在文圖關係變革上所能抵達的深廣度。戲劇方面,六七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姚一葦諸多劇作表明,臺灣戲劇已進入強調劇場(舞臺)視聽印象與意象的“導演劇場”①王友輝:“姚一葦研究綜論”,《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21 姚一葦》(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第76頁。,拓展了圖像從“靜態”向“動態”轉化的藝術空間。
幾乎與此同時,文圖影響在文學的現實主義流變上也日益明顯,其深化現實主義的作用往往藉助於跨媒介實現,而以電影的介入最爲明顯。例如,1950年代前期的香港小說,尤其是香港寫實小說,廣泛借鑒電影畫面的各種手法來增強其被社會大衆接受的程度。例如,侶倫早早雙棲於小說、電影創作,其戰後最重要的長篇小說《窮巷》(1952,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在社會寫實中嫺熟化用電影構圖、組接手法,成爲最早“全面深刻寫香港現實的作品”②柳蘇:“侶倫——香港文壇拓荒人”,《讀書》10(1988)。。舒巷城的小說“最具香港的鄉土特色”③梁羽生:“舒巷城的文字”,《南洋商報》1982-09-27。,其成名作《鯉魚門的霧》(1950)講述香港貧民窟鯉魚門漁民遺腹子梁大貴“出走—歸來—離去”的故事,後出有水彩畫的“圖文本”,成爲“文圖轉化”的範例。報刊在連載這些小說時,往往每期都配以插圖,每期插圖多幅時已類似“連環畫”。值得關注的是,此種作家與畫家的合作同步進行,他們都必須適應報紙連載的形式,及時得知讀者觀感,調整自己創作,以求得連載的延續,由此形成作家、畫家、讀者的多向互動。其中一些廣受歡迎的小說隨即會被改編成電影等,形成小說—“連環畫”(繪本)—電影(電視劇、舞臺劇)的多媒介參與的創作。這種文學作品二次甚至多次圖像呈現的過程從1950年代開始,到1960年代成爲臺灣、香港連載小說的一種常態,不僅讓小說在與受衆始終“對話”的過程中深化了現實主義的表現,而且不同圖像媒介、不同改編者改編同一部小說原著的差異性,往往啓動了小說文本在“文字閱讀”中易被忽視的意蘊(例如,小說隱含的多角度、多聲部敍事,在不同媒介“修正性”的圖像呈現中往往可以顯露),具有了文學史的“經典性篩選”功能。
臺灣、香港文學與影視等的聯姻發生在五六十年代兩地城市化進程中,成爲兩地大衆傳媒環境中城市文學傳統形成的重要環節。都市消費文化的生態促使堅守文學立場的作家探尋多層次的文學消費,強調與現實社會保持密切聯繫的現實主義進入了更爲開放的時期,而都市大衆媒介是其中重要的助力。被公認爲“對香港文學貢獻至深”④梁秉鈞:“《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書序”,《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2010),ⅸ。的劉以鬯就是在“賣文爲生”的生涯中,自覺藉助文圖,展開其稱之爲“開放的現實主義”創作的。他在其主編的報紙副刊進行形式多樣的文圖互文實踐(例如,邀約青年作者在副刊合作發表詩畫作品、親自設計副刊版式,尤其是配圖連載小說的版式),而他自己的創作從印刷版式與作品文本之間的“圖文”關係受到啓發,直接藉助於印刷文字“排列”變化中的“語象”擴展、增強小說的意蘊(例如,巧妙使用印刷字體的不同種類、色塊、排列等,顯露小說文本隱含的多重敍事),頗多成功之作(如“故事新編”《蜘蛛精》,長篇小說《黑色裏的白色 白色裏的黑色》,微型小說《打錯了》等)。這種利用漢字印刷字體多變的結構、排列的文圖寫作也發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臺灣。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現代圖像詩的創作潮流,它與古代圖像詩形式上最大不同就是成功藉助了現代印刷體多變的視覺形象,完成詩的知性表達,由此還形成獨立而有特色的詩學。這一創作潮流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之後的臺灣新世代詩歌。
現代舞臺劇提供的複合動態(舞臺聲光色形與演員身體的組合)圖像在影視技巧中得到極大豐富,並通過影視的觀賞複製性進入更廣大的受衆。多層次的受衆與影視圖像的審美多樣性構成的互動,促成各種文學形態進入影視改編後自身的豐富、成熟。1960年代臺港言情、武俠小說的勃興,1970年代臺灣鄉土文學的崛起,1980年代臺灣女性文學的再度興盛,都很快進入影視改編熱潮,“施爲”(動態)圖像世界無論在色調、筆法、構圖等表現上,還是在意象、空間、形象等構成上,都遠比靜態圖像豐富,使得“語象”與“圖像”交融越發深入,提升了通俗文學、鄉土文學、女性文學等的文學表達。
四 1980年代後的臺灣﹑香文學與圖像
1980年代,電視劇作爲新的動態圖像藝術大量出現,其大衆化、日常化的傳播方式很快吸引了文學界,以香港金庸、臺灣瓊瑤爲代表的小說改編爲電視劇,成爲影響廣泛的大衆文化現象。在文學與電影結緣基礎上展開的文學與電視劇的交流進入較爲內在的文圖轉換關係。1987年、1991年香港開拍的電視劇集《小說家族》,成功地將包括也斯《李大嬸的袋表》、西西《像我這樣一個女子》、鍾曉陽《翠袖》、劉以鬯《對倒》等香港現代小說名著改編成電視劇,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等現代小說因素成功表現爲電視畫面,從而使得“現代小說的探索,吸收了影視帶來的視野,也消化了它的表達的方式和附帶的觀念”①也斯:“文學和影視的對話(代序)”,《小說家族》(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7),第3頁。。文學的電影改編上,如臺灣的朱天文、香港的李碧華那樣雙棲於小說創作和電影編劇的佼佼者出現,將文圖對話帶入新境地。李碧華首部編劇電影《父子情》(1981)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首部長篇小說《胭脂扣》(1985)改編成電影後獲七項香港電影金像獎,之後《霸王別姬》等影片更有國際聲譽,而她的小說藉助影像的視覺性展開的越界書寫,已有爐火純青之感,語象的組合、呈現,將文字的形、聲、色賦予最大的視覺化,以致於電影可以完全忠實於文字而表現得完美。朱天文1982年開始與侯孝賢合作,多次斬獲臺灣電影金馬獎等獎項也已是作家與電影導演合作的佳話,但與李碧華小說視覺化的大衆觀賞小有不同。她將女性藝術思維的長處發揮得淋漓盡致,萬千顏色、氣味,極多變而差別細微的形態,原本極難描摹,卻被朱天文舉重若輕,一一穿插於小說中,而其指向往往是人物心理,對視覺藝術的主動接納使得她在“讀圖時代”遊刃有餘發揮文字的表現力。在這些人的努力下,電影影像的諸多新語法,諸如拼貼(collage)、文字的圖形化運用、蒙太奇、場面調度等都轉化爲文學敍事語法。同時,影視編導也從文學作品中汲取靈感和表達方式,提升影視藝術畫面的表達。例如,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對劉以鬯小說《對倒》的借鑒,是兩位大家心靈的對話,卻包含了影視向文學致敬的取向;而在臺灣,作家與電影導演共同成就了臺灣“新電影”。此時期,文字靜觀圖像與影視施爲圖像的互文,進入了文圖內在轉化而豐富的途徑。作家關注繪畫,更多的是如香港詩人王良和那樣,關注畫家觀看事物的方法。王良和詩集《火中之磨》《樹根頌》中的不少詩作都涉及羅丹(A.Rodin,1840—1917)的雕塑,就是意識到“羅丹的雕塑很有文學性,如從但丁的《神曲》汲取靈感,賦予雕塑複雜的內涵,他強調觀看事物要直達事物的靈魂,直達中心,里爾克詩的觀物方式與他相應”②梁志華:“細味記憶中的沉積與經驗——專訪王良和”,《文學世紀》16(2002)。。
此時期,後現代思潮的出現,引起文圖關係的新變化。後現代對各種界限,尤其是各種藝術界限的突破自然有助於文字與圖像的聯姻。早期現代主義強調形式的重要性,必然強調藝術的“純粹性”,其藝術文本的“自足”觀念會拒絕視覺藝術與語言文字的合作。所以,現代主義從形式主義的角度而言,某種程度地切斷了語言與圖像的藝術關聯。這種藝術“潔癖”有可能產生“雙重感染”,既影響作家寫作,也影響畫家等視覺藝術家的創作。此時,文學中的圖像影響往往主要表現爲圖像對作家創作的“內化”影響,而畫家也較少藉助詩與文字解說來拓展圖像空間。後現代時代的影響就在於其“不強調純粹”,多媒介的混合和多風格的並置突破了以往的藝術界限的突破,就有可能恢復並拓展作家和視覺藝術家的“雙向”合作,由此產生的“雙向越界”也是後現代背景下香港、臺灣文學與圖像關係深化的一個關鍵內容。
前述《文藝新潮》等開啓的香港現代主義詩畫“互文”孕育了香港戰後新一代作家。這批大致在1970年代成名的作家首先表現出多媒介時代的詩畫取向並有了重要突破,其中最重要的兩位,西西和也斯,都是在詩畫互文中“越界”而出的。西西在2006年臺灣《中國時報•開卷週報》主持的“香港城市作家”調查中,得票數超過金庸,成爲香港讀者認爲“更能代表他們”的作家,這自然是因爲西西更自覺地關注、表達香港經歷和經驗。其代表作《我城》(1975年報紙連載,1979年首版單行本)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就在於它非常自覺地以“城市”爲對象展開敍事,創意無窮的“西西”體也由此形成,而其源頭就“取法於電影和繪畫”。1960年代初,當“內地人忙於各種政治運動時”,西西就致力於從西方一流電影、繪畫中“尋求敍事靈感”①淩逾:“爲什麽要閱讀西西?——在西西作品展上的演講”,《城市文藝(香港)》60(2012)。,系統研究繪畫理論和電影手法。1963—1966年,她在《中國學生週報》發表了六十篇畫論,從世界繪畫變革中借鑒文學變革的思路。之後,她小說的結構、筆路、章法,所發前人之未發,往往就是跨界語圖之間的結果。而《我城》以作者百餘幅手繪插圖與文字互文展開的敍事,傳統長卷畫與現代電影手法的化用等,都使得“時間化與空間化的對立統一”“取得最優的狀態”。之後四十餘年,西西寫作創意滔滔不竭,文圖“互通”是重要的藝術源泉,轉化成小說敍事方式之豐富,是中國文學中絕無僅有的。而《我城》圖文溝通的文體創意綿延衍生,2005年,問世三十年的《我城》繁衍爲香港藝術中心集體創作的跨媒介藝術共生的《i-城志——我城05跨界創作》,小說、戲劇、繪畫、動畫、攝影一起來表現“我城”,包括香港著名作家潘國靈的中篇《我城05之版本零一》和謝曉虹的中篇《我城05之版本零二》,《我城》成爲香港城市文學傳統的重要內容。
也斯自述是在《文藝新潮》代表的1950年代香港文學熏陶下開始自己的創作道路的②黃淑嫻、宋子江、沈海燕、鄭政恒 編:《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書局,2013 ),第5頁。,而他被視爲從小說、詩歌、散文到學術隨筆乃至研究專著,都能講好“香港的故事”的第一人,圖文互涉是他創作不囿於任何規範,越界而成永恆的重要方面。他是最早表達自己在“後現代時代”的“詩與畫”信條:“快門”下“氾濫的”現代“影像”與“落霞與孤鶩”代表的傳統寫意畫像都要突破,但“什麽都可以,什麽都無所謂”的態度也必須摒棄(詩《大角嘴填海區》),而後現代詩觀對他的影響反而使他對詩與畫、意旨與意符不確定的多維關係中的藝術因素更爲關注,由此去更多地“發現”。他1980年代的詩集《游詩》就是詩畫合集,他也稱自己八九十年代的詩爲“游詩”,自然包含跨藝術媒介的對話、融合,所以他的詩作會直接與銅版畫、照片搭配展出(如《形象香港》等),也會直接藉助於形體藝術戲劇、舞蹈等演出(如《尋找一個詩人》),詩集《衣想》(1998)則是他與時裝設計師合作的詩與攝影集,後來更成功進行過創作詩歌的舞蹈、影像、吟唱演繹③“舞文誦影:都市綜合媒體對話”,《文學世紀(香港)》1(2003)。,在詩歌的越界游動上他是嘗試最多的一位作家。這種前所未有溝通文學與其他藝術,尤其是視覺藝術聯繫的創作實踐是也斯總在尋找新的、吸引自己也挑戰自己空間的表現。從1970年代讓他聲名鵲起的長篇小說《剪紙》起,也斯就持續不斷進入包括文體形式、溝通方式、編輯樣態、語言遷徙、符號互涉等在內的藝術形式的越界,進入以藝術通感跨越哲學、文學、歷史、美術、音樂、攝影、戲劇、建築、雕塑、電影、民歌、裝置藝術、民俗工藝、翻譯乃至種種流行體例的廣闊領域,甚至進入互爲狀態中的“情感越界”,在其所寫的人與人、人與城、人與物樸實升華的情感中最終回歸到“人”。這種“越界”創作使他成爲“爲數不多擁有真正現代世界觀的中國作家之一”,甚至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唯一一位用世界大同主義和與不同藝術互動對話,對世界藝術產生持續影響的華人藝術家”。④顧彬:“爲什麽要談香港的文學?”,《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香港:香港故事協會,2009),第51頁。
作爲1970年代後香港最有成就作家中的兩位,西西、也斯的文圖互文創作能在香港文學史中留下重要足迹,在於他們的努力都進入了香港城市文學傳統的建構中,其中對都市多元化媒介資源的敏銳開掘是其溝通語圖的重要途徑。而當1980年代後的數字科技時代出現,多媒體日新月異發展後,臺灣、香港的新世代作家幾乎無一例外地作出了積極回應。隨着現代藝術修養的增強,作家“越界”進入繪畫的增多。例如,臺灣作家杜十三,1980年代起,就在繪畫、音樂創作上斬獲頗豐,洛夫稱讚他以“映射與詩的婚媾”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散文文體”①洛夫:“映射與詩的婚媾——論杜十三的散文藝術”,《愛情筆記——杜十三散文選》(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第1頁。,就因爲他將自己的文學、繪畫、音樂、設計的創作實踐融合一體,其詩其文與聲光、音圖成爲完整藝術品。在香港,2002年,作家綠騎士《詩畫展——嘉年華•彼岸》那樣有影響的文圖展覽陸續出現。而更多作家,利用網絡多媒體,展開詩畫間更廣泛的對話。
臺灣新世代作家是將新世代“代”的崛起與網絡時代的跨媒介密切聯繫在一起,其“代言人”林燿德的理論主張最清楚地表明這一點。他將新世代的“時代精神”視爲掌握數字科技以展開“如何進行與世界的深層對話”,而其創作,比比皆有“計算機影像思維”的影響。平路的科幻、後設、解構小說,則在計算機視覺形象與小說形式的結合中,對人工智能時代人的命運表達文學關懷。更多詩人開設個人網頁,文學的展示平臺得以通過計算機極大擴展,“小衆”的詩歌藉助網絡世界的聲、光、色進入大衆視野,整合文字、圖形、動畫、聲音的多媒體多向文本改變了社會的文學生活,圖像、文字、音樂等原先各成體系的符號系統都具有了高度的媒體融合性,從而產生了新的文學形式。新世代的創造力與數字科技的開發力無疑將文圖關係帶入更有創意的境地,在諸多個人文學網頁爭奇鬥豔的同時,諸如“繪本”“作家紀錄片”等新語圖形式得到開發。前者仍是“靜觀”圖像,但有着現代都市圖像文學的活力;後者作爲“施爲圖像”,圖像與文學卻仍處於“協同”而非“僭越”的關係。兩者都在文化消費的城市環境中,促進了文學的傳播。
綜上所述,考察臺灣、香港百年來文學與圖像的軌迹,可以對中國百年文學展開一種較完整的論述,因爲它顧及了文學史脈絡的內(文學思潮等)、外(社會媒介等)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圖像作爲現當代文學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參與了中國文學現代性多方面的展開。百年來,無論在臺灣還是香港,現實主義的深化、開放,現代主義的興起、“突圍”,後現代的變革、超越,還有文學“在地”傳統的形成,都有着“圖像”的重要參與。而20世紀迄今的三大類媒介——現代印刷術、影視、多媒體的先後興起,成爲文學圖像變化最重要的源頭。對照於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圖像較多地受制於近代以來民族、國家、階級、政黨等觀念的變化,臺灣、香港地區的文學圖像更多具有文學民間的傾向,也使得它有可能突圍出政治運作的社會媒介意識形態,而它的經歷、經驗可以成爲建構中國現代文圖關係理論的重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