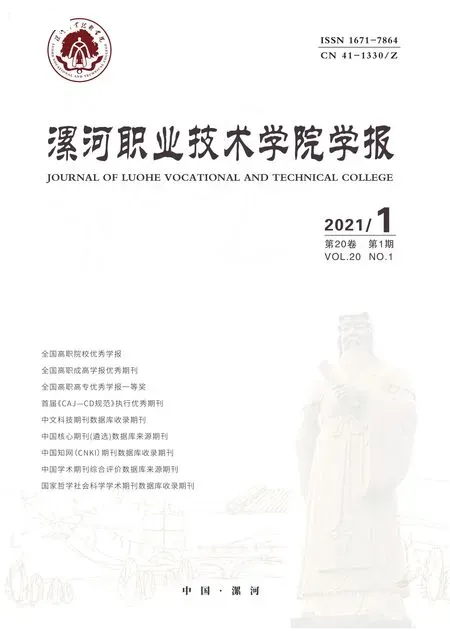意义与空无
——论海德格尔时间性视域下的两种世界
代 俊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海德格尔(以下简称海氏)哲学以“存在”主题贯穿,“时间”和“世界”始终伴随左右,他的时间和世界不再是基于形而上学的时间和世界,即海氏为流俗的时间和世界找到了根基。时间是时间性的整体到时,世界不再是机械的物的集合,而是此在展开的世界,与此在水乳交融,共为一体。从日常生活的有意义世界走向运思中的空无世界,便是走向存在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时间性的阐释
时间问题,如存在问题一样,一直是西方哲学绕不开的问题。海氏认为,存在一直被存在者遮盖,未得到昭明,是因为本源时间的拒绝与遗忘,即使哲学家们都自诩研究的是存在,一直以来,时间都是以物理学意义的面貌出场。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时间做了精确的解释,把时间作为“所计之数。”[1]18用一个场景对这个定义做形象化的解释:眼前有一串没有尽头的不断匀速运动的小球,一个小球消失了另一个小球来到了。到来一个小球,便记下一个数。眼前没有尽头的运动的小球,便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线性,无穷无尽,且只有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时间的长河”便是对这种时间观最好的理解。海氏认为,这种时间观,是抽离了具体生存内容的时间观,然而仍源于本源的时间,即使是本源的非本真时间。从古希腊开始,人们便根据运动的事物来理解时间,在时间中,运动开始或停止。运动的事物一定是处于关联中的事物,关联中的事物在非本真的时间里获得时间规定性,同时成为时间自我解释的参照系。人们根据事物作为某种存在者来确定时间,比如,人们理解了树木可以制作板凳,即把树木作为木材这种存在者,于是就能明白这样三段时间:不久就可以坐在板凳上休息,先前没有砍倒树木,现在要立即行动。这样的时间是充盈着生存内容的。没有了生存内容的时间即是本源时间的遗忘,这种遗忘导致了人们一贯的认知:时间和事物都是永恒自在的存在。
海氏看到自古希腊以来,本源时间的遗忘,又在康德的影响下,有了本源时间的觉醒,提出了时间性。时间性与死亡不可分,“时间性就是向死亡存在开出的。”[1]90死亡,需在现象学意义上理解,人们通常以自己的经验把死亡看成生理事件,死亡在遥远的将来才会降临,是别人死了,我仍活着。现象学意义上的死亡是此在无可逃脱且不得不承担的可能性,死亡不再是将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是现在在场。有生也有死,使得此在的整体存在成为可能。更具体地说,生死相伴使得此在每时每刻都是整体存在,而不是等到真正死的那一刻此在才完整,那一刻,此在已经不存在了,更不会有什么整体存在。时间性来自死亡,当此在能够真正把死亡作为本已的可能性并勇于承担死亡时,此在才有时间性,而本源的时间即是时间性的整体到时。
本源的时间同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一样有现在、过去和将来,但同死亡的理解一样,应在现象学意义上理解三者。首先,三者是同时整体到时;其次,将来不再是未到来的时间,而是作为可能性存在,过去也不是已经流逝消失不见的时间,而是作为现身情态出现,现在即当下,开展出世界。当时间性以本真的方式到时,将来作为“持守着死亡的可能性”[1]5显现,已在作为“持守且一直持守着这种可能性”[1]5显现。此在先行到死亡中,承担起本真的罪责存在,并在当下的时间性到时中,开展出一个空无的世界。非本真的时间性到时,将来作为持守着关联中的可能性显现,同时,已在作为一直持守着这种可能性显现。此在逃避着死亡,带着期望环视周围,将存在者作为特定的什么置于关联中,并从中领会着自己的存在,在当前化中开展出有意义的世界。
二、有意义的世界
有意义的世界即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有意义的是要首先探讨的问题。从日常经验来看,我们周围有各种事物,我们每天都在自然不过的使用它们,用笔写字,用杯子喝水等。此在认识世内存在者的方式是“使用着的操劳。”[2]79而它们也是作为用具来与此在照面。用具一直处于上手状态,以致于此在认为自己生活的周围世界便是这一个个世内存在者的集合。这些世内存在者不就是随手就可以触碰到的吗?情况并非如此。当用具处于在手状态时,如凳子坏了而不能坐时,欲写字而找不到笔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世内存在者的其他样式体现了出来:“触目、窘迫和腻味”[2]87。在这些样式中,上手事物的指引功能体现了出来,同时,上手事物得以显示的根基即世界性也随之体现。指引是含义的关联,“是一种因缘关系”[3]78,这些关联构成了关联整体,即意蕴的指引整体,即世界性,而领会这个意蕴的恰恰是此在。非本真的时间性到时,此在没有先行到死亡中去,而是以非本真的领会方式——期望,匆忙地环视着周围的世界,把周围的事物置于特定的关联中,当成特定的存在者,这恰恰是此在逃生意志的体现。在畏惧中,死亡现身,此在发现自己的被抛,但情绪往往想逃离这种“公开的负担性质”[2]158,因此,此在逃避着死,并用昂扬的情绪将负担摆脱,积极地环视着周围,领会着意蕴,开辟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是此在在生的意志的驱使下积极开创的,正因为这种开创,历史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在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此在通常与其他的此在共处。“共处首先和往往只基于在这样的存在中共同被操劳的东西。”[2]142日常生活中,此在通过工件来与其他此在照面,因为工件能够指向“承用者与利用者”[2]83。此在通常就根据世内存在者来领会其他此在,从而领会自己。花园里的花,此在会把其他此在领会为种花者,而把自己领会为赏花的人,并且问自己能否也成为种花者。共处中,此在成为常人,在匆忙的环视中投身于世界,从其他存在者那里领会自己可以怎么样: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像他一样优秀的人,胜任他的工作,并且不停努力着。此在从世内存在者那里领会自己的可能性,比如:我可以成为一名教师而不是工程师,这仿佛是在做自己,但这只是常人自身,而不是本真的自身。常人淹没在公众意见中,兢兢业业地认可并维护着有意义的世界,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是有秩序的、安宁的。
常人所维护的这个世界,在现代则体现为技术世界。常人把存在者置于关联中,即是榨取存在者的何所用,这种榨取在技术发达的今天体现为“促逼意义上的摆置”[4]14。常人把存在者置于订造的漩涡中,解蔽为持存物,以“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4]14的方式摆置并促逼着自然。水流为了水压而摆置,水压为了发电机而摆置,发电机为了电网而摆置。常人自认为是自然的主人,一个又一个成就更增强了其摆置自然的决心。翻开人类的历史,这种征服战胜的姿态便一目了然,但海氏认为,这不是人掌握技术的世界,而是技术统治一切的世界。技术的本质是集置,集置作为摆置的聚集,人也在这个框架之中。人被订造成持存物,陷入了被订造以及为了订造的联系中,成为特定的人:生源、病人资源、技术人员。并且,人的被订造是首先发生的,“惟有人本身已经受到促逼、去开采自然能量而言,这种订造着的解蔽才能进行。”[4]16首先受到促逼,处于订造漩涡的人,为了订造其他存在者,开启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根基是根据律,要在表象活动中对某物进行计算性说明。当物成为表象活动中的客体时,人也就成了主体,从而淹没了人的其他可能性。在这个有意义的世界里,充斥着发达和繁华,一切都迅速地发展着,常人安于进步和美好,而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订造的危险。
三、空无的世界
本真的时间性到时,此在先行到死亡,承担起本真的罪责存在,在当下开展出一个空无的世界。空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万念俱灰。空无的世界解除了因缘关联,存在者的上手状态和持存物状态消失了,有用性也随之消失,从而作为自身存在,但空无的世界通常为有意义的世界所掩盖。作为常人,我们通常就安心地生活在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空无的世界从何而来?海氏谈论真理而论及艺术时,给了我们启示。当此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保存者时,可在当下开展出空无的世界。既为空无,便不能找到相应的存在者,它不像有意义的世界那样可触可感,它是运思中的世界。
艺术作品的保存者绝不是博物馆负责保管作品的工作人员,而是艺术作品的鉴赏者,但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鉴赏者。怎样认识艺术,便有什么样的艺术保存者。一般的鉴赏,是把艺术作品当成审美对象。海氏认为艺术鉴赏不再是作为依附于个人的审美体验,“而是把人推入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归属关系之中。”[5]48试想这样一个问题:远古时期人们盛水用的陶器,如今变成了艺术作品;农妇每天劳作穿的鞋,在梵.高的笔下也成了艺术作品。为什么?因为无论是陶器还是农鞋都保存了它的世界。作品的存在在于“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5]51,所谓“建立世界”,便是开放一个敞开领域,这个敞开领域便是作为原始争执的真理所争得的,并且这个领域的结构是自由的。所谓“制造大地”,可以分成两个词理解。大地是“遮蔽的、庇护的涌现着的自然”[3]219,是“大地整体本身”[5]29,是万物;对“制造”最贴切的解释还是孙周兴译《本源》时所用的“挪”字。“挪”体现了一种运动变化的状态,“制造大地”即存在者整体进入世界所敞开的自由领域,处于无蔽状态。因此,在农鞋这幅作品里,农鞋的有用性消失了,凸显出来的却是其“可靠性”[5]17。可靠性保证了万物的自由,田野、寒风、谷雨自由在场,“只是这样在此存在”[5]17。
艺术作品的保存者又是如何开展出这个空无的世界?在先行的决心中,将来的时间性以“持守着死亡”而显现,承担起本真的罪责存在,而“承担起”意味着此在已经且一直持守着无关联的可能性存在了,并在当下开展出一个空无的世界,千年万世都是如此,此在一向这样存在,世界一向如此。伽达默尔提出“集体主义的未来”[6]92,单个的此在组成一个集体,而借集体重演着世界,从而永恒性便凸显出来了。当此在欣赏作品时,不过是“艺术作品所曾在的世界借它而与实际在此的“此”一起到时”[6]88。天空、大地、植物、动物都在这个空无的世界显现。空无世界开展的前提是时间性的本真到时,因为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品的保存者。艺术馆擦拭作品的清洁工,就不能称为作品的保存者,他和用陶器盛水的远古人无异,因为他们都在非本真的时间性到时中,开展着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既然空无的世界在运思中展开,那么,当我们能够运思,便可以展开空无的世界。艺术作品的保存者,只是身份的设立,根本上是要求我们诗意地看待每一物。
时间性是海氏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只有在时间的视界下,世界、真理、艺术、语言才能得到本源的解释。非本真的时间性到时,有意义的世界得以开展;本真的时间性到时,空无的世界得以开展,空无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世界。海氏在此绝没有褒贬的倾向,只是从日常经验出发说出实情,并引领我们逐渐深入思考,最后踏上存在的道路。我们安于有意义的世界,徜徉在科技主导一切的世界里,世界万物以及人自身都成了持存物,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自然失去了诗意,被改造的面目全非,而人类如今不得不面对自己造成的恶果并开始拯救自然,拯救自身。海氏恰恰为迷失的现代人指出了明路:在运思中展开空无的世界,让世界万物都如其本然存在,才能还自然诗意,达到真正的自由和永恒,这便是思想的意义,也是海氏哲学的实践性意义。而空无世界的开展,首先要从运思开始,从诗开始,听从语言的呼唤,从而开始诗意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