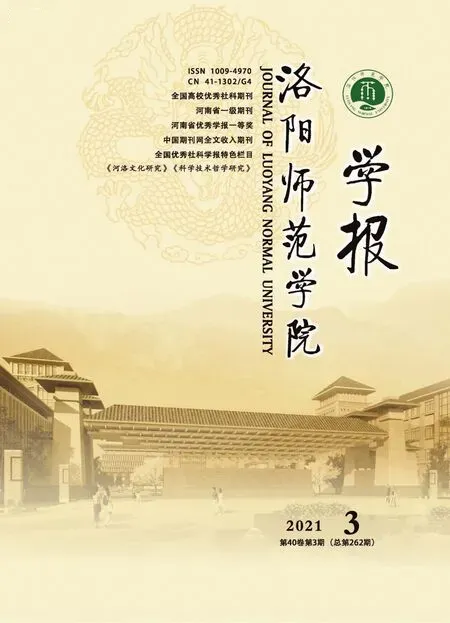孔子复礼梦碎后的《春秋》抒写
张世磊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孔子的政治构想
从《论语》的记载中不难发现,孔子喜好西周礼乐文化,向往西周前期宗法礼制之下那种依礼行事的社会形态: 各阶层都在相应礼制规范下活动,各依其礼,各行其道,行为有序,又能相互爱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孔子政治思想中鲜明地体现出礼义与仁爱的特点。
礼、义、仁三者之中,礼和义在西周宗法制度下已形成其内在含义与要求。《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之言曰: “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1]92僖公二十八年又载“礼以行义”,即是说“义”是“礼”的内在精神与理论根据,礼则是义的外化,是具体行事的规则。《乐记》中载: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2]可见“礼”和“义”都是服务于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但这种外化的规则——礼,若只是强调义的精神,势必会使上下阶层间的对立意识增强,从而引发阶层矛盾。孔子在继承礼义思想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仁的思想。
仁者,人也。人皆有情感,孔子的仁即建立在血亲情感的基础上,并超越个体血亲情感,将一己血亲之爱推到爱一切人身上,即爱人。如果抛除义、礼不论,单说仁的话,它具有平等精神。但追求单纯的仁爱是有难度的,《论语·雍也》载: “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3]64显然在孔子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即使是尧舜也很难做到。因此孔子思想中的仁是学理思想上的期望,而不是墨家那样的兼爱。在现实政治中,孔子仁爱的推行,与义、礼相关联,具有人道主义与宗法意识的二重性,即爱人是有差别的,受宗法等级约束。对此,韩愈在《原道》篇中有经典的阐释,他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即是说博爱的推行和义是分不开的,要能恰当地推行,这样就避免了博爱沦为兼爱。如此看来,孔子的政治构想既照顾到了君主,又顾及了民众。
二、君主修身爱民与民修身守礼
在家天下的时代,君主处在社会政治的核心地位,君主的优劣对于一国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孔子政治思想中清楚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如《论语》中载: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田耕滋曾指出: “因为王权是政治的核心,人臣的任何政治理想的实现,都必须依赖王权,国君自身的政治品质决定着政治的优劣。”[4]正是因为君王在社会政治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孔子非常看重君王自身品质的提高,因此,修身被列为儒家从政的第一要务,对君王的要求更是严格。《论语·宪问》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 ‘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 ‘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3]156-157不管是求得认真的态度,还是使他人、百姓安乐,提高一己的修养都是一个前提条件,最高境界是使民众安乐,很显然,做到这一步是有难度的,孔子再一次说出了“尧舜其犹病诸”。
王自身德性的提高,其身正,则下民自然会顺服,这样有利于消解阶层间的矛盾,以便能达到理想的治世效果。如《论语·颜渊》所载孔子答季康子之言: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127孔子以草随风比喻上对下的影响,突出上位当权者在社会政治中的核心作用。
孔子对修身的要求不独对君王,也指向一国之臣民,他理想中的臣民通过提高自身德性,能自觉遵守礼规,因礼行事。《论语·为政》载: “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11-12意思是说,对于民众,若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整治他们,民众只是暂时免于罪过,但没有廉耻之心。若是以道德来引导他们,以礼来教育他们,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甘心顺服。孔子看重的正是通过修身,个体的德性修养提高之后,内心对于礼规的自觉遵从,在这种政治思想下,刑罚显然不被孔子看重。《大戴礼·礼察》载:
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5]
这是儒家对礼之用做出的十分透彻的解释,礼与刑法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是防患于未然,即所谓“绝恶于未萌”,儒家的理想是将人人守礼向善常态化,从而达到于不知不觉间不逾矩的良好状态。
三、孔子复礼梦碎的原因
毫无疑问,孔子的政治思想及其设想的政治模式是有极高理论价值的。但再美好的思想种子,也需要合适的土壤。孔子所处时代为春秋晚期,周王朝早已江河日下,诸侯国弱肉强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趋势下,孔子推行礼治,试图复礼治国的理想,并不合乎当时的社会实际。说到底,春秋战国之际是一个极其功利的社会形态,各诸侯国都渴求快速富国强兵,并且强兵用武是必然。反对使用武力,甚至不主张运用刑罚,首先就与那个时代相龃龉,况且礼治的推行更宜在一个相对安定统一的国度,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点孔子也非常清楚。如《论语·子路》载:
子曰: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据此不难看出,仁政礼制的推行,确实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仁政礼治的这一要求与春秋战国之际动乱的社会现实相悖,与诸侯王渴望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国的功利需求相悖。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谋求推广其政治思想,结果很不理想。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6]647-648而在孔子归鲁作《春秋》之前,于困厄之际曾召其弟子子路、子贡、颜回,就自己信奉的道义是否错误及处境问题,向他们逐个询问。其中颜回的回答最切中孔子内心:
孔子曰: “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6]2339
孔子引《诗》陈述自己周游而不被任用的事实,进而让弟子讲出各自的看法,颜回的回答最切中孔子的心理,说中了士君子阶层的责任使命意识与价值理想,即“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孔子也确实没有因现实中的挫折而改变自己的信念,所以当子贡说出“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时,孔子并不赞同,并批评子贡“志不远矣”。返鲁以后作《春秋》,可看作孔子作为士君子阶层责任意识的体现。
四、《春秋》的主旨与文体
鲁国史书原有《春秋》,如晋国之《乘》,楚国《梼杌》。孔子在鲁《春秋》的基础上选择史事,增删文言,编成孔子《春秋》。孔子《春秋》与一般史书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一般史书是客观记事之书,孔子《春秋》则重史事背后之义理。因此,孔子《春秋》有孔子的思想寄托,是孔子的一家之言。如梁启超先生所说: “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7]该语指出了孔子作《春秋》是有目的的。
既然有编著目的在,那么其内容的选择以及所采取的文体样式,必然会围绕着编著目的来展开。孔子编著《春秋》的根本目的就是警世、诫君、尊礼。《孟子·滕文公下》载: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8]孔子干七十余君而不被用,意味着在现实中,其政治理想无法得到践行,面对春秋末期的各种暴行悖礼事件,作为士君子,他仍有改变社会现状的责任意识。《史记·孔子世家》载: “子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6]2352不难看出,面对自己的年迈,面对社会的暴悖,孔子内心的价值信念,使其不忍碌碌而终,如其所言“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后世铭记,而是担心作为君子阶层中的一员,若没有为后世称道之处,会有损君子阶层之名。孔子坚持士人之道,即使其思想不被君王采用,不被那个时代接受,至少还可以是“不容然后见君子”。
从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的创作情况看,孔子作《春秋》显然有其思考和尊崇的纲领。“约其文辞而指博”,是说孔子在原史书的基础上有意精简文辞,形成提纲式的文字,而这些极简文字的背后,却极富警世诫君之理与严谨的礼仪规范,这正是孔子所追求的东西。
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中说: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9]意思是说,作者要表达的情感思想不同,文章体式也会不同,这是因为作者会根据自己表达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文体样式,而不同的文体样式会形成不同的风格。孔子追求的是“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即用抽象的语言褒贬是非,不如用那些已经发生了的史事,其所映射出的道理,更能给人以警诫。这样一种写作构想决定了《春秋》不会像其他史书那样长篇记叙,追求客观详尽,而是提醒式地记述典型事件,要言不繁。如记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旨在表明多行不义必自毙;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赐”,旨在判明事先预备凶事不合礼。又如桓公五年,只记“大雩”二字,是为说明雩祭的时间不对。僖公二十二年,“求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旨在明示,邾国虽是小国,但由于鲁僖公轻敌大意,不听臧文仲劝谏,鲁国的军队最后溃败。
因为是记事,非抒情,《春秋》之言为散语而非韵语。孔子周游列国,始终奉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6]2347的原则。孔子为国家,为君主,但不是专为某一国、某一君,若世无明君,他便待来者,如《论语·子罕》载: “子贡曰: ‘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1]90孔子这种思想也使他能从容地放眼于后世,不会因为某一国某一君的不接受而郁郁寡欢。而是做出一名贤士应该做的,不使自己虚有君子之名,因而《春秋》的句式只追求精准记事,而不是像《天问》句式那样充满悲愤、质呼之气。
《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6]2353孔子在做司寇之官时,在听取诉讼者口供书写判辞时,凡应与人商讨的地方,绝不独自专断。但对于作《春秋》,则完全由自己,弟子最善文辞者,也不能增删一辞,因此《春秋》完全出自孔子之意,寄托其政治信念。
总之,孔子的政治构想在继承周代礼义思想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仁的思想,使其政治思想能照顾到统治阶层与普通民众,并对统治阶层与民众的行为伦理提出了要求,以利于这种政治思想的践行,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但这种构想与春秋晚期的时代主流不合,孔子周游过程的落魄是很好的说明。出于士君子阶层的责任意识,归鲁后编著《春秋》,是其复礼政治思想的继续。正因为有编著目的在,《春秋》才文体精简,风格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