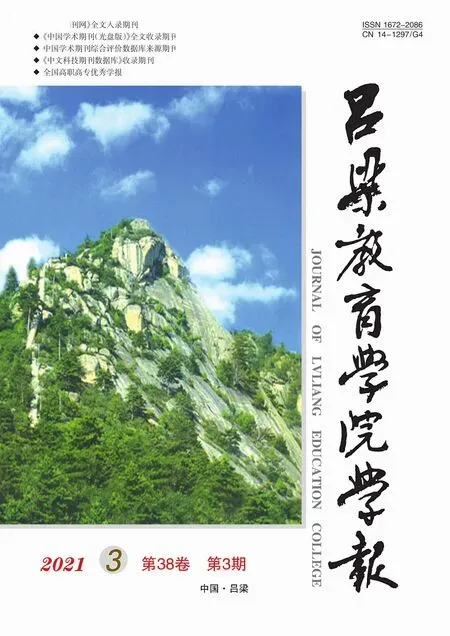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的叙事艺术
薛 慧
(南京农业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5)
1980年代是话剧实验探索、创新拓展的十年,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有利环境,“五四精神”再次进入戏剧家们的关注视野,戏剧家们纷纷发挥自身的审美创作才情,表达自身的主体意识。这十年是戏剧发展充满生机,成就卓著的十年。在众多的题材中,无论是从创作数量上,还是从总体取得的成就来说,农村题材的话剧似乎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桑树坪纪事》和《狗儿爷涅槃》等农村题材剧作,无论是文学层面还是剧场层面的探索对当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相较于其他题材的话剧创作, 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创作呈现出何种特征?或者说,戏剧家们是如何艺术性地讲好中国农村故事的?是否能对当下戏剧创作提供借鉴意义?因此,梳理戏剧家在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的叙事艺术便成为本文应有之义。
一、史诗性宏大叙事
随着话剧民族化的讨论逐步深入,以及寻根热、文化热的此起彼伏,1980年代的剧作家们不再拘囿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而是转向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的多元化创作,他们更期冀于从中国因袭的民族文化中重新审视日常中的问题。因而,从农村题材中追寻由历史线性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文化便成为这一时期戏剧家一种思考与表达的方向,并且往往呈现出宏大的叙事场面。
如1980年代的东北农村题材话剧《田野又是青纱帐》,这部剧塑造了性格迥异且人物特色鲜明的39个人物,通过日常生活中充满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的细节,解读长久形成的青纱帐文化。而在话剧《高粱红了》之中,剧作家刻画了19个不同身份的人物,围绕1976年到1980年这段历史时间展开,整体呈现着剧作家对人性、人情的沉思。在剧作《古塔街》中,剧作家通过一条狭窄的古塔街道,探讨在这个小小空间中众多的人物命运,剧作刻画了22个人物的生活走向。同样地,在话剧《昨天、今天、明天》中,剧作家运用了象征化的戏剧语言,探讨20多个人物在不同时间段的人生际遇。当然,被誉为农村题材话剧两座高峰的《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同样也在思考着类似的主题。
可以说,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把视角延伸到农村这片天地中时,戏剧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宏大的史诗性叙事,因而,人物数量之多,事件发生的延续时间之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庞杂,宗族关系与新的社会关系的冲突纠葛,都成为剧作家们关注到的问题。可以从《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以及《荒原与人》的叙事构架中窥探全貌。
《狗儿爷涅槃》的叙事便是围绕狗儿爷的一生际遇所展开的,狗儿爷的一生典型性地代表了一大批跟他一样的农民生存境遇。《桑树坪纪事》则以桑树坪这个封闭落后的农村为载体,叙述了这个村落里发生的几个事件,刻画了村落里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剧作通过1968年到1969年的片段历史却让人们看到了千百年农村文化的历史缩影。
《狗儿爷涅槃》以狗儿爷这一人物为叙述主题,通过收芝麻、分门楼、分地续娶、买地发家、失地、得地、烧门楼等细节展开,狗儿爷所经历的也正是中国千百万农民所经历的,这并不是简单的个人遭遇,而是一个农村社会几十年变迁的缩影。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依赖、痴迷甚至疯狂,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构建的过程。虽然剧作做了艺术的夸张象征处理,但却真实反映出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农民与土地的复杂纠葛关系。土地,对农民而言,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有了土地农民便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农民便脱离了穷苦。千百年来农民憎恨土地的所有者“地主”,也羡慕着土地的所有者“地主”。于是,狗儿爷对祁永年的情感十分复杂,搀杂着羡慕、嫉妒、恨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历史变迁对农民命运的发展变化影响巨大,社会政策的变化很容易引发农民生活状态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狗儿爷的个人命运发展便是如此:从发家到分得土地、从菊花青充公到土地上交,导致狗儿爷发疯。剧作除了揭示大跃进时期的公有化制度不合理之外,更多地是在讨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绝对依赖直接表现为丧失了土地便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所有基础。这与狗儿爷的儿子(陈大虎)新一代农民形成了鲜明对照。新一代农民的发家致富基于改革开放的自由环境,可以说,历史的发展不可阻挡,而农民的生存境遇与社会政策的出台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剧作刻画了残忍、蛮横却终究落魄的祁永年地主形象,刻画了善于变通、圆滑、自私的苏连玉农民形象,也刻画了积极维护党的政策的农村干部李万江农民干部形象,以及其他一些善良、纯朴的农村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村人既有着农村人的质朴、善良,也有农村人的狭隘、自私。
可以说,剧作者试图把各种各样的农民囊括在历史发展的场景中去展现他们真实的生存处境。几代农民的发展奋斗历史可以贯穿成农村发展史。于是,农民复杂的文化人格,便成为剧作家试图去分析清楚的对象,其中不乏对农民文化人格中“劣”的揭示与探讨。
如话剧《桑树坪纪事》通过“麦客榆娃和小寡妇许彩芳的恋爱”“福林和他的婆姨”“杀人嫌疑犯王志科的遭遇”和“耕牛豁子之死”的故事来揭示由封闭村落的贫穷而带来的一系列农村问题。
贫穷的境遇可以产生与愚昧、与伦理道德相关的联系,农村人的贫穷直接导致娶不到媳妇、吃不上饭的问题。于是,转房亲、换亲、贿赂讨好估产干部、赶走外姓人王志科、杀死耕牛豁子的事件接踵而至。
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男尊女卑的古老命题。女性被暴打在农村往往习以为常,生女儿是别人家的媳妇的观念也早已根深蒂固。在剧作中,李福林在一群汉子的怂恿下脱下了青女的裤子,并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喊声:“我的婆姨!钱买下的!妹——子——换——下的!”导演在舞台表达上运用了雕塑,用一尊侍女雕像以虚代实,运用象征的手法,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引发人们对农村无数类似女人命运的联想。
其次在这个封闭的村庄,李金斗成为另一种隐喻象征,他为农村平均粮食的估产受尽屈辱,但在对付麦客榆娃和彩芳、对付外姓人王志科时显示了他专制、阴险、狠毒的一面,阿Q式的欺下怕上在李金斗身上暴露无遗。李金斗在被公社干部打了之后说:“咱庄户人还算个人吗?打了也就打了…… ”但是在村民们逮住彩芳和榆娃的时候,他凶狠而毫不掩饰地下着命令:“少噜苏!接着打!在桑树坪这块地方,我说了算!”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对上送礼谄媚对下压迫专制的官僚作风依然在桑树坪畅行无阻,更要紧的是家族血统等级观念在这里形成了坚固的堡垒似乎牢不可破,并且成为一种深入大脑的思维定式。
例如,城里来的大学生朱晓平在得知李金斗被打后,为他打抱不平,但他的反驳依然也是以权压权的思维逻辑,他说:“你长着耳朵去打听一下,我爸爸是干啥的。”而一旁的许彩芳道出了朱晓平的身世:“这娃他大在省革委会当大官哩。”这一番对话让我们看到封建血统论在农村的滋生蔓延与顽劣已经演变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定式。令人玩味的是,剧作者用心良苦,通过角色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如果没有好大呢?显然,没有这个在省里做官的好大,朱晓平的打抱不平丝毫没有分量,也不会起半点涟漪。一方面,我们看到李金斗熟谙官场家族血缘关系的道理,利用后台达到估产目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也体察到剧作者对“要是你没有个好大”的质问与焦虑。
与《狗儿爷涅槃》有所不同的是,《桑树坪纪事》的叙事方式并不标明故事发生的时间,使得故事本身极具象征意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片热土上似乎上演的是循环重复的故事。时间和人物都转化成剧作家表达思考的符号。
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在前两部作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该剧用一种意识流的写作方式,描述了一批知识青年在农村下乡的遭遇。其中杂糅了许多剧作家自身的个人经历。在极端封闭的环境中,荒原与人既是充满生存艰苦的冲突构成,同样也是构建人与人纠葛而无解的荒原精神之地。因此,抽象的荒原,既是实在的北大荒,同样也是荒芜的精神荒原。人性的挣扎与美好因意识流的呈现而更显宏大张力。 这几部农村题材话剧之所以达到史诗的规模,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任何内容的表达都需要诉诸于形式,这两部成功的史诗性剧作能在短短的几小时之内在舞台上充分表现,无疑离不开剧作家精心的编剧创作,这种成功便不得不提到布莱希特陌生化的编剧创作应用。正由于借助了布莱希特陌生化叙事方法,这一史诗的内容才能在舞台上自如地展开,这也是剧作家艺术观照的侧重点。
根据布莱希特的理论,陌生化效果的编剧应用可以通过寓意、历史化、歌唱的方法来创作。布莱希特认为,寓意是叙事剧最合适的创作形式,他说:“历史事件是只出现一次的、暂时的、同特定的时代相联系的特殊性,它具有被历史过程所超越和可以超越的因素,它是屈服于从下一时代的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的。不断的发展能够使我们对前人的举止行为越来越感到陌生。”[1]刘锦云在谈及塑造狗儿爷这一人物形象时说道:“要超越自己的表现对象,去思考形成这一切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诸种复杂根源。这样,当我和我笔下的人物拉开一定距离的时候,便不仅看到了一些可恶、甚至可憎之处……”[2]因而,我们看到狗儿爷的“疯”带有极大的寓意性。失去土地之后的农民发疯,正是其精神世界彻底坍塌的表征。
同样,歌唱也是史诗性叙事达到陌生化效果的一种方法。它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打破舞台幻觉,推翻第四堵墙来达到陌生化效果。如话剧《桑树坪纪事》中的歌队运用,歌队可以直接评论剧情甚至和剧中人物对话。
总之,对照其他题材的话剧,农村题材的话剧明显显示出在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上先天优越的题材优势。具体而言,农村题材的话剧《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所容纳的历史变迁、人性复杂、农民性格、民族文化等内容的庞大为史诗性的作品提供了可能,而剧作家娴熟的专业技能与深刻的生命体验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这种宏大的史诗性叙事,利用政治、人性和文化的宽广视角对几千年积淀的民族文化进行多维审视,并借助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而成为探索的典范。当然,剧作家除了在时空构架中思索农村承载的文化之外,在农村这一比较独特的语境中也不遗余力地探寻着农村之味。
二、凸显农村之味
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相对于历史题材、都市题材的剧作更凸显出剧作家或者导演对农村味的深刻领会。这种农村味表现于作品和舞台上便是生动的戏剧动作、丰富的民俗习惯与待人接物的方式,而这些舞台表现的背后则已经标识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格内化。欣赏一出出农村题材的话剧,就是在品味乡村文化所渗透的农村味道。
(一)方言俚语之“土”
戏剧动作通过形体、言语、心理甚至静止来推动剧情发展、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从而彰显戏剧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在戏剧语言上采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来突出农村的生活风味。
农村题材的话剧在语言上凝练集中地展现农村真实生活的风貌,通常通过舞台提示语、对话、旁白和独白等形式来呈现。剧作家在舞台提示方面用心营造农村土味十足的氛围。如话剧《桑树坪纪事》中李金斗在检举信上按手印的舞台动作,李金斗用尽了全身力气扑倒了桌子,死死地摁住掉在地上的状子,然后用力按上他的手印。在这一系列舞台动作当中,“撩胳膊卷袖子”表现出李金斗极其重视的心态和认真严肃的心理,继而“桌子被按倒”“趴在地上”“死死按手印”的一系列动作提示,可以看出,李金斗对外姓人王志科的排斥越发坚决彻底,人物的心理发展层层递进。最后,李金斗自私、狭隘的农村文化人格由此立体呈现。
我们发现,农村语言在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中被剧作家作为展现农村地域色彩的一个重要元素。一方面农村题材话剧通过方言的表现,也即利用俗语、人名、语气词、粗话等,对农村生活原貌进行艺术的集中展示,另一方面也是对农村文化的心理揭示。正因为独特的方言所散发的农村味,才能使得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许多农村题材的剧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自觉地在作品中着力凸显这种农村味。
方言的口语使用如“咋整的” “躲窝铺”“我中”“不埋汰”等。在舞台表现上,剧作家力求做到真实生动。如剧本提示“卖耗子药的(山东口音):这香瓜多少钱一斤?俺买两个,口渴的冒火,这地方耗子真多,一门打架,他娘的,吱吱地叫!”可以看出,方言的大幅度使用不仅给观者带来亲切的感受,也帮助人物更加生动真切。几乎所有的农村题材作品都会用到俗语,如 “青瓜裂枣,谁见了谁咬”“急水滩的石头——经过风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瓦盆破了当土碗,蚯蚓死了还要‘扳几扳’呢”等。这些俗语对农村人来说信口就来,运用自如。语言是话剧的关键,可以说,人物的塑造、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生动的语言表达,不管是东北的“咋整”,山东的“俺”还是粗俗的习语加调侃,这种扎根于泥土的本色才是农民的颜色。
(二)民俗风情之“土”
民俗习惯与待人接物方式也被剧作家关注撷取成为标识农村味的另一方面。如话剧中多次用到了二人转,二人转作为东北民俗的一种娱乐形式在剧作中反复出现,就连《古塔街》中的段傻子也会熟练地唱几句“叫声丫环跟我走,一到花园去散心儿;小丫环便在头里走,后跟着美蓉大闺女儿……”当然,农村题材话剧作品中对农村“换亲”“借寿”的习俗也多次关注。《桑树坪纪事》《好媳妇访问记》《红白喜事》等对此习俗一再提及。
有时候农村人的土气在迷信的标签下却也显得可爱而质朴。如《田野又是青纱帐》中彦子对农村习俗的揶揄“(念黄纸)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拘魂码”“左眼跳财,右眼跳祸”等。这种体现着各个地方民俗色彩的娱乐形式、婚丧习俗、祭典仪式虽或寄托着创作者的批判之旨,但同时也弥散着特定地域的乡土气息。
(三)待人接物之“土”
农民待人接物所恪守的原则,应变处世的习惯性选择都渗透着农村文化的深层积淀。比如,农村中对人名的称呼是直来直去,但是这种直率本身就是农村人特有的性格。如“陈大脚”“老疙瘩”“狗不理”“八聋子” “王半拉子”等,这种在城里人看来是侮辱别人的绰号在农村人看来却是异样的亲切朴实。
当然,农村人的土气也体现在对“性”的直白调侃中,如小英子二人转中的“气坏了三条腿的大裤裆……”农村人的性调侃是在被封建礼教压抑的环境中释放被压抑的力比多的不自觉意识。
对骂、打群架在农村习以为常。如在话剧《桑树坪纪事》一开头,陈家源村与桑树坪村因为下雨就引发了言语冲突,开始对骂:
“桑树坪村民 (吼)
黑龙黑龙(仓)过过哟(哜当当)
走到南边(仓)落落哟(哜当当)
邻村村民 (对喊)
黑龙黑龙(仓)站站哟(哜当当)
站到北边(仓)落落哟(哜当当)
……
[桑树坪人急了,冲着邻村人骂了起来。]
桑树坪村民:狗日的心黑,喊雨站哩!
邻村村民:驴日的心坏,把雨往这搭赶哩!”
以上的对骂语言相当粗俗直接,并且还形成了民间小调,对仗工整,不失为充满农村特色的对骂。下雨本身并不会按照个人的只言片语发生转变,但是大家依然相信祈祷的力量,通过向天祈祷,希望龙王多向自己所在的村子下雨,而与之相关的邻村村民,生怕龙王听到显灵去了邻村,于是也集体祈祷。但凡有一人脱离开祈雨的情境,把矛头指向对方,那便很快形成了集体对峙,事情已经脱离了祈雨本身,对骂与打群架便相继发生。由此,农村人在面对外来冲突的团结一致与内部争斗时的狭隘自私在对骂中得到了详尽的展示,农村因袭的文化在农民应变处世的戏剧情境中得到丰富化与生动化的揭示。
可以看出,在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中,农村味的突显往往使这些作品呈现强烈的风格化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地头田间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为指物、论理、说事的辅助,从而产生了丰富的比喻,比兴,歇后语;秽语、脏话,侮辱性的绰号以不雅不敬的方式表达人际关系的亲热;性的调侃瞬间释放了礼规所压抑的欲望。而体现着各个地方民俗色彩的娱乐形式、婚丧习俗、祭典仪式虽或寄托着创作者的批判之旨,但同时也弥散着特定地域的乡土气息。而农民待人接物所恪守的原则,应变处世的习惯性选择都渗透出农村文化的深层积淀。
总之,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所有的舞台创作包括剧作者、导演、演员等都有意识地通过突出农村味来表现农村生活。农村味的着重体现是农村题材创作的必然要求,也是话剧独立于政治寻求自身艺术性的努力,1980年代农村题材的话剧剧作家正是回到话剧本体,扎根于现实,对农村的历史现状进行思考。其中,对农村味的着力凸显其实也是剧作家们对话剧艺术观照的努力尝试。
三、叙事在继承与探索之间
1980年代话剧艺术观念多元化并存,一方面是由于戏剧家们在戏剧危机的事实面前,发现当代戏剧自身封闭的严重性,新中国以来,话剧“易卜生——斯坦尼模式”被程式化后越发脱离了生活基础,“问题剧”“领袖剧”丧失观众共鸣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翻译界领域的不断拓宽,之前对苏联、挪威等国家的译介开始向西方其他国家拓展,贝克特等的荒诞派戏剧、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格罗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以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种戏剧流派的戏剧理论主张都被大量地译介到戏剧家的面前,其中各流派所表现出对传统的反叛、对自我个性的弘扬和艺术舞台表现形式的多元化都对中国戏剧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西方戏剧对中国戏曲“写意”的借鉴也引发了国人对自身民族戏曲文化的思索,戏剧家从“舞台假定性”出发发掘了民族戏曲中“写意”的艺术魅力和审美资源。胡伟民认为:“中国话剧艺术的革新浪潮是大胆走向复归戏剧的本质假定性,其总趋向是在追寻我们民族戏剧艺术传统之根。”[3]高行健也提出:“借鉴西方戏剧,显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结合我们本民族的戏剧传统,去研究我国戏剧艺术发展的道路。”[4]那么作为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也必然在探索话剧思潮下做出积极的回应,需要明确的是,这样的探索是奠定于继承基础上的多方探索。就农村题材话剧来说,一方面在剧作创作手法上表现为对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回归继承与对中国传统戏曲、西方现代流派创作手法的借鉴吸收;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表现为对斯坦尼斯表导演理念继承与对布莱希特演剧体系以及中国戏曲演剧观念的借鉴吸取。
(一)剧本创作探索新现实主义风格
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创作广泛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新现实主义创作风格。1980年代前期农村题材话剧创作注重描摹真实的农村生活情态,剧作情节的展开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守则,情节随着事件自然发生的时间发展,并不采用过多的创作技巧,大多采用的是开放式的戏剧结构。如《赵钱孙李》中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情节便是依据1979年深秋的某天上午的自然时间顺序而展开。同样在《张灯结彩》《落凤台》《吉庆有余》《山乡女儿行》等作品中的时间发展也是按照事件起始时间展开。这些作品并不精心于表现形式的多方变换,而是注重于对现实农村生活的真实展示与生动描绘,主要通过人物关系在事件刺激下的调整来深入刻画人物性格。这种真实的农村生活情境与戏剧表达的主题往往结合紧密,引导观众在如临其境的农村生活中洞察戏剧主旨。
新时期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在回归的同时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以真实反映农村生活为基调的多种舞台语汇表达,包括对中国戏曲当中写意化的动作、场景的吸收以及对西方现代流派中时空交错、内心外化、灵魂出现、幻觉、歌队合唱等的学习借用。可以看出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方创新,是剧作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努力超越,但这种新现实主义创作依然不能脱离人物、事件的具体真实背景。譬如《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便是农村题材话剧新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狗儿爷涅槃》在反映几十年农村变革与狗儿爷生存遭遇的基础上利用时空交错、心理外化、灵魂、写意性的布景与动作等手法来强调剧作者的主旨,从而激发观众产生共鸣的观剧心理效果。《桑树坪纪事》采用几个真实的生活片段故事,刻画桑树坪农民的不同性格,其浓郁的文化批判在“围猎”“打牛”的象征意象中激发观众思考。
不论是农民性格还是农村实际生活内容都具有重实际、求实效的特征,农民在动机与目标之间往往采取直接自然的路径。这就使得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的剧作家多选择与表现对象和表现内容相适应的写实手法,包括如实呈现农民的生活内容、命运遭际,采用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但同时也对表现形式进行多方积极尝试,打破以往单一僵化的创作理念,努力丰富舞台语汇。
(二)舞台呈现既写实也写意
在舞台呈现上,斯坦尼斯的演剧体系中“重体验”“演员、角色”所激发的“幻觉”效果体现在舞台背景的真实描摹、演员的真实体验等方面。1980年代《红白喜事》等作品便是对这一舞台理论的积极实践。《红白喜事》中的舞台背景,烟囱可以冒烟,机井可以打出水来,房顶结实得可以站人,这种纯写实的舞台呈现有利于观众身临其境地观剧体验。而农村题材的话剧表演风格也极力贴近农民真实的生活情态,努力刻画逼真的农民性格形象。
随着探索思潮的发起,布莱希特演剧中打破第四堵墙产生“间离”陌生化的剧场效果也为农村题材的表演吸收,同时中国传统戏曲中写意性的场景、程式化的动作等也被农村题材话剧的舞台所采用。由此,在继承先期斯坦尼演剧体系理念的基础上,布莱希特、中国戏曲等演剧理念进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探索视野。探索的重点一方面表现在剧作内容的“心理外化”“鬼魂”“梦幻”“插科打诨”“歌队”“时空转化”等的摄入,另一方面表现在舞台表现形式中的观演关系调整。在调整舞台表现形式的“观——演”关系方面,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的导演、演员和舞美都表现出积极的主体意识。
首先,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导演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导演的艺术创造使舞台得到不断深化与升华。导演的主体能动性在探索话剧中表现的更加明显,以徐晓钟和林兆华为例。
徐晓钟在剧作中引入了自身对写意的思考,同时也成为其二度创作的特征。第一,《桑树坪纪事》中麦客进村、出村的场面,徐晓钟利用写意的艺术手法,让演员们围成一个圈,组成一支浩荡的大军做着舞蹈化跑圈的动作,同时转台则逆着麦客的行进方向转动。演员的动作与转台的逆转,音乐的烘托,营造出诗意的幻觉,中华民族的艰难历程与这诗意的场景融为一体,扩大和延伸了观众观赏想象力。第二,对于再现与表现两种不同的美学原则,徐晓钟把二者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在话剧《桑树坪纪事》中,一方面导演在人物关系、矛盾冲突以及性格塑造等方面,基本运用再现的美学原则,真实描绘了桑树坪村民们的生活、青女的悲剧婚姻、彩芳被逼投井、月娃被卖、志科挨打入狱等等,这些情节都是写实的再现的去表现村民们极度贫困和愚昧不堪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导演融入了歌队、舞队、唱词、曲调、形体造型等形象来再现情节。比如“围猎”式审美舞台意向成为一种象征而成为导演的独创。第三,导演融入了更多戏剧性因素。导演的二度创作中,全剧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是贯彻完整的,在三个篇章中,以彩芳、青女、月娃、外姓人志科和老牛“豁子”的遭遇和命运为五条情节线索而互相穿插。如把志科受整的情节线与老牛“豁子”情节线交叉起来,把老牛和志科的“围猎”联结起来。导演试图让观众在“体验”的同时也不时地“间离”,对作品产生理性的思考。第四,徐晓钟结合了具象与抽象的手法。如“月娃出门”“青女过门”“青女铺排男人”等具象化的情节和“青女受辱”“围猎”之后的裸女石雕等抽象化,体现出很大的隐喻特征。
林兆华导演在总结话剧《红白喜事》创作经验时说:“我发现,习惯往后看容易满足,而往前看无穷的世界,则更能唤起我创造的激情。因此,我喜欢不停地探索、实践。历史和未来,我更着眼于未来。”[5]《红白喜事》是以继承写实为主的作品。如舞台上的烟囱可以看得见冒烟,机井可以打出水来,房顶牢固得可以站人,树上的喇叭可以真的发出声音……尽管如此,导演也努力打破写实观念的限制,尝试“虚”的设置,如他把写实布景的正面房屋(郑奶奶和热闹的新房)面对观众的墙拆除,使观众能清楚看到两个空间进行着的不同生活状况,给演员的表演也带来直观能动的好处,这是导演艺术思维上的创新与突破。
《狗儿爷涅槃》中导演灵活转换时空,使得现实、回忆、想象、梦幻互相交错或者平行。如人与鬼魂的同台对话交流,或者通过演员走一个阿拉伯数字“8”字形来说明空间的更换。全剧主要利用写意的手法来表现一位中国传统农民在新的社会变革中所经受的精神磨难,他对土地和劳动的眷恋以及他自身的狭隘与保守交织在一起。导演用一种反时空的方法来外化人物心理,如一开场时狗儿爷亮相,他划了一根火柴,并点燃了火把,随着光影,身后出现了祁永年的幻影,而幻影又从身后吹灭了火把,惊异的狗儿爷开始与之对话,于是人与幽灵在同一时空展开了灵魂角逐。狗儿爷几十年生活的变迁辛酸往事,他对高门楼的恨和成为自己私有财产后的誓死捍卫的心理都得以在舞台上表述,这种舞台假定性的时空构筑,在制造幻觉的同时又打断它,形成了主观体验和流动写意结合的艺术时空。
需要注意的是,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在借鉴各种舞台表现手法的同时也面临内容与形式的适合与否的问题,不管是任何的舞台语汇,其目的始终是为表达戏剧内涵而服务。但是在1980年代的舞台多样化语汇创作中同样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为形式而形式,为迎合观众而粗制滥造,甚至出现“一窝蜂”的雷同现象,或者是过于抽象的舞台语汇让观众不知所云,或者是过分的“间离”导致了审美疲劳。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同样面对着如此的困惑,包括锦云在1989年创作的《乡村轶事》都存在过分抽象化而晦涩难懂的嫌疑。诸如此类的弊端并无助于农村文化特质的揭示与对农村审美规范的沟通。
四、结语
总之,在实验探索的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历史政治环境,戏剧危机所激发的关于“戏剧观”的论争以及由此形成戏剧革新的戏剧文化环境,大大提高了戏剧家们的主体意识。正是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创新所融汇交织的历史文化环境奠定了话剧光辉而卓有成效的十年,农村题材话剧在继承与探索之间进行积极尝试,从而在这光辉十年当中撑起一片别开生面的天空。正如此,其史诗性宏大叙事模式、凸显农村之“土”味,以及在继承与创新间积极探索的尝试带给当下戏剧创作回味无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