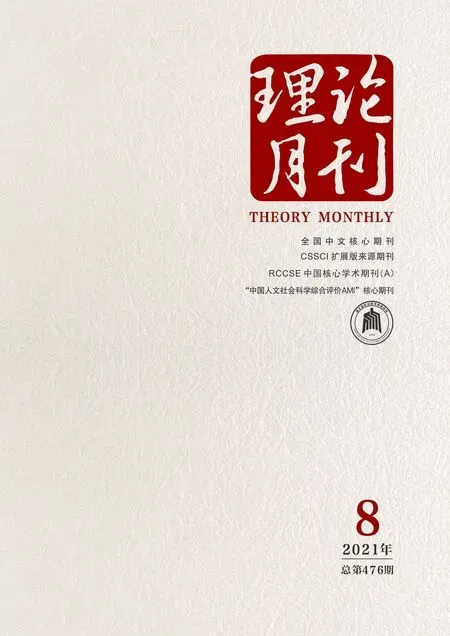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逻辑线索及其内在关联
□张 鷟,李桂花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既是一个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又是一个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因而他们的生产力观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富有建设性的。但由于受到苏联教科书体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影响,这些研究大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主要体现在科技生产力方面,并认为这种生产力是一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性力量,因而将他们的生产力观冠以只见科技、不见自然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主义”等称谓。事实上,这是对他们生产力观的严重误解。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梳理,我们发现,他们的生产力观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绿色意蕴。基于此,本文认为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线索主要有两条,即作为显性逻辑线索的科技生产力观与作为隐性逻辑线索的生态生产力观。
一、显性内在逻辑线索:科技生产力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促动效应,形成了系统的科技生产力观,成为他们生产力观最为突出的方面,构成了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该线索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基本要素、资本主义批判、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上。
首先,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基本要素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全面渗透于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中。其一,就劳动者要素而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规律和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艺。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简单的分工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规律使生产过程的每一局部操作获得了适合局部工人的特殊形式,并将这种特殊的劳动技巧发展到了极致,从而使总体工人的成员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同时,资本家为使工人更熟练地进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便对工人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大量工人以此提升了自身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智力和劳动技艺。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1](p204)其二,就劳动对象要素而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劳动对象愈益丰富,使用高级的劳动对象逐渐成为可能。在传统生产条件下,加工技术条件的限制和生产工具的简单粗陋,导致工人经常因缺乏生产所需的材料而陷入长期的停工,致使工业生产、消费需求长期得不到扩大和满足。新机器的发明与技术改进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对象对生产的限制,而且也推动了煤、铁、玻璃、陶瓷等材料的加工技术的发展。同时,生产的发展也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创造了条件,而自然科学的进步又大大推动了材料加工、创造与废料回收利用的能力,“从而无须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2](p699)。其三,就劳动工具要素而言,科学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工具形态的革新,科学技术逐渐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改变了原有生产工具的简单落后状态,创造了自动的机器体系并塑造了机器大工业。马克思以机械性劳动资料的固定资本衡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动的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成熟形态,以生产力的形式出现并凭借其庞大的机器“器官”使工人本身的生产力作为无限小的力量趋于消失,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从属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所以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1](p198)
其次,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视域。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原有的阶级构成与宗法关系,造就了大批无产者。在传统生产方式下,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多是散居在农村的农民。他们在宗法制度下过着田园诗般的较为自由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还不是一无所有。然而,以机器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3](p34)无情地斩断了他们温情的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同时也剥夺了他们仅有的生计来源,大量农民被迫变成无产者,沦为一种不得不出卖自身活劳动能力的特殊商品。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4](p390)。另一方面,科技异化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叙事,深刻表现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话语展开中。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充当了异化劳动的“催化剂”,使工人的生存境遇更加悲惨。其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具有物之性格。在科学技术的催化效应下,工人以更高的生产率在更大的规模上生产出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存在物,从而加速了工人与自己的无机的身体的分离。由此,工人丧失了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人格物化的程度愈益深化,最终沦为僵死的物一般的存在。其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使劳动者逐渐简单化。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发挥,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只是在肉体的外在强制下被迫劳动。在科学技术的“催化”作用下,工人的片面发展达到极致。在机器大工业中,自动的机器体系代替了大量工人的手工操作,工人只是作为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一个零件而存在。恰如马克思所言:“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单个人只是整体的一个环节……是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种铁的机构的有节奏而均匀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动作而工作着。”[1](p320)在如死的机器一般的工作状态下,工人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单向度的“机器人”。其三,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使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更为激烈。(1)科学技术所塑造的机器大生产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为剩余价值的榨取提供了技术保障。资本家通过提高机器的转速和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单位劳动时间内充满更多的劳动,以致工人因肉体与精神方面的过度劳累而早衰。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3](p34)(2)机器生产的替代性劳动使大量的成年熟练工人被妇女和童工所取代,成为“过剩”的产业后备军。因而失去了生计来源的大量成年工人便与妇女和儿童处于更为激烈的竞争之中,进一步恶化了工人的生存处境。(3)“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1](p359)正是由于工人、资本家、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异化相互交织,从而使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更为残酷和激烈。
最后,从科学技术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为人类解放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4](p185)。虽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加速了私有财产的积累,使人深陷于异化与物化的奴役之中,但马克思并未反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而是透过科技的异化表象看到了其在促进人类社会形态变革中所蕴含的推动人类解放的巨大力量。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形态的基本判断之中。其一,在“人的依赖关系”[1](p52)的最初社会形态下,社会生产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个人还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不具有独立性。其二,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p52)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下,工业生产实践为自然科学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物化为机器形态的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但在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面前,即在物性的虚幻表象下人又再度丧失了自身,深陷于商品、货币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中。仅仅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相对独立性并非真正的独立性,人尚未真正脱离物的生活真正进入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人有限的相对独立性并没有消除人所经受的诸种异化、物化,在科学技术加倍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物的奴役反而变得更加普遍、更为突出,人依旧戴着沉重的镣铐。但马克思并未据此就否认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促动效应,相反,马克思肯定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p56)这表明,马克思认为科技发展进程中伴生的异化、物化现象有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必然性,是个人获得自由解放的必经之路。只有在科学技术造就的巨大生产力的基础上,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足的社会物质财富才得以可能。其三,在“人的自由个性”的第三大社会形态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53)。而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恰恰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必然要素,尽管我们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必然还要遭受科技异化的侵扰,但科技生产力量的积累必然会产生质的飞跃,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
总的来说,科技生产力观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最为突出的方面,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始终。只有科学地理解科技生产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中的地位,才能对其生产力理论乃至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科学的阐释与时代化发展。
二、隐性内在逻辑线索:生态生产力观
通过文本梳理,我们便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除是显性的科技生产力观外,也是与自然生态紧密结合的、蕴含着丰富生态意蕴的生态生产力观。这构成了他们生产力观的一条隐性内在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资本主义批判、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上。
首先,从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来看,生态生产力主要体现为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自然生产力构成了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的天然物质基质。长期以来,学术界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将生产力视为“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5](p116)。该认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了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正确认知。因为这个定义尤为突出生产力概念中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强调的只是人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征服与改造,却将社会生产力得以产生与持续发展的自然根基完全阉割掉了。“它离开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素,孤立地侈谈‘人的能力’,只突出了生产力的社会性,似乎‘生产力’仅仅是指‘社会生产力’”[6],因而也就严重忽视了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外部自然界是人类生命和物质生产发展得以存续的首要前提与天然物质根基,并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p170)。就劳动者要素本身的自然生产力而言,这种自然力是劳动者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最基本的力量,其归根结底来源于自然的供给。因为外部自然对象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均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即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4](p161)。就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要素而言,无论是天然的自然资源或“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2](p211)皆来自外部自然界,离开外部自然界,我们便什么也不能创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专门阐述了自然力应用于社会生产的问题,“大生产……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1](p356)。通过对自然生产力在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中地位与作用的考察,马克思认为,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既定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单纯存在是以自然生产力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自然生产力充当了一定量的必要劳动,从而构成了剩余价值存在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同其他生产部门相比,自然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为突出,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及其所体现的使用价值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土地的生产率。因此,马克思指出自然生产力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
其次,从生态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态异化现象。正是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揭露,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坚持了外部自然的优先性,而且进一步深化了生态生产力观。一方面,资本主义过分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生产力片面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诸生产方式下,尽管生产力发展低下,但总体来说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同情和共感。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生产成为人的目的,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聚建立在对人与自然的极度剥削的基础上,人与自然只是作为生产的前提条件和手段而存在,这就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
在资本逻辑的策动下,资本凭借其强大的宰治力在全球范围内到处扩张,素被尊崇的自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自然被视为完全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内在价值的僵死之物,仅仅作为一个天然资源库成为依据资本增殖而被任意使用和破坏的客体。这些做法不仅对自然界造成了毁灭性的损伤,也破坏了生产力持续增长的物质根基。诚如恩格斯在谈及英国煤炭业发展受限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土地耕作的改良和森林砍伐殆尽,木炭越来越贵,产量越来越少。”[4](p39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阐述了机器大工业在农业中的使用所造成的人与土地物质变换断裂的现象。马克思认为,机器大工业虽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但是这种革命性的作用是以对土地的破坏和土壤肥力的衰退为代价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p579)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2](p580)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将自然生态提升到文明兴衰的高度。他通过列举人类为短期利益破坏自然生态而丧失生产根基的事例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p559-560)在这里,恩格斯既通过鲜活的历史教训批判了资本主义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肆意干预自然的短视行径,也划定了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指明了人类生产发展的永恒生态限制,从而警醒人类必须在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与自然进行合理有度的物质变换,更要注重生产力发展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否则,对自然的无节制开发必然会引发生态灾难,招致自然无情的报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的生产力片面发展还造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资本主义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不断扩大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价值的生产,因而也就需要不断扩大对外部自然的索取。这必然造成自然资源的加速耗费以及生产废料的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社会生产发展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所以,资本主义差不多每十年就要遭受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一方面大量的自然资源被浪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时空的压缩加速对自然的掠夺。这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毁伤,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正如马克思所言:“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3](p37)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了同它的外壳不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生态性这一痼疾,必然超越自然所能承载的限度,无论其在生产中如何节约,都无法逆转这一不断衰退的趋势,从而必将被一种绿色的生态化的发展方式所取代。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生态生产力概念,但通过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我们可以看出其生产力观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
最后,从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来看,生态生产力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必然路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p185)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路径非常明晰: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对奴役人的一切关系的积极扬弃。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以上诸种矛盾皆根源于私有财产。因而,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便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不仅指明了人与自然矛盾的制度根源,也表明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而不仅仅是人的解放。
资本主义在大量占有与消耗自然资源基础上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虽然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创造了条件,但在其非生态性的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所以,资本主义不仅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无法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永恒生态限制,更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至多是实现人的物性意义上的相对自由,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不存在生态关怀。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我们将超越物的依赖性之下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虚幻共同体”,进而迈向社会生产力从属于“人的自由个性”的真正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到那时人类将摆脱资本逻辑的发展桎梏,外在自然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永恒界限,“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p928-929)。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4](p184),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的社会性的统一。因此,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更要注重生产力发展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这样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终极关怀,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重要体现。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生态生产力概念,但从生态生产力的几个侧面——生产劳动、资本主义批判、共产主义——来看,生态生产力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拥有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从根本上驳斥了国内外学者对他们生产力观的批评指责,彰显了他们生产力观的科学性、革命性、真理性。
三、内在关联: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的辩证关系
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内在逻辑线索,构成了他们生产力观的整体性视域。那么,两条逻辑线索的内在关联便成为我们当前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生态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力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生态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力具有承载功能,是其存续的自然前提与物质基础。科技生产力作为改造自然的巨大物质力量,其产生是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而也是通过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三要素得以实现的。而这三要素归根结底建立在自然的根基之上,离开了外部自然,它们只能作为抽象的生产力构成要素而无法现实地作用于生产过程。就劳动者要素而言,无论劳动者智力、文化水平的高低,他们都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因而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p220)就劳动对象要素而言,劳动对象是科技生产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无论是未经人类加工就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还是在科学技术作用下经人类加工而产生的劳动对象,皆是自然资源或自然资源形态变化的产物,其终极来源皆是自然界。因而,外部自然是人类生产的现实劳动对象和可能的劳动对象的总和。就劳动工具而言,劳动工具是科技生产力的集中显现。无论是最初应用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简易工具,如石器、磨、风车、水车等,还是随后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机器、自动的机器体系等,其生产的材料、原料、动力来源的燃料能源等,皆来自自然界。因而马克思将自然界视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9](p428)。可以说,离开了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就没有劳动工具的存在,科技生产力也就无法存续。关于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2](p586)并将外部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分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土壤的肥力、水产丰富的河流)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奔腾的瀑布、森林、煤炭矿产)两大类。马克思认为,在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初期,生产力发展取决于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在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取决于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这就从劳动者对自然界的本原性、劳动资料对自然界的根源性、劳动工具对自然界的依赖性等方面,揭示了生态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力的前提性与根基性作用。因而,马克思将“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p170)。
另一方面,生态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力也具有制约性或颠覆性影响。诚然,自然资源所蕴含的巨大自然力作为不费分文的资本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资本家积累了超额利润,也为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可以说,自然资源的丰裕度或自然生产力的大小与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按照马克思“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的思想,科技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皆是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作用于生产过程的,因而必然从根源性上受到外部自然的制约。马克思认为,生态生产力的这种制约性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这里,价值体现在多少产品中,取决于土地的生产率”[8](p924-925)。即自然条件的优劣决定了农业产量、使用价值的高低。尽管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优化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改变了土壤的原有条件,实现了对土地的科学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肥力与劳动生产率。但归根结底,无论科技生产力在农业中表现出怎样的革命性,始终不能消除自然条件的永恒限制。在工业生产中,马克思指出“就各个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中断”[10](p121),比如十八世纪的工人经常因缺乏劳动资料而停工。这种中断突出表现在季节性的生产部门因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发生的不同程度的中断上。尽管强大的科技生产力消除了劳动资料短缺对生产造成的困扰,也通过对自然规律相对科学的认识、利用以及对自然的全面改造,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但是科技生产力仍然处处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仍面临着被颠覆的威胁。目前,我们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生产力,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全球仍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威胁,仍被可持续发展挑战的焦虑所困扰。这是因为,“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11](p32)。总之,科技生产力面临着生态生产力的永恒限制。
(二)科技生产力对生态生产力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对科技生产力的不合理使用改变了人们对生态生产力的看法。科技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巨额的社会物质财富,因而被资本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与发展。正是科技生产力这种强大的支配力,使资本逻辑得到空前发展。资本逻辑将生产力的片面发展、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作为生产的价值归宿。这样,其过分追求的经济利润最大化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大量耗费与毁损的基础上的,必然以牺牲生态生产力为代价,会导致科技生产力的片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2](p589),“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8](p289)。科技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在观念层面形成了见物不见自然的“拜物教”,即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物质要素狂热追求的物役经济,使人们从思想意识深处弱化了自然及其内蕴生命的价值。由此,自然被视为完全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内在价值的僵死之物,仅仅作为一个被动客体成为“依据我们的目的加以使用的‘它’”[12](p218)。这为资本主义疯狂地开发、掠夺自然资源,榨取自然生产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护,使其具有了“合法性”的外观,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资本主义对科技生产力的不合理使用而引发的一系列生态问题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与深化了生态生产力思想。
另一方面,科技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有机结合,既可以促进生态生产力的发展,又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前所述,没有生态生产力,科技生产力就无从谈起,而没有科技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得到有限的利用,而不能大规模应用于生产过程,也就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马克思在谈到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时指出:生产力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p53)所决定的。因而,我们可以将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视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因素,将之归属于科技生产力范围;将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视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因素,将之归属于生态生产力范围。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科技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科技生产力既改变了自然生产力的自在状态,也放大了自然生产力所蕴含的生产效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2](p444),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内在逻辑线索,既强调了科技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强调了生态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是与自然生态紧密相连、充满绿色意蕴的科学理论,而绝非是一些国内外学者所认为的只见科技不见自然的“生产力决定论”。因此,只有充分认识自然生态在他们生产力观中的重要地位,才能科学而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