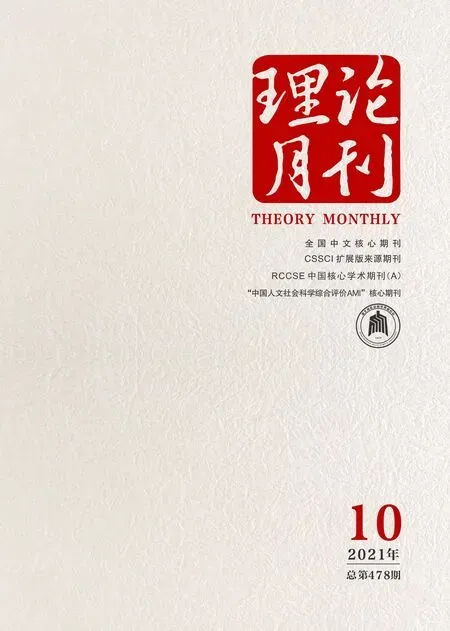矛盾与创构:从读书法看朱熹的经典诠释
□汪冬贺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48)
谈到朱熹读书法,以往的研究或是仅停留在读书理论层面,没有看到朱熹读书方法与经典诠释的关联①此类成果最多,如郑春汛:《〈朱子读书法〉学术价值新探》,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邓庆平、王小珍:《论朱子读书观》,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杨天宏:《读书六法:朱熹读书方法演绎》,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另有大量侧重中学语文阅读的成果,兹不枚举。;或是从诠释学角度解读,重在构建朱熹阐释学体系,但未将读书法与其诠释实践活动相结合②如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春青:《朱熹与中国经典阐释学》,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即使有注意到朱熹经典诠释的作品研究,亦只强调其实践与理论相一致的部分,未能对朱熹读书理论及诠释思想作以整体的观照③如尉利工《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一书第五章“朱子经典诠释的个案研究”考察了朱熹《易》《春秋》《诗经》《尚书》《礼》等诠释思想,参见尉利工:《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95页。。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朱熹读书法,厘清朱熹读书法的基本意涵、学术价值及其内在理路,再结合相关读书实践,观察朱熹是否遵从其读书方法阅读经典。进而思考:朱熹读书法蕴含了怎样的诠释思想?朱熹读书法以怎样的路径进入其理学思想体系?现代学术视野下对其应如何评价?如欲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从朱熹读书法本身谈起。
一、朱熹读书法的理论进路
宋人齐熙曾将朱熹读书法系统提炼为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1](p15),这样的好处是便于辑编成书,将符合每条主题的言论置于其下,一目了然;缺点是过于笼统,容易将读书方法的不同层面混在一起。尽管事实上朱子读书法本身确是将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谈的,但并不代表没有逻辑,相反,朱子读书法有着明晰的内在理路。钱穆在《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学籥》等书中设专章反复详说。徐复观更是说:“朱元晦真是投出他的全生命来读书的人,所以他读书的经验,对人们有永恒的启发作用。”[2](p200)那么,朱熹读书法的具体含义究竟是怎样的?其在哪些层面“对人们有永恒的启发作用”?
读书,按其模式一般可分为知识型阅读和研究型阅读,朱熹之读书无疑属于后者,这是由其疑问的读书方式决定的。正如左东岭先生所说:“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往往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质疑,尤其是对于经典的作品与权威人士的著作更是如此。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大不相同,怀疑是读者面对所有著作所应持有的态度。”[3](p67)朱熹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4](p343)前一阶段是发现问题,后一阶段是解决问题,疑问之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便是学问长进的过程。而疑问的提出尤其重要,学术研究的推进正是以疑问为起点的,只有先发现问题,才有解决问题的前提,从无疑到有疑正是朱熹问题意识的表现。学问长进的表现是解决问题,达到“无疑”,但实际上,每个人囿于知识水平等因素,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朱熹又提出“阙疑”,即存疑。他认为遇到暂时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倘若强解,难免穿凿,不如阙之。“经书有不可解处,只得阙。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谬处。”[4](p351)并且朱熹认为阙疑并不影响学问长进:“大抵读书须见得有晓不得处,方是长进。又更就此阙其所疑而反复其余,则庶几得圣人之意、识事
理之真,而其不可晓者不足为病矣。”[5](p2646)这尤其体现在朱熹《楚辞集注·天问》中,其间有多处无法解释的问题,朱熹均以阙疑存之。概言之,朱熹“阙疑”并非置之不问,而是反复玩味而未能发覆者,方且存焉;同时不强解,体现了朱熹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朱熹阙疑之处客观上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学术研究的问题,可谓一种隐性的“有疑”。
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对文本作精细化阅读,而精细化阅读的前提是熟悉文本。朱熹以为熟悉文本的基本方法在于多读、反复读、逐字逐句地读。如他以《大学》为例:“若看《大学》,则当且专看《大学》,如都不知有它书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穷,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莫论遍数,令其通贯浃洽,颠倒烂熟,无可得看,方可别看一书。”[5](p2421)又说:“读书之法,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时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时如不知有下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从头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贯。然方其看此段时,亦不知有后段也。如此渐进,庶几心与理会,自然浃洽。”[5](p2810)可见熟悉文本之要诀在多读,不计遍数,但并不意味着死记硬背式的读书,而是包含一定次序:逐字逐句、由章入篇、从头至尾,并且一书“无可得看”之后,方另看他书。当然,强调循序渐进也是朱熹一贯的看法。
阅读的精细还包含对比式阅读,在对比中进一步思考问题。在朱熹看来,发现问题后,须参看前人诸家解说,在不同注解中发现差异或矛盾。对此,朱熹说得很详细:“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4](p350)对比的目的是进一步发现矛盾,然后将诸家之说相互诘难,将其推至极处,“穷尽其词”,然后判断是非对错,如此“自然光明灿烂在心目间,如指诸掌”[4](p3815)。这一过程就需要不断回头阅读原文,玩味细绎,仔细思考,从而进一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
此外,还有读书的精神状态——虚心。朱熹谈读书反复强调虚心,如:
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4](p334)
虚心平气,徐读而审思,乃见圣贤本意,而在己亦有着实用处。不必如此费力生说,徒失本指而无所用也。[5](p2040)
大率观书但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5](p1342)
“虚心”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它要求读书时抛却纷乱杂念,同时保持专一投入的精神状态,并且包含不以己意强解圣贤本意的读书原则。抛却杂念即“刷刮净了那心”[4](p333),专一投入“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4](p333)。同时,“虚心”还有一个特定要求——不责效。“责效”即追求效果,一旦心存责效之念,虚心所蕴含的湛然凝定之内在要求便荡然无存了。所以朱熹说:“读书看义理,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责效。才责效,便有忧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结聚一饼子不散。今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只专心去玩味义理,便会心精;心精,便会熟。”[4](p317)也就是说,读书要放宽心,不能忧愁急迫,一旦内心有这些求功求速之念,就难免急躁,一急躁便无法专心细读,如此就难以发现问题,更别说解决问题了。而且,不虚心就无法深切体会圣人之意,容易代以己意,这是虚心的第三个层次,也是朱熹读书的原则问题。
关于读书原则,朱熹强调最多的是尊重文本及圣贤之意。他谈读书时屡屡出现“正意”“本文之意”“圣贤之意”等字眼,要求随文解义,以书观书。与“正意”“本文之意”“圣贤之意”对应的是“己意”“私意”,朱熹反对先立“己意”、附会穿凿。有学者称之为“圣书意识”[6](p156),这种“圣书意识”决定了朱熹阅读经典的基本原则。
由于此原则与本文所论问题关系密切,故将朱熹部分相关言论摘录于下:
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圣贤真实意思;如其不然,纵使说得宝花乱坠,亦只是自家杜撰见识也。[5](p2457)
近见学者多是率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撰成耳,如此岂复能有长进?[5](p2600)
大凡读书,须是虚心以求本文之意为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即是任意穿凿。[5](p2219)
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5](p2213)
大抵近世说经者,多不虚心以求经之本意,而务极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间略有缝罅,如可钩索,略有形影,如可执搏,则遂极笔模写,以附于经,而谓经之为说本如是也。[5](p2415)
朱熹批驳当世学者读书不虚心求本文之意,而附会穿凿,曲解圣贤原意。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圣贤原意与文本之意的关系,朱熹认为二者是统一的:“本意”是给定且唯一的,古代圣贤将自己的本来意图寄寓在经典作品之中,只要回归文本正意,确保其真实不虚,便能保证圣贤原意。
其次是如何确保本文之意的客观性。朱熹认为主要是摒除自家私意。所谓“自家私意”,可以归纳为朱熹所言的两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4](p343)“旧有先入之说”即先儒旧说,朱熹并不反对前人注解,而是反对不加分辨地以旧有之说解释原文。而“私意”便是“自主己说”,朱熹多次言及读书不可先立己意,否则便是“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4](p3681),如此只是穿凿附会、空成杜撰、自家见识,而不能见圣贤本意。
作者之意与文本之意的关系,是现代诠释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朱熹的观点实际上也涉及中国传统经典解释理论与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区别,对此,已有学者进行比较①参见邵东方:《朱子读书解经之诠释学分析——与伽达默尔之比较》,载陆晓光主编:《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80页。,本文无意赘言,但我们需要认清朱熹坚持此种读书原则的依据,即为什么圣贤原意与文本之意是统一的。这源于朱熹“理一分殊”的哲学依据,因为天理只有一个,正所谓“理一而已,安有两三说皆是之理?”[4](p3447)“经书中所言,只是这一个道理,都重三叠四说在里,只是许多头面出来。”[4](p3731-3732)所以,把握住文本之意即得圣贤之旨。
综观朱熹读书法,各个层面呈现出密不可分的关系:疑问是研究型阅读的入门,精细化阅读是进一步思考疑问的关键,也是提出问题的前提,而虚心之精神状态则是保证精细化阅读的内在条件,同时又指向抛却私意、回归文本之意、得圣贤之旨的读书原则,这种读书原则反过来又要求对文本精熟,反复玩味、细绎涵泳,整体上融贯会通、明晰有序。
二、朱熹读书法与诠释实践的矛盾
既已弄清朱熹读书法的基本意涵及理论进路,我们需进一步考察的是:朱熹是否遵从其读书法读书,也即其读书理论思想与实践活动是否具有一致性。
如前所述,朱熹强调“本文正意”“圣贤之意”,反对“尽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4](p336)。在这一基本原则下,文献上尊重古书版本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给许顺之的书信中,朱熹说得很清楚:
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旧来亦好妄意有所增损,近来或得别本证之,或自思索看破,极有可笑者。[5](p1749)
朱熹言之深切,唯恐轻易更改,变了前贤之意,误了后辈学人,更强调“其罪将有所归”。因此在版本上要求尊重古本,有所依据,不妄意增损。但在朱熹的著作中,其所行与所言相悖之例甚多,《大学》便是很明显的例子。
朱熹对《大学》的改造很多,今人多有辨正①。概言之,朱熹对《大学》主要有三点调整:一是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7](p4);二是将《大学》原文所引的《诗》《书》等内容因其含义加以拣择,并依据三纲八目的次序重新排列;三是补写了“格物致知传”。对比前文朱熹所宣称的读书之法,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是不可接受的。朱熹之所以作出以上调整,主要在于他认为“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次序”[7](p4);至于“补传”,则“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弟子已有怀疑,《大学或问》中记载有师生对话:“曰:然则子何以知其为释知至之结语,而又知其上之当有阙文也?曰:以文义与下文推之,而知其释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为结语也;以传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阙文也。”[8](p523)即使如此,朱熹的解释依然无法弥合矛盾:从文献学角度来说,对版本的改动必须有版本学依据,用朱熹自己的话说,要有“别本证之”;以文义、句法推论,亦不符合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态度;而所谓经传体例更是朱熹自己的设定,以自己的预设来推导结论则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淖。今人业已指出:“《大学》本身的文义结构是很完整的,并不存在前人所说的阙文、错文等问题。同时,《大学》也不存在程朱所说的经传之分。”[9](p69)但朱熹对自己的这番操作显然颇为满意,他在《大学章句序》中明确说:“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7](p2)“窃附己意”已然是承认了自己视为禁忌的“己见”“私意”。尽管朱熹强调轻易改动前贤文字“其罪将有所归”,此处亦称“极知僭踰,无所逃罪”,但“未必无小补”已然透出自得之意。
再看朱熹要求的“不任意穿凿”。朱子最重要的“格物”说显然并不是“本文之意”,且难脱“以附
①相关成果颇多,如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59—71页;陈来:《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载《文史哲》,2007年第2期;丁为祥:《〈大学〉今古本辨正》,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对朱熹《大学章句》的改动问题均有详细论说。于经”之名。这从“格物致知补传”中可以看出: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7](p7)
关于“格物”,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7](p4)陈来将其归纳为三个要点:即物、穷理、至极。朱熹认为格物的基本意义是要穷理,但穷理要具体事物上穷,穷理又必须穷至极至[10](p140)。这是朱熹理学的话语,而非《礼记·大学》中“格物”的本义,按回归文本之意即圣贤原意的读书原则,朱熹对“格物”的理解明显是不符合其本意的。
不过,“格物”的本义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关于《大学》今本与古本的争论,更是从古至今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只是借“格物”的争论说明朱熹读书方法与其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如朱熹读书法所言:“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4](p652-653)然而,朱熹之“格物”不是“圣人句中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朱熹读书法与实践的矛盾还体现在其对《诗经》的解读。朱熹认为前代以《诗序》解《诗》“委曲牵合”,失了“诗人之本意”,批评道:“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11](p13)朱熹认为回归《诗经》的本意,要“以诗解《诗》”,还《诗经》以“诗”的本质,即要以文学的眼光审视《诗经》。
譬如《关雎》主旨,朱熹在《诗序辨说》中反驳《毛诗序》:“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盖淫者,乐之过;伤者,哀之过。独为是诗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而序者乃析哀、乐、淫、伤各为一事,而不相须,则已失其旨矣。至以伤为伤善之心,则又大失其旨,而全无文理也。”[11](p16-17)这就辨正了《关雎》的主旨,非为后妃之德,而是文王之德,更非刺诗,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乃情感的中和程度问题,而非《诗序》所说“忧在圣贤”之说。从朱熹所言“诗之本旨”的角度观之,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辨正可谓有正本清源之功,驳斥了长期以来《诗序》牵强附会的解读方式,所以莫砺锋指出朱熹“使《诗经》学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12](p79)。但深入研究《诗集传》,却发现朱熹并非专一于《诗经》之“文学性”,以理学观点论述《诗经》篇目不胜枚举。就《关雎》而言,尽管朱熹认为孔子所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但在后注中却指出“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11](p3)。如果说“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依然属于儒家温柔敦厚的风教诗学传统,那“玩其理以养心”则为宋代理学话语。在《周南》中,朱熹又言“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11](p1)。可见朱熹一方面承认国风为民俗歌谣之诗,一方面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约之,这显然是朱熹诗学解释的矛盾。
同样的矛盾亦出现在《楚辞集注》中,朱熹言《天问》旧注“不复能知其所以问之本意,与今日所以对之明法”,于是“悉以义理正之”[13](p63),对屈原《天问》之问题除所谓“无稽之言”“诸怪妄说”不答以外,余者皆逐一作以尽可能的回答,但问题在于朱熹多以理学话语作答,所谓还《楚辞》以文学面貌亦终成虚话。
三、矛盾之原因与朱熹的理学创构
从前文所述可见,尽管朱熹谈读书时一再强调不能以己意解说经典,但其读书实践与理论思想却多相扞格。那么,作为大思想家,朱熹缘何会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呢?显然并非其功力不行,亦无关学术态度。黄榦有言:“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见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夜坐或至三四更”[1](p99),可见其努力;朱熹注书更是字斟句酌:“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轻等重方敢写出”[4](p3446),可证其严谨。所以刘笑敢高度评价朱熹:“就个人的文献水平和学术功力而言,朱熹绝对属于最高层次的人才和学者,其兴趣之广,钻研之深,是很少有人可以超过的。就个人的态度和努力程度来说,恐怕更是数千年难以有人相提并论。”[14](p233-234)其实,这样的尴尬困境,主要是由以下三点原因造成的:一是读书与注书的不同性质;二是朱熹读书的终极目标;三是朱熹理学循环论证思维的先天缺陷。
首先,读书与注书的不同性质。尽管从诠释的过程来看,读书是注书的前提,但仍有必要细加辨析。陈立胜已从二者的承担主体角度指出了其差异:“读者和释文者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读者可以仅止于阅读而已,而不必将读书之所得形诸文字;而释经者则要把阅读所获得的‘意义’予以文字的表达。读者阅读过程中所牵涉的‘诠释’因素,对于读者本人而言,完全是非课题化的、不自觉的;而诠释者之为诠释者,理应把文本的解读作为自己的专题。学理阅读现象学与文本诠释学亦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焦点与领域。”[6](p155)读书与注书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形式,注书是一个历时性的意义转换过程,需要从各个角度审视,如语言角度、历史环境、文本的历史性与思想的创生性之间的矛盾等。在这一过程中,朱熹客观上不得不面对注书时四重时间的交错:圣人思想文本的历史时间、历代研究史的动态时间、自己对经典注疏的构思时间及其真正着手注疏行为的发生时间。易言之,他在主观上想要重新回到《四书》等经典的原初思想世界,但现实中,他与经典文本处于不同的历史时空,社会背景、学术环境乃至语言情境等差异悬殊。以《大学》为例,《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若要回到《大学》文本所表征的原初世界及意义中去,则须契合先秦的礼乐社会及礼学学术之历史语境,而朱熹所处的宋代是理学发展的时代,这种偏差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应该注意,朱熹所言读书是一种研究型阅读,具备现代意义上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朱熹在读书法中要求尊重本意,还原经典原义,确保经典意义的客观性,力图克服个人主观上的偏见或误解,以重现文本所体现的圣人思想,实为其求真求实的学术追求之体现。然而,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往往以注释、解说经典为载体,而非现代论文的形式。古代的注经者也往往借助经典注释、解说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由此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学术传统。如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王夫之《庄子通》《庄子解》《读四书大全说》、方以智《药地炮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皆是借用经典文本来创造新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每一代的思想家都是通过经典文本的解读不断回溯传统思想家的观念和思想,完成自身思想的表达和观念体系的建构”[15](p128)。这一传统使得经典文本形成巨大的意义空间与诠释张力。朱熹身处其中,因此在其读书实践中,就很容易将读书之学术研究与思想创造两种不同方式混为一谈,这是不可避免的。刘笑敢曾明确表示:“经典注释和诠释会带来文本的限制,而体系建构则要求创造”,这种经学注释传统“必然会出现经典文本自身意义与诠释者的新体系之间的紧张或矛盾。”[14](p51)所以,朱熹面对建立自己理学思想体系的内心呼唤时,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尊重文本正意以求还原圣贤本旨的学术追求。如注解《四书》时,不同经典之间的意义并不契合,他既需要调和不同文本的意义冲突,又要尽可能地融贯前人尤其是二程之学于经典著作中,以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所以在其真正着手注书时,必然会出现经典文本原初意义与其所创构的新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就产生了朱熹读书法与其经典注疏之间的龃龉。
其次,朱熹读书的终极目标。朱熹所言读书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纯阅读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他多次教育门人:“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4](p337)读书当反求诸身,就自家身上推究,而非只当文字看。在朱熹眼中,“读书乃学者第二事”[4](p313),“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4](p313)。可见,“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第一事、第一义,切于身心才是目的所在。这首先体现为“读书是格物一事”[4](p319),因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5](p668),读书是格物必然之功夫,这于前文所述读书方式、精神状态以及原则上多有体现。此处,不妨再多举一例证之,朱熹谈《论语》读法时告诉弟子:
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将两段比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将第三段比较如前。又总一章之说而尽比较之。其间须有一说合圣人之意,或有两说,有三说,有四、五说皆是,又就其中比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彻,则知便至。[4](p660)
“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是读书的次序问题;读《精义》为注重前人解说,将两段比较,判断得失是非,是对比式阅读;“合圣人之意”是朱熹回归圣贤本意的读书原则,“看得此一章透彻”乃读书要求之效果,而这些都可以统归于格物致知。正如陈来所言:“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直接关系到一切理学体系的着眼点——为学之方,又是他全部哲学第一个最终归宿。”[16](p284)但格物致知又并非其哲学的终点。朱熹又说:“《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圣贤之域。”[4](p480)可见,格物又是学者入道之门,物格知至,切己成圣,最终优入圣域,才是朱子哲学的终极旨归,亦是儒家思想体系中各家的普遍追求。因此,读书只是朱熹切己成圣的一种手段,是为其成就圣贤而服务的,至于学术研究的求真求实,自然归于次要地位。
最后,朱熹理学循环论证思维的先天缺陷,致使其无法保证客观还原圣人本意。所谓循环论证思维,即朱熹在论证问题时,往往预设前提,再围绕前提加以论证。比如朱熹在诠释《大学》之“明明德”处言:“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7](p3)在朱熹的思想中,“理”的本体性质规定了其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人生而具理,但在成长过程中人之气受到污染,因此需要“复其初”。由于“理一分殊”,“理”落实到人为“性”,“性”具于“心”,“心”具众理。那么,顺着孟子的“性善说”,性无不善,理无不善。但朱熹为了论证人和物的差异,只能提出“气”的范畴,但又无法说明“气”从何处而来,“理气同异”几乎是其哲学中“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16](p124)。
回到朱子读书法本身,“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4](p314)。读书的直接目的是“观圣贤之意”,而最终目的是“观自然之理”,这是由“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4](p3805)决定的。圣人之言是天理的表达,读书是为了体悟天理,而悟出天理的文本标准便是义理贯通浃洽。朱熹认为义理浃洽,自得于心,便是体认到天理,自然也就得圣人之意,“解读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4](p655)。所以天理随处充满,文字只是形式,不必过于拘泥。“理”的本体性存在决定了朱熹在论证问题时完全围绕“理”,所谓义理浃洽的文本标准亦是朱熹循环论证的必然方式而已。在这种思维模式的预设之下,也就不难理解朱熹读书理论与其具体读书实践所产生的龃龉了。
四、余论
明了朱熹读书理论与其实践产生矛盾的原因之后,我们则需在现代学术视野下重新评判朱熹的读书法及其经典诠释思想。
朱熹对经典的诠释,从学术研究看,是文本细读下对经典本意的追寻;客观效果上,是理论创构的思想体系建立之工作;就终极目标而言,则是体认天理、切己成圣的格物功夫。朱熹一方面强调求得文本正意、圣贤本旨,另一方面,他并非不明白这一原则执行的难度,他曾坦言:“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4](p2844)但是朱熹无法摆脱中国学术的注经传统,既囿于注疏经典的古老形式,又难以回避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时代要求,更限于其理学循环论证的思维模式。所以,即使是已经被朱熹视为文学作品的《诗经》《楚辞》,亦是格物穷理的对象,万事万物皆具天理,文学作品亦然:“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11](p2)甚至校勘学著作《韩文考异》,本应是纯粹性的文献文本,也渗透着朱熹的理学思想,钱穆便曾评价:“其所校勘,乃以求史实,而主要更在发挥义理。”[17](p1745)更不用说《四书》这种极具阐释张力的文本了。
当然,尽管朱熹付出极大努力也没能完全调和经典注释与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但我们却要看到朱熹已然是相当成功了,他努力以理学融贯不同文本的异质性,以格物致知为方法途径,以体认天理、优入圣域为终极目标,建立起了融贯会通的理学体系。其经典诠释与思想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固然重要,但思想体系的创构性却着实令人赞叹。
那么,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如朱熹经典诠释般的矛盾呢?现代学术中,注释、解说不再是经典诠释的唯一形式,学术论文、著作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情况突破了传统形式的藩篱,忠实于文本的对象性、客观性研究与不受特殊经典局限的开放性、现代性的思想建构活动可以同时存在[14](p59)。因此,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便不能重蹈朱熹矛盾的“覆辙”,毕竟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历史还原,求真求实是其内在要求。左东岭先生曾言:“我们真正需要的学术史是:研究者需要具有明确的学术原则与研究目的,他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应对各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学术贡献及发展过程作出客观清晰的描述,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方向偏差、理论缺陷、不良学风及学术盲点进行清楚的揭示,对将来的学术研究中可能解决的问题、采用的方法及拓展的新空间进行符合学理的预测,从而可以将后来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18](p20)首要前提便是客观清晰,否则就无法保证后面更深层次的要求,推进学术研究也就更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