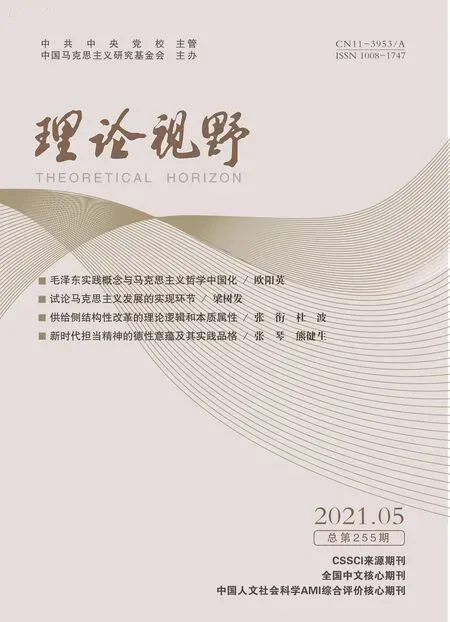马克思对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的批判*
■童 萍
【提 要】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诉诸永恒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认为正义的实现主要是分配制度的改良而非消灭私有制的革命,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并非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而是实现向小私有制的复归。马克思在批判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基础上,认为正义的性质不是源于抽象的永恒的正义观念,而是植根于经济关系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规范;正义的主题不仅仅是财富和权利的分配,而是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合理化;正义的实现不是某种思辨正义观念的自我运动过程,而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
近年来,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这就需要我们系统梳理和研究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深入挖掘马克思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时包含的关于正义问题的学术资源和方法启迪。本文以马克思对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三个层次的批判为主题,试图挖掘贯穿于其中的马克思正义观的丰富内涵和科学方法。
一、方法论的思辨性和非历史性
庸俗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他们在正义问题上也同样陷入方法论的思辨性和非历史性的误区。以蒲鲁东为例,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把正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工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在蒲鲁东看来,“正义是位居中央的支配着一切社会的明星,是政治世界绕着它旋转的中枢,是一切事务的原则和标准”[1]。而现实社会之所以充满不正义,就在于人们对于“什么是正义”这一原则问题不清楚。于是,蒲鲁东致力于为大家寻找一个关于“正义”的绝对真理。在蒲鲁东看来,正义的核心就在于平等,正义“就是在劳动的平等条件下使每个人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2]。也就是说,只有符合绝对等价交换原则的社会才是正义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3]。而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不合理就在于资本主义违背了这一社会发展中应该遵循的绝对等价交换原则。
如何确定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平等的呢?蒲鲁东引入了“构成价值”的概念。蒲鲁东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所组成,使用价值用来指称“一切天然产物或者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4];交换价值用来指称这些产品“所具有的相互交换的性能”[5],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商品之中是矛盾和对立的,而且这种矛盾和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商业竞争,市场竞争,产品过剩,货物滞销,颁布各种禁令,扼杀竞争,垄断独占,降低工资,制定限价法律,财富悬殊,贫困现象;这一切都源自价值的二律背反。”[6]而“构成价值”这一概念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何为“构成价值”?就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价值之间所形成的比例关系。对此,蒲鲁东有多次说明:“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方式自然地形成的社会里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7]“作为产品比例的价值,换言之,即构成价值,必然包含同等的效用与交换能力,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离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8]蒲鲁东提出,只要在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按照“构成价值”来进行交换,就能使劳动产品的价格和其实际价值之间保持公平的关系,从而增进社会的整体财富。
对于蒲鲁东从“构成价值”入手来构建一个社会发展的永恒正义原则的做法,马克思给予了严肃的批判。这一批判始于《哲学的贫困》一直持续到《资本论》。
第一,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错误地颠倒了正义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正义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法权和道德上的抽象表达,是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决定正义,而不是正义决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没有超越特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永恒的正义原则。而蒲鲁东则试图把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看成是原理、范畴的产物,“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9],并用黑格尔关于正题、反题、合题的纯粹逻辑公式来建构一个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永恒正义原则,这无非是奉行“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10],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1]而每个世纪出现什么样的原理是由“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2]来决定的,也就是由现实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无人身、无主体的抽象理性决定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也清晰地批判了蒲鲁东对正义原则和现实关系的颠倒,“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13],而不是以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为依据。在恩格斯看来,“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14]。
第二,蒲鲁东用“构成价值”来解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创新”事实上是对李嘉图理论的歪曲。马克思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斯密首次用劳动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不够彻底,斯密既强调劳动在价值标准中的作用,又承认其他价值标准,如斯密指出:“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等量谷物(即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比等量金银或其他货物,似更可能购买等量劳动”。[15]李嘉图指出了斯密的不足:“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他有时把谷物当做标准尺度,有时又把劳动当做标准尺度。”[16]于是,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进一步推进,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李嘉图指出:“衡量一种商品的贵贱,除了为取得这种商品而作出的劳动的牺牲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投入商品的劳动量的或多或少,是其价值变动的唯一成因。”[17]对于李嘉图的这一理论贡献,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嘉图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工资、利润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18],从而“使他的理论称为科学的体系”[19]。
而蒲鲁东的“构成价值”不过是把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进行平等主义的应用,是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乌托邦化。蒲鲁东认为,根据李嘉图提出的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可以推导出相同的商品价值包含相等的劳动量。因此,只要在劳动者之间保持恰当的价值比例关系,就可以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社会的正义,所以蒲鲁东认为:“价值比例理论其实就是平等的理论。”[20]“只有当每一个人的产品都和产品总量成比例时,劳动才能成为福利与平等的保证,因为劳动所交换或购买到的价值始终只能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21]上述分析表明,蒲鲁东之所以把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应用到平等和正义的理论建构中,无非是试图建构超阶级和超历史的正义观,并把这种超阶级和超历史的正义观运用到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以实现劳动者之间绝对的等价交换原则。对此,马克思给出了评价:“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揭示;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22]
二、“分配正义”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
由于蒲鲁东坚持正义的思辨性和非历史性,所以尽管他满腔热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但是他没有深入分析资本主义不正义的社会现实基础,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关系,而是仅仅在劳动产品之间是否实现等价交换的问题上兜圈子。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明确地提出了“合乎等价交换的才是正义的”这一观点:“农夫以某种数量的小麦卖给消费者,在称好分量之后,他伸手到量器中抓出一把粮食来,那就是盗窃;主讲的教授是由国家支付薪给的,如果他通过书店又把讲课的内容再出卖一次,那就是盗窃;领取干薪的人利用虚名作为代价而得到很大的利益,那就是盗窃;公务员、劳动者,无论是谁,当他所生产的仅仅是一,而领取的工资却是四、一百或一千,那就是盗窃;这本书的发行人和我这个作者,如果所取的代价高出它的价值一倍,那我们就是在盗窃。”[23]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是不正义的,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就是对工人劳动成果的盗窃。蒲鲁东认为,要实现合乎正义的等价交换,就必须“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24]。
和蒲鲁东一样,李嘉图社会主义者也持同样的观点。李嘉图社会主义者虽然内部思想有分歧,但他们分享着共同的思想倾向,即“同情工人运动,将欧文合作社运动的许多观点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著述中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阶级冲突视角联系起来”[25]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试图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吸收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如威廉·汤普逊认为:“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劳动是财富的显著属性。自然的力量不能使任何东西成为财富品。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26]既然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那么等量劳动应该得到等价报酬,这是“分配的自然法则”,遵循了这个法则的交换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各种等量的劳动,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那是公平且合理的。”[27]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不正义的,就在于劳资之间的交换不是等价交换,“一方只是都给出去,一方只是都拿进来,一切不平等的实质和精神也在于此”[28]。“在生产者与资本家间的全部交易,明明是一种欺骗——是一幕滑稽戏剧。在事实上和在千千万万的实例上,这一赤裸裸的盗窃,已成为资本家与业主所赖以设法使他们自己寄生在生产阶级身上,并且从他们身上啜吸全部精华的合法勾当了。”[29]因此,要实现社会正义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交换制度,按照贡献原则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对于庸俗社会主义从交换领域和分配领域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正义问题,马克思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交换领域就是初次分配领域,交换是由生产决定的,交换和生产、分配、消费作为环节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总体。其中“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30]。因此,那种把分配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相并列的做法“完全是幻觉”。交换领域中的自由平等和等价交换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正义性,相反,资本主义恰恰是在交换领域自由平等原则之下隐藏的生产领域的不平等,所以仅仅追求交换领域中的劳资等价交换或分配领域中的应得正义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对于这一理论失误,马克思指出,“从这种简单流通本身(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这里掩盖了产生简单流通的各种较深刻的过程)来考察,除了形式上的和转瞬即逝的区别以外,它并不暴露各个交换主体之间的任何区别。就是自由、平等和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王国”[31],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庸俗社会主义者却“把适应于这种等价交换(或被认为是等价交换)的平等观念等等拿来同这种交换所导致和所由产生的不平等等等相对应”[3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根源并不在流通交换,庸俗社会主义者却一直在批判交换和流通领域的不正义,显然是没有透过资本主义社会流通表象的迷雾,触及生产领域的不正义问题。
强调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的正义在实践中必然走向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马克思认为,既然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那么只有通过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实现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社会正义。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不正义、不平等’与资本主义总体系统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并且永远不能被改良。”[33]而庸俗社会主义“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矛盾,但又认为这种矛盾是可以在这一制度的框架内加以消除的”[34],因此他们拒绝革命,比如蒲鲁东提出:“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由个人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35]于是他们主张实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36],试图通过改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银行和资本来实现社会正义。对于庸俗社会主义的这一主张,马克思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37]和庸俗社会主义的改良方案不同,马克思主张“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38]。恩格斯也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他也批判过仅仅把追求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确信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一定会发生变革,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350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39]
三、复归小私有制的理论旨归
如上所述,在蒲鲁东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不正义就在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没有实现“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于是,蒲鲁东极力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不是为了要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为了返回到小资产阶级私有制,在这里每个劳动者都成为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小私有者。正如日本学者城塚登所指出的,蒲鲁东所“攻击的并不是所有的私有财产,他不过是反对造成大资本家有可能掠夺小生产者那样的财产。他一贯认为,人人都要有少量的财产,这是幸福的保证。因此,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工人用自己的储蓄购买工场成为小财产的所有者,而不是扬弃私有财产的本身”[40]。
对于蒲鲁东复归小私有制的理论旨归,马克思进行了批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小商品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者是交换价值的发达形式,后者是交换价值的简单形式,蒲鲁东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抓住交换价值本身的简单规定性,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比较发达的对抗形式”[41],但是蒲鲁东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42]。也就是说,劳动者个体私有制作为私有制的一种形态,随着分工的扩大和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蒲鲁东等人的想法十分愚蠢,“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43],于是蒲鲁东提出要消灭资本和货币,从而恢复到自由平等的交换制度。马克思认为,这些口号的实质就是试图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退回到小商品生产,从而否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开历史的倒车。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庸俗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须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44]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继续批判道:“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45]
与蒲鲁东为代表的庸俗社会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主义制造了大量的不正义,但同时孕育了消除这些不正义的现实力量和经济条件,“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46]。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当作伦理不正当简单抛弃,而是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现实的变革和实质正义的实现。对此,恩格斯的理解把握住了实质:“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47]
小结
通过对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的批判,马克思立足于历史根基批判和建构其正义观的致思路径得以澄明,马克思正义观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得到彰显。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性质不再是源于抽象的永恒的正义观念,而是植根于经济关系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规范,因此应该回到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去追寻正义的存在论基础;正义的主题不仅仅是财富、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而且是更深层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应该以消除异化和剥削为核心,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目标;正义的实现不再是某种思辨正义观念的自我运动过程,而是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应该以无产阶级为主体,以扬弃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为基本前提,使劳动真正成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手段,实现人类物质生产和自主活动的有机统一。恰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48]马克思并非拒斥正义,而是坚持必须通过变革现存生产关系的革命实践以实现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正义,因为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正义最终必将带来普遍的人的正义。
注释
[1][2][23]【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4~55页;第271页;第304~3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4][5][6][7][8][20][21]【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85页;第100页;第102页;第100页;第109页。
[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10][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第607页;第607~608页。
[13][36][37][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第436页;第436页;第77~78页。
[14][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第164页。
[15]【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页。
[16]《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页。
[17]《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71页。
[18][19][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页;第93页;第93页。
[24][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第191页。
[25]【美】E.K.亨特:《经济思想史》,颜鹏飞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26]【英】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页。
[27][29]【英】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7页;第53页。
[28]【英】约翰·格雷:《人类幸福论》,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7页。
[30][41][42][43][45][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3页;第204页;第453页。
[31][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5页;第305页。
[33]【美】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8页。
[40]【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