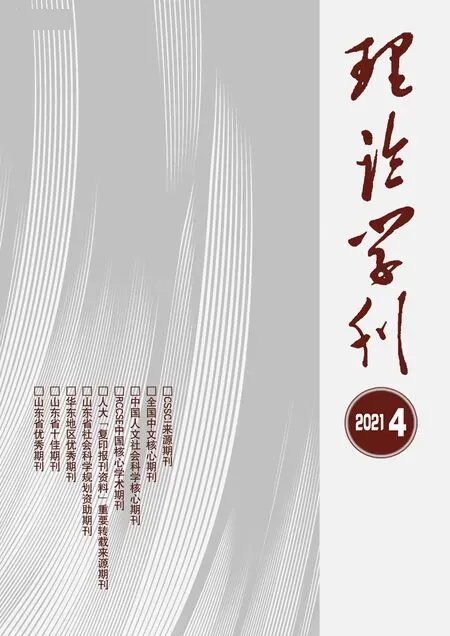调查与革命:社会改造追求下的李大钊
黄道炫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社会调查兴盛于近代中国,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的形成,同李大钊关系至大。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凭着对社会改造的关怀及学者的训练,已经对社会调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改造要求和实践传统,自觉地通过社会调查了解中国实际。李大钊的改造社会要求使他能够很快接纳近代兴起的社会调查,而社会调查的结果又导致他更加坚定自己的社会改造立场,加速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一、人力车夫和自杀者
近代中国的社会调查肇始于晚清,据统计,《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计有调查消息和案例1489个,其中中国人自己做的国内调查有957个(1)参见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当然,这时候的调查多数都比较粗浅,比如《浙江潮》1903年刊登的《处州青田县调查稿》,涉及青田县的官场、书院义塾、学生、历史人物、田产交易、土产、风俗、烟馆、妓院等,均只有寥寥数语(2)《处州青田县调查稿》,《浙江潮》1903年第6期。。较具学术自觉的调查一般认为是1914—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做的《洋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该调查得到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的帮助,共调查了302个洋车夫的生活情况。此后,社会调查在中国广泛开展,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经久不衰的现象。
社会调查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同近代中国的大变局息息相关。面对列强的冲击,晚清中国自觉意识不断强化,在和西方世界的比照中,既猛醒自身之不足,大力学习西方科学;也在碰撞中区分自我,产生更加浓厚的自我认知要求。社会调查兼具这两个因素,既有科学精神的渗入,也代表着中国人自我观照的努力。体现近代社会的目光向下要求,这样的观照又具有明显的底层特征,调查对象主要是城市或农村的中下层民众。正如北京社会实进会在《新社会》创刊号发刊词中所说:“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以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其中社会学的研究态度是社会改造的重要方法,要“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3)《发刊词》,《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社会调查在马克思主义中更是备受推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社会调查都极为重视。恩格斯在谈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时说:“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3页。1889年至1893年,在萨马拉期间,列宁经常到农民中作调查。他于1893年写成的第一部著作《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就是农村调查的产物。正因如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社会调查的双重资源,他们从新文化中吸取科学精神,又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实践态度,社会调查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必修课,即如毛泽东所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身,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作为中国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可谓中国社会调查的先行者。同为北京共产党组织发起人的张国焘曾评判说,李大钊“很注重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0页。,这应为中肯之言。纵观李大钊的求学历程,可以发现,他和19世纪末兴起的社会学有不解之缘。1907年,李大钊入天津法政学堂,清末以降,一些法政学堂已将社会学列入教材(7)《法政学堂教科书一览表》(下),《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1910年12月26日)。。1913年,李大钊赴日,次年进入早稻田大学修习政治经济学。在早稻田大学的第二学年,李大钊有16门必修课、6门选修课,必修课包括财政学、货币与信用论、工业政策、农业政策、社会政策、经济史、文明史、统计学、格廷库斯社会学基础等,选修课包括都市问题、保险政策等(8)参见韩一德:《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史实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这些都和社会学有着相当的关联。当时,社会学刚刚兴起,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根据当年日本大学的惯例,把社会学放在哲学课内,规定第二学年修习(9)《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纪要》,《东方杂志》第2卷第4号(1905年5月28日)。。李大钊必修课里的社会学,就是基于这一学术背景。
社会学的修习经历,对李大钊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后来,李大钊一直对社会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写于1919年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10)《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应该说明的是,此时关于社会学的概念还不严密,当李大钊讲社会学的时候,可能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也可能是指社会科学。20世纪20年代中叶,他对维柯、孟德斯鸠、孔多塞、圣西门的讨论,既是历史哲学的讨论,也是社会学的讨论,如其所言:“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11)《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0页。
社会学的修习和改造社会的愿望相互作用,让李大钊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保持密切关注,并使他和社会调查结下了缘分。从日本回国后不久,他和一班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学生一起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学会,宣称:“本会以研究经济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12)《京师警察厅抄报李大钊等组织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致内务部备案呈》(1917年4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该会会员分甲乙两种,其中甲种为承担学会义务和经费的基本会员,1916年有甲种会员11人。李大钊作为发起者之一,是当然的甲种会员。该会确定的主要职责,就是开展研究调查。
同中国最早具有学术自觉的社会调查选择了以人力车夫为对象一样,李大钊最初的社会观察目光指向的也是人力车夫。1917年2月10日,李大钊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一文,描述了他眼中的人力车夫:“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李大钊发现:“北京浊尘漫天,马渤〔勃〕牛溲都含其中,车马杂踏之通衢,飞腾四起,车夫哮喘以行其间,最易吸入肺中。苟有精确之观查,年中车夫之殟〔殭〕而死者,必以患肺病者居多。”(13)《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页。1870年,日本人高山幸助首先造出人力车,法国人梅纳尔很快引入中国作为新兴的交通工具,由此而催生出人力车夫群体。李大钊对人力车夫的感受和北京实进会的调查是相通的,该会的调查结论是:人力车夫劳动极为费力且不经济;工作不合卫生,佝偻身躯奔跑,阻碍胸部发展,呼吸急促,吸入街上污浊的灰尘,影响肺部健康;付出的体力与得到的报酬不相称。人力车夫的问题不仅为个人或国民经济之问题,实为极重要之社会问题(14)参见陶孟和:《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0—121页。。李大钊则进一步强调,这些人力车夫背后面对的是“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15)《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页。。正因如此,人力车夫当年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注意,继李大钊之后,胡适、陈独秀、鲁迅、沈尹默、叶圣陶、刘半农、郁达夫等都写过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文章、小说或诗歌,至于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也是以人力车夫为主角。新一代知识人对人力车夫的持续关注,寄托的是对普通民众的深刻同情,李大钊可谓开风气之先者。
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呼声日渐强烈,社会调查成为知识青年的普遍自觉。1919年7月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秉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的中国”的目标,在其创办的《少年世界》中明确标示了刊物宗旨:“注重:(一)实际调查,(二)叙述事实,(三)应用科学。”(16)参见舒新城:《我和教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1919年12月4日,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了王光祈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主张过工读的生活,“每日作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作为娱乐及自修之用”,要求拟加入者“代调查手工艺种类,并说明需要资本若干”(17)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报》(北京)1919年12月4日。。调查成为这一时代年轻人进入社会的通行方式。
1920年1月,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了《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这是一群受李大钊影响的青年人到人力车夫聚居区域所作调查的记录,内称:“先索得该区警署所存的极贫居户册子,里面开列贫民姓名门牌,共计百五十余家,所以调查时比较的容易着手。我们一共十人分五组,每组担任30户。”调查呈现了惊人的贫困:“他们的衣服除小孩了〔子〕大多穿着破棉外,大人有穿夹袄的下面大都穿着单裤――以妇女为最多。……土炕上有许多是没有被窝的,有的是摊着烂穿了的,或东一块西一块的什么东西。一家五六口的,也只有一个土坑,甚至有两三家拼住一间小屋的。屋里的黑暗污秽不通气,无异旧式的牢监。”这篇社会调查最后写道:“这些贫民,并不是懒惰不愿做工,实由社会组织不良,叫他们无路可走。”(18)光舞:《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晨报》(北京)1920年1月26日。
无论是李大钊,还是其他调查者,都特别关注艰难生活的人群,以此自杀者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李大钊的视野。通过自己的观察及利用相关调查材料,李大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文章。1913年的《原杀(暗杀与自杀)》首度涉及自杀问题;1915—1919年的《厌世心与自觉心》《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一个自杀的青年》等文,继续对自杀问题有所申论。1919年底、1922年分别写成的《青年厌世自杀问题》和《论自杀》,则运用调查材料,更为深入地探讨了青年自杀问题。
今人说到自杀问题的研究,很容易想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出版于19世纪末期的社会学名著《自杀论》,李大钊的《青年厌世自杀问题》和《论自杀》采用了大量《自杀论》的数据,不过他所参考的并非前者,而是意大利精神分析专家恩里科·莫尔塞利的《自杀论》。
19世纪意大利的精神病学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莫尔塞利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有学者指出:“热那亚的莫尔塞利(E.Morselli,1852—1929)是《科学心理学评论》杂志的创办人,他写过一本精神病手册(1885—1894)和一部详细的人类学通论(1899)。他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在这里,他对人的临床心理特性及疯人的个性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19)[意]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中),程之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59页。莫尔塞利的《自杀论》出版于1879年,是涂尔干写作《自杀论》的重要参考书,其中的调查材料也是李大钊讨论自杀问题的重要数据来源。
目前尚不清楚李大钊究竟是如何读到莫尔塞利的《自杀论》的,推测应该是从日文翻译中获得,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他引证的莫尔塞利书中的数据并不是转自涂尔干的《自杀论》。李大钊文中利用莫尔塞利的数据证明知识精英自杀率最高,曾提及“自杀最多者为从事科学文学的人,百万人中有六百十四人,其次就是从事国防的四百零四人,从事教育的三百五十五人,从事行政的三百二十四人,商人二百七十七人,司法官二百十八人,医师二百零一人,从事工业的八十人,从事原料制造的二十五人”(20)《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而在涂尔干的书中,这些数据被作了大幅度简化:“在意大利,莫塞利可以把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职业分出来,并发现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中自杀的人数大大超过所有其他职业。他估计,在1868—1876年,每百万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中有482.6名自杀者;其次是军队,有404.1人。”(2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1页。从李大钊引用的数据远比涂尔干完整可以证实,涂尔干不大可能是李大钊和莫尔塞利之间的桥梁。
相比后来中国知识界关于自杀问题的连篇累牍的讨论,李大钊的上述文章很难说有什么特别的观点,给人印象深刻的毋宁说是李大钊在讨论中对数据的重视——文中除了有从莫尔塞利等西方作者借用的数据外,还有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统计数据,比如日本警视厅及中国内务部和京师警察厅的统计材料,以调查材料展开论证而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显示了李大钊的社会学素养,引领了当年中国关于自杀问题讨论的风向。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体现了李大钊作为学者的一面,这使之成为以深厚理论功底结合现实关怀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
二、工人调查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这里距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唐山开滦煤矿只有百里之遥。当年,唐山拥有中国其他地区不多见的大比例产业工人,如后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汇报时所说:“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工业中心。这里有:(1)二千五百工人的京奉铁路修理厂;(2)两千工人的启新洋灰公司;(3)一万四千工人的开滦矿务总局。我党在这个地区正竭力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以及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小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员工小组。在它们周围,我们团结了一批相应的工会。”(22)张太雷:《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就开始关注家乡唐山工人阶级的状况。1919年3月9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这可以说是中国相当早的关于工人生活的调查文章。该文采用间接调查方式,通过询问唐山煤厂来的朋友,了解那里工人的生活状况。虽然以现代眼光来看,该调查不能算十分的专业,但是调查的一些要素已基本具备。李大钊最关心的是工人的生活,文中写道:“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饮膳还要自备。他们……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他注意到了唐山煤厂的包工制度,写道:“资本家对于工人不生直接的关系,那包工的人对于工人,就算立在资本家的地位。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怀着改造社会的心理,李大钊特别关注工人的组织状况,发现拥有八九千人工人的唐山煤厂,“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23)《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436页。。作为弱势一方的工人,他们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利用数量上的优势,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李大钊此时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经凭着自己对社会的了解,初步窥到了这一症结。
五四运动后,1919年7月下旬至9月初,李大钊又亲身到唐山开展社会调查。其间,他访问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调查开滦林西矿,以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同时,李大钊还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到工人中去。1920年初,为更加深入地了解工人情况,李大钊安排北京大学的罗章龙、新潮社成员罗家伦等到唐山,在唐山京奉铁路制造厂、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展开劳动状况调查,所写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即署名“无我”的《唐山劳动状况》(一)和署名许元启的《唐山劳动状况》(二)(24)许元启当时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参与了罗章龙等组织的相关调查。。
两篇调查报告详细记述了唐山三大企业的情况。从调查看,三厂工人处境不完全一致。唐山京奉铁路制造厂技术含量高一些,工人知识水准较高:“工人大都居唐山乡间,知识程度比他种工人为高。厂中每年每人有一次来往京奉路三等旅行券,每年有外加一月(依星期计算,一月扣除三日)无工资名为奖励金。厂中有工课夜课社使工人补习。”(25)许元启:《唐山劳动状况》(二),《唐山工运史资料汇辑》第1辑,唐山: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1985年版,第16、22页。正因如此,这里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错:“常见有每月赚四五十元钱的工人,他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冬天就穿上皮袄,其余就可想而知。小工们赚钱不多,自然是不能阔绰,然尚不至十分狼狈。”(26)无我:《唐山劳动状况》(一),《唐山工运史资料汇辑》第1辑,唐山: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1985年版,第11—12页。启新洋灰公司实行按日计薪制,工人做工时间通常为十小时,“厂里全是包活,工人做的快,工价自然赚得多,跟制造厂的办法相同。其生活状况,也跟制造厂的工人相仿。惟装洋灰的小工,因洋灰末一经启动,弥散到空气里,吸入鼻管喉咙里,就干的难过;吸进肺里去,若日久天长,大有生命危险”(27)无我:《唐山劳动状况》(一),《唐山工运史资料汇辑》第1辑,唐山: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1985年版,第11—12页。。劳动量最重、生活最艰难的是开滦煤矿的工人。调查报告详细记载了开滦煤矿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工人“每日分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时”,很多矿工一天上两班,做十六个小时的工作,而“每日所做的工一吊六只够他一人生活,要赡若家室非做双工不可。工人的工钱连‘五铜子’想储蓄都不能”。他们的住屋叫“鸟窝”,“‘鸟窝’里……一盏灯油,睡的地方也没设备,只有一只空炕,无数的工人枕着砖瓦而睡”(28)许元启:《唐山劳动状况》(二),《唐山工运史资料汇辑》第1辑,唐山: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1985年版,第16、22页。。
当年的技术条件及工人本身的无力,导致工人的生产环境异常恶劣。调查报告写道:“我们亲自去调查的是第七层和第八层。大路阔十一尺高十尺,途中昏黑没灯火及种种设备,非常泥泞,路旁有水沟,水深过膝。路中设轨,用骡车运煤,阔只七尺,高只四尺半。走时须俯伏行走。……空气里夹着煤气、水汽、硫磺气和种种重浊的臭气。气温高至摄氏三十八度。”生产安全几乎无从谈起,工人死伤率很高:“每月因伤死于矿内者平均四人,多的时候十几人,几十人不等(病死者不计)。大半因不通风的闷死和中毒死,伤的人数比死的多两倍。”(29)许元启:《唐山劳动状况》(二),《唐山工运史资料汇辑》第1辑,唐山: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1985年版,第22—23、25页。
和李大钊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样,调查报告也引人注目地提到了工人组织。辛亥革命后,唐山工人一度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可惜在1914年“二次革命”后消亡。五四之后,又有同人联合会成立。调查报告认为:“在救国的题目下,这种组织不是纯粹工人的组织,所以不能发扬工人的精神,更不能专做谋工人幸福事业。现在也有不少人觉悟到此,想另组劳工团体,他们成功的快慢,就要看工人要求的决心。”(30)许元启:《唐山劳动状况》(二),《唐山工运史资料汇辑》第1辑,唐山: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1985年版,第22—23、25页。工人组织问题的反复提出,如果和此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准备及走向工人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可以见出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们逐步具有了开展工人运动的理论自觉。
由于李大钊等的提倡,20世纪20年代初,关于工人、工厂的调查蔚成风气。1921年4月,李大钊出席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调查北京之平民学校及平民讲演所,并设法使变为社会主义化”(31)《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五一”活动等事项报告》(1921年4月8日),《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08页。。《新青年》杂志设计了一个社会调查表,提出展开工农调查的详细项目。该刊第7卷第6号系“劳动节纪念号”,登载了12篇中国各地劳动状况的调查,涉及南京、唐山、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天津等11个地区。《劳动界》等杂志也发表了大量关于工人的调查文字(32)参见熊秋良:《“寻找无产者”:五四知识分子的一项社会调查》,《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邓中夏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发刊词中发出号召:“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场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现在办理情形,所出产的物品概况,工人的数目种类——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形,工钱的制度,做工的时间,工场的规则等,和工人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见,对于家庭的关系等一切情形,随时详详细细的告诉给我们。”(33)《邓中夏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9页。
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将视线下移到底层,目的在于改变现状。1924年,李大钊访苏期间,“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遂写下《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表达了对上海童工的关切。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材料说:“上海市分为十区,共得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这些“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他们大都是站立着作工。分日夜两班换班,直到一星期终了的时候,才停一班”。丝厂的童工多是女性:“小女孩子们在那里作些刷茧、去障碍、剖出丝纤的工作,为机工作预备工夫。此苦工作,须临于盛着沸水的盘盆前边,他们的小手,须和沸水相接,以致手受痛伤,显出粗丑的样子”。李大钊痛切地希望:“留心社会的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以改进之。”(34)《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4页。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先驱,但他关于工人的社会调查常常更多诉诸情感。无论社会调查还是政治革命,都不离开情感的关怀,这是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明显的特点。
三、农村与农民调查
李大钊出身农村,对中国农村问题有着深切的认知。虽然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理念,工人问题更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其对农民问题却也从未忽视。1918年3月,李大钊去清华学校参观后,盛赞该校学生:“于课余之暇,尚在校外附近乡村中为各种改良社会之活动,已在附近二三里许之某村设一职工学校,上午授课,下午工作,以收附近村中之贫儿,闻成绩颇著。”(35)《李大钊先生来函》(续),《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0日。次年2、3月间,他撰文呼吁青年人面向农村,了解农村:“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36)《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439—440页。他要求青年人“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37)《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439—440页。。
随着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深入,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革命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共产国际和苏俄也给予了有益的指导。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还在酝酿阶段,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致电维经斯基(吴廷康)时要求:“必须立即通过电报传送关于农业问题的材料:第一,哪种土地所有制最有代表性——是大土地占有制还是小土地占有制?第二,怎样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把农民分类,例如什么叫大土地所有者或中农?第三,农村有没有无产阶级,有多少人?第四,因农村人口的减少,城市居民增长的幅度有多大?第五,有多少人兼营副业?第六,人均占地是多少?第七,有多少人租种土地?请提供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38)《阿勃拉姆松和勃隆施泰恩致吴廷康的电报》(1920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可见,面对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一开始就已在国内外的革命者眼中聚焦。正如邓中夏1923年所言:“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的参加,那有希望?”(39)《邓中夏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农村调查备受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曾受中共北京党组织指导的贺昌撰文提供了农村调查的调查大纲,包括地理上的大概情势、农民的种类及其生活状况、生产的种类、农村的副产、生产的方法、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教育、农村的风俗习惯、普通农民生活最低限度的标准、农民一般的负担、灾荒情形、农民破产情形、农民的心理和要求、农民运动的状况等(40)《贺昌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8页。。贺昌的调查大纲比之上述俄共提出的调查计划,明显更为完整细致,这表明,中共党内的调查研究方法日趋成熟。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开办了中共第一个区委党校。李大钊给学员讲授了土地与农民问题的课程,训练农民运动骨干。时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的乐天宇回忆道:“在共青团支部时,刘伯庄同志(地委书记)曾向他们传达过李大钊同志的指示:要求他们支部的团员每天都要找一位农民谈话,并作谈话记录。支委则每天至少找一位农民谈话,并且把谈话记录向支部汇报。”(41)《乐天宇同志的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页。李大钊深知,“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42)《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就是说,要深入推进中国革命,就不能不去了解农民。
1925年冬,李大钊到河南郑州一带走访农村,撰成《土地与农民》一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论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该文指出,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分为两类:一类欲行公有,一类欲借土地增加税源,后一类是历史上的主流。由于政权以土地为逐利工具,造成豪强兼并、土地不均,不断发生的平均地权运动即成为农民与土地关系一个不绝的旋律。土地是农民的命脉,中国革命不能不面对农民和土地问题。李大钊强调:“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如何完成这个任务?首要的是真正了解乡村的现实状况。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经济,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李大钊使用数个调查材料以证明这一趋势,包括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全国农家户数表,民国九年、十年河南、山西、江苏等六省区合计农田亩数统计比较表,京兆、直隶、吉林等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累年比较表,等等。
在李大钊看来,要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和佃农的破产问题,必须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他使用芜湖102个农家社会经济调查及郑州附近的河南荥阳五村、密县二村、汲县一村农民生活要项调查,通过数据的分析、比对,证明道:“农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较大的农场,为最迫切,因为农具设备效率增大的结果,可以增大场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级农民的痛苦”。因此,国民革命应该切实推行土地改革:“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冋题,当能谋一解决”。解决农民问题,除了革命政权的努力而外,还要有效组织农民。李大钊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看得出来,李大钊对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能否切实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并不乐观,前文中的“苟能”一词,很能代表李大钊内心的真实判断。因此,由中国共产党来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形成自己的土地改革推动力量,就成为李大钊思考的方向:“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更能体现李大钊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思路的,是他提到的农民武装组织问题:“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43)《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07页。。李大钊对红枪会这样的农民武装组织抱有高度期待,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李大钊是最早注目于此的革命领袖之一。
红枪会作为农民自保组织,成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民国初年,政治控制力式微,战争频仍、盗匪蜂起,地方由实力人士领头,组成村或村落间的防卫组织。红枪会目标在于自保,并无抗御官府的主观意图,但由于代表本村利益,一旦壮大,必将抵制官府苛剥,甚至拒绝官府的正常税赋要求。李大钊对红枪会的组织力量印象深刻。1925年,当皖西大刀会占领县城、组织农民政府的消息传出后,中共北方区委立即派乐天宇以应聘安徽第三农校教员名义,到苏家埠、麻埠、金家寨等地访问,写成调查报告转报李大钊(44)《皖西革命史(1919—194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李大钊多次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红枪会的报告。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次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召开,在李大钊等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强调:“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括,苛捐苛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应注意使农会成为整个的农民组织,红枪会成为农民武装组织。”(4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8月,李大钊又依据对北方红枪会的调查和分析,写成《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继续阐发改造红枪会为农民武装的设想,即“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以“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46)《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通过武装的农民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是李大钊经由调查得出的结论,尽管文中或有高估红枪会组织之嫌,也未能指出“没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指导帮助”,像红枪会这样的农民武装很可能“化为土匪、教匪,或者受军阀土豪所收买利用,反而变成压迫农民的武装势力”(4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但他建立农民武装的呼吁,对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还是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实际上,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已在努力探索组织和领导农民武装的途径。1927年3月,经由中共北方区委联络,河南召开各地红枪会代表集会。“各代表在会议席上之主张甚为热烈,表示愿受派遣在各地方组织劳工中央部(机关)联合,并坚固各地方红枪会之组织,然后创建联合机关”。虽然该次会议“实际上所代表之地方甚少,不能有良好之活动”(48)《关于河南组织红枪会联合行动及党员服务情形工作地点等项之报告》(192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但会上呈现的组织化趋势,尤其是中共党组织参与其中,已经显示了党独立领导农民武装的努力和可能。
李大钊一生注意扎根现实社会,特别强调个人人格的树立及社会改造的必要。他在谈论教育时曾批评道:“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视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49)《记者与李大钊氏之谈话》,《教育与人生》第1期(1923年10月15日)。李大钊不希望知识人只是在书斋中求取知识,而主张走进社会、调查社会、了解社会,找到改造社会的路子,从而既健全个人的人格,又使社会得以进步。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对工人、农民问题的充分了解和重视,都和注重调查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可以说既出自他的社会学训练,也来自改造社会的愿景,还和健全人格的要求及脚踏实地的思想风格无法分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自己的认识和良知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是极具个性和情怀的一代。具体就李大钊而言,他既是一个学者,又走入社会成为倡导政治和社会改造的革命者,社会调查隐隐然成为居于其间的两种气质的结合点。事实上,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也被打造成知识者了解革命、投身革命、融入革命的一条有效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