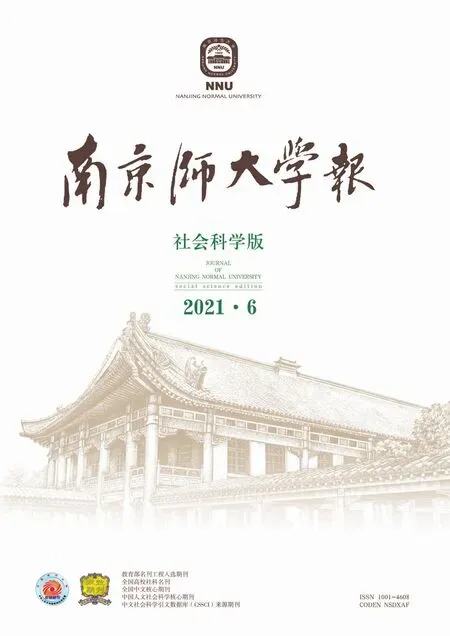“怀疑”与“相信”之间:蒙田人文主义思想特质
吴爱武
蒙田一向以“人文主义思想家”著称,所获称谓颇多——“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低调济世的人文主义巨人”“最后一个人文主义者”“深沉的人文主义者”等等。(1)[法]蒙田:《蒙田试笔》,梁宗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柳鸣九:《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钟谟智:《人文主义的由来和定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卢敦基:《深沉的人文主义者》,《读书》1988年第8期。吊诡的是,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蒙田人文主义思想的本质内涵,以实现它对当下人类处境的启迪价值的话,竟然无处寻觅。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具体化在蒙田的写作特点、文学性、历史观、教育思想、伦理思想等人文主义思想的应用领域,而其思想内核——人文主义,却沦为某种形式的符号,始终模糊不清,抽象空洞。这解释了以下的现象:“作为作家的蒙田,一向享有崇高的地位;作为道德家、哲学家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观察家的蒙田,声誉却长期游移不定”。(2)韩伟华:《隐微写作与经典新解——评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如果能够从一个新视角,对蒙田人文主义思想做一点基础性的澄清与反思工作,对其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爬疏、反思与批判,对于弥补当前对蒙田的片面化解读缺陷,还原一个真实而立体的蒙田,重新发现他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教训,是本文旨趣所在。
一、 蒙田张力重重的“怀疑”与“相信”
解读蒙田人文主义思想,存在三重难题。其一,来自于文本。以三卷本的思想代表作《随笔集》而言,它用古法文写成,又引用了希腊、意大利等国的语言,以及大量拉丁语,涉及的题材极其庞杂多样,内容包罗万象,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人生哲理等等无所不谈,特别是旁征博引了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论述。文本使“阅读蒙田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不少读者和蒙田的蜜月期注定不会长久。在迷恋上他娓娓道来的言说不久,他们会陷入困惑。读他的作品,人们仿佛步入了一座繁花似锦的花园,香味馥郁,但也渐渐迷失在语词的迷宫中,为找不到出口而苦恼”。(3)王宏图:《智慧、虔敬与诗情——法国文学断想》,《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其二,在于蒙田的写作方式。众所周知,蒙田开创了“随笔”这一写作体裁的先河。随意、自由的写作风格之外,隐喻手法也是这一写作方式的主要特点。隐喻式的写作方式之下,蒙田有意无意地将自己“逊位”与“隐身”,从而带来了解读上的困难。蒙田的传记作者之一——英国新文化史学者彼得·博克,甚至认为蒙田是“故意以毫无系统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谁想要系统地阐述他的思想,谁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了”。(4)[英]博克:《蒙田》,孙乃修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6页。其三,思想自身的复杂性。“人文主义”之外,“怀疑主义”同样是蒙田挥之不去的标签,二者同为蒙田的思想底色,纠缠不清地展现在他的著作中。鉴于此,本文采取收缩聚焦的方式,集中于《随笔集》中蒙田“表达怀疑思想的高峰”(5)甘均先、毛艳:《怀疑之箭——论蒙田的怀疑思想》,《法国研究》2003年第1期。之作——《雷蒙·塞邦赞》,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来展开对蒙田人文主义思想的初步探问。
《雷蒙·赛邦赞》被广泛认同为《随笔集》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思想价值的作品,是一篇长达十多万字的文章,充分透露出蒙田货真价实的“怀疑”。他对“人”提出质疑:“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虚弱,也是最自负的是人”;(6)[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怀疑人的理性与知识:“他心中不能说没有一些真正的知识,但是这是偶然得到的。谬误也可以通过同样途径,用同样方法输入到他的灵魂中,他的灵魂没有能力甄别和区分真理与谎言”;(7)[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第221页。怀疑人对存在和永恒的相信:“说到头来,人的实质和事物的实质都没有恒定的存在。我们,我们的判断,一切会消失的东西,都在不停地转动流逝。因而谁对谁都不能建立一个固定的关系,主体和客体在不断地变换更替”(8)[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第262页。。“我知道什么?”“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我不置可否”,彻底的怀疑性语句铭刻在蒙田的骑士勋章和书房的梁柱上。蒙田的怀疑主义思想,广为人知,亦成共识:“蒙田秉持的是一种腐蚀力极强的怀疑主义,他的信条是:‘我知道什么?’,人们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地探寻的人和事物的真理、实质在他眼里都不过是过眼泡影,虚浮不定”。(9)王宏图:《智慧、虔敬与诗情——法国文学断想》。
然而,仔细研读文本,困惑之处跃然而出:高呼“怀疑”的蒙田,却也从未停止自己的“相信”宣言。以被认为是蒙田怀疑主义思想最彻底、突出、深具个人特征的部分——对宗教的怀疑与批判为例。一方面,宗教问题的批判,随手可得:“人占了主导地位,在利用宗教”,(10)[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第101页。“我们创立宗教是为了剔除罪恶,而现在却在掩盖罪恶,培养罪恶和鼓动罪恶”。(11)[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第102页。另一方面,相信之词贯穿全文:“知识和智慧只能属于上帝,只有他能对自己作出评价,只有他能赋予我们值得骄傲的有价值的品质”,(12)[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第106页。“人也不可能超越自己,超越人性;因为他只能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手抓取。只有上帝向他伸出特殊之手,他才会更上一层;只有他放弃自己的手段,借助纯属是神的手段提高和前进,他才会更上一层。欲图完成这种神圣奇妙的变化,依靠的不是斯多葛的美德,而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13)[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第264页。
通过文本的细致解读,还可以发现蒙田的另一重“相信”——相信“人”以及作为“人”的“我”。他说:“最美最合理的事莫过于正正当当做人,最深刻的学问是知道自然地过好这一生;最险恶的疾病是漠视自身的存在”;“我乐意采纳的哲学思想是最坚实的,也就是说最人性化的、最符合我们的。我的言论符合我的为人,平庸谦让”;“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14)[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15、317、320页。;“我的信念是一切都取决于自己”(15)[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第24-25页。。类似表达俯首皆是。与蒙田明确宣称的“相信”相比,这另一重“相信”未予明言,却是他思想与行为的信心依据,也是蒙田被视为人文主义者的缘由。
纵观蒙田言之凿凿的“怀疑”声明、“信誓旦旦”的信仰宣言、人文主义的生活信念,其中或隐或现地交织着的“怀疑”与“相信”的重重张力,颇让人疑问重重。博克曾说:“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又怀疑人类理性探知上帝的能力”,并称他的信仰为“不动感情的带着怀疑的顺从”。(16)[英]博克:《蒙田》,孙乃修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51页。《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史》一书谈及蒙田的信仰时,说道:“蒙田的论证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还是伪装的嘲讽和攻击…研究他著作的人,从当时直到现在对此一直争论不休”。(17)[美]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史——哲学家、思想与思潮的历史》(卷1),查常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对于这种重重张力之下的思想矛盾性,蒙田自己也心知肚明。他说:“我看问题不会超过我平时的学习习惯,没有规则可遵,提出看法也笼笼统统,摸索前进。比如这一条:我发表鸿论,前后章节不连贯,仿佛不能一口气把事整段说出来似的。在我们这些平凡庸俗的心灵中不存在连贯与一致”(18)[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第300页。;“我也是比谁都看得清楚,我的这些文章只是在儿时对学问学了些皮毛的人在说梦呓而已,只记得一个模糊不全的印象,东扯西拉,一知半解,倒是十分法国式的”。(19)[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雷蒙·赛邦赞》,2009年,第131页。
二、 “存在”抑或“此在”:“怀疑”与“相信”之间的深层纠葛
“蒙田的自谦背后是自负,他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学才能都极其珍视,他是以否定的方式强烈肯定自己的存在”,(20)李永毅:《结构的悖论:德里达与蒙田》,《国外文学》2015年第2期。这个洞见非常敏锐而深入。事实上,对蒙田而言,“存在”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始终是困扰他的最核心问题,也是他一生所思、所想、所念、所欲解决的终极性问题,并且他意识到这个形而上的超越性问题必须且只能通过超验的信仰来解决,这宣称的“相信”显然与他声称的“怀疑”构成了剧烈的对立冲突。同时,由于现实的“生存”处境难题,“存在”问题被无意识地转换成为“存在者”的“此在”问题,因而被消解在他用以解决“此在”问题的怀疑主义的人文主义生存策略与方式之中,由此也形成了他内在的多重张力,终其一生无法摆脱“此在”与“存在”引发的自我冲突的枷锁与困境,在“怀疑”与“相信”、“肯定”与“否定”之间徘徊挣扎。
(一) 声明的“怀疑”与宣称的“相信”之间:蒙田的“存在”之重
蒙田说:“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早在19世纪初,已经有人说蒙田是当代哲学家”。(21)[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译序,第15页。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原因不仅在于蒙田基本上从未专门论述过学术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而且,虽然他的文章中处处在思考与谈论哲学问题,但他言说的方式不是逻辑论证的“哲学”专业模式,而是自己开创随性淡然的“随笔”风格。对此,蒙田明确指出过:“我对自己做出判断,凭的都是真实的感觉,不是论证”。(22)[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第300页。这种不同于常规的思维方式正是蒙田人文主义思想值得深入探索的思维特征,但却一直被忽视了。现在先让我们回到蒙田被视为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上来。
“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这篇文章的标题凸显了蒙田的哲学思考。在该文的开头,蒙田说:“西塞罗说,探讨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准备死亡”。(23)[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第70页。其实,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在《斐多》中记载着苏格拉底的观点:“许多人不懂哲学。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24)[希腊]柏拉图:《斐多》,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这个观点影响了之后的哲学家,众多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将死亡问题当作了自己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甚至于伽达默尔提出了“死亡是人的本体论光荣”(25)[德]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选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的观点。由是观之,在此阐明蒙田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与写作,重点不在于证明蒙田是否是一位哲学家,而是这件事本身反映了蒙田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反映了尽管他从未系统性地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也一再声明自己“不是哲学家”,但他所有的思考都涉及生还是死、存在还是虚无、短暂还是永恒的本体论问题。简言之,对“在者之在”“是其所是”“何以可能”等“存在”问题的追问和追寻,是蒙田最根本、最核心、最真实的问题,也是他对一切问题思考的出发点。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各种事物总有一个决定它们为何所是的最终根据。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来说,这个根据就是存在,存在决定存在者”。(26)张汝伦:《论“内在超越”》,《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根据这个对“存在”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可以发现,对一直苦苦追问的“存在”问题,蒙田给予了两种答案——“怀疑”的声明与“信仰”的宣称,而二者呈现为难以调和的对立冲突。从彻底的怀疑主义出发,蒙田以“不确定性”来解释“存在”问题,即对“是之所是”的最终根据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怀疑一切,认为一切都“不确定”。对此,有学者总结为:“蒙田怀疑论的基本依据是:人本身的不确定性”,(27)鲁成波:《蒙田怀疑论的个性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因而,“蒙田总是处在不确定之中”。(28)邓刚:《蒙田与法国近代哲学开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9日,第A6版。然而,从蒙田宣称的“相信”来看,“古希腊的存在概念不仅在事物的最终根据意义上是超越,而且它在永恒存在和始终不变的意义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因为无论是自然事物还是人类,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和始终如一。这些也正是基督教超越的上帝的基本规定。上帝是事物的最终根据,只有上帝才是永恒存在与始终如一”。(29)张汝伦:《论“内在超越”》。显而易见,蒙田确实是自相矛盾的。他将“不确定”与“上帝”同时作为事物的最终根据,以此来解释“为何所是”的“存在问题”,这种本体论问题的认识论解决方案的矛盾与张力赫然可见,从中也可看出蒙田苦苦追寻却始终无法走出“存在”之重的部分原因。
另外,据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蒙田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外祖父母“被西班牙排犹运动驱赶避难来到法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成为‘马兰内’的一员”。(30)李英华:《潜藏的“犹太性”——蒙田的宗教本相》,《基督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马兰内,亦称马兰诺(marranos),特指为逃避迫害被迫改信基督教,但私下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谨言慎行的“马兰内”祖先对蒙田有着深厚的影响,也造就了“蒙田一生谨慎,他表面上采取迎合基督教的态度,避免自己作为异端而被审查甚至判刑”,形成了他“潜藏的、含混的宗教本相”。(31)李英华:《潜藏的“犹太性”——蒙田的宗教本相》。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蒙田“所主张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带有实用主义目的的道德信仰,是他超越人性的一种工具,属于他‘生活哲学’的一部分”,因而,“从存在方式看,蒙田始终在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中挣扎与徘徊”。(32)肖四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连续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换句话说,蒙田自己宣称的“相信”只是在一个工具性的位置,是为他的现实生存与生活、理想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自我实现服务的,由此导致大家对他所宣称的“相信”充满怀疑与质疑,认为他并非如其所言地信仰。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而这也是蒙田始终无法挣脱“怀疑”与“相信”的漩涡,从而无法走出“存在”之重的另一重原因。
(二) “怀疑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蒙田的“此在”哲学
自从巴门尼德将“存在”作为核心范畴引入哲学后,便开启了形而上学这门关于“存在”的科学的先河,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与思想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也是一部对“存在”自身的研究史。在巴门尼德那里,对“存在”作出著名的论断:“存在存在,而非存在乃是不存在的”,(3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3页。意思是说,“存在”如其所是地存在着,是一种绝对肯定性的力量,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可怀疑和不可拒绝的,这种绝对的断定、绝对的肯定把“存在”不可动摇地确立在自身之中,使其作为真理而显现,与事物的生灭变化无关。基于此,巴门尼德将思考“存在”的道路称为真理之路,思考“非存在”的道路称为意见之路。赫拉克利特则以怀疑论为前提,从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出发,进入到对不变的“逻各斯”的寻找、思考与研究,走上殊途同归的形而上学之路。总而言之,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体现了哲学独特的问题意识、思维与言说方式。以此来看蒙田,可以再一次验证蒙田的哲学意识和他真实的问题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怀疑主义”与“信仰”之下的内心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入点”差异,可以进一步反观到蒙田在“怀疑”与“相信”重重张力之下的更深层纠葛。
与巴门尼德从“存在”进入“存在”、直接言说“存在”不同,赫拉克利特则从“现象”进入“存在”,由可见入可思,因而对巴门尼德的绝对肯定提出了质疑,说出著名的断言:“我们踏入又不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34)苗力田:《古希腊哲学》,第43页。这就给“存在”问题的“否定”留下了余地。从此,“存在”的确定性在肯定、否定、辩证与存疑置悬之间摇摆动荡,并就此延展出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也构成了不同的存在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借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进行进一步分析。
从现象学存在论出发,海德格尔将存在与存在者进行了区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3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页。这是说,存在与存在者不同,存在者是具体事物,存在不是这些具体的事物,而是存在者的根据,是这些具体事物得到肯定的前提,存在超越了存在者,在一切存在者之上。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开始到近代的形而上学,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遭到忽视,“存在”本身遭到了遗忘,在此基础上,他将思考“存在”的着眼点放在“存在者”上,提出:“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是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不妨说,就是要从存在者身上来逼问出他的存在来”。(3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8页。如此一来,海德格尔将“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转为“此在”(“作为存在者的存在”),以作为生存的此在来解决存在问题,以生存现象学构建了一种新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形而上学)。
当我们以此分析视角来看蒙田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出,蒙田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演示了一种生存现象学视域下的“存在”解释。具体而言,蒙田真实的问题意识——“存在”,被无意识地置换为“此在”,以可见的存在者“生存”的现实问题取代可思世界的“存在”问题。进一步说,蒙田无意识地从求而不得的“存在”转向各种现实的人生问题,以“怀疑主义”与“人文主义”为内涵,对存在者的“此在”给出了自己的思想方案与行为回应,完成了一种“此在”的生存哲学,与此同时,“存在”随之被消解与解构。然而,作为终极性、根本性的“存在”问题,是无法被遗忘的,这就造成了蒙田内心永远的冲突与矛盾。
面对类似“处在我们已经忍受了三十年的乱世,任何法国人,个别的或是集体的,随时随地都处在倾家荡产的边缘”(37)[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的恶劣“生存”环境,人文主义思想为蒙田发挥了根本性的生存意义。它将人本身作为人的终极根据,带来存在者的肯定感,激励着蒙田“要做自己,成为精神的主体,并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去面对纷繁、复杂的转型时代的种种矛盾、冲突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焦虑、混乱与茫然”。(38)李征:《坚守的力量——蒙田对现代性问题原初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1期。看起来“蒙田很懂得如何避开痛苦,享受快乐。他把真正地思考自己转化成思考各种人生问题,从而借此逃脱不幸”。(39)毛红玉:《安宁的生活可能吗?——帕斯卡尔与蒙田的对话》,《求知导刊》2016年第1期。但是,持有“不确定”信念的怀疑主义思想却导引出蒙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处事原则:凡事存疑,不做判断:“凡事疑而不决,不是胜过陷入幻想所产生的种种谬误吗?暂且不作决断,不是强于参加乱哄哄的纷争吗?”。(40)[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第161-162页。怀疑主义的人文主义引发的内心矛盾与冲突随处可见。比如,蒙田一边说:“当前法国分崩离析,我们陷入四分五裂的时代,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努力保卫自己的事业,但是即使是最优秀的人士也要借助伪装与撒谎”,(41)[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第201页。一边又说:“真实也有妨碍、不便之处,还会给我们带来变故。因此,为了不自欺,我们不得不撒谎骗人”,(42)李英华:《潜藏的“犹太性”——蒙田的宗教本相》。殊不知,剧烈的内在冲突凸现的恰是“撒谎骗人”之后真实的“自欺”,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挣扎与痛苦。
长期以来,蒙田被认为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完成,大家普遍认为,自他之后,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注重人的潜能与创作力,强调个人尊严、价值和通过理性而实现自我,等等,成为人与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他对他之后的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不少名人巨匠,如笛卡尔、培根、莎士比亚、伏尔泰、孟德斯鸠、茨威格等等都带去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事实没有这么简单。相反的是,蒙田始终处在“存在”还是“生存”的拷问之中,内心充满着“怀疑”与“相信”的多重张力,一直缺乏真实的信心,终其一生没有如他自己希冀的那样活出本真的自己,享受坦然与安宁。正因如此,蒙田的自我评价充满矛盾,而《随笔集》自出版以来,也是遭遇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如在《随笔集》的《致读者》中,蒙田说:“我没有什么目标,纯粹是居家的私语”“只是寄语亲朋好友作为处世之道而已”,但他又说:“我愿意大家看到的是处于日常自然状态的蒙田,朴实无华,不耍心计;因为我要讲述的是我”。“因此,读者啊,我自己是这部书的素材,没有理由要你在余暇时去读这么一部不值一读的拙作”。(43)[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第38页。又如,“在19世纪下半叶和我们的世纪,蒙田这个道德学家和人受到一部分人议论和另一部分人颂扬”,“如果说让-雅克·卢梭精神病态古板,不喜欢摇曳多姿的文章,对蒙田持保留态度,那些百科全书派、时尚文人、诗人则把蒙田引为知己”。(44)[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第34-35页。自相矛盾的自我认知与云泥之别的两极化评论,可谓信手拈来,在此不予赘述。
三、 从“思-在-疑”到“信-在-思”:蒙田人文主义思想的危机与超越
综前所述,具体的现实生存需要迫使蒙田把可见世界定格为第一位的,如何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完成“此在”变成了最真实的人生问题,并由此发展出了怀疑主义的人文主义,但由于“存在”的“遗忘”,最终导致他始终无法挣脱本体论困境。这不能不让人思索:原因何在?出路在哪里?
实际上,“存在”的“遗忘”,绝不仅是蒙田的怀疑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困境,它是形而上学危机的体现,因此就连海德格尔本人也未幸免。有学者指出:“海德格尔虽然区分存在与存在者,但他还是误解了存在本身,存在本身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它是对存在者存在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存在者无关,不是从存在者自身当中能寻找到的,它是以一种特殊的哲学转向为前提的,哲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是促进这种转向,而不是去威逼存在者”。(45)王俊:《于“无”深处的历史深渊——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范例的虚无主义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结合这句话,通过对蒙田内在冲突的分析与揭示,我们可以看到,“威逼”“存在者”的生存现象学路径是无法解决本体论困境的,也就是说,提出“存在的被遗忘”的海德格尔,同样“遗忘”了“存在”。它的意思是,“存在的被遗忘”“意味着人的存在的被遗忘,以致人作为一种存在者成为了形而上学或者经验科学的规定对象”,而“这种对于人的存在的遮蔽是无法通过任何其他形而上学而被消除的”。(46)陈勇:《人文主义危机与存在问题》,《哲学分析》2018年第2期。换言之,就是当“存在”成为“思”的对象时,必然产生对“存在”的“怀疑”与“否定”,最终导致“存在的被遗忘”,对此我们只能诉诸于特殊的哲学转向,即从“思-在-疑”向“信-在-思”转换,走出本体论危机。
我们从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着手进行分析。在广为接受并作为人文主义研究基础的阿伦·布洛克所著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他归纳了三种思维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之为‘超自然’或‘超验’的神学模式,其关注焦点在于上帝,人则被视为上帝所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可以被称为‘自然’或‘科学’模式,它所关注的焦点是自然,而将人与其他生物一同视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是人文主义模式,它以人为中心,并且以人的经验来作为人对自己、上帝和自然进行了解的出发点”。(47)[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年,第14页。“以人为中心”“以人自身的经验为中心”,是人文主义思维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它在对抗因第二种模式的过度膨胀而表现为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程度上的救正性功能。这正是蒙田人文主义与其他形态的人文主义的共性特点。前文曾提及过,蒙田做出判断不是依据逻辑论证,而是“跟着感觉走”。他秉持对理性强烈的批判精神,嘲讽人类理性的傲慢,并运用“经验”“体验”的方式将非理性的情感和丰富的存在性情绪察觉并表达出来,呈现出不一样的思维与言说方式。正因为这种不同于以晦涩面孔呈现的逻辑论证的“哲学”方式,这种贴近大众的感受与经验的方式,他的著作被称为“生活的哲学”“大众哲学”,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与追捧。
不过,当我们再深入下去的时候,可以发现,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经验思维与他们所批驳的理性思维体现了同样的底基——对象化的思维特征,只不过,前者体现为不一样的经验理性倾向。这种对象化思维以“思”为基准,将一切化为“思”的对象,直至近代,达到了其顶峰状态,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开端,形成了各种形式的主体主义哲学。以下描述清晰地将此点表达出来:“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对举地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手段性等。作为文化观念,人文主义即使不曾获得命名,也渗透体现在从政治运动、工艺思想到文学艺术与环境保护广泛的形态中。因而‘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思潮态度与立场,它属于思想史范畴”。(48)尤西林:《“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哲学上发生了认识论转向,简单地说,就是改变古代基础主义的思想方式,即一种关于绝对不变的存在的先验构想,代之以认识问题来解决本体难题,“在”的问题转为“思”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思想”,人文主义同样发生了颠倒,以“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是意义的最终来源与最高价值”作为自己的核心命题,(49)陈勇:《人文主义危机与存在问题》。蒙田也说得很清楚:“我研究自己比研究其他题目多。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我的物理学”,(50)[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3卷),第277页。从而,“在-思”的本体论思维转为“思-在”的认识论思维。主体主义哲学集中表现为主体成为唯一的标准与权威,但是,当有限的主体将其自身作为标准和权威时,也就无异于对标准和权威的取消,对绝对真理的僭越,最终陷入本体论危机而不能自拔。
对于蒙田而言,他的“怀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中和了典型的“人文主义”本体论危机。典型的“人文主义”指的是我们熟知的中世纪时期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形成的人文主义,被学界称为“意大利人文主义”,(51)肖四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三种主要形态》,《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可谓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呈现出一种艳丽的感性色彩,而不是深沉的理性精神。这场风靡意大利的文化运动片面地复兴了古代世界中的那些具有感性魅力的东西,它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琳琅满目,但是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却收效甚微,而且也没有对罗马教廷和意大利现实社会产生明显的变革作用”,(52)赵林:《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求是学刊》2018年第5期。蒙田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人文主义完全偏于感性的问题,走上了怀疑之路,呈现为另一种形态的人文主义——怀疑论人文主义,亦称为蒙田式人文主义。
不过,根据前文的分析,怀疑意味着对不确定性的肯定,怀疑论人文主义就意味着用这种不确定性的怀疑来保证确定性的自我,在“疑”与“信”之间,“存在”无法被回归自身的“肯定”状态,最后走向“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循环在“思-在-疑”的思维模式中,仍然难逃本体论危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蒙田式人文主义看到的只是人的有限,却没有看到人的精神的超越性存在”,原因在于“蒙田式人文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道德论意义上的‘生活哲学’,是一种形而上的伦理建构,即缺乏一种使人性超越的启示性信仰,上帝只是它借以实现道德完善的工具,是伦理建构的手段”。(53)肖四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连续性》。奥古斯丁认为:“怀疑主义从根本上取消了‘信仰’问题,怀疑主义者夸大了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对他来说,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人生存于‘匾乏’状态,所以人就更迫切需要一种确定性,并以之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因而,“对奥古斯丁而言,解构思想,确立信仰是消除怀疑的必由之路”。(54)张荣:《“Si fallorc,ergo mum”——奥古斯丁对希腊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由此观之,就不能不提及另一种具有“使人性超越的启示性信仰”视角的人文主义形态——基督教人文主义,也称为圣经人文主义。
“由于社会发展轨迹的不同,从早期人文主义时期起,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就具有了自己的特征。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德国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故而被赋予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称谓,伊拉斯谟被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55)王亚平:《培育宗教改革运动的人文主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概括而言,不同于呈现为世俗人文主义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与蒙田怀疑主义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没有诉诸于人性的解放与世俗生活的感性享乐,也没有用“怀疑”消解“相信”,而是以超越性的信仰作为基础,主张从内部进行改革,支持宗教改革。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又不同于宗教改革家,“他们的志向不是去革除教会的腐败和教皇的专制,而是在不触动现行体制的情况下尽可能使基督教多一点人性色彩”,“由于对高雅古典文化的迷恋以及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眷情而最终与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分道扬镳”,没有能够最终实现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倾向于并顺应了理想对现实的屈从,(56)赵林:《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也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当时的教权与王权。究其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信仰的皈依,任何人文主义者,甚至基督教人文学者都无法理解到圣经神学中罪与恩典、律法与福音、生与死之对反关系的深度”,“这恐怕也是作为宗教改革家的路德与人文主义学者之间最深刻的分歧所在”。相反的是,“路德以上帝之道为中心,最终跳出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圈子”,(57)张仕颖:《马丁·路德与人文主义》,《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完成了思想与现实中的革命,在领受天启的前提下,强调人的主体性,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作为有力的武器,解构了那个以神权压抑人性的时代,实现了超越视角下的“信-在-思”本体论转向。
“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即自启蒙以降的人本主义思潮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道虚构的人文主义的长城,实际上已经在各个方面被僭越,现在矗立在那里的可能只是一道幻影般的空壳。”(58)蓝江:《走出人类世:人文主义的终结和后人类的降临》,《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笔者希望危机重重的人文主义,不仅不必沦为“幻影般的空壳”,而且还能够通过对自身清晰的认识,实现固有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