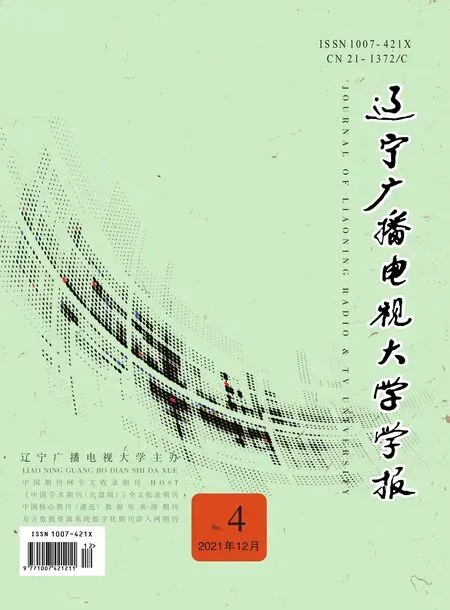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中的生态思想探析
刘冬梅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34)
史诗性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描写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人的生活,以及哥萨克人在两次战争、两次革命中战斗的历史。小说的主旨在于探索陷入1914—1921 年事变强大旋涡中的哥萨克人的悲剧命运。作者肖洛霍夫对战争以及战争带给哥萨克人的灾难性后果做了详细的描写,同时对生态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作品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占据了很大篇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的母题,也是生态哲学的基本命题。21 世纪以来,生态问题逐渐成为涉及自然、社会、精神等领域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现代生态学观点出发,对《静静的顿河》中人与自然主题内蕴的生态思想进行探析,阐释其对当今世界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一、生态思想概述和生态批评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所谓生态思想,是通过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认识人与自然,从而实现生态与社会协调的一种价值观。
中国自古就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哲学思想。当前,国际生态伦理学界被更多人认同的主张和观点,有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等人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平等主义,以及怀特海等倡导的有机论等。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构想,即人和各种生物、自然物同为大地共同体的成员而互相依存,人类应改变在大地共同体中扮演的征服者的角色,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1]。深层生态学也主张尊重和关爱自然。当下,中国特色生态哲学也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点,倡导人与自然为生命共同体,人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生态文学于20 世纪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兴起。以生态文学为基础,王诺在其论文中阐释了“生态批评”的概念,提出文学作品要能揭示和反映生态思想、文化根源和生态审美等核心内涵[2]。鲁枢元提出了“精神圈”概念,认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个“精神圈”,它由人类精神状态构成,对地球生态系统有着重大意义,发挥着重大作用[3]。
二、《静静的顿河》中的自然生态思想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描绘了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和人类战争中的悲惨世界。他把作品精心置于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之下,对处于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危机之下的顿河哥萨克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深入探究。
作为一名乡土作家,肖洛霍夫和顿河哥萨克一样热爱草原,珍视土地,亲近自然。他在哥萨克那里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作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投射在《静静的顿河》中,构建了一个充满灵性的自然世界。在《静静的顿河》中,自然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是一个自足自全的世界。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有着自己的节律和生存法则。读者可以发现,自然这个概念不仅指自然世界客体,更指一种非粉饰的、非雕琢的、非人为的本然。没有什么比自然世界生命存在的更替轮回更加自然而然了。肖洛霍夫在自然之美中体悟到了一种内在节奏,体会到了一种韵律和谐之美,领悟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精神。只有体悟到这些自然之美,才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激起内心深处对根的眷恋,进而感悟自身生命的意义。作家似乎在暗示我们,只有感悟到了自然之美,将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人的生存状态才能真正进入自由的境界,与自然融为一体[4]17。
然而,随着战争爆发,这种和谐被打破了。哥萨克人被迫离开故乡的土地,肖洛霍夫由此开始揭示人与自然分裂后的悲剧后果。当“为了证明人是万物之灵,在很远很远的干谷里,还有一挺机枪一个劲儿恶狠狠地、低低地嗒嗒响着”时[5]1098,“浸在血海里的白俄罗斯的上空,星星闪着凄凉的目光”[5]442,而曾经“骄傲”的太阳已经失去威风,“扮出一副寡妇般的笑脸”[5]322。孕育一切生命的大地“在众多的马蹄践踏下,发出喑哑的呻吟声”[5]249。“愁苦的脸被炮弹打得像麻子一样”[5]277,生命在“悲伤地沙沙哭泣”,在“流血死去”。被吓坏的动物“纷纷离开了荒野山林,向内地逃去”[5]411。鱼鹰被吓得在“水塘上空惊慌不安地叫着”[5]1036,“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村子里明显地露出败落景象”[5]414,被战火焚烧的世界陷入一场空前绝后的危机。战争打乱了自然界的合理秩序,战争是破坏和谐的根源。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世界观问题上,肖洛霍夫认为,应正确理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源于犹太—基督教教义的“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和“把人类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的观点,都要予以坚决反对。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物的一个类别,唯我独尊只能导致自身灭亡。
三、《静静的顿河》中的精神生态思想
战争在破坏自然世界的同时,也破坏着人的精神世界。在这场人祸面前,肖洛霍夫关注更多的是人的“精神自然”。作家将战争引入自然世界的和谐之中,一边展现一个荒芜的内部自然,一边反思人类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
战争使哥萨克人直面残酷的死亡威胁。战场上,为了保全自己,就必须杀死敌人。在这种敌对双方的战斗中,士兵们逐渐抛弃了对生命的尊重与敬仰,人性不断迷失、沉沦,在更多的战斗中表现出兽性的冲动与狂热。对于每一个参战的哥萨克人来说,虱子、恐怖、死亡和无法排遣的思乡情绪在逐渐毁灭他们。可见,战争就是导致人孤独、彷徨、迷惘、脆弱、失去归宿的根源,战争也暴露出反人性、反道德的本质。战争摧残了哥萨克的身体,也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善良纯朴、道德健全、敬爱亲人,这一切美好在残酷的战争中都荡然无存[4]33。小说中的加夫里尔·利霍维多夫就被眼见的死亡吓疯了。
当人类世界在相互厮杀时,自然世界依然在以它自身的生命节律运行着,与充满凶杀和仇恨的残酷而动荡的人类世界相抗衡。在钩儿被杀害的半个月后,他的坟堆上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新生命,还出现了一块由一位不知名的老头儿安放在坟头上的供牌,“在供牌的三角形水檐下的阴影里,是圣母悲哀的面容”。这个供牌警醒着世人不要再自相残杀,只有放下仇恨,才能开始全新的生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生存本身。自然的生命是生生不息的,于是作者又特意描写了一群野鸭的生活:“过了不久……一只母鸭子生下九个蓝中带黄的花蛋,母鸭子便卧在这些蛋上……”[5]1704通过对大地上自然景物的描写,肖洛霍夫似乎在暗示着一个哲理:人们要向大自然学习,以大自然为榜样,按照大自然那种安宁而有序的样子来重新建设人类的生活。
在小说中,肖洛霍夫对主人公葛利高里复杂矛盾的心理世界进行了精妙刻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葛利高里的人性是完满的。他身心健康,热爱劳动,珍惜生命。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的人性越磨越少,兽性越聚越多。在人性堕落的可怕时期,他时常梦想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和劳作,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具有一种使人获得新生的神奇力量,童年是人最纯真的一个时期。他的这一理想,使他恢复了生命激情,激发他向人的本真状态回归。在古希腊人那里,自然的含义更多的是指“本原”或“本性”。肖洛霍夫告诉我们,“人与自然同一”还蕴含着人与自身自然本性的和谐统一。完整人性应从属于自然人性,它“源于自然所固有的内在秩序”,自由、单纯、和谐、有序、关爱生命……作者由此促成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认识的和谐统一[6]。
在小说的最后,葛利高里将他的步枪扔进水中,回到他的家乡。作家坚信,生活仍在继续,故乡的土地和孩子是象征意象,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孩子象征着繁衍和生生不息。只有回到故乡的怀抱,人们的精神才有寄托,生活才有血缘根基。葛利高里的世界是人民的世界,肖洛霍夫的回归本土,可以看作是民族生活美学理想的回归。
结束语
自然往往能代表并展示文艺的最高理想——美。古今中外的作家和智者,经过上下求索之后,最终总是回到自然,以美作为最高的寄托。肖洛霍夫受到一种积淀在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影响,通过自然整体意象,反映出俄罗斯民族同时也是人类心灵美的客观实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既与作家的理想有关,也体现了俄罗斯人的美好愿望,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民族精神。21 世纪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促进和谐共生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会议上多次倡议,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