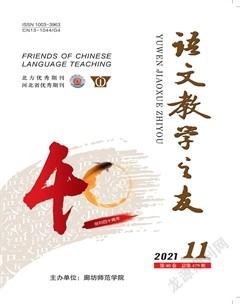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文言虚词教学
摘要:“矣”是常见的文言虚词,有表肯定、感叹等用法,教学中教师往往满足于学生掌握了“矣”的意义用法,对其表达的情感意蕴重视不足,这是有违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精神的。“矣”的意义、发音使得其在表情达意、挖掘情感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矣”既可用于针砭时弊、说理分析,又可用于表达关切感慨、理解人物,是把握文脉、建构个性化解读的重要抓手。
关键词:矣;针砭时弊;说理关切;个性化解读
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通过丰富的语言实践,形成个体言语经验,突出“审美鉴赏与创造”的重要性。反观目前的文言文教学,存在教学目标异化、教学评价单一化等问题。一些教师过分注重教学成绩,对考查题型、答题技巧训练较多,而对学生的参与生成、个性化审美解读重视不够。
具体到文言虚词教学,基本是教师的独角戏,课堂互动仅限于机械的师问生答,少有生成性的交流。教师对文言虚词的意义用法大多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诚然是读懂文言文的基本功,但虚词出现频率高,用法活跃,且不说源自英语语法的表承接、表转折等知识能否与文言文内在结构完美对接,单就课堂效果而言,片面追求学生掌握虚词的意义用法,整堂课就会“死于章句”。这种教学模式,不符合以“学”为中心的理念,但却是当前文言虚词教学的常态,尤其生源较差的学校,学生功底薄弱,教师需花大力气夯实基础,词法句法的讲与练占据了文言文学习的大量时间,导致教学内容固化、教学方法僵化。
文字是古代士大夫交流思想、抒发情感的重要工具,是有血有肉鲜活的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文言虚词教学在激发学生审美体验与创造、培育核心素养方面可以改进,拟以“矣”字为例进行分析。
一、忧之深责之切——《师说》三叹针砭时弊
论说文教学着眼于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侧重于分析论据之精准、论证之严谨。受文体所限,论说文语言朴实平易,精炼准确,不以夸张渲染见长。选入教材的议论文大多篇幅短小,结构简单。论说文不是“以情动之”,而是“以理晓之”。然而,好的文章是情感、义理、文辞并重的,短的文章很难仅以义理见长,情感支撑必不可少,论说文也不例外。
《师说》是劝士大夫主动从师学习的论说文,作者韩愈的情感态度非常鲜明,虚词“矣”的频繁使用即是明证。“矣”在古代汉语中有表肯定、表完成、表感叹等用法,这些在《师说》中都有体现。
《师说》一文第2段历来为人称颂,该段中“矣”出现了6次,对作者的情感表达有重要作用。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中的“矣”既表完成(既成事实)又表感叹,说明士大夫群体中从师求学已过时,“耻学于师”風气延续很久了。作者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谁懂得儒家之道谁就可以做老师,不应拘泥于年龄、地位等因素,这是应有的从师之道,士大夫忘记了这点,作者才有感而发,有了这个逻辑前提,“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话锋一转,切换到针砭时弊。“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惑矣!”“师道之不复可知矣!”三个“矣”三次感叹,由浅到深,“矣”作为关键词,有力助推该段内容和情感进程。
第一个“矣”在肯定客观认知规律的基础上反向证明“耻学于师”的荒谬。“惑矣!(糊涂啊)”则是针对士大夫“于其身也,则耻师焉”的感喟,言辞恳切。同为士大夫阶层,韩愈对门第贵族止步于现有层次而不主动学习提升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和不满。第三个“矣”更进一步,与“巫医乐师”对比后,更加突出“士大夫之族”的愚蠢可笑,在从师求学这点上,他们甚至比不上低他们一等的“百工之人”,一向自诩为知识精英的士大夫陷于自身的傲慢和偏见,砥砺学术方面远远落后于底层各种工匠,理由竟然是“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作者听闻后,不禁“呜呼!”
《师说》一文第2段是全文的主体,旨在批评士大夫“耻学于师”。文中运用了三组对比,前人称之为“三峰插天,轻重相形”:先是纵向与“古之圣人”对比,批评“今之众人”自以为是,由“众人(普通人)”堕为“愚人”。然后横向与“童子”对比,童子尚且从师学句读,身为成人的士大夫却“耻师焉”,实在是“小学大遗”,轻重不分!最后,为士大夫不齿的“百工之人”钻研技艺,“不耻相师”,士大夫竟然“群聚而笑之”,活脱脱一群小丑形象。
作者对这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疾,情绪越来越激动,该段的情感由铺垫到高潮,有迹可循,始而语重心长“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继而感喟责怪“惑矣”,终而痛心疾首“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三叹一次比一次强烈,溢于言表,可谓“忧之深,责之切”。“矣”丰富内涵的揣摩体会可作为分析该段的重要线索,可通过合作探究、个性化朗读等方式品味作者时而感叹时而激动又夹杂着些许愤怒的复杂心情,这些都缘于作者对“耻学于师”的不满。
二、细微处显功力——“矣”背后的说理与关切
《六国论》是借古讽今的一篇政论文,是一篇非典型性议论文,作者苏洵钟情于现实政治需要,文章热情有余而思辨不足,不过可看出作者对北宋潜在危机的深度关切,“矣”在文中出现5次,具体如下:
1.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2.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3.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4.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
5.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5个“矣”辅助说理,更重要的是表达忧思。贿赂秦国使六国越来越弱,秦国越来越强,此消彼长、实力悬殊导致各国无法善终自保,先后灭亡,“矣”的作用是陈述、感叹,指出韩魏楚赂秦的危害和齐国妄想独善其身的短视。前4个“矣”语重心长,第5个“矣”饱含热泪,作者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意在提醒北宋统治者勿重蹈覆辙,“下而从六国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一句可见其写作意图,“矣”一声感叹蕴含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居庙堂之高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割地求安的外交政策十分担忧,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规劝北宋统治者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迷途知返。
作者爱憎分明。韩楚魏三国贿赂秦国直至亡国,不值得同情,齐燕赵没有贿赂秦国,情况各不相同,齐国是秦国的盟友,不用贿赂,燕国实力弱小,影响不了大局,作者最欣赏赵国,强硬对抗到底,中了反间计惜败,最值得敬佩。作者惋惜六国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尤其韩魏楚被秦国“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假如六国团结抗秦,“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呜呼”“悲夫”两词可见作者感慨之深。“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是全文内容主旨句,作者卒章显志,讽喻北宋统治者坐拥统一国家,国土面积数倍于六国中的任一国,如果效仿韩魏楚,一味屈膝求和、赂敌求安,结局将是亡国灭种。
“是又在六国下矣”同样也是全文情感高潮句,末尾“矣”改成“也”并不合适,同样表感叹,同样是肺腑之言,“矣”比“也”关切更深,情感更浓烈,语气却更隐忍克制,有一种沉郁顿挫的美。“也”一般是心有同感、恍然大悟而发,如:“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从发音口形来看,“矣”的韵母“i”是齐齿呼,适合深沉浓烈心情的克制表达,符合大臣向皇帝谏言的身份、场景,更容易让皇帝体会到自己的赤诚之心,进而获得同情支持;而“也”的韵母“e”是开口呼,较为洒脱随性,类似于仰天长叹,多用于抒发个人感叹,其目的不在于获得对方支持认可,不适合用于向皇帝谏言。可见,虚词虽不表实际意思,却也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存在,苏洵作为文学名家,对“矣”的使用非常恰当、很见功力,既论证了贿赂敌国的后患无穷,又表达了有志之士的深度关切,还顾及到了皇帝的面子和感受。
三、或恭或倨不辱使命——“矣”折射的人物形象
《烛之武退秦师》中“矣”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左传》的特点是叙事简省,给读者留下了补白空间,“矣”作为重要语气词,是把握人物心理、揣摩语气进而建构个性化人物解读的有效切入角度。
秦晋围郑,“国危矣”是忧国忧民的佚之狐内心焦虑的自然外化,应情感饱满,低沉呜咽地缓缓读出这三个字,尤其“矣”应咬紧牙齿读才可见担忧之切。生死存亡之际,慧眼識珠的佚之狐向郑伯推荐了烛之武。
“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矣)。”此句貌似推托,实则是烛之武的牢骚,借机发泄其没早被重用的不满,并非真觉得自己年老不中用。两个“矣”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烛之武语气中隐含的怨气,读时应适当上扬并拖长语调。有学生根据对话内容想象建构了郑伯与烛之武对话的情境:烛之武弯腰低头,双手抱拳放在身前,喜怒不形于色,郑伯听出了话外之音,从台阶上走下来,耐心解释。
也有学生认为烛之武是时来运转,在郑伯面前没那么恭敬,而是有点倨傲的,他脑海中双方对话的情境是:烛之武说这句话时,右腿支撑全身,左腿向侧前方叉开一步,略带得意地微微晃动,双手负后互握,放在腰间,腰杆挺直,头呈45度角向侧前方扬起,不满中带着些许得意,不拿正眼看郑伯,郑伯则放低姿态,陪着笑脸解释道歉,道歉无果,郑伯恼羞成怒,“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语带威胁,目露凶光。
哪种情境更合理呢?
有论者指出,春秋时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室虽然衰微,士人仍从属于周天子,对居住地的诸侯王没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选择赏识自己的诸侯国,所谓“贤臣择主而事”。烛之武之前不受郑伯赏识,怨恨在心,此时发泄不满也合情合理,无需顾虑太多,这样看第二种情境可能更符合实际。
不管怎么说,烛之武答应了郑伯的请求,同意去说服秦穆公撤军。说退以虎狼之心觊觎中原的秦穆公,需要冷静理智的局势分析。“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中的“矣”相当于“了”,陈述客观事实,不做无谓的抒情感叹,以秦穆公的精明,不讲点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是没有用的,所以烛之武一开始就承认郑国毫无还手之力,没有说什么大国不能联合欺负小国的大道理,紧接着帮秦穆公分析了郑国灭亡后的地缘政治局势,认为亡郑利晋,存郑利秦。“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进一步火上浇油,翻出晋国的黑历史,提醒秦穆公晋国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并不值得信任,还有可能反戈一击。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个简单的“矣”字其实有丰富的内涵,韩愈的三次感叹、忧深责切,苏洵、佚之狐的爱国之心,烛之武的牢骚满腹、或恭或倨、外交才华都由此可见一斑。
“矣”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表感叹、表完成、表肯定等标签往往抽干了语境的多义和复杂性,不符合新课标“情境中教学”的要求。只有通过文本细读、咀嚼品味,才能见微知著,建构属于学生自己的审美鉴赏与创造情境。
作者简介:张红万(1982— ),男,浙江省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文言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