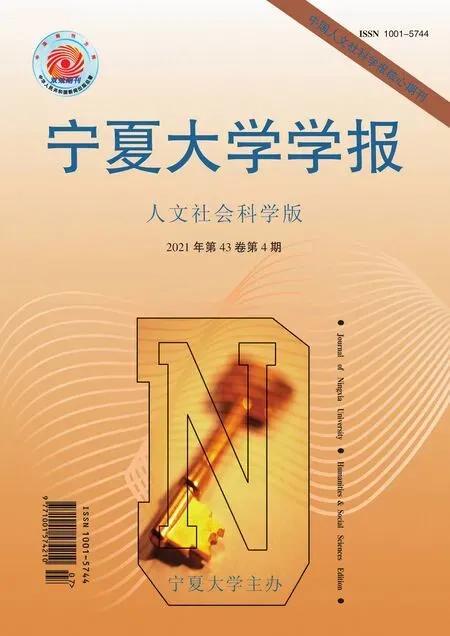论明代前后七子的六朝文学观
王雷超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由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在明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序》云:“嘉靖之季,以诗鸣者有后七子,李、王为之冠,与前七子隔绝数十年,而此唱彼和,声应气求,若出一轨。海内称诗者,不奉李、王之教,则若夷狄之不遵正朔”[1]。如果从弘治六年(1493年)李梦阳最早举进士步入文坛算起,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后七子中最为高寿的吴国伦去世,在这恰好百年时间中,“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2]的理念深入时人心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认为前七子的复古途径当是“敦古昉自建安,掞华止于三谢,长歌取裁李杜,近体定轨开元”[3]。“三谢”指的是谢灵运、谢惠连、谢脁,主要活跃在六朝中的东晋、宋、齐三代。无独有偶,李攀龙在《报刘子威》中亦赞同道:“汉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废,惟唐中叶,不堪复入耳”[4]。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前后七子对于处在“汉魏”和“盛唐”之间的“六朝”文学给予一定关注,他们对六朝文学的品评和态度的微妙变化,是其文学史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一 古近体之交中的六朝文学
王九思所说的“诗必曰汉魏盛唐”的主张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在古体诗中师法汉魏及汉魏以上之古诗,如《诗经》《古诗十九首》等均应计入其中;二是在近体诗中师法盛唐,如李白、杜甫等大家。众所周知,近体诗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六朝文学中许多对偶工切,用律妥帖的作品实际上为盛唐近体诗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前后七子对六朝文学的评论亦常常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前七子多从古体诗的日趋破碎批判六朝文学,而后七子则立足于近体诗的产生充分肯定六朝文学的转换之功,包括对偶、格律、境界等多个层面。在这一过程中,后七子警觉到复古运动中出现的模仿蹈袭现象,借对六朝诗“偶合”古语的评论开启了从“格调”向“神韵”论诗的先声。
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出了一个当时关于古体诗的经典论断:
“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比空同尝称陆、谢,仆参详其作,陆诗语俳体不俳也,谢则体语俱俳矣,未可以其语似,遂得并例也。故法同则语不必同矣。”[5]
针对他的这一说法,李梦阳可能认为此书信后段中“舍筏登岸”的论点更值得批判,所以并没有直接予以回应。从李梦阳在主持刊刻陶渊明、陆机、谢灵运三人诗后所写的《刻陶渊明集序》《刻陆谢诗序》来看,李梦阳亦不可能对何景明的说法予以赞同。他在《刻陶渊明集序》中说道:“夫陶子,知其人者鲜矣”[6],又在《刻陆谢诗序》中说:“子亦知谢康乐之诗乎?是六朝之冠也”、“夫五言者,不祖汉,则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当效陆、谢矣”[7],认为陶、陆、谢等人不失为学习五言古诗的进阶法门。倒是李梦阳的追随者黄省曾在《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中说道:“今有号称海内名流,而乃为论曰……至于退之、陶、谢,亦可少宽宥矣”[8]。从这封书信来看,“海内名流”所指的当是何景明,黄省曾认为他的说法过于严苛。前七子中的王廷相则在《答黄省曾秀才》中为何景明辩解道:“诗至三谢,当为诗变之极,可佳,亦可恨也,惟留意五言古者始知之”[9],将讨论的中心从谢灵运扩展到“三谢”。前七子文人集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立论颇高,试以陆、谢之具体诗作加以说明。陆机的名作《又赴洛道中二首》已经注意在古诗中间部分进行俳偶化描写,如其中的“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10]一联对仗工偶。此诗从整体上而言仍然能够一意直下,古诗的体格仍存。至于谢灵运,以他的《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为例,对偶的成分明显增多,诗中的“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11]一联,用语巧妙,色泽艳丽,和质朴浑厚的古诗已经气象大别。“诗弱于陶”的论述,应当是指陶渊明淡泊自然的风格和慷慨多悲思的古诗代表了两种风格倾向,属于见仁见智的风格范畴。
在前七子讨论六朝古体诗的基础上,后七子的目光从古体转向了近体。前七子论六朝文学时注重上比于汉魏文学,而后七子讨论时则注重六朝之下启于盛唐。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谢氏俳之始也,陈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极也。六朝不尽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时代优劣也”[12]。虽然认为六朝文学在古体中加入俳偶对句的功夫未能臻于自然,但总体而言仍是持褒许的态度,不再以时代为优劣轻视六朝的俳偶之作。王世贞更从“调”“气”之角度肯定谢氏诗人对于唐调的启发:“灵运语俳而气古,玄晖调俳而气今”[13],谢榛将此概括为“诗至三谢,乃有唐调”[14]。重视诗之“调”与可歌咏本为明代前后七子论诗的共同特点,李梦阳在《缶音序》中曾以“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15]来指责“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16],但对于唐调何来没有作深究。后七子于此深思转密,较前七子再进一步,这和前后七子的实际创作成就有密切关系。谢榛曾引用栗太行语道:“李献吉、何仲默,古体可追古人,近体尚隔一尘”[17],认为前七子的专长在古体诗创作。后七子娴于近体诗的观点以胡应麟之总结最为恰当:
“于鳞七言律绝,高华杰起,一代宗风。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驾。……子相爽朗以才高,子与森严以法胜,公实缜丽,茂秦融和,第所长俱近体耳。”[18]
从实际创作中的体会出发,后七子对于六朝文学俳偶化的发掘实是必然的结果。
六朝文学中的俳偶、格律化之作是文学形式逐渐发展的要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内容的绮靡一直以来被后代诗人们所诟病。李梦阳在《章园饯会诗引》中说:“大抵六朝之调悽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19]。不仅批判六朝文学,且将俊逸的六朝书法也一并驳斥,颇有一笔抹杀的倾向。其实早在唐代,从李白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20],到韩愈的“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21],绮靡的文风一直同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不符。同样是唐代的作家,虽然对六朝多有批判,他们诗歌的意象境界和六朝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后七子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道:“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22],指出初唐四杰能够在绮靡之中注入“老境”风骨,方能胜之。谢榛指出盛唐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同,即使模仿六朝诗句,亦能够摆脱软靡的倾向,他在《诗家直说》中以杜甫的“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等诗为例,认为这些诗“诸联绮丽,颇宗陈隋。然句工气浑,不失为大家。譬如上官公服,而有黼黻絺绣,其文彩照人,乃朝端之伟观也”[23]。在后七子的眼中,唐诗能够化六朝之绮靡为盛唐光英朗练的气象。如陈后主向来被视为宫体诗的代表人物,谢榛认为他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一联“气象宏阔,辞语精确,为子美五言句法之祖”[24],充分体现出代不废人,人不废诗的论诗精神。
从诗歌的境界风格而言,前后七子所偏爱的是雄浑高华的风格,李梦阳将此概括为“高古者格,宛亮者调”[25]。谢榛又以“韵”济之,他提出“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26]的审美理想,并引《扪虱新话》中的陶渊明、谢灵运诗为例证:“诗有格有韵。渊明‘悠然见南山’之句,格高也;康乐‘池塘生春草’之句,韵胜也。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27],格、韵并举。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主要就六朝人诗歌中用语偶合古人的现象说道:
“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如‘客从远方来’,‘白杨多悲风’,‘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窃也。其次裒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如鲍明远‘客行有苦乐,但问客何行’之于王仲宣‘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陶渊明‘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之于古乐府‘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王摩诘‘白鹭’‘黄鹂’,近世献吉用修亦时失之,然尚可言。”[28]
合而观之,王世贞的“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和谢榛的“韵贵隽永”是对李梦阳“高古者格,宛亮者调”的修正和调剂,启发了七子派后劲胡应麟提出“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29],进一步完善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审美境界论和法度论,对复古运动避免陷入模拟蹈袭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二 前后七子和明代的六朝派
李梦阳在《章园饯会诗引》中言及在前七子兴起的同时,其交游中存在一个学习六朝文学的群体,包括顾璘,朱应登,刘麟等人:
“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习、是尚,其在南都为尤盛,予所知者,顾华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习而尚之,固宜。庭实,齐人也,亦不免,何也?”[30]
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得知这个团体以南京为中心,主要包括一些南方籍的士人。李梦阳敏锐意识到当时有向六朝文学转向的士人,所以针对六朝文学进行了批判:“夫泝流而上,不能不犯险者,势使然也。兹欲游艺于骚雅、籀颉之间,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31]。他认为六朝文学以及六朝字学只是文艺复古的一个阶段,最高的目标应当是诗中之“骚雅”和字中之“籀颉”。李梦阳在世的时候尚且能够维持复古运动群体的向心力,避免此派诗人因学习六朝文学造成复古运动的分崩离析。以徐祯卿为例,王世贞认为他是明代六朝派的代表人物:“六朝之华,昌穀示委,勉之泛澜”[32]。徐祯卿在进士及第后主动向李梦阳靠拢,《列朝诗集小传》云“(祯卿)登第之后,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33]。他的遗稿由李梦阳亲手进行删订后方才刊行,李梦阳所删掉的实则多半是徐祯卿的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34]等具有六朝风味的诗。
正德年间,李梦阳和何景明二人往复辩难,此后复古派文人亦分左右袒。由王廷相主试时所提拔的薛蕙在当时是尊何抑李派中的一员,他在《戏成五绝》中说道:“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35]。薛蕙是当时六朝文学的学习者之一,王世贞以“六朝之才”许徐祯卿,“六朝之学”许杨慎,再将薛蕙与二人对比,指出“薛君采才不如徐,学不如杨,而小撮其短”[36]。何景明受到薛蕙的推崇,正可能是因为他晚年和杨慎、薛蕙等六朝派文人关系密切,在创作中出现了一定的转向。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曾记载何景明《明月篇》《流萤篇》等诗的创作缘由:
“仲默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37]
何景明在《明月篇》的序言中也提到了此诗的学习对象为初唐四杰,他说:“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38]。朱彝尊曾评价何景明之《明月篇》道:“初唐四子体,今人弃之,若土苴矣。然其音节宛转,从六朝乐府中来,初学者正不可不知也。仲默《明月篇》,拟议颇工,未堕恶道”[39]。值得玩味的是何景明并不承认是在学习六朝,只言明他学习的是初唐体,可见当时六朝派习气未浓。何景明另一则肯定六朝初唐体的记载牵涉到当时关于唐诗七律第一的争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记载何景明以沈佺期的《独不见》(又名《古意呈乔补阙知之》)为唐诗七律第一:
“何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压卷。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40]
沈诗末句作“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41],《独不见》本就是乐府古题之一。其实何止末句,沈诗起句“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42]也颇具六朝乐府特色,清人方东树评论此句道:“本以燕之双栖与少妇独居,却以‘郁金堂’‘玳瑁梁’等字攒成异彩,五色并驰,令人目眩,此得齐梁之秘而加神妙者”[43],可谓独具只眼。
在嘉靖初年前七子与后七子交接的空白期,学习六朝、初唐体的士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影响到了于嘉靖中期崛起的后七子。嘉靖八年进士陈束在《苏门集序》中言及当时的风气转向道:“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学士辈出,力振古风,尽削凡调,一变而为杜诗,则有李、何为之倡。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斌斌盛矣”[44]。王世贞在《答王贡士文禄》中提及后七子崛起前的文坛经历过六朝派的一番洗涤:“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其情辞丽矣,其失靡而浮”[45]。同时学习六朝的,还有吴中的皇甫涍、皇甫汸兄弟等人。王世贞正是受到皇甫汸的启发才开始重视六朝文学的价值:“吾于文虽不好六朝人语,虽然,六朝人亦那可言。皇甫子循谓藻艳之中有抑扬顿挫,语虽合璧,意若贯珠,非书穷五车,笔含造化,未足云也。此固为六朝人张价,然如潘、左诸赋及王文考之《灵光》、王简栖之《头陀》,令韩柳授觚,必至夺色”[46]。后七子的另一领袖李攀龙也在《报刘子威》中说:“汉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废”[47]。此时期重视六朝文学的另一个直接表现是对六朝文学的整理刊行。杨慎在云南戍所编选《五言律祖》,专门取六朝文学中的合律之作;黄省曾编选《诗言龙凤集》,同时的还有薛应旂作序的《六朝诗集》,张谦、王宗圣编选的《六朝诗汇》,冯惟讷编选的《古诗纪》等。李攀龙的《古今诗删》在他去世前数年编成,当为嘉靖末或隆庆初年,时代明显晚于上述选本。受此时代风气影响,李攀龙在《古今诗删》中给予六朝文学充分的篇幅,《古今诗删》34卷,六朝文学独占5卷,收录了多位六朝诗人的古诗,包括谢脁32首,陶渊明24首,谢灵运16首,其他诗人如鲍照、陆机等人亦皆有十首以上作品入选。这一系列六朝文学占重大篇幅的古诗选本的刊行和后七子对其的重视,都表明后七子受到了当时六朝派时代风气的影响。
三 从“理胜则传”到“视古修辞,宁失诸理”
在对六朝文学态度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前七子文学思想中理学内涵的剥落现象。讲学与心学风气过盛后引发出了一种重道轻艺的潮流,为此后七子们另立“视古修辞,宁失诸理”[48]的口号,在实际创作中亦不回避对六朝文学的模仿。
李梦阳在发表关于六朝文学的评价时常常援引宋儒之语为证。他在《论学》中认为陶渊明平和淡泊的心境可以和周敦颐、程颢并驾齐驱:“赵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别是一气象,胸中一尘不染,所谓光霁风月也,前此陶渊明亦此气象,陶虽不言道,而道不离之。何也?以日用即道也”[49]。不仅如此,他还于《刻陶渊明集序》中提出千古以来能知陶渊明其人其诗者寥寥无几,朱熹是真正洞彻渊明心境的人:“夫陶子,知其人者鲜矣,矧惟诗?朱子曰:‘《咏荆轲》诗,渊明露出本相。’知渊明者,朱子耳”[50]。前七子时常将合道之文置于纯粹的诗文之上,前七子中真正将重道轻艺发展到极致的是王廷相。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以为廷相之学根源自张载:“先生主张横渠之论理气,以为‘气外无性’,此定论也”[51]。在《近言序》中,王廷相从文为主而道为客的角度批判魏晋之后的文学道:
“载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该于道,繁则赘,丽则俳矣,故君子鄙之。尝观唐、虞、三代之典,即事命辞,而文生焉,盖道为主而文为客也。魏晋以降,即辞撰事而文饬焉,盖文为主而道为客也。”[52]
他在为友人刘节所编选的《广文选》作序时谈到萧统的《昭明文选》最大的不足是“法言大训,懿章雅歌,漏逸殊多”[53],显然是针对萧统在《文选序》中所说的:“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54]王廷相之后又在《钤山堂集序》中断然认为:“君子修辞,要在训述道德,经理人纪,垂示政典,尚也。必品格古则而后文之美备,故曰‘理胜则传’。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55]。
阳明心学的开创者王阳明本亦为弘治文学复古运动中的一员。李梦阳在《朝正倡和诗跋》中说:“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余姚王伯安”[56],明确将王阳明引为诗学同志之一。阳明心学盛行后,反过来作用于当时的复古运动,造成其中的一部分人由热衷谈论诗艺变为讲致良知之学。正德五年,王阳明至京师,徐祯卿听其谈论后叹曰:“道果在是,而悉以外求?吾不遇子,几亡人矣”[57]。同时受到阳明心学影响而改弦易辙的尚有“弘治十子”中的郑善夫等人。这股风气在阳明殁后仍然不衰,嘉靖年间唐宋派的出现便是得益于唐宋派主将和阳明弟子的交往。李开先的《遵岩王参政传》中记载王慎中居官南京后:“益得肆力问学,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58]。之后王慎中重读宋儒书籍“,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59],唐顺之最初以头巾气鄙之,不久亦变而随之。这种改变使唐顺之晚年的诗“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欲摹效之”[60],又回到了李梦阳倡导文学复古时所批判的“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61],可以说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有被讲学运动吞没的危险。
在此形势下,李攀龙于《送王元美序》中批评王慎中等人道:“今之文章,如晋江、毘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62]。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他提倡“视古修辞,宁失诸理”[63]。李攀龙的理论变革和实际创作是同步进行的,他以《古今诗删》代表他评判抉择的范本,又对选入此书的诗,包括六朝文学作品,一一模仿学习,在具体创作时注重辞藻与技艺的抒发而不注重感情的节制,这其中未必没有和“理胜则传”“理胜相掩”对抗的意味。以他自己创作的四首《乌棲曲》和选入《古今诗删》的梁简文帝、梁元帝《乌棲曲》对比可见:
《乌棲曲》李攀龙
芙蓉如绣柳如织,浣沙渡头日将匿。髙髻双珠玳瑁簮,采莲一曲倾江南。
珠履错落华灯光,长袖宛宛属羽觞。含笑一转心相知,谁能不前复自持?
江南女儿蹋蹀歌,阳春窈窕出绮罗。黄金辔头紫骝马,长安少年事游冶。[64]
《乌棲曲》梁简文帝
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65]
《乌棲曲》梁元帝
沙棠作船桂作楫,夜渡江南采莲叶。复值西施新浣沙,共向江干眺月华。[66]
李攀龙的四首诗从用语的艳丽和辞藻的堆积都超过了简文帝、元帝原作。不仅如此,李攀龙还在《古今诗删》中选入了梁武帝的《白纻辞》以及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等诗,在自己的创作中留下了《白纻舞歌四首》《圆砚效徐庾体》等作品。这些诗作的选入或创作,可以视为对理学风气过于浓厚、重质轻文的一种反驳。
四 “文运”与“世运”:前后七子文学史观的一个中心
前后七子对于六朝文学的书写,是建立在他们的历史观、文体史观和文学史观之上的。从历史观而言,如何看待六朝文学和如何评价六朝的历史地位互为表里,“世运”和“文运”之间关系密切。从文体史观出发,将“文运”和“世运”画上等号后产生出了一种诗文“代有降而体不沿”[67]的单向复古观,这种观点在处理文体的嬗变时容易忽略旧文体中新文体的萌芽因素,导致拟古的失败和赝古的盛行。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史观的构建过程中,对待衰世文学和盛世文学的关系从简单取代到包孕的转化,体现出七子们利用衰世文学再造盛世文学的政治与文学理想。
明代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当时文人对于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尚未能从多民族统一的高度出发进行思考。王廷相在考较士子时所出的《策问》中说:“晋以虚无放荡为尚,使先王礼乐刑法崩弛大尽,在上者无纲维固结之术,在下者成淫僻颓靡之风,是以五胡乘隙因之以浊乱天下,固其然矣”[68]。王世贞对于晋代的评价稍宽,他在《重刻晋书序》中说:“自南渡后,其君臣稍能自标明其统,举聪、矅之耻而洒之,不至若建炎、开禧之单”[69]。认可了东晋初年的士人对于西晋灭亡的反思,但整体而言前后七子对六朝的评价依然否定多于肯定,他们一致认为世运倾颓则文运不振,所以才有李梦阳的“说者谓文气与世运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70]这一代表观点。归根结底,处于明代上升期与成熟期的前后七子在士人心态上认可的是古朴高古的汉魏或昂扬向上的盛唐,文学复古和历史重估是同步的。康海在《王舜夫集序》中说“:明兴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于弘治、正德、嘉靖之间”[71],张佳胤在《沧溟先生集序》中说:“髙皇帝起元季,扫六合之腥膻,而归之大漠之外,天地若辟而朗者,此其盛不直际三代?”[72]无不发越的是这种反思历史、再造盛世的士人理想。
前后七子对于文体史观的考察结论如何景明在《杂言》中所说:“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73]。主张文体代变的文体史观。这种观点在后七子中进一步扩张,王世贞在《李于鳞先生传》中言:“盖于鳞以诗歌自西京逮于唐大历,代有降而体不沿,格有变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损,而能纵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为篇,篇得而为句”[74]。以这种文体史观来评价六朝文学特别是六朝诗,前七子多从古体诗之立场出发,认为六朝文学只不过是学者入门的一个次优选择,后七子则能从近体诗滥觞于六朝立论,较他们的前辈有所开拓。文体的嬗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在考其源流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片面的割裂一种文体的历史容易走向极端。从理论指导创作而言,树立某种文体于一代之最高标准,句模字拟、生吞活剥这些“圭臬”,“于法不必有所增损”,容易抹杀个人的独创性,从拟古走向赝古。两相对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倡导的“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75]、在《宋诗选序》中提出的“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76]无疑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从文体史观的片段论、独断论引发的创作上的失败,根源在于缺乏自身神情,钱谦益批评李攀龙时说的“今也句摭字捃,行数墨寻,兴会索然,神明不属,被断菑以衣绣,刻凡铜为追蠡……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言今则别中、盛为河汉”[77]不无道理,后人对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反思也正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的。
对待衰世文学的一个态度是弃之如敝屣,截然斩断衰世和盛世文学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方法是取长补短,为建立新的盛世文学作积极的准备。何景明学习六朝、初唐体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将六朝和初唐放到了一起进行对比学习;谢榛独见陈后主诗对于杜甫的启发,亦归功于能将衰世文学和盛世文学联结起来。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趋下’。又曰:‘胜国之败材,乃兴邦之隆干;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虽人力,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78]。这和当时流行的“六朝闰汉而开唐”[79]的说法有密切联系。前七子中的王廷相曾为杨慎的《选诗外编》一书作序,序中有“六朝者,唐人之所自出也;汉魏者,六朝之元始者。故得六朝则知唐,得汉魏则知六朝,遡而上之,三百之旨,可以径造,右之性情,风教不于是循以立之”[80]。在七子派和六朝派的交往中,这种观点逐渐趋于成熟,引发出王世贞关于文学史观中“盛衰倚伏”的新思考。注重通变的文学史观也和七子们对《易》的研讨有关。早在李梦阳时就提出:“知《易》者可与言《诗》。比兴者,悬象之义也;开阖者,阴阳之例也。发挥者情,往来者时,大小者体,悔吝者验之言,吉凶者察乎气”[81],此后李攀龙提出借鉴《易·系辞》中的“拟议以成其变化”来进行诗歌创作[82],王世贞曾为《周易辨疑》《易意参疑二编》等书作序,自谦道:“余不佞,家亦世世受《易》,前后踰二十人,然仅以取科第,而亡能名一家言”[83],继以“《易》体不恒,而其用时不尽”[84]来重新思考以周易的变化之道指导文学史观,采用《剥》卦、《复》卦中的阴阳之气迭为盛衰消长来说明文学史的盛衰变化。《剥》卦之象以一阳在上,五阴在下,象征天地间阳气为阴气所侵蚀,恰可比喻衰世文学;《复》卦则以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象征天地间阳气回复,必致亨通,正是指盛世文学的逐渐到来,二卦的关键在于《剥》卦中最上方仅存的阳爻蕴含《复》卦底部阳爻的生长之机,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85]以此二卦观照文学史,可将文学史观中的直线断崖式下跌论改变为波峰与波谷的盛衰倚伏论,辩证看待衰世与盛世文学的关系,才能发出“自是天地间阴阳剥复之妙”[86“]六朝人亦那可言”[87]的感叹,为文学史观的书写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