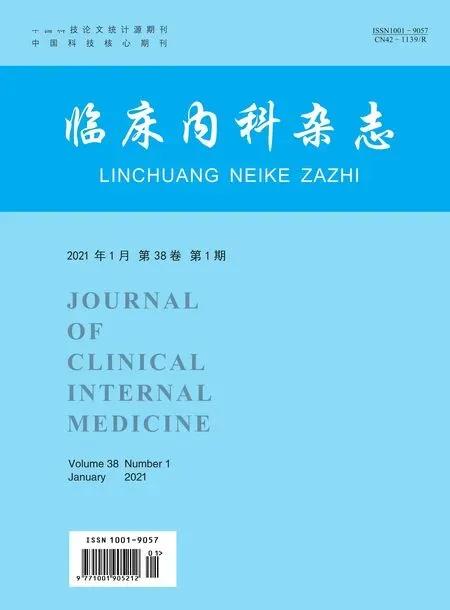妊娠与肺动脉高压
孙荻 刘国莉 任景怡
随着先天性心脏病(CHD)患者的生存期延长及高龄妊娠增多,全球范围内妊娠合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并成为妊娠女性的前3位死因,在发达国家甚至已成为妊娠期死亡的首要原因[1]。其中肺动脉高压(PH)是预后极差、不可治愈的进展性疾病,既往报道妊娠女性的死亡率为25%~56%[2],随着诊治方法的进步,近年来死亡率已较前下降,但长达10年的ROPAC研究发现妊娠合并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患者的死亡率可高达9%,远高于总体死亡率0.6%,在多种妊娠期心脏病中死亡率最高[3]。妊娠期和围产期患者血流动力学显著改变,可加重心脏负担及原有的PH,从而更易发生右心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恶性心律失常、肺动脉高压危象(PHC)、心源性休克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因此,目前国内外指南共识均不建议PH患者妊娠[4-6],但对于有妊娠意愿或在妊娠期首次诊断为PH的患者,如何科学专业进行管理从而改善其临床结局是至关重要且亟需关注的问题。
一、定义
PH是指由多种异源性疾病(病因)和不同发病机制所致肺血管结构或功能改变,进而引起肺动脉压力升高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继而发展成右心衰甚至死亡。PH定义为海平面静息状态下经右心导管(RHC)检查测定的肺动脉平均压(mPAP)≥25 mmHg[7]。考虑到妊娠期间尽管血容量增加,但外周血管阻力包括肺血管阻力下降,mPAP可<25 mmHg[8],对于这部分患者,需结合临床表现等综合评估,必要时可行RHC检查。
根据肺动脉楔压(PAWP)是否≤15 mmHg,PH血流动力学分类可分为毛细血管前肺动脉高压和毛细血管后肺动脉高压。临床分类则将PH分为5大类:(1)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2)左心疾病所致肺动脉高压;(3)肺部疾病和(或)低氧所致肺动脉高压;(4)慢性血栓和(或)栓塞所致肺动脉高压;(5)未明和(或)多因素所致肺动脉高压[7]。本文主要关注第1类PH,即妊娠合并PAH。我国最常见的PAH原因为CHD,其次为特发性PAH(IPAH)及结缔组织病(CTD)相关PAH(CTD-PAH)。在我国,CTD-PAH中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引起PAH最为常见,随着更多SLE患者选择妊娠,妊娠期SLE-PAH值得特别关注。此外,抗磷脂综合征可导致血栓、流产,也可引起PAH,需引起警惕。妊娠期PH各类分型的具体发病率尚不清楚,既往国外研究报道妊娠期PH患者中近60.0%不合并其他原发性心脏病如心脏瓣膜病等,5.8%为IPAH,3.0%合并艾森曼格综合征,2.5%为SLE相关PH[9]。
二、妊娠期PAH病理生理变化
PAH为进展性疾病,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最终发生显著的血流动力学改变、肺血管重构、外周血管阻力增加、右心衰直至死亡。而妊娠期间的诸多正常生理变化,如血容量及心输出量(CO)明显增加等可进一步加重心脏负担,使PAH患者面临更大的风险。
妊娠期间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可发生明显变化。在妊娠28天~第34周时,妊娠女性循环血容量会明显增加,可达妊娠前水平的1.5~2.0倍,并持续至分娩[10]。然而血容量明显增加的同时红细胞数量不能平行增加从而导致生理性贫血。同时,妊娠期间机体的耗氧量也明显增加。这些原因可使机体代偿性CO增加30%~50%,表现为妊娠早期以每搏量增加为主,而妊娠晚期以心率加快(增加15~20次/分钟)为主[11]。
妊娠期间血管舒缩因子及激素水平的变化可影响外周血管阻力。一氧化氮(NO)及前列腺素原等舒血管物质分泌增加,使全身外周血管扩张,全身血管阻力(SVR)显著下降,从而血压下降;对于艾森曼格综合征患者,SVR下降可增强右向左分流从而加重缺氧[12]。此外,妊娠期激素水平发生变化,雌激素与孕酮可对心肺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二者可扩张血管,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并减少利钠肽分泌从而导致水钠潴留、血容量增加;另一方面,还可通过扩张血管降低肺血管阻力,但其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可能与促进扩血管物质生成及减轻对血管收缩物质的反应有关[4]。
由于凝血因子、抗凝因子及纤溶系统异常,PAH患者呈高凝状态,血栓栓塞风险明显增加。既往研究表明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可能破坏凝血与抗凝平衡。PAH患者中检测到血栓调节蛋白、蛋白C或蛋白S异常、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和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水平升高,以上异常变化均可能在慢性血栓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13]。此外,血小板功能异常也可能导致高凝状态。妊娠期间凝血因子和纤维蛋白原水平增加,蛋白S减少,获得性蛋白C抵抗,从而导致高凝倾向,增加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14]。
右心衰是导致PAH死亡的主要原因,随着疾病进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右心衰。妊娠期高血容量及左向右分流均可加重右心前负荷,肺血管收缩、重构、肺血栓栓塞形成及肺血管阻力增加均可增加右心后负荷。此外,缺氧及酸中毒等可直接损伤心肌,心肌耗氧量增加及交感神经激活等可进一步加重右心功能障碍。右心衰反过来进一步导致灌注不足、严重心律失常及其他器官功能受损[10]。此外,PAH患者在诱发因素作用下,原有的肺高压基础上发生肺血管痉挛性收缩、肺循环阻力升高、右心排出受阻,从而导致突发性肺动脉压力升高和低心排出量,即PHC[6]。妊娠晚期、分娩期间及产后1周是发生严重右心衰、PHC风险最大的时期;妊娠晚期明显增大的子宫可压迫下腔静脉从而影响静脉回流,分娩后腹腔压力骤降,这些均可导致回心血量减少,血压下降等;产后血流动力学的剧烈变化及激素的保护作用减弱,也导致心血管事件风险极大、病死率极高。
三、诊断
1.临床表现:妊娠合并PAH的临床表现主要与右心功能不全相关,初期多为非特异性表现,随着疾病的进展,可出现更多典型右心功能不全的症状。此外,会出现与伴随疾病及并发症相关的表现,如肺血流异常分布引起咯血、CHD相关心脏杂音及紫绀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妊娠期首次诊断为PAH的部分患者,PAH表现为恶心、呕吐,这与正常的妊娠反应类似,如未引起重视可能延误诊疗时机。
PHC的诊断标准为肺动脉压突然升高并达到或超过体循环压力,常由感染、劳累、缺氧、手术、酸中毒、药物等因素诱发,临床常有典型的右心衰表现,如烦躁不安、心率增快、血压显著下降、血氧饱和度下降等,甚至有晕厥及濒死感,多见于分娩期和产后最初72 h内。PHC可导致严重的低血压及低氧血症,死亡率极高,一旦确诊需立即抢救[15]。
2.辅助检查:对于妊娠特殊人群,部分辅助检查特别是放射性检查并不适用,临床上可用于诊断及评估妊娠PAH的方法相对有限。
(1)心电图:心电图对PAH诊断的敏感性较低,主要提示右心增大及肥厚。严重的PAH可出现肺性P波、电轴右偏、右心室肥厚、右束支传导阻滞、QTc间期延长等表现,疾病晚期可见室上性心律失常。
(2)超声心动图:超声心动图由于其简便易行、可重复、无辐射等优势成为妊娠合并PAH的一线筛查诊断方法,并可鉴别病因、评估风险、预测预后等[4]。
超声心动图可估测肺动脉压力(PAP)并结合其他右心功能指标评估PAH可能性。PAP通过估测三尖瓣跨瓣压和右心房压力(RAP)获得,测量静息状态下三尖瓣返流峰值流速得到三尖瓣跨瓣压,RAP主要通过下腔静脉直径及吸气时塌陷率估测,其他评估PH的指标包括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心室做功指数、左心室偏心指数、右心房面积等右心功能评估指标,根据以上指标综合判断PAH的可能性,并分为低、中、高度可能[7]。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妊娠期机体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循环血容量明显增加可高估RAP从而高估PAP。
二维斑点追踪技术可通过测量心肌运动应变从而定量评估心房及心室功能,除传统的TAPSE等右心评价指标外,右心室游离壁纵向收缩期峰值应变有助于评估右心收缩功能,右心房应变包括舒张期正向应变、主动收缩期负向应变及右心房整体排空分数等指标可弥补以下腔静脉直径和吸气时塌陷率简单估测RAP的缺陷。研究发现斑点追踪技术参数右室应变及右房功能对判断PAH患者的预后有重要价值[16-17],未来或可应用于妊娠合并PAH患者的心功能评估[18]。
(3)右心导管:RHC为诊断和评价PH的“金标准”,可准确了解PAH血流动力学障碍的严重程度,明确左-右心内分流情况,有助于制定PAH治疗策略[19]。然而,RHC需要在X线直视下操作,通常很少用于妊娠PAH诊断,但并非禁忌。2018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妊娠期心血管疾病诊治指南》对妊娠期RHC的推荐为:RHC推荐用于证实PAH诊断,可在妊娠期间进行RHC检查,但必须严格把握适应证,推荐级别为Ⅰ类C级[4]。既往有小样本研究同时评估超声心动图及RHC对妊娠期PAH诊断的相关性,结果表明RHC排除了约30%超声心动图诊断的PAH[20]。此外,RHC行急性血管反应试验(AVT)可筛选出对口服大剂量钙通道阻滞剂(CCBs)有效的患者,而且AVT阳性患者的预后优于阴性患者。值得注意的是,妊娠合并PAH行RHC检查需严格把握适应证,由经验丰富的术者在使用铅裙对妊娠女性腹部加强防护的情况下进行,并尽量缩短操作时间,减少母亲和胎儿接受射线的剂量。
(4)实验室检查:目前仍然没有反映PAH的特异性标志物,但目前常用的利钠肽[脑钠肽(BNP)和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指标可广泛用于评价右心功能、PAH危险分层和判断预后。其他检查如血常规、血气分析、肌钙蛋白、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电解质等有助于评估病情及合并症等;抗核抗体谱、抗心磷脂抗体、狼疮抗凝物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指标、HIV检测等有助于筛查PAH病因。
3.病情评估及危险分层:结合临床症状、WHO功能分级、6分钟步行距离(6MWD)、超声心动图指标、血流动力学参数及血清生物学标志物等可对PAH患者病情进行综合评估,以判断预后并指导个体化治疗。对妊娠合并PAH患者进行危险分层至关重要,但目前尚无专门的妊娠合并PAH危险分层量表,评估因素可参考非妊娠人群。2015年ESC肺动脉高压指南推荐使用简化的危险分层量表,指标包括WHO功能分级、6MWD、BNP/NT-proBNP水平、RAP、心脏指数(CI)、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vO2)[5]。既往一项国内回顾性研究纳入2012~2015年妊娠合并PAH患者214例,产后随访6周,结果发现心脏并发症的发生率为28.10%,死亡率为2.81%,不良事件发生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症状快速进展、BNP≥300 pg/ml、PAP≥80 pg/ml、WHO功能分级Ⅲ~Ⅳ级、妊娠前PH及28周后分娩,提示该简化分层量表可能适用于中国妊娠PAH患者[21]。2016年中国妊娠合并心脏病专家共识制定了中国心脏病女性妊娠风险分级,将轻度PAH(PAP<50 mmHg)、中度PAH(PAP为50~80 mmHg)和重度PAH(PAP≥80 mmHg)分别判断为妊娠风险Ⅲ级、Ⅳ级与Ⅴ级,风险分级越高,妊娠女性死亡率和母儿并发症发生风险明显增加[6]。改良版WHO孕产妇心血管疾病风险分级将合并PAH的妊娠女性定为Ⅳ级,建议终止妊娠,如继续妊娠,需告知其风险并多学科团队密切监护,每月定期随访。
四、PAH治疗
妊娠合并PAH的患者,治疗目标为改善症状、延缓疾病进展及改善预后提高生存率。妊娠合并PAH的患者应就诊于具有肺高压专业的中心,并由经验丰富的肺动脉高压、产科、麻醉科、重症监护、新生儿专家等组成多学科专业团队进行管理,并制定详细的治疗护理及随访计划。
1.基础治疗:妊娠女性应合理膳食、保证营养,尽量减少体力活动,必要时卧床休息,避免感染。有低氧血症的患者应予以吸氧以维持血氧饱和度在90%以上。出现心衰时需要使用利尿剂,也可用于分娩时减轻液体负荷,一般选择呋塞米或托拉塞米,螺内酯在妊娠早期有抗雄激素作用,不建议使用。铁缺乏的患者需补充铁剂[22]。
2.PAH特异性治疗
(1)靶向治疗:近年来,靶向药物在妊娠合并PAH患者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靶向药物的应用可能与患者预后改善有关。一项Meta分析纳入31项研究共包括77例接受靶向治疗的PAH患者,结果显示其死亡率(16%)明显低于1998年(38%)[23]。内皮素、NO及前列环素为参与肺血管阻力增加及PAH发展的3条最重要途径,PAH靶向药物为针对这3条途径发挥作用的药物,主要包括内皮素受体拮抗剂(ERA)、5型磷酸二酯酶(PDE5)抑制剂、鸟苷酸环化酶(sGC)激动剂及前列环素类似物、前列环素受体激动剂[24]。妊娠期用药极为特殊,药物危险性等级可参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妊娠分级,根据危险性由低到高分为A/B/C/D/X级,其中X级为禁用。
妊娠前已经接受靶向药物治疗的患者如无禁忌应继续治疗;对于妊娠期间新发PAH的患者,序贯治疗还是起始联合治疗预后更佳目前无相关证据,考虑到妊娠期PAH的危害性,通常倾向于起始即联合治疗。关于启动靶向治疗的时机目前尚无相关推荐,但有研究报道显示,相较分娩前或产后启动治疗,早期治疗可明显改善预后。此外,妊娠合并PAH患者死亡可发生于产后数月,故产后应继续延长药物治疗。既往多项回顾性小样本研究及个案报道了靶向药物在妊娠PAH患者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但还缺乏相关对照研究。
(2)CCBs:对于AVT试验阳性的患者,CCBs治疗可显著改善预后,应给予足量CCBs治疗[25]。一项回顾性注册研究发现AVT试验阳性的患者应用CCBs治疗后,妊娠期未出现并发症,硝苯地平、地尔硫卓、氨氯地平为常用的长效CCBs药物,维拉帕米因其负性肌力作用常避免使用。
(3)抗凝治疗:妊娠期至产后8周机体处于高凝状态,尽管尚不清楚妊娠合并PAH是否会增加深静脉血栓栓塞风险,但若无禁忌证,对于妊娠合并PAH患者推荐抗凝治疗,且产后24 h后若无出血倾向应继续抗凝治疗。华法林可导致胎儿出血、中枢神经系统畸形及自然流产,妊娠期间不推荐使用华法林及非维生素K口服抗凝药物。妊娠期PAH患者推荐尽早使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治疗期间需密切监测凝血功能,特别是在妊娠初期及产前,分娩后如无禁忌可改为口服抗凝药物治疗[22]。
3.手术治疗:严重妊娠合并PAH最终发展为终末期心衰,治疗目标通常为减轻负荷、改善氧合及循环灌注。经充分药物治疗(包含前列环素类似物)后无效、WHO功能分级Ⅲ或Ⅳ级、心脏指数<2 L·min-1·(m2)-1、RAP>15 mmHg、6MWD<350 m及有进行性右心衰迹象的PAH患者建议行肺移植,包括单肺移植、双肺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绝大多数推荐行双肺移植[5]。球囊房间隔造口术(BAS)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为肺移植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BAS通过建立心房内右向左分流,降低右心压力,尽管可降低动脉血氧饱和度,但通过增加心输出量仍可改善循环。BAS通常作为等待肺移植的桥接治疗或姑息治疗,可使患者等待肺移植术的成功率达30%~40%。ECMO分为V-V ECMO及V-A ECMO,在术中及术后ECMO支持可减少围术期并发症,避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等。近期一项妊娠PAH系列研究中,6例严重PAH患者产后使用了ECMO,但最终数月后死亡,高死亡率主要与PAH本身严重程度相关[26]。
五、妊娠管理
妊娠合并PAH预后极差,目前对于PAH患者,一旦确诊PAH应告知妊娠风险并建议严格避孕,指导PAH患者选择有效合适的避孕方式。雌激素类避孕药物应注意静脉血栓栓塞(VTE)风险,仅使用孕激素类避孕药物不增加VTE风险,波生坦等ERA可降低避孕药物效果;放置宫内节育器较为安全,如采用永久性避孕措施如输卵管结扎术应注意围术期风险[10]。
妊娠期诊断PAH的患者同样建议及时终止妊娠,对于不愿终止妊娠的患者,应由多学科团队联合管理,加强妊娠期监测,并制定详细的个体化妊娠诊疗计划,包括分娩的时机与方式等。终止分娩的时机尚无统一定论,应根据心功能、胎儿情况、孕周等综合考虑,如患者病情不稳定,不能耐受继续妊娠,则应随时终止妊娠。在妊娠32~34周有计划地终止可降低母婴死亡率,改善预后;仅病情稳定的轻中度PAH患者可维持妊娠至34~37周;对于风险极高的患者如重度PAH、合并艾森曼格综合征等,妊娠周期一般不宜超过32周。
妊娠晚期特别是分娩期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可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带来极高的死亡风险,因此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至关重要,涉及分娩方式、麻醉选择及预防产后出血等方面。目前最佳分娩方式仍有争议,尽管诸多专家推荐剖宫产手术,认为可缩短第二产程,降低分娩过程中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性,但目前并无证据支持。经阴道分娩可减少出血及感染几率,但产程过长、疼痛及Valvasa动作可减少回心血量并增加心肌耗氧量等从而恶化病情。分娩过程中的麻醉方式也存在争议,2016年中国妊娠合并心脏病诊治专家共识推荐全身麻醉,但也有既往研究发现全身麻醉与产妇死亡率密切相关,硬膜外麻醉或腰麻-硬膜外联合麻醉可能是最佳选择[27]。妊娠合并PAH患者产后出血风险极高,缩宫素可用于治疗产后出血但可导致肺血管收缩,PAH患者应用大剂量缩宫素后可增加肺动脉压力从而引发PHC,因此对于重症PAH患者一般采用物理方法止血。
由于产后回心血量明显增加、疼痛刺激、精神紧张及激素水平剧烈变化,产后第1周为产妇死亡发生率最高的时期,因此分娩后应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此外,死亡高风险可延续至产后数月,因此出院后应继续密切监测心功能及超声心动图等,规律靶向药物治疗,继续个体化口服抗凝药物治疗,并积极治疗右心衰。
六、预后
妊娠合并PAH患者妊娠期并发症多、死亡率高,心衰等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显著高于正常妊娠女性,来自美国的一项大样本研究纳入2003~2012年1 519例妊娠合并PH患者,分析发现与无PH的妊娠女性比较,PH患者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风险显著增加(24.8%比0.4%)[9]。该研究同时发现PH的亚型是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因素。
既往多项研究试图探究影响妊娠合并PAH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但目前多为小样本回顾性研究。ROPAC研究纳入151例妊娠合并PH患者,但仅有26%为PAH患者,分析发现产后1周患者死亡率为3.3%,而产后6个月内仍有2.6%的患者死亡,其中IPAH亚组死亡率最高达43%,但该研究中IPAH样本量过小(7例),与其他研究结果不符;妊娠期间27.0%的患者发生心衰,产科并发症包括流产(5.6%)、胎儿死亡(2.0%)、早产(21.7%)、低出生体重儿(19.0%)和新生儿死亡(0.7%)[28]。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一项研究纳入94例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PAH(PAH-CHD),以母体死亡、严重的心衰及PHC为复合终点,发现总体死亡率为6.4%,艾森曼格综合征、低氧血症、BNP水平升高及心包积液为其独立预测因素[29]。
此外,既往研究大多关注妊娠期及产后短期预后,关于妊娠对PAH患者的长期预后影响尚不清楚。一项来自上海的研究纳入156例妊娠期间首次诊断为PAH的患者,发现在第2次妊娠中新发PAH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初产妇,即PAH发病率随着孕产次的增加而增加,且伴有更加严重的PAH及心衰发生率,产后2年内死亡率也显著高于初次妊娠(10.4%比2.8%)[30]。
PAH带来的产科结局最常见的为胎儿生长发育迟缓、早产、流产及死胎。国内有研究回顾了78例妊娠合并PAH患者的产科结局,发现不良事件包括新生儿死亡、新生儿窒息、低出生体重儿及小于胎龄儿,其中重度PAH与新生儿死亡相关[31]。
尽管随着诊断水平、多学科管理、靶向治疗的发展,妊娠期PAH的死亡率较以前已有所下降,但仍高达8%~16%。此外,近年来妊娠合并PAH的类型有所改变,IPAH之外的PH发病率呈上升趋势[32],因此对于伴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尽早筛查PAH可提高诊治率从而改善预后。对于妊娠合并PAH的此类高危患者,既往研究多为单中心、小样本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从而改善母婴预后,包括最佳药物治疗和产科管理等诸多方面,未来仍需要来自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的证据来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