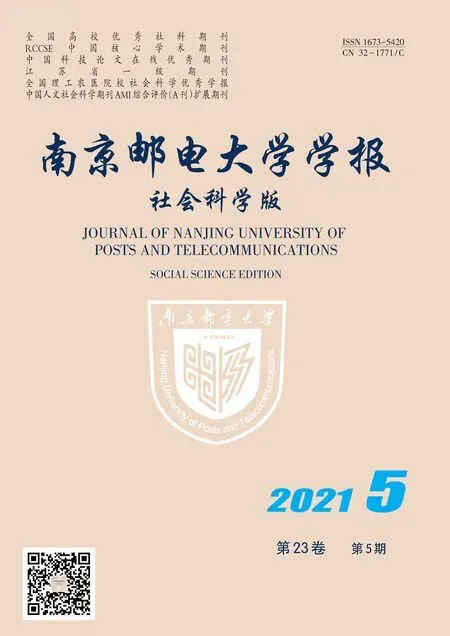从物象到意象:移就修辞的心理表征机制
鲁俊丰
(嘉兴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移就(transferred epithet)是将原本描写X的修饰语A移用到描写Y上,而Y本不属于修饰语A的描写范畴(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the epithet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appropriate noun to modify another to which it does not really belong)[1]315。国内语言学领域关于移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语义的角度探讨这种违背思维规律的修辞现象,认为移就是利用事物间相近、相关原理,依靠人的联想将语义临时巧移,通过形成新的搭配关系揭示词语内部合乎逻辑的深层语义关系[2-3];二是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分析移就构式和语义压制之间的关系,认为构式对移就修辞格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构式的整体意义赋予移就修辞格的意义[4-5];三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把移就视作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交际行为,揭示认知语境在移就修辞格推理中的作用及认知推理如何推动移就修辞格交际意图的实现[5];四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移就的成因,较有代表性的是映射论和概念整合论,前者将移就看作一种认知模式,把已熟知的有关人的情感、行为特征等范畴概念投射映现于具体或抽象事物的范畴概念中去[6-7],后者认为移就是其两个输入空间抽象框架I1与实际情景I2之间的映射,各空间内的成分相对应并在合成空间整合成有违逻辑的虚拟场景,从而形成新的概念[8]。此外,近年来亦有研究涉及移就的态度功能[9]和评价功能[10]等,而心智哲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移就提供了另一研究视角[11-12]。
心智哲学和语言研究密不可分之处在于语言是基于心智的,语言对现实的表征依赖于大脑对现实的表征[13],大脑对现实的表征属于语言前思维即心理表征阶段。可以推测,在确立语言表达式之前,实际的思维过程中还有一个内部语言的阶段,任何意义的表达都通过人的身体的活动图式、心理意象等方式来呈现[14]。有鉴于此,本文将移就视作一种心智活动,通过考察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及感知模拟的实施,来探讨移就修辞的心理表征机制,拟证明心理表征过程是移就意义建构及其语言表达式形成的基础,旨在为移就修辞提供心智层面的解释依据,进一步拓宽移就修辞的研究路径。
一、心理表征的概念
心智哲学认为,语言是从心智产生的,语言的塑造、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心智[15]。具体而言,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如眼、耳、鼻、四肢等)与外部世界展开互动,接收来自外部的信息,以确定客观物体的类别、性质和特征等,即主体心智通过意识活动把人类自身的“感知信息或涉身经验”看作“语言表征或概念的形成与组织的基础”[16],由此形成并强化某种语言表达式结构。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无疑是语言形成的基础,但语言的形成亦离不开人的直接作用和涉身经验。心智哲学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和知觉介于其间[17]。换言之,主体心智上所形成的概念、范畴、图式等并不是对外部世界一对一的镜像反映,而是心智对输入的外部信息进行提取、转换、抽象和加工后,以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的形式呈现在大脑中。
表征是信息在大脑中的呈现方式,既是大脑对客观外物即物象(object)的反映,同时也是大脑加工和处理的对象。现实表征是客观外物的存在方式,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开展活动的物质前提。比如,“屋子”“树” “猫”等都是客观存在于物质世界的,进入人的感知系统被大脑加工和处理后,这些物体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心理表征是指存在于心智上的一种假想的语言,亦称之为心理语言(mentalese)或语言前思维,是具体的语言表达形成之前在大脑中呈现的一种意象(image)。意象是一种基本的心智机能,包括感觉(sensory)意象和认知(cognitive)意象[18]37。前者与心智意象的建构有关,后者与可能的概念类型有关[19]。
以“屋子”的心智加工过程为例,认知主体必须先获得对现实中“屋子”的感知,即通过视觉、触觉等获得对“屋子”这一客观存在的直接感觉,在此基础上提取和储存“屋子”的外形、大小、材质、功能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大脑的处理和加工,会成为主体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并保存在其长时记忆中。由具体的“屋子”转化为心智上抽象概念的“屋子”的过程就是心理表征的过程。一旦“屋子”的概念被提及,上述这些信息就会在大脑中被激活,以心理意象的形式进入思维和语言过程。再如,当听到或看到“动物用爪子贴着地面移动身体或人用手和脚一齐着地走路”的描述时,人们会想到“爬”这一概念。“用爪子/手和脚”“贴地移动身体/着地走路”的一系列状态和动作,将构成“爬”这一概念的动作思维形象地刻画出来。不难发现,“爬”的外部语言表征最先来自认知主体对于“爬”这种状态和动作的切身体验、感受,在心智上以心理意象的方式呈现,形成符合“爬”的一系列心理表征。
由此可见,心理表征是多维的、立体的、非线性的,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同时,心理表征是对客观外物的主观映现,是对现实表征抽象化和概念化的结果。概念化的过程凸显了人的主体因素,因此概念化了的感知信息不一定是对客观外物实际情况的完全反映,而是附加了一定程度的人的主观映像。人类对客观世界经验的概念化的结果,形成了以类层级结构形式储存在人类大脑当中的百科知识[20]。Langacker将意义等同于身体经验的概念化,因而语义就等于能在心智中被激活的概念内容,以及加于其上的识解[21]297。不同于自然语言表征,心理表征无法用具体的词、短语或句子等来表达。心理表征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思维活动,人类心智运用动作思维和意象思维,将大脑中呈现的语义内容抽象成概念和命题,为最终被语言符号表征即形成符合规范的语言表达式做准备。
二、移就心理表征的感知和感知模拟
人类的认知规律表明,主体在大脑的作用下有意识的活动贯穿了认知过程的始末。作为个人经验的主观现象,意识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表征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22]。语言是主体认知活动的外化形式之一,但作为一种概念符号,其本身并不具有意义。认知主体在对外部世界进行感知、选择、处理、抽象化的基础上完成语义建构,然后经过转换、删减、融合、重组、提升等,以特定的概念符号实现意义的表征。受语言符号的有序性和大脑思维的跳跃性这对矛盾体的影响,语言在表达和使用时往往遵循简洁和凝练的原则,相比之下,语言前思维过程则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无限性和混沌性。
任何一种修辞的语义都是由一个本源体和一个修辞体构成,是从源模式到对象模式的映射结构[23]71。在移就修辞中,其本源体就是认知主体(人),而修辞体就是被主体所指向的客观外物,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映射通过心智这一媒介联系起来。一般而言,客观外物的具体特征被人的感知器官接收后进入主体的心智。人们通过视觉感知外物的形状、大小、颜色等;通过听觉分辨声音的强弱、来源、音质等;通过触觉感受冷暖、干湿、软硬等;通过嗅觉识别气味;通过味觉体验酸甜苦辣咸等。移就的本质在于寄情于物、借物传情,因此离不开对物的选择和指向,这就需要充分调用主体的感知觉系统,实现心智与外部信息的有效关联。分析移就的心理表征过程,首先要从主体的“感知”和“感知模拟”等心智运作模式入手。
例1:Instead of drowning the students’ compositions in thecritical red ink, the teacher will get far more constructive results.
例2:Jonathan whispered, putting areassuring armaround my shoulder as we were waiting in front of the courtroom.
例3:花儿诉说着她的快乐,她用五彩芬芳的语言在诉说着她是生命的精灵。(陈立《送你一缕心香》)
例4:头上顶着昏黄的太阳,脚下绵延着绝望的沙漠。(邵会平《寂寞》)
例1中,“red ink”(红墨水)不仅能让认知主体在视觉上感知墨水的外部特征——红色、液体状,而且能激活其大脑中与“critical red ink”(批阅的红墨水)相对应的感知模拟——教师用红笔来批阅学生的作业。通过感知模拟,即便眼前没有实实在在的红墨水,当看到或听到“critical red ink”的语言表达时,主体心智依然可以构建起相关的心理意象。例2中,认知主体运用肢体的触觉即“arm”(手臂)来搭建心智与客观外物的关联,并激活大脑中“将手臂搭在人肩上”这一动作的感知模拟,继而从已有的感知经验中提取有关“reassuring arm”(宽慰的手臂)的隐含信息。通过感知模拟,可以做出如下推断:Jonathan将手臂搭在我的肩上,目的是暗示我放宽心,打赢官司的概率很大等。
例3和例4则是认知主体分别从视觉(花/沙漠的颜色)、嗅觉(花的气味)、触觉(沙漠的温度)及味觉(沙漠致人干渴)等多方面来感知客观外物的特征,因此调动了人的多重感知觉系统。多模态感知(multimodal perception)是语言使用者运用一种以上的感觉系统,或综合使用若干感觉系统吸收两种模态形式的外部符号,强化感知同种意义的表征、建构与理解过程[24]。具体而言,例3中认知主体利用长期的视觉和嗅觉经验,辨色断物、闻香识物,以感知和模拟现实中花的色彩和气味,从而生成对“花语”的心理意象。相比之下,例4中甚至没有出现任何关于沙漠的颜色、温度等物理特征的语言描写,但通过大脑中被激活的多模态的感知模拟,人们在听到或看到“沙漠”二字时很容易触发其心智上的相关视觉(黄沙漫漫)、触觉(昼热夜寒)和味觉(口干舌燥)经验,久困其中必然令人心生“绝望”。
上述各例中的移用语“critical”“reassuring”“五彩芬芳”和“绝望”都是对客观外物的主观评价。移就修辞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使客观外物带上主体的情感色彩,因而不能忽视主体对客体的依赖和顺应。作为寄情之“物”,无论是指向外延还是指向内涵,对其所承载信息的理解与识别往往取决于个体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感受[16]。由此可见,对客观外物的感知及感知模拟的实施能激活认知主体相关的涉身经验,消除物我之间的相对独立,是移就心理表征的前提和条件。
三、移就心理表征的运作机制
移就以客观外物的审美特性同人的思想、情感相契合为客观前提,以主体情感的映射和想象力、创造力为主观条件,是凸显形象和主观情感的有机统一[25]153。人们不是将外物单纯地作为其理性加工的对象,而是通过直观感悟将外物和人的主观意识相融合,在物我的双向互动和观照中实现客观物象的主体化。因此,作为一种心智过程,移就很大程度上受主体意识活动的影响。从修辞心理上看,主体的心理因素能对修辞行为的产生和实施进行有目的的操纵,从而影响对话语的意义建构和理解。根据移就修辞的内涵和特点,可以对其心理表征过程做如下的假设:(1)移就心理表征过程是一种由主体感受而引发的意象思维过程;(2)客体的某些属性具备帮助主体表达某种心理状态的可能性;(3)主体有意识地选择和指向客体;(4)移就心理表征的内容可以随语境不断补足和扩展。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认为移就的心理表征过程具有较强的抽象度和主体性。
例5:Soon after my arrival in Mrs. White’s house, the host handed me ahospitable glass of wine.
例6:历史/倚着愤怒的废墟/站在地狱的门口/以热血/一次次淘洗我们/黎明前的祖国。(李瑛《我的中国》)
上述二例中,“glass”(杯子)和“废墟”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被主体心智选择后进入人的大脑,此时的“glass”和“废墟”已不是物体本身,而是现实表征在大脑中内化后成为主体的意识对象,具有与之相对应的心理表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物体的心理表征要比现实表征更为抽象,也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特征[26]。比如“glass”的心理表征有如下意象:可盛放液体、可用作饮用器具等;而某些与之相关的其他特征是可以缺省的,如杯子的拥有者,宴席上用来敬酒或庆祝、联络感情或结交朋友等。同样,“废墟”的心理表征有如下意象:残破的存在,自然灾害或人为所致;亦可以有某些缺省的特征,如规模大小、历史意义等。不难发现,心理表征都以完整的格式塔(Gestalt)的形式存现于我们的大脑中[26],其中,每一个格式塔包含多个格式塔的终端, 这些终端通常由一系列缺省值填充,填充的方式取决于认知主体的个人经验,具有明显的经验性质。
早在1929年,心智哲学在对人的“身心关系”的研究中就提出了“感受质”(quale)这一概念[27]121。所谓“感受质”,就是客观外物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可以被主体辨识并且在不同的经验中被反复体验,可能因人而异,同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辨识性。感受质是人们直觉的产物,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即客观外物的物理属性对认知主体引发的一种主观的、直接的感觉体验,因此也被称为事物的“心理属性”(mental property)。心理属性依赖于事物的物理属性,但并不等同于物理属性,在主体心智的作用下,这些心理属性被大脑所调用,成为心理表征的对象。比如,例4中提到的沙漠,“昼热夜寒”“干旱缺水”等是其物理属性,而“绝望”是这些物理属性带给人的心理感受(心理属性)。徐盛桓把事物的“心理属性”看作事物自身的性状特征等作用于感知主体的心理所得到的“心理感受”[11],包括愿望 、信念 、感情等,认为心理属性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1)心理属性是事物自身的性质,能被感知主体所辨析;(2)心理属性是感知主体对感知对象直接的、具体的感受;(3)心理属性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形成某种感受的本源;(4)心理属性有“普遍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由此进一步可知,在移就修辞中,主体对于寄情之物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物是否具备某种(些)心理属性,并值得被心智调用来表征主体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感知对象的属性是本源的,感知主体感受到感知对象的特定属性后,引发其某种心理状态[11]。具体而言,例5中的“glass”(杯)本是没有生命的,但成为主体的意识对象后,其“可盛放液体”“可用作饮用器具”等心理意象特征就被大脑所激活。与此同时,作为聚亲会友的一种常见方式,喝酒能够交流感情、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是被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于是在特定的语境中,glass of wine(酒杯)所具有的“联络感情”“表示友好”等心理属性被主体心智充分调用,经过上述心理表征过程,说话人欲传递的“(主人递给我)酒杯以示其热情好客”的意义就得到了建构,表层结构则通过语言表达式“hospitable glass of wine”实现。例6中,“废墟”作为一个区域或物体在遭受毁灭性破坏后的残留物或遗迹,在主体心智上通常会呈现出“残破”“荒凉”等心理意象,这是物象“废墟”概念化后存在于经验中的普遍特质。该例中,当战火留下的废墟映入眼帘时,与之相关的其他心理属性,如“受敌侵犯”“国破民亡”等得到了及时的补充和表征,为作者构建“废墟使人愤怒”的语义做好了铺垫。可见,移就表达式“愤怒的废墟”经历了从物象(废墟)到意象一(残破),再到意象二(国破民亡)的过程,即“愤怒”是由废墟的心理表征激发出来的。
心智哲学认为,主体的心理感受对同身体当时有关的物理事件具有随附性(supervenience)[22],同一个物理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物理事件只能激发出同一种心理感受,那么语言表达便会显得苍白无力[28],因此,认知主体对同一外物在不同的时空和情境中也会有不尽相同的感受。也就是说,一方面,心理表征会受到客观外物的影响,对于客观外物有依赖的一面;另一方面,心理表征又不完全受客观外物的制约,视具体情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自由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心理属性所具有的“普遍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进一步回答了心理属性是如何被主体心智选择和调用的问题,为移就修辞的心理表征机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解释。
例7:Haunted by the procedural complexities and troublesome matters in business, Wesley awoke early after adisturbed night.
例8:袅袅秋风起,萧萧败叶声。岳阳楼上听哀筝,楼下凄凉江月,为谁明?(李祁《南歌子》)
例7中,“night”(夜)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存在于客观世界,并不具有任何的主体情感特征。经过主体心智抽象和加工过的“night”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已失去了原本的客观性特征,而是作为感知对象派生出诸如“休息时间”“宁静”“难以入睡”“漫长”等一系列心理属性,这为认知主体在特定的情境下自主选择情感提供了“依存”空间。试想,当Wesley被生意场上的复杂程序和接连不断的麻烦困扰时,自然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主体在心智的作用下,调用了能体现上述特征的相关心理属性并加以表征,构建了“彻夜心神不宁”的语义。可见,移就表达式“disturbed night”的生成对于“night”的所具有的心理表征既有依赖的一面性,又有独立的一面。例8中,乐器“筝”的弹奏声或缠绵悲切、回味绵长,或如泉水般欢快、清脆灵透。古筝本身并无情感可言,这里所说的“悲切”或“欢快”均源于古筝本身的某些特质及认知主体对于弹奏古筝直接的、具体的体验。同样是听到古筝的弹奏声,被激发的主体心理感受可能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外界的声音在一定情况下会对人的心理造成负向干扰,令人沮丧与消沉,甚至悲观和厌世。该例是作者登岳阳楼时所写的,从更大的语境中不难发现,楼外秋风袅袅、落叶纷飞,楼下江景凄凉,当楼上古筝声响起时,作者感受到的弹奏声之“悲”,凸显和表征了古筝在此情此景中的心理属性。于是,作者寄情于“筝”,建构了“其声愈悲、其情愈哀”的语义,在外部语言上表征为“哀筝”二字。
四、结论
本文通过英、汉两种语料,详细分析了移就修辞的心理表征机制。心理表征以现实表征为基础,是大脑中所呈现的一种意象内容,表现为与客观外物相关的一系列心理属性及对这些心理属性的加工。感知主体通过感知和感知模拟,选择和调用客观外物的心理属性,从而为表达某个特定的心理状态的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人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不断获得感知觉体验,丰富了心理表征的内容和范畴。心智哲学的理论并非研究移就修辞所专属,但关于移就的研究可以置于心智哲学的视角,以揭示其生成的心智过程。作为语言前思维阶段,心理表征过程体现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移就修辞的意义建构和外部语言表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