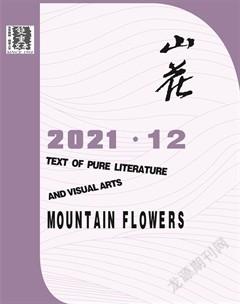喧嚣中的静寂
蓝庆伟
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建筑工地的施工现场、自然中的人为建构……在城市中,人们匆匆而行,每天与这些熟悉的景象擦身而过,偶尔为之注目,随即抛之脑后,即使它们走进记忆,往往也是模糊的存在。这些人工“风景”的命运似乎就是被忽视和遗忘,但是当这些场景中的“人”消失后,它们成为独立存在的景观,反而滋生出一种人力不可及的冷峻气质来。王风华的作品,往往关注的就是这样的景观——它们过于真实,却因大量的直线结构而显得抽象;过于熟悉,却在观众的注视之下显出几分陌生;过于冷静,以至于似乎生出了自己的情感。
这些风景因人而生,却在无人之处呈现出特别的魅力。
无疑,城市及城市化运动给人类社会的现实景观带来的变化是王风华作品的重要主题。城市化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成就之一,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个空间不断重塑、时间不断加快、视距不断缩小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文明的发展既让每一个个体被“卷”入日常与微观之中,也让个体的时间被悄然占用。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人的视域不断下沉,逐渐被忙碌与效率充斥,少有时间和空间能够展开自我与生存环境的思考。与古长安城登塔远眺的视野与心情相比,城市化的西安成为全国的大多数城市中并不起眼的“之一”,登上高楼远眺,立刻会被另一座高楼挡住视野,城市的庞大与人视域的不断微观化形成了对比。王风华虽然在西安城中的西安美术学院教书,但更喜欢在课余偏安一隅开展自己的绘画创作,从早期的纺织城艺术区到现在的满江红工作室,王风华在工作室的选择上有意无意地与现代城市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不断在城市与乡野中穿行,体验着两种不同的视域观看、接触着两种不同的人群、变换着不同的思考方式。基于此,我们可以把王风华称之为“城市观察者”,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乡村观察者”,了解这一背景,也就不难理解王风华作品中的“风景”从何而来了。
王风华描绘城市边缘地带景象的“隅境”系列作品,不免让人联想到爱德华·霍珀,在爱德华·霍珀的作品中,绘画成了生活瞬间的记录者,在这些充满着生活场景的画面中却充满了孤独感——一种现代社会的嘈杂与人际之间的闭塞所形成的违和感。这种“孤独感”和“冷漠”同时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特征,以袁庆一《春天来了》(1984年)、李贵君《140画室》(1985年)为代表的作品有着对“孤独感”的崇尚,在批评家易英看来此类作品有着明显的象征主义倾向。易英在《当前创作中的象征主义倾向》(《美术》1985年第10期)一文中引用了法国戏剧批评家阿·爱华德对象征主义的定义:“象征主义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既满足我们描写现实的愿望,同时也满足我们超越现实界限的愿望。它给我们具体的东西,同时也给我们抽象的东西。”文章最后,易英提示,在这些艺术家具有象征主义倾向的作品中,“强烈的社会意识”是不容忽视的。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作为“池社”的发起者,张培力的《仲夏的泳者》(1983年)、耿建翌的《灯光下的两个人》(1985年)和“理发”系列作品,给人以冷漠感,画面中的人物面容呆滞,与画面之外的观众没有任何的交流,气氛凝重。在此之后张培力与耿建翌的作品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向。2004年,王风华在泰特现代美术馆观看了爱德华·霍珀的个展,并迷上了这位美国艺术家。在此之前,受过学院写实技法训练的王风华饱受写实与观念之间的矛盾的困扰,在他看来写实与观念是一对对立概念,爱德华·霍珀的绘画似乎为他的困扰提供了一种“疗愈”方法。而去欧美观看展览亦成为王风华创作“疗愈”的一种固定方法,年年如此。对西方绘画的学习让王风华在写实与观念之间有了自己的选择——写实成为观念表达,即运用自己擅长的表现方式来拓展新的创作空间。与爱德华·霍珀、袁庆一、耿建翌等因个人原因塑造独特画面不同,在王风华的作品中,虽难觅人的身影,却写满了人的踪迹。也有人说王风华是一位残酷的城市图景裁切者,在他的作品中使人看到那些熟悉的遗忘。
在王风华“大玻璃”系列作品中,城市图景有了新的指向,现代城市建筑最为普遍的玻璃幕墙已成为城市中处处可见的景观——既是楼宇景观,同时也为幕墙内外的观看者制造了阻隔。由“大玻璃”反观王风华的其他作品,这种“阻隔感”随处可见,“隔离”系列作品(包括《蓝色隔离》《白色隔离》《夜隔离》)的出现便是这种人与人关系的一次直接提示。这些建筑工地之外的打围提示着现实中“建设与建成”的两种状态,这像极了身在玻璃幕墙办公楼里向外观看风景的人——他(她)在看风景,却不再成为别人的风景。王风华在2012年3月的个人阐述中,将隔离墙这一普通建筑材料视为历史与当下两个世界的隔离,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感受最深的便是身在其中的人们。在历史与当下的流变之中,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而自然的变化又充当了时间的替代者,在王风华的“隔离”系列作品中,隔离板之间的缝隙常常有植物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时间的记录又是生命的隐喻。在这期间,王风华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全天候的油画创作转为白天画油画,晚上画素描,在这两种形式完全不同但有内在关联的绘画方式中切换视角,以转换思维。而选择在夜晚画素描,恰恰又与王风华多年来创作的主线——物的冷漠——有关。在两个喧嚣的白日之间,夜是静的,素描让人的心绪愈加沉稳平和;在轰轰烈烈向前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夜是休止的,素描也是王风华在油画创作进程中短暂的休整。反之,日与夜的对比也是艺术家理解中油画与素描之间关系的投射——对比繁杂热闹的油画世界,素描过于客观,因色彩、材料的限制,素描的画面不能横向地无限发展,而必须在细节中不断深入。就像人类的活动在白天总有无限可能,但如果没有黑夜,没有休止,总会耗尽精力。让自己从热闹中抽离的“冷”是人类应有的自省,也是自救。
无论是回到远古时代还是眺望充满科幻想象的未来世界,在关于无人地球的想象中,自然的力量始终存在。在信息化、城市化不断加速的今天,在探讨人与城市的关系之中,王风华在最新的作品中又迈了一个台阶,来到自然之后——一种荒无人迹的景象。描绘自然是一种古老的绘画形式,在当下也看似是一种退步的做法,但王风华的“自然”并不是风景的自然而是人为的自然,这种人为的自然因为没有人工物品的存在,使得观者难以辨析“人”对现场的干预。事实上,这些看似自然长成的杂草、石头却是人为影响后的景象。王风华将“自然中的自然”和“人为的自然”置于同一画面中,似乎在用一种最原始的风貌来回应今天最发达的社会,以此讨论城市、人、自然的关系,并为之命名“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毫无疑问,今天哪怕在最为原始的自然之中,也已遍布人的踪迹,从占据到浸染,从未停息,哪怕广阔如海洋也不能幸免。在表面看来没有人、没有人工制品的自然中依然充斥着人的干预因素,“明天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题目是对人的反思,也充滿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担忧。除此之外,王风华在画面上的这种看似从城市向自然的图像“退步”,却在一步步的强化“人”的隐喻。众所周知,在现代主义以来,“人”在思想、艺术上的解放,使得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在当代艺术的范畴中也不例外,“人与人的生存”成为当代艺术中重要的话题。
王风华画的是客观世界,是废墟,是物,但此处无人,处处人迹。人类活动造就了这个世界的样子,世界反过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要什么样的明天,取决于今天我们的所做所为。为了明天我们该如何做?艺术家并未给出答案,有时我们更需要的也不是答案,而是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