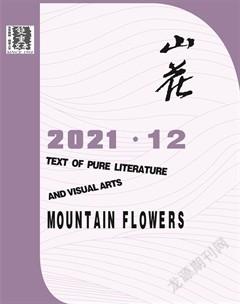幽灵书:尺牍上的自赎
北野
一
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单是我们在生存。万物都派出肉体、风声、阴影和灵魂。所以,万物都各有新生和死亡,各有真理和谬误……
一个幽灵跪在村外诉说自己的委屈;一个幽灵被碾死在路上又变成另一个幽灵;一群幽灵在庙前争抢钱币、车马和仆童;另一群幽灵挤破庙门;更多的幽灵飞翔在风中,借着风的脚力走到各处去,并在风中唱歌、诅咒,向行人掷石头、扬沙子、发脾气。幽灵把你的衣服弄皱,把你的头发弄乱。它坐在窗棂上吹口哨。它吊在树枝上嘻嘻笑;它在尘土里跳舞,跳得一身霉味、冷气森森;它下到井底喝水,搅得水花在半夜里哗哗响。
一个幽灵逃不出狗的追击,十个幽灵就可以对狗进行一场调戏。当一条狗向着不同的方向狂吠乱叫,有多少调皮的幽灵在暗中变得洋洋得意?人的幽灵奴役着动物的幽灵、植物的幽灵。人的幽灵迫使鸟的幽灵居住在星座与星座之间,只允许它的翎羽在雪花中慢慢飞翔和回忆。一个爱心不散的幽灵,把三个迷路的瞎子引到大路上;两个嫉妒心不死的幽灵,把一群快乐的人推倒在地;一个儒雅的幽灵,在书房里默默站在读书者背后,并情不自禁地读出其中几句。
一个醉鬼长时间徘徊在酒坊之外;一个饿鬼闻到美食就流口水;一个病魔把一个健步如飞的男人按倒在床上;一个学过哲学的幽灵永远赢不了另一个学过哲学的幽灵,即便他们夜夜在空中辩论,即使他们吸引了全部幽灵做听众。只有具备足够的美德和才能的幽灵,它才可以跳出树冠和屋檐,跳过讲坛上两个哲学家明亮的头顶。
幽灵在风中吃风、喝露水、结蛛网,做着勾魂摄魄的勾当。更多的幽灵拥挤在空气里,并没有返回人间的希望,只有在沉默中老去。那么幽灵真的会老么?如果幽灵不老,更多新的幽灵的出路在哪里?幽灵把脚步声和身影放在图书馆的走廊上,并在书架间穿行;幽灵把舌头伸进女歌星的嘴里,使她的歌声突然变得鬼哭狼嚎;幽灵把手伸给伤心人,让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幽灵把一双长腿伸出去,绊倒的人有醉酒的、奔跑的、摇摆的、得意忘形的、不知深浅的;但幽灵同时也把自己绊倒:尘土飞扬、烟气缭绕、枯叶溅动,站在逆风中呼哨的树梢,都是幽灵虚无的身体砸翻的羽毛。
我们不敢忽视幽灵的存在,像不敢忽视我们自己的身影。幽灵应该是无所不在的,它们出没在历史里,发黄的典籍中,神话或传说之间。它们诞生在睡梦里,它们不断消失在生活中。埃及人说:我们生存在一个亡魂的世界。我们怀疑是因为我们的虚伪和恐惧,我们不愿意相信有人一直在背后盯着我们(不管它是人还是幽灵)。我们不知道它是谁,它身在何处有何目的?谁在商店疯狂购物却用着一团纸灰?谁在雕像后面发出大笑?谁在用亡者的嗓音说话、唱歌、喝酒?谁在用着仆童的大脑但却做出魔鬼的思考?谁让你得了近视眼,阻止你看到远处?谁让你平白无故跌一跤?谁让你沉默寡言的老婆突然像个母夜叉一样唠叨?
临刑的死囚看见自己的灵魂已经提前走了,他无声地站在自己的背后,看着刽子手把自己的身体,像一件衣服那样折起再放倒。他抱着一本书在半夜痛哭,如同一个饱学之士守着一座博物馆依然孤独。猫头鹰在夜幕下降临,不要把它视为丧门星,雅典娜女神就跟在它的身后,她们一起驾驶着落叶、风声和尘土。而我们必须藏起来,或者销毁死者的一切遗物,以使他们的仇恨和重生的希望变得无迹可寻,让他们的记忆一片模糊;如果他们因此而变成鸟,我们仍然需要躲藏,鸟能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是神秘的,它会在夜晚向一个女巫说出我们未来的诡计。
一个画家在街头看见一群跛足的马匹,他认出那是从他画中逃走的动物。你梦中的祖先会告诉你,你在他坟前焚化的纸车纸马,正在被他所骑乘和享用,他的生活因此而超越其它幽灵;而他如果通过一张肖像,把一个宗族的福音降临给自己的子孙,他就会在一所空房子里发出笑声。如果一个名字在一个氏族里是有限量的,那么你的名字占用了谁的机会?你的名字必由长辈所赐,你的到来必被幽灵所推举,你的命运必定意味着庇护、嫉妒、图腾和赞颂。
所以一个人必然和幽灵有关,尽管幽灵是空洞的,你也不要轻易谈论它或蔑视它。非洲人用巫术生活、狩猎、祈祷、擦拭武器甚至进行战争,他们请求河流带走自己的咒语并在莫名的波浪里弄翻仇人的独木舟,把瘟疫和仇恨放在仇人的村庄之中。尽管我们对未来的关注超过我们模糊不清的前生,但我们没有时间去追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更关心如何为下一代铺平道路。这代代相传的薪火是谁点燃的?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谁?在我们到来之前呢?答案只有一个:幽灵!它是我们的父辈或更远的亲戚。
幽灵在黑暗中吞噬着战争中被杀死的人的心、肝、脂肪和脑髓,以迅速占有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幽灵们在野外猎杀豺狗并吸走它的脑浆,以使自己迅速增加诡诈、机敏、跳跃和隐身的能力,如同掌握了人的头发、指甲、口水、名字或肖像,就可以控制这个人一样,幽灵从火里取走活人烧化给死者的食物和钱币,但永远没法取走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幽灵是无形和空虚的,它们流着泪徘徊在亲人附近。
只是一个瞬间,幽灵就失忆了。只有这样,幽灵才能安心离去,从此人的生活才能与幽灵分开,人才能阴阳两隔:一个留在人间,一个进入地狱。幽灵在黑暗中漂泊,没有家园也没有伴侣,没有直覺也没有嗅觉,对爱麻木不仁,对恨无所辨析。只有经过了一百年劳役之后的幽灵,才能在梦游中把自己弄醒,并学会提着灯笼飞行,它们从此开始有了辨析是非的能力,开始有了仇恨的鬼火和报复的力气;所以一个坏蛋的子孙总要在百年之后才能遭到报应。一个再贪财的人也不一定能富过三代。一个傻乎乎的庸人三辈子也可以造就一代贵族,也可能在梦中生下一个绝顶聪明的后生。这一切都由命运来设计,都属于鬼使神差的范畴。其实这多么合乎天道规范:白天车马喧哗,人声鼎沸;晚上人心惶惶,惊魂不定;即使是人间的英雄,和幽灵站在一起,也必须规规矩矩,鸦雀无声。
当我和幽灵谈到死亡与再生,我们一起为这个话题震惊和迷惑,其实幽灵也必须反复思考这个话题的严肃性,以打开自己尘封已久的心灵,放出另一个不死的幽灵。我接受它们一次问候,就减少一次体重,降低一次体温,以便我们友好相处和在废墟上坐得更久,以便于我们在城头相见并被再次放下城头。百年的幽灵在水塘边抱着七月十五的河灯,它们互相看见熟悉的面孔;一千年不息的爱情之心让一对夫妻在苍茫的天空下互相找见,重新上演一场人鬼不了情;一万年前的祖先突然会以子孙的身份来到人间,也许会带着一万年仍然没有褪尽的毛发、口音和屁股上的青斑。
如同今天的我们一样,我们同为昨天的来者,又必将死于明天,而明天的新生之人就是我们的替代者,他们将代替我们进入遥远的未来,并享受未来的荣耀和磨难。循环往复的路程上,走着多少是非和恩怨、血泪和不死的眷恋。但人的幽灵并不能全部为人所看见,动物的幽灵也不能全为动物所看见。通灵者生活在偏僻的乡下,能望日的鸟自己飞翔在浩渺的蓝天。
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连诗人也是荒谬的。苏东坡的幽灵沉睡在月光之下,李白的幽灵游荡在酒肆和烟花柳巷之间;但更多诗人的幽灵开始变得厚颜无耻。它们奔跑在夜晚,它们开始拨弄是非、故作清高自大但却笑出一脸暧昧莫测之色;而那些用狐狸的柔情迷惑着后世子孙的幽灵,又受到了谁的指使和蛊惑?谁在其中用着李清照的忧伤和身体?谁在灯红酒绿的街头用着纳兰性德的富贵和灵感?夜猫子的心就是幽灵的心。月亮的脸就是幽灵的脸。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团,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告诉你:幽灵有空洞的身份,与一切未知的世界相等,但我依然无法用祈祷或赞美使幽灵出现在你面前。
幽灵用理性命名并在多维世界找到感性的化身,但我必须坚信它的存在,坚信它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这样我才能恰当地认识世界并对它充满神秘的信心;才能不断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崇敬生命的流逝也崇敬生命的诞生,崇敬真实的物质存在也崇敬无形的精神压力。现在我需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漫长的磨难和痛苦之中,谁在我们的心里注入了虚荣、残忍、妒忌、罪恶、智慧、诗意和爱情等众多幽灵的声音和身影?谁将在一个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接住我坠落的身体,并使我获得其中有限的安慰、寂静和提升?
二
雷声总是追着人走的。那么它最终追上了谁,这应该是一个秘密。
我可以避开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但我避不开雷声。雷声在高处,它能看见或一直追踪我的身影,连我的隐私和缺点都无法隐藏,我惧怕它的来临,它的滚动有不可阻挡之力,如同真理(真理总是来势汹汹)。一个恶人不服从于真理总要受到真理的惩罚,这是一定的。而雷声被堆积在一起,就是火焰,它在燃烧之前有爆炸的风险,并且让人无处躲避。现在它沉默,这更可怕。我们需要在一瞬间决定自己的选择。假如你看到我头顶上的黑气,你可以猜到我大脑里的恐惧此刻正如一片波涛翻滚,但这有意义吗?
一只苍蝇爬到雷上的结果和一个大力士爬到雷上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它)都将被震晕或被烧得粉身碎骨。祭坛上的通灵者和尘土中漂泊的生灵,不会比一个圣人更善于消遣自己;他不会以为思想在握就变得趾高气扬,他会装成患病的老虎藏身在一座山的背后,并把居住在闹市的隐士当成道德中的耻辱,并使水边徘徊的湿淋淋的幽灵,有了一身书卷之气。圣人一声大喝,就触痛小人的软肋;但圣人只对人间有用,而对雷则毫无用处。雷声滚过,大地颤栗,人类纷纷躲避。我用圣人的名义说:我们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必须在雷声里重估自己(即使我们为此而受到惩罚并付出代价,那又怎么样呢?)。
雩雷祈水,雰雷向雾,雯雷彩云,雱雷大雪,霜雷飞凇,霎雷细雨,霾雷生烟,霭雷聚气,霪雷洪涝,霹雳追魂……田野上多了一场大雨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大雨下过七天七夜就是一场阴谋。一个村庄遇到干旱并不是干旱,一万个村庄遇到的干旱将祸及三年幸福之地,桃花源将被废弃,绿洲将被改变,连天堂也将荒芜一片。酒坊里的酒瓮必须被打碎,打谷场上的谷子要被最后翻动一次;一百年前的亡者有太多的思乡之情,也有太多的隐私和雷打的烙印没有了被抚慰的机会。春天有众多的鸟想飞离大地,也有太多的人想把铁犁插入土里。惊蛰之后,雷声把小雨、雾气、云霓、晴空、彩霞、烟岚、洪水、霜冻、孢子、乳胚、冰雹、凶器、陨石、光芒和种子……以及一切已知和未知的奥义,都降落给你。
在疾病不来的地方,幸福之人也不能复生;在鳄鱼重返河汊的地方,猴子并非为了捞出月亮才俯身深渊;灰鹤也并非为了饥饿才啄掉河马唇边的臭泥,而大海则必须在远方等着迎接消失在河水里的亡灵。雷声在此时并不是喝彩,而是在时间里轮番转换着不同的面孔,假装拎着屠刀,并让明亮的刀锋发出思想家的叫声。一个想凿穿大地的人是危险而又愚蠢的,而一个炼石补天的人的功劳。肯定超过一个炼丹之人的功劳。一个怀抱炸弹并以炸弹为正义的人叫雷公,一个爱上怀抱炸弹者并追随正义的人叫电母。
水雷屯、泽雷随、风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颐、地雷复、震为雷……水雷带来热水、雪花和酒曲;泽雷带来泉眼、湖泊和大海;风雷带来呼啸和流动的身影;天雷带来预兆、转世的哲人和宗教中的祥云;火雷烧毁森林、神殿和点燃最高的山顶;山雷改变大地和风声;地雷带来八十万吨磷肥和布谷的消息;震雷用地震和海啸收走梦中的城市和乡村……这样看来,我们的生存越强大,我们的内心就越可怜;我们今天生活得越天衣无缝,我们的未来就越有缺陷。如同我们把理想和心愿安排在天使和恶灵之间,或者我们本身就是天使和恶灵,我们有暴跳如雷的坏脾气,我们有惹是生非的恶行。历史里尽是一些自高自大、执迷不悟的人,现在我必须问自己:是迷信一个脑袋顶雷的人,還是对一个面孔黝黑空话连篇的圣贤发出疑问?
我听见雷声在远处轰响,我不知道它确切来自哪里,地狱、天堂?或废弃的城市和荒凉的乡村之间?黑暗的深渊被照亮。悬崖和老虎被照亮。而我在其中露出一张鬼魂的脸,我有窃贼的心事和酋长的宏愿,但藏在我心里的闪电却一声不响。我只把一堆石头放在山顶,只把两个打铁人的炉火放在云端,把灯熄灭,把思想召回,把耳朵塞上鸡毛,然后等着身体里的骨头嗤的一声被一把锤子砸断。我的等待不能为你所测知,我在等待中承认回忆之苦,否认再生之欢,虽然时间可以把许多人的命运劫走,但却不能把我的幻想打断;当我在梦中被一匹快马带走,我发现有一千匹马在身后滚滚而来,它们举着的,是我内心里全部的雷鸣和闪电。
三
我心里的世界就是一座空房子,它空空如也,像一个嗡嗡响的空剧场。
幽暗的四壁,空旷的心脏,诡谲的歌喉是你的隐身之地。冰冷的城堡,石头的四壁,寂静的天穹被抽空,梦把沉睡者带上了黑暗的塔顶,留下一排空椅子指认你的身份,留下十排空椅子接受一朵乌云的烟雾,留下更多的空椅子承接无声的脚步。而你对此一无所识,你甚至不能从它的身上认出你自己的倒影。
一座木笼仍然有森林的雄心;而一堆被削平的石头堆放在一起,既有山峰的影子也有光明的苦闷。这时你从暗中走出来,你神秘的心事未曾暴露。你有无可奈何的气质和眼神。你信心全无。你壮志未酬。你无法说出的梦想要依赖舞台和舌头来虚构,为此你的命运等于虚无。一个富人的优雅成为社会典范,一个穷人的寒酸使道德蒙羞;一个好人的笑容挂在城头,一个坏人的泪水受到人生的嘲弄。一群影子的阴谋得逞之时,我头上的屋顶就塌了下来。当这群影子再次被塑造成英雄,我的头颅里出现一片晴空,而我的心却成了生活的陷阱。
我无法说出我的悲观和愤怒。我的嘴巴被堵住,我无法喊叫或痛哭。一个人在黑暗中喃喃自语,而另一个喃喃自语的人却被他所利用。他说着那些崭新的词汇,而那些词汇是一种破坏和引诱。我其实一句也不明白它的含义,但我却必须要装作已经被它感动。那个喃喃自语的人为此越过我的头顶而升高,他在各个角落里飞翔,他有魔鬼的光彩,但他是个囚徒。他说真理在握,他说生活漏洞百出;他說仇恨和奢侈的善意一刻也不能消失;他说我们幸福的生活一定要结束,而更大的幸福将被用来阻住灾难和未来。他的话让我迷惑和震惊。
一个傻子坐在舞台中央陷入回忆。两个面目模糊的病人在他身旁探讨社会生活的技巧,他们甚至谈到了命运。更多的精神狂人爬到神像之上,向天堂乞求人生的果实。只有一个思想家躲在阴影里一声不响,其实他是一个早夭者的遗腹子、城里的流浪儿、魔鬼的奴仆,他偶尔露出鬼魂一样苍白的面庞,像小偷的窃笑闪着诡异的光。狂人们用“钱币”这个词买通一所监狱,让更多的不义之人越过高墙。而一个心无未来的人则死于内心的忧伤和绝望。一个或许能预见到未来的人将成为明天的主人。
两个拳击手在对决,其实是一个仇恨生活的人反复把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打倒在地上;或者两个同样热爱生活的人因对生活的热爱而互相撕咬在一起,他们想要独占生活的秘密和爱情的广场?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一个人在大笑,另一个人在痛哭;当灯光再次暗下来,黑暗也不能减弱他们过去的疯狂。一个种植园主人心里有辽阔的秋天和忧郁,有一颗被钢铁大王所讥笑的脆弱的心脏,有一个农民愚蠢的善意和狡滑的沉默。
一群稀有的种鱼撞死在被截流的堤坝上,而堤坝继续增高,像一片密集的帆影;突然一个影子向它吹了一口气,帆影像风筝一样飘走了,它消失得像我们大家模糊的理想。空洞的舞台像盗贼的心灵一样空旷,而忧伤像梦一样缓慢。
浑浊的月亮升上来,每一个卑微的生灵都沐浴着它寒冷的光辉;她孤独的寓意和美丽是无力的,只能由冤魂去热爱和赞美。一个人用自己的名字在大声歌唱,一个人用鬼魂的喉咙在无声地叹息。对一个走在路上的人来说,朝阳是个安慰,夕阳是个惩罚。
关于现在,我一塌糊涂;关于未来,我一无所知。这世界宁静而危险,如同幽灵心中的童话,幸福的人依然背井离乡,而不幸福的人却要坚持着活在繁华的世上。雪花,纸片,神秘的天光,十双手拉不住夜行人,一群宿鸟在梦中飞翔。穿针引线的人把许多人捆绑在一起,推着他们的影子在睡梦中流浪;此时,有家可归的人比无家可归的人更多、更伤心和惆怅。
一个坐着葫芦周游世界的人有着隐士的面庞;一个带着金银和驼队穿越大地的人,渴死在白云之上。一个财大气粗的人精明得像个殖民者,他喜欢金钱和森林,也喜欢美女和在沙滩上晒太阳,他的慈善和阴谋使他声名远扬,最后他成了一个生活在地洞中的人,他背着钱袋子在黑夜里到处躲藏。一个顺着原路走回昨天的人,发现昨天已经成了一片衰败的墓地,而生活在昨天的人都已经像惊慌的游魂或漏网之鱼,他们在破碎的风中四处飘荡。他为此大声哭泣,他为此深信连时间也会死亡。
一群沉溺在抑郁中的人在昏睡。他们甜蜜的梦乡吸引了更多的人,但一个靠灵魂生活的人却对此不屑一顾;靠灵魂生活的人是清风中的月光,他提着自己的身影一个人在飞翔。而我们被命运拖累,我们追不上他的飞翔。我们只能仰望他的光,与风声融合,与大地平等,保持一个普通人的骄傲和本性,接受一切必须来到的责任和义务,接受一切惩罚和鼓励。
接受出生的时刻,这隆重而不公的仪式,就像接受死亡一样——死亡是人类最平等的荣誉;人总归是平等的。死亡有令人惊叹的一致性,它在摧毁生命的同时建筑了另一种公正和美。死亡不需要过渡,它一下子就来了,像梦中一种甜蜜的力量,在疾病和磨难中保持温柔的尊严,在正义和真理之间保持仁慈和宽恕;为此我们坚持做一个普通人并需要一个普通人的全部幸福和柔情。一颗安静的内心可以放下世界上所有幸福的时光。
陨石的降落并不代表神意或恰当的惩罚,而恶依然存在,就像善依然努力生长并成为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一样。人永远陷于内心隐秘的欢愉和渴求之中,服从真理、荣誉还是时间的享乐?
这需要一个角色出场。而我听见的掌声突然使一片屋顶摇晃起来。
四
月亮和思念没有关系。月亮是天上一桌没有人享受的晚餐。举着空杯的人杯里注满露水,饥饿的人面无表情地站在地上,嘟嚷着,怨恨着,弹跳着,像个木偶人被提在线上。
我有足够的耐性否认月亮。我有足够的仇恨,推倒半夜里漏风的茅草房。我的耐性连我自己都惊讶,我的耐性是魔力的深渊。
一座孤岛在今夜变得像浮萍一样,而月亮为它在黑暗中的移动提供了光亮。
月亮是荒野中一座冰冻的池塘。临渊照影,我们内心疑惑,浅草遮不住狐狸的柔情,深水同样淹死醉醺醺的思想家,只有负心人的尸体漂浮在细小的波浪上。
失足者、溺水者、殉情者,其中必定也有陈世美的同乡;但失足者绝不是粗心大意没心没肺,而殉情人一定是因为思念和焦虑才痛断肝肠。
乌鸦的叫声激起幽灵的泪水和歌唱,也激落了我脸上的一层白霜。
月亮是一个荒谬的酒瓮。一个荒唐的诗人,和众多不知荒唐为何物的诗人,淹死在它的中央。月亮因此而出产好酒,那么多芬芳的灵魂攀附在桂花树上,衣袂飘飘,南风鼓荡。穿过这面镜子,有多少蝙蝠和兔子的身体摔死在月亮上,有多少沸腾的心愿和悲悯的目光,折断在虚幻的路上,又有多少异乡的鬼魂飘荡在空中,并不断长出新的翅膀?
而月亮首先看见这一切,她什么也不说,月亮像一个巨大的窟窿,她吸进了嫦娥、吴刚,吸进了李白、苏东坡,吸进了古代书生和现代怨女,吸进儒士也吸进流氓,最后她把我也吸了进去,我赤身裸体被绑在她冰冷的宫墙上。月亮在看见我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由酒瓮变成了染缸。
而月亮绝不是一个当垆的好女人,她不抵卓文君的一个指甲。连黑格尔也说:只有阳光才能把灵魂的声音敲响!
月亮是过去的梦境,她时过境迁;月亮是未来的乌有之乡,她一团虚幻。所以你计算一下距离吧,你估计一下高度吧,你拼尽全力跳高也白费,你拼尽全力追赶,也无法握住一束月光。
她就在那里,她高高在上。她被思念所占有,也必将为思念而消亡。她被时间所覆盖,被空间所供养,被天堂所接纳,被人间所赞美和永久仰望。而我的文字只是一副眼镜,它让你在黑夜里,看到月亮的另一面;但你必须挤出心中的噩梦,才能看见她的裂缝和其中漏出的点點光亮。
月亮是一个废弃的祭坛。命运里的赶路人,偶尔回头对她看上一眼,就大失所望;只有哭瞎眼的新娘,才敢对着她久久凝望。这是凡人的生活逻辑,凡人都被累死在神话和谎言的长途中,只有云中的妖精们在咧嘴大笑,并顺手拣食风中的月饼,飘渺的线香、甜蜜的美酒;它们挥舞长袖,使月宫尘埃落地,使空中鬼火飘荡,让东方的嫦娥与西方的阿尔忒弥斯偶然相遇。
一个生锈车轮的转动之声是刺耳的,一口枯井的黑暗之光是令人眩晕的。乘着月色赶回家乡的人,在大哭三声之后,猝死在村口;而诅咒月亮的伤心之人,却突然看到天空寒风吹拂的宫阙之间,一股神秘的轻烟正袅袅而上。
一棵枯树被斧子砍倒。一群鸽子沿着树枝,飞入现实和梦乡之间。一个落魄的书生,为此抬起头,为此一声不响。而我在此时,写下“月亮”两个字,我的脸上一片泪光!
五
我看见过捕鼠者的结局,但一只被捕杀的老鼠,我曾经有意回避。
一只老鼠在城里遭受电刑。一百只老鼠,在草原上迎风怀孕。城里的老鼠受刑不过,全部变节,虽然被捕鼠者所讥笑,但却被流浪猫视为同盟。而草原上的老鼠却团结一致,试图在沙尘暴中举行一场暴动,它们共同推动一片巨大的沙漠做后盾,而它们的头顶上正有一团乌云在上升。这是哪个时代的乌云?它那么黑,那么安静,像一团绝望的帆影!
一只老鼠在人群里穿梭。它不但学会了说脏话,还学会了风情万种;这是一只有文化的老鼠,这是一只儒雅到虚伪的老鼠。它和猫站在一起,与人类共同分食面包和瘦肉。它与城里人共同反对肮脏的空气和嘈杂的噪音,反对淹进洞里的油漆和自来水。而冲下山顶涌到高速公路上的老鼠,什么也无暇顾及,它们为饥饿和风声所追赶,为命运所左右,只有亡命地奔跑着,追上运粮车,即使被碾死在车轮之下又有什么呢?只要有一线机会,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只,都可能成为天下鼠辈中的饱死鬼和富翁。
我今天撞上的老鼠,是一群无知无畏的老鼠。它们在草原上留下了一群吱吱叫的子孙,留下了一群晕头转向的吸血鬼。一只老鼠为一粒粮食常常感到迷茫;一只老鼠为吃饱肚子,常常从天黑奔跑到天亮。但一只掉进米缸的老鼠,却无疑是自掘坟墓,即使它吃尽了全部米粒,也一样要被自己的粪便所埋葬。
而仓鼠、灰鼠、白鼠、松鼠、鼹鼠和黄鼠们,正在进入黑暗的冬眠,即使它们肚子里颗粒皆无、噩梦连连,也必须遵从祖先的遗训,在昏迷中等到惊蛰的一声雷鸣。否则所有的公鼠将不再发情,母鼠将不再怀孕;一个萧瑟的鼠国,将被蝙蝠和毒蛇所占据。而我看见一只鼠王被关进风箱,它上蹿下跳毫无反悔之意。它咬断自己的尾巴,向自己的影子狠命抽打;它拒绝被用作试验品,拒绝被划开肚皮,暴露出一个王朝衰败的密码,但它无法拒绝寿限的突然来临。在死亡之前我猜测它会喊出一句什么,肯定的,但至今我也没听见它喊出的话。
六
在一所空房子里读书,而不被鬼魂打扰;在一座破庙里睡觉,而不被狐狸精纠缠。在一个井台上照镜子,除了看到自己,你还看到了什么?敢于一个人穿过黑夜里鬼火飘荡的墓地,而不脚步凌乱;但在迷茫的生活里,我多么需要一种心地无私的智慧和胆量。
大树不光为一个人避雨,还为另一个人乘凉;太阳普照万物,也烧瞎偷窥者的双眼;樵夫上山,渔民下海,胆怯的人都隐身于草莽;只有无知者,才敢对着空旷的大地大喊一声,而回声却像鬼魂一样紧紧把他缠住。
福生舍亲,祸起萧墙。而收紧一颗善良的心,却需要多少温暖的力量!门里的土龙,即使把你绊倒在地摔个鼻青脸肿,也不能用铁锹把它铲平;晴天霹雳是神明在追赶恶人,有时也会把好人误杀在闪电之下。
居住在印度深山里的巴干达人,早就知道:人只有不高声说话,才能瞒过响尾蛇和鹰的灵魂。而我生来胆小,小时候奶奶曾告诉我:举头三尺有神灵!我今天能平安长大,这除了我身体中固有的神秘之力,还有谁的帮助和抚养?
在麻雀的词典里,也许从来就没有“人”这个词,有的也许是更多凶恶的猛兽,它们天天在大地上,傲慢地呼喊和游荡,区别于鸟的,只是因为它们推动着翅膀,才增加了沉重的思想。农民按着谁的布置在大地上四季耕耘?老皇帝一个人躲在深山里为子孙后代,修补着漏雨的宫廷;而巫师却骑着一条大蛇,在河流上飞行,我能看到的,只是她身后彗星一样熄灭的光芒。
所有应该出现的,都会在我的生活里留下身影;所有必须隐藏的,都会在我的眼前慢慢消失。就像我自己,我的最后一次出现,也必定是在告诉你 :我也要把自己彻底隐藏!
敢于在雷雨里穿行的人,必有神奇之力;而半夜里的敲门者,一定是错过了命运的好时光,所以他要被怀疑和阻拦。
我忍不住要大声喊叫,虽然我内心正在流下泪水,而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呢?一个我和我,在体内握手言和;另一个我和我,又在体外互相攻讦。其实我知道,此时还有一个我正留在夜里做梦;而另一个我,正在写下这个混乱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