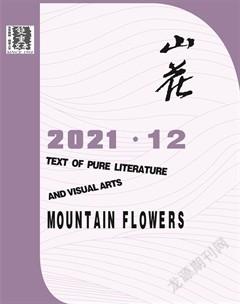潜流
唐简
一
凌晨两点,从那个梦里咳醒,一头的汗。抹抹汗,伸手去摸,没摸到什么,入手处空落落的,没摸着利兹。这才记起妞儿上个月搬到了新男友家。男人一年答应给她多少钱,学费加生活费,5万?不想也罢。总是梦多,睡不踏实,好像有三年了?医生说要吃药。吃了半颗安眠药,感觉又做梦了。
一场暴风雪后,白色宝马埋在了雪下,起床一看,街上的雪被铲雪车推到路边,在车的左侧筑了道矮墙,车门被封得死死的,根本打不开。车的一头一尾又拜自私的车主所赐,塞了老高两堆他们刨过来的雪。天很冷,雪下结了冰,硬邦邦的,手里的硬塑料铲撼动不了。麻烦事。只好到大楼地下一层找楼管路易斯。
也许是公牛与公牛之间的敌意,二公牛相对,即便是敷衍一声“你好”,他也扬起鹰钩鼻,撇撇看似有裂痕的嘴角——自打见他第一面起,就厌恶他。一直不把厭恶放在脸上,仅在肚里做文章,但厌恶像只跳蚤,近距离一接触,就不声不响地叮咬了对方,所以他知道。
路易斯不在。抓了他放在角落的长木柄铁锹回到街上,先铲掉左前门处的雪,打开门,启动了引擎和前后窗的热风。看情形,怕是得半个小时,没别的办法,干吧,无奈卯足了劲,大刀阔斧,狠铲猛砸,把铁锹摔打得像是在对付狂躁作死的野狗。野狗嗷嗷叫,像利兹呜呜地哭,脸丑得变了形,毫无俏丽可言,且面目可憎。不一会儿,他大汗淋漓,有股听到妞儿求饶的快感,“嗷”,“嗷”,她发出两声低低的哀嚎。
就在那时,“咔”的一下,木柄齐根而断。恰巧路易斯从旁经过,一眼认出了他的铁锹——头和柄分家的铁锹。正要解释,对方已拉长马脸,眼神冷冰冰,口气居高临下:“你拿了我的铁锹?你怎么有权利不打招呼?还弄断了!你知不知道我的工作很繁重?你怎么可以给我添麻烦!”
遂眯起眼看他。真冷啊,空气都冻僵了,四周一片空白似的寂静,空空荡荡,眼见他逐渐从公牛蔫巴成一只喋喋不休讨人嫌的斗鸡,嘴壳兀自机械地吧嗒个不住。呱唧呱唧,斗鸡埋怨开了,冬天除雪,秋天扫落叶辛苦之极,清洁大楼费劲得不得了,这里那里修缮也不容易,到了新年,也不是家家都打赏他小费。呱唧呱唧,斗鸡叫嚣着,“我有劳动工会撑腰,你能怎么样!”一年八九万,医保、养老金一样不少,住宿免费,斗鸡还甚感委屈。
是的,谁又能拿他怎么样?拿蠢透了的合作公寓管理规定怎么样?年年上涨的管理费,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供养他和他的两个助手一辈子,除非他犯下蠢到了家的错,否则休想干掉他,干掉一个不知感恩的家伙,一只斗鸡!
斗鸡的嘴壳越吧嗒越快,越吧嗒越响,本怀了一丝歉意,现在,歉意早已被火速升温的烦乱取代了,斗鸡一副讨打的样子,显然是在邀请人给它脑袋上来个几下,它才会立刻停止聒噪。也许在那么想的同时,手中的木柄就自动飞过去,照准它的脑袋来了一下、两下、三下……
心里有个声音说,这不是真的,是梦!
但是,这却是真的,千真万确,而且就发生在两周以前。不过,无法确定如果事情再来一回,能否忍住不砸斗鸡的脑袋?想来想去,不得而知。好在法律是人性的,在诠释和执行上,与其说人性在处处未覆盖到的地方留下余地,不如说留下余地之处皆因人性所致。如今,人性的法律把这个袭击斗鸡自卫的人交给了律师,律师要他扮演这个角色,要他看心理医生,是的,医生,十点钟看医生,看一个女人。
老样子,七点后再也睡不着。冷,这个冬天雪可真多,又一场雪,比任何时候都大,风吹得浮浅无依的东西发出各种声响,纽约的冬天可以猛烈至此,除了冷还是冷,除了雪还是雪。这没什么不好,可也没什么好,冬天就是冬天,夏天就是夏天。有人搬走了,有人去看医生,有人去看德妮丝·雷恩。
出门前,仔细地刮了胡子,戴上新配的隐形眼镜。镜子里,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那,不过就是镜子成的虚像而已,他那张黝黑的方脸算得上英俊吧,算得上有吸引力,他和她就要见面了,他和她相遇将会是怎样的光景?
没开车,坐的地铁。坐地铁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想东想西,即非自得其乐,也自得其便。某天在网上搜索,竟发现了她。照片里的她三十多岁,看着亲切,瞧她的眼睛,灰蓝灰蓝的,亮,清澈,毫不晦暗,一点儿也不冷。她心里应该是有温度的。她肯定是一个合适的金发美女,而且还是一个不凡的医生。医生嘛,就该是个女人,还该是漂亮的女人。
嗯,她的工作室,或者诊所,也漂漂亮亮,起码干净、舒适,淡蓝的墙,米色沙发和浅褐色百叶窗,叶片的缝隙间漏进来缕缕雪光,地上一道浅灰,一道肉色,一道紫灰,一道熟褐,坐在沙发上等她,有什么在条纹间咚咚跳。忐忑。
二
等了二十分钟,门开了,她走进来,光彩照人,比照片上的还要亲切……
见到她了。她就在眼前。
“郭先生,你好!”她说,远远就伸出了手。白皙的没有血色的手,想起了那个梦。那个梦里的那只手。但她的手看样子是多么灵巧,也许是激情的,也许善于传播理解和同情,也许它的主人与别人不同。它在两个人的房间里无声地穿行,空气轻柔地从它的指间划过,她的手又像是逡巡在温柔的水中,正越过一道道条纹,一点点靠近。奇妙的令人兴奋的感觉。忍不住盯着她的手看,直到它到了跟前。握住它的体验会是怎样的呢?它的温度、力度如何?握一秒,还是两秒,还是更久?终于握了握它,也不知道是几秒。它正如想象的,一点儿也没令人失望,它符合全部的预期。但它的主人随即挤了泡沫洁手液,在手上揉搓,同其他的医生并无区别。为什么她闻不到他手上橘子味洗手液的香气?他坐下来之前,才在卫生间洗了两遍手!这一下,他咳起来,咳得全身颤抖,脸红了吧。她又伸出手,只是很快又缩了回去,连声问你怎么了,有没有生病。嗯,她的确还是与众不同,有点像母亲和丽莎。好吧,没事,没有关系,不要紧的。德妮丝·雷恩,毕竟是德妮丝·雷恩。
她递过来一杯水,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啊,你当然可以!她蓝灰色的眼睛在镜片后温情而闪亮,贴身的黑色套装和白色低领口衬衣被挤擦得发出阵阵温热。肯定的,她肯定可以做点儿什么,为他,当然也为角色做点儿什么。那袭击斗鸡自卫的角色正站在角落里召唤。角色说:“我不知怎么开头。”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对方回答。
真的?真的吗?在人的梦想和现实中间有一段空间,借用一句纪伯伦·哈利勒的诗,“只能靠他的热望来通过”。热望。
“我真不知怎么说。为什么你不问我?”角色以退为进。
“好吧。”她说,“你的基本情况这里写着:郭明,32岁,单身,网络游戏设计师,住在城堡村。”
“对。”
“工作压力大吗?”
“还好。公司同意我有时在家工作。”
“喜欢你的工作吗?”
“还好。”
“喜欢城堡村吗?”
“嗯,对也不对。我睡不好觉。”
“说来听听,怎么对也不对?为什么睡不好觉?”
在一串干巴巴的问与答之后,角色发出了种种暗示。是时候了。他深吸一口氣,试着去深思。每个空间的最深处均有潜流在冲击神经,像地表下的水循隙而来,昼夜不断,流淌不息。累,疲累。瞧,有一头动弹不得的公牛,地上的四个深洞陷住了它的腿,一块钻了四个洞的木板横亘在牛腹和坑洞之间,四周围满虐食者,屠夫举起尖刀,一下一下蛮横地切割,公牛一声一声惨烈地嘶鸣……
这很不好!不,难道就这样服服帖帖地被医生切割?律师怎么说的,不管医生问什么,你都得去回忆,回忆,并说出实情。
实情就是,自己对被捕的那一幕仍心有余悸:路易斯前额的那道伤口像条血色的蜈蚣,鲜血一滴滴坠落在雪地。咳嗽,咳个不住,感觉额头的青筋在皮肤下发胀和鼓凸。到底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吗?没有,但是警察来了,两个腰里别着枪的警察,一个白人,一个拉丁裔,凶神恶煞……无处逃遁,无路可走,时间凝住了,却看见丽莎突然从街口跑来,金色的长发被风吹得凌乱,仿佛听见她喊:“明,抓住我的手!”多年前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两个人紧紧拉着手,迈开腿往前奔去,像一阵风似地朝中学门口的母亲奔去,把几个追赶的校园恶霸甩在身后。母亲神色紧张,不停地喊着:“快呀,孩子们,快!”她伸出双臂,无比焦急也无比慈爱地等待着。就要碰到母亲的手了,就要碰到了。终于,在温暖、喜人的日头下,摔倒在地——被警察掀倒在地。丽莎不见了,母亲一脸揪心的痛苦,空中突然传来父亲的一声冷笑,那么冷,那么刺耳。有一样冰冷、坚硬的东西锁住了双手。是的,手铐!
“你怎么了,郭先生?”德妮丝·雷恩的声音打断了回忆。静默,暗流涌动。角色眼睛紧闭,内心无比沮丧。没有光,没有花香,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不再重要,不重要了。整个世界充斥着防腐剂的味道,有一只巨大的怪兽,把周遭的物事统统吞进肚里,然后吐出一团黑雾,那个梦就从黑暗中跃出,迅速地弥漫和膨胀,同现实发生了交汇:S城,一个人,四周都是水,水的颜色是黑的。有一只手破水而出,像是在吸引人注意,角色有点紧张,又有点好奇,但是那只手不断地灵巧地晃动,遂踏水而去,拉住那手。一个陌生女人从水里冒出来,她面色苍白,眼睛红肿,嗫嚅着要说什么。惊骇!等她完全从水中升起,样貌变得再生动不过,竟然是死去的母亲!“小明,”母亲的嘴唇终于张开来,声音微弱得像在叹息,“去把你爸叫来!他在哪?去叫他!”她飘过来,伸出手,充满爱怜的,轻轻的,无比温柔的。他迎上前,心里一阵温暖一阵愧疚,眼里有泪流出。她说:“傻儿子,妈妈知道,妈妈知道!”他泪眼模糊,一句话也说不出,母子手拉手在水面上滑行,有风吹来,黑水被吹得哗哗响,她白色的长袍被风撩开,露出浮肿而灰暗的身体。防腐剂的味道里夹杂着一丝腐臭。他脚下前行不止,却闻到腐臭味越来越浓,她正在变样,正在残忍地失去人形。他怕她变了,闭眼不敢再看。待睁开眼,她的身体变成了一具骷髅,头在慢慢地转动,带着躯体越退越远。不论怎么喊她,怎么追她皆无济于事,他的喉咙被硬块堵着,两腿被什么牢牢拖住,胸口压抑、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咳嗽,直咳到醒来。
角色的确是在咳嗽,咳个不停。德妮丝·雷恩塞给他几张纸巾,似乎伸出手,轻拍了拍他的背。
“你不舒服吗?要不要休息一下?”她问。“我会一直在这里。我会帮助你。”她补充道。
胜任不了这个角色!为什么不能是平日那个郭明,将那些梦和影像分隔在它们应该被闭锁的空间!但德妮丝·雷恩的脸多么柔美,那是一张带有关切和母性的脸,始终是和利兹不同的脸,长着这张脸的人应该不至于背叛。如果有人能提供有力的帮助,如果存在可以与之建立某种可靠关系的人,这个人也许就是德妮丝·雷恩。到目前而言,她难道不是基本上印证了先前的预想?她难道不是友善、温和之极?对,德妮丝就是德妮丝,她的善意应该得到回应。微笑吧,露出牙齿,露出经过矫正并且光洁的牙。她注意到了,因为她也笑了:“你想躺下来吗?为什么你不躺下呢?”
“靠着这个枕头,”她命令道,“我数一二三四五,你试着慢慢吸气和吐气,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两三分钟后,竟像是被催眠了。感觉很好,房间里没别人。她就在身旁。闻得到她身上的味道。迷迷糊糊地,记不清和她说了些什么,那些蠢动的时间的游丝再一次蛰伏,一直到诊疗结束。
三
雪已经停了,天空竟有放晴的迹象。回到城堡村,信步到花园的小径走走。小径的雪显然已被清理过了。路易斯在花坛那边忙着什么,不得不按法官签署的该死的人身限制令,避开他,同他保持50英尺的距离。但有阳光,看得到冷冽空气中的颗粒浮在空中,无人的花园是好的,阳光的丝丝温热使人受益,鼻子边若有若无的,是德尼丝的气息。很庆幸去看了她。
被捕后,很快保释。提审已过,上庭时间定在三个月以后。检控官这样起诉:恶意殴打受害者及拒捕。实际的情形是,警察来的时候,丽莎和母亲的出现是那么真实,所以才情不自禁地去追赶她们,回到过去。那时常常和丽莎手牵手地奔跑,从操场一路跑到中学门口,跑到母亲身边。记得丽莎的金发是有幽香的,隐隐若现的樱草的香味。喜欢贴近她。当她的发丝拂面而过,一股热力就从心中升起。是的,很奇妙,既新奇又令人担忧。也记得丽莎的脸,她蓝灰色的眼睛纯净如海水,她长大的模样应该是像德尼丝。那时的天空湛蓝极了,夏日里蜻蜓们到处乱飞,但丽莎父亲的公司把他调到×城,她不得不跟父母搬去了那里。
是的,×城,金利之地。那里有个男人被称作父亲。他从那里发出冷笑,他冰冷的眼神直抵S城——母子曾生活的地方,也是母亲去世的地方。母亲和儿子的家就是母亲和儿子的家,只是母子的。每天放学回家,儿子进厨房吃母亲备好的水果。儿子每天也吃鸡蛋,喝母亲煲的汤。儿子吃,母亲看。空气中,只闻得到母亲中药的气味,分辨不出食物的香气。母亲一直病着,她的脸色慢慢变得又黑又黄,但她的五官依然清秀。母亲给儿子买他喜欢的东西,她自己的衣服却总是旧的。她不让儿子洗菜或洗碗,他手上的皮肤比女人的还要细腻。十多年的时间里——从儿子记事起,母子的家里偶尔飘进父亲的烟味。当他坐在饭桌对面看儿子,他的神色阴晴不定,即便挤出笑容,也伴随尴尬。儿子不笑,儿子有时同他对看,眯起眼看他在面前千变万化:毒蛇的冷漠、狐狸的狡诈、黑熊的贪婪……不知道他是什么,看到最后,儿子额头的青筋往往发胀,心里升腾起莫名的烦躁。他的烟味会持续几天,他一离开,立即便被中药味掩没。夜晚和清晨,母亲喜欢打开窗户,在窗边倚望。听不到父亲和他女人来自×城的笑声,也许他们的浪笑母亲听得见。母亲的眼底蓄着忧伤。儿子最终靠奖学金留学了;母亲最终在三年前患了肺癌。
坐在城堡村的单居室里,咳嗽,没完没了。后来应该是跟德尼丝谈到了那个梦,那个关于母亲的梦。依然听得见母亲微弱的呼吸。她就躺在那,在病床上,嘴巴和鼻子被氧气罩盖住,左手手背打着吊针。氧气罩上端是一根半透明的软管,软管穿过病床垂到地面,与几米外的氧气瓶相连。灰色、笨重的金属瓶立在地上,里面的气体使细长的软管有了生息。母亲的胸部在白色的被子下一起一伏,一丝丝的氧气正流进她的体内。那一刻,不敢拉她的右手——毫无血色的手,可以活动的空有自由的手,但还是握住了它,握住它说:“妈妈,我来了!”她慢慢睁开眼,眼里满是笑意。不敢同她对看,不敢。只好低下头跪在床边,泪流满面……
有谁愿意伸过来她的手?德尼丝,可愿伸过来你的手?母亲的容颜和朝气就是那样被病痛夺走了,她像断水的植物,在垂死之时衰老展露无遗。母亲不在意那些肤浅的东西,但它们和她的生命自始至终不可分割,在它们被抽离的瞬间,公牛被推向了遭切割的境地。
突然,母亲气喘吁吁,急切地说:“小明,是妈妈不好!”不知她哪来的力气扯下氧气罩。痛,心里惊痛。想立即给她戴上氧气罩,她说:“让我说完!妈妈对不起你,你这些年寄的钱都用光了,没能给你留下。你是不是借钱了?”“怎么会!”当然不可能,绝对没有。即便有,也不能让她知道。
忘不了。无法忘记。如果还有谁能明白,也许就是德尼丝。
等,飘忽的夜,来来去去的风。等德尼丝。
四
再见面时,她还是远远就伸出手。手在孤独的海里穿行,抵达彼岸,握住一只无助的手。
“这一次,郭先生,让我们谈谈你的母亲。”她的声音温暖而柔软,如何能抵抗?也不想抵抗。好,自然好,但她为何不喊“明”?
“你可以喊我‘明’吗?”
她似乎一愣: “我認为你对你母亲的死感到内疚。我需要问你一些会使你痛苦的问题,可以吗?”
“嗯。”
“好吧,明。”她笑了,好看。她有一张姣好的脸。一张悲悯的脸。
“好的。”
她开始问:“明,你母亲哪年去世的?她得的什么病?”
“三年前,肺癌。”
“真抱歉!是你照顾她的?”
“是。”
“你父亲呢?”
“他不在。”
“他在哪?”
在×城,和他的女人在一起。母亲让儿子去找他。她不是真的要儿子去找他。她拉着儿子的手,目光闪乱,吃力地呓语着说老郭,老郭你来了。一个多月里,母亲有几次神志不清。药物损害她的身体,疼痛损伤她的心智。白天不是白天,黑夜不是黑夜,母亲不再是她自己。一次次同她握手的,是死亡本身。死一次已足够,母亲却遭受极刑,死过去又活过来。每天,每一天,心向泥土靠得更近,无法解脱。
“明,你父亲呢?”德尼丝又问。
既不想抗拒,自然该和盘托出,也该把一切告诉她了。毕竟一份关系需要有人开始。也许可以得到她的允许拉她的手?
没办法对母亲说不,还是为她去了一趟×城。那个被称作“父亲”的男人打开保险柜,取出三叠纸币扔到桌上,他说,“哼,你的来意我懂,你把钱拿去,告诉你妈我祝福她。”他终究不愿看望母亲,他的女人在客厅等着他。客厅角落的大花瓶看起来足够重,事情以花瓶飞向他,他躲开了告终。
关于那个男人,就此画上了句号。母亲呢?医生给她换了固定的呼吸机,她再也无力扯脱。病房中,只有母亲和儿子,只有母子两个,就像从来就只有母子两个。他小的时候她为他做的,现在反过来,他为她做。她好的时候,儿子给她读书,给她讲故事。她不好的时候,儿子替她擦汗,握紧她的手。她看着儿子,专注地看他,眼里又是欢喜又是求恳。她的意思,他懂。为母亲做某件她想要做的事,是一份罪恶。是的,软管和氧气瓶延续着母亲的生命,把它们切断,砸碎,把它们彻底摧毁,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他高兴。他悲伤。他痛恨。他不敢想。他做梦。他做了好些奇怪的梦,梦见金属瓶里的氧气耗尽,梦见连接它的软管破裂。母子两个耗着,终于到了那个夜晚,那个给他噩梦的夜晚。
一周三四个晚上,他在医院陪床,白天抽空回家冲澡,吃东西。家里的中药味已淡了许多,有一天会完全消逝。以后呢?那晚,闻着母亲身上的怪味,他坐在母亲的病床边陪她,她睡着了,眉头紧皱。也许是过度疲倦,也许是眼睛花了,他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一张痛楚的脸,渴求解脱的脸。那张脸上,遍布的皱纹正在裂开,血淋淋的伤口正静静翻涌,一道接着一道。他就那样看着,像梦游一般,直到他的椅子压住那根软管,直到他顺势枕在床上睡去。半夜里,查夜的护士推醒他,连喊你妈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一个儿子就是那样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自己,自我,他没法在叙述中称自己“我”。他是杀人犯。
现在,有谁可以救他,救这个杀人犯?殡仪馆的工人给母亲的遗体抹了很多防腐剂。防腐剂的味道连同她的中药味最终消散殆尽。天地间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梦。但是德尼丝——那个长大的丽莎,她会明白吗?
那根软管的确是被椅子压住了。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想了三年,想不清楚。静寂,又感到了公牛的痛,来吧,切割吧,该来的终究会来,在两个人的房间里,等待命运对被告的裁决。
“明,”过了几秒钟,德尼丝终于开了口,“如果你睡着时移动了椅子,根本不能怪你。如果是睡着前移动的,你仔细想想,是不是无意中压住软管自己却不知道?另外,你母亲很可能是因为呼吸衰竭而死。”
德尼丝是在给被告“benefit of the doubt”(“假定我无过失”)。他的眼底开始潮润,她的确是像丽莎一样维护自己。但凶手还是凶手。
凶手喊道:“在护士推我,在我还没听清楚她的话之前,我已经知道母亲死了!”
“我这样问吧。你马上哭了吗?”
“应该是。”
“你马上就被悲伤填满了,还是悲伤中夹杂着很多混乱的情感?”
“我不知道。不知道。”
绝望,濒于狂乱,公牛气息奄奄。德尼丝,快,快啊!不要等,立刻说出来!
她像是听见了,眼睛一亮,提高了声音:“那么你的悲伤是压倒其他情感的。请仔细听我说,我可以判定,你母亲的死根本同你没关系。护士一推醒你,你就知道她死了,那不是你的认知,而是你心理本能的反应。你事先已有预期,预知你母亲会去世,所以你一被叫醒,这个预期就立即浮现。你明白了吗,明?”
真的吗?但愿是真的!脑子里嗡嗡响。可事实是,压住软管,割破软管,自己的确想过。罪恶的事不是自己干的,谁能断定,有何凭据?
“你必须相信我,明!”德尼丝坚定地说,“即使你想过要帮你母亲解脱,在那样的情形下,也并不是罪恶。由于复杂的根源,人们偶尔会有恶毒的想法。想没想过并不是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想过,没有做,但是发生了悲剧的事情,不等于你的想法造成了悲剧,两者没有关联。你懂了吗?听明白了吗?你要学着接受自己。明……”
明,明怎么了。她说“明”,喊着“明”的名字。难道这还不够吗?三年来,有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也许明白了我,是的,我。是“我”。这是一种不同的感受。我咳嗽起来,身体发抖,德尼丝轻拍着我的背。我又学会了哭。我开始痛哭,沉闷地抽搐似地哭。我捂着腹部,疼痛感正从那里向四处放射,从里面一个带血的肌体放射,流遍全身。是我允许一切负面的情感内化的,我就是允许这个肌体生长的人。但是现在,这个带血的肌体正从里面被生生地剥离。痛,感到了剥离的切肤之痛,也经历着失去和成长的撕裂的痛。痛像是毛毛虫,每一节肢体長期被撑开到最大限度,被针刺到每个细微的间隙,猛然间挣脱,万痛齐发。这个新我渐渐软倒在地,几乎晕厥。
“明,好些了吗?”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一两分钟,也许一个世纪,给我自由的人说。
冷天,大风,天色暗沉沉,远处的地道口透进了亮光。有人逆光而来,女人,女巫,还是德尼丝?
回家时在电梯里碰到了路易斯,我避开了。心里的跳蚤已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