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废柴”身上都住着一个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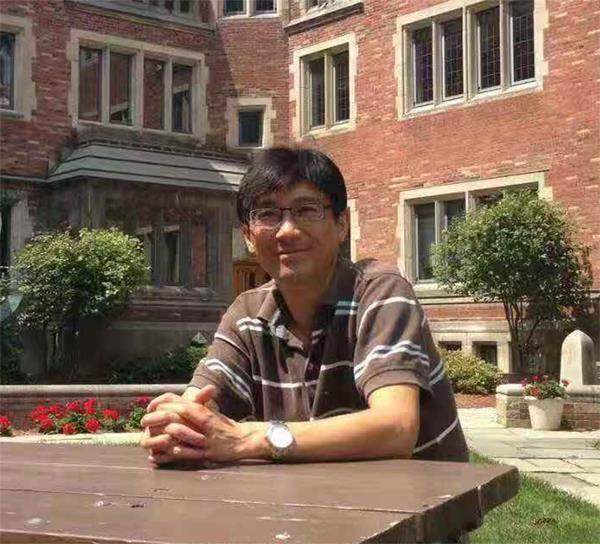
主持人: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史铁生评传》等多部专著。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励。
中国新文学史上,城市题材向来是一个热门的创作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城市作为一种地理空间和文化符号,多少都寄托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想象与价值诉求,而且它也是中国作家书写城乡对立和城市文明病,以及城与人之关系的专门领地。但由此生发繁衍,乃至蔚为大观的城市书写,却终因固化成了一种叙事范型而渐显落寞。而我们的问题是,在新世纪城市文明的发展日新月异之时,作家还能否以早年的城市书写书写城市?城市所隐喻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又将如何在新时代的作家笔下得以呈现?本期邀请的三位作者,虽然在关注的具体对象上各有侧重,但大都思考了这一问题。
李璐的文章,以几位青年作家为例,探討了城市书写的新样貌。在她看来,“80后”“90后”作家笔下的城市人物,“无论是试图以个体的力量概括和把握文化融合的规律,或者孜孜于对物质与爱欲的追求,或者对这一切采取审视和怀疑的态度,都充满了浓烈的英雄气质”。
裴亮的文章,认为一座城市的“时之气”与“土之力”,“往往就是城市文学书写的出发点与立脚点”。由此出发,他不仅梳理了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武汉书写,而且还认为在武汉作家笔下,“武汉也成为了他们文学书写的永恒底色。他们的武汉故事与武汉想象是历史的投影、现世的生活与个体的趣味的混合物”。
周卫彬的文章,谈的则是叶兆言的《南京传》,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关于南京的城市变迁史,同时也是精神史与心灵史”。在他看来,这部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文学在描写城市的时候,其实是“召唤那个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史相契合的家园,在辨识城市记忆的同时,也在踊跃唤起我们自身的经验”。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包含着与“新变”、“创造”有关的内容,包蕴着“现代”的观念。“城市文学”的提法并非“题材决定论”,而是由城市本身包含的巨量内容决定的。
中国现在的都市,呈现的面貌可能比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论述的1852—1870年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更加复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形态。个体的经济存在方式,以及种种文化因素、伦理、观念在人的精神和行动层面排列组合的可能,不亚于天文数字。
在观照众多“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时,我们往往能发现这样一个叙事者,他可能是第一人称“我”,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作者或叙事者。他像本雅明笔下城市中的“游荡者”一样,不受工作或刻板生活方式的约束,在城市的各阶层之间游走,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总结周围人与城市的存在状态。他的目光播洒在方方面面:文化、经济、爱情……本文标题所用的“废柴”一词,是说这样的叙事者与20世纪西方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力量并不足以超出周围环境、甚至低于周遭,但不约而同的是,他们都具有某种英雄气质,或者说,他们的身上,悄悄地住着浪漫主义时代的“英雄”。
中国有北、上、广、深等十余个特大城市,还有众多的二线城市和巨量的小城镇。这些地方,人口流动非常快,每个人携带着各自原初地方的观念、伦理、风土、习俗,在城市交汇了。这时便秉持着“1+1> 2”的原理,原本异质的文化因素在相遇后彼此吸收、生长,产生出更丰富的变体,更适应于时代、人群、环境的新变化。这是城市文化呈现出繁复生机的原因。
年轻的作家身处这样的环境,以敏锐的感触把握到变化,以理性的思索和张扬的想象力对神奇的一幕幕进行描摹和概括,写出了可称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文化因子直接就是架构小说的因素,是真正的主人公。其中,1982年生于沈阳,在广州读书、工作,近年又回到东北的“80后”作家金特,以及生于广西、在北京生活的陆源,他们的作品是“文化小说”中的佼佼者。
金特的小说《西伯利亚》从题目看,似乎说的是中国境外的那片荒原。其实,这里的“荒原”是一个隐喻,且是T·S·艾略特那首长诗《荒原》意义上的隐喻——这片荒原,是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的荒原;是古典主义达到最繁盛的时期,即将产生出大量新物的荒原。小说将主人公的居所设置在广州这座城市的“大城小爱白领公寓”、让他跟着身为房产中介的妹妹走家串户,都是作者富有深意的安排。于是,我们看到,在公寓的大堂里、在火锅店里,年轻人热烈地交换着彼此的人生经验和感悟。而“我”走街串户,先后接触了家庭主妇、拆迁户、教师、官员、商人……这是更年长的一群人。与前述年轻人相同的是,他们自我陈说,用观念的方式为自己和世界作着定义,努力将个体对世界的理解、分析、把握呈现出来,凸显出各自的存在状态、生存逻辑。他们的文化根柢、价值理念,涵盖了从中国传统的养生送死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意识的理路,一直到富有萨满色彩的老家“保家仙”的民间崇拜。这一个个人物开口说话,对自我和世界作充满激情的陈说,像莎士比亚戏剧里人物滔滔不绝的独白,多声部的复调让整部小说充满了繁复的思辨和咏叹。
同样致力于在小说中将不同的文化因素并置的,是陆源。陆源2015年发表的《省城双姝》和《按摩禅》,便已显出鲜明的文化小说的特点。小说的人物设置中,省城陋巷金丝巷、银丝巷中的普通平民是这样进入读者视野的:这里有“深研西洋哲学以致神经搭错线的老天才”,有“天生阴阳眼,通晓问米之术”的老姑娘,有“商务印书馆本省印刷部的校对员”,有“省城水厂的首批工人”,以及“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苗族青年”,甚至木匠刘哥四夜晚在城中漫步时,还遇到个“江边待渡的水妖捧着《西洋番国志》认真阅读”。
凡俗生活中的小人物被陆源纷纷加以“大禅师”、“水果王子”、“哲学家”、“云上轻骑兵”的令名,他们因作者赋予的文化意味而绽放光彩。陆源即将完成的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瀛波志》,开篇头一句即是:“瀛波庄园坐落于大都会的南部边缘。实际上,它是一扇时空之窗,三个世界在此重叠。”从这第一句即可见出作者的野心,他试图以虚构的方式揭示中外各文明彼此融合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图景。
类似这样,以个体的知情意对人的内部、外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进行整体把握的尝试,本身便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倾向。这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一重显现,其深层含义,是各种文化深入交织、融合的外部世界在年轻作家眼中的样貌。
1921年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发表,提出了青年人“生的苦闷”与“爱的苦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城市文学”这个范围里,亦是核心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80后”、“90后”作家描写农村人口在城市境遇的作品不少。在抵抗“生的苦闷”与“爱的苦闷”方面,宋小詞的小说《直立行走》颇为读者关注。
也许没有比《直立行走》更低的关于女主角的设定了:进城务工的杨双福不美且贫穷,为了能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竭尽全力讨好着男朋友周午马。小说围绕着同样贫寒的周午马一家关于拆迁的算计展开。为了多分到按人头计算的三十平米,杨双福与周午马火速结婚;周的老父亲去世了亦秘不发丧。在与拆迁组的争执中,杨双福为保护丈夫,袭击了工作人员,不但入狱,且接到了婆家的离婚协议,显出进城者个体被命运吞噬的不幸。
但令读者惊讶的是杨双福身上存在着的勃勃生机:她的婚姻中没有任何爱意和温暖可言,自始至终周午马不过将她当成“炮友”,但她能在一次次心寒中自我安慰,并在周父弥留之际推老人家出去晒了晒太阳,让老人在离世的最后一刻感到了适意。被周家彻底抛弃之后,虽然在狱中她立誓要报复周午马,而在潜入他的新家,看到他的巨幅婚纱照和“变态宽的床”之后,她对他没有了恨意——“这张变态宽的床让杨双福感到猛烈的心酸,这巨大的宽阔是以前憋屈太久了的一种宣泄,是痛诉,是愤慨。她忽然感受到了周午马对以前生活强烈的恨意。”她“同情地理解”了周午马的苦楚;周午马也是能爱一个人的,虽然他爱的那个人不是她。
“周午马……娶了理想中的妻子,又孕育出了下一代,而且住上了窗明几净的房子,多么美好的结局,总算苦尽甘来了。她要好好祝福他下半辈子的人生。”因为感觉到一个凉薄之徒也是有“爱”的,因为感觉到从艰难环境中挣扎出来的不易,虽然面对的是造成自己苦难的人之一,仍然选择原谅,杨双福在这一瞬间洋溢着英雄气息。其实,之前她勉力维系着不成样子的周家时,也足以让读者感到她内心的坚韧。
这个平凡的小人物是耐人寻味的。她的耐人寻味之处,便在于她身上住着的这个英雄。我们不禁要问,这个英雄是从何而来的呢?
也许可以这么理解:杨双福“这一个”人物不仅仅是“这一个”,她是由千千万万进城务工者凝结而成的理念。城市的激烈竞争、更高的经济花销令他们倍感压力,他们靠着吃苦与忍耐,抵抗着“生”与“爱”方面的种种不足。也许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勃勃生机给了他们在这里抵抗和忍耐的愿景。靠个人的抵抗和忍耐,融入城市,也正为此而互相理解——也许可以说,这是这个时代的于连之一。人物的勇气和英雄气质,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
同样的顽强,我们也可以从文珍的作品中读到。文珍的小说集《十一味爱》,从字面上便显出一代人对爱的追求。文珍的小说塑造了城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年轻夫妻、公司白领、刚毕业的大学生、卖麻辣烫的美丽姑娘……与宋小词小说中的人物设定相比,他们在“生”的层面所受的压力较小一些、在“美”的层面更有优势一些,在“爱”的方面便格外地要追问个清晰明确。
这似乎可以看成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当代的发枝散叶。爱情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重大主题。这一主题在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又几乎成为“主题中的主题”。
现代都市中,人与人的遇见更为频繁。“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穆旦诗)如何在更其繁复的无数个“你”“我”之间确定“独一个”的价值,文珍的小说以细腻精微的文字、漫漶而富于感染力的情绪,考察着人们的情感,描摹爱情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消亡……在一次次的追求、动摇、幻灭之后,人物依然充满对爱的希望。这是以一己之力怀疑着、又抵抗着爱的虚无的英雄。
在“80后”作家中,对身处的城市达到形而上的整体观照的,是胡迁。胡迁有中短篇小说集《大裂》、《远处的拉莫》,长篇小说《牛蛙》,导演了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胡迁对城市文明的整体批判,是通过在小说《牛蛙》中一个荒诞的设定达到的——叙事者“我”的表姐将要嫁给一只牛蛙。
整件事情的由来在于,富人张乔生不同意儿子张翰与“我”的表姐结婚,提议在同样的经济待遇下,让表姐嫁给一只牛蛙——确确实实是当天即将被厨子拿来炖的牛蛙中的一只。这荒诞的要求居然被表姐接受了。并且,婚礼前夕,这只牛蛙神秘地被“谋杀”了,而“我”必须查出谁是凶手……荒诞的情境,接续了卡夫卡小说中,人变成甲虫的传统——这是从婚姻关系观照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恶意。同样富有意味的是小说结尾,张乔生计划用下水道里的几亿吨污物覆盖整座城市。而原本显然对张乔生无甚好感的“我”,因为听说这个计划而对他产生了无限的钦佩。
这里,城市象征着文明。整体取消文明之意义的原因,是《牛蛙》里“我”对世界的判断——这是一个恶意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互相侵占,“侵占”是生命的真相。所以,这个世界如果被毁,并不会令人感到可惜。
看似决绝的毁灭态度,却正显出胡迁内心的温柔——正是对于“侵占”的愤怒,才会发出“毁灭”的咒诅。
在小说之外,胡迁在创作谈《<大裂>之后》中说:“每一代有每一代人的痛楚。上一代人,现代社会的分裂畸形替代了战争对更上一代人核心的摧残。”而当下“概念化、目的化和庸俗化的表象”替代了对人的疼痛的感知。也就是说,对事物“理性”的、抽象的“概念把握”削平了时间,也削平了“自我的其他部分或者外界的其他事物”。也许可以说,这是胡迁在他的小说中,让城市被淹没的另一重意义:作为人类理性、概念的象征的“城市”陆沉了。
胡迁在小说中以城市的陷落提出了警示。在城市的繁荣发展时期,胡迁的眼光已蔓延至了文明衰落的晚景。
同样激烈的情绪,可以在慢先生的《山阳山阴》、《落潮》中看到。在澳大利亚从事着工科生涯的“90后”作家慢先生,祖籍苏州,出生于西北,父亲所在的工厂里又有很多东北工友,这使他可以用好些不同的腔调来叙事。他写起小说来那一股狠劲,可以与胡迁相比。相较而言,胡迁更忧伤,而慢先生趋于暴烈。
《山阳山阴》写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苏州的样貌。小说里出现了叙事主人公陈卅的父母——這是同样被城市化浪潮裹挟的上一代年轻人。他们每个月初去新华书店选新书,空余时间在舞厅和排练乐队中度过,“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安排,整个城市最无所事事的聪明人都走到了一起”。父辈的先锋姿态启发了后辈,校园里具有反叛味道的四个小学生组成了被戏称为“四大金刚”的一群,不见容于刻板的教育模式,常被连人带包扔出来,在校园里“漫游”。小说的高潮之一,是当陈卅的表白纸条被老师发现之际,患有多动症的宽子为掩护陈卅,制造混乱、吞下纸条,被灌镇静剂药物和毒打。为解救宽子,陈卅踏进老师办公室,“冲上前去把那小半瓶药全部倒在了嘴里——以后我没法管,但今天,这个药我包圆儿了”。这不要命的举动,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对窒闷的周遭环境能做出的最激烈的反抗。
以上可以看作城市这一综合了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诸多要素的巨大实体在几位“80后”、“90后”作家作品中折射出来的光线。我也想起魏思孝的小说《一个废柴的日常生活》,阅读时不难发现,人物带有鲜明的自矜气息。自命“废柴”的人物是谦逊的,也是骄傲的,他自己明白他作为个体的价值,虽然不一定需要表露出来。
本文的立意亦是在此。从几位“80后”、“90后”代表作家作品中浮现的这一可称为“废柴”的普通人形象,是脱胎于传统知识阶层的新的知识阶层,他是伴随着城市发展而产生的新人物。他的力量来源于城市及与其相关的现代意识,他拥有强大的自我反省的力量,甚至超前到预见了文明消亡的前景。可能也正因为外部实体如城市的巨大,叙事主人公常感到某种无力。
但一切都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试图以个体的力量概括和把握文化融合的规律,或者孜孜于对物质与爱欲的追求,或者对这一切采取审视和怀疑的态度,这些都充满了浓烈的英雄气质。这可能同样有时代的加成因素在起作用。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很难有类似日本太宰治的“斜阳派”作品,即使低至最低处,骨子里也有着生机。或许可以说,这个具有英雄气质的叙事形象,正是当下活跃在中国城市的普通人们的形象凝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