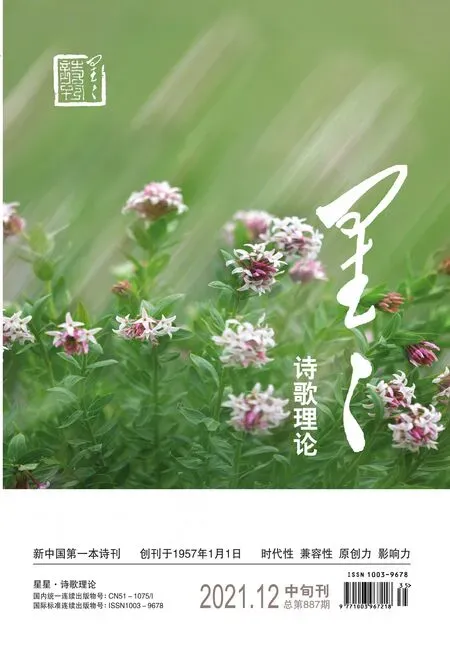故乡辞
——致我们终将消殁的幼年
>>> 周俊锋
首届光中诗歌奖征文活动以“乡愁”为主题,结合诗人的个体创造和发现来处理这一惯常而熟悉的题材,从技艺层面切实呈现出当代汉语诗歌语言试验的繁复或精湛;然而,在诗人手艺的背后容易忽略的问题可能在于技艺尺度与价值尺度二者的混淆,单一尺度上的诗学技艺已然很难对当前人们既有的、略嫌僵化和贫瘠的知识结构实现切实有效的更新,甚至有浮泛成为一种怀旧式、小情绪的风险。回顾获奖作品的乡愁书写,或是重新对乡愁书写传统进行一次粗略的检视,横亘在繁复炫丽的诗人手艺之外的恰恰不是“写什么”或“怎么写”的问题,往往聚焦于“为什么写”这一关涉文学书写自身的问题导向:故乡辞的重复书写,不断激活个体与历史、时代普遍联结的文化记忆和源头印迹,然而故乡和传统已将注定走向消殁,迎难而上的乡愁抒写是否能够给予我们足够的“发现底惊异”呢?
青小衣的诗歌《虫鸣,即乡音》以细小的切入口来呈现抒情主体内在的心理冲突,前行与回溯、喧腾与寂静、温柔与暴烈,类似的表达充满情感逻辑的悖谬和张力。抒情主体藉由虫鸣展开对故乡或乡音的辨认,然而这段旅途必然面临一种来自历史与空间的双重挤压,“回家的路途,信封上模糊的地址/名字,户口本上失踪的籍贯/宗谱上陌生的血脉”,以反向的方式探询故乡的难度,实则从另一方面衬托出“我”想要抵近故乡的执著追求与坚定信念。此外还应当注意到,该首诗歌对抒情场景的转换和塑造特别是黑夜、月光、泥土/地下等意象营构仍有继续细腻打磨的空间,月光的“闪烁不定”与“明晃晃”、泥土里拔出来以及从地下重新长出来等表达,在一首诗歌内部缺乏相应的区隔。
檐瓦,闪现于汉语新诗的意象长廊之中有着特殊的诗学蕴意,时间与空间的叠合使得故乡老屋的形象呼之欲出,浸润着故乡记忆的沧桑、斑驳以及世事浮沉更迭的羁绊。陆健的诗歌《想起一片瓦》情感绵密,以“故乡是……”的比喻句式串联起父亲的肩背、母亲的爱情、奶奶的小脚、爷爷的蹒跚,以及南下外出务工的人们,抒情主体不断指认“故乡”的同时也在不断确证“家”的最初涵义:我的故乡情结源自于对家的体味和重复辨认。想到一片瓦、想到心里的一根刺,想到我们“在自己的身体里埋葬又新生的自己”,想到清晨距离眼前一亿四千万公里远的太阳,对生命时间和故土记忆的那份热望被重新激活。而龙向枚的诗歌《青瓦之上》更为注意“青瓦”意象的引入与衔接,以“远行的出走——乡愁呼唤”的情感逻辑勾勒出“你却没有回头”的抒情主体形象和诗歌结构。诗歌首节富于画面感和声音表现力,“一条河流能带走河沙,从不带走两岸”,巧妙传神地抒写出故乡承托的那份坚韧与厚重,伴随着苍茫奔走的旅途,不断堆叠起硕大的乡愁。这首诗歌的立意和辞藻别具匠心,胜在对诗歌细节的处理和情感冲突的设置,“青瓦之上”以及离乡对远行意义的探问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故乡书写在诗歌经验的创造性处理上获得超拔,离家的选择则成为一种必然。而区别于这种否定性的情感指向,陆健的诗歌借农民工的选择和行为来仔细辨认对故乡的“逃离”——“好像离家越远反倒离家更近”,以细腻而绵密的方式强化主体对于故乡的情感羁绊,用正面的方式加深用汗水血肉捂热的那段现实,实则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诗人田禾的获奖作品《冬眠》朴素而深沉,以“可能与不能”的关系性话题并置眼前,大地、茱萸、青蛙、乌龟、蜗牛等,开始陆续进入冬眠,开始实现退回根部、实现深土里和石缝中的冬眠,乃至于万物用全部的身心拥抱这个特殊节季里必然的可能性。“词语在冬眠”,然而由“但”字所领起的、诗歌所要倾心关注的恰恰是另外一个刺点,从大地上的动植物再到多数的鲜花“假寐式”的休眠,父亲以及他所贯注全部心力的乡土世界,在冬眠时节里猛地迸发出内在的隐力,“炉火不能冬眠,炊烟不能冬眠/它会比平时燃烧得更旺”,淬火的镰刀以及父亲、酒、火炉勾勒出来的乡村生活图景,鲜亮而富于生命本身的热情和生力,借明月的光芒“照亮”更多隐秘的角落和隐微的生存。
邵散燕的诗歌《我与故乡隔着一首诗的距离》侧重于凸现内在情感的厚度和可能抵达的广度。他青睐于采用一种背离的方式贴近和强化诗意的主旨,“不断尝试远离故土”“我离她越遥远”,以减法来不断删刈关于故乡分外沉重的情感羁绊,最后只留下“一条江,几座山,零星地名”,然而愈是被删减后的故乡记忆却不断延展,甚至像似括号的一边,无形地勾连起任何一个我可能存在的遥远地方。
诗人徐俊《故乡啊,我是活在你光明中的瞎子》更为聚焦的是一种我与故乡之间展开互动和对话的关系,故乡为我所馈赠的礼物,“让我有足够的力气,托举这星辰”,以及我能够为故乡所反哺和回馈的愿念,“我会用全部的生命,/为故乡铺一条通往太阳的道路”,灶膛里的火焰、门前老树的枝桠、一篮子鸟鸣,以及与半生运命紧密联结的造房婚育、庄稼欠收,故乡紧紧跟随并且疼爱我、养育我、裹挟我,成为无法诉说的恩情。整首诗歌的内容丰厚,情感较为浓郁,但同时也遗留不少亟待浓缩和提炼的诗意缺憾,有如“让民间祥瑞”“让大地光明满溢”“喂养天空和大地”等类似表达在不少获奖作品中多有显露,笔触上略嫌笼统和宏阔,相反却忽视掉原本可以细腻展开的有关故乡的那些潮湿的、引发颤栗的事物,诗歌比拟“自己就是那树上的一根枝桠”“这疼痛的枝桠/让大海激荡不已”,而典型意象和情境营设的过程中诗人似可以展开更为幽微曲折的文学风景。值得注意的是,该首诗歌不同程度上呈露出史诗向度的写作尝试,但“祭拜太阳的仪式”“众神降落,鸟群飞过月亮”等内在的情感线索和整体的诗歌结构,或许在有限的诗歌篇幅中尚不能形成足够有效的统一。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嵌入故乡的文学母题,抵近故乡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主体自身,乃至成为更普遍意义上的一种对文化记忆和原初印迹展开历史性的叩问。从技艺的维度来看,故乡辞的重复抒写和诗学变形不断激励和唤醒我们对故乡、对当下、对自身的本源认识,而故乡的琉璃瓦盏愈是精微、故乡的檐瓦青苔愈是苍翠,反倒衬托出当代汉语藉由诗歌激活一代人故乡记忆的能力愈发贫弱。从价值层面或另一个敞亮的视野来看,故乡辞的书写又能够在多大限度有效更新、乃至改变同时代人们对个体和社会互动关联的既有认知呢?文化或能反哺、记忆或许闪现,而我们终将消殁的幼年却早已经成为定局,紧随着故乡的生命消瘦,文字的生命也如烛火微暗的摇晃,难有叩击人心或灵魂的涤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