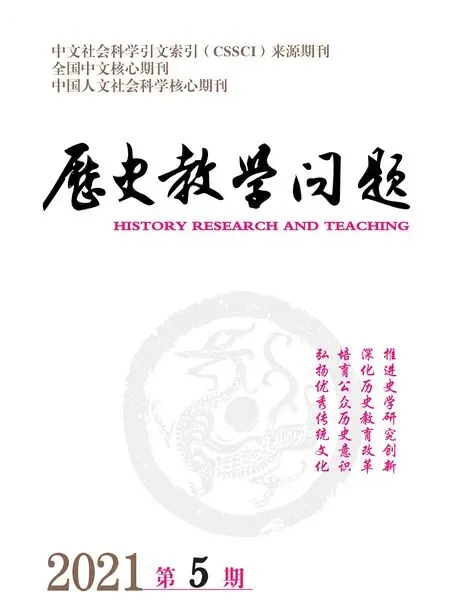论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的对外扩张
——以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为材料
刘凤华 袁指挥
自从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479—前1425 年在位)征伐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后文简称为“叙巴地区”)以来,埃及在该地区逐步确立起了统治地位。埃及对叙巴地区采取了派驻官员、驻扎军队的间接统治方式,各个附属国的国王仍然享有王者的尊贵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管理着他们的国家。利用埃及间接统治所留下的权力空间,一些附属国开疆并土,而宗主国埃及对这种扩张行为采取了一定的反制措施。
在对巴勒斯坦地区埃及附属国的扩张的研究上,学界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单纯研究埃及附属国的扩张,这以库费尔特、罗斯的研究成果为代表。①另外一种是把萨克穆的拉巴玉的扩张与以色列的扫罗所建的北部王国的扩张作比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为扫罗北部王国的建立寻找历史依据,这以芬克尔斯坦、那曼、克费尔的研究成果为代表。②总体上看,学界已有的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这些附属国扩张的细节,但是,对于它们为什么能够频繁对外扩张,至今未见学者做过深入探讨。为此,笔者在学界的研究基础上,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的扩张、埃及的应对措施、埃及附属国不断扩张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讨。

一、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的扩张
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可以看出,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些附属国对埃及保持忠诚,而另外一些附属国则推行地区性的霸权政策,如,萨克穆(Shakmu)、加兹鲁(Gazru)、金提凯尔米鲁(Ginti-kirmilu)等等。在拉巴玉及其子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中部山区的萨克穆采取了对外扩张的政策,把矛头对准了周边国家,尤其是耶斯列谷地的美吉多。在米尔凯鲁、贝鲁达尼统治时期,加兹鲁不断扩张势力,扩张的主要目标是耶路撒冷。在塔盖统治时期,卡梅尔山附近的金提凯尔米鲁与加兹鲁结成攻守同盟,向外扩张势力。通过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扩张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拉巴玉主导扩张的时期,第二阶段是米尔凯鲁领导扩张的时期,第三阶段为贝鲁达尼扩张的时期。
在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萨克穆是扩张的主力,加兹鲁扮演协助者的次要角色。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提供的信息来看,萨克穆的统治者拉巴玉与加兹鲁的统治者米尔凯鲁结成了攻守同盟。在一封泥板书信中,萨克穆的统治者拉巴玉对法老说,“瞧,(这就是)我的叛逆,瞧,(这就是)我的疏忽,因为我进入了加兹鲁城”(第253 号阿马尔那泥板书信第18—22行①文中所引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均为笔者翻译,以文中夹注的方式标注。后文简称为:第X 号泥板书信第X 行。),在另外一封泥板书信中,拉巴玉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我的罪行在于,我进入了加兹鲁城与我所说的话”(第254 号泥板书信第19—23 行)。在这两封泥板书信中,拉巴玉提及进入加兹鲁城,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萨克穆入侵加兹鲁,还是拉巴玉与米尔凯鲁秘密会晤商讨要事呢?尽管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另外一封泥板书信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在这封泥板书信中,一个小国统治者贝鲁曼罕尔说,“愿国王把话送给我,别让米尔凯鲁、拉巴玉听到”(第249 号泥板书信第15—17行),显然贝鲁曼罕把米尔凯鲁与拉巴玉看做是一伙的,他担心这两人知晓他与埃及法老之间的情报交流。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拉巴玉到了加兹鲁,与其统治者秘密会晤。
在米尔凯鲁的支持下,拉巴玉至少攻占了5 座城市,在第250 号泥板书信中,一个附属国统治者转述了拉巴玉的儿子对他的父亲的对外扩张的描述,“这个城市(指吉提帕达拉)是我们的父亲拉巴伊曾经夺取下来的”②拉巴伊为拉巴玉异体写法,下文不再赘述。“当他(指拉巴玉)进攻苏那马城、布尔库那城、哈拉布城的时候,他驱逐了他们。他夺取了吉提里穆尼城,他耕种了国王、你的主人(的土地)”(第250 号第13—14、42—47 行)。在攻占了这些城市后,拉巴玉把矛头对准了美吉多,美吉多的统治者比里迪伊向法老汇报说,“拉巴玉对我发动了战争”,拉巴玉“决定去夺取美吉多”(第244 号第11—12、22—24 行)。
拉巴玉死后,米尔凯鲁成为扩张的主角,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的扩张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米尔凯鲁与拉巴玉的两个儿子结成新的同盟,“此外,米尔凯鲁进入了他们跟前,他们之间公平地交换了问候礼物,这样,他离开了(国王),米尔凯鲁进入到拉巴伊的两个儿子的条约之中”(第250 号泥板书信第31—36 行)。米尔凯鲁还与金提凯尔米鲁的统治者兼他的岳父塔盖结成结盟,耶路撒冷的统治者阿布迪希巴在泥板书信中把两者并列提及,“至于米尔凯鲁和塔盖”(第289 号泥板书信第11 行),暗示了这两人有着密切关系。从第290 号泥板书信来看,米尔凯鲁与另外一个统治者苏瓦尔达塔结成了同盟,“瞧,至于米尔凯鲁和苏阿尔达图(苏瓦尔达塔的异体写法)对国王、我的主人的土地所做的事情”(第290 号泥板书信第5—7 行)。此外,米尔凯鲁还与“阿尔沙亚的儿子们”也结成了同盟,“米尔凯鲁没有离开……阿尔沙亚的儿子们”(第289 号泥板书信第5—7 行),现在还不清楚阿尔沙亚是哪个国家的统治者。
这样,米尔凯鲁利用这些同盟国的力量,夺取了耶路撒冷与加兹鲁之间的鲁布图。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的一句话——“当他们占领鲁布图的时候”(第289 号泥板书信第13 行),表明该城已经落入了米尔凯鲁之手。第250 号泥板书信对夺取鲁布图城的细节作了描述,“瞧,至于米尔凯鲁和苏阿尔达图对国王、我的主人的土地所做的事情,他们集结了加兹鲁的军队、吉姆提的军队、凯尔图的军队,夺取了鲁布图的土地。”(第250 号泥板书信第5—11 行)然后,米尔凯鲁号召同盟国一起孤立耶路撒冷,“米尔凯鲁写信给塔盖与(拉巴玉或阿尔沙亚的)儿子们,(说),‘做(这样的)人吧!把他们所有的要求给凯尔图的人们,让我们孤立乌鲁撒伦(即耶路撒冷)。’”(第289 号泥板书信第25—29 行)阿布迪希巴直接告诉法老,“这些事情都是在米尔凯鲁的命令下、苏阿尔达图的命令下、金提的统治者(的命令下)(做)的”(第250 号泥板书信第25—28 行)。
与此同时,“拉巴玉的儿子们认真地继续他们父亲的事业”,①George Kufeldt,p.222.正如一个附属国的统治者所言,“拉巴亚的两个儿子一直说,②拉巴亚为拉巴玉异体写法,下文不再赘述。‘像我们的父亲一样,进攻国王、你的主人……’”(第250 号泥板书信第40—41 行)。结果,拉巴玉的两个儿子,“调转了他们的脸,这损害了国王、我的主人的土地”(第250 号泥板书信第5—7 行),至于他们如何扩张的,现存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没有记载,可能与拉巴玉当年的扩张轨迹相似。
但是,米尔凯鲁拼凑的这个同盟,逐步分崩离析了。第366 号泥板书信提及阿布迪希巴与苏瓦尔达塔一起对阿皮鲁作战,“我与阿布迪希巴对阿皮鲁作战”(第366 号泥板书信第20—21 行),这表明苏瓦尔达塔退出了米尔凯鲁的同盟。从其他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来看,苏瓦尔达塔显然加入了一个更大的同盟,除了苏瓦尔达塔所统治的国家外,还有耶路撒冷、阿克、阿卡沙帕,“阿克的统治者苏拉塔与阿卡沙帕的统治者伊塔鲁塔,召唤了50 个人来到我(指的是苏瓦尔达塔)这里,现在,他们与我一起出征”(第366 号泥板书信第22—28 行)。至于其他同盟国,可能还站在米尔凯鲁一边。有学者猜测,米尔凯鲁的死亡,最终使得这个同盟自然瓦解了。③R. W. Ross,“Gezer in the Tell el-Amarna Letters”,p.68.
接替米尔凯鲁统治加兹鲁的是亚帕胡。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来看,亚帕胡似乎放弃了对外扩张的政策。但是,亚帕胡与他的兄弟关系不睦,在写给埃及法老的书信中,亚帕胡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我那更年轻的兄弟敌视我,他已经进入了穆哈珠城,他把他的双手给了阿皮鲁,现在,他正在与我作战。”(第298 号泥板书信第22—29 行)双方争斗的结果以亚帕胡的失败而告终,“我失去了我的土地上的物资,现在我一无所有。”(第300 号泥板书信第12—14 行)在亚帕胡之后,加兹鲁的国王是贝鲁达尼。贝鲁达尼是不是亚帕胡的那个兄弟呢?现存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对此没有记载。贝鲁达尼统治时期,加兹鲁再次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的扩张进入了第三阶段。在写给埃及国王的泥板书信中,贝鲁达尼描述了他在山区修建城市以对付来自山区的敌人,“(因为)山区(的国家)敌视我,我建造了1 座城市,它的名字叫曼哈图城,以准备(接待)国王、我的主人的弓箭手士兵的到来。”(第292 号泥板书信第28—32 行)此处提及的敌视加兹鲁的山区国家指的是哪个国家呢?在米尔凯鲁时期,加兹鲁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巴勒斯坦山区的耶路撒冷,因此,这里的山区国家很可能指的还是耶路撒冷,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贝鲁达尼统治时期,加兹鲁再次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由于资料的缺乏,学界对贝鲁达尼的扩张具体情况知之甚少。
二、埃及对巴勒斯坦地区附属国扩张的应对措施
从萨克穆、加兹鲁、金提凯尔米鲁的扩张来看,萨克穆、加兹鲁是扩张的主力,而金提凯尔米鲁似乎仅仅配合或策应加兹鲁的扩张。萨克穆的扩张方向为耶斯列谷地,而加兹鲁的扩张目标是山区的耶路撒冷。耶斯列谷地是多条商路的必经之地,其中一条商路经过以巴路山(Mt. Ebal)与基利心山(Mt. Gerizim)之间峡谷,通向萨克穆。对于萨克穆而言,若要完全掌控峡谷商路,必须得控制耶斯列谷地。美吉多是耶斯列谷地最为重要的城市,通向叙利亚地区的“沿海大道”的东支路经过美吉多。如果能占领美吉多,萨克穆不但能掌控峡谷商路,而且还会控制“沿海大道”东支路。这样,耶斯列谷地的战略要地美吉多成为萨克穆攻击的主要目标。加兹鲁控制着从沿海平原通向内陆的道路,因“沿海大道”所在的沿海平原对埃及非常重要,加兹鲁若入侵沿海平原的话,必然会遭到埃及的残酷镇压,因此,加兹鲁转而试图控制山区的商路,最终选择夺取山脊之路(Ridge Route,也称族长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耶路撒冷。一旦夺取了耶路撒冷,那么,加兹鲁不但将掌控沿海通向山区的商路,而且还可控制山脊之路的重要路段。
在拉巴玉联合米尔凯鲁扩张的时候,埃及对两个附属国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埃及意识到米尔凯鲁在扩张中所扮演的是协助者的角色,故而对他采取怀柔的政策。为此,埃及法老放下身段,给米尔凯鲁送去大量礼物:
你(使节),对加兹鲁的统治者米尔凯鲁(说),“下面是国王的话。”现在,我把这块泥板送去给你,对你说:现在,我派遣弓箭手士兵的马队指挥官汉亚,连同美丽的女持杯者所需要的东西:银子、金子、亚麻袍子、红玉髓、各种各样的石头、乌木椅子,各种各样类似的好东西,合计:160 提板;①此处的提板是对古埃及的重量、货币单位德本()的阿卡德语音译。合计:40 个女持杯者。1 个女持杯者的价格是40(谢克尔)银子。因此,在送给你的十分美丽的女持杯者中,没有任何人是冒名顶替的,国王、你的主人对你说,“这太好了,根据他送给你的命令。”愿你知道,国王安好,就如太阳神一般,他的军队、他的战车、他的马匹非常好!阿蒙放置了上地、下地——从太阳神升起到太阳神落下地方——在国王的双脚下。(第369 号泥板书信)
在现存的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多是附属国写给埃及的书信,而埃及写给附属国的书信非常罕见,可能出于怀柔加兹鲁的目的,埃及法老才一反常态写信给米尔凯鲁。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附属国往往主动或应埃及的要求向埃及进献各种物品,而在第369 号泥板书信中,法老送给米尔凯鲁40 名女持杯者及其所用的各种物品,由此可见埃及的良苦用心。至于这些东西是法老主动送的呢,还是米尔凯鲁索要的呢,由于史料缺乏,无法得知。但是,在第269 号泥板书信中,米尔凯鲁曾主动向法老索要珍贵的药材没药(murru):②没药:阿卡德语词汇为murru,英译为myrrh。一般把myrrh 翻译为“没药”,也偶尔翻译成城“末药”,这是没药树的树胶凝结成块状物,可以入药,有消炎止痛的功效。
你(使节),对国王、我的主人、我的神、我的太阳神说,“下面是你的仆人、你脚下的尘土米尔凯鲁的话。”在国王、我的主人、我的神、我的太阳神的脚下,我七次又七次地拜倒在地!我已经听到了国王、我的主人送来的(话)。愿国王、我的主人派来弓箭手士兵给他的仆人,愿国王、我的主人送来用以治疗(疾患)的没药。(第269 号泥板书信)
虽然米尔凯鲁在问候语中,极尽谄媚,贬低自我,像其他附属国统治者一样,“七次又七次地拜倒在地”,但是,他要求埃及法老送给他珍贵的没药,俨然一副大国统治者的派头。埃及并不产没药,它的没药主要来自蓬特(可能是今天的阿曼或索马里一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没药对于埃及而言,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物品,而附属国统治者米尔凯鲁却张口向埃及索取没药,个中意味耐人寻味。
对于首恶拉巴玉,埃及最初的措施比较温和,埃及法老质问拉巴玉与米尔凯鲁的结盟的事情,拉巴玉对此辩称道,“我已经听到了国王、我的主人在你送来的泥板上写下的话。瞧,我是国王的仆人,就如我的父亲一样,就如我祖父一样,很早以来,我们是国王、我的主人的仆人,我没有反叛过你,也没有忽视过你。瞧,(这就是)我的叛逆,瞧,(这就是)我的疏忽,因为我进入了加兹鲁城,我说了下面的话,‘国王优待我们’!现在,我没有其他的目的,除了侍奉国王之外,不论国王说什么,我都会听从的。”(第253 号泥板书信第7—31 行)对于法老质问其子与阿皮鲁勾结的事情,拉巴玉以不知情来搪塞(第254 号泥板书信第32—35 行),为了免受其子的牵连,他把儿子交给埃及官员阿达亚(第254 号泥板书信第36—37行)审判。埃及对此并不满意,最终采取了有限打击的政策。攻打拉巴玉的军队是埃及军队,还是附属国组成联军,从比里迪伊向法老汇报的泥板书信中能找到一点线索,“因为弓箭手部队已经返回,拉巴玉对我发动了战争”(第244 号泥板书信第9—12 行),此处提及的弓箭手部队是返回埃及还是返回其他地方,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埃及主导的一次战争。拉巴玉的城市被占领了,他对此抱怨道,“在战争中,城市已经被占领了……城市被夺走了,与神一起(被夺走了)。”(第252 号泥板书信第9—13 行)
埃及分化瓦解拉巴玉-米尔凯鲁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拉巴玉对于埃及法老没有惩罚米尔凯鲁十分不满,他抗议道,“国王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而米尔凯鲁的东西在哪里呢?我知道了米尔凯鲁对我所做的事情。”(第254 号泥板书信第24—29 行)有的学者认为,这句话表明了米尔凯鲁与拉巴玉分道扬镳了。③R. W. Ross,“Gezer in the Tell el-Amarna Letters”,p.64.在压制了拉巴玉之后,埃及回过头来惩罚米尔凯鲁。埃及官员延哈马没收了米尔凯鲁的财产,要求米尔凯鲁交出妻儿做人质。(第270 号泥板书信第9—21 行)
不久,拉巴玉再次发动了对外扩张,对埃及的统治中心美吉多下手。美吉多对埃及非常重要,拉巴玉“对沿海大道地区的入侵侵犯了法老的利益,使得法老没了耐心”,④Yohanan Aharoni,,trans. by Anson F. Rainey,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1967,p.163.在埃及的部署下,比里迪伊集结其他几个附属国的军队征伐并生擒了拉巴玉。①但在押解拉巴玉去埃及受审的途中,阿克的统治者苏拉塔擅自释放了拉巴玉。至于苏拉塔为什么会不惜忤逆宗主国埃及而释放拉巴玉,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没有提供任何信息。但是,逃脱之后的拉巴玉,最终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在第250 号泥板书信中,拉巴玉的儿子提及了父亲被杀的事情(第280 号泥板书信第17—18 行),第280 号泥板书信中也有“曾经夺取过我们的城市的拉巴玉死了”(第280 号泥板书信第30—32 行)的语句。
在米尔凯鲁主导扩张同盟的时期,埃及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现存的泥板书信对此没有记载。有学者说,“在某个时候,拉巴玉的儿子从阿马尔那书信中消失了”,而他们的同盟国加兹鲁的“王位更替终结了阿马尔那时期的示剑占领迦南中部地区的野心”。②此外,埃及扶植亲埃及的政治势力以取代苏瓦尔达塔,不甘受埃及摆布的苏瓦尔达塔抗议道,“为什么我的兄弟为国王所喜爱呢?”(第284号泥板书信第14—15行)从第366号泥板书信来看,最终苏瓦尔达塔放弃与米尔凯鲁的结盟,与阿布迪希巴一起对阿皮鲁作战。在贝鲁达尼扩张的时期,埃及同样对加兹鲁的扩张采取了措施。埃及官员马亚夺取了贝鲁达尼建造新城曼哈图城,贝鲁达尼写信给法老叙述了此事,“但是,瞧,马亚把它从我的手中拿走了”(第292号泥板书信第33—34行)。此外,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提及一个叫佩亚的人攻击了加兹鲁城,“瞧,古拉图之子佩亚对加兹鲁城——国王、我的主人的女奴——所做的事情”(第292号泥板书信第41—44行),有学者猜测佩亚是埃及官员。③但是,从第294号泥板书信来看,佩亚似乎还攻击了另外一个附属国统治者,这样,对其身份的确定变得困难起来。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第295号泥板书信的作者也叫贝鲁达尼,在这封书信中,贝鲁达尼提及自己遭到了腓尼基地区的国家西顿的攻击,而这块泥板是用西顿附近的推罗的泥土制作的,很难想象加兹鲁统治者贝鲁达尼能扩张到推罗那么远的地方,因此,笔者认为这个贝鲁达尼与加兹鲁的贝鲁达尼不是同一个人。
尽管拉巴玉、米尔凯鲁等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扩张过势力,但埃及仍然控制着这一地区。在加兹鲁挖掘出一个象牙日晷,上面描述了第19王朝法老美楞普塔(公元前1213—前1203年)跪拜拉-哈拉凯提神,除此之外还发掘出第19、20王朝时期的其他物品,④这些东西可能暗示了埃及的势力在加兹鲁的存在。美楞普塔的胜利石碑(也称以色列石碑)提及“攻下了卡扎尔()”,⑤鉴于这块石碑的碑文的诗歌体裁,学界很多学者认为美楞普塔对巴勒斯坦的征伐可能并不存在。此外,新王国时期的诅咒文没有提及加兹鲁,这说明埃及人没有把加兹鲁视为敌人,有学者由此认为,到了第19、20王朝时期,加兹鲁仍在埃及的控制之下。⑥在萨克穆出土了一些新王国时期的圣甲虫雕刻、印章,其中一个是18王朝时期的费恩斯圣甲虫雕刻,上面的象形文字读作Hmt nswt tiy,意思为“提伊王后”,另一个年代为第19王朝的圣甲虫雕刻,上面画着一个裸体的男子,他的左边的象形文字读作kADn r xASwt pHr,意思为“诸圆形外国的战车兵”,⑦由此看出埃及与萨克穆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在第19王朝时期的阿那斯塔斯纸草上,提及叙巴地区一些城市的名字,其中就有萨克穆,“萨克穆的山在哪里?”⑧笔者由此推测,萨克穆还在埃及的控制之下。此外,埃及和赫梯和平条约签订之后,巴勒斯坦属于埃及的势力范围。

三、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附属国屡次扩张的原因分析
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的扩张,具有扩张时间长、扩张范围广、参与者众多的特征。从时间上,不管是萨克穆还是加兹鲁,都是持续性的扩张,大约都持续了2 代统治者的时间。从武力进攻的范围来看,拉巴玉及其子主要进攻耶斯列谷地,而米尔凯鲁、苏瓦尔达塔、贝鲁达尼主要进攻的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中部山区,这些国家扩张的地域范围从耶斯列谷地延伸到耶路撒冷,这样看起来范围还是不小的。从参与者来看,除了萨克穆、加兹鲁外,还有金提凯尔米鲁以及几个不知名国家,这样算起来,牵扯到了至少5 个国家,而埃及在整个叙巴地区的附属国才有40 多个。
面对这些附属国的扩张,埃及采取了怀柔、分化、威慑、征伐等措施以应对。在对待萨克穆的扩张上,埃及采取了威慑、有限征伐的措施,在拉巴玉夺取5 城之后,埃及只是教训了一下拉巴玉,这并没有根除拉巴玉发动扩张的根基,在拉巴玉进攻美吉多的时候,埃及采取了组建附属国联军的方式,杀死了拉巴玉,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剪除萨克穆发动战争的能力,之后拉巴玉的两个儿子接替其父继续扩张。在对待加兹鲁上,埃及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怀柔、分化措施,甚至主动向米尔凯鲁赠送礼物。在对待其他附属国上,埃及则采取了分化的措施,迫使苏瓦尔达塔退出了米尔凯鲁的同盟。由此看来,埃及对附属国扩张行为的处置,似乎不太有力,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讨论埃及对叙巴地区的治理体制。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对叙巴地区附属国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统治。叙巴地区的附属国进行自我管理,虽然其统治者臣服于埃及,但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王权,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叙巴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统治者们互称“国王”(šarru),①该词的意思为“王”,为君主的一般性称呼。一些附属国统治者在写给法老的信中自称“某某国的统治者(amēlu)”,由此可见叙巴地区的埃及附属国统治者享有王者的尊贵地位。当然,埃及对这些附属国也采取了一些约束措施,如,迫使附属国宣誓效忠,把附属国统治者的子嗣扣为人质,更为重要的是,埃及在一些重要的城市,派遣官员以监督附属国,驻扎军队以威慑地方。②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埃及在叙巴的统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 期。在这种体制之下,尽管埃及官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把“亚洲城市的日常行政管理权拱手让给了地方统治者。”③D. O’Conner & E. H. Cline,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228.这种间接管理体制削弱了埃及的统治,为某些附属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空间。
但是,埃及为什么采对叙巴地区采取间接统治方式呢?一个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叙巴地区自然环境复杂,文明程度较高,埃及直接统治起来不容易,且埃及最看重的是叙巴地区的商道优势,因此,没有必要占领整个地区,只需在战略要地驻扎一些官员、军队就足以保护商道,于是,埃及采取了一个比较温和的间接统治方式。④D. B. Redford,Egyp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93.但是,这种观点很难站得往脚,因为就当时埃及的南北两大势力范围——叙巴地区、努比亚而言,两个地区的文明程度难分伯仲。事实上,与埃及文明相比,在前王朝时代努比亚文明并不逊色,在第二中间期努比亚人建立科尔马王国的文明程度高,国家实力强大,曾经与北部的希克索斯王朝合作围追堵截埃及南部的第17 王朝,由此看来,叙巴的文明程度并不比努比亚高。埃及对努比亚采用了直接统治方式,而对叙巴地区采用间接统治方式,并非埃及权衡文明程度后而做出的选择。叙巴地区环境的确多样,但并不能对埃及军队形成某种不可逾越的屏障,因为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多次率军队深入叙巴地区。因此,环境复杂多样并不是埃及采取间接统治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叙巴地区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埃及不宜也不可能实行直接统治。⑤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埃及在叙巴的统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 期。从埃及控制商道的需求,埃及帝国的治理困境,以及埃及的独特的文化等方面来探讨埃及的间接治理体制,可能会更得要领。
埃及在新王国时期进入帝国时代,控制了叙巴地区和努比亚地区,那么,埃及帝国建立的目的何在呢?一般而言,“就其职能而言,帝国是个政治工具,用以维持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进程和(或)直接组织这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进程。换句话说,帝国就在于直接控制业已存在的较大经济网络。”①K.埃克霍尔姆、巴里·K.吉尔斯:《古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帝国主义与剥削》,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5000 年?》,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75 页。因此,笔者认为埃及帝国的创建,本质上是埃及追逐各种资源的产物,正如有学者所言,“建立帝国一个主要的动机是为了控制贸易路线并对其进行征税”。②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可以看出,埃及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一方面有着掠夺物资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有控制贸易路线的打算。随着新王国时期埃及对外扩张的步伐,埃及逐步控制了叙巴大部分地区,巴勒斯坦地区成了埃及与西亚大国交往的通道。虽然沿地中海近海航行也可以与西亚大国互通有无,但是,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来看,似乎当时的使节(同时也是大国之间礼物贸易的承担者)仍然选择走陆路,巴比伦王布尔拉布里亚什二世派往埃及的商人(即使节)遭到叙巴地区小国的打劫,“现在,我的商人,与阿胡塔布一起出发的,在迦南做买卖被扣留了。当阿胡塔布向我的兄弟行进的时候,在迦南的欣那图那城,巴隆美之子顺阿达与阿克城的沙拉图之子苏塔特那,派遣他们的人,他们杀了我的商人,并夺走了他们的银子”(第8 号泥板书信第13—21 行)。巴比伦王也曾提及大马士革的统治者抢劫商队,“我向你派去的使节嚓勒穆,在他的旅程中被抢劫了两次。第一次比尔亚马扎抢劫了他,在他的第二次旅程中,你的疆土上的帕马胡总督抢劫了他。”③(第7 号泥板书信第73—77 行)佩拉的统治者穆特巴鲁写给埃及法老的泥板书信提及法老要求他释放埃及派往米坦尼的商旅,“国王、我的主人把哈亚派给我,说,‘去哈那加尔巴特的商旅,瞧,我派出来的,(你)派走它吧!’我是谁啊?我能不派出国王、我的主人的商旅吗?瞧,我的父亲拉巴亚侍奉着国王、他的主人,他急速派出了国王派往哈那加尔巴特国、卡拉杜尼阿什国的商旅。愿国王、我的主人派出商旅!我会带着大量的护卫护送它”(第255 号泥板书信第8—25 行),还有一个附属国统治者表示,“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我会护送国王、我的主人的所有商旅,直到布什鲁努城”。(第199 号泥板书信第9—13 行)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埃及与西亚大国的交往中,巴勒斯坦地区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④

埃及进入叙巴地区后,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势力范围”,⑤叙巴地区的国家成为了埃及附属国。怀特将这种帝国与附属国构成的体系称为宗主国体系,附属国(边缘)与帝国(核心)构成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⑥叙巴地区的附属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当属此类关系,而这种关系体现为核心对边缘的控制,正如学者所言,古代和古典时代农业帝国通常是“核心城市对其邻国实行不同程度的行政和军事控制。”⑦但是,由于帝国缺乏“固定的地理边界和统一的国内政治控制”体系,造成了“在固定的边界内,帝国没有程度一致的统治权,其统治权随着对一些区域控制的日益减弱而递减”,⑧这样就造就了一种等级结构:“完全从属”于核心的地区、“半独立的”地区和“虽然独立但处于核心巨大影响力之下”的地区,而帝国“对最边缘地区”的控制只是一种“霸权”而已。⑨詹姆斯通过对阿马尔那泥板书信的研究,也观察到了埃及对叙巴地区控制力递减的情况,他以距离埃及远近而将叙巴地区划分为沿海平原、南部内陆地区、北迦南地区和最北部地区:埃及对沿海平原的控制力最强,在沿海平原基本上全是忠于埃及的附属国;在内陆地区,埃及的控制力下降了,“随着距离埃及越远或地形变得越难走,可以发现这个地区的附属国的独立性越强”,在这个地区比较容易出现无秩序的情况,能够看到“当地统治者与埃及法老之间关系比较紧张”的证据;在北迦南地区,埃及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大马士革和阿姆鲁肆无忌惮扩张势力;最北部地区的附属国傲慢无礼,法老无法约束。①埃及在对叙巴地区的控制上,面临着所有帝国都会面临的难题,正如晏绍祥教授所言,“在古代那种交通和通讯条件下,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政令达到如此遥远和广大的地区,”②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埃及帝国显然无法解决距离造成的对附属国控制递减的问题。
埃及独特的地域中心主义思想,也阻碍了埃及对叙巴地区的直接统治。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称呼为“黑土地”()或“土地”(),对埃及之外的地方称为“红土地”()或“山地”(),古埃及人把尼罗河谷的平坦的黑色土地与两侧的崎岖不平的沙漠、山地视为截然不同的地方,加上尼罗河流域土地的肥沃以及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使得埃及人非常迷恋故土,对于埃及之外的地方有着某种不适应。古埃及的《对美利卡拉王的教谕》生动地记载了埃及人对叙巴地区的看法;“瞧,可怜的亚洲人,因为他们居住在没有甘泉、林木的地方,山峦叠嶂,道路艰险”,③在另外一篇教谕文学作品中,描述了被派往叙巴地区的埃及士兵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行军穿过山坡,每三天才能喝到一次水,这水里有臭味和咸盐味”,④阿那斯塔斯纸草描述了叙巴地区的地理条件,“那里的天是黑的,地上长满了参天的柏树、橡树与雪松,那里的狮子比豹子、鬣狗更厉害”。⑤金寿福教授认为,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反映了习惯于平缓和开阔地理环境的埃及人初到西亚以后所感受到的不适与不安。”⑥金寿福:《古代埃及人的外族观念》,《世界历史》2008 年第4 期。与这种不适、不安并存的是,古埃及人对故土的异常眷恋,从《遇难船夫的故事》、《辛努亥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流落在外的埃及人对故土非常眷恋,他们的叶落归根的思想根深蒂固。⑦袁指挥:《古埃及人的民族意识和观念》,《世界民族》2006 年第1 期。金寿福教授说:“由于古代埃及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他们对于外族和外国持有一定的优越感,同时也不乏恐惧感。”⑧金寿福:《古代埃及人的外族观念》,《世界历史》2008 年第4 期。这种优越感、恐惧感使得埃及人不愿长期生活在叙巴地区。若是直接建立统治的话,那么,会有很多埃及人需要长期甚至世代生活在叙巴地区,甚至死后还得葬在叙巴地区,这对眷恋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以上三个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影响了埃及对叙巴地区的统治方式。帝国的治理困境——帝国触角的延伸能力,制约了埃及对叙巴地区的统治的深度和广度,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采用了间接统治方式。而叙巴地区在西亚、北非交往中的通道地位,使得埃及满足于自身与西亚大国之间商路的畅通,这强化并固化了埃及对叙巴地区的统治方式。埃及的地域中心主义观念,阻碍了埃及在叙巴地区建立直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