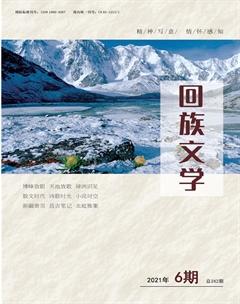江布拉克
陈霞
一
奇台县地图,像一只骆驼的大腿和脚。倒着来看的话,是一座城堡式的烽火台。
在这样一个半马鞍形地貌南部,自博格达山脊流淌下来的九条河,白杨河、根葛尔河、达板河、吉布库河、碧流河、宽沟河、中葛根河、新户河、开垦河——如九条盘龙由南向北日夜不停地奔流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生成一片巨大的绿洲平原,使一块土地因为水源的充足、水质的清澈而孕育出一片闻名遐迩的胜境——江布拉克。
由于职业的原因,我曾无数次在这里流连忘返,被它神奇多彩的自然风光迷醉;也曾多次书写过其境内的一座汉代古城,被耿恭将军抗击匈奴英勇惨烈的故事打动。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冷静地坐下来,认真地审思这块土地的前世与今生。直到跟着景群标志牌设计师周总,地毯式地在整个江布拉克勘察一遍时,才恍然有悟,觉它新鲜至极!丰富至极!震惊至极!
美丽的江布拉克,令我震惊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它像所有的仙境一样有着太多的名字——原来不就是半截沟吗?现在它叫空中草原、瀚海明珠、天山麦海、松翠谷、花海子,如此等等。而且,在这些新名字前面,依然还有许多被当地人叫惯了的“老”名字穿插其间,比如麻沟梁、石城子、刀条岭……同时,在这些或新或旧的地名中,又时不时地听到一些隐藏在深处的原始的儿孙辈乳名,比如庙梁子、三道编子、腰站子、车牌梁、中葛根、宽沟、直沟、哈熊沟……如果再探究的话,还有一棵树、三碗泉、羊圈弯子……至于耳熟能详的五哥泉、七彩湾、镜湖、墨湖、仙人洞、奶头山,就不必一一赘述了。
我纳闷,从前它叫半截沟的时候,这里寻常得很,就像养在深宫里不为人识的女儿一般,可一经更名为“江布拉克”之后,竟一夜間成了惊鸿一瞥的稀世美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一块封闭多年的处女地,就这样奇迹般地复活了!
如今,横空出世的江布拉克,稍作打扮,便震动了世界四方。一时间,境内14个景群29个景点,谁见了都要大呼小叫赞叹不已,激动的程度不亚于看见了泰山、黄河,是那种忍不住要冲向太阳问好的兴奋。眼下,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政府正在深度挖掘它的文化底蕴、独异风采,进行品级打造,申报国家5A级景区。可见,一个地方的冠名何等重要!为了期待它的闪亮登场,人们静候了几千年。
二
从前,这里还叫半截沟的时候,听老人讲,沟沟坳坳长满了麻,一种叫野生麻的植物,漫山遍野。我翻过资料,这种麻,称之为汉麻,起源于中国,是人类最早用于织物的天然纤维,有国纺之源头、万年之衣祖的美誉。由于汉麻有良好的纤维性能,吸附性强,又有较强的抑菌性,加之麻的表皮长而结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用来制作麻绳。细麻绳纳鞋底,中麻绳做缰绳、捆东西,粗麻绳做井绳、拉东西、拴车套。经年累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这种野麻,便约定俗成取名为麻沟梁。
后来,麻沟梁改称刀条岭时,我听过两个传奇故事:一个关于黑涝坝,一个关于老虎爪。
提起“黑涝坝”,人们有很多版本。马镫说,神仙说,野人说……众说不一。其中,最难理解的一种说法是关于黑涝坝的“三奇说”。这第一奇,是水色。见过黑涝坝的人都知道黑涝坝分大小两处,惯称大涝坝、小涝坝,均在马鞍山下。这两处的水有个怪现象,远看黑似炭,近看绿如墨,可舀起来时,却白净透亮,盛在碗里,捧在手里都是无色的。说到这第二奇,那就是坝水无底,深不可测了,但,临近看它时却浅如一面灰镜。实际上它内存7个盆沟,表面看面积不大,内里却有湖泊相通汇成汪洋一片,称为100米条状。遇到水量多的年份,底深丈许,无人可探。所以,民谣曰:“涝坝水,饮不尽,喝不完,千年万年永不干。”这第三奇呢,主要指水的长度。那么,黑涝坝的水,究竟长到了何等地步,这要慢慢道来。传说蛮荒年代,老林里居住着十来户人家,山洪暴发,天降大难的那一夜,全村人坐了一辆马车出逃,行路到了山口,巨浪滔天,被一潭深水横截。情急之下,黑马奋蹄鸣天,三响后,迎水而上,带着一村老少冲进了无底深渊……时隔三年后,人们在318.8公里处的巴里坤湖边,看到了那辆马车的残骸和那匹黑马的缰绳。
至于“老虎爪”,那就更奇了。
据说这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人们正在外面看电影,突然从东面飞来一个圆盘:一个草帽状的碟形飞行物,周围有一圈泛白的光圈,一上一下飘浮不定在空中飞行约八分钟。由于半截沟当时还有林场,那个圆盘垂直下来落在了一块林区。当时林场的职工及附近的村民都被惊动了,小孩子们追着跑……几分钟后,见那飞行物落在了半山腰的林子里。当时,林场好多松树被齐腰折断,有的树皮被烧焦,有的树被击成空壳郎,但人畜家禽无一伤亡,林区的高压线完好无损,电杆无一折断,只是不明飞行物降落过的地方,留下一个近两米的老虎爪痕迹。
人们为此疑惑不解,把那块烧焦的地方叫作“老虎爪”。多少年过去,那里永远留着一个硬生生、光秃秃的老虎脚印,凡爪印涉及范围之内平光无物,寸草不生。
三
江布拉克到底有多神奇,谁也说不清楚。
先不说麻沟梁究竟有没有外星人光顾,也不说黑涝坝地下水域能不能通到巴里坤,单是“刀条岭”这个名字的出现,就让游客震惊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是雄卧于这沟坳里的一道横梁;有诗人形容它像一把青龙月牙大刀,虽然它没有华山的险峻,也没有秦岭的豪迈,但是,它干净!绿得没有一点杂色,又是那样无拘无束浑然天成。
可是,当人们置身于这广袤宁静的绿色中不能自拔时,突然一声惊雷巨响,爆出一条特大新闻震动了世界:自古水往低处流,而偏偏这坡上的水往高处走。这颠覆了人们的惯常思维,天下奇闻!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纷纷就地亲测,经无数次试验,最终得出结果——所有的滚动体皆往高处走。
怪坡的问世,让世人震惊不已。这半截沟一带,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需要追问?
沟里的山榆为何都是两两相依成双成对,如恋人般浓情蜜意?坡上的山路为什么用脚一跺、用石头一敲,发出“咚咚咚”沉闷而宏大的声音?古河道上游的那一片草地上,为什么有一个椭圆形的太极八卦怪石圈,是游牧民族的墓葬群,还是自然界土壤凝结移动的作品?当然,怪坡,属于江布拉克最大的地球之谜;这个隐藏在自然界的千年秘籍,有谁来解?
2005年3月10日,奇台县外事侨务旅游局,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对“怪坡”的长度及难以解释的现象进行事实保全公证,同时,向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提出“世界最长怪坡”的申请。专家先后两次到现场详尽考察,对相关事实进行论证,勘察者采用观测机动车滑动、篮球滚动和水的流动情况进行实地验证,并进行了现场记录、摄像和摄影。结果证明:该坡在机动车空挡熄火的情况下,能够由坡底自动滑行到坡顶,篮球能从坡底自然滚向坡顶,水能从坡底自然流向坡顶。由此,这个神秘的怪坡,一时风靡世界,受到了科学家的重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负责人向奇台县颁发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认定该坡总长度为290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怪坡。
随着怪坡扬名四海,神奇的江布拉克如虎添翼,无数游客闻名而来,自然探秘,人生解惑……人们经过各种猜想,在种种科学解说之后,隐约发现了一种神秘力的存在——猜想地下有一个密度质量很大的未知物体。这将为下一个诺贝尔奖提供新的课题,留待后人继续探寻真相和谜底。
四
有人讲,“江布拉克”这四个字,哈萨克语为“圣泉之源”的意思;也有人说,蒙古语将它译作“水草丰盛的地方”。可是,以我之见,是哈萨克语还是蒙古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无论用哪一种语言来诵读“江布拉克”这四个字时,都为其赋予了人文气韵。“江布拉克”像一首诗!它是一首朗朗上口,独具音乐之美,富有内涵,充满理想色彩的现代诗。
当然,从严格的地理位置来看,江布拉克只是一个泛指:广义指它包括整个天山东部的冰川和山脉。东至大东沟(开垦河),与木垒山相连;西至黑沟(白杨河),与吉木萨尔接壤;南至奇台县与吐鲁番、鄯善两县市的分水岭。狭义讲,主要指奇台境内南山山区与丘陵地带。
翻看地图,有点意思。
你说天山东坡绵延数公里,大多山丘都是荒巅秃岭,呈现出焦枯的裸露状态,即便是博格达峰下的大黄山、小黄山、水西沟等处,虽有富足的矿藏,但颜色平平,毫无生机。唯独到了奇台区域,天山似乎在这里打了盹,挺着大肚皮伸了个懒腰,吐了一口清气,就悠悠那么一弯,便弯出一段绝佳风水,兜住了阅尽天风的千古冰川,抱住了奇台县境内的5个乡镇与3个团场……在这里,所有的山谷中,都流淌着溪水,九条河,自南而下,像九条巨龙昼夜不停地奔流着,把晶莹的雪水送至戈壁平原,惠及下游的农田,成为滋养20多万人的荒漠甘泉。
曾99次行脚江布拉克的一位本土作家,在一首诗的开篇写道:“蘼下山川,有河也有沟,72条梁89道湾,源头始于平顶山……”诗中所提到与此关联的地名有十几处,如一棵树、宋家梁、七户人家、开垦河、塘坊门、皇宫村、碧流河、吉布库、根葛尔、白杨河、东湾乡等。作家之所以突显这些地名,因为与水有关,与粮食有关,与神话传说有关,与历史征战有关,与当地人民富足的生活有关……意思是说,这些古老的村庄与河流似江布拉克一样的富有情趣美丽动人。即便你无缘和这些乡村邂逅,只要唇上吟咏“江布拉克”四个音节时,你也会把它和草原鲜花连接在一起,同松林湖泊连接在一起,与世间一切美妙绮丽的风光连在一起。
说到风光,年轻的江布拉克,属稀世的特殊画卷。
这里的云朵,是水汽的温柔。这里的岩崖石上,有花草的刚健。这里是前耕后牧,雌雄同体;这里能文能武,刚柔并济。它是旱漠中的绿洲,也是家畜鸟虫的最佳栖地……在这里,山有胭脂兮花有仙气,坡有线条兮谷底藏琼玉,水是山泉水,风是千年讯,随便捡一块瓦片,都有历史的重量。野人沟长虫梁的精怪,响破怪圈木笼坝的霹雳,都不足以表达游人们在此行脚的酣畅。
在江布拉克深地,有一处,叫石门子。两山之间有一座门,左山为阴面,右山为阳坡。某年天光劈射山崩地裂,石门被电光分裂开来,直立为两半成天然标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难见一点“隧道”半米不到的阴影,过石门,天地洞开,一片敞亮。
映雪灿阳下,山阴有致,松涛浩浩,一派清穆岚烟;沟底有河,水声清亮,游者只闻哗哗作响,却神龙无形清流无迹。晨阳照着绿草,四处光鲜清暖,仰头看天,碧蓝如洗,不由人神清气爽忘不了高歌一曲……环望四野,碧草青青,野花绽放,遍地的中草药散发着浓郁的气味,黄的党参,蓝的当归,绿的马齿苋,红的枸杞子,还有大黄、赤芍、贝母、满天飞的蒲公英,野椒蒿、野芹菜、野茴香、野蒜苗等野菜来不及分辨,来不及品尝。踏在轻柔的草甸上,大口大口吸气,恨不能像身旁的醉羊那般,卧在草丛里咀嚼几口香浓的青草。如果赶巧山花正开,红艳艳一片芍药,令人无法挪步。徜徉在如此郁葱的田野上,看见麦苗儿挺立,豌豆儿吐芽,苹果、杏子、桃子花谢花飞,使人在一片绿色的海洋里迷醉。
江南大学者梁某,初次来到这块草地,由于过于震惊绿色的强烈,被地上缠绕的栀子花牛蒡子绊倒,也不在乎,顺势趴在草丛里,向山坡下滚去,嘴里发出“啊啊——啊啊——”的叫声,滚到沟底,把头埋在绿草中,贪婪地汲取着草的清味,忘情地接受着草的抚慰……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转了一圈新疆,江布拉克是最能留人的地方,既有喀纳斯的松柏密林,又有伊犁草原的天然牧场,还不缺天池‘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
有位诗人,第一次看见江布拉克草原,一改平日的斯文,脱掉上衣裸着膀子在山坡上呼喊疯跑……另有一位台湾画家,来到天山脚下的江布拉克后,发出由衷的感叹:“上了天山才明白,原来古人居住的地球如此美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何等幸运,尚有如此仙境可以游玩!”
五
如果认为江布拉克之魅力,仅限于这些神奇的自然风光,那就大错特错了。
放眼世界,比此清绝撼世的美景多了去了。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江布拉克这样守一内敛,以绿的瀚海与人文乾坤独立于世,没有一座老城,像疏勒城这样被掩埋得如此宁静!
凡有风光的地方,都是有魂魄的。
然而,能感知一塊土地的历史烽烟和文化价值,需有超凡的大脑和寻古的眼光。说到江布拉克的人文山水,这要感谢薛宗正先生,在这里,透过两千年烟尘找到了耿恭抗匈奴守耕战的足印。回眸往昔,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学界对汉代疏勒城究竟在哪里争议不定。多年来,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才生薛宗正先生,始终认为石城子就是耿恭当年驻守的疏勒城。缘由是他亲自参加了奇台县第一次文物普查。当时他在中学做语文教员,天赐良机,就因为他的参与,慧眼识宝,推进了汉代疏勒城的发现和定名。
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艰苦。薛先生和另一位相伴的工作人员骑上雇来的两头毛驴,带上简单的行李、罗盘仪和廉价的照相机——逢沟进沟,见山钻山,走到哪里吃住到哪里……薛宗正把曾经学过的历史考古学知识,迅速地在脑海中清理、翻晒、整理、分析,应用到当时的工作中。一天中午,他们来到天山脚下的麻沟梁,薛先生突然从马上摔下来,屁股被磨烂,鲜血渗透了裤子,他只好趴伏在马上行进,翻了一个坡,忽然他眼前一亮,不远处几块灰色的瓦片和青砖抠着了他的眼球,他心中一惊一喜,猛地将马鞭一抽,恨不得立刻跳到瓦片面前。可是马一受惊,他身上的水壶甩起砸向头部,躲不及,三颗牙被打飞,满口流血,他顾不得这些,翻身下马,连滚带爬,捧起地上的砖瓦查看,凭直觉,他觉得那些碎在地上的砖瓦极其珍贵,便和同伴俯身拾捡,一片一片收集在一起,雇了一辆毛驴车拉回县上,回来以后,钻进史料堆里,昼夜不停查找论证,终于认定这里就是史学家百觅不得的汉代疏勒城。
薛宗正先生断定石城子为疏勒城的主要依据有五点:一是城为夯筑,明显汉代建筑;二是汉军就地屯田,解决汉朝开拓西域自供军粮的难题;三是城中出土五铢钱、铁刀、马灯、绳纹板瓦、灰陶罐等大量汉代实物;四是地形险峻,石质坚硬,傍有涧水可固,城中有穿井痕迹;五是石城子位于天山山脉的层峦叠嶂之中,北部有山路可通行,具有天然军事要塞的特点,有文献可考;另外,据点南隔天山,与鄯善柳中城相望,且有多条谷道相通,诸如今木垒的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今吉木萨尔的他地道等,而当地人都知道由石城子出发,南入夹皮山,隔山越黑涝坝,有一条峡谷崖道,叫包尔太小路,可直通鄯善这一路。
据70年代石城子看护员老赵讲,最早在这里落户的人家,在麻沟梁一带大都拾捡过散落在地上的灰陶盆、灰陶罐、灰陶瓮……因为不知道这些灰陶的价值,村人并不把这些盆盆罐罐当回事,做器具装东西的有之,当喂猪盆的有之,现在奇台博物馆展厅陈列的那些汉陶文物,基本上都是文物工作人员当时以新换旧征集来的。其中有一陶瓮,高62公分,直径30公分,口小腹大,灰黑色,不盛水,不盛粮食,也不作酿酒使用,是一件二次葬用具。《后汉书》对这件器物特殊的用途有所记载。人死后,实行土葬,随棺入土,时至肉体腐烂,重新开棺把人体的骨头捡起放置陶瓮里,将口封死,进行二次埋葬。
一直到了80年代末,麻沟梁一带还随处可见遍地散落的汉瓦碎片。甚至到了90年代,石城子四周仍然可以捡到一些汉代灰陶残片。记得有一次,我与两位文物干事黄卫东、徐华林上山巡查时,看护员老赵讲,在他家后墙边挖土时挖出一具古尸,男性,身长1.74米。出土时,奇怪地发现这男尸,铺瓦,盖瓦,尸体两边挡的还是瓦。细问,才见8块板瓦原地不动地放在墙角。走近看时,全是清一色的汉瓦,外,绳纹形;内,细布纹;长27厘米,宽22.5厘米。其中,6块完整,1块残角,1块中间有裂痕。再看,另有200多块同形的板瓦,整齐地摞在后院的墙根;我围着那一层层国宝级的文物转了几圈,想,这么多的汉瓦,完好无损地放在这里,城中又有那么多烧过的釉子,附近一定会有汉代的砖窑。又联想到馆藏文物中,有一件比石城子陶罐更为古老的器物,那是战国晚期的一口行军锅,叫青铜釜。重45公斤,高62公分,直径达半米有余,为新疆最大青铜釜。惊世于1986年夏天,出土地点正是距半截沟不远的碧流河山坡。当时工人在林区伐木筑路,一声巨响,这件青铜釜便从山崖上滚落下来,在陡峭岩石猛烈的碰撞下,战锅摔开了一个大口子,中间有了裂缝,锅边一侧卷起,半腰双耳完好无损。由此,可以推断,这块土地,在历史的烽烟中,属于铁骑与战马叱咤的疆场。
再次夯实麻沟梁石城子遗址为《后汉书·耿恭传》中所记载的疏勒城定论的,是47年以后的事了。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了长达6年的考古发掘;考古所联合国内10余家科研院所,在前人勘探的基础上,利用环境考古、电(磁)法物探、遥感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辅助发掘工作,利用碳14对出土的木头、骨骼测年后得出数据,断定石城子遗址的年代为两汉时期。“我们今年的发掘范围涵盖城门门道及内侧遗迹区,以及城西墓葬和陶窑。清理出门道1条、门墩2个、房址4间、柱洞35个、柱槽7个、排插柱20个、踏步3条、沟槽1道。从现在发掘的情况看,当年疏勒城的门道顶部已坍塌……那就是发掘出的城门,史书记载,这是汉代疏勒城唯一的城门,当年东汉名将耿恭就是站在这个城门上拒绝匈奴劝降的。”考古研究者吴勇这样说。为此,“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被定为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之一。
借疏勒城钩沉历史,是为了说明这块土地的久远与古老,凭吊疏勒城威震四方的战功,是为了缅怀麻沟梁这一片绿海深处的英雄……对于闻名遐迩的江布拉克胜境来说,如若少了耿恭守战这一章,没了这股神奇大地上的浩浩长风和雄雄铁魂,这“风景”,恐怕就单薄得只剩下风景了。
六
天风难扫千年雪,最是人间不舍心。
当我有幸再一次推开那扇宣统年间的大门时,正值麻沟梁最后一批搬迁者的最后一段日子……明天,对于这些在此生活过五辈子的人来说,关门是一个大动作,梁上的人家,都在做关门的准备,在他们关门之前,我是最后一个闯入者。
关闭了那些古旧斑驳的大门,就带走了一个时代的烽烟……然而,他们老了,身子下了山,心却不能走。拖拉机、汽车、摩托车……装满了,“突突突……”一车一车往山下搬东西,人们站在院子里,地埂上,马路边,一堆一堆,舍不得走。
看到一家家搬下山,一户户关了门,最后的收割人,把平常用的镰刀、筢子、锄头、背篼、铁锨、铲子、柳条筐等一切农具锁在一个旧的仓库里的时候,我听见一个甘肃口音的男人坐在他将遗弃的板床上,闭着眼睛唱:
民國33年来
青砖瓦房盖
一辈子终老不下山
千年的粮食吃不完……
迎着麻沟梁最后的一道炊烟,我一气儿走访了9户人家。这些即将离去的人们,一个个故事陈旧而荒蛮,一个个命运多彩而艰难,但有一点却是惊人的相似,那就是,无论是年轻的小媳妇,还是耄耋老人,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他们“最舍不得的东西是麦子”。麦子是他们的命。因为麦子,他们世世代代不求人!现在不管搬到哪里去,麻沟梁还是他们的家。
是啊!搬走了房子却搬不动土地。麦子啊麦子,金黄的麦子……它,才是这一块土地最宝贵的东西。2000年的土地,2000年的万顷良田,在海拔1700米的高山上,绵延了多少个春冬秋夏,20万亩的天山麦海,独享着世上最高、最大的麦田桂冠,属于农耕文明之辉煌。
你可见它一绿过后的千帆金浪吗?
它在神秘莫测中,千变万化,它春有春的美,秋有秋的美,冰川雪水将它浇灌,松柏密林将它守护,它气势恢宏,随山渐变,递次叠级,以9层以上的美景撼动天地。当麦子还是麦子的时候,这里的世界,是白色的!雪山雪松雪平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白色的江布拉克都在万籁静谧的沉睡中;当麦子是种子的时候,这块土地,是黑色的!黑土黑湖黑松林……整个江布拉克都笼罩在清穆的风岚之中;当麦子抽芽之后,这里的山峦,就变成了滚滚绿浪!绿草、绿树、绿山坳……整个江布拉克都成了碧绿的海洋;当麦子结穗成熟,这片绿野就变成了金色的海洋……金坡、金梁、金太阳……整个江布拉克到处都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
可是,当麦子收割归仓,唰啦啦一划,齐茬茬的麦田,便一块块、一道道梦幻般成了七彩斑斓的原野——赤、橙、黄、绿、青、蓝、紫……千沟万壑都染了颜色,整个江布拉克会在魔法师的调色盘中推陈出新,变成空前绝后的视觉盛宴。
真的,汉开西域,屯田戍边。因为如此,国泰民安。
七
在数点了黑涝坝、天山怪坡、老虎爪传奇之后,在欣赏了女性般柔美的草坡以后,在粗略地浏览过江布拉克的景群,领略了一块土地带给我们的浩浩长风、雄雄铁骨之后,在醉赏了碧波荡漾而又金光灿烂的万亩旱田之后,现在,有必要来看看江布拉克的山雕和岩刻了。
也许,远古年代,这里被圈养过的动物或者家畜太多,这里随处可以瞥见马鹿、棕熊、野猪、红狐、山羊、雪鸡的踪影。虽然时过境迁,这些曾与人共处过的山禽和动物,始终没有远去,全部变成石刻留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内。它们撒着欢,在山坡上逃奔,有的正在回头张望,有的定格在半山腰,成银鞍马镫,成军刀铁犁,有的已登高攀缘屹立山巅,或牛背牧童,或醉羊卧睡……可谓雪泥鸿爪,应有尽有。它们以变形的符号被凝固,被观瞻,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经年累月,沐浴着天风与人共处。
有疏勒城的那年
就有了金蟾
它在城南的河边
悠闲自在地嬉闹
当匈奴摇旗呐喊
如一片乌云压来
金蟾一蹦一跳
爬上山顶
咕咕……咕咕……
第一时间把信息发给哨兵
……
这首标题叫《金蟾戏月》的诗,写得很酷,属于江布拉克的点睛之笔。作者许立国是当地一位摄影爱好者,其以刀刻般的目光,洞察到了巅峰上的灵犀。那天,他做向導,带着我们走完了雄伟险峻的疏勒城。我们顺着麻沟河一路往南走,城河戒备森严,沟深百丈,河水虽不大,却潺潺有声。河宽约两米,右侧岩石陡峭,怪石嶙峋。诗人边走边现场讲解,他指着岩崖上千奇百怪的造型让我们一一辨认,孙猴王、神马奋蹄、野象观天、藏金洞、火岩浆、黑发瀑布……走了大约十来米之后,一个活脱脱的金蟾,跃然眼前。我们很是吃惊,凝视细看,趴在山崖上的金蟾,如一名侦探,神情严肃地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像潜伏了千年之久的忠诚战士,耐心地等待着援兵到来。
如此逼真、鲜活的一个“哨兵”,潜伏于悬崖这么久,为何不被世人觉察?这是寓言,还是秘籍?在通往赛尔台的路上,在马鞍山的下方,站在三道编子的岔路口,正当我冥想答案之时,忽听一声“噢哟——太宏大了!”猛一抬头,一座山雕横在面前。神奇!一幅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幅驼雕。
那是一个自东向西,浩浩荡荡的万峰驼群。
头驼昂首挺胸,腾云驾雾,从雪堆中伸出一张庄严俊美的脸,它眉目清晰,气宇轩昂,君王般的额头一半埋在千年积雪里,挺直的鼻梁上一双深目注视着前方……它的目光,笃定沉稳,它的神情庄重深邃,它昂首阔步,目不斜视,时而安静,时而雄壮,时而引颈仰天嘶鸣……它的步态坚定踏实,它的脖子在积雪的覆盖之中,整个身子都镶嵌在冰雕深处,总体感觉是,它背着一座大山,傲然挺立在西域古道的雪域山巅。
可是,它身后紧紧地跟着一支驼队!
那些大大小小的驼峰,排着长长的队伍,由远而近地来了。好似沙漠里的驼舟,一群一群,此起彼伏,没有间断,个个儿坚忍不拔,一寸不离地跟着头驼缓缓前行。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谁曾想到一座山脉,也会养育出与此匹配的奇珍神兽。这些山雕崖刻,惟妙惟肖,土生土长。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看,总有你想看到的东西。正如诗人周涛看博格达峰一样,当它是蓝袍镶金,白帽抹红,英俊伟岸,傲视众雄的少年。
这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疏勒城的金蟾也好,耿恭的雕像也好,赛尔台的驼群也好,都是千年遗物,铁石的语言,不朽的标志。这些皆为江布拉克的秘藏珍宝,它们以远古主人的身份在这里静候着,以顽强的姿态翘首眺望,期盼着一个鼎盛时代的重新复活。
[栏目编辑:韩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