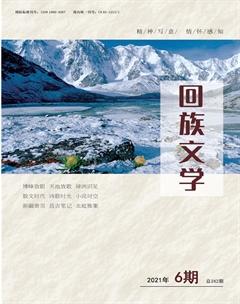高原松
李晓林

记忆是个非常难以捉摸的美妙东西,它会让某些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去,又让某些往事活生生真切切地涌现在眼前,不停地闪现、升腾,让你回味,让你念想。
比如,在我戍边的岁月里遇到的一棵小松树,直到今天,仍然凝固在记忆中,以至于现在只要看到手机里有高原雪山的照片或视频时,脑中便能闪现出那棵松树的雄姿。不禁感慨,它要是存活的话,说不定和现在高原上的其他树木一样,也会长成又高又粗、令人仰慕的参天大树了,说不定还可能是高原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呢。
1986年7月,我到团里俱乐部开会,在门外等候的时间里,突然发现,在俱乐部进出口处有一棵身材瘦弱、腰杆笔直的松树。起初,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等我走到树跟前再细细辨认时,顿感惊讶,没错,就是一棵松树。我围着这棵松树走了一圈,轻轻抚摸着它粗涩枯硬的树皮。细细打量,树高有一米六的样子,树干有十公分粗,树枝矫健强悍,一层一层向四面舒展,绿叶婆娑,如尖如针,上面落有淡淡的尘灰,有种非凡的性格与精神,显示着一种坚强不屈、不怕困难打倒、不怕严寒侵袭的气势。来到帕米尔高原时间不长的我,如发现了宝贝似的兴奋,看得极其认真,心中疑惑,风雪帕米尔高原还能栽活松树?它是哪一年栽下的?
之前,我到过潜藏凶险的喀喇昆仑山,又去过西藏阿里高原的大部分哨所。应该说,西部地区海拔最高、最险的生命禁区边关哨所大都去过,见到过不少在空旷戈壁滩、草场边上成片或零星孤独生长的树,也见到过代代官兵在哨所门前栽下的或大或小的树,它们全都是经得住狂风肆虐、受得了寒冷折磨的柳树、杨树、沙棘树等。今天,在帕米尔高原上见到了一棵松树,且从树龄长势上看,至少在高原上落户有十年以上,对于走过高原边关许多地方的我来说,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这棵松树一看就知道不是天然长成的,它应该是老一代戍边官兵亲手栽种的。常识告诉我,俱乐部跟前应该不只栽下一棵松树,一定还会有的。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再次来到俱乐部,我四处不停地寻觅,寻觅,终于又发现了一棵松树,它位于俱乐部的另一出口,只不过,它因缺水和高原气候的肆虐,不知道在何年何月枯死了,留下了劲风雕刻后的坚硬赤裸根部和给它浇水用的圆形蓄水池痕迹。再巡视四周,离它不远处,有一排乱石垒起的水渠,水渠边上有大小不一十多棵白杨树,整齐挺拔,旺盛地成长着。这些白杨树和松树应该是知己,有着共同的理念,同属兄弟,相互陪伴着、衬托着。我便给那棵活着的松树起了一个令人鼓舞又好记的名字——高原松,这个称呼,对它来说,感觉最贴切不过了。
高原松,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子里了,直至如今,总是难忘这个名字。
树,对于山下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城市里,山野中,随时都可能见到,但对于常年生活在没有任何花红草绿的荒凉世界里的人来说,那就是一种追求与奢望。试想,一个人,生活在四季冰天雪地、缺氧寒冷孤独的世界里,看不到绿色,见不到树林,那種肉体上、精神上的隐隐折磨,是多么痛苦,多么煎熬,于是,有树的地方,成了高原上最美丽、最向往的地方,也成了高原上人们的一种信念、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寄托。
20世纪的帕米尔高原,气候十分恶劣,空气稀薄,氧气不够,山高水冷,冰雪为伴,一年四季,常常是送走风雪,迎来严寒。栽树,是那时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军民每年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听老高原们讲,当时的塔什库尔干县十分荒凉,全县城里看不到几棵高大旺盛的绿树,原因是当年栽下了强壮的树苗,寒冬一过,第二年春天,好多树苗都被严寒摧残夭折。即使这样,全县各族军民仍然信念执着,绝不放弃,每年的三四月份,仍要进行声势浩大的植树劳动。部队营区大院内也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为了营造一个美好的营区环境,一年又一年,官兵们像养育儿女一样精心地栽培着每一棵树,倍加照顾,每日每时,心心念念。
俱乐部建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背后是平缓的戈壁石小山,大家称它为后山,意思是后面的山。正前方是团部办公楼,左右两边是连队。俱乐部处在团部院内最中心的位置,是团里官兵集会最多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是当时团里重要活动的“打卡地”。选择在这个地方,专门栽下两棵松树,足见当时决策者的远见卓识。我猜想,那一定是要求守卫在这里的官兵们,要像松树一样,战高原,抗严寒,迎风斗雪,时时保持着一种坚韧不屈的品格,艰苦奋斗,奉献自我,安心守边。
松树是从哪里挖来的?哪一年官兵们栽下来的?怎样在没有多少土壤、没有多少水分的戈壁上,奇迹般生根发芽、生长起来的?这些疑问不曾见任何记载。我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喀什到部队所在地有近三百公里的路程,汽车上山要走两天时间,高原上不可能生长松树,树一定是从山下挖出运上来的。我曾试着从那些兵龄长一点的干部中打听有关高原松的消息,从团队职工中打听高原松落户的时间和发生在它身上的有关故事,然而,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令我失望与遗憾。后来一想,高原松在什么时间栽下、谁栽下的,其实对于今天的官兵来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在于当下,如何把它呵护好,让仅有的一棵高原松茁壮成长,再不能被无情的恶劣的高原气候所残害。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无限护卫它,用心灵去亲近它,定期给它浇水,给它赋予“血液”与能量,关注它每月的生长变化。就这样,在此后的岁月里,高原松静静地面对川流不息的时光,时刻展现着无穷的力量,孤单地生长着,日复日,夜复夜,狂风吹不倒它,严寒冻不死它,缺氧无情折磨它。而我们呢,每天都迎着旭日东升的阳光在它身边走过,出操、训练,进进出出到俱乐部里看电影、听英模事迹报告,迎接新兵、欢送老兵……
高原松,它成了生活在这里的军人们敬仰的生命神树、精神象征树。每次,官兵们路过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它的身姿,情不自禁地向它投去深深的敬意目光,行一次注目礼,以此小小的举动来感谢它的存在和鼓舞。官兵们讲,每看一眼,树身上那种峥嵘风骨,遇强则强、四季常青的品格,令戍边男儿血脉偾张,激情澎湃。
高原松,是高原上一棵稀世珍贵树。我曾利用执勤、下工作组等机会,走遍了帕米尔高原边关一线哨所,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松树生长,也没有听到官兵和附近驻地的牧民讲到别的地方有松树的存在。我断定,在整个帕米尔高原上水草富足的牧区,部队的哨所营区,这棵看上去不太显眼的松树,一定是高原上唯一的一棵松树了。
高原松,是帕米尔高原上最闪亮、最令人敬佩的一棵树了。无论是狂风劲吹的春天,还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无论是秋风扫落叶的秋天,还是大雪压雪山的冬天,它都是昂首挺胸,笑容面对。狂风来了,其他的树枝被吹得摇摆不定,难以支撑,而高原松却始终顽强挺拔着,看不到丝毫摆动。假如夏季有一场大雨飘过,它的枝叶显得更加郁郁葱葱,令人喜愛。记得有年冬季,高原上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雪,整个高原顿时白茫茫一片。高原松披着片片洁雪,枝干中闪耀着苍翠的绿色,如岿然不动的哨兵一样,默默地站立着,显得那样伟大,那样自信。此情此景,陈毅元帅“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陡然在我脑中闪现,感觉在这里诵读这首诗,更能体会到它内在的品格。
年复一年,我同这棵高原松度过了七个春秋,看着它经历春夏秋冬,看着它渐渐成长。
后来,我调到山下,离开高原,但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棵松树,每每上高原,再忙都要抽出时间去看看它的长势,更多的时候是站在松树身边,静静地看着。我不知这棵松树身上有多少年轮,有多少道纹路,我不知有多少戍边军人从它身边走过,它记录了多少动人的戍边故事。
他叫帅佳宏,四川乐山人,1997年4月出生,2017年9月入伍来到帕米尔高原海拔4300米的克克吐鲁克边防连,2021年7月7日,在雪山执勤中突发心源性休克,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他的灵魂永远融入了雪山,长眠在风雪边关。他站立成为雪山,倒下成为江河,升起成为星辰,飞翔成为骏马。他是帕米尔高原上永远挺拔的“高原松”。
时光荏苒,又是一年夏季时,退出现役的我来到帕米尔高原,抽机会到了团部大院,想看看那棵高原松还在不在了。
陪同我的是一位营职干部,在高原上戍边已经十九年了,他身材消瘦,面孔黝黑,热情地带我到营区内参观,之后又把我带到团部家属院后面原来的菜地上,指着两棵白杨树说,部队营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高原松生长的地方,已被新建的连队宿舍代替了,现在只有这里的两棵白杨树是老树了。
我走上前去一看,直径约有一米的两棵高大白杨树上面,悬挂着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戍边杨。看到此牌子,怀念与感想,回忆与旧梦,在心中时时萌生。这两棵白杨树,20世纪80年代,我在此戍边时就生长着,现在算来,两棵白杨树至少有四十年以上的树龄了,应该是历史中的白杨树了,也是官兵们的心灵之树。
我站在那里久久地仰望,多么想在这里留下属于我的情感符号,但我却没有任何刻刀。我只能凝视着它们,期望它们记住我投射于它们的目光,相信我同守卫这里的人一样,也曾经是它们的伴侣,对于它们有着同样的真诚与依依不舍的情感。
告别团部,我驱车来到了位于慕士塔格峰下面的卡拉苏连队。我跟随蹲点的雷营长一起走进连队的蔬菜大棚内,眼前的景色令我大开眼界,大棚内有长势喜人的西红柿、茄子,还有西瓜,它们个个亲吻太阳,根须伸进了缺氧贫瘠的土地,长出了丰实的躯干和繁茂的枝叶,结出了喜人的果实,为高原增添了一种别样的快乐。二十年前,为了在这块贫瘠、寒冷的土地上种出绿色蔬菜,官兵们想了不少办法,下了许多功夫,都被冷酷的恶劣自然环境打败了,如今,奇迹终于在这里出现了。
走出蔬菜大棚,眺望对面巍巍雪峰,一阵寒风吹来,我的心忽如打开了一扇窗户,顿时明白,当年我所见到的那棵松树虽然不在了,但其精神早已渗入到戍边人的血液中去了,化作无形的参天大树,矗立在风雪高原,守卫着祖国的边关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