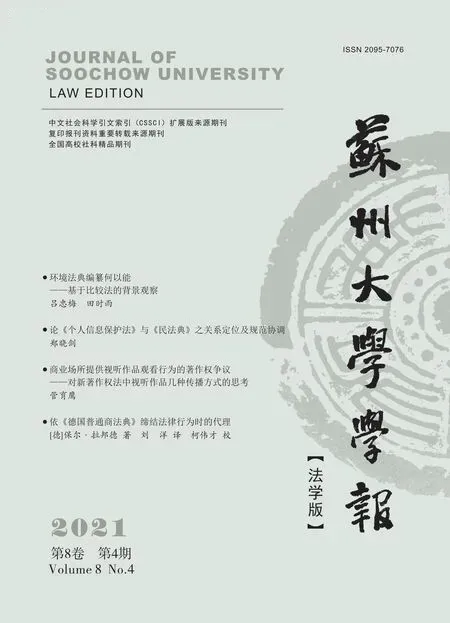象征性刑事立法:概念、范围及其应对
陈金林
一、问题的提出
频繁的刑事立法活动将我们带入了刑事立法学的时代,检验立法的正当性并对不具有正当性的立法进行批判,已经成为理论界的重要使命之一。将特定条文定性为象征性刑事立法,是一种流行的立法批评方式。不过,就哪些条文应被归入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范畴,学界的观点相去甚远。刘艳红教授将恐怖主义犯罪、网络犯罪与环境犯罪作为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典型代表,同时认为虚假破产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等其他十几个罪名也属于象征性刑事立法。(1)参见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45页。程红教授则认为前述批评过于宽泛,主张象征性刑事立法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领域,其典型例子是虚假广告罪。(2)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26页。不过,在判断方法上,两位学者则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即都将条文对应的判决数作为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决定性标准。对此,张明楷教授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将适用的频率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认定根据,不能将司法的问题归责于立法,将前述犯罪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观点不能成立,(3)参见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5期,第158-159页。由此形成了对这种立法批评模式的反批判。贾健则不仅不认同前述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方法,还表达了与其完全对立的立场,认为有必要在一定条件下肯定象征性刑事立法。(4)参见贾健:《象征性刑法“污名化”现象检讨——兼论象征性刑法的相对合理性》,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第67-79页。
面对理论上的纷争,有必要追问:批判象征性刑事立法是否还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实践意义?如果是,应如何划定其边界以防止批判过于泛滥并伤及“无辜”?对于象征性刑事立法,我们应采取何种应对之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回顾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弄清其初衷及其在今天的意义,从多个维度对象征性刑事立法进行精确定义,确立其认定标准,指出当前理论界对它的误用,并结合我国刑事立法指出其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提出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应对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方案。
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文章在以下几方面有创新之处:第一,明确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判断重心是立法的机能,并从法益保护缺位和“象征”的欺骗性效果两个层面确立其判断标准。第二,重新划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范围,根据其产生原因(即欠缺适格的法益、法益侵害归因错误、违背刑法的作用机理)对其进行类型化,指出我国刑法中容易被忽略的象征性刑事立法。第三,提出应对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具体方案,包括在立法中直接或间接提示法益,对法益侵害作精准归因,尊重刑法的作用机理;在司法层面,以批判立法的法益为指导,通过补充构成要件要素等方式限制或架空象征性刑事立法。
二、象征性刑事立法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一)象征性互动理论对立法价值构造侧面的揭示
对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探讨,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社会学理论“象征性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它通过对人行动规律的揭示,动摇了启蒙主义以来有关刑法的基础性假定:判断犯罪的标准是客观的;刑法受目的理性的指导,其任务是通过预防犯罪实现法益保护这种经验性的目的。在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学家Cooley、Mead等人于20世纪初勾勒了象征性互动理论的雏形,并由Blumer等人在20世纪中叶继承和发扬,由此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5)Vgl. Christopher J. Schreck, ed., The Encyclopedia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Justice, Vol. 2,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p. 855.该理论认为,人同时生活在物理和象征性环境中,两者都能给人行动的激励。象征通过其意义和价值(对应于物理环境对人感官的刺激)对人产生作用,个体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学习象征的意义和价值,并在互动的过程中定义他人、定义自己,同时被他人定义,由此形成自我观念并据此行动。(6)See Arnold M. Rose, A Systematic Summa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in Arnold M. Rose, ed., 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Proces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Routledge, 1962, pp. 5-11.
象征性互动理论揭示了意义赋予对社会分析的价值,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人们相信什么而不是事实上是什么。据此,所有的人类行动,包括对犯罪的定义,都是主观判断的结果。从象征性互动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犯罪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认为,越轨行为是人们标定为“越轨”的行为,越轨者就是被成功贴上了这种标签的人。(7)See H. S.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Free Press, 1963, p. 9.既然如此,为了获取犯罪或越轨行为的全部图景,就不能只关注犯罪人及其特征,而是必须同时揭示社会对违规行为的反应。人们贴给他人的标签,也会影响被贴标签者的行为,后者会将这种标签内化,并选择与其相符的行为方式。(8)See S. Kobrin, Labeling approaches: Problems and Limits, in J. F. Short, ed., Delinquency, Crime,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 245.
象征性互动理论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标签理论原本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其初衷是为了全面揭示犯罪定义的过程及其对被定义者产生的影响。当然,这一描述性的理论也必然会带有政策性启示:第一,基于象征性符号的负面效果,国家应慎用越轨者和罪犯等标签。第二,有必要对犯罪定义过程也即刑事立法进行反思,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社会学家Joseph Gusfield有关禁酒令的研究,他通过历史考证指出,美国禁酒的法令并非是为了追求工具性的目标(instrumental goals),而是一种象征,是其支持者确认、捍卫其社会和政治优越性的方式。(9)See Joseph Gusfield, Symbolic Crusade: Status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 University of Illinos Press, p. 166.而这一研究,也直接启发了德国刑法学界。
(二)德国刑事立法学对法益保护原则的捍卫
德国学界对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反思与批评,是在捍卫刑法目的理性(通过预防犯罪实现法益保护)、反对无节制的理念性建构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1973年,德国法学家Peter Noll出版了其有关刑事立法的专著,该专著以提升立法的理性为其核心目的之一,因此Noll特别强调立法的有效性,要求确保作为立法结果的规范是实现立法目的的适当工具。象征性立法是作者看来不能满足有效性要求的立法形式之一,即自始即不追求事实上的有效性(faktische Wirksamkeit)而是以其颁布实现其他社会效果的立法。(10)Vgl. Noll, Gesetzgebungslehre, 1973, S. 157.此后,Monika Vo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象征性刑事立法展开了系统性研究,指出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本质是对事实性问题(Sachproblem)的情绪化(Emotionaliesierung)处理,她主张以法益保护、比例原则、经验性检验等方式控制不可欲的象征性立法。(11)Vgl. Voß, Symbolische Gesetzgebung, 1989, S. 4 f.在此之后,Hassemer通过其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将象征性刑事立法置于“现代”刑法的大背景之中,认为象征性刑事立法是指隐性机能(latente Funkitionen)超过显性机能(manifeste Funktionen)的规范,而规范的显性机能是指通过规范适用来规制具体的行为以实现法益保护这种客观效果。Hassemer希望通过对象征性立法的批判,捍卫古典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12)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6.由于Hassemer强大的学术影响力,象征性刑事立法迅速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批判性标签,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立法批判的实践中。
可见,在德语法学圈,作为批判性标签的象征性刑事立法,是以结果导向和犯罪预防这一基本假设为前提的。只有在世俗、工具(instrumental)属性还是刑法的主旋律时,象征性刑事立法才能被作为一种例外的病理性表现成为批判的对象。批判象征性刑事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刑法在法益保护这一经验、目的理性的轨道之内。正如Hassemer指出的那样,只有刑法的正当化依赖于外部产出之时,才有批判象征性刑事立法的余地;对于只看输入而不问产出的刑法,象征性立法自然不会成为问题。(13)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7.
(三)小结:象征性刑事立法的两个侧面
象征性互动理论和德国刑事立法学,分别为象征性刑事立法提供了一个判断面。象征性互动理论以描述性的研究揭示了其积极面,即刑事立法所具有的规范性价值建构(“象征”)属性,这是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表象特征;而德国刑事立法学则以规范性批判的方式指出了其消极面,即象征性刑事立法不具有经验事实层面的法益保护机能,这是象征性刑事立法应被批评的质的属性。象征性刑事立法是这两个侧面的融合,忽略、误解其中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将导致这一批判性概念的误用。
当然,为了避免其误用,只确立其积极和消极面依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以这两个侧面为基础,进一步对其进行细化,以系统性地确立其判断准则。正如Hassemer指出的那样,象征性刑事立法并非一个不具有破坏力量的分析性概念,而是一个具有规范意义的战斗性术语,因此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14)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6.而这自然以一个精确的定义为前提。
三、象征性刑事立法的精确定义
对于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认定而言,判断重心、判断标准和程度把握,这三者具有关键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严重分歧。
(一)判断重心:立法过程、机能还是适用结果
不少学者将判断的重心放在立法过程上,尤其偏重立法过程中的立法目的。例如,根据Krems的观点,如果立法只是为了对规范作申明(Deklaration der Normen),只是为了让社会大众形成合法与不法的意识,而非影响个人的行为取向,这种立法就是象征性立法。(15)Vgl. Krems, Grundfragen der Gesetzgebungslehre, 1979, S. 34.希尔根多夫也在立法动机层面界定象征性立法,认为象征性立法的本质在于立法者通过刑法措施“营造一种积极性的印象,而不必承认它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16)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Newig明确提出要区分象征性立法(行动)和无效的立法,并在立法行动意义上界定象征性立法,认为它是“可预期”的实质法效很低、政治-策略性效率很高的立法。(17)Vgl. Newig, Symbolische Gesetzgebung zwischen Machtausüb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r Selbsttäuschung, in Cottier/Estermann/Wrase (Hrsg.), Wie wirkt Recht?, 2013, S. 304 ff.在我国大陆地区,刘艳红教授也更多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象征性立法的概念,她认为象征性立法更多只是“为了”表达立法者的某种姿态与情绪、态度与立场。(18)参见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36-37页。也有学者结合立法者的主观态度和立法的动态过程界定象征性立法,认为其目的是政治性的,希望借助立法增强执政信心与民众安全感,树立国家消除危险、保护人民的正面形象,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甚至直接排斥立法实效,且立法过程欠缺理性,在未经缜密考察论证之前仓促立法;只要立法者考虑了“实际效果”,就不再是象征性立法。(19)参见郭玮:《象征性刑法概念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第98页。
另一种观点将判断的重心放在立法的机能之上。例如,Hassemer反对将象征性立法建立在任何跟态度(如目的或意图)相关的要素之上而应建立在“客观的机能”之上。他认为,具有批判意义的象征性刑法是指潜在机能超过显性机能的规范。其中,显性机能是指法益保护,而其潜在机能则是多种多样的。(20)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5.
还有部分观点将象征性立法的判断重心放在立法适用的结果之上。刘艳红教授以环境刑法并未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由,将其归入象征性刑事立法。(21)参见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43页。程红教授也以虚假广告罪对应的规范未能有效限制虚假广告为由将其归入象征性刑事立法。(22)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26页。
考虑到批判象征性刑事立法的目的与意义,应将立法的客观机能作为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判断重心。批判立法并非是为了谴责立法者,立法者作为一个模糊的集体,无法承担责任,也不会从批评中感受到压力。好的制度是进化、优胜劣汰而非立法者刻意设计的结果,(23)[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立法的功能远比动机与过程重要。因此,对立法动机或过程的批评并无实践价值。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识别,只能以规范的客观机能为重心,这种安排有助于识别值得改进的法律并对其进行完善,同时避免将法律适用的责任归咎于立法。
这样一来,就不能将追求象征性价值的立法动机作为认定象征性立法的根据,也不能将保护法益的动机作为否定象征性立法的根据。此外,特定的法条是否属于象征性刑事立法,也可能随时间和社会条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曾经的象征性立法可能会变成具有法益保护实效的立法,曾经具有法益保护实效的立法也可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变成象征性刑事立法。
(二)判断标准:实质与形式
1.实质:法益保护机能的缺失
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实质侧面,是法益保护机能的阙如。为了精准判断象征性刑事立法,有必要厘清刑法保护法益的机制。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以如下假设为前提:立法者将事实上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作为犯罪写入刑法,为其配置法定刑,并通过民众对刑法的遵从、司法机关对刑法的适用来防止法益侵犯。从这一假设中,可以解析出法益保护机能的两个必要前提和两种选择性的作用方式。
前提I:存在明确的法益以及该法益被侵害的事实或风险。
前提II:对法益侵犯的事实有准确的归因,即在经验上明确究竟是什么行为在侵犯法益。
作用方式I:单纯通过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抑制犯罪,从而保护法益。这种作用方式无须借助现实的判决。刑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法益而不是惩罚本身,因此这种作用方式是最为理想的法益保护方式,“刑期于无刑”就是在传达这一理念。
作用方式II:通过刑法的现实适用,借助于刑罚的特殊预防或一般预防效果预防犯罪、保护法益。这种作用方式有赖于对已发生的犯罪作出判决(定罪量刑),因此,判决数只是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一种征表,而不是其认定的标准。在第二种作用方式中,需要结合特殊预防、一般预防的基本原理判断立法对法益保护的作用。一般预防的效果受惩罚概率和刑罚严厉程度的影响,且前者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后者,刑罚的严厉程度则具有很高程度的可替代性。(24)参见陈金林:《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35页。换言之,为了提高惩罚概率而削弱刑罚的严厉程度,能提高法益保护的水平,因为前者对预防效果的影响力度更大。
2.形式侧面:作为一种价值建构的“象征”
有关“象征”的界定,当前理论界多以消极的方式展开,即它不是什么或者是什么的对立面,例如“不确保规范的执行”“不具有带来改变的能力”“立法现实效果的对立面”或者“其法益保护机能只是一种‘伪装’”。(25)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5.但仅从消极层面界定“象征”,无异于放弃这一要件,因为它不过是前述实质侧面的重复。实际上,并非任何没有法益保护机能的条文都能被归入象征性刑事立法。例如,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也不再具有法益保护机能,但很显然,它不属于象征性刑事立法。因此,从积极层面界定“象征”是不能回避的任务。
Amelung曾尝试积极地为“象征”赋予实质内容,即立法者的“面子”(Prestige)。(26)Vgl. Amelung,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und Strafgesetzgebung, ZStW 1980, S. 54.但这一限定显然过于狭窄。从语源学的角度分析,“象征”是指代表、指示另外一件事物的东西。在社会科学领域,象征被分为具象型象征(elaborating symbols)和浓缩型象征(summarizing symbols)。其中,前者是描述性的,仅具有指代的功能,如Horatio Alger对美国梦的具象化;后者则具有整合能力,能引发特定的情绪,且其意义通常被绝对化,不接受任何质疑,如国旗、十字架等。(27)See Sherry B. Ortner, On Key Symbols, 75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338, 1339-40 (1975).象征性刑事立法中的“象征”应属于第二种,它具有基于情感要素的整合能力。这也符合象征性互动理论对“象征”的理解,即价值建构与认同。象征并非某种有经验事实根据的东西,而是因为人们“相信”被赋予意义并获得支持的特定目的。正是因为它的这一特性,象征性刑事立法具有高度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能在法益保护缺位的前提下为刑事立法赢得拥护。至于“象征”的具体呈现形式,则可能是多样的,包括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认同的价值、道德或情感,或者立法者回应社会问题或民众诉求的姿态,甚至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真挚但却无效的保护法益的努力。
(三)程度把握: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
象征性互动理论指出,象征性是所有政治活动的固有属性。Hassemer也认为,刑法的象征性不是有和无,而是多和少的问题,对于象征性立法,找不到一个确定的质的标准,只有量的标准。(28)Vgl. Hassemer, Das Symbolische am symbolischen Strafrecht, FS-Roxin, 2001, S. 1016.不过,为了避免立法批判过于泛滥,必须区分作为刑法普遍属性的象征性与值得批判的象征性刑事立法。为此,Hassemer区分了具有批判潜能的象征性刑法和“沟通性刑法”,(29)Vgl. Hassemer, Das Symbolische am symbolischen Strafrecht, FS-Roxin, 2001, S. 1011.后者是指在保护法益的同时也能实现其他沟通性目的的刑法。与此类似,程红教授区分了刑法的象征性和象征性刑法,认为前者是刑法的当然属性,后者才是值得批判的对象。(30)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26页。问题是,如何区分两种概念?就此,存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两种立场。
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只要立法的象征属性超越了法益保护属性,即可成立象征性刑事立法。例如,Hassemer认为,只要刑法的隐性机能超过了其显性机能,即可将其认定为象征性刑法,而对于法治国家的刑法而言,其显性机能只能是法益保护;而隐性机能,则是涉及欺骗、伪装的观念性内容。(31)Vgl. Hassemer, Das Symbolische am symbolischen Strafrecht, FS-Roxin, 2001, S. 1017.德国学者Newig也是相对主义的代表,他以坐标图的方式呈现了象征属性与法益保护属性这两个变量与立法分类的关系:其中,蓝领性立法是指在法律-实质效能高而象征性-政治效能低的立法,它承担了大量“蓝领性”任务,却未获得多少象征性-政治声誉;文件性立法则是指为了贯彻某种文件(如国际条约)的要求制定的、法律-实质效能与象征性-政治效能都不高的立法;整合性立法是指两者都很高的立法;象征性立法则是法律-实质效能低但象征性-政治效能高的立法。(32)Vgl. Newig, Symbolische Gesetzgebung zwischen Machtausüb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r Selbsttäuschung, in Cottier/Estermann/Wrase (Hrsg.), Wie wirkt Recht?, 2013, S. 306.

图1 象征性立法与其他类型立法的关系
但该观点缺乏可操作性,象征属性和法益保护属性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很难进行程度的比较,即便要比较,最终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价值权衡。
与此不同,绝对主义的观点认为,象征性刑法是除了象征之外别无任何其他意义的刑法。程红教授持这种立场。(33)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23页。不过,既然象征性是所有刑法的必然属性,就必须为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形式侧面确立量的标准,否则,所有缺乏法益保护机能的立法都将被归入象征性立法的范畴,“象征”本身就丧失了意义。在缺少法益保护机能的刑事立法中,象征性刑事立法的独特之处在于象征的“欺骗”属性——一定范围内的价值认同掩盖了其在正当性上的瑕疵,因此它能在缺少法益保护机能的前提下获得事实上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在程度的把握上,应采用以绝对主义为基调的综合标准。象征性立法的成立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没有法益保护机能;第二,象征属性欺骗性地掩盖了其正当性的不足。
综上所述,象征性刑事立法可界定为完全没有法益保护机能仅以价值认同为存在根据的罪刑规范。
四、象征性刑事立法批判的误用、质疑及其回应
在精确界定象征性刑事立法后,理论界误用该概念的原因以及质疑该立法批判模式的缘由也就清晰起来了。
(一)象征性刑事立法批判的误用
1.片面强调象征性刑事立法的积极面及其认定的表象化
如前所述,价值追求只是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表象。片面地强调其表象侧面,容易导致象征性刑事立法认定的表象化,从而将所有具有价值构造特征(如回应民众诉求)的立法都认定成象征性刑事立法。
德语法学界曾将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表现形式细化为以下四种:(1)立法式的价值声明(gesetzgeberische Wertbekenntnisse),例如有关堕胎犯罪的立法;(2)具有(道德)呼吁性质的立法(Gesetze mit (moralischem) Appellcharakter),如旨在提升国民环保和生态意识的环境刑法;(3)立法者的替代性回应(Ersatzreaktionen des Gesetzgebers),即未准备付诸执行的立法(Alibigesetze)和危机法(Krisengesetze),例如为了平息公众恐惧和愤怒的反恐法;(4)折中式立法(Kompromißgesetze),如在立法者经过艰难的角力之后为满足“行动需要”而制定的不决定任何事项的空条款。(34)Vgl. Voß, Symbolische Gesetzgebung, 1989, S. 25 ff.但实际上,这里列举的形式对于象征性立法的认定仅具有“征表性意义”(indizielle Bedeutung),其批判性资格(kritische Qualität)应是法益保护机能的缺失,(35)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6.而非这些表象。前述类型中所附的例子,如堕胎罪、环境刑法、反恐法,原则上都有对应的法益,其处罚的行为与法益之间也不缺乏最低程度的关联。国内部分运用象征性刑事立法进行立法批判的学者,更多是在看立法是否符合前述表象,是否在回应公众诉求,而不是用精确的定义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36)例如,刘艳红教授认为,我国有关恐怖主义犯罪、网络犯罪与环境犯罪的立法是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典型代表。参见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45页。
2.对象征性刑事立法消极面过于狭隘的理解
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消极面也即质的属性是法益保护机能的缺失,不过,如前所述,法益保护机能的作用方式有两种可选择的方式。而我国学者在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时,既没有详尽地分析法益保护机能的实现机制,也没有厘清立法和司法之间的责任界限,而是直接以判决数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尽管有罪判决是刑法保护法益的常用方式之一,但它既非刑法法益保护机能的全部图景,也并非其必要环节。将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认定标准限定于司法判决,既可能导致象征性刑事立法批判的泛化,也可能导致立法者和司法者责任的错乱,(37)参见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5期,第158-159页。更有甚者,这种认定方法可能催生一种错误的政策性主张,即用无意义的司法判决掩盖原本已经无意义的象征性刑事立法。
前述误用既可能忽略真正的象征性刑事立法,错失必要的立法批判,也可能导致象征性刑事立法批评的泛滥。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概念,一旦被滥用,就会损及自身的批判效力,会遭受反批判,直至引发逆反的心理,转而支持象征性刑事立法。
(二)对象征性刑事立法批判的质疑
肯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观点认为,立法彰显国家价值观、回应民众内心的不安具有正当性,因为在后传统社会,道德评价标准被金钱、权力等象征性符号以及专家系统的权威所取代,可以让刑法扮演信任重塑和秩序整合的角色,对背离重要社会共识以及引发民众强烈不安和焦虑的行为,有必要规定为犯罪。(38)参见贾健:《象征性刑法“污名化”现象检讨——兼论象征性刑法的相对合理性》,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1期,第75-79页。根据这种观点,即便与法益保护没有直接关系,只要具有象征性价值,也可以进行刑事立法。在严格限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前提下,肯定它就意味着放弃法益保护原则。问题是,放弃这一基本原则的理由是否充分?放弃这一原则是否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首先,并非任何道德观念都值得维持。在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传统道德确实面临着挑战,也确实曾出现过用刑事立法捍卫道德的立法实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在规范上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追求。例如,有关忠贞、性风俗的传统道德观念就曾屡屡遭受挑战,也确实曾在某个时间段给部分民众带来了焦虑和不安,但结合跟性相关的观念演变史不难发现,这种观念自身也发生了转变,部分民众曾经的焦虑也已经逐渐消散。既然如此,为何要用刑法来维持这种观念,而不是让其朝更多元、宽容的方向发展?
其次,即便特定的观念确实值得维持,也未必需要动用刑法,象征性的内容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实现。象征性刑事立法也是一种刑法,在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对国家刑事司法资源的消耗上,它与普通刑法完全没有差别,它的独特之处“只是”缺乏法益保护机能。因此,谦抑性原则也当然适用于象征性刑事立法,在其他手段足以实现象征性目的之时,刑法就不应介入。就此,Roxin教授曾结合《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第3款的规定予以阐释:德国希望借此强调自己对纳粹暴行的承认,表明自己在“二战”后已经得到了净化,变成了维护和平、注重少数群体保护的国家。这当然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精神,但无论是表现还是贯彻这种精神,刑法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手段,除非刑法必不可少的法益保护与其同时存在。(39)Vgl. Roxin/Greco, Strafrecht, AT, Bd. I, 5. Aufl., 2020, S. 47.
最后,象征性刑事立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焦虑或不安。象征性刑事立法只是呈现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欺骗性外观,它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延缓甚至阻碍人们探讨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刑法是国家能够采取的最严厉的手段,象征性刑事立法一旦被用来应付某一问题,就会营造出这样一种假象:国家已经为这个问题穷尽了一切手段,如果刑法都没能解决,那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民众也会逐渐接受现状。但事实上,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通常也存在刑事立法之外的解决方案。
因此,对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批判,是一种绝对不能放弃的使命,当然,这种批判必须以严格限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范围为前提。
(三)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范围及其类型化
根据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定义,尤其是结合刑法法益保护机能的前提及运行机理,可以将象征性刑事立法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可以在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中找到例证。
1.因为不存在适格的法益而出现的象征性刑事立法
法益以现实的基底为前提,只有受因果法则支配的、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才能成为法益,道德、意识形态等纯粹理念性的构造不是法益。(40)参见陈金林:《现象立法的理论应对》,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478页。法益是与依靠规范建构而产生的“象征”完全对立的概念。因此,如果特定的条文事实上是在保护规范的构造物,它就不是在保护适格的法益,应被归入象征性刑事立法。
刑法中保护道德的罪刑规范,至少在通常理解的意义上,是这种类型的象征性刑事立法,其适例是聚众淫乱罪和组织卖淫罪。当前,通说的理论认为这类犯罪的犯罪客体或法益是“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41)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46页。“公众对性的情感,尤其是性行为非公开化的社会秩序”(42)张明楷:《刑法学》(下)(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3页。或“众人不得在一起进行聚众淫乱的性风俗”(43)黎宏:《刑法学各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页,第477页。。但这些内容都是一种价值论上的构造,是一种多数人认同的性观念,不具有现实的基底,因此不满足成为法益的基本前提。而且,以此为法益,也很难解释为什么直接参与性交易的行为人反倒不构成犯罪,因为他们才是前述风尚、情感或风俗的直接破坏者,组织卖淫的人只是外在的协助者。正因如此,已经有不少学者呼吁废除聚众淫乱罪(44)参见李银河:《关于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提案》,载《法制资讯》2010年第4期,第67页。和组织卖淫罪(45)参见徐松林:《我国刑法应取消组织卖淫罪》,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第101页。。
2.因为法益侵犯归因错误导致的象征性刑事立法
即便存在被侵犯的法益,如果立法未能准确定位法益受侵犯的原因,也可能导致象征性刑事立法。这种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范例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法定刑的调整。立法者的意图是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的产权,但民营企业面临的不平等,不是企业内部人员实施犯罪时惩罚力度比公有制企业低,而是税费负担、融资条件、可享受的公共服务、产业和市场准入等竞争性条件的不平等。(46)参见刘志彪:《平等竞争: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之本》,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4期,第42页。事实上,内部犯罪并非民营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类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反倒屡屡被当成公权力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通道,(47)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6)川委赔3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所示,该案中,赔偿义务人、原办案机关将挪用资金罪的涉案资金没收,而未退还给被害单位。而非法益保护的卫士。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前述条文无助于改善民营企业产权的地位,只是表达了立法者对民营企业平等地位的关切而已。
3.因为违反犯罪预防的作用机理出现的象征性刑事立法
如果立法采取的法益保护措施违反了刑法保护法益的作用机理,立法也会成为象征性刑事立法。在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1)为提高法益保护力度,却降低了相应犯罪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九)》第43条废除了嫖宿幼女罪,该罪是专门保护处在色情交易状态下的幼女的条文。该罪被废除之后,嫖宿幼女的行为通常只能依照《刑法》第236条第2款,在3到10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根据201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奸淫幼女1人的,可以在4年至7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而按照原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其量刑区间则在5年至15年之间。可见,尽管这一立法修订表面上顺应了民众严惩相关犯罪的呼吁,却在事实上弱化了对处于色情交易状态下的幼女的保护。
(2)为了提高惩罚力度,牺牲惩罚概率。《刑法修正案(九)》第45条是其适例。《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的《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九)》第45条将《刑法》第390条第2款修订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立法修订确实传达出了坚决打击贿赂犯罪决心,但其实际效果则是在整体上削弱了法益保护的力度。现实中,贿赂犯罪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惩罚概率低,附条件地宽恕对向犯中责任较轻的一方,有助于形成“囚徒困境”,促成行为人之间的不信任,让犯罪同盟从内部崩塌,从而提高惩罚概率。削弱从宽的力度,就会降低行为人背叛的激励,从而降低惩罚的概率。根据一般预防的基本原理,惩罚概率的意义远高于刑罚的严厉程度,因此前述立法必然会对一般预防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削弱法益保护的力度。(48)对此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陈金林:《通过部分放弃刑罚权的贿赂犯罪防控——对〈刑法修正案(九)〉第45条的反思》,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9页。因此,《刑法修正案(九)》的前述规定,也是典型的象征性刑事立法。
五、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应对
象征性刑事立法本质上是对法益保护这一目的理性的偏离,因此,应对它的基本方案就是确保立法对法益保护的有效性。对这种手段-目的型的正当化尝试,可以作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外部批判需追问目标设定的合理性,也即,相应立法是否有适格的法益。内部批判需要追问手段(具体的条文)是否有助于实现特定的目标。(49)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这种检验可以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展开。
(一)立法层面
由于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判断重心是罪刑规范的机能,而不是立法动机与过程,因此,对所有当前有效的罪刑规范,都有必要作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检验。立法历史上的主观目的,立法过程的民主、科学性,都不是豁免这种检验的充分理由。在这种意义上,刑事立法作为一种制度产品,必须永远确保自身的质量,也即对法益保护的有效性。而这一质量担保只能通过学术界的批判形成压力并最终经由立法者通过不断的立法修订来实现。当然,这一批判也完全可以融入立法过程中。
1.对刑事立法的外部批判
对刑事立法的外部批判,应围绕是否存在适格的法益展开,即追问特定的条文是否有明确、清晰的法益作为正当化的根基。在这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可以在两方面做出改进。
第一,以法益为中心展开立法的正当性论证。我国当前的立法,通常以落实相关政策或者解决具体问题为基本动因,法益更多被当成了纯粹的解释工具。这样一来,很多刑事立法建议根本没有经过以法益为指导观念的论证便得以通过。尽管这未必意味着刑法一定不能保护法益,但至少提高了条文在部分情形下演变为象征性刑事立法的风险。例如,如果不明确药品类犯罪的法益,这类犯罪就可能被用来惩罚纯粹不符合行政要求的行为(如陆勇案)。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就有必要在立法论证或罪刑规范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示其法益。《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妨害药品管理罪中规定“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在妨害安全驾驶罪中明示“危及公共安全”,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的入罪情节限定为“造成重大损失”(删除“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一入罪通道),将这三个犯罪的法益分别明确为“药品消费者的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金融机构的财产”,具有借鉴价值。
第二,以明确、具体、有现实基底的法益替代“伪法益”。我国的不少刑法规范虽然明示了处罚根据,但其指明的根据未满足法益的基本前提,如非法经营罪中的“市场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金融秩序”等。这种情形也可能导致象征性刑事立法,因为以此为根据的规范,在部分情形下可能只是在维护某种禁忌或特定管理机构的权威。为了消除这一隐患,有必要分别以“对消费者盘剥的危险”或“超过集资参与者认知范围的投资风险”替代前述根据。就此,Hassemer曾指出,法益越模糊,其包含的内容越多,成为象征性立法的可能性越高。(50)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8.此外,由于这类“伪法益”会让象征性立法披上法益保护法的外衣,以此为基础的隐性象征性刑事立法危害性甚至会高于明显的象征性刑事立法。
2.刑事立法的内部批判
刑事立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法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刑事立法需满足以下前提。
第一,法益事实上存在,仍在遭受侵犯或有被侵犯的危险,且立法处罚或拟处罚的行为是法益遭受侵犯的原因或主要潜在威胁。为此,有必要充分展开经验调查,以确保作为刑法介入根据的法益侵犯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臆测。德国学者Graul曾用一个教学案例阐释完全没有法益侵害事实根据的刑法:为了保护一种珍稀的鸟,法律禁止于繁殖期A、B、C三个月在湖泊X周围举行任何休闲活动。即便这种鸟基于某种原因不再于X湖繁殖或已完全灭绝,该禁止仍有可能被继续维持。(51)Vgl. Graul, Abstrakte Gefährdungsdelikte und Präsumtionen im Strafrecht, 1991, S. 67, Fn. 257.我国刑法中也有类似的情形:随着“金税工程”的推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防伪已经不再依赖于发票的载体而是依赖于税控系统的验证,因此,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意图保护的目的(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载体的信赖)已经不复存在,(52)参见陈金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困境与出路——以法益关联性为切入点》,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2期,第43页。但直到今天,该罪名依然在获得适用。此外,还有必要通过经验分析确保刑法拟处罚行为与法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刑法修正案(十一)》用同等处罚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内部犯罪的方式实现平等保护企业产权的目的,就是因为立法者误解了民营企业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原因。
第二,根据刑法作用的基本原理,立法采取的措施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提升法益保护的机能,且不会造成不可预期的附随后果。为确保这一前提,有必要弄清立法变动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了法定刑,会不会因此而影响惩罚概率或通过其他方式对法益保护产生负面作用。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使其与集资诈骗罪之间的法定刑差距缩小,实际上就会导致行为人更倾向于选择集资诈骗罪,这反倒会损及集资参与人的利益。同样,提高民营企业内部犯罪的法定刑不会提升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力度,反而会强化公权力对民营企业的干涉,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的地位,因为更高的法定刑会形成更强的查处犯罪的激励,(53)法定刑的高低会影响规范的社会关注强度,进而影响刑事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调动和配置。这一原理在制度上的证据是,重大立功和普通立功之间的区分、追诉时效以及诉讼期限的延长,都与法定刑高低相关。而更多的内部犯罪查处并不利于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
(二)司法层面
在司法层面,也存在对象征性刑事立法进行补救的空间,也即通过实质解释将条文与适格的法益建立关联。由于刑法是法益保护法,它处罚的行为必须与法益具有最低程度的关联,即便立法并未明确这种关联,司法者也应通过解释将其补充进来。
首先,司法人员应以适格的法益作为实质解释的指导观念。适格的法益,是确保刑法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刑法,作为一种严重侵入公民自由权利的强制,必须始终确保自己的正当性,无论是在立法环节还是司法环节。因此,刑法适用者不能满足于用所谓的“方法论法益”对立法作实质解释,(54)其实,方法论的法益只不过是目的解释的工具而已。Vgl. Roxin/Greco, Strafrecht, AT, Bd. I, 5. Aufl. 2020, S. 25.实质解释的指导观念只能是为刑法赋予正当性的法益,也即通常意义上的批判立法的法益。如果立法的历史-主观目的或者通常指导条文解释的观念不符合前述要求,法律适用者就有义务用符合前述条件的法益替代它们。例如,通过性的自决、健康和青少年保护而不是“有关性的风俗”来解释与性相关的犯罪,(55)Vgl. Hassemer, Symbolisches Strafrecht und Rechtsgüterschutz, NStZ 1989, S. 558.以“终端消费者在重要物资上免予被盘剥的自由”替代非法经营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56)在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但“粮食流通的主渠道”“市场秩序”“社会危害性”也并非适格的法益。
其次,司法人员应通过添加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的形式,将罪刑规范处罚的行为与适格的法益之间建立关联,以限缩象征性刑事立法的适用。象征性刑事立法与适格的法益之间并无常态的关联,但可以通过补充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两者之间建立关联。例如,可以用对他人生活安宁的侵扰来解释聚众淫乱罪,为聚众淫乱罪补充“能够为他人感知且没有根据要求他人回避”的要件;(57)张明楷教授为本罪添加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当场可能认识到”的限制性条件。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3页。但“可能认识到”依然不足以起到充分的限制作用,而且,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分析,只有侵犯他人的利益才能成为处罚的充分根据,“让他人认识到”本身还没有越过这一门槛。可以通过传播性病的危险来解释刑法对组织卖淫罪的处罚,因此,只要采取了有效措施控制性疾病传播的风险,组织卖淫的行为就不应被认定为犯罪。(58)张明楷教授认为手淫、乳交、组织女性被特定人“包养”等行为不宜解释为“卖淫”。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528页。背后的原理,实际上是这类行为造成性病大范围传播的危险较小。而且,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刑法选择处罚组织者而不是直接处罚出卖和购买性服务的人,因为让前者而非后者为卖淫场所的公共卫生负责更合适。
最后,如果完全无法通过添加构成要件要素的方式在象征性刑事立法与适格的法益之间建立最低程度的关联,就应当通过实质解释、刑事政策的权衡、自由裁量权等方式架空甚至间接废除相关的条文。例如,可以通过适用《刑法》第13条的“但书”、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相对不起诉等方式抵消《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人从宽幅度的压缩。在这一问题上,可以从韩国对通奸罪的处理中获得启示。在韩国宪法法院2017年废除通奸罪之前,韩国刑法有关该罪的规定是典型的象征性刑事立法,就此,司法实践采用了事实上架空其适用的方案。据统计,自1984年以来,韩国通奸罪占全部犯罪比率从1984年的1.09%变成了1998年的0.34%,不起诉的比率更是从1984年的70.3%上升到1998年的83.9%。(59)参见吴昌值:《韩国刑法上的通奸罪考察》,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6期,第119页。
司法对象征性刑事立法的补救或架空,比立法的纠正更灵活、及时,也更有可能成功,因为应对象征性刑事立法需要更多的专业精神,这正是司法人员的专长,而倚重民主的立法程序则先天地偏向象征性刑事立法,期望立法自身克服这种秉性是不现实的。这样一来,司法人员有责任扛起捍卫法益保护原则的大旗,限制或架空象征性刑事立法。
尤其要注意的是,司法人员要克制用象征性的司法去掩盖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冲动。对法益保护而言,最优的结果是有法益保护功能的罪刑条文不战而屈人之兵;次优的结果是有法益保护机能的条文在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普遍的适用;较差的后果是象征性刑事立法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而最坏的局面就是象征性刑事立法被广泛执行并产生了大量的有罪判决。这也是理论上不能以司法判决数的多少为标准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政策性原因。
六、结语
象征性刑事立法是指完全没有法益保护机能仅以价值认同为存在根据的罪刑规范。判断象征性刑事立法,应当以立法的机能为判断重心,以法益保护机能的缺失为实质依据,以民众的价值认同为表层依据。立法动机、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判决数、法律适用后对相应问题的解决效果都不是认定象征性刑事立法的决定性根据。
象征性刑事立法与普通刑法一样,会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消耗社会资源,却没有法益保护的机能,还具有高度的欺骗性,因此应成为立法批判的核心目标。当然,立法批判的前提是严格限定批判的对象。通常被学界归入象征性刑事立法的环境刑法、反恐刑法、网络刑法、公共安全刑法以及反腐败刑法,并不缺乏法益保护机能,因此并非象征性刑事立法。当前我国刑法中的象征性刑事立法,除了聚众淫乱罪、组织卖淫罪等有关性风俗的犯罪之外,更多是因归因错误和违背犯罪预防基本原理的隐性象征性刑事立法,如提高民营企业内部犯罪法定刑、废除嫖宿幼女罪、压缩行贿罪的特别从宽事由等立法修订。对于象征性刑事立法,应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以补强它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关联。在立法尚未作出修订且不能通过解释补足法益关联的前提下,司法人员应限缩这类条文的适用。
尽管所有的刑事立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象征属性,但只有象征成分的刑事立法一定是不具有正当性且有严重危害的立法。在刑事立法中的价值建构主义越发盛行和强势的社会背景之下,法律专业人士应准确识别、批判、矫正和抵制象征性刑事立法,捍卫法益保护原则,确保刑法在目的理性的范围内运行,防止刑罚这种最严厉的国家暴力建立在没有现实基底的规范构造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