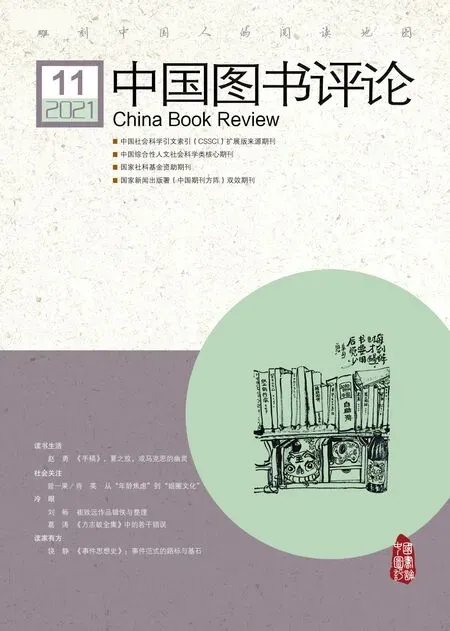“智慧风貌”“第三维”与莎剧《亨利四世》
——从吴兴华到傅光明
□何建委
【导 读】莎士比亚历史剧当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亨利四世》。而吴兴华的译本与导读,是“‘十七年’时期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身处21世纪的傅光明则追求适应时代变化。鉴于此,参考卢卡奇的“智慧风貌”、艾略特“第三维”理论,立足《亨利四世》复译本,考察其背后的时代变迁与理念更迭,很有必要。
从1921年田汉翻译莎剧《哈孟雷特》以来,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已长达百年。在这百年的翻译长河中,莎剧中文译者名家迭出,其中最闪亮最瞩目的无疑有朱生豪、梁实秋等大家。不过,正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莎剧翻译。在鲁迅看来:“而且复译还不只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鲁迅的观点意味着,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翻译,方能适应语言的时代变化,方能形成“近于完全的定本”,更能有助于中国文艺的发展。而吴兴华、傅光明的莎剧翻译,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吴兴华的“莎士比亚的评论和译介,是‘十七年’时期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傅光明是21世纪第一个力图以一己之力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中文译者。相比朱生豪等人的译本,吴兴华、傅光明的译本,在追求适应汉语时代变化的同时,皆注重“丰富的注释、翔实的导读”。其中,关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最成功、最受欢迎的《亨利四世》,吴兴华的译本初次出版于1957年,傅光明的译本出版于2020年。鉴于此,考察莎剧在中国译介的传播,考察莎剧复译本与中国文艺的互动,有必要思考不同译本背后的时代变迁与理念更迭。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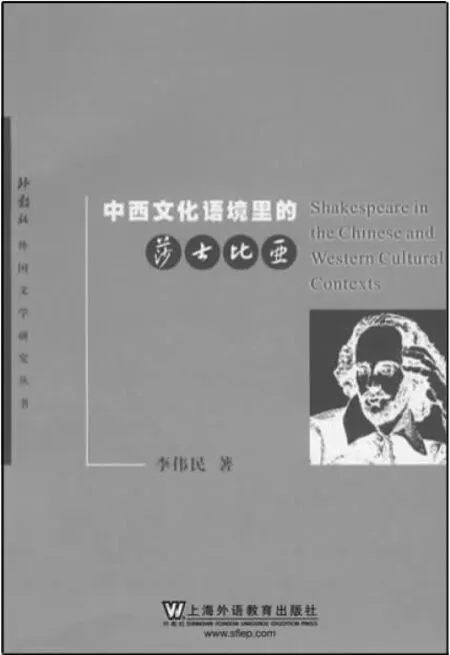
吴兴华翻译的《亨利四世》出版于1957年。对此,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参照同时期国内的莎学研究风向。尽管在1956年以后,西方文学的多数因为被认为宣传人道主义显得不合时宜而被禁止,但莎士比亚文学是被允许阅读的。1949—1965年是莎士比亚译介在中国的“繁荣期”,不仅各种译作被纷纷出版,包括《莎士比亚戏剧集》于1954年被出版,而且“中国莎评出现了第一个高潮”[1]31。莎士比亚译介在中国的这个“繁荣期”,与当时追随苏联文艺政策和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即国内重视什么文艺作品的重要参照标准,是看苏联重视什么。莎士比亚既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又一直被苏联视为“革命的同盟者”,是苏联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2]与此相应,在苏联受到高度重视的莎士比亚,也受到了国内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国内莎学,也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为指导”[3]的,比如,当时卞之琳等人的莎士比亚研究借鉴苏联莎学“较多地运用了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再比如,莫洛佐夫的《莎士比亚在苏联》与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于20世纪50年代纷纷被译介到国内,后者的著述“差不多成了外文系、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不可缺少的参考书”。[1]31,36与此相应,与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被封杀不同,莎士比亚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国内成为不受影响的经典。莎士比亚译介在中国的“繁荣期”,无疑为当时吴兴华翻译《亨利四世》提供了便利,并不失为一种安全的做法。
当时的莎学在“较多地运用了社会学的批评方法”的同时,特别注重莎士比亚戏剧当中的“人民性”。比如,国内马克思主义莎学代表人物卞之琳从阶级分析等角度出发,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民性”;孙家琇借助马克思主义视角,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两个时期交汇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民性”,等等。受此影响,“人民性”长期以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的“核心概念”[4]。从他们的莎士比亚研究来看,“人民性”视域的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是对莎学的丰富,是不同理论的碰撞与对话。而且“人民性”也很适合中国国情。在政策方面,中国长期注重“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创作方面,许多作家“自觉地认同以人民为轴心的人民话语”,并以其为指引,从人民当中“找到力量和灵魂”[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80年代初期,“人民性”是强调“阶级性”的,是排斥“人性论”的。也就是说,“人民性”是大多数“人民”的,而不是少数非人民的,比如,某些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就没有“人民性”。同时,“人性论”是忌讳,是令人担心甚至给人带来无妄之灾的“标签”。
在这个大背景下,吴兴华在序言里也不可避免地谈论了《亨利四世》的“人民性”。在他看来,《亨利四世》“深刻地处理了王权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多方面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人民选择亨利四世,是因为他们“厌弃理查二世暴政”;人民“不情愿地支援”“不能够真正承担人民信托”的亨利四世而非叛乱贵族,是因为他们“希望国王能够压抑贵族和教会,保护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不仅如此,吴兴华还认为,“莎士比亚在广大无名的人民身上寄托了他遥远的理想”。由于福斯塔夫是《亨利四世》的重要人物形象,他对福斯塔夫进行了阶级、“人民性”的分析。吴兴华说道:“他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是合拍的,他反映了广大人民模糊意识到的一种愿望。”而福斯塔夫集团“代表的是一个特殊阶层”,“恩格斯认为正是从这个阶层里渐渐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先辈”。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的产物,福斯塔夫是个矛盾的混合体,“新的和旧的,先进的和落后的品质互相依附”,比如,习惯上有“封建社会”旧阶级“旧日的坏习惯”,但“永远不忘记把自己列入年青一代的队伍里”,痛恨战争,却又觉得战争“也是一笔横财”。他代表了特殊阶层的反抗,比如,他“年轻人总要活命的”等话语“变相地隐藏着真正被压迫者的声音”,而且他还有“不肯改变自己的生活、出卖自己的理想而把背转向富贵的大路”这种勇气。因此,吴兴华提醒我们:“最后的高潮场面:福斯塔夫的斥逐。它照亮了全剧,使复杂错综的现象归于条理化,并且深刻地指出了历史必然的动向。”[6]183
吴兴华的这些论述是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阐释与展开,与“重量级的莎剧翻译家和莎评家”卞之琳的观点多有相似之处。卞之琳写于1955年的《论 〈哈姆雷特〉》文章对“人民性”的论述,在“照搬”了苏联莎评学者莫洛佐夫、阿克尼斯特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借鉴了鲁迅关于“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观点。与此相应,他认为莎士比亚笔下“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广大人民”,且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人’本质还是资产阶级的‘个人’”。[7]8,9莎士比亚只有在“转入悲剧时期的作品”才有“站到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大众方面,做出自身阶级的叛徒”的人文主义倾向,从而证明“人”“包含了社会上的极大多数人”[7]108。可知,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人民性”所对应的主要还是广大的被压迫阶级,也就是中国语境中的工农阶级。对特殊时期的“人民性”的解读,卞之琳在后来的岁月中认识到,之前的“阶级分析,固然有点简单化、庸俗化、机械、生硬,大体上倒还通达”[7]8。苏联与国内“文革”前后的马克思主义莎评的“人民性”论述,也强调“人民性”当中的“阶级性”,主要注重莎士比亚“体现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部分。
除此之外,吴兴华引用了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并着重强调了《亨利六世》“上篇”“中篇”“下篇”以英法百年战争、凯特起义和玫瑰战争为题材,第一次向剧院观众和其他剧作家们显示了记事史里的材料如何可以点化成为具有高度效果的戏剧。接着在舞台上出现的,有他的《李查三世》《约翰王》《李查二世》。“从这些剧本里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是如何敏锐地在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摸索其中的规律,同时企图把历史和目前情况联系起来相互印证。”可以看出,吴兴华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解读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十七年”期间马克思主义莎学多有不谋而合之处,即强调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社会学意义,着重莎士比亚历史剧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关注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人民性”,从“人民”的角度分析福斯塔夫的特点与局限性。
二
当然,吴兴华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解读仍多有闪光之处,比如,他阐释《亨利四世》:“宏伟的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这些都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创造,带有他个人天才独特的印记,不是任何原始材料里所能寻找得到的。”且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情节通过莎士比亚的艺术“重造”与加工组合“获得了崭新的深邃的意义”,从而“就跳出了枯燥的纪事史范围,成为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这些解读显示了吴兴华在特殊年代解读《亨利四世》的难得之处与可贵之处,他的解读虽然是在特定年代进行的,但溢出了特定年代的局限,超越了同时代的认识,甚至与艾略特的“第三维”、卢卡奇的“智慧风貌”理念有多处不谋而合。
在艾略特看来,“第三维”是莎士比亚戏剧具有深度的关键。正是“具有第三个维度”,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字常常有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其根须一直向下扎入人们埋藏最深的恐惧和欲望”;正是具有“第三维度”,“莎士比亚敏锐地捕捉到了更加广泛、深刻和玄秘的人类情感”。而最清晰地显示出来的“智慧风貌”,在卢卡奇,是“完成作品中的中心任务的一种不可缺的必要东西”,而“智慧风貌的描画,就常常预定了人物的一个非常广大、深刻和普遍的人类的性格创造……在一个极其强调的情境中的人物的非常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社会问题的错综的最深刻的矛盾”。智慧风貌的刻画与作品成为世界伟大作品、人物成为世界伟大形象密切相关。[8]183与吴兴华相比,傅光明的翻译更多地揭示了“智慧风貌”,显示了莎剧的“第三维”。相比吴兴华用百余字简要地介绍了原型故事,傅光明的《亨利四世》导读用了7000多字详细地梳理了原型故事。而且相比吴兴华力图从《亨利四世》等历史剧中寻找英国历史,傅光明则认为“莎剧中的‘历史’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并非英国历史,而且莎士比亚的历史甚至“覆盖和屏蔽掉”了真正的历史。基于此,傅光明引申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包括《亨利四世》,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包括亨利五世特别是福斯塔夫,更多是纯粹为舞台服务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为了剧团、剧院的商业运作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怎么写、写什么的目的是“既满足观众,还能挣到钱”。与此相应,可以说,这种商业化运作决定了莎剧中的历史与真实的英国历史与后人眼中的历史的不同走向,决定了福斯塔夫的复杂面向与后人的无限解读。
关于福斯塔夫的复杂面向,王元化在写于1997年的《福斯泰夫与猪八戒》中说道:“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泰夫这个人物使我联想到猪八戒……为什么这个丑陋的、有着恶习的角色,竟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乐趣,甚至得到儿童的普遍喜爱?作者凭什么本领化腐朽为神奇,从丑中提炼艺术的魅力,显现人性的弱点,却又用滑稽突梯把辛辣和苦涩变为可笑?……一直萦回脑海中的猪八戒形象,却给那段枯燥沉闷的日子带来了不少生趣,使我至今难忘。”[9]猪八戒如此,福斯塔夫亦是如此,他虽然是个大腹便便、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丑角,但引起无数人的喜爱,让无数人难以忘怀。可以说,福斯塔夫是莎剧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乃至能与哈姆雷特相媲美。与王元化从显示人性弱点角度思考福斯塔夫的广受欢迎不同,吴兴华通过阶级、“人民性”等方面,着重分析了福斯塔夫的跨时代特征。在他看来,福斯塔夫的不朽,在于“他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是合拍的……他的行为和言论在千万同时代人的心灵深处敲响了一个键子,引起共鸣。不可能想象一个简单的丑角能够发生这样大的作用”。作为与时代精神合拍的人物,福斯塔夫的“玩笑、嘲讽和胡闹都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他给予剧中的中心主题以一种新的深度,像历史上的欧尔卡苏一样”[6]183。
对于王元化将猪八戒和福斯塔夫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归结于他们“显现了人性的弱点”,傅光明无疑是认同的。在他看来,大家更喜爱福斯塔夫“这个懦夫”,“或许因为在很多时候,人们都会在福斯塔夫式的本能驱使下,自然变成懦夫”,或许因为“不招我们反感,还令我们愉悦。人自娱自乐,也叫别人快乐”。不仅如此,福斯塔夫既是时代使然,却又解构了时代;与此相应,大家偏爱福斯塔夫,还在于可以“透过他的形象解构自己所处的时代”。基于此,福斯塔夫“绝好体现着莎士比亚的喜剧才华”“远远超出了时代”“是说不完的”。也正因为福斯塔夫的魅力,“从戏剧结构看,亨利王子与福斯塔夫两个人的联手戏,是贯穿并撑起整个上下篇的重要支点。比较而言,剧名虽题为《亨利四世》,但国王亨利四世在剧中倒似乎是配角。《亨利四世》(上篇)与其说该剧是‘亨利四世的悲剧’,倒不如说它是‘福斯塔夫的喜剧’”[10]。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傅光明的译本窥探一二。在下篇第二幕第四场中,当哈尔佯装要处置他,福斯塔夫赶紧抵赖:“没诽谤,内德,天地良心,诚实的内德,一点儿没诽谤。我在歹人面前说他不好,是防着坏人爱上他。我这样做,算尽到了贴心朋友和忠诚臣子的一份心,你父亲该感谢我才对。不是诽谤,哈尔。没一点儿诽谤,内德,一点儿没有。没诽谤,真的,孩子们,没诽谤。”从耍贫逗趣、闹剧色彩中可以看出福斯塔夫的“巧舌如簧”以及面对穿帮、面对窘境时的自信与自如,硬生生将诽谤说成了贴心与忠诚,硬生生地心不惊胆不战地信誓旦旦地对别人的话予以否认,可谓扯牛皮的最高境界,可谓生活最普遍不过的场景。在第二幕第一场与大法官交锋时,面对大法官对他了如指掌,不吃他那套“约翰爵士,约翰爵士,你弄虚作假的这一套,我太熟了。你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你一大串粗鲁无耻的言辞,改变不了我的公正判断。依我看,你骗了这个生性慷慨的女人叫她把钱袋儿和身子都拿来供你享用”“欠她的债,你得还;对她干下的坏事儿,也得补偿。还债,用实打实的钱;补偿,用真心忏悔”时,福斯塔夫照样应对自如:“大人,这个可怜的疯婆子,满大街嚷嚷她大儿子长得像你。”并且丝毫不服软,以“王命在身”,要“跟随约翰亲王去约克郡平叛为由,叫大法官发话,命官差放了他”。至此,福斯塔夫“脑子反应奇快”“耍无赖的本领简直无人能及”体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可以试想,面对福斯塔夫,不仅现场的观众笑不拢口,而且每个时代的读者也喜闻乐见,正可谓“不招我们反感,还令我们愉悦。人自娱自乐,也叫别人快乐”,正可谓与时代同在、与读者同在。值得注意的是,傅译的语言,比如,“不光一点钱的事儿,老爷,是全部——我所有的钱。他把我整个家底都吃没了,把我全部财产都装他大肥肚子里了”,富有时代气息,非常贴切形象。
再以吴兴华与傅光明的注释译文进行对比为例。关于第二幕第四场,吴兴华解读说,“这一场卓越地体现了莎士比亚描写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能力”,而“在福斯塔夫和桃儿、桂嫂两个妇女的关系上,除开很明显的滑稽畸形的一面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善良的伴侣感情的成分。尽管福斯塔夫对她们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欺骗吹牛手段,有时也占她们一些小便宜,但他也给予她们并且和她们共同享受一定的快乐。最后的分手场面写得很真挚动人的”。与此相应,分别场面,吴兴华译本是这样的:“福:再见,老板娘;再见,桃儿。好姑娘们,你们看有本事的人是不是到处都有人找?那些庸庸碌碌不值一笑的人可以睡大觉,可是干事业的人就消停不了。再见,好姑娘们。我要是不急急忙忙地被派走,我走以前一定还来跟你们见个面。桃:我话都说不出来了,如果我的心不是眼看就要碎了——好吧,亲爱的贾克,好好当心你自己。福:再见,再见。桂:好吧,再见。我认识你要等到绿豆生荚的时候,算来也有整整二十九年了。可是再要找比你更老实、更心地厚道的人——算了,再见吧。”可以看出,吴兴华是从下层阶级感情的角度对福斯塔夫和桃儿、桂嫂的关系进行了解读,并认为他们的感情真挚感人。同时,为了服务于他的“人民性”分析,他将英文名“道尔”翻译成了带有中国下层阶级普遍的名字“桃儿”,并将福斯塔夫的语言中增加了“亲爱的”等感情真挚的词。而傅光明是这样翻译的:“福斯塔夫:再见,老板娘。——再会,道尔。——瞧见了吧,我的乖女人,男人一身本事,自有人找上门!会干事儿的一经召唤,窝囊废就可以睡大觉。再见乖女人,只要不立刻出发,走前我再来看你们。道尔:我说不出话了。——倘若我的心不是马上要碎,——唉,亲爱的杰克,照顾好自己。福斯塔夫:再见,再见。桂克丽:好,再见吧。到豌豆荚结籽儿的时节,我跟你相识整整二十九年。可一个更诚实、更真心的男人——算了,再见。”不难看出,相比吴兴华,傅光明的翻译突出了福斯塔夫吹牛皮、大色鬼的本质,而且将桂克丽语言当中的性暗示、性双关通过注释进行了揭示。
的确,尽管“所有评论家都认为,本剧的设计中心是那位瘦亲王,而不是这位胖爵士”,但事实上福斯塔夫的重要性超过了那位瘦亲王。梁实秋揭示道:福斯塔夫“在《亨利四世》里所占的重要性远超出寻常丑角的比例。上篇一共19场,福斯塔夫出现了8场,第2、5、7、10、12、15、17、18各场都有他的戏”。对此,卢卡奇从“智慧风貌”的角度予以回答,他认为:“作者给他的人物以某一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主要人物或穿插的人物……莎士比亚在他的许多成功的剧作中利用着类似的生活的平行的描画,就常常通过这种有意识地概括其生活的能力,给他的主要人物以他们的‘地位’,使他们适宜于在情节中成为中心的人物。”与此同时,“这种人物却不必一定有着正确的观点……如果这个斗争是深入地正确地被把握,那么作者就必须就其个人的特性使那些个人成为主角,在其智慧的风貌上发挥尽致,而这个斗争,这时候也就可以最生动、适当地表现出来了。就同一的作者来说,这要看被处理的问题的性质,和最适宜于问题的表现的人物的智慧风貌而定”。[8]179,180,181不难看出,从卢卡奇“智慧风貌”的角度来看,福斯塔夫恰恰是这样一个“主要人物或穿插的人物”,也更“适宜于在情节中成为中心的人物”。他的观点大多不正确,但“深入地正确地被把握”,被“最生动、适当地表现出来”了,有利于莎士比亚把智慧风貌发挥到极致。
在艾略特看来,福斯塔夫正是将“第三维”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人物,他“体现了一组更错综复杂的情感和欲望,也体现了一种更灵敏更易感的性情。福斯塔夫不仅是腹中填满了布丁的曼宁特里烤牛而已,他也会‘垂垂老去’,而且到末了,他的鼻子还尖得像笔杆。也许他‘满足’了人们更多、更复杂的情感,像过去那些伟大的悲剧人物一样,也许他是更为深刻玄秘的感情的产物……这些感情更为深刻”。对此,兰色姆阐释道:“人们说莎士比亚的文字盘根错节,深入底里,还说他笔下的人物体现着一组‘错综复杂’的感情和欲望;他们以福斯塔夫为例,说明他生理特征的多样或复杂。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意在说明,莎士比亚的文字和人物具有多方面而非单方面的实际含义。它们当然在全剧的结构(情节)范围内扮演指派给他们的角色,但同时又独立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戏剧的合理性原则不能干预它们。于是就有了那个比喻,说它们具有额外的维度,有了这一维度,它们就可以成为实在的物体。就我所知,如果说艾略特相信‘诗歌缺乏逻辑关联’的说法的话”。[11]113,114,115,116谁说不是呢?显示人性弱点的、时代使然又解构时代的福斯塔夫,满足了无数个凡夫俗子更深藏、更深刻的“更多、更复杂的情感”与欲望。他在剧中有自己的角色,却又扮演着自己,从而有了“第三维度”,有了无尽的蕴意,有了说不完的阐释。
三
除此之外,吴兴华还着重分析:“太子的成长和转变过程是全剧倾向性的钥匙……他们的结合、分离和对立,构成了支撑一切的骨干。只有在很好地全面估计了这两个人物,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和所起的作用之后,剧本的真实轮廓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才初次显示在我们面前。”尽管他的论述强调了二人的阶级差异,但他以太子和福斯塔夫这两个人物的互相关系分析莎剧,是抓住了《亨利四世》的关键,是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奥秘。在艾略特的“第三维”理念中:“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可以生活在莎剧为他们安排的处境之外,在莎剧中,人物性格得到了最强烈、最有趣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并未穷尽人物具有的种种可能。在莎剧中,效果来自人物的相互作用。”[11]110卢卡奇也持类似的观点。在他的“智慧风貌”理念里,伟大作品中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智慧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彼此“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这些相互的关联发展得越是多方面,则这作品越成为伟大的,因为,它是越接近生活的实际的丰富,越接近列宁所常说及的所谓发展的真实过程的‘巧妙’了”。这是因为“只有在比较中,在和别的人物的对照中,作家的人物才成为典型的,而别的人物,也同样地把那在多少是非常的方式中影响他们的生活的同一矛盾的别的阶段和表现,予以显示。只有作为这么一个很复杂、流动和重大的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充满着极端的矛盾的,这才可能把一个人物提升至真正典型的高度”。而莎士比亚的创作的丰富、生动正“是从人性的热情,从人们的多重的斗争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现实中的人不是彼此并立,而是互相扶持或互相敌对地行动的,这种斗争,做成了人类个性的存在与发展的基 础”。[8]172-221,173-176正 是“关 涉人物的最深刻的、个人的和典型的特性,尤其是关涉智慧风貌的仔细描画”,福斯塔夫才成为世界文学的人物,《亨利四世》等莎士比亚戏剧才成为“世界文学上的伟大杰作”。[8]183,196阅读《亨利四世》不难看出,正是通过与哈尔王子的对手戏,正是通过他们的“互相扶持或互相敌对地行动”乃至斗争,正是通过与亨利四世、哈尔王子、大法官等人的对照,福斯塔夫“最深刻的、个人的和典型的特性”才得以凸显,才“越接近生活的实际的丰富”,从而从极端矛盾当中把自己“提升至真正典型的高度”,从而“人物性格得到了最强烈、最有趣的表现”。其实,中国的“福斯塔夫”猪八戒何尝不是如此?!
关于《亨利四世》当中的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傅光明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在援引乔纳森·贝特“《亨利四世》是一部双重戏,满场都是成对的人物”论述的基础上,傅光明阐述道:“在剧中设置成对人物,是莎士比亚一成不变的戏剧手法。”但莎士比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舞台狭小”,是因为“说穿了,莎剧秘籍只有一条:为舞台而写”。在这个前提下,人物成对出现“外在形式”的背后是“运用各种显性、隐性对比塑造和刻画人物”之“内在堂奥”。“拿《亨利四世》(上篇)来说,国王与王子、哈尔与福斯塔夫这两对人物的联手戏,同亨利王子和霍茨波这对人物的对手戏,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戏剧结构。此外,纵观上下篇,类似的联手戏很多,对剧情和结构起到不可或缺的起承转合和烘托作用”。在此基础上,傅光明详细分析了亨利四世与亨利王子的相互关系、亨利王子与霍茨波的相互关系、哈尔与福斯塔夫的相互关系,以及福斯塔夫与大法官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亨利四世与亨利王子的相互关系,傅光明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子在自我进行着‘内我’(王子)与‘外我’(浪子)的对比”。
关于哈尔与福斯塔夫的相互关系,吴兴华以“奇怪的收尾场面”作为切入点,解释道:“首先,态度对福斯塔夫始终是有保留的、若即若离的,而福斯塔夫对太子表现出一种几乎是盲目的迷恋和信任……在太子眼里看来,一切都服从于一个最终目的:他要做一个强大的君主,如果必须用福斯塔夫等人来做阶梯,他是准备践踏着他们登上去的,因此最后的转变不能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其次,由于“福斯塔夫缺乏正面的理想和品质”,太子始终不会依靠他,最后不得不斥逐他。“不可能想象福斯塔夫和他的伙伴们代替大法官等人掌握政权。如果我们承认专制君主的政体在当时是必需的,那么斥逐像福斯塔夫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随之俱来的结论。”“但莎士比亚天才的伟大胜利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更深地向根源探索……为了表面的调协而粉饰现实是一种很强的诱惑,但莎士比亚抗拒了这种诱惑。他向我们暗示:亨利五世斥逐了福斯塔夫,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人民的信托。福斯塔夫失势了,绞架和重税就又活跃起来”。[6]184,185
对于这些,傅光明是认同的。他认为:“哈尔从没信任过福斯塔夫。”他对他早就看透了,他只不过是暂时和他们一块儿放浪形骸,一块儿玩玩解解闷。与此相应,他用“给福斯塔夫起了好多绰号”表达了他对后者的“鄙夷”,与此相应,福斯塔夫只不过是他的笑料或消遣罢了。可是,福斯塔夫始终信赖他、恭敬他,深信不疑地以为哈尔掌权后自己也会“鸡犬升天”,自己也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对上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塔夫与哈尔之间唯一的联手大戏”这个“篇幅在全剧中最长”、多达405行进行“稍做分析”后,傅光明得出结论,“或许莎士比亚事先已想好”,“事实上,剧终幕落之时,只要观众/读者仅凭观看演出或阅读文本时的本能思维,稍微替福斯塔夫回想一下,便能立刻明白,这场联手戏注定了福斯塔夫的命运”。因此,福斯塔夫的结局被驱逐,是“福斯塔夫式的本能”——“常对哈尔把 ‘等你当了国王’挂嘴边,因为他最担心哈尔当了国王之后变心”的必然结局。此外,傅光明强调以桂克丽和道尔这两个底层女性人物举例,欣赏和解读莎剧,注释的不可或缺,需要直接和正式提出来。毕竟莎剧有大量的双关语特别是性双关。而“若没有注释,其中的戏剧滋味将大打折扣”。
乔治·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一书中提出“understanding as translation”“翻译即理解,在文字、文学、历史和文化所交织的意义之网中来回反复,永无止境”。[12]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作为一种理解,不仅在“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而且在丰富着莎士比亚的“第三维”。正因为如此,一代之一代的莎士比亚的翻译与言说,汇入与成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既“超出了莎士比亚自身”,又或许不再是莎士比亚。
注释
[1]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1.
[2]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337.
[3]李伟民.阶级、阶级斗争与莎学研究——莎士比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J].四川戏剧,2000(03):7.
[4]李伟民.莎士比亚批评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J].上海文化,2016(08):35-36.
[5]黄发有.当代文学的接续与更新——基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的文学史考察[J].文学评论,2018(05):176.
[6]吴兴华.吴兴华诗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8][匈牙利]乔治·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1938)[A].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9]王元化.思辨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32.
[10]傅光明.俗世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史剧世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161-270.
[11][美]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M].王腊宝,张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2][美]乔治·斯坦纳.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