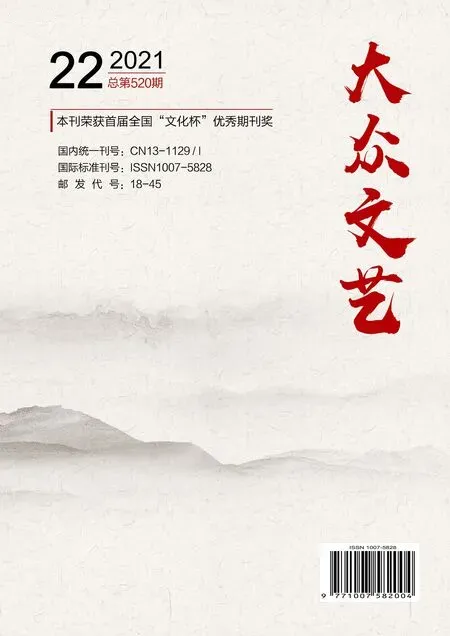电影作为伦理实验
——《无理之人》中的道德之辨
樊姝彤
(武汉传媒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伪善者与真正有道德的人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把他的焦虑看作其美德的一个肯定的抵押物,但道德性则处在对此不断询问的痛苦中。
——克尔恺郭尔
《无理之人》是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的电影作品,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却丧失目标和生存的意义的哲学教授艾伯,如何短暂地找回生命的乐趣,随即又陷入永恒的深渊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仅与两个女人纠缠不清,并以两条生命的无妄陨落为代价。学者Sinnerbrink.R在提到通过电影学习伦理的理由和意义时说,“因为电影是一种具有投射和揭示虚拟世界能力的媒介,它激发我们的情感,锻炼我们的道德想象力,质疑我们的信仰”。事实上,人们其实有很多途径来思考伦理问题,如通过新闻或者小说:新闻作为真实的事件,按理说应比电影有更佳的说服力和现实意义;而小说和叙事电影相似,同样具有叙事性,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故事,使观众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事情的真相并作出伦理判断。但电影和二者相比而言优越性更多地体现在电影可以同时兼具新闻所带来的真实性——也就是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又可以具备多角度叙事的可能性——从不同的人物出发讲述同一个故事,因此被视为极佳的进行伦理实验的装置。在《无理之人》这部电影中,伍迪•艾伦就主要通过艾伯非同寻常的选择和行为,向观众们提供了一次精彩的伦理实验。
艾伯在影片的一开始是一个颓废而郁郁寡欢,对生命提不起任何兴趣的哲学教授,而女学生吉尔则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想要拯救他失落的灵魂,但做了很多努力后却依旧无济于事。而真正改变艾伯的是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次可以通过行侠仗义而切实帮助他人的机会,他的生活和生命状态由此被完全改写。但在成功暗杀了法官以后,艾伯不仅没有感到一丝愧疚,还运用自己的一套诡辩的哲学理论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道德的,更可怕的是,当吉尔发现他的罪行而提出要举报他时,为了一己私欲,艾伯不惜向他的女友吉尔痛下狠手。艾伯作为哲学教授具有一套极具迷惑性的理论,而本文将基于存在主义伦理观来详细论证男主角艾伯的种种行动是一种伪善,而并非真正的道德。
一、存在主义伦理观——自由的价值和限度
波伏娃提到存在主义伦理观认为:没有行为是经过授权的,存在主义伦理学拒绝所有可能来自文明、时代和文化的先前辩护,同时拒绝一切权威原则。这表明存在主义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人的行为应该被赋予极大的自由,不应该收到外界标准的干涉,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没有限度的,Crowe.J在总结萨特时提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出了一种存在主义伦理观,即“一个人在道德上必须承认自己自由和他人自由的价值”。这意味着存在主义伦理观要求人们在重视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意识到他人的自由的重要性。另外,若想进一步探讨个体是否遵循了存在主义伦理观,在方法论上则无可避免地涉及对“选择”这一重要的存在主义话题的探讨。正如Corey,K.L.和McCurry,M.K.总结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选择的关系时提到的“存在主义的第一条原则是‘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而在创造本质时,一个人有通过行使选择的权利来决定他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由”。总的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反映了他的价值体系,因此本文将从艾伯所做的两次重要的选择入手,来对他行为的道德性进行分析。
二、存在与选择
(一)第一次选择——杀死法官
艾伯的第一次决定是在餐厅偷听到了一个母亲对某个不公正的法官诉以声嘶力竭、绝望的控诉后,艾伯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私刑的方式来帮助这位可怜母亲且不受到制裁,因为他和这位母亲理论上是素不相识的。而有勇气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他拥有运气,之前的俄罗斯转轮和游乐场事件让他觉得运气站在自己这一边,自己的予以私刑的行为不会被警方发现。然而,运气作为存在主义所强调的自主选择的反面,实则弱化了人的能动性和对命运的掌控能力。
事实上,“运气”这一主题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如电影《赛末点》就是围绕运气这一概念展开的,有学者将影片中男主角克里斯的运气概念与列维纳斯所描述的道德被动结合在一起,认为克里斯对幸运生活的追求构成了一种道德意识,它既塑造了他,又使他在寻求救赎和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方面容易失败,因为自我享受是在绝对孤独的幻觉下进行的,但这种幻觉却被另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存在所粉碎,这表明克里斯对运气的追求是不可靠的,极易被打破的,因为人们无可避免地与他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同样,在这部电影里,成就艾伯第一次谋杀成果的因素“运气”,也同样最后导致了他的死亡。若不是手电筒在关键时刻从包里跑出来,艾伯也不会踩到手电筒,随即滑倒,并且跌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中导致身亡。而这手电筒是在游乐园里,艾伯凭借自己的好运气为吉尔赢得的礼物。因此,这里的运气产生了矛盾性,他似乎是无用的,同样又是决定性的。导演仿佛在用戏谑的方式表达:运气是不可靠的。
第二个理由是基于,他认为这个行为是道德的,是能够切实地帮助他人的。正如在影片前半段艾伯刚刚来到学校,同事们接待他时提到他写过一篇有名的关于情境伦理学的文章,他在此处做出选择所基于的道德观就是一种情境主义,正如Dimmock,M.,&Fisher,A.评论情境主义伦理学时说,情境主义提出,“一项道德法则是,我们应该始终采取行动,以便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爱”。这种伦理观以结果为导向,只要结果能够给大部分人带来最多的爱,那无论手段如何,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而艾伯在此时的去杀害法官的行为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他认为杀害那个无良的法官能够为那位可怜的母亲和孩子带来希望,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这个第二点理由,事实上很容易被推翻,因为他听到的只是母亲那一方的一面之词,并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实,他并没有对案情和真相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核实,因此他的这个决定是不严谨的。
(二)第二次选择——杀死女友吉尔
在审视艾伯的第二次重要选择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第一次选择以及第一次行动给艾伯带来了什么。在这个决定之前,他酗酒,没有目标,也没有生命的渴望,甚至没有性欲。但在这个决定之后,他开始对食物、对享乐、对生命有了渴望。这里印证了波伏娃提到的人的生存具有模糊性,波伏娃认为,人作为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存在是人的境遇模糊性的根源,在艾伯这里精神和物质的需求和快感则发生了相互的融合交叉。如果说最开始是因为艾伯在头脑中做出了这个决定而在身体上获得了快感,那么后来再做出第二次杀人的决定之前,更多的是因为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物质和肉体的快感而迫使他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在这时,人在精神和物质中同时生存的论述得到应征,二者相互影响。
艾伯的第二个选择是杀掉吉尔,逃脱法律的审判,并且逃亡到欧洲,继续享乐。如果说第一次杀掉法官的行为还是出于他内心所谓的“善意”,那么第二次杀人行为则完全沦为了满足私欲的行为。如果吉尔把他告发,那么即使艾伯杀人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可避免地会在现代法律系统里受到制裁和惩罚,艾伯自己也知道,这种惩罚将会是严苛的。而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慢慢享受充实生活以及物欲的乐趣,开始能够像正常人那样享受生活了,他此刻和影片开始时的状态已截然不同,他已经无法割舍这种自在享受生活的乐趣,于是他必须杀掉吉尔——这个唯一的知情人。另外,波伏娃也提道:“暴君和善良的人的区别,就是前者对其目的的肯定性,而后者则处于不停的自问之中:我所做的是否有益于人们的解放?”而在影片中,艾伯对自己目的一直都保持了绝对的确信,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道德且没有过错的,且丝毫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可能损害的牺牲者,因此综合艾伯的两次行为,以及行为前的动机,可以推断艾伯的行为并非真正的道德,而是一种伪善和暴君的行为。
三、结语
事实上,伍迪艾伦的电影《赛末点》《罪与错》《独家新闻》都探讨了类似的伦理困境,以及与运气和正义的关系。三部电影有相似之处,即主角都有谋杀行为,不同的是,有的角色摆脱了惩戒,有的受到了惩戒。这些相似主题的影片的不同变形,事实上就是电影作为伦理实验的绝佳例证:也许改变一点变量,影片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和可能性。正如 John.D.M所说,“伍迪•艾伦的电影放逐为他的电影艺术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为我们的伦理关系开拓了新的视角,艾伦并没有在他的电影中创造伦理。相反,他是在发现和探索人际关系的伦理结构”。
伍迪•艾伦作为一个风格显著的电影作者,在《无理之人》这部电影中一贯地倾注了对伦理道德、存在主义哲学等主题的探讨。通过对主角艾伯的两次谋杀行动逻辑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艾伯的行为并非出于真正的道德,而是一种伪善,因为他的道德决定不仅极大程度上基于运气、极具随意性,且部分出于一种自利的主观目的。总之,本片很好地作为伍迪•艾伦电影序列中的一个补充,为观众带来了一次精彩的伦理实验,通过投射和揭示现实世界,它激发人们的情感,锻炼人们的道德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