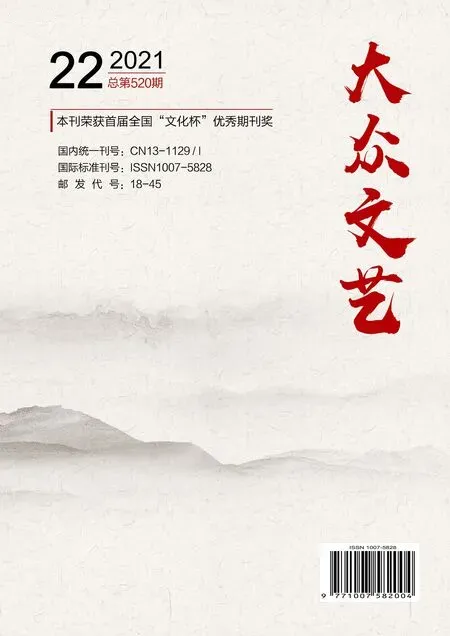浅谈形而上之“光”与光效应艺术之“光”
罗晋豪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08)
一般来说,专注表现光的绘画皆为视为光效应艺术,但真正站在公众视角上的光效应艺术源于1964年光效应艺术家在《时代》杂志采访中的自称,随后《时代》将其采访内容撰文并公布于众,这一艺术的名称和风格也随之迅速扩散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一支流派。光效应艺术家们利用印象派对于光学研究的成果、通过在画面之上绘制微妙的补色关系,表现出闪烁的光芒,虚构出对视网膜产生刺激的纯粹幻象。光效应艺术象征着抽象艺术走到如此地步,已经达到了极致,而回溯抽象思维的悸动,和对于光的痴狂,届可追溯至中世纪,中世纪的美学理念与光效应艺术必然有着深刻的联系,而形而上之“光”则在中世纪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笔者观照光效应艺术的作品时,明确感受到光效应艺术虽以形而下的光学成就为基础,然而其画面所呈现的光在本质与形而上之“光”必然存在着关联,要探究这一联系,需对形而上之“光”在西方历史视角的理念演变以及艺术中的应用加以探究以寻求其脉络。
在原始的太阳崇拜中已潜藏形而上之“光”的特质;希腊神话中的光明之神埃忒尔(即以太)象征形而上之“光”,泰坦神族的赫利俄斯(即太阳)象征形而下之“光”。而在希腊早期自然哲学中,西方哲学之父泰利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此时并没有光的一席之地,但恩培多克勒认为土、气、火、水为万物之源,其中火为世界本源,火所包含的“明亮”属性则与光相关。在巫术仪式中,祭祀在“阿多尼斯苗圃”中通过点火召唤阳光,将光判定为火的从属。柏拉图划分火的类别,将一类火定义为眼睛提供光明的火,该火即是所谓的光,柏拉图提出万物流变的现实世界与本质永恒的理式世界的理念论,在“洞穴比喻”中将太阳比作理式世界的最高理式——善,将太阳神圣化的同时,也赋予了太阳所散发的光的神圣性,太阳产生的光可使认识者拥有认识“理式”的能力,柏拉图认为的人眼与灵魂相关,灵魂来自理式世界,分有至高理式的性质(以太阳发光的形式),柏拉图曾表“星辰最美丽”,人类用肉眼观照天体,所观照的美丽是天体光明之美,又因光其可为眼睛观察的“可见性”成为物质世界与理式世界的媒介。在《斐德诺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到灵魂在未坠入尘世之前在天上见到“美本身”,称其是“光辉灿烂的”。故光即美,这种美被称为“美本身”。亚里士多德遵循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秩序与比例,而将光定义为颜色,规定了光的物理属性,即所谓形而下之“光”。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现代科学定义的光的缘起,亦是印象派至光效应艺术的应用源头,但是将形而上之“光”应用至美术创作中仍是中世纪艺术的主流,不过形而上之“光”的应用多是精神层面,中世纪闪烁的光仍表明艺术家对形而下之“光”形式的遵循,即使较为浅薄,但亦是制作画面的基础,但目的与印象派不大相同,仍是传达形而上之“光”的神圣。
中世纪美学以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传统,公元4世纪合法化的基督教信仰又奠定了中世纪美学,柏拉图主义的至高理式、理式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观点与基督教的上帝,上帝与人的关系存在契合。新柏拉图主义的诞生使体系化的基督教神学成为可能,形而上之“光”依托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深远影响,其进一步的神圣化成为必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认为最高理式为太一,太一无法被限定,因其自身的完满性必然向外流溢,但因其至高特性并不会减损自身,流溢以光的形式呈现,神圣之光照亮黑暗混沌,所以光是万物可见的因,太一向外发光创造世界,首先创造与物质世界分离的纯粹理智(美本身),理智以光为形式流溢灵魂,是现实世界与理式世界的媒介,其部分追逐理式,部分与来自黑暗混沌的质料结合产生现实世界,完善至不完善的流溢过程都是以光作为形式展现,视觉美正是与质料结合后的灵魂通过眼睛看见了与自身相同的形式,即看见了光的流溢,从而感受神圣性。形而上之“光”的崇高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圣奥古斯丁的光照论则将光拔高到全新的高度,奥古斯丁认为形式(理式)存在于上帝心中,最高理式即是上帝,美来自上帝,光的流溢是认识到上帝的必要条件,是使事物被理解的理由。波那文都继承其理念认为上帝是存在本身,心灵的认识需要通过感觉至想象至判断,而判断需要遵循法则,法则流溢自上帝,以光的形式照耀。拜占庭帝国的美学家假托雅典法官狄奥尼修斯之名著述,将绝对美视为最高理式,而绝对美正是上帝,上帝是美的动因,以光照耀万物分有绝对美。这些对于光的神圣定义与《旧约》近似。也许正是由于“光”本身所具有的非质料(物质)性和活动性、能动性,使得希伯来人赋予了它一种精神性的品质,并把这种品质和上帝的创造性、无所不在的神性或神秘性联系在一起。
根据基督教神学,无论如何描摹,其形象都远离真正的上帝,因上帝原型不可模仿,即使模仿到极致也是滞留在物质世界,那么正相反,不模仿也许会接近上帝,所以中世纪艺术家们以强烈的感性形式外化神的精神形象,观者在观摩图像志时不会因刻意“还原”的形象而停留于观照的对象,而追求其对立面,从不完善到完善,回归永恒上帝。中世纪美学消解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模仿,其物质光与精神光的划分具有抽象思辨意味,在宗教疯狂之下,中世纪美学依然有着柏拉图式理性,其追求内心的抽象思辨与刻意偏离的描绘对现代美术的抽象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基督徒毁灭了艺术,却以形而上之“光”为手段创造了新的艺术,自觉强调宗教狂热的象征性,否定艺术本体的价值,却不自觉提升了艺术主体的价值,在光效应艺术中这种抽象性达到了从内向外转变的极致。光在中世纪美术中的应用可见于各类圣像画,哥特式教堂光怪陆离的彩色玻璃花窗也诱导人们产生幻想,这些花窗因其构造的展现给人以强烈的主观精神性,个人的感受远多于古希腊罗马式测量的特质,一切外在形式都服从于内在精神的自觉,颇具“有意味的形式”的特性,自然光透过玻璃照耀在教堂内景,教徒沐浴其中,神情肃穆,充盈着神秘的气氛,此刻,形而下之“光”转变为具有普遍的神圣性与象征超越的形而上之“光”,在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人们觉得只要身处其中并潜心祈祷,就能以有限的感官追逐无限的真理,使其灵魂仿佛回溯到上帝身边,获得终极解脱。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产力提升,资产阶级崛起,教廷掌控力减弱,世俗化精神抬头,光的神秘性衰弱,使抽象思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到了19世纪至20世纪,农学与医学的进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科学主义在阶级意义上日益衰弱宗教的统辖之下逐渐跃起占据人们的内心,物质世界的充裕、战争的狂乱、思想的解放使人们重新回归内心的思考,光学的研究也有了显著跨越,印象派沉醉于自然光色,修拉更是埋头于光谱色彩的实验,这里的光早已失去了宗教性,是彻底的形而下之“光”,光的表现即是画面的基础,亦是画面的目的,将形而下之“光”探索至极致,形而上之“光”的运用处于艺术创作的边缘,然而光效应艺术以印象派的“技术革命”和科学精神的基底,以艺术变革的抽象形式将形而上之“光”再度显现。光效应艺术在绘制时常用直尺和圆规等工具,画面效果具工业设计感,强调现代化的理性。“这些作品不仅是作为一张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感觉反应的激发者而存在。”光效应艺术展现在观者面前的是纯粹图形,并非还原某一广为所知的主题或对象,作者也刻意回避笔触表现,抗拒所谓艺术性的表层表达,但这种拒绝却构造全新的表现法则,这与中世纪的毁灭却又创造的艺术有着暗合的亲近,光效应艺术利用技术表现形而下之“光”是无可争议且无法逃避的,然而与印象派仅停留于形而下之“光”不同,光效应艺术中的光与中世纪美学中的光都有着形而上的目的,本质上都是形而上之“光”,从圣像画画面的表面出发却又离开画面诉诸自我感觉的体验与光效应艺术制造的幻觉有着近似的情感律动。不过光效应艺术与中世纪形而上之“光”承载的含义不同,创作者因时代原因会改变创作的意图,艺术品承载着作者的诉求与作者所处社会的时代精神,光效应艺术亦是对时代的一种面对以及反馈,其中的光传递着形而上的现代化思维、现代社会城市化的疏离之感、充盈着科学主义的思维模式与超越一切的秩序,在内承载着理性的内核,这与中世纪美学有着明确的关联,正是这种理性,为这两种艺术的形而上之“光”的呈现提供了空隙,缔造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桥梁,而非单纯地在形而上或形而下的领域中反复探索。光效应艺术之光通过如连续、并列、连续并列混合的对比表现手法、空间营造,光学理论指导下的色彩的增减、画面调子的把控,构造出画面的形而下般闪烁的形而上之“光”,此光是光效应艺术传达理念、诉褚对象的首要媒介、手段,是引导观者进行精神化体验的钥匙,光效应艺术家索认为他自己所表达的东西经过了抽象化的提炼,已经超出了自然本身,即是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这一领域未必属于上帝,或许属于新的上帝: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