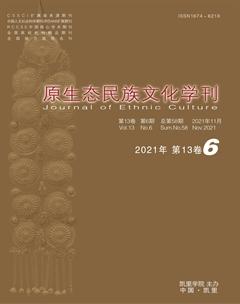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
桂榕
摘 要:新媒体与社会同步发展、相互影响,是集媒介技术、工具形态、传播生态为一体的复合性概念。20世纪末以来,新媒体在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技术及体系的创新和博物馆等文化遗产机构社会教育与服务模式的发展变革。新媒体应用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及综合性研究的特点,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数字媒体与数字遗产及遗产本体的关系、新媒体应用的社会效应、新媒体应用问题及对策三方面。与国外相比,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具有中国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特点,但在数字遗产基础理论及深层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探索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参考借鉴角度,展望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发展,可以加强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在内的遗产全方位数字化科学保护管理为基础;以推进和完善以社区(社群)为基础的新媒体社会应用实践为抓手;以强化社会公众层面的数字遗产宣传教育和参与体验,使文化遗产融入大众生活为关键内容;以发挥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为目标任务;将建立和加强数字遗产国际合作,推动跨国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鉴,作为国家文化外交重要工作内容。
关键词:国外文化遗产;新媒体应用;数字遗产;科技传媒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6 - 0060 - 13
伴随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面世,长期以来建立在物质(有形)文化遗产基础上的遗产原真性观念和历史的、文献学的遗产态度得到修正,文化遗产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静态的、僵化不变的文化遗留物,而被理解为是活的、创造性过程[1]。而遗产实践所推动的遗产观念转变,与科技传媒的发展息息相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建立全球通信网络和快速收集、传输和共享数据和思想的手段[2]。20世纪末,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率先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化遗产领域。一系列数字工具、通信技术和交互技术被用来解释和重现文化遗产,并对遗产观念构成技术、操作和参与三方面的实质性挑战[3]。对世界范围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及研究现状的梳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传媒科技影响下的人类文化遗产观念及实践的发展变化,对探索解决数字遗产所带来的深层社会文化问题及推进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
新媒体是与社会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概念。1953年,麦克鲁汉最早使用新媒体一词。而当下的新媒体主要指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移动传播)和数字媒体,涵盖传播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各种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4]。Lev Manovich认为,新媒体的逻辑与后工业社会重视个性而不是整合的逻辑一致[5]。翁秀琪强调互联网是当今新媒体应用和发展的基础设施与平台[6]。Allan H. K. Yuen认为,新媒体以数字代码和超文本作为技术手段,涵盖了大众媒体、在线媒体、平板电脑和社交媒体等。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和新媒体正在促成人类交往和社会联系新机制的出现[7]。新媒体使传播信息的流通结构从垂直传递式转变为水平网络式,融合了新旧媒体的个人化传播生态[8];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站的出现和流行,改变了大众传媒的传播格局,提供了更方便的表达方式和更丰富多样的内容[9];新媒体体现出实时性(real time)、异步性、全球化、信息空间无限、数据库、多媒体、超文本、互动性、个人化、分众化等传播特质[10]。如魏然所言,可将其视作从系统、内容、平台、传媒管道到终端的媒体生态系统;也可将其视作从内容生产、加工、平臺传送、网络服务、到终端产业的价值链[11]。综合以上观点,新媒体具有媒介技术、工具形态、传播生态、价值链等多重属性,是包容性极强的复合型概念,数字技术是其根本属性。20世纪末以来,新媒体在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技术及体系的创新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是利用新媒体对珍贵历史文献进行保护利用的标志性事件[12]。同年,美国17所知名大学和州立图书馆合作的“俄亥俄图书馆和信息网络计划”逐步发展为电子信息检索网络。1993年,美国国家图书馆实施“美国记忆”数字化平台建设计划。印第安纳大学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了传统音乐档案库,内布拉斯加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建立了惠特曼文本数字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视觉媒体中心开展了系列文化遗产收藏和虚拟艺术品展示教学实践。美国一些大学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展了系列考古文化遗址数字化保护项目[13]。199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始构建数字化图书、检索、图像数据库。法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7国成立G7全球数字图书馆项目。1999年,欧盟启动以文化遗产数字化为核心的项目,芬兰、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塞尔维亚等多国制定文化遗产数字化国家战略[14]。欧盟开展了一系列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项目,如应用于土耳其萨加拉索斯考古遗址的3D MURALE项目、创建3D虚拟展览的Arco项目、解决文化遗产信息标准化问题的CHIOS项目和推动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与观众互动的COINE项目[15]。日本国会图书馆从1994年开始实施数字化建设。2003年,韩国政府颁布“在线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基本计划”,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综合服务管理系统。2004年,“加拿大文化在线”计划启动,推出拥有数百家博物馆收藏品的虚拟博物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维多利亚历史档案馆、澳大利亚图书馆、国家电影和音响档案馆等应用数字技术进行运行管理[16]。2005年,英国宣布实施“欧洲文化和科学内容数字化协作行动计划”。2010年,欧盟发布构建整个欧洲文化遗产数字化共享资源平台的eEurope计划,英国、法国、瑞士、德国、瑞典、希腊、意大利、匈牙利、荷兰9国共同创建“欧盟文化遗产在线”(ECHO)。近年,亚太地区文化中心(ACCU)建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17]。除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系统及共享平台的建设,新媒体技术在考古遗址保护方面成效显著,实现了对吴哥窟遗址考古数字信息的绘制、阿尔蒂纳姆港城市环境的可视化数字重建、古埃及帝国的空间考古研究和意大利罗马剧院的数据重建[18]。可见,国外的新媒体应用同时覆盖了文物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和传统艺术等非遗领域,并建成世界区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合作共享体系。
(二)博物馆等文化遗产机构社会教育与服务模式的发展变革
以博物馆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博物馆通过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极大提升了博物馆藏品保管、展览展示和社会教育等基本功能。1998 年,“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概念提出后,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兴起,欧洲虚拟博物馆(European Virtual Museum)、谷歌艺术计划(Google Art Project)等较具代表性。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在20世纪后期开展了“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Global Digital Museum)。 韩国等国家于2009 年启动了“智慧博物馆”项目[19]]118 - 119。新媒体在博物馆领域的应用,造就了博物馆新的数字化服务运营模式,也改变了观众和博物馆的互动关系模式。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后,利用网站和虚拟展览的方式能够更加便捷地传播展品信息。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移动访问和超级链接成为可能。在法国,各大博物馆纷纷投身开发能够于 Apple 和 Google 平台下载的参观应用程序。最新被应用于博物馆的技术赋予了场馆和展品在虚拟领域更多可能性[20]。2000年以来,包括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和混合现实(MR)技术在内的沉浸式技术应用于非遗领域,在虚拟博物馆建设和公共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21]。人们利用博物馆的方式也在转变,多数观众通过移动设备和互联网获取来自世界范围的知识和资源,利用网络提供的内容和知识进行自我教育和学习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特征[22]。新媒体为观众与博物馆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互动方式和新的文化体验,使文化遗产不断融入社会。
总体看,新媒体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文物遗址、文献影音资料、民间艺术等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管理、教育传播及社会服务等领域,在实现世界遗产资源共享的同时,也使文化遗产通过博物馆等社会平台与普通大众有了广泛多样的接触。可以说,世界范围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引发了学术界持续的研究探讨。
二、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研究
笔者借2019年在美国访学之际,进行了相关英文文献资料的收集。检索发现,新媒体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英文成果大都发表于21世纪以来,这与新媒体在文化遗产领域开始广泛应用的时间段吻合。由于跨学科的缘故,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遗产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博物馆学、传播学、社会学、计算机通信等多个学科领域,未见专门学术刊物,涉及的学术期刊主要有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ibraries、Popular Communication、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等。目前,专题探讨新媒体与文化遗产的著作有New Heritage : 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Yehuda E. Kalay, Thomas Kvan &Janice Affleck,2007)和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A Critical Discourse(Fiona Cameron and Sarah Kenderdine,2007)两本,另有部分著作也有所涉及,如Uses of Heritage(Laurajane Smith,2006)、Global Indigenous Media(Wilson P and Steward M.,2008)、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rizpe and C. Amescua, 2013)、Heritage in Action:Making the Past in the Present(Helaine Silverman ,Emma Waterton,Steve Watson,2017)、Searching for Sharing: Heritage and Multimedia in Africa(Daniela Merolla, Mark Turin ,2017)等。这些著作多为汇集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集,研究对象和案例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及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族群。总体看,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新媒体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特色,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3方面。
(一)关于数字媒体与数字遗产、遗产本体(数字历史对象)关系的探讨
新媒体应用改变了文化遗产原来的存在形式、发展轨迹及其文化政治生态,由此产生数字遗产(digital heritage)這一新的遗产形式。在相关文献中,数字遗产也被表述为新遗产(new heritage)、虚拟遗产(virtual heritage)。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数字遗产保护指南》和《数字遗产保护宪章》,阐明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和创造性表达以数字形式产生、分发、获取和维护而创造了新的数字遗产;数字遗产包括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有的模拟资源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有关资源及信息,如文字、数据库、静止的和活动的图像、声音和图表、软件和网页等;对数字遗产的保存,包括数字信息从产生到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1相关研究基于对遗产本体与数字对象、数字媒体及技术的区辨,探讨了新媒体对文化遗产从外在的重构、解释其内在价值意义的深刻影响。如,Trinidad Rico指出,遗产的意义存在于遗产本体,而不是创建的数字对象,数字媒体只是提供了重新解释遗产管理及其呈现方式的机会[23]222。Yehuda E. Kalay从媒体理论家Lev Manovich提出的数字媒体的五个所谓一般原则和特性(数字表示、模块化、自动化、可变性和代码转换)出发,说明数字媒体已成为文化遗产再现、管理和传播的首选媒体,并影响着文化遗产的创建、管理和传播等各方面,强调数字媒体赋予文化遗产新的再现形式及能力,也因此带来新的诠释[24]。Fiona Cameron阐明遗产本体的文化身份、价值观由创造者的文化态度、学科价值及策展实践等因素塑造和建构[25];而数字媒体塑造了其生产和消费方式,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不同社会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创造性互动,使数字遗产的生命力、意义和社会价值得到体现[26];基于通讯技术,数字遗产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实践的相关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得以重塑[27]。Thomas Kvan指出,基于数字工具、通信技术和交互技术,新媒体对文化遗产的解释和重建,可能比任何旧的技术更有可能影响遗产的文化形象和意义,数字媒体已经嵌入了遗产价值和消费的循环之中,并在更广泛的遗产综合体中嵌入了制度化的实践和理念[28]。
综上可见,相关研究已深入到文化政治层面,对数字媒体与数字遗产及其遗产本体的关系,特别是新媒体应用对数字遗产及遗产本体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揭示出数字遗产及其实践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可以说,关于数字遗产社会应用的基础理论已形成,可为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二)关于新媒体应用社会效应的探讨
由于新媒体针对不同类型文化遗产会呈现不同的技术倾向,加之不同使用者的目标定位、主体性及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因此新媒体应用的社会效应是复杂多样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新媒体对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实践的社会影响,关注新媒体与遗产持有者、数字遗产的设计生产者、消费使用者(用户)等相关主体的互动。学界普遍对新媒体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效果持肯定态度。媒介理论家Ginsburg F.把媒体看作是一种社会革新手段[29];Jeff Malpas认为,新媒体利于更深入地解读文化遗产和增进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的理解和合作[30];Erik M.Champion从新遗产的5个特点(探索性空间、影子体现、社会领域、不确定性描述和可验证的历史学习)出发,认为数字媒体能提升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体验,有助于提升参与性、记忆力和更恰当的学习,虚拟遗产项目有助于创建一种社区感或一种文化存在感[31];Xiaolei Chen 和 Yehuda E. Kalay强调,虚拟遗产设计的关键是要促进不同模式和层次的解释及有意义的交互[32]。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社区(社群)和博物馆领域。
关于社区的数字遗产保护、传播与发展,研究普遍认为新媒体应用对推进遗产与日常生活、地方及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及遗产实践具有积极影响。如,Elisa Giaccardi和 Leysia Palen从遗产的社会生产视角,认为跨媒体互动(cross‐media Interaction)所创造的传播和互动空间,使社区能够参与到遗产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使地方感及遗产与生活的可持续关系加强[33];Jeff Malpas关注到在文化遗产与地方的连接中,新媒体促成的互动形式能帮助更好地理解地方、文化和身份感、遗产感,为文化传承实践提供了一个真正革命性的途径[34];Marina Svensson和Christina Maags以中国案例说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以创造出与传统文化互动的新形式,利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遗产实践和反思[35]。Ramesh Srinivasan着力于土著和少数族群社区的研究,借鉴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扁平而非层次性的根状茎可容纳多种关系和视角”的观点,提出流动本体(fluid ontologies)概念。本体是指知识被表达、解释和形式化的模式;流动本体是一组由社区成员表示的分类和语义关系,是可容纳多种关系和视角的无中心的组合及联盟形式。研究强调土著和少数族群社区在设计新媒体技术和开发项目时,须考虑当地的本体和实践,而不是沿用西方创造的知识表达;认为新媒体应用可以激发和塑造文化本体,进而影响社区保存、共享信息和开发集体基础设施的潜力,最终可能催生一种本土发展方式[36]; 结合对多元知识产权的伦理问题探讨,提出以流动本体方法设计数据库,激活社区成员,使他们不仅是用户,而且是系统的设计者,以打破西方那种固定的、等级化的、主导性的知识构建和表达方式的霸权[37]。以博物馆为主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新媒体应用研究,则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媒体应用带来的良好社会效应。如,Susan Hazan从权力的角度,认为新媒体应用与博物馆实践的整合,加强和延展了博物馆的使命,在博物馆的情境化体验、观众与博物馆互动、社会广泛参与等领域开辟了创新的道路[38];Janice Affleck和Thomas Kvan从话语的角度,认为网络媒介建构的虚拟社区为参与者创造了话语解释的环境,并对由遗产地和博物馆构建的传统制度化知识形成补充[39];Elisa Giaccardi从跨媒体互动的角度,认为虚拟博物馆模型基于多种媒体和社会实践的跨媒体交互,不仅仅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和保存遗产的工具,还可以成为社区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40];Andrea Witcomb从情感的角度,认为博物馆里的多媒体装置可以促进对展览历史和展品的情感反应[41]。
综上可见,以上研究是对数字遗产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基于地方感、社会生产、流动本体和文化本体、权力、话语、情感等理论概念和视角开展的研究,在观察、解释和评判社会行为表现及其效应方面,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魅力;而且研究普遍对新媒体应用的社会效应给予肯定性评判。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及研究结论都对中国研究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特别是Ramesh Srinivasan提出的以流动本体方法设计土著社区数据库的观点,可能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开发具有启发意义。
(三)關于新媒体应用问题及对策的探讨
新媒体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带来社会文化、政治伦理、技术、认知观念诸多方面的问题。相关议题主要有4个。
1.关于新媒体应用的技术统治与遗产价值、遗产技术民主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数字技术方法在遗产保护中广泛使用,催生了权威的技术专家,也创造了特殊类型的数字遗产主体,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个用来构建、重建和协商价值和意义的概念。近年,西方学界意识到社会和文化背景在数字技术的创造和使用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大多数技术方法未能捕捉到非物质遗产的复杂性及围绕遗址和文物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同时,对数字技术标准化的强调,体现了遗产作为一套实践和知识所面临的被忽视的危机。针对这些问题,Trinidad Rico提出,关于遗产价值及遗产技术的民主化讨论需要在实践中以利益相关者的动员为中心进行[23]224。
2.关于新媒体应用与非遗保护困境的问题。一方面,如Ke Xue等人所言,新媒体在非遗领域的应用实践和理论研究本身就相对不足[42];另一方面,近十余年,如Michael F. Brown的研究所表明的,面对媒介的巨大冲击,学术界已从曾经倡导的宽容的文化混合观转向对文化的全球流动可能危及社区文化原有真实性的警惕。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担心自己的语言、传统习俗和价值观被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文化影响所颠覆,互联网和其他信息社会的入侵已经迫使许多土著居民产生向内的保护性转变。如何平衡遗产保护目标和社会开放的价值观成为难题。此外,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技术更新之快会导致许多记录因设备过时而无法读取,数字拷贝与非数字文化遗产的边界日益模糊,遗产有形属性之外的内容、背景和流动性等无形方面易被忽视、丢失等等[43]。
3.关于理解数字遗产本质的困境。数字(虚拟)遗产研究不仅受到数字媒体所使用的技术和表现形式的影响,还受这些表现形式所鼓励或反映的潜在观念、立场的影响。在遗产作者(及其个人责任)退居幕后的真空中,人们很容易屈从于数字媒体提出的所谓科学事实,追溯信息的来源或真实性也变得更加困难。而遗产本质上是嵌入在不断变化的当代语境中的一种社会活动,数字遗产面临的挑战应是促进这种活动。为此,Neil Silberman提出,应把对数字遗产本质的追寻重点放在其作为社会历史反思工具的作用上[44]81。
4.对土著社区及少数族群问题的关注。新媒体为发展对话的交际形式提供了许多可能性,从根本上挑战了20世纪以来的工业文化的单向度。媒体在行使文化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公开表达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确保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和抵抗他者、改变身份或利益,提供了关键的空间[45]。Neil Silberman认为,在21世纪的多民族环境中,数字遗产应在承认民间传统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宗教团体、土著和少数族群,创造双向传播的信息渠道,理解和鼓励关于集体记忆的各种文化表达形式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44]89。Sherry S Yu 强调在一个日益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语言的媒体环境中,族群媒体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公共话语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6]。Jan Bender Shetle以 Mara文化遗产数字图书馆创建为例,说明有关数字遗产所有权的政治或法律问题所面临的道德和政治困境比克服巨大的技术和经济障碍更令人不安,最大的问题是涉及土著社区的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这是复杂的伦理问题[47]。Srinivasan等人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与信息研究院与新墨西哥州祖尼博物馆、文化中心合作的RDO联合项目为例,强调建立文化机构和土著团体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提倡数字博物馆按照社区利益和知识产权管理标准构建参与式目录,让文化遗产资源对象的所有权、描述和使这些对象有意义的本质完全掌握在土著社区手中[48]。
从以上相关阐释及观点态度可见,伴随新媒体在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发展,国外研究关注的问题已从新媒体技术应用层面拓展到技术伦理、数字遗产本质、非遗类型、土著社区及少数族群的文化政治、知识产权等深层社会文化层面;问题普遍聚焦于數字遗产背后的价值、伦理观念、权力话语和利益;其中,土著、少数族群及特殊群体的非遗保护及新媒体应用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这部分的探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关于数字遗产深层社会文化问题及涉及土著、少数族群及特殊群体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对中国可能具有启发意义。
综合看,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大体反映出国外文化遗产领域新媒体应用与研究齐头并进的状况;从研究与社会的关联度看,不能发现其正从新媒体技术、数字遗产属性等基础理论层面逐渐向新媒体、数字遗产与社会文化深度交融的现实层面不断拓展。关于新媒体应用社会效应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社区(社群)和博物馆两大社会公共领域层面,对新媒体在社会文化领域应用的整体效果普遍持肯定态度;而关于新媒体应用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多个现实层面,更多关注了数字遗产背后的价值观念、权力话语等内容,揭示了具体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这两个方面的应用研究正好形成互补,较全面反映了新媒体在文化遗产领域应用所带来的正负社会效应,可为中国提供预判参考和经验借鉴。
三、对中国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中外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以国家文物局2001年启动“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为起点,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在近20年取得较大进展。2010年,文化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纳入“十二五”规划。2013年,制定完成非遗数字化保护标准,并建成国家非遗数据库。2016 年,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7年,《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智慧博物馆云数据中心、公共服务及业务管理的支撑平台和体系。目前,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形式主要是网站、数字博物馆、APP、数字化出版物及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县都建立了文化遗产数据库、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数字遗产平台。以数字博物馆建设为例,2001年,中国教育部启动“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工程”。2012 年,“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上线。2005 年,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共同建设“中国数字科技馆”项目启动。2014 - 2015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确定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7 座博物馆为智慧博物馆试点单位。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阿里巴巴合作的“文创中国”平台,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智慧故宫等成为博物馆领域技术创新应用的重要示范[19]118 - 119。可见,与国外一样,我国数字遗产非常丰富,新媒体已普遍运用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社会教育服务等公共文化领域。此外,数字创意产业还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性保障可能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新媒体应用发展的一大优势和特色。但通过各种途径的检索又会发现,新媒体在国家和省级的许多文化遗产单位并未实现从保存修复到展示传播全环节的应用,大多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产品仍以视频、照片及录音等记录形式为主,面向公众的大型文化遗产数据库、数字博物馆、移动终端APP等数字化平台总体上数量有限,内容普遍缺乏交互性和延展性。
与新媒体应用进展同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大都发表于近些年。与国外研究相比,在研究议题和内容方面,国内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数字技术层面,侧重从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方式、途径和媒介效果的角度,探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发展等方面的社会效应,较少关注到新媒体技术对文化遗产本身及其社会价值意义的影响,涉及知识产权、文化政治、伦理等社会深层问题的讨论研究相对较少,对新媒体技术运用于文化遗产所产生的数字遗产方面的专门研究,尚未见深入的探讨。在研究学科领域和理论视角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传播、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博物馆、档案等学科领域,研究以具体文化遗产类型案例研究为主,个案类型及涉及范围较广,但跨学科研究和涵盖多种文化遗产类型的综合性研究相对较少。
基于中外比较可见,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具有中国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特點;在数字遗产基础理论及深层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探索方面,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社会推广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参考借鉴视角下的中国新媒体应用发展方向
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密不可分,共同服务于新媒体的应用发展。新媒体的应用发展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国,涉及文化遗产管理的最高行政机构主要是文化与旅游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国家文物局(设有文物保护与考古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从2021年5月25日文化与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简称《规划》)和国家文物局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最新精神可见,政府对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发展的强调和重视。《规划》明确了“十四五”非遗保护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1在加强非遗调查、记录和研究的任务部分,专门指出电子化、多媒体方式和大数据的应用以及数据库的建设;在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的任务部分,以专栏形式提出非遗新媒体传播计划,提出要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支持各类媒体利用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全面深入参与非遗传播和支持有关行业组织统筹直播、短视频、社交等平台力量。22021年7月18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也强调了新技术在遗产领域的使用。3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还特别指出,要鼓励社会参与,坚持惠及民生;让文化遗产成为公众的共有记忆和共同财产是可持续保护的根本。4根据以上文件精神,从可持续保护理念出发,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发展,不仅要强调技术层面的纵深发展和社会层面的宣传推广,还应注重让文化遗产真正融入百姓生活、惠及民生,这是未来新媒体应用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目标之一。当然,这是一个涉及科技、制度体系、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的复杂问题。在此,笔者仅从参考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成果的角度,就我国文化遗产领域新媒体应用发展的方向,提出以下几点设想。
1.以加强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在内的遗产全方位数字化科学保护与管理为基础。可参考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技术体系及社会教育服务模式创新的经验,推进我国从文化遗产资源库、传输管道到终端服务系统的新媒体覆盖率和应用推广面,加大各地文化遗产数据库等基础资源平台的建设,健全各地文化遗产数字化综合服务管理系统,在有条件的区域建成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合作共享体系,提升我国文化遗产领域新媒体应用的整体水平,为文化遗产高效保护传承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筑牢基础。
2.以推进和完善以社区(社群)为基础的新媒体社会应用实践为抓手。从国外研究所反馈的社会效应和主要问题看,社区(社群)往往是文化遗产领域新媒体实践的基础单位。社区(社群)不局限于地理概念意义上的某个族群、村落、社区,也包括以共同关注某个文化遗产单位或非遗项目而形成的线上社区(社群),如某个具体的博物馆、文物景点或非遗项目的爱好者网络群体。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社区(社群)往往线上线下交融,通过个体成员社会关系的延展,社区(社群)还具有社会覆盖面不断扩充的巨大潜力。正是明确的社群身份认同和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使其可以成为新媒体应用实践环节的抓手。在参考借鉴国外如何通过文化遗产激活社区(社群)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如何通过社区(社群)的数字遗产实践,使文化遗产真正成为公众的共有记忆和共同财产。
3.以强化社会公众层面的数字遗产宣传教育和参与体验,使文化遗产融入大众生活为关键内容。从国外关于数字遗产社会应用的理论反思,到通过具体案例所揭示的社会效应和问题的分析探讨,可见国外新媒体与文化遗产、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度交融。无论是关于新媒体技术、数字遗产属性的理论观点,还是从社会公共领域到具体现实层面的研究结论,国外的经验成果,对今天正处在新媒体蓬勃发展、数字遗产不断融入百姓生活的中国而言,都有着重要参考借鉴意义。当下,我国新媒体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涉及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播、数字产品开发、遗产旅游、创意产业、非遗生产性保护、非遗扶贫、非遗社会教育与公共服务等诸多层面;但同时也面临诸多亟须探索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如何通过新媒体推动非遗融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让人民群众参与保护传承和享受保护成果;如何在实践中通过科技赋能,实现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不断增强非遗生命力,等等。
4.以发挥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为任务目标。国外文化遗产与媒介研究较早关注到遗产、媒介与文化政治、国家意识形态间的联系。有学者提出,遗产与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是相互交织的,遗产是创造民族归属感的话语实践,是国家构建集体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49]。近些年,欧陆学者引领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研究甚至强调,媒介及信息传播技术已开始影响乃至控制了社会形态的构型过程[50];Ralph Schroeder通过美国、瑞典、印度和中国的比较研究,认为媒介化一方面表现为媒介对社会的日益渗透,但同时也强化了其社会文化服务功能[51]。此外,关于媒体的情感效应观点也非常有启发意义。如,认为社交媒体提供了直接接触人们情绪和情感动态的途径;情感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新媒体技术比以往更有效地利用了情绪;媒体可以唤起一种团结感,等等[52]。中国文化遗产既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结晶和现实见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外来文化冲击、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政治工具。《规划》指出,要通过深入实施非遗传承发展工程,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让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共享保护成果,不断增强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新媒体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发展无疑将是巨大的推力。此外,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新媒体应用发展,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国外有关土著、少数族群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权力话语、知识版权、数据库设计的流动本体方法论等观点,对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新媒体开发与传承传播都有一定借鉴意义。特别是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少数民族医药、传统技艺、歌舞艺术类非遗,具有推动跨文化交流、实现民族文化创新交融的潜力,若能通过新媒体的应用推广,可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5.将建立和加强数字遗产国际合作,推动跨国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鉴,作为国家文化外交重要工作内容。国外的新媒体应用已促成世界区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合作共享体系,并显现出有益于国家和地区情感共通、形成文化合力的积极作用。展望未来,中国在以文化遗产为纽带,建立国际友好关系、传扬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应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数字遗产合作,推进世界范围的遗产共享与交流合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助力,为维护国际文化秩序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BORTOLOTTO C. From Objects to Processes: Unesco'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Journal of Museum Ethnography, 2007(19):21 - 33.
[2] P. ERIC LOUW.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M].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2001:57 - 125.
[3] KVAN T. Conclusion:A Future for the Past[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304 - 313.
[4] 魏然.新媒體研究的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31):221 - 240.
[5] MANOVICH L.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M].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2:60 - 63.
[6] 翁秀琪.什么是“蜜迪亚”?重新思考媒体/媒介研究[J].传播研究与实践,2011(1):55 - 74 .
[7] YUEN A H K. The Changing Fa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ew Media, Knowledge Practices, and Multiliteracies[C]// MA W W K, YUEN A H K, PARK J et al. New Media, Knowledge Practices and Multiliteracies: HKAECT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ingapore:Springer,2015:3 - 9.
[8] 李蔡彦,郑宇君.信息科技与新媒体研究之发展[J].传播研究与实践,2011(1): 75 - 80.
[9] YI L, WEI C ,JING 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a in New Media Environment[G]// XIE Y G. New Media and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Springer,2017:25 - 46.
[10]黄懿慧.网络公共关系:研究图像与理论模式建构[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19):181 - 216.
[11]魏然.新媒体研究的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31):221 - 240.
[12]EDMONDSON R, JORDAN L, PRODAN A C.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Key Aspect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M].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2020:1 - 35.
[13]周明全,等.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6 - 12.
[14]OGNJANOVI? Z, MARINKOVI? B, ?EGAN - RADONJI? M et al. Cultural Heritage Digitization in Serbia: Standards, Policies, and Case Studies[J].Sustainability.2019,11(14).
[15]MACDONALD L. Digital Heritage Applying Digital Imaging to Cultural Heritage[M]. Oxford: Elsevier Ltd.,2006:461 - 463.
[16]彭冬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50 - 58.
[17]余日季.基于AR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开发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18]WANG X Y, LASAPONARA R, LUO L et al. Digital Heritage[M]// GUO H,GOODCHILD M F, ANNONI A. Manual of Digital Earth. Singapore: Springer.2020:565 - 591.
[19]郭骥.2018年博物馆领域技术创新报告[J].博物馆·新科技,2018(3 - 4):116 - 125.
[20]RIVI?RE P.科技與博物馆:日新月异的20年[J].班班,译.博物馆·新科技, 2018(3 - 4):10 - 17.
[21]Bekele M K, Pierdicca R, Frontoni E, et al. A Survey of Augmented, Virtual, and Mixed Reality for Cultural Heritage[J].ACM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2018,11(2):36.
[22]PROCTOR N.博物馆技术的前沿问题——23年经验的回顾与分享[J].刘清清,译.博物馆·新科技,2018(3 - 4):56 - 63.
[23]RICO T. Technologies, Technocracy, and the Promise of “Alternative” Heritage Values[G]// SILVERMAN H, WATERTON E, WATSON S. Heritage in Action:Making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2017: 217 - 230.
[24]KALAY Y E. Introduction: Preserving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Digital Media[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1 - 10.
[25]CAMERON F. Beyond the Cult of the Replicant: Museums and Historical Digital Objects[G]// CAMERON F, KENDERDINE S. 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A Critical Discour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7: 49 - 75.
[26]CAMERON F.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Authorship: The Case of Digital Heritage Collections[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170 - 184.
[27]CAMERON F, KENDERDINE S. Preface[G]// CAMERON F, KENDERDINE S. 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A Critical Discour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7:1 - 15.
[28]KVAN T. Conclusion:A Future for the Past[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304 - 313.
[29]GINSBURG F. Rethinking the Digital[G]// WILSON P , STEWARD M. Global Indigenous Media. GA: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 139.
[30]MALPAS J. Cultural Heritage:In The Age of New Media[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1 - 26.
[31]CHAMPION E M. Explorative Shadow Realms of Uncertain Histories[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185 - 206.
[32]CHEN X L, KALAY Y E, Making a Livable Place Content Design in Virtual Environment[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207 - 221.
[33]GIACCARDI E, PALEN L.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Heritage through Cross - media Interaction: Making Place for Place - mak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08,14(3):281 - 297.
[34]MALPAS J. New Media,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Sense of Place:Mapping the Conceptual Groun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08,14(3):197 - 209.
[35]SVENSSON M , MAAGS C. Mapping the Chinese Heritage Regime Ruptures, Governmentality, and Agency[G]// MAAGS C, SVENSSON M. Chinese Heritage in the Making:Experiences, Negotiations and Contestation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8:11 - 38.
[36]SRINIVASAN R. Indigenous, Ethnic and cultural articulations of New Medi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9(4):497 - 518.
[37]SRINIVASAN R. Re - thinking the Cultural Codes of New Media: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Ontology[J].New Media & Society,2012,15(2):203–223.
[38]HAZAN S.A Crisis of Authority: New Lamps for Old[G]// CAMERON F, KENDERDINE S. 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A Critical Discour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7: 133 - 147.
[39]AFFLECK J, KVAN T. Memory Capsules,Discursiv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New Media[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91 - 111.
[40]COLORADO, GIACCARDI E. Cross - Media Interaction For The Virtual Museum,Reconnecting to natural heritage in Boulder[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112 - 131.
[41]WITCOMB A. The Materiality of Virtual Technologies: A New Approach to Thinking about the Impact[G]// CAMERON F, KENDERDINE S. 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A Critical Discour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7:35 - 48.
[42]XUE K, LI Y F, MENG X X. An evaluation Model to Assess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2019(40):124–132.
[43]BROWN M F. Heritage Trouble: Recent Work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005,12:40–61.
[44]SILBERMAN N. Chasing the Unicorn? The Quest for Essence in Digital Heritage[G]// KALAY Y E, KVAN T, AFFLECK J. New Heritage:New Media and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81 - 91.
[45]COTTLE S.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2.
[46]YU S S. Ethnic Media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J].Journalism,2016:1 - 18.
[47]SHETLER J B. The Mara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Librar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igital Return of Oral Tradition[G]// MEROLLA D, TURIN M. Searching for Sharing: Heritage and Multimedia in Africa.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2017:23 - 40.
[48]SRINIVASAN R, BOAST R, FURNER J et al. Digital Museums and Diverse Cultural Knowledges: Moving Past the Traditional Catalog[J].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9,25(4): 265 - 278.
[49]HARRISON R.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M]. London: Routledge,2013:142.
[50]戴宇辰.“舊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9(4):68 - 88.
[51]SCHROEDER R. Towards a Theory of Digital Media[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 21(3):323 - 339.
[52]CURRAN J,HESMONDHALGH D,and Contributors. Media and Society[M].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2019:332 - 336.
[责任编辑:吴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