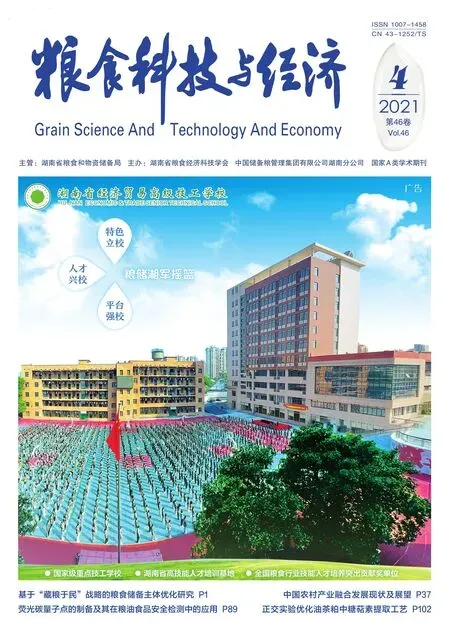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需求与政策优化
吴易雄
(1.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晋中 030801;2.湖南开放大学 终身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4)
2012年以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每年的省委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国内学者以湖南为例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的成果较丰富,如郑海燕等[1]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湖南模式”;吴易雄[2]基于湖南株洲、湘乡、平江三县市的调查,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困境与突破;米松华等[3]基于浙江、湖南、四川和安徽的调查,研究了新型职业农民的现状特征、成长路径与政策需求;王刚等[4]基于湖南涉农高职院校的实证分析,研究了涉农高职院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战略路径;汤旺利[5]基于湖南“湘农科教云”平台运用与推广,提出了开启新型职业农民线上培育新时代;王静怡[6]研究了基于高职教育资源共享的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吴易雄等[7]基于湖南省平江县的调研,分析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刘宝磊[8]研究了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的绩效评价;谭星[9]探究了湖南农村电商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但有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状况、政策需求及政策优化研究甚少。为此,笔者赴湖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县及培育机构开展深度调研,通过面对面与农民交流,走进农业农村部门、农业院校进行座谈,深入乡村了解情况,走访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217名新型职业农民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状况、政策需求和政策意见建议进行了调研,并作了深入思考。
1 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特征
1.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个体特征
从年龄看,46~59岁最多,36~45岁次之,16~35岁较少,60岁以上最少。说明湖南农民以中老年为主,青少年为辅。从性别看,男性居多,女性较少。说明男性务农成为主力军。从学历看,大专以上较多,其中博士、硕士占了一定比例,高中以下居多,小学以下最少。说明湖南尽管学历层次在不断提高,但低学历农民仍占多数。从从事的主要行业看,种养业是主业,其他行业是副业,加工、服务业比例低。说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低,农村加工业、服务业发展空间大。从现在掌握的主要技术看,懂种养技术的最多,懂其他技术的次之,懂信息技术、农产品销售技术、农用机械技术、质量安全技术、贮藏加工技术的均较低。说明亟需提升农民的贮藏加工技术、质量安全技术、农用机械技术、农产品销售技术、信息技术。从现在最缺的能力看,规模生产比例最高,经营管理和其他能力比例较少,媒体应用和组织沟通比例均最少。说明要加强农民规模生产和市场营销能力提升。
1.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特征
从对三农政策的了解情况看,不完全了解比例最高,完全了解比例居中,完全不了解比例最少。说明农民对三农政策的了解程度整体上不高,及时宣讲三农政策需要提到重要日程上。从知道如何了解三农政策看,不完全知道比例最高,完全知道和完全不知道比例相当。说明农民对三农政策了解的渠道不畅通,需要开辟多种渠道让农民了解三农政策。从所在地政府对三农政策落实情况看,没完全落实比例最高,完全没落实比例略高于完全落实。说明需要督促当地政府落实三农政策,才能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政策效果。从发展产业得到政府扶持看,超过半数的农民没完全得到,完全没得到的比例也较高,而完全得到的比例很少。说明政府扶持产业发展需要全覆盖,广大农民的产业发展积极性才能充分激发出来。
1.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特征
从主要通过何种渠道获取农业知识看,手机、电脑等媒体是首选,其次是自身实践总结,再次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通过农技推广部门、农业院校、亲朋经验交流、其他渠道获取农业知识的很少。说明新媒体是农民获取农业知识的主渠道,需要加大农技推广部门、农业院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优质资源传播农业知识的力度。从当前教育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最大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其次是教育培训次数较少,再次是教育培训时间不适宜、监督检查不到位、教育培训质量差。说明农民倾向于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培训,尤其需要的是能解决实际生产经营管理问题,通过增加教育培训的次数和加强监督检查,提升教育培训的质量。从了解三农政策的主要渠道看,首选看新闻,其次是其他渠道,再次是参加教育培训,听别人说和读报纸比例都很低。说明教育培训不是农民了解三农政策的主渠道,因而在农民参加教育培训中,需要加大三农政策宣讲力度。从接受康养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知识教育培训看,超过半数完全接受,完全没接受的比例较低,没完全接受的比例次之。说明农民接受康养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知识教育培训的意愿强烈。从最希望通过教育培训获取的知识看,首先是生产技术,其次是社会化服务技术,再次是经营技术、管理技术、三农政策,最后是其他知识。说明农民将生产技术摆在第一位,将社会化服务技术摆在第二位,因为这两项技术在农业产业链过程中至关重要,因而农民最希望通过教育培训掌握这两项技术。从最需要的教育培训方式看,首选现场指导,其次是互动教学,再次是一对一咨询、课堂讲授,最后是网络学习、专题讲座及其他方式。说明农民最需要现场指导的教育培训方式,农民遇到什么问题,教师就指导和解决什么问题,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希望通过教育培训的目的看,最多的是引领农民创业致富,其次是掌握一门以上技术,而取得教育培训证书及其他目的的比例很少。说明农民的大局意识很强,旨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重要的教育培训阶段看,普遍认为社会教育和中等教育是最重要的阶段,基础教育次之,再次是高等教育,幼儿教育最少。说明抓好社会教育和中等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至关重要。
1.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特征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扶持政策看,首要的是技术跟踪服务,其次是小额信用贷款、完善基础设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再次是农业保险全覆盖、土地集中流转和其他扶持政策。说明农民最需要专技人员提供技术跟踪服务,解决小额信用贷款、完善基础设施、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政府购买服务的类型看,首选技术服务,其次是农产品,最后是人力资源。说明技术服务和农产品是农民在生产和销售中遇到的两大难题,最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社会力量介入看,首选工商资本,其次是土地流转,最后是绩效评估。说明农民最关注的是工商资本和土地流转,解决钱从哪里来,力往何处使的问题。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文化发展看,现代文化最多,农耕文化次之,而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最少。说明在新型职业农民文化发展中,农民对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的需要很少。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职业认同看,经济效益好是首选,其次是胜任力强,最后是社会地位。说明农民追求的经济效益高于社会效益,发展经济是农民的硬核。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财政补贴类型看,种植补贴是首选,其次是社会化服务补贴,而养殖补贴与农产品加工补贴较少。说明农民亟需要全面解决的两大补贴是种植补贴和社会化服务补贴。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社会保障看,创业保险居首,其次是养老保险,再次是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说明农民的创业热情很高,但面临的创业风险也很大,农民能拥有养老保险也是农民的心声。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产业扶持看,产业项目最高,产业技术次之,产业设施最少。说明产业项目是农民发展产业的重要支撑。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土地流转方式看,村“两委”统一流转比例最高,接近一半,其次是农民自主流转,通过社会组织流转土地比例较低。说明改革现有的土地流转方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人才激励看,物质激励(奖金等)最多,精神激励(荣誉等)、政治激励(选任干部等)次之。说明农民看重的是实物,不太有精神和政治追求。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运行机制看,保障机制最高,其次是联动机制,而领导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比例接近一致,监督机制、评价机制、奖惩机制比例很少。说明建立保障机制和联动机制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机制。
2 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分析
2.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不够健全
全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目前湖南新型职业农民总量不到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2%,很难满足湖南乡村全面振兴对人才的需求,其根本原因是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体系不够健全。与外省相比,天津、甘肃两省就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均早已提供立法保障。虽然湖南也早已将农民教育培训立法问题列入省人大农业立法计划,并开展了立法调研和召开了立法听证会,但迄今尚未出台“农民教育培训条例”,因而无法可依,难以有效有力保障农民教育培训资金足额专款专用,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缓慢,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惠农政策落实督查制度执行力度不大,14.75%的农民反映所在地政府完全没有落实三农政策,35.94%的农民反映发展产业完全没得到政府扶持。
2.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不太明显
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培训,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保证粮食安全人才供给的重要手段。尽管湖南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在审计调研和整体绩效考核中得到国家审计署及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整体绩效评估组的充分肯定,但调研反映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存在问题的现象依然存在,40.09%的农民反映理论与实践脱节。此外,湖南农民参与高职扩招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全省仅衡阳市配合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完成了农学专业扩招录取300人的任务。
2.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不很充分
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调研,充分挖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求性,是确保新型职业农民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求性还没有充分挖掘,58.53%的农民反映最需要的教育培训方式是现场指导,66.82%的农民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职业认同是经济效益好,64.52%的农民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人才激励是物质激励,63.59%的农民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文化发展是现代文化,57.14%的农民完全接受康养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知识教育培训,52.53%的农民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最需要的政府购买服务类型是技术服务。
3 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优化建议
3.1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
要重点加强高素质农民发展立法制度建设。将农民教育培训立法列入省重点农业立法计划,将认定管理、教育培训、政策扶持、跟踪服务、绩效评价、社会保障和督查落实等相关方面以立法方式进行全面规范,尽快颁布实施。要重点加强高素质农民发展常态联席会议制度建设。成立以政府分管农业的领导为组长,办公、农业农村、财政、教育、科技、自然资源、人社、金融、妇联、团委、工会等多方参与的高素质农民发展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自职责,将高素质农民发展工作纳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3.2 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
要增强“双师型”教师和“乡土专家”两支农民教育培训师资力量的吸引力,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师资课酬,将课时计入职称评审教学工作量,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先、评优和晋升职称。要采取“菜单式”“订单式”确定教育培训内容,按照产业小类分级实施教育培训,对有教育培训需求的农民不受参加次数限制。要按照农业生产周期和农时季节分段安排课程,农闲时间理论学习,农忙时间现场指导,加强理论与实践紧密衔接,强化实际操作。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开展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质量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要改革高职扩招高素质农民有关工作,实行注册入学,免费就读,食宿自理,严格过程和结果管理,毕业后与招干、晋升、社保、项目等政策待遇挂钩。
3.3 适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
根据高素质农民创业需求,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四荒地”使用权和大型农用生产设备等抵押贷款覆盖面。强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每个产业投资1亿元,每个省领导负责1个产业。按照农村产业基地规模大小,实行差别化扶持政策,严厉查处虚假申报产业规模套取国家惠农资金的行为,严审示范性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评选奖励。参照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的做法,实施“定向免费培养农科生计划”,在农村服务期5年结束后在升学、晋升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坚决督查落实“谁种植、补贴谁、谁受益”的补贴政策,严厉查处虚报荒田骗取种植补贴的行为,取消已抛荒多年或根本没种植的稻田粮食补贴,增加春耕补贴项目。出台“农业生产资料规定”,保障农业生产资料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