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型翼伞 拼搏人生
马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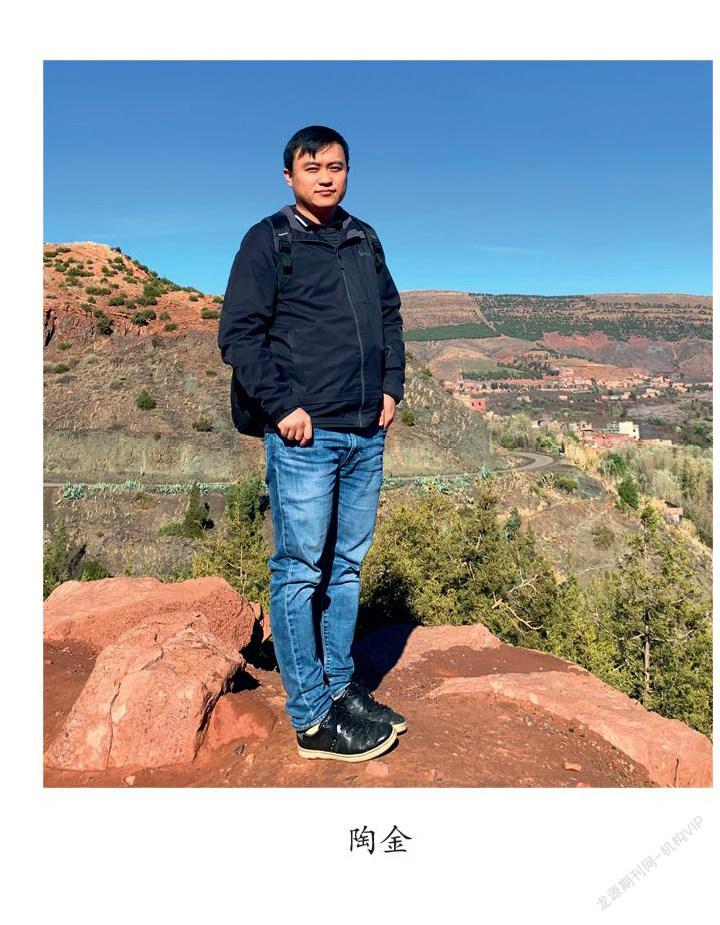
电影中,经常看到这样一幕:当火灾、水灾等重大危险降临时,人们会一边自救,一边在无能为力之时,向上天祷告,祈求神的降临。但是神并非无处不在,这时救援还需要一个个肉体存在的人。在中国,很多危险救援都是由中国子弟兵完成的,他们不是神,但他们确实也是从天而降,而帮他们实现快速救援的,就是武器——翼伞。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当时,电路破坏,道路损坏,暴雨突击,余震不断,整个汶川陷入绝境。当地面救援部队难以抵达时,空降兵成为最后的希望,极端情况下,是15名子弟兵背着翼伞完成了“惊天一跳”,为后续救援打开了一道窗口。
据了解,现在的翼伞种类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齐全,有一种武装翼伞,在极端条件救援时,跳伞员可以带着搜救犬、救援专家等一同从天而降。翼伞被科学家们进行了极大化利用。
因为具有良好的滑翔性与操控性,翼伞现如今在軍事、民用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而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翼伞未来还将在航天搭载器回收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南开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陶金及其研究团队,就是翼伞研究的主力军,在研究一个个轻型而威力巨大的翼伞时,他们的人生也变得厚重而坚实。
拼搏坚持
为充实的人生积蓄力量
微博上有一个每年都重复的热门话题:如果不考虑收入,你会做什么工作?评论区里,各种和自身职业毫不相关的选择在这里涌现。幸运的是,也有少数人将理想照进现实,并在兴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陶金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他这条路走得也是一波三折。
2004年高考结束后,从小就对机器人颇感兴趣的陶金,毫不犹豫地在高考志愿专业填报栏中写下了自动化。本科期间,他在自动化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科毕业后,他继续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深造。硕士第二年,陶金的硕士导师孔峰将他推荐给北京大学谢广明教授,在北京大学这座高等学府,陶金度过了充实的硕士生涯。硕士毕业后,他前往北京市三一重工研究本院工作,想将兴趣和职业深度结合,但烦恼也接踵而至。3年工作,让陶金摆脱稚嫩,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主任工程师。同时,他也不断思考当时专业选择的初心。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生活中,除了要学会坚持,也要学会适时转身,调整方向。思虑再三,2014年,他终于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辞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回到南开大学后,陶金选择在自动化控制方向继续前行。他深知,控制学科不是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之上。为了让科研生活尽快步入正轨,他开始高强度地投入科研工作。2014年,刚入学校不久,他就跟随导师孙青林教授从事翼伞建模与智能控制相关研究。科研工作对重新回到校园的陶金来说,并不轻松。但陶金扛住了压力,一方面快速消化吸收新的知识,另一方面灵活地将知识运用于实践。那段时间,陶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将全部精力用在难题攻克上,在他夜以继日的研究下,翼伞难控的问题最终被成功解决。2016年,他获得国家博士亚尼举升奖学金,后来,又获得南开大学周恩来奖学金,这是南开大学学生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奖项。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南开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他本人也被评为南开大学优秀毕业生。
博士毕业后,陶金选择前往芬兰阿尔托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说:“做事情必须认准一个方向,然后深入做下去,才能把事情做好。”在芬兰阿尔托大学,陶金结合自身背景,继续深研控制科学,并成功研究了一种新型声学微操纵方法。针对现有技术在生物相容性和多功能性方面仍具有较大局限性,陶金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声激励的三维微操纵方法,引入系统分析和先进控制理念,通过节点或节线间区域变化的动态能量梯度控制,实现在三维空间中同时且独立地操纵多个微物体或微物体群,而不局限于在声势陷处操纵微型对象。目前,研究已取得创新性成果。
2018年,陶金获评芬兰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获得芬兰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基金资助,继续在阿尔托大学从事科学研究。不仅如此,陶金还获得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资助,跟随谢广明教授开展控制方向研究。
在国外工作的4年,陶金像一块海绵一样,疯狂汲取知识,壮大自身,也是在整个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磨炼,他锻炼了科研思维,培养了科研自信,提高了科研素养。这为他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深厚的力量。
博士后工作结束后,陶金在众多高校伸出的橄榄枝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开大学。“首先,我对南开大学有很深的感情;其次,自由的科研氛围,浓厚的学术底蕴,对我而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在结束芬兰之行后,陶金开始在南开大学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乐观向上
向翼伞回收难关发起挑战
从博士时期开始,陶金就聚焦在翼伞领域做研究。多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他以实现翼伞系统在风雨复杂环境下的建模和精确归航为目的,通过理论分析、数值仿真和空投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翼伞系统动力学、归航轨迹规划和轨迹跟踪控制、空投试验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不断取得业内的认可。也因此,他成功申请了多项科研项目。
近3年,作为独立PI,陶金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1项,芬兰科学院博士后基金1项,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芬兰科学院一般项目2项。丰富的科研项目也带来成熟的科研成果,研究至今,陶金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会议发表SCI/EI学术论文60余篇。
随着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陶金的科研思路也在不断深入,从翼伞的控制到翼伞的航迹规划,陶金最终将目标放在了翼伞回收。他解释说:“传统的无人飞行器,都是用圆形的降落伞,但圆伞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控制飞行方向,而翼伞可以控制方向,实现无人飞行器的精准、无损回收,实现其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射成本,同时保证落区安全,因此,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研究翼伞的精准回收。”
但翼伞回收研究并不被人看好。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翼伞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因为实验费用太高,他们后来便把这项军事项目停掉了,此后多年,相关的研究热度渐渐降低,翼伞的控制研究也逐渐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中国对翼伞的研究进度并没有搁置,而是在快马加鞭中进行。在兴趣和求知欲的带动下,陶金和团队多年如一日,在科研条件水平远不如国外的情况下,不断追赶,虽然目前翼伞回收技术也还不成熟,但他们已经在原来的水平上提高了一个档次。陶金解释说:“我们课题组目前的研究方向是翼伞的自动控制,即翼伞的自动回收,包括自动航线规划、定点着陆、精准降落,这是一个全自动的过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陶金和团队提出了空地协同回收的概念。他解释说:“空中,翼伞带物降落;地面,四小车织成的多点牵引回收网,接收翼伞。这样一来,即使翼伞找不准降落点,地面的小车也能够精准移到降落点,解决翼伞着陆冲击大的问题,实现翼伞无损回收。”
陶金说:“虽然理论上已经不算新鲜了,但是用实验实现真的很难,毕竟,理论到实现确实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是,他话锋一转,笑着说:“我平时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能想好绝对不会想坏,我从来不做最坏的打算,只做最好的打算。”翼伞无损回收实验难,成本高,但只要实验中有一道缝隙,陶金也会想办法把光透进去。现在,乐观就是那道充满希望的光。
翼伞的研究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作为一名科研人员,陶金将接受挑战,促进相关科技向前发展。另一面,作为祖国的一分子,发挥自己的力量,不畏艰险、顽强拼搏,为国家安全、国防装备发展做贡献,也是应尽之责。陶金相信,虽然翼伞控制之路很长,各国竞争的力度也不小,但大浪淘沙,在团队的努力下,胜利必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