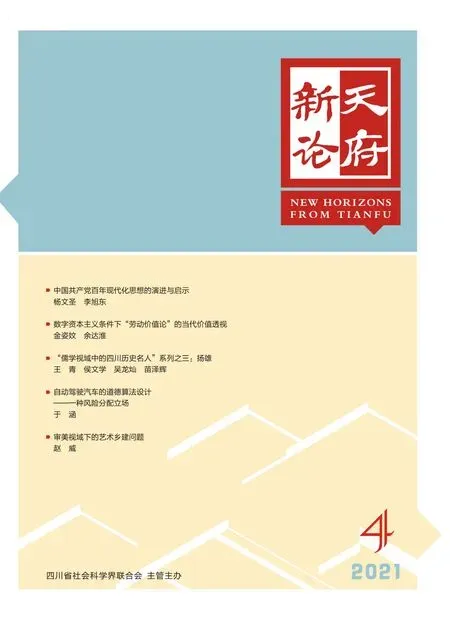征兆·语言·镜像:表情包与自我关系透视
龚 力
今天,表情包已经构成人们日常社交行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依靠技术而生,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它孕育于虚拟世界,却不可逆转地成为现实世界的物质元素。表情包起源于弥补文字语言即时交流的匮乏环节。在Web3.0时代,作为一种传播符号,表情包由其自身的丰富性与社会性而获得了文化意义。我们通过表情包的使用表达个性、彰显风格甚至释放情绪,表情包的社会功能早已超越了传播的范畴,上升为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们依据模仿机制创造了表情包,预设了表情包的使用情境,限定了表情包的使用规则,然而,我们又不断颠覆这种限制,使表情包包容了多样态的文化征候,而这种征候是人的社会性的集合体。正如语言逐渐拓宽表意的边界,表情包以一种图像化、直观化的思维方式,重塑我们的社会现实。那么,表情包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又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与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它是如何通过主体的心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它与我们有什么隐秘的关系?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最令人困惑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情感、思想与行为的内在性问题。
一、起自话语失效之处:作为征兆的显现
与文字语言不同,表情符号以“相似性”为意指原则,从而“被严格限定在视觉的维度”(1)赵宪章:《文体与图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有学者认为,表情包并不能离开文字独立地发挥作用,似乎只能是语言的一种辅助手段。从表情符号诞生的目的及其早期形态来看,的确如此。能指与所指约定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表意所抵达的准确位置与无限边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语言创造了历史。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解释,语言编织了象征世界,而在人们日常面对面交流过程中的征候(symptoms)作为一种语言无法收编的现象而被历史忽略掉了。征候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它的存在表明人之所以为人,正如彼得·L. 伯格等指出的: “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各种征候(symptoms),从而把握住对方的主体性”(2)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39页。。在早期互联网虚拟社交体验中,表情符号依据这种人的需要以“征候”的角色登场,旨在模仿面对面交谈的绘声绘色情境。它起到两方面的作用。首先,表情符号保证了意义(及情感)的准确传达,在对符号约定俗成的使用法则下,表情包的编码与解码是一一对应的。其次,它使人们更为理智。虽然表情符号在形态与结构上具有属于无意识领域的“征兆”(3)也可以理解为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症状,此处与前文出现的征候(symptoms)表达的意思一致或接近。的特征,然而,它对这种特征的表达却是一种有意识选择,它是人类积极主动表达自我的结果,体现出无意识对意识的入侵。在这一过程中,“征兆”便具备了可操控性。人们可以按照交流的需要选取适合的表情符号,以营造一种希望形成的话语氛围。换言之,表情包的使用不是表达我是什么情绪,而是呈现我应当是什么态度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表情包符合彭兰“面具说”的比喻。不可否认,在主动调度表情包的过程中,人类消解了征兆本身的破坏力。
齐泽克指出: “征兆起自词语失效之处,起自符号性交流圈(circuit of the symbolic communication)崩溃之处,它是‘以其他方式对沟通所作的延伸’。”(4)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86页,第86页。表情包的使用无疑复刻了词语失效的情形。当文字语言所包含的信息不足以表达我的情态时,表情包充当了意识状态的使者。只是不同于面对面交谈的手势与面部表情,表情包无法(或不需要)“通过阐释来消解自己”(5)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86页,第86页。。换言之,它不是“病理性”的,它为符号性交流圈所收编,它具有被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正如弗洛伊德认为的,无意识转化为意识的条件是它与语词的联系。因此,表情包仅仅是互联网社交语境下工具性的产物,它模拟了征兆的外观,却缺失了征兆的构成性意涵,使得对征兆的表达回归某种安全地带。它的本质是文化及艺术。同样,精神分析学指出,艺术(6)诺尔曼·布朗以弗洛伊德对“诙谐”的描述来指代艺术。(诙谐)“以游戏为开端,目的是从语词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得到乐趣”(7)弗洛伊德: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37页。。诺尔曼·布朗认为,艺术作为“无意识的自觉意识到有条理的表达(conscious articulation)”(8)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韦铭、冯川、伍厚恺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使被压抑的无意识获得了解放。事实上,从Web1.0 到Web3.0 时代,表情包的发展正是朝着这一趋势变化的。表情包从一种传播辅助工具演变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并以自嘲的姿态发起了对现实话语秩序的挑战。它通过自身的壮大不断超越它的功能桎梏,以改变它所遭遇的结构性处境。本质上,这是征兆驱动着表情包等文化艺术形式为其寻求现实世界出路的结果。表情包起源于对征兆的模仿,又通过抵抗(消解意义)形成了征兆本身。同时,它需要通过主体显现这种个性,即征兆能够通过文化实践被主动表达。通过文化投射的形式,表情包转变为一种自觉意识,它可以保持其最初的意义,也可以消弭这种意义。
那么,表情包是如何表现主体的征兆以获得快感的呢?或者说,这种快感是如何获取的?它进而又是如何呈现为一种社会性的狂欢?从静态的emoji到gif动图,表情包所容纳的元素更为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主体而言,一切语言(包括表情符号)都“只是他自身的对象化”(9)周文莲:《镜像、语言和无意识——从马克思到拉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1页。,主体通过表情包获得其作为个体的现实生活的表现。表情包实际上形成了社会的表征,它的涵义不断扩充,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它将一种紧张与冲突戏谑为快感的游戏。如emoji表情“笑哭”曾于2015年入选《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其原因在于,作为英美两国的社交使用高频词,“笑哭”最具代表性地说明了现代人在社会中的无奈情境与妥协心态,颇有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嘲讽意味。赵毅衡提出存在一种通过非语言(此处语言指文字语言)进行思维的直觉表意系统,即“心语说”。他认为,心语是一种内化的“语言”,它的范围远超过语言的网络,还包括又不止图像、意象及模型。当我们产生了交流的需要时,心语就会被社群语言所覆盖。我们可以反过来进行理解,图像比文字更接近心语,更贴近直觉。因此,在表意的过程中,表情符号使难以言表的征兆/心语获得了媒介性的传达,或者说它表现征兆更具有优势,不论这种表现是刻意还是无意。齐泽克将征兆比喻为“一个抵抗沟通和抵抗阐释的惰性斑点 (inertstain)。”(10)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88页。它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却有存在的必要。征兆与人类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紧密相连,它需要以某种形式浮现,而表情包提供了这种形式。
以汤圆酱家族表情包为例,该组职场篇表情包表征了社会中职场人的真实状态,刻画了“社畜”“996”“打工人”的心理过程。如表情“坐等下班”“摸鱼”“马上到”等反映了职场人混时间的工作心态,体现的是职工与老板博弈的生动情境。这些本不该在工作时间产生的行为与念头,却通过表情包的感同身受获得了情绪宣泄与“精神胜利”的快感。“我太难了”“还要改”“犯困”等表情,则以自嘲的方式消解了工作压力带来的紧张感,并增添了几分现实生活的乐感。当这种个体的征兆以群体的形式显现的时候,征兆便成了社会症候群。这时,看似具有偶然性的个体事件也能在时代中找到其必然性。表情包的媒介意义在于,它传播并整合了这种征兆。人们可以使用现有的表情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情绪特征创造表情包,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创造性地使用他人创作的表情包。而表情包通过这种使用、传播获得了生命价值,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一种集体症候。我们运用征兆、组织征兆消解压抑,获得快感。同时,它解决了征兆的“麻烦”(11)齐泽克认为,征兆是“一个能造成大量麻烦的因素,它的缺席却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即整体性的灾难”。参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2页。。换言之,在表情包的作用下,我们以维护征兆存在的方式消解征兆。表情包取代了我们的征兆,是征兆发明了表情包。
二、建构社会知识词典:作为语言的结构
表情包既然是人们对征兆表征的有意为之,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必然遭遇客体化的淹没。这时,表情包便进入了语言领域。本杰明·李·沃尔夫认为: “语言形式为情境套上某个定义,并由此做出某种程度的分析、归类,将它分配在一种世界格局中。”(12)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语言对世界有着建构性的影响。当我们在运用一种语言的时候,就是尝试在用这种语言的边界进行思考。尽管“萨丕尔—沃尔夫假说”(13)即“语言决定论”“语言相对论”。有其片面性,但语言仍然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为我们的日常生活预设好了一种秩序。这种“社会坐标”即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格局”,语言不断“把有意义的事物填充进来”,从而“为我持续提供必要的客观化”。(14)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页,第45页。这一客观化,由“词的秩序”来维持,并通过与他人共享某种知识而被奉为常态。那么,表情包是如何获得它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的呢?“人的表现性可以被客体化,也就是说,它通过人类活动的产品展现自己。”(15)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页,第45页。作为人类创造的意识产物,表情包被组织进了日常生活,获得了一种持久性与稳定性。即,表情包通过使用,将人类的主体性客体化了。虽然它起自人的情绪征兆,但一旦意义被固定,它就形成了符号性的指示,或者说它替代人类承担了某种符号性的委任。例如,我们在虚拟社交过程中,当得知在对方身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时,我们会下意识地发出“流泪”一类的表情,以表示我们对对方的关怀与理解,但事实上我们可能并没有做出任何面部表情或产生这样的情感。这时,作为身体指标的征兆便遭到了客体化,这种符号“把刻画主观意义当作自己的明确任务”(16)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7页,第49页,第189页。,以营造表意的现实感。
而这种客体化对于表情包建构人们的现实社会至关重要,即主观意向被锚定,并与主体分离,这些基于共享经验(社会症候群)的表情符号被编纂进入了一个社会知识的仓库之中。仓库或称词典,它“用以堆放丰富的意义和体验”,同时“把这些物品及时保存下来,并传给下一代”。(17)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7页,第49页,第189页。索绪尔同样指出,语言的产生是由于社群“把同样的词典发给每个人”的结果。(18)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页。词典通常“将占有主导地位的语词表达和语词意义表述成惟一的语词表达和语词意义”。(19)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而这往往巩固了某一社群的语言观,以及依据该语言观所构建的社会知识体系与行为体系。通过词典提供的知识,世界被客体化了,并成为事物的内在属性。
作为一种直观的视觉符号,在适应时代变迁与人类需求的过程中,表情包与文字语言发生了某种融合与替代。那么,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是替代效果,作为媒介的社交工具的程式设定刻意培养了人们运用表情包的习惯。以微信为例,在文字输入的过程中,但凡触及到某表情包关键词,输入框右上方就会出现表情包的备选项,可以通过便捷的操作快速地替代文字语言。比如,当在输入框中键入文字“哈哈”时,右上方会出现适应不同情境的“哈哈”表情符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聊天的情景,迅速选择符合条件的“哈哈”表情对文字进行替代,当然,前提是用户已经选择了部分表情包添加至自己的表情包词典中。这样,微信从功能上便提供了使用表情包的便利性。而表情符号“哈哈”则取代文字“哈哈”,编入了用户大脑中的信息仓库。
其次是融合效果。图像表情符号内嵌的多义性与暧昧性,决定了某些时候表情包无法独立地表意与叙事,尤其“当图像的隐喻性意指需要明确表达时,往往借助语言的引导或限定,或者说图像的意指往往需要依赖于语言文本”(20)赵宪章:《文体与图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这时,表情符号与文字符号的结合,便是两种符号系统妥协的产物,它们只为意义传达而服务。有一类表情包,其表情符号均为图像配给了文字说明。如表情“谈话结束”“你继续说”“穷醒”“超凶凶”等,如果缺失了文字指示,该类图像将会变得难于理解或产生多种解释;而如果仅仅用文字来表达此类含义,又丧失了图像本身的直观性与生动性。因此,通过这种折中的形式,图像表情被进一步收录入了现代人的话语词典,旨在保证词与意义的稳定对应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与可预见性。
通过这些方式表情包部分取代并组织进入了语言系统,它从创造者与使用者的情绪(征兆)中抽离,形成了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事实。一旦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表情包便逐渐生成了一种固化语言模式,并不需要在使用中重建其形成的原始过程。因此,在第一个层次上,它具备了可运作性,即创造了社会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形塑表情包样式规范其指涉意义的条件。如2021年2月28日,腾讯公司宣布下线“悠闲吸烟”这款emoji表情,这一措施显示了表情包文化对社会倡议的主动响应,通过对表情包词库的删除与修正,积极社会意义与主流价值观得以渗透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社会机构获得了一种文化性的把控力量。“在不断维护现实的同时,交谈工具也在不断地修正现实”(21)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7页,第49页,第189页。,一些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被剔除了,合理的现实得到巩固。在更深层次上,被客体化了的表情包处在能够反过来影响人的思维的结构性位置。也就是说,表情包的使用正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生活与思考的方式,而这一过程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皮尔斯谈道: “每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向意识提交情感、形象、概念,或其他再现作为符号。”(22)转引自赵毅衡:《思维-符号与心语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这一“提交”是人们在大脑词汇库中搜索的结果,它来源于一种社会事实,也来源于意识形态,是沉淀了的概念化与符号化的精神观念。而词库的范围即表情包客观化的程度,从某种意义而言,决定了我们思考的维度。可见,语言(这里包含表情包)仍然是思维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们的思维活动就是在语言中的词和语法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词和语法规则作为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物质材料,具体的思维就不能进行”(23)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3页。。而表情包由此也就确立了它的话语地位,它通过把自身转变为一种外部事实,“为客观化的社会世界提供了最基本的外置逻辑”(24)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3页。。换言之,表情包把一种规则的思维逻辑施加在了其语法之上。我们通过表情包调度与修正思考,一方面,基于其形态的视觉惯性加诸我们的思想系统,表象化的方式作用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我们学会使用直观的语言去驱逐抽象;另一方面,视觉的刺激又不断地提示大脑,我们该如何去表情,或者我们可以怎样表情。这将影响到我们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我们不自觉地模拟表情包的情境,并赋予了这种虚拟社交以物质意义,使之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即通过表情包“词汇”指涉行为类型或样式。可以说,表情包通过语言的机制实现了对人与社会的反向建构:媒介技术创造出新的“词域”(表情包词汇),并迅速传播,占领话语表达的领地。由此足以见得,“语言社会学建构的图景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建构的图景保持一致”(25)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
三、心理互动隐秘作用:折射“他者”与“自我”关系的镜像
事实上,人与表情包互动的过程依赖某种内在的心理情境,而这将表情包与自我的关系导向了精神分析的寓言。遭遇精神分析意味着自我与表情包的关系绝非机械的作用机制,精神分析的寓言赋予了表情包知识仓库之外的生命气质,即表情包需要应用到人的行动中、处于与人的关系中才能持续不断地获得意义,“有些概念内容只有在形象化的话语中才能够被对象化”(26)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反映》,刘萌、张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前文提及,表情包遵循“相似性”原则而被创造,它是观者基于过去经验联想出的若干视觉刺激物,而这种“相似性”指向的是人类自身。不论是“小黄脸”、动物、影视截图,抑或是自制形象,表情包临摹的对象始终是人及其之所以为人的特征。人通过表情包,标志了自身(身体)的永远在场。表情包既可以被视为人(身体)的替代物,也可以被视为自我的镜像。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人类的“一次认同”,婴儿通过镜中影像及亲人形象确立自身轮廓及自我认知,这种认同来自碎片化的身体经验,它本质上是一种误认,是一种不完整的认识。网络的匿名性或安全空间距离的幻觉,很大程度上将人们拉回到某种“退化”状态。人类使用表情包,通过表情包确立自身形象,又通过这种形象认识自己,颇类似镜像阶段的肌理。但这种认知往往是不全面的,人类通过表情包镜像所抵达的是“理想自我”(ideal ego,Idealich)。而理想自我是想象性认同的结果,即我通过成为理想自我而取悦我自己。我选择使用某一表情包,这种表情包形象就是我的镜像,它也是我为自己确认的我在社会交往中的身份。如某些年轻人使用中老年表情包,通过形成一种反讽实现代际区隔,以此标榜自己处在时代的前端。这种想象性的胜利感,往往强化了误认的无意识。
但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取悦”他人的位置。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镜像来反思自己。镜中形象(表情包)是“与一个真实事物相似的、被制造出的他者。”(27)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反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第19页,第14页,第30页。他者通常体现为与自我的区别。在表情包与自我的二元关系中,它包含于我又超出我,它是对我内心的非直观情态做出的可理解性说明。通过对真实自我的夸张、变形甚至扭曲,我看到了我。这种心理过程在面对面交流中是不具备的。在面对面交流的情境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对谈话的对象及交谈的内容做出某种表情,但这一表情的“发送”是我们不自知的,它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除非我们使用录像设备进行记录,但这种记录与反馈仍存在滞后性。换言之,我们无法凝视自己,这印证了从面部表情到表情包的过程也是符号化、客体化的过程。既然无法被客体化为一种物象进而被及时地显现,便难以觉察我们是否处于符号性认同所应安放的位置。符号性认同确认了人类的社会结构。而通过聊天工具发送表情包则制造了一种可能:我得以看见我自己,我可以审视我与他人这段对话的关系,并且这一过程能够从大脑中投射到手机屏幕上进行。当我向他人发送表情包时,这一经由选择的自我形象同样折射到了我的视域范围之内,我惊讶地发现:这就是我自己!透过屏幕,我遭遇了我自己!通过这种凝视观察到了我是什么样子、我在他人眼中是什么样子。这一虚拟形象(被映射物)依赖于我(映射物)而存在,它在社会结构中表征了我。而表情包社交为我们预留了修正的空间。我正是通过这种目光的折射,不断调整自己的外部形象,以使自己看上去更接近符号性认同的模样,即我通过获得别人的喜爱,来迎合社会的秩序。“镜像关系的核心是,我在他者中认识到我自己,但仍然进一步认识到它是一个他者。”(28)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反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第19页,第14页,第30页。在此意义上,表情包可以被视为自我关系的媒介物。我们通过他者把握自身。因此,镜像关系的本质意义在于塑造了一个“他者”,而这个“他者”与“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激发着“我”运用感性经验去诠释社会性的“我”。
镜像成立的目的在于“我”可以对镜自观,揣摩自己的举手投足。通过镜像,“我”的主体性被确立,我能够能动地调节自己的行为、选择自己的形象,我既赋予了表情包以存在意义,使之跳出客体化的机械循环,同时赋予了我自身某种个体性并能够发挥这种个体性。这种个体性就是属于我的意义,是我与他人区别的提示。尽管我们生成自己的镜像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性行为,但仍然无法排除无意识的作用。因为在精神分析学中,无意识是一个与压抑密切相关的概念,只要压抑存在,无意识便蠢蠢欲动。我们透过镜像映射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压抑”的自己,是本我与超我对抗的产物,因而这一镜像形象体现的是我的征兆,是感官上对我及我裹挟的独特生命经验的在场性还原,它使我“在象征中变得可理解”(29)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反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第19页,第14页,第30页。。只要这种特性存在于我的身上,我便“与众不同”。“镜像被理解为从世界涌向个体存在者并以它的个体性来规定它自身的所有力线(Kraftlinien)的集合点。”因此,镜像寓言将某种神话性赋予了词语秩序,“在映射的视域性之中,这些个体的独特性被建立起来”(30)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反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页,第19页,第14页,第30页。。即使我与他人使用同一表情包,但所处的位置不同,所反映的形象也有所区别,这种差别建立在连续性的经验感受中,由使用者的习惯、风格及性格等所划定。在这种差异性中,形成了我与该表情包独特的亲缘关系。如我通常习惯将某一表情符号应用于此话语情境,而他人却偏好将此表情符号运用在彼话语情境,由此便产生了不同的表达效果。当一系列风格相似的表情包不断为我释义时,我的个体标识就建立起来了。这种自我内部的镜像互动关系就由自我的分裂缝合为了与外部相对应的整体,而镜像的直观化、形象化提供了可比较的途径,它使我们回归到日常的知觉中,将我们内部世界的规律性做了视觉化处理。换言之,每个人的表情包都是“一面以它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每一个事物的整个宇宙的镜子”(31)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Metaphysische Abhandlungen”,in Hans Heinz Holz,Kleine Schriften zur Metaphysik,Darmstadt,1965,p.77.。也正是由于镜像的作用,我才能知道我怎样看待/对待我生活的世界,同时,反映了现实社会对我施加了何种程度的“力”,才使我看上去如此。表情包的镜像效应穿透了人类复杂而神秘的心灵空间,通过彼岸世界到达了此岸世界,如此往复循环,生成新的意义。
四、结 语
人类因为焦虑创造了文明,这种焦虑感书写了文化的谱系,它们被表征为症状,一方面遭到意识形态的排挤,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释放自身。当下时代,“现代性的危机”加剧了人类内心的紧张感,人类既发明了技术,又将自己关入了技术的牢笼。似乎唯有文化与艺术能够排遣这种痛苦感,能够使人类重新获得自身的主体性。于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症状与文化艺术合谋生成了对精神虚无与压抑霸权的抵抗物,表情包便是这样一种抵抗形式。它模仿症状、“美化”症状,保障症状的安全,并秘密地忠实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快乐原则,一次次地促成网络上的狂欢盛宴。而表情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因沟通而生,因而通过媒介的机制被巧妙地收入了广义的语言系统,并延续了语言的效能,即思维的语言表述性。表情包的图像思维特性部分改写了人类的表意习惯。它通过设定程式、划分类型使人们在新的知识库中行动,也使得人类活得越来越像自己的表情包。事实上,表情包本就是与人类互相建构、互相作用的自我镜像,人类通过镜像进行着某种身份认同,若过分执着于取悦自己,这将形成一种误认。镜子的作用在于,让我们能够面对它端详自己,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不断促成自我个体性的确立。最终,人的个体性被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所形塑。表情包与自我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与人类的关系、是进步与爱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