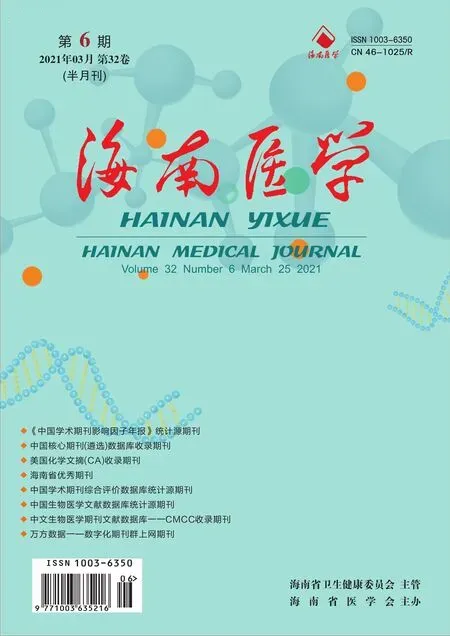结直肠癌的治疗:以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为靶点的新观点
魏颖婷 综述赵逵 审校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贵州遵义563000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有研究统计,有50%~75%的患者在诊断为CRC时已发生转移[1]。随着诊断和治疗手段的提高,早期CRC患者预后较好,但晚期患者的预后仍不容乐观[2]。近年来,新出现的证据表明,CRC细胞与其肿瘤微环境之间存在动态的互相作用,肿瘤微环境中存在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u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可以刺激CRC的增殖、迁移、侵袭、血管生成和转移,同时其也是肿瘤细胞放化疗抵抗以及免疫学治疗中不可或缺的因素[3-5]。本文就TAM在CRC治疗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做一综述,旨在为CRC的临床诊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TAM概述
TAM在传统上分为M1和M2两种极端的类型。M1巨噬细胞又被称为经典活化的巨噬细胞,其特征是产生抗原呈递分子、淋巴细胞的共刺激受体以及表达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一些促炎细胞因子(如IL-1β、IL-12、IL-6、IL-23和TNF-α)等细胞毒性物质,同时表达趋化因子CXCL9和10,招募Th1和CTL,有较高的杀菌和杀瘤活性,在抵抗病原体感染、促炎和抑制肿瘤的先天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M2巨噬细胞也被称为替代活化的巨噬细胞,可通过产生表皮生长因子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来促进肿瘤的进展及生长,同时产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促进血管生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等促进基质重塑。此外,它也产生免疫调节因子如IL-10、IL-6和TGF-β1等来抑制免疫反应,通过分泌趋化因子CXCL17、22和24等来招募Th2和Treg,具有抗炎的功能,可以促进伤口愈合、血管生成和重塑,主要在组织修复、免疫抑制和促进肿瘤进展中发挥作用[6-8]。
2 TAM与CRC
目前发现与TAM极化的相关机制有NF-κB信号通路、STAT信号通路、IRF信号通路等[9],而与CRC有关的细胞信号转导通路主要包括Wnt-β-catenin信号通路、Hedgehog信号通路、Notch信号通路、TGFβ-Smads信号通路、Jak-STAT信号通路、Ras-Raf-MAPK信号通路以及PI3K-Ak-mTOR信号通路等[10]。对TAM在CRC预后中的作用现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表明,高水平的M2巨噬细胞浸润与CRC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而M1表型巨噬细胞的存在将有利于减少CRC细胞的生长,且能给CRC患者带来更好的预后[11-14]。
3 靶向调控TAM可参与治疗CRC
TAM可以在某种刺激或诱导下从M1转变为M2,反之亦然,这赋予了巨噬细胞独有的特性,决定了TAM与癌细胞之间的不确定关系,这种能力被称为巨噬细胞的可塑性[15-16]。利用这一特性,选择性地将TAM培养或重新编程成肿瘤抑制表型可能是一种潜在治疗CRC的新观点。
3.1 M1巨噬细胞的吸引极化
3.1.1 抑制microRNA-21(miR-21)miR-21是哺乳动物细胞中含量最丰富的microRNA之一。研究发现,JAK-STAT1途径主要参与M1极化,肿瘤细胞刺激巨噬细胞miR-21的表达,直接下调STAT1,间接下调JAK2,通过抑制STAT1、JAK2和PDCD4的表达来抑制STAT1和NF-κB的激活,并防止抗肿瘤的M1极化[17]。在抑制miR-21的情况下,TAM中的STAT1和NF-κB都被激活,以驱动杀瘤的M1极化。同时,该研究发现,miR-21的抑制在体内或体外肿瘤细胞存在的情况下都可以促进TAM极化成M1样表型,提示miR-21抑制可能是靶向治疗CRC的一种潜在方向。
3.1.2 促进蛋白激酶Cα(PKCα)表达PKCα参与调节细胞周期进程、黏附和转化等多种细胞功能的信号通路。在肠道中,PKCα起着肿瘤抑制因子的作用[18]。CHENG等[19]发现,在高表达PKCα的肿瘤组织中能检测到更多的M1巨噬细胞,同时,PKCα在肿瘤中的高表达与CRC患者更好的预后明显相关,其机制为PKCα通过促进MKK3和MKK6的磷酸化来靶向激活P38,从而促进细胞因子IL-12和GM-CSF的表达和分泌,驱动巨噬细胞向M1样表型极化,以达到抑制CRC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的目的。
3.1.3 沉默Agpat4 Agpat4也被称为溶血磷脂酸酰基转移酶δ,在巨噬细胞极化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ZHANG等[20]认为Agpat4是CRC细胞中溶血磷脂酸(LPA)的主要调节因子,Agpat4的沉默诱导了CRC细胞释放LPA,并通过LPA受体1和3使巨噬细胞极化为M1样表型,这种M1激活的特点是p38/p65信号增强和促炎细胞因子增加,同时LPA可诱导M1巨噬细胞依赖的CD4+和CD8+T细胞的浸润和激活,因此猜想Agpat4/LPA/p38/p65轴可能是临床治疗CRC的多个潜在靶点。
3.1.4 TBs温控机器人和聚焦超声治疗KALYANI等[21]用生物素-链霉亲和素化学方法将低温敏感脂质体(LTSL)附着在减毒沙门氏菌膜上,合成了载热敏感脂质体沙门氏菌(Termobots,TBs),这是一种新型的温控机器人,它能在CRC细胞内主动转运附着在膜上的LTSL,以触发阿霉素释放,并在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加热(40℃~42℃)下将巨噬细胞极化为M1表型。使用沙门氏菌运输LTSL可提高肿瘤的靶向性、定位和最大耐受阿霉素剂量,不会引起严重的全身毒性,将TBs和HIFU加热相结合,可以诱导巨噬细胞相关的免疫变化,协同加强CRC化疗。这一组合技术在CRC的治疗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3.2 抑制巨噬细胞聚集和M2极化
3.2.1 在肿瘤形成晚期使用氯膦酸钠BADEER等[22]发现在肿瘤形成的晚期去除巨噬细胞可以有效地减少肿瘤的生长,这个过程与肠组织中巨噬细胞标志物和趋化因子的减少以及与CRC相关转录因子的减少有关。他们通过使用化学诱导的AOM/DSS模型,发现在肿瘤发生的晚期使用氯膦酸钠能使肿瘤数目减少约36%(特别是直径大于1 mm的肿瘤),选定的泛巨噬细胞标记物F4/80、M1标记物IL-6和M2标记物IL-13、IL-10、CCL17的表达减少,强巨噬细胞趋化因子——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的表达减少以及调节致癌过程的转录因子STAT3、p38和ERK的激活减少,猜测氯膦酸钠有可能成为治疗CRC的潜在新策略。
3.2.2 抑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信号通路EGFR信号通路在60%~80%的CRC中过表达,可以促进M1巨噬细胞向M2巨噬细胞的极化[23]。抗EGFR单克隆抗体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图单抗已被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CRC[24]。研究发现,利用西妥昔单抗治疗可抑制AOM/DSS小鼠模型Arg1、IL-10和IL-4 mRNA的表达,减少F4/80+/CD206+巨噬细胞数量,提示西妥昔单抗抑制巨噬细胞聚集和M2极化[25]。同时,经EGFR基因敲除的结肠癌细胞条件培养液可抑制M2相关标志物如Arg1、CCL17、CCL22、IL-10和IL-4的表达,并诱导巨噬细胞表达M1相关标志物如诱导型INOS、IL-12、TNF-α和CCR7。这些结果表明,抑制结肠癌细胞中EGFR信号可以阻止巨噬细胞M1到M2样极化,从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3.2.3 促进蛋白激酶N2(PKN2)的表达PKN2参与肿瘤细胞的迁移、侵袭和凋亡。研究表明,PKN2在结肠癌中起肿瘤抑制因子的作用,PKN2通过抑制结肠癌细胞IL4和IL10的表达和分泌而抑制M2极化,其机制可能为PKN2通过抑制ERK1/2的磷酸化来抑制IL4和IL10的表达[26]。在PKN2高表达的肿瘤组织中,M1巨噬细胞明显增多,而在PKN2低表达的肿瘤组织中,M2巨噬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提示肿瘤中PKN2表达越高,预后越好。
3.2.4 拮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通过促进血管生成从而促进肿瘤进展。在VEGF家族中,VEGF-A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血管生成诱导剂,VEGF-A结合并激活VEGFR-1和VEGFR-2,但一般认为VEGF-A/VEGFR-2通路是推动血管生成的主轴[27-28]。四肽Arg-Leu-Tyr-Glu(RLYE)是一种新型的VEGFR-2拮抗剂,有学者研究发现,在CRC小鼠模型中,通过将RLYE的N-末端乙酰化(Ac-RLYE),可显著提高其在血清中的稳定性,更有效地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和生长,并且通过增强肿瘤血管的内皮细胞连接和周细胞覆盖,改善血管的完整性和正常化,阻止巨噬细胞向肿瘤的浸润,并阻止巨噬细胞向M2表型的极化[29]。此外,Ac-RLYE与化疗药物伊立替康(CPT-11)联合治疗,通过改善药物进入肿瘤的灌注和输送,并刺激TAM向免疫刺激的M1样抗肿瘤表型的转化,可协同增强其抗肿瘤效果。该研究结果证明Ac-RLYE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VEGFR-2拮抗剂而用于抗血管生成肿瘤治疗以及增强化疗药物的输送和疗效。
3.2.5 运动训练除了上述药物作用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之外,MCCLELLAN等[30]观察了运动对小鼠肠道肿瘤形成模型中巨噬细胞亚群相关标志物表达的影响及与息肉特征的关系。他们使用了ApcMin/+小鼠,将其随机分为静坐(SED)和运动(EX)两组,结果发现,EX组巨噬细胞通用标志物F4/80mRNA表达明显降低,M2巨噬细胞相关标志物CD206、CCL22和Arg的mRNA表达降低,CCL17有降低趋势,M1巨噬细胞相关标记物IL-12表达也降低,但IL-23和NOS2没有变化。同时,EX组的大息肉数量比SED组少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小息肉和中型息肉的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该实验提供了关于免疫调节的重要新信息,提示运动训练可能通过影响TAM从而延缓CRC的进展。
3.3 M2巨噬细胞的重新编程
3.3.1 拮抗EP4受体前列腺素E2(PGE2)是肿瘤细胞分泌的维持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的重要调节因子,是参与CRC发病的主要前列腺素。EP4是PGE2的受体亚型之一,在髓系细胞中高水平表达。研究发现,Ep4拮抗剂降低了ApcMin/+小鼠腺瘤中ERK和PI3K-AKT-mTOR信号通路活性,抑制了M2表型标志的Arg-1mRNA和蛋白的表达,相反,作为M1表型标志的iNOSmRNA和蛋白水平都随着EP4的拮抗而增加,同时腺瘤数量和大小均受到明显抑制[31]。也就是说,EP4受体的抑制可使巨噬细胞由促肿瘤M2表型向抗肿瘤M1表型发生转变,提示髓系细胞EP4受体在大肠癌发生中的重要调控作用,并确定EP4受体可能是预防或治疗CRC的潜在靶点。
3.3.2 靶向NF-κB诱骗转染由于NF-κB是巨噬细胞极化的关键调节因子,KONO等[32]开发了一种体内TAM靶向递送系统,该系统将甘露糖修饰的泡沫脂质体/NF-κB诱饵复合物(Man-PEG泡沫脂复合物)与超声(US)照射相结合。实验结果提示,与对照组相比,经NF-κB诱骗转染和超声照射后,TAM中VEGF、MMP-9和精氨酸酶的mRNA水平显著降低,Th2细胞因子IL-10水平减低,Th1细胞因子IL-1β、TNF-α和IL-6水平升高,最重要的是,TAM靶向NF-κB诱骗转染抑制了小鼠肿瘤的生长并延长了存活率。因此,TAM靶向NF-κB诱骗转染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基于TAM表型从M2向M1转化的抗癌治疗方法。
3.3.3 激动共刺激表面受体CD40抗原特异性T细胞对抗原的有效识别依赖于特殊的抗原提呈细胞(APC)的存在,如B细胞和树突状细胞。APC通常表达共刺激表面受体CD40,它是连接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重要免疫细胞通讯介质。CD40L是CD40配体的其中一种,属于TNF超家族成员,是免疫系统的关键调节因子。MERZ等[33]开发了一种六价受体激动剂HERA-CD40L,它是一种有效的CD40激动剂,经它处理后的B细胞,NF-κB信号可以被强烈激活。将单核细胞暴露于HERA-CD40L中,可导致强大的APC的成熟,并将巨噬细胞的平衡从促肿瘤的M2型转变为支持T细胞增殖的抗肿瘤的M1表型,且其作用呈剂量依赖性。因此,通过该途径靶向操控TAM对于开发新的抗人CRC免疫治疗策略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3.3.4 地塞米松(DEX)的使用DEX已被证明通过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来破坏COX-2mRNA的稳定,从而发挥其抗炎作用[34]。有学者研究合成了氧化还原和pH双重敏感的多肽-地塞米松偶联物(L-SS-DEX),极大地促进了DEX在肿瘤组织内的蓄积[35]。在小鼠CRC模型中,经L-SS-DEX治疗后,M1型巨噬细胞和M1/M2比值增加,意味着肿瘤正从促肿瘤炎症状态向抑瘤炎症状态转变,同时,L-SS-DEX治疗组的Th1型细胞因子IFN-γ和TNF-α的表达均高于其他组,Th2型细胞因子IL-10的表达在治疗后明显降低,而其他治疗组无此作用,猜测DEX可通过降低COX-2的表达而有利于缓解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
3.3.5 抑制GTP环水解酶(GCH1)GCH1是产生必需酶辅因子四氢生物蝶呤(BH4)的关键酶。新喋呤是四氢生物蝶呤(BH4)从头合成的副产物,反映了BH4合成级联反应中限速酶GCH1的活性。新喋呤在晚期癌症中增加,并被用作癌症生物标记物,表明病理上增加的GCH1活性可能会促进肿瘤的生长。PICKERT等[36]发现,GCH1抑制剂的治疗使TAM的表型从促血管生成的M2向M1转变,表现为血浆趋化因子谱向包括CXCL10和RANTES在内的肿瘤攻击性趋化因子的转变,提示抑制GCH1活性可能会在肿瘤治疗中发挥作用。
3.3.6 抑制环氧合酶-2(COX-2)COX-2是一种炎性应激激酶,催化形成PGE2,发挥肿瘤免疫逃避的作用。研究发现,ApcMin/+小鼠息肉中TAM的浸润偏向具有交替激活的M2表型,并且息肉的细胞因子环境以Th2为主[37]。选择性COX-2抑制剂塞来昔布以IFN-γ依赖的方式,使ApcMin/+小鼠息肉中的M2 TAM向M1倾斜,并且使COX-2依赖的ApcMin/+小鼠息肉数量减少,证明了COX-2抑制剂可通过重新编程TAM的表型而减少ApcMin/+小鼠的肠腺瘤数量和大小。
4 小结
TAM根据激活方式的不同,既可攻击肿瘤细胞维持抗肿瘤免疫,也可作为肿瘤促进剂引起免疫抑制,它们通过调节肿瘤生长、获得性免疫、间质形成和血管生成来左右肿瘤的进展和转移。对CRC与TAM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及靶向调控TAM表型的表达可能有助于CRC的治疗进展。本综述总结了近年有关于调控TAM表型的科学研究方法,希望能为新型抗癌药物的研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