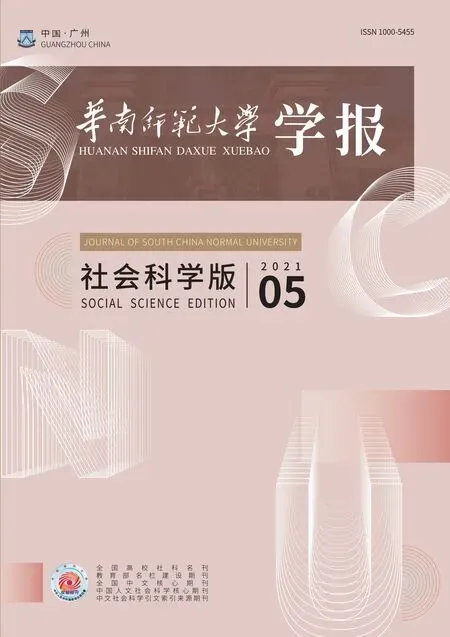“以文为诗”话题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展开
马 茂 军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006)
中国古典的诗与文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至宋代已经非常成熟,富于思辨精神的宋人展开了诗、文的文体体性探讨。陈师道《后山诗话》提出了著名的“以诗为文”和“以文为诗”的命题,总结中唐文学转型中的杜甫和韩愈的诗歌变体现象;北宋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继承了杜甫和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并且发扬光大。这种创作实践的转变,预示着中国文学从抒情传统向叙事传统的重大转型,引发了后代理论界的长期争鸣,从而促进了古代诗、文文体理论的深化发展。
一、“以文为诗”与宋代诗学的展开
“以文为诗”从杜甫已经开始,但是进行理论总结较早的是宋人陈师道 。据《后山集》卷二十三:“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①江西派权威黄庭坚针对欧阳修推崇韩愈“以文为诗”的现象作出了批评,陈师道自己没有发表意见,他引用黄庭坚的话,认为诗、文各有体,韩愈“以文为诗”,杜甫“以诗为文”,故不工,从诗歌体裁辨体角度提出了诗歌“本色论”的问题。
如果细细考证,“以文为诗”的说法源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其中对“以文为诗”的背景分析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得其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螘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1)欧阳修:《六一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第272页。
对诗、文的态度,魏晋以来有三变。六朝文笔之辨,推崇韵文,以为笔是韵文之余,是一变。在唐代韩愈那里,以诗为文章末事,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载道,诗歌是余事,所以“以文为诗”,将诗歌的内容从个人的抒情变为家国天下,表达方式也多了叙事和议论,是二变。“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的提法代表了儒家的态度。“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以叙事为诗,从抒情转为叙事,是杜甫诗歌在中唐的转型;韩愈进一步从诗人转型为散文家,将这种转型扩大化,开启了文的时代,预示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到来。作为政治家和主考官身份的欧阳修变唐代的诗赋取士为以文取士,是文的传统的政治定型化和制度化。其时诗歌式微,欧阳修在文人和诗人的使命感驱动下,仍然推崇诗歌,甚至推崇格律。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是唐宋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是旧时代的终结者,也是新时代的开创者,具有开拓者的开放胸怀和气度。他表扬韩愈在格律内的纵横恣肆,笔力强健,无施不可,自是天下至工,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评价很高。北宋后期,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流行,守成期的黄庭坚对待韩愈的立场又不尽相同。黄庭坚与陈师道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坚持传统诗法理论的回归,强调文体说与诗法说,认为诗、文各有体,则文体无高下之别;杜甫之诗法,韩愈之文法也,韩愈“以文为诗”,杜甫“以诗为文”,都是变体,故不工尔。很明显,黄庭坚坚持大雅,不喜欢变体,甚至认为杜甫的诗歌也不工。
然而,北宋是个思想繁荣、颇具开拓精神的时代,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尚。陈师道《后山诗话》还有讨论变体的其他记载:
龙图孙学士觉,喜论文,谓退之《淮西碑》,叙如书,铭如诗。
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
庄荀皆文士而有学者,其《说剑》《成相》《赋篇》与屈骚何异?
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耳。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
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此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钅刑所著小说也。(2)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309-310页。
陈师道详细描述了自韩愈开始的中唐文学转型。随着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有了自信与恢宏开放气度。文学的发展自成一体,各种文体纷纷变体,以记为论,以文为赋,以赋为记,叙如书,铭如诗,以文体为对属,以传奇为记……可见,变体成为一种趋势,成为文学繁荣的象征。但陈师道是暗含厚古薄今的批评态度的,认为今不如古,变不如正。他与同道黄庭坚是盟友。黄庭坚则更进一步,他精读史书,强调治经术,属于文化文体保守派。
北宋后期属于宋代内部的转型期和守成期。思想文化开始收紧,批评界开始反思变体,提出文体超越时代、不工、本色等问题。陈师道还将“本色论”推广到词学,而其本质是抒情与叙事、议论、言志之争。“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3)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309页。陈师道是个比较保守的文体学家,提出“本色论”,有一定见识而立场顽固(秦七黄九肯定不能代表宋词的最高水平),所以得出了一些违反文学史实际的结论。一种文体的原初状态肯定不能作为文体的正体,变才是文学史发展的主流,固守正体只能抱残守缺。唐宋词花间、南唐为一变,柳永为一变,晏殊、欧阳修又一变,苏轼又一变,周邦彦为一变,辛弃疾又一变,姜夔、吴文英又一变。秦七黄九何正之有?从词这个早熟文体,我们更能看清一种文体的快速裂变才带来繁荣的过程。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色只能拘束陈师道这样的普通人,韩愈、苏轼天才横放,还真不是本色能够拘束的。他们创造一切,开拓大天地。本色也意味着墨守成规,意味着局限和束缚。秦七黄九虽然本色,但绝非一流,陈师道的成就与见识更次一等。从本质上说,五代词的本色是抒情,柳永之变是叙事;苏东坡之变是议论,是言志;周邦彦、吴文英之变也是叙事,通过叙事、议论扩大词的容量,适应更加丰富复杂的时代与人心。“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已,彭城人。受业曾巩之门,又学诗于黄庭坚。”(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中华书局,1965,第1329页。陈师道的地位和思想与他得曾巩和黄庭坚真传有关,而此两位都是文化保守派。陈师道与欧阳修唱反调,提出“本色论”,虽然未必正确,但无疑总结了中唐的转型,将“以文为诗”问题的讨论深入化,推进了宋代诗学的演化。
“以文为诗”,诗文之辨,是文学思想内部的核心命题,几乎涵盖中古时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又是唐宋时期的核心诗人,随着以文为诗与诗文之辨关于诗歌体性论的讨论展开,不可避免地波及杜诗学、唐宋诗之争话题。每个重要的诗人、批评家都必须有所表态,参与到这个时代话题中。以杜甫为分界线,杜甫、韩愈皆是宋诗的开创者,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皆可命名为“杜韩诗派”。它不同于传统汉魏六朝诗歌的抒情传统,而是一个叙事、议论诗派。杜甫是江西诗派之祖,则“杜韩诗派”可扩展为杜甫、韩愈、黄庭坚、陈师道;就宋诗而言,代表人物非苏轼、黄庭坚莫属,“杜韩诗派”又扩展为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他们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虽然黄庭坚、陈师道对“以文为诗”有比较保守的看法,但黄庭坚创作的本质是“以文为诗”的典范,这是文学史的事实。换一种说法,“杜韩苏黄诗派”叫宋诗派,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是与唐诗派的抒情传统分庭抗礼的。
作为宋代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对杜诗学和宋诗派,创新大师苏东坡提出了更为创新的提法。《后山诗话》云:“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苏子瞻曰:‘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耳。”(5)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历代诗话》,第303-304页。陈师道的提法, 有保守的尊体意识。从诗法的角度看,诗、文各有体,诗有诗法,文有文法。体,是陈师道的价值观之一,韩愈“以文为诗”,杜甫“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工,也是陈师道的价值观之一。但陈师道旗帜鲜明、无条件地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所以陈师道也是理论与创作实践脱离的理论家,心口不一。如果说诗、文自有体,则杜甫、韩愈皆不工:杜甫有规矩,借鉴了散文技法,但是走得不是太远;韩愈走得太远,纵横恣肆,写得像议论文了。与陈师道变体观相比,苏东坡的变体观则持开放的文体观,提出了集大成的说法,认为杜甫是诗歌传统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诗文合一传统的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杜甫的集大成是创新的,“以文为诗”,统合了文的传统入诗,是开放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苏轼的看法,是在元稹所认为“杜甫是诗歌传统集大成说”基础上的创造性阐释。同样的道理,苏轼根据自己的创造实践,认为韩愈之文,其中自有诗歌的诗性,“以诗为文”,不平则鸣,抒写自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还将作诗看成文,家国天下,政治议论,“以诗为文”,诗文合一,也是一解。可见,苏东坡作为全能型文化巨匠,大气磅礴,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做出立意高远的阐释。反观陈师道作为一个儒家诗人,不能认识到干预现实的叙事和议论追求正是儒学复兴大潮下的时代命题,不亦悲乎。
从时代风气而论,陈师道心存传统古典诗歌理想,作茧自缚,狭隘的“本色论”在宋代就受到批驳,并不是主流。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秋词;‘落日绣帘卷,庭下水澄(连)空’,快哉亭词……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毎况愈下?盖其谬耳!”(6)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199-200页。阮阅对陈师道的“本色论”很不以为然,以苏轼成功的创作实践加以批驳。阮阅能够从词学发展的角度发现苏轼以叙事议论、家国情怀入词,“以文为词”开创词坛新局面的重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不仅仅是”以诗为词“,而是得风气之先,“以文为词”,以叙事议论传统入词,比柳永的以叙事入词、抒写个人悲欢离合故事又进一步,以儒家家国情怀入词,在思想、技法上都比柳永更加创新,将宋词从花间派的个人抒情传统带入了一个新时代。杰出的人总能通过创新带来革命性变革,成为规则的改变者,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普通人则只能是规则的跟从者。
随着理学的深入发展,南宋后期儒家诗学对唐宋诗之争,对“以诗为诗”“以文为诗”“以诗为文”做出了新解。文,不仅仅是体式,而是体性,是家国情怀和忠君爱国。方凤《仇仁父诗序》云:“余谓作诗,当知所主,久则自成一家。唐人之诗,以诗为文,故寄兴深,裁语婉;本朝之诗,以文为诗,故气浑雄,事精实;四灵而后,以诗为诗,故月露之清浮,烟云之纤丽。”(7)方凤:《仇仁父诗序》,载方凤撰,方勇斠补:《存雅堂遗稿斠补》,学苑出版社,2014,第80页。他对保守的“本色论”进行了反思:“四灵”最本色,他们之后的诗人“以诗为诗”,但效果如何?不过是“月露之清浮,烟云之纤丽”——过于清风明月,过于浅薄罢了。方凤还是喜欢“以诗为文”。此处的“文”,是抒写家国情怀的;这种诗歌,是文章学意义上的诗歌。所以唐人之诗是“以诗为文”。文,是体性论上的文,是家国情怀,故寄兴深、裁语婉,有家国情怀的寄寓。宋朝之诗,干脆“以文为诗”,是技法、诗法、诗性上的文,是散文化、议论化,文以载道,似乎又过了一点,故气浑雄,事精实。意象和家国情怀应该有个比例,符合黄金分割律才完美。缺少家国情怀的“以诗为诗”,只能是风花雪月的“四灵”之诗。
从批评史的角度,晚宋对“以文为诗”批评影响最大的是严羽。严羽在诗歌传统上主张诗必盛唐,全面否定宋诗派,也暗含了对杜诗派的否定。但是,当时的批评家并不认同严羽的思想,严羽并非主流。方凤《仇仁父诗序》对唐宋诗歌的看法是比较公允的,也可见晚宋诗文之辨是个时代命题。方凤谓作诗当知所主,久则自成一家;有主有辅,但要自成一家。金元人面对唐宋诗歌的丰富遗产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唐代诗歌发达,诗歌功能强大,除承载抒情功能外,还可以承担文以言志载道的双重功能,所以是“以诗为文”。这里的“为文”是为文的功能、体性,不是技巧,所以唐诗派寄兴深;在写作技巧上还是“以诗为诗”,所以裁语婉。而宋诗派则是另外一番模样。宋人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宋代新儒学的洗礼,理性主义流行,诗性相对少了一点,所以惯性的以散文的思维、技巧和功能来写诗,因此出现了严羽批判的“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但《仇仁父诗序》却强调宋诗别是一家,宋诗自有自己的风味、特点、长处,“本朝之诗以文为诗,故气浑雄,事精实”。方凤的意思大概是有所主,有所辅,博采众长,不主一家。故四灵派“以诗为诗”他也能看到优点,“四灵而后以诗为诗,故月露之清浮,烟云之纤丽”。同时,对纯粹的“以诗为诗”传统反而有所保留了。这是诗文之辨的新的高度和认识,是创新主义者的价值观,打破了墨守成规。而学杜甫的意义,就是东坡集大成的意义了,是“以文为诗”“以诗为文”“以诗为诗”的三合一了;不仅仅纠结于诗与文之分,而是能够肯定诗与文之合,也更能对诗歌提出高境界高标准的要求,是一种开放的文学观、文体观。这是“杜韩诗派”的观点,是“苏黄诗派”的观点,也是唐宋诗之争及唐宋诗之别。
从时间节点上看,与诗歌创作实践相对应,批评界在中唐、北宋这一“以文为诗”及宋诗派的形成、拓展、实践阶段,一般比较鼓励“以文为诗”和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实践。这一时期文人创作发达,对新生事物保持强烈兴趣,没有过于强调辨体。可以说,“以文为诗”是江西诗派、宋诗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石及创作实践的重要手段,是中华民族经历了隋唐的力量与激情之后,再度强调思想、强调理性这样一种思潮在文学和创作上的反映,是儒家人文关怀思想再度成为民族主体思想的时代要求,是杜诗学、江西诗派、宋诗派逐步奠定主流地位的一种大趋势。而文学理论的发展往往围绕“以文为诗”这一核心话题展开。杜诗学专家蔡梦弼引陈善的《扪虱新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元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所谓无出韩杜。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8)蔡梦弼:《草堂诗话》,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第29页。宋人讲究传承,讲究借题发挥,从别人理论中生发自我的观点。陈善从谢眺和唐子西的旧理论阐释“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以为诗、文的技法可以互相助益。好的诗歌应该自然流畅如散文,没有太多的跳跃、对仗之类的雕琢,而像流水对一样自然,圆美流转如弹丸,好的散文中也应该有诗的节奏和声调。陈善未能提出文中有诗意,而提出语句精确,大概是琢磨讲究、字斟句酌、强调语言的诗意化。与以前诸家不同,他的“以文为诗”,不是布局,而是语言流畅。他将“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转换为“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与大部分强调文体相克、文体谨严的观点不同。他实际上是从诗与文体性相通、体裁相生的角度出发的,是一个开明的讲究文学艺术性的文体学家,与苏东坡的集大成说也有内在关联性。“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说明这句话几乎成为一个大众参与的热门话题。
“以文为诗”的讨论,加深了杜诗学的研究深度。随着讨论的展开,对杜甫的表述从“以诗为文”转化为“以史为诗”。针对陈师道所说杜甫与韩愈“以文为诗”不工的问题,方逢辰《邵英甫诗集序》也云:
诗不必工,工于诗者,泥也诸?所以吟咏性情,足以寄吾之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辈有以放而诗者,谢灵运是也。有以狂而诗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诗者,陶渊明是也。有以穷而诗者,郊岛是也。有以怨而诗者,屈平是也。以文为诗者,昌黎;以史为诗者,少陵;以侠为诗者,非今之江湖子乎。放也,狂也,寓也,穷也,怨也,文也,史也,虽其为诗,有不能皆出于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诗,则亦各寄其情性而已。惟侠,则诗之罪人焉。邵兄英甫,吾乡之秀也,读书之隙,且寄意于吟咏,集而成编,来谒予序,予谓子非侠者也,岂其文乎?史乎?穷乎?怨乎?抑狂乎?其放乎?子以儒业其身,而志于诗,子姑以此寓性情可也,勿泥于工,请子识之。(9)方逢辰:《邵英甫文集序》,载《蛟峰文集》卷四,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798页。
这一开放的文学观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以诗为诗”是工的话,那诗不必工,吟咏可也;主张可以“以文为诗”“以史为诗”,以种种为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唯独不欣赏江湖派。其实江湖派“放也,狂也,寓也,穷也,怨也,文也”,而其所以为诗,亦各寄其个人情性而已。方逢辰大概一为纠时偏,一为警戒青年人需要关注杜甫式的家国情怀,故有此说。随着“以文为诗”讨论的展开,人们对诗、文文体的认识逐步加深,认为文学抒情性是第一性,体式是第二性;而衍生的“以史为诗”的提法,颇具创新性。可见,方逢辰觉得“以史为诗”比“以诗为文”更能概括杜甫的诗歌特点,与后来“六经皆史”的提法具有同一史学关钮与视角。这也是“以文为诗”话题深入讨论所带来的诗学理论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化。理论来源于思辨,来源于争论和撞击。
诗文之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诗与文,也影响到四六文。随着“以文为诗”的大讨论,带来了对文学本质和文学传统认识的深入,带来了思想的解放。有人拓展为“以四六为文”。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云:“而尤长于四六,近得启事数篇,观之交乎上者不谄,交乎下者不倨,且铺叙旋折,咳唾历荦如散文,每篇于颂之末,必有所规,规之末必有所劝。若施之制诰,当有彦章之得,而无景伯之失矣。陈后山有言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余于胡公四六,亦云。”(10)方逢辰:《胡德甫四六外编序》,载《蛟峰文集》卷四,见《北京图书馆古籍修本丛刊》第88册,第800页。一般认为四六文偏于雕琢,粉饰太平。而胡德甫的四六文有讽谏的精神,又铺叙旋折、咳唾历荦如散文。可见宋代散文文体发达,成为主流。各种文体均被散文的引力吸引,从散文文以载道、铺叙手法中汲取营养,向散文文体靠拢。在理性化的宋代,这是一种潮流。
儒家诗学最终在思想论争中胜出,文体探讨的结论是以本体、体性为先,体性决定体式,是本末的关系。南宋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人们讨论文体论逐步超越了“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技巧、形式之争,更加重视文章的本体性。一方面,以本体性阐释“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另一方面,直指人心,直指本体论。宋代何梦桂《潜斋文集》卷五《王樵所诗序》:“先辈谓杜工部以诗为史,韩吏部以文为诗,繇其胸中储贮博硕,然后信笔拈出,自成宫商;非抉摘刻削,求工于笔墨言语以为诗也。”(11)何梦桂:《王樵所诗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二九二,第35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第69页。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本无史、文之分,皆发自胸中,然后信笔拈出,自成宫商;非抉摘刻削,求工于笔墨言语以为诗也,削足适履,形式的过于讲究是无用的;本体是绝对的,文体是相对的。从文章的本体论到体性论再到体式论,很有高度。衍生出来的“以诗为史”的提法是杜甫诗史说的原型。这种探讨往往是杜诗学的深化,是儒家诗学深入发展的一部分。
二、诗文之辨与元代文学思想解放
元代儒学走下神坛,无疑为古典诗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松绑和自由发挥。元代是围绕“以文为诗”展开诗文之辨的重要时期,元人更多从纯文学的角度展开话题,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提出了“阳刚为文”“以质为文”“诗人之诗”“文人之诗”“诗者文之变”等重要观点,“以文为诗”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激发了元代古典诗学思想的发展。
“以文为诗”是元人不可回避的话题。元人创新地提出了“文在其中”的说法。元代王义山《稼村类稿》卷五云:“予因是而知陈君工于诗,而文在其中矣。观陈君庚辰以后之诗,后山所谓以文为诗,以诗为文也,文不在兹乎!”(12)王义山:《稼村类稿》卷五,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33页。后山所谓“以文为诗”“以诗为文”向来令人费解,王义山给了比较明确的解读;杜甫“以文为诗”,诗歌中大量应用了议论、叙事的散文技法;“以诗为文”,就是把诗歌写得具有散文的载道功能,诗歌中有家国情怀,天下责任。那么,散文的功能不就在杜诗里了吗?
元人有元人的独特气质,喜欢阳刚一派,将“以文为诗”理解为文学的阳刚风格。刘履《风雅翼》卷十三《韩文公诗十首》:“论者谓其以文为诗,故其词多奇劲雄壮,而少冲淡,然不知其于古作,殆有非冲淡者可得而及也。”(13)刘履:《风雅翼》卷十三,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第207页。韩愈“以文为诗”,文以载道,心怀家国天下,胸中一股忧郁不平之气,肯定会使文章气质偏于阳刚,平淡不下来。
“以诗为诗”与“以文为诗”的探讨,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创造实践,进一步解放了元人的思想,开拓了元人的眼界,引发了学界对传统诗文正变观的质疑。袁桷将“以文为诗”与新的正变观结合在一起,《书括苍周衡之诗编》云:
《诗》有经纬焉,诗之正也。有正变焉,后人阐益之说也。伤时之失,溢于讽刺者,果皆变乎?乐府基于汉,实本于《诗》。考其言,皆非愉悦之语。若是,则均谓之变矣欤?建安、黄初之作,婉而平,羁而不怨,拟《诗》之正,可乎?滥觞于唐,以文为诗者,韩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于其近体,犹规规然守绳墨,诗之法犹在也。宋世诸儒,一切直致,谓理即诗也,取乎平近者为贵,禅人偈语似之矣。拟诸采诗之官,诚不若是浅。苏、黄杰出,遂悉取历代言诗者之法而更变焉。音节凌厉,阐幽揭明,智析于秋毫,数殚于章亥,诗益尽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学诗者,咸宗之。括苍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束书来京师,以是编见贽。意度简远,议论雄深。法苏黄之准绳,达《骚》《选》之旨趣。历览名胜,长歌壮吟,亦皆写其平生胸中之耿郁。至于词笔,尤为雅健,读之亹亹忘味,诚有起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气,何地无奇才。感叹之余,因书此以赘其卷首,延祐六年闰八月庚申,前史官会稽袁桷书。(14)袁桷:《书括苍周衡之诗编》,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七二二,凤凰出版社,1998,第347-348页。
袁桷对“以文为诗”问题的讨论深入了很多。首先,他对传统的正变观提出质疑,认为不能将讽刺诗说成变,这不符合汉魏诗歌史的实际。唐代韩愈“以文为诗”,不平则鸣,但是仍然合乎诗法。宋代儒家诗学是主流,“以理为诗”,过于平淡,不一定合乎诗法。至于苏东坡、黄庭坚,雄放杰出,实际上是“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不平则鸣的集大成,至此诗歌的正变观实际上被颠倒了。诗歌是发展的,时代的主流诗人就是正,杜甫、韩愈、苏东坡、黄庭坚就是正。袁桷表扬青年人的诗歌“议论雄深,法苏黄之准绳”,“长歌壮吟,亦皆写其平生胸中之耿郁,至于词笔,尤为雅健,读之亹亹忘味”。文章讨论的问题高屋建瓴,涉及重大理论问题,思维敏锐,拨乱反正,很有理论意义。将“以文为诗”拓展为与议论雄放、雄放杰出、阳刚之美结合在一起,与怨而怒、哀而伤、打破中庸之道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可见,“以文为诗”往往和创造、打破、革命、狂飙突进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改革、进步和革命的动力,成为反叛的动力。
金元时代儒学中落,思想宽松,学人往往能够跳出三界,自由通达,直指文心,上趋汉魏盛唐。元好问言:“汲字伯深……自号西嵓老人。有《西嵓集》传于家。屏山为作序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谓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敎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即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耶!比读刘西嵓诗,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简而有理,澹而有味,盖学乐天而酷似之。”(15)元好问:《刘西嵓汲》,载元好问编,萧和陶点校:《中州集》“诗人小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94-95页。其创新处有三:一是以为诗无定体,各发心声、各言其志之说甚有创造性;二是认为言为心声,言而中理者谓之文,文而有节谓之诗,是一种全新的文体观,阐释了言、心、志、文、理、诗的关系,从体性及体式上划分诗与文的界限,非常新颖独到;三是颠倒诗文次序,认为文而有节谓之诗,诗歌是文章的繁缛、节奏化,故“诗者文之变”,这样的说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元代理学家吴澄从理学的角度回应讨论,将“以文为诗”提升到“以质为文”的高度。《东麓集序》云:“主簿石君以东麓张君诗文四卷示余,余读之理胜气胜,诗文以理为主,气为辅,是得其本矣。其诗不尚纤侬,不拘拘于法度,以文为诗者也。其文不尚俳丽,不屑屑于言辞,以质为文者也。”(16)吴澄:《吴文正集》卷十六,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77页。把“以文为诗”提升为“以质为文”,实际上是以理气为文,体现了元代理学家的文体观。这也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以文为诗”的儒学背景对诗学的强势影响。正是基于儒学复兴运动,才有杜甫、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和宋代对“以文为诗”的理论总结。可见文体的体性是第一位的,体式只是被决定的形式而已。吴澄所提出的“以质为文”概念,暗含与“以诗为诗”“以诗为文”的对立,大抵将骈俪、言辞看成“以诗为文”,形成文质对立的文学观。
“以质为文”是理学立场,刘将孙《养吾斋集》进一步将“以文为诗”发挥为从“诗人之诗”向“文人之诗”的时代转型,则是文学史家的立场。“诗有可改者,不可改者;篇中之句,句内之字,可改者也。长篇之曲折,不可改者也。长篇兼文体,或从中而起,或出意造作,不主故常,而收拾转换,奇怪百出。而作诗者,每不主议论,以为文人之诗,不知各有所当。诸大家固有难言者,如昌黎东坡真以文为诗者,而小律短绝回文近体,往往精绝。”(17)刘将孙:《养吾斋集》卷十,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92页。这是“以文为诗”的新解,认为长篇诗歌要有散文的波澜壮阔的文体特性,长篇之曲折,收拾转换,需要散文的章法结构才能呈现。“以文为诗”同时也是严羽批评的主议论的问题,刘将孙对严羽的看法做出了回应。刘将孙还提出了“文人之诗”的问题,将“以文为诗”“议论为诗”与“文人之诗”结合在一起,开启了“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学人之诗”的学术讨论。好发议论是“文人之诗”,“诗人之诗”过于清风明月;杜甫的议论是政治抒情诗,是儒者之诗;韩愈则是散文的章法句法而已。宋人的创作是“文人之诗”,从唐到宋,完成了“诗人之诗”到“政治之诗”“文人之诗”的转型。时代变了,士人也转型了。从“以诗为诗”到“以文为诗”,实际上是诗歌从唐代诗人之诗向宋代文人之诗的转型。诗人溺于情,文人好议论,但是文人不是纯粹的理学家,他们往往被理学家瞧不起。儒者多政治抒情诗,理学家诗歌则充斥着道学气。
三、诗文之辨与明清诗学理论的深化
明人的诗文之辨观分为两派:一是古典保守派,强调汉唐诗歌的抒情性,强调含蓄、韵味,提出文贵显、诗贵隐,诗者文之精,诗高于文的说法;一是创新派,宋诗派结合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成功的创作实践,强调时移世易,求新求变。
辨体是明代文体学的一大特点。明人强调诗必盛唐,强调抒写性情,将诗文之辨落实为唐宋诗之争,分辨唐体宋体。王用章《诗法源流》曰:“诗原于德性,发于才情,心声不同,有如其面……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18)傅若金:《诗法正论》,载王用章辑:《诗法源流》卷之上,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5册,齐鲁书社,1997,第60-61页。特别注重唐宋的区别:唐人以诗为诗,唐人直接抒情,宋人议论则偏于理性、叙事。王用章的议论已经超越“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而能够讨论才情与理性的问题。才情无疑更接近传统文学的本性,三百篇是诗歌抒情的原初榜样。
明人辨体在文体尊卑论方面提出了“诗者文之精”的说法,对元代方回的“诗者文之变”的观点做出别出心裁的反拨与回应,提出诗高于文,让诗歌重新成为强势文体。郑潜《樗菴类稿》原序:“余闻之方回先生曰:‘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然则诗之作,难言也,苟求其精,非能言,而文者不足以与此也。三百篇之作,非皆出于能文者,而语无不精,先王之教也……唐韩昌黎以文为诗,杜少陵以诗为文,各极其精,而不能以相掩,宋之苏黄犹唐之李杜也……明矣,要在乎精之而已矣。”(19)郑潜:《樗菴类稿》原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第94页。所谓精妙,是精妙的技巧、精妙的诗歌艺术和组织布局。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都是组织布局;黄庭坚、苏轼格高律熟,也是精妙。可贵的是作者强调不能贵古贱今,要考察诗歌的艺术水平;而艺术技巧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以文为诗”“以诗为文”就是诗歌艺术技巧的进步实例。李东阳认为:“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近见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为诗,则毫厘千里,终其身而不悟,然则诗果易言哉。”(20)李东阳撰,周寅宾、钱振民校点:《李东阳全集》,岳麓书社,2008,第1504页。强调诗文之分,以为诗文不同体,诗人文人才性不同;而文章家能文未必能诗,诗歌高于文章 。
明人在文体体性论方面展开辨体。车大任提出文贵显、诗贵隐的体性辨体思想,其《又答友人书》从文体学的角度讨论诗文之辨,强调辨体之严:“窃谓诗文之道,其体最严,其用最大。”(21)车大任:《又答友人书》,载余姚,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一,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4册,第2854页。车大任以为“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涉及到诗文的体用关系,而体则最严,不能混乱。“夫文贵显也,不显不足以敷畅其事情;诗贵隐也,不隐不足以见深长之味。”(22)同上。从隐显的关系讨论诗文之辨,很有见解。他对“以文为诗”和“以诗为文”的评价不高,“设若以文为诗,堕议论之窟矣,以诗为文,乏经纬之章矣”(23)同上。。这是明代文人经过中唐至宋元的创作实践后,对诗文关系有了新的全面的认识。他强调体式,强调辨体,认识到“以诗为文”和“以文为诗”的局限性和缺点,却不能认识到“以文为诗”的积极意义。“以文为诗”成为明代文体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
在体味论方面,胡胤嘉《诗艺存玄选序》进一步认为诗文之辨在于味的有尽、无尽的辨体思想。“余观仲鲁之名诗,而叹其深于诗也。夫诗异于文也,味之跃然于胸,歌之欲溢于口,而解之卒不易解,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严仪氏仿彿言之矣……诗之为道,所最忌者长言咏叹而意先尽也,故理穷于《易》,情穷于《诗》,法穷于《春秋》,非以能尽为穷,而正以其不必尽为穷……故余尝语朱原信曰:‘中晚之无诗,不以其靡,而以其尽也。’今以诗为文,且为今制艺之文,其能无尽乎。 ”(24)胡胤嘉:《诗艺存玄选序》,载余姚,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百八,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6册,第5652页。序文从探讨诗文区别开始,以为诗文之异在于味,味在于不尽,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诗的极致。当然,文章也是以韵味无穷为最上,以不尽之意为最上。其实,认为中晚唐的诗歌“尽”(即无言外之意)也是传统的看法。中晚唐诗歌何尝尽?不仅不尽,而且比盛唐别有味道。只是传统诗教以为时代衰则诗衰,甚至将时代衰归因于诗衰。
“以文为诗”也是明代杜诗学不能回避的命题。郑善夫更进一步从诗歌要隐秀含蓄的体性出发,批评“诗圣”杜甫的“以文为诗”。《唐音癸签》载:
郑善夫有批点杜诗,其指摘疵类,不遗余力,然实子美之知己,余子议论虽多,直观场之见耳。尝记其数则,一云诗之妙处,不必说到尽,不必写到真,而其欲说欲写者自宛然可想,虽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风人之义。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一云长篇沈着顿挫,指事陈情,有根节骨格,此杜老独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诗正不以此为贵,但可以为难而已。宋人学之往往以文为诗,雅道大坏,由杜老启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脱去唐人工丽之体,而独占高古,盖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随场作剧也。然诗终以兴致为宗,而气格反为病,善夫之诗本出子美,而其持论如此,正子瞻所谓知其所长而又知其敝者也。(25)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57页。
郑善夫主张诗必盛唐,认为诗之妙处不必说到尽,含蓄蕴藉才得风人之义,杜甫之诗往往似散文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批评宋人“以文为诗”的风气,追溯到杜甫。而杜甫含蓄有含蓄之妙,尽透有尽透之用,则是论者有所不知了。
另外一派是“挺杜派”。随着杜诗学的发达,明人将“以文为诗”与学杜结合,宋讷试图解释“以文为诗”是一种布置、结构、结撰,是文学技巧的提高。《纪行程诗序》载:“昔人论杜少陵以诗为文,韩昌黎以文为诗者,盖诗贵有布置也,有布置则有得其正造其妙矣,故学诗当学杜,则所学法度森严,规矩端正,得其师焉。永福张惟薫先生读书构文之暇,尤工于诗,故凡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与夫歌行之作,必以布置为体,而后炼其句也,又能以杜为师,故诗人与其得正造妙者多矣。”(26)宋讷:《纪行程诗序》,载《西隐集》卷六,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894页。宋讷的观点是诗歌要有文章的布置,杜甫“以诗为文”,法度森严,规矩端庄;不是“以诗写文”,而是将诗写得像文章,写得有文章的体式、体性、法度、格局、规矩;杜甫的“以诗为文”,实际上是“以文为诗”,是散文运动的产物。正与不正的关系是一个新的话题。宋讷以为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故有布置,“有布置则有得其正,造其妙矣,故学诗当学杜,则所学法度森严,规矩端正,得其师焉”。从文学史的实践来看,学习杜甫肯定是学诗正途,所以“以诗为文”肯定是正途,而不是一般批评家认为的变体。历史地看,从唐宋保守派的角度,杜甫、韩愈的“以文为诗”是变体;从元明清的诗歌史实践看,天下无人不学杜,变体逐渐成为正体,这就是正变的辩证法。边缘逐渐成为新主流,旧的主流逐渐被边缘化。
“以文为诗”不仅是明代文体学、杜诗学的命题,也是明代文学史家不可回避的命题。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价值在于变,在于创造了文学顺应时代的新传统。明人逐步认识到,变才是文学史发展的主旋律,才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明代林俊《严沧浪诗集序》云:“诗写物穷情,慨时而系事,寄旷达,托幽愤,三经三纬备矣,降而《离骚》一变也。而古诗、乐府,苏、李、张、郦,一变也,曹、刘、张、陆,又一变也。若宋若齐若梁,气格渐异,而尽变于神龙之近体。至开元、天宝而盛极矣,而又变于元和于开成。迨宋以文为诗,气格愈异,而唐响几绝。山谷词旨刻深,又一大变者也。”(27)林俊:《严沧浪诗集序》,载祝尚书主编《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2010,第2006页。林俊举诗歌史凡七变,而以变为常数,没有不变的道理。严羽标举盛唐,苏轼重提陶渊明,都是复古主义。古人已逝,不可再生,那只是个回不去的理想而已。任何人都不可能回到陶渊明,回到盛唐了。变永远是诗歌的正道,变体才是正体。正体只是个传说,即使在东周春秋的《诗经》时代也没有所谓的正体。
清代宋诗派居于主流地位。在清代批评家看来,时代变了,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复杂了,诗人们在创作上“以文为诗”,几乎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绿杨红杏轩诗集序》云:“文章古称韩柳,尚矣,若韩之于诗,硬句排奡,横骛别驱,以文为诗者也。今之言诗者,争趋之。”(28)姜宸英:《绿杨红杏轩诗集序》,载《湛园集》卷一,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第624页。虽然是无奈的语气,但也说明唐代之后,诗歌创作只能走“以文为诗”的宋诗道路了;比较简单纯粹的中古盛唐不可重复,回不去了,近代的诗人们别无选择。《义门读书记》卷五十二云:“《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以文为诗题,固当如是也。”(29)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87,第1079页。诗的题目像散文,叙述清楚,交代全面,这是时代内容急剧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以文为诗”的影响力拓展到了诗题。可见宋代之后,诗歌的发展不仅是“以文为诗”,而且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散文思维渗透到大部分文体的领域。“《李商隐诗集·镜楹》:陈无已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30)同上书卷五十八,第1260页。李商隐的诗有叙事的成分,有故事、人物、事件,也是“以文为诗”,这大概代表了中晚唐大部分诗人“以文为诗”的时代趋势。
清代文学史家充分认识到杜甫、韩愈之后开创诗歌新传统的创造性价值。《御选唐宋诗醇》云:“唐宋人以诗鸣者,指不胜屈,其卓然名家者犹不减数十人,兹独取六家者,谓惟此足称大家也。大家与名家犹大将与名将,其体段正自不同。李杜一时瑜亮,固千古希有,若唐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继苏者有黄,在当日亦几角立争雄,而百世论定,则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其视白苏较逊。退之虽以文为诗,要其志在直追李杜,实能拔奇于李杜之外。务观包含宏大,亦犹唐有乐天,然则骚坛之大将,旗鼓舍此何适矣。大家全力多于古诗见之,就近体而论,太白便不肯如子美之加意布置,昌黎奇杰之气,尤不耐束缚,东坡才博又似不免轻视。”(31)清乾隆十五年敕编《御选唐宋诗醇·凡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8册,第2页。有清一代,诗歌理论突破了诗必盛唐的藩篱;宋诗派力量强大,对诗人的创造性比较强调,杜甫、韩愈得到重视,元稹、白居易以叙事议论的讽喻诗出名,东坡议论杰出。选家对韩愈的看重是因为他从“以诗为诗”转型为“以文为诗”,拔奇于李白、杜甫之外,这是很有见识的。
相对而言,明代政治文化上回归汉唐,强调诗必盛唐,强调“以诗为诗”,维护古典诗歌抒情性的本色论。清代直趋近代,宋诗派占优,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的“以文为诗”得到推崇,学杜成为一时风尚。可见“以文为诗”不仅是技法问题,更是时代命题,是深厚的文化转型变革,是文学传统从抒情转型为叙事议论的大趋势问题。由此可见,“以文为诗”话题是古典诗学的重要话题,该讨论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演进的重要形式。
“以文为诗”的宋诗派对唐诗派的变革毕竟是在古典诗学内部进行的,真正具有革命性颠覆意义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诗——白话诗运动,他们“以文为诗”,或者说干脆是“以文为文”了。胡适说:“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32)胡适:《胡适文存(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5,第214页。他们抛弃了古典诗歌的根本形式(押韵、格律),代之以散文的散句单行,甚至不以书面语,而以口语体写诗。那么,他们的创作是不是诗?正如废名所言:“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33)废名:《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20页。“所谓散文的文字,便是说新诗里的句子,要是散文的句子。”(34)同上书,第29页。现代新诗的内容是诗的,形式则是散文的。它们是散文诗,追求的是散文美。
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康白情等人创作的是叙事和议论成分比较多的散文诗,引起了诗歌体性的混乱。创造社诗人认为情感和想象才是诗歌的本质,遂产生了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的充满情感和想象力的系列诗。湖畔诗派更大胆、真切、热烈地歌颂爱情,其自由诗强化了现代诗歌的爱情主题,让人感觉到现代诗歌自由书写现代人情感的抒情体性。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针对散文诗无韵的缺憾,开始大力提倡新格律诗。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诗的三美(即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戴望舒的朦胧诗强调诗歌的意象美、朦胧美,都是对古典诗歌“以诗为诗”的回归。努力是可贵的,探索是艰辛的。正如唐宋诗转型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痛苦砥砺才能凤凰涅槃一样,“以文为诗”、散文化的现代新诗,在“以诗为文”的历程中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