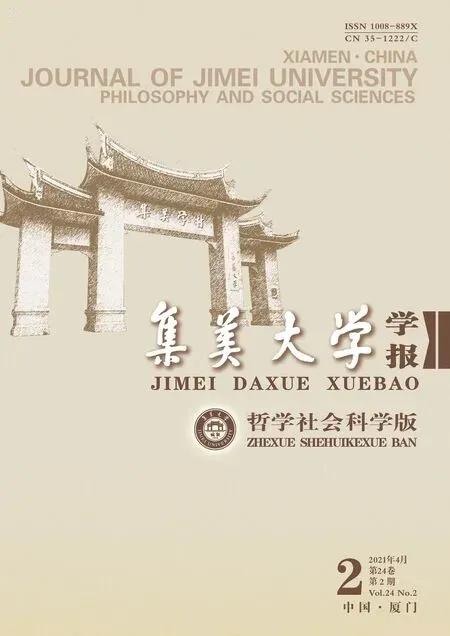博尔赫斯迷宫叙事与中国想象
曾丽华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阿根廷文学巨匠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是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其小说创作犹如文字迷宫的建造,充满瑰丽奇幻的虚构与想象,借助匪夷所思的幻想和梦境,思考宇宙间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时间与死亡等命题,带有极强的思辨精神。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颠覆了世界小说的传统,以超常的睿智通向了后现代写作,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
博尔赫斯是跨文化交流的一朵瑰丽之花。2018年11月28日,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文中习近平肯定了博尔赫斯作品中提及的庄周梦蝶、长城等中国元素,倡导中国与拉美国家应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1]。中国文化有着非凡的气度,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研究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的交流及相互影响,进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能够更好地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自信,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
一、迷宫叙事中的时空观念
博尔赫斯作品中“迷宫”一词出现频率极高,已经被文学界视为博尔赫斯的标志。古希腊神话中,忒修斯依靠阿里阿德涅彩线的帮助,杀死克里特岛上的牛头人身怪物并走出了迷宫。迷宫之类的建筑物结构复杂,曲折幽暗,有许多通道和无数尽头,让人迷惑惶恐。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迷宫象征着世界的变幻性、不可知性及其带来的疏离困惑。迷宫意象造就了博尔赫斯文学创作幻想腾空的翅膀。
博尔赫斯将世界看作一个谜,作家是“一个不断做梦的人”[2]357,文学作品就是对谜底的推测和假想。博尔赫斯常做关于迷宫和镜子的噩梦,迷宫叙事成为他虚构小说的理想方式。在他的笔下,有美妙的双梦记梦中梦,有通天的巴别塔图书馆,有无尽页码的沙之书,有曲径分叉的花园,有罗盘和铜镜子等。在一次访谈中,博尔赫斯说:“我把它们(迷宫曲径)看作是一些基本的符号、基本的象征。我总是感到迷惑,感到茫然,所以迷宫是正确的象征。它们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感受和生活的方式。”[3]51较典型的小说有《阿莱夫》《小径分岔的花园》《环形废墟》《通天塔图书馆》《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永生》《镜子与面具》《永恒的历史》《死亡与指南针》《秘密的奇迹》等,均显现着神秘、虚幻和镜像等扑朔迷离的迷宫情境。
《小径分岔的花园》把幻想因素编织在真实的文献资料《欧洲战争史》中,借助侦探小说形式来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事件,德国间谍余准杀害英国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以传递地名的军事情报。博尔赫斯虚构出艾伯特家一个亦真亦幻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以及云南总督彭归隐后建造的迷宫(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意在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迷宫,写小说和盖迷宫是一件事。小说展示了建造迷宫的方式为不断循环、无限增殖、穷尽未来。小径分岔的花园包容着时间的无限性、相对性和可超越性等诸多抽象艰深的哲学命题。“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4]78在作家看来,时间是无限的、相对的,但也是可以超越的。这种超越有两条基本的途径:(1)想象可以突破物理时间的束缚,使人隐藏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之中; (2)时间无垠,但是死亡却可以“冻结”它,彭、艾伯特、余准等人正是通过死亡游戏超越时间而达到永恒。
《通天塔图书馆》描述图书馆由许多六角形的回廊组成,数目无限,周而复始。书籍以无序重复排列后便成了有序的宇宙秩序。《环形废墟》借用庄周梦蝶的意象,构筑起一场永恒的轮回。小说中魔法师在火的帮助下,在梦境中创造了一个少年,他依照魔法师的心愿成长。在小说末尾,魔法师舍身奋力从火焰中挽救少年时,才恍然发觉自己也不过是另一个人梦中创造的幻影。现实与幻境交错轮回,时间沿着环形轨迹行走,宇宙间的循环虚无而荒谬。《皇宫的寓言》叙述艺术世界的梦幻魔力,中国皇宫安置了金属镜子和刺柏围篱,诗人的诗歌杰作仅一个字,却囊括从古至今一切瓷器、凡人、神和龙种的遭际,恼怒的皇帝认为诗人掳掠了他的皇宫,于是诗人被杀成为艺术的殉道者。迷宫般的小说正是作家对困扰人生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作家一反传统的小说叙事观,运用文本互涉、开放式结构、迷宫叙事等多种手法,模糊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幻想的界限[5]。
博尔赫斯关于时间的文章有《循环时间》《时间》《时间与邓恩》《对时间的新驳斥》《阿喀琉斯和乌龟永恒的赛跑》等篇。1978年6月,博尔赫斯在贝尔格拉诺大学讲课,选择了五个与时间有关的题目,其中《时间》是一篇最有代表性的精彩论述。开篇假设人只有一种感官——听觉,那么世界就成了音乐的同义词,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永远会拥有时间,因为时间是延续不断的。[6]博尔赫斯提到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说明河流与人都是变动不定的。紧接着回顾了柏拉图、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关于永恒以及圣保罗关于“我天天死亡”的说法,回顾了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芝诺悖论、柏格森和罗素等人的观点。博尔赫斯说,既然空间(芝诺悖论“飞矢不动”)的细分永无止境,那么时间亦当如此[7]。《对时间的新驳斥》否定了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引向这场驳斥的基础是两个论点: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和莱布尼茨关于无可辨认者的原理[8]。文章列举贝克莱、休谟、叔本华、庄周梦蝶、《印度哲学》及《弥兰陀王问经》等众多例证来否定连续,否定共时。
二、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
在博尔赫斯天马行空、幽玄绮丽的文学想象图景中,中国文化元素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博尔赫斯阅读过不同语种翻译的中国书籍,广博的知识视野使他运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化思想及中国文学写作模式,这种运用带有异国构想式的西方特色。他把幻想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神秘玄奥机智联结,建造出独具时空观念的文学迷宫世界。
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指出,“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9]。在博尔赫斯构建的迷宫故事里,他钟情于运用一些特定的文化象征物来想象中国,描述中国文化。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认知开始于童年阅读,中国文化中的神秘元素吸引着他。他对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01)深感兴趣,通过各种译本阅读了中国典籍《诗经》《红楼梦》《聊斋志异》《水浒传》,甚至熟悉《老子》《庄子》《易经》等,众多经典著作促使他对中国文学进行多面向的评述改写和巧妙利用。
(一)中国文学和哲学
博尔赫斯十分推崇中国经典,他在《文稿拾零》中有篇评论短文《曹雪芹<红楼梦>》,指出弗兰茨·库恩博士翻译成德文的《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小说,这是优于我们近三千年的文学中最有名的一部小说的第一个西方文学版本(其他都是缩写本)。”[10]375他介绍《红楼梦》的章节内容,并评论《红楼梦》复杂的人物关系具有迷宫的属性,特别指出第五、第六章的魔幻,赞叹“贾瑞误照风月镜”“该章绝不逊于埃德加·爱伦·坡或弗兰茨·卡夫卡”[10]376。因此,博尔赫斯在他极为重视的《幻想文学精选》中选编了两篇《红楼梦》的章节,命名为“宝玉的梦”和“风月宝鉴”,分别对应的是《红楼梦》的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和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博尔赫斯在中国文学中寻找幻想文学因素的意图十分明显[11]。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学中的奇幻世界十分痴迷,曾专门为《聊斋志异》写过一篇序,指出聊斋世界“是梦幻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梦魇的画廊和迷宫。”[12]92《小径分岔的花园》特意将迷宫般时间网的发明权交给一个中国人,意在告诉读者,小说中关于时间的观念是受东方文化思想的启迪,时间具有无限性,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与此相对照,小说中的人物都只不过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彭在明虚斋十三年苦心孤诣的“迷宫”小说正是以《红楼梦》为基石而创造出来,小说中的手抄本、《永乐大典》的佚卷是作为营造古典文化氛围的象征物而出现。
博尔赫斯迷恋神秘深邃的哲学思想,“我花了多年时光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我很感兴趣的道家学说,但是我也研究过佛学”[2]73。通晓东西方哲学的博尔赫斯多次在作品中提到《易经》,甚至以《易经》为题作诗,利用中国哲学典故佐证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文学思想。在《论古典》中,博尔赫斯沉醉于《易经》仅有六十四卦却包罗万象的魅力,那些六线形符号虽是有限但变幻莫测、环环相扣的属性,与作家崇尚的迷宫属性不谋而合。除此之外,博尔赫斯还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提到了《道德经》,在《扎伊尔》中引用《礼记》有关人类规范的记载,提到孔子的门徒做事正确无可挑剔。
博尔赫斯把庄子尊称为“幻想文学”的先祖,“‘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公元前200多年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13]192。他的作品中时常可以读到《庄子》和《道德经》的寓言,或引用或暗示,同时又将庄周梦蝶这一意象与自己的文本融会贯通,甚至在《对时间的新驳斥》中以大段篇幅分析了这个寓言。庄子“人生如梦”模糊了真实和虚幻的界限从而消解了时间的观点,与博尔赫斯的时间非连续性观念不谋而合,蕴含了现实与梦境、有限时间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多重关系。
(二)中国历史文化物象
博尔赫斯在文学创作中对中国文化元素加以巧妙利用。代表性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关涉众多历史文化物象:青岛、海丰、云南、天津、明朝第三位皇帝、中国音乐、纸糊的灯笼、天文学与占星术、书法、凉亭、道教、佛教、和尚、一座高高的中国漆的桌子。小说写到两个园林,余准生活过的广州海丰对称的花园和艾伯特博士家的花园。中国形象始终与花园、迷宫相连,奇妙瑰丽,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凉亭、中国音乐、灯笼、瓷器、东方书籍和蜿蜒小径构成的中国园林是现实的迷宫,令余准流连其中;余准的曾祖父彭花费十多年时间撰写的玄奥小说则是象征意义上的迷宫。艾伯特认为,彭 要揭示的谜底是“时间如迷宫”,人物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同时选择一切可能,从而创造了多种未来、多种时间,构建了一个复杂奇幻的叙事时空,而《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彭设想中建构的宇宙图景。
长城作为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象征物,在世界文学中有不凡的书写。卡夫卡从未到访过中国大地,写作的《中国长城建造时》将时空和人物抽象化,表现出怪诞、神秘的色彩。长城为何而建?如何修建?最初命令从何而来?卡夫卡由文本中的长城,引申出康德关于人类不能领悟“整体”之意义的思考。博尔赫斯则景仰神圣的万里长城,“做梦都想去中国”,生前夙愿是“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13]190。他的《长城和书》对秦始皇规模庞大的建设与破坏之间的矛盾表示折服和不安,修建长城是对空间的抗拒,焚书坑儒是对时间的抗拒,二者是旨在阻挡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14]。焚书和筑城徒留形式,抽象成为作家对克罗齐、佩特观点进行哲学思考的物象。
(三)对中国人形象的描述
博尔赫斯小说中明确描述中国人形象的作品,主要是《女海盗金寡妇》和《小径分岔的花园》。《女海盗金寡妇》收录在1935年出版的《恶棍列传》中,这是博尔赫斯早期的小说创作,大都是模仿或直接根据前人作品进行改编的故事。小说描写金寡妇的英勇善战并得到善终的结局,体现出作家对人物形象的赏识。金寡妇的形象极为生动具体,她“身材瘦削,轮廓分明,老是眯缝着眼睛,笑时露出蛀牙”[4]18,这种描写显然与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不相符合,反而更贴近西方设定的男性海盗形象。指挥有方的金寡妇率领着海盗们辉煌扬威十三年,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朝廷的招安,“狐狸寻求龙的庇护”[4]21。“龙”是至尊皇权的象征,即使是再狡猾的“狐狸”也难以逃脱臣服的命运,反映出博尔赫斯对封建中央集权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水浒传》故事对他的影响。
《小径分岔的花园》发表于1941年,经过时间的积淀和幻想文学思想的形成,博尔赫斯对中国人形象的塑造更为饱满。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一生漂泊,一战期间沦为德国间谍,遭受英军特工马登上尉的追杀。为了把英军炮兵阵地的名字告知德军,他通过电话簿选择了艾伯特教授进行杀害,他完成此任务的原因是为了证明黄种人并非无能之辈。余准的行动是一种可悲的被迫寻求认可的努力,为混乱时局下的荒诞生存而抗争,最终却得不到认同,只剩下无限悔恨和厌倦。小说描述“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青铜凤凰”“红瓷花瓶”“蓝瓷”等中国元素,它们与余准一样远离故乡,为西方人所有,甚至彭的手稿和亲笔信都落入了外国汉学家手中。艾伯特教授甚至解读出曾祖苦心孤诣创作的迷宫式宏伟小说及其时间主题。彭、艾伯特可以视为作家自己在梦蝶幻境中的理想化身,热爱中国文化并奉献终生。
三、幻想文学思想的融通
异国形象作为作家和社会文化对“他者”的集体想象物,在塑造过程中一般表现为两种倾向:仇视或亲善。处于20世纪的博尔赫斯对中国的理解是“亲善”的态度,与同时代的社会集体想象略有不同。博尔赫斯精通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西方语言,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型作家。他通过迷宫叙事对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等哲学命题进行思考,开拓幻想小说创作的新格局,倡导现实与虚构交错的幻想美学思想。对博尔赫斯而言,中国是一个神秘遥远的存在,是通过文字构筑出来的迷宫,令人流连忘返。在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是站在内在化西方视点的立场上来审视、反思西方文化,发现世界文化的共通点,从中国形象中寻求文学思想的共鸣与融通。
(一)西方文化的反思
自《马可·波罗游记》开始,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不断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15]。被博尔赫斯称为“先驱者”的卡夫卡、庞德等人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迷茫时期,在精神的迷雾中将思索的目光投向东方,于道家玄学及佛教思想中寻得慰藉。作为他们忠实的读者,博尔赫斯自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书籍钟情于神秘东方从而构建绮丽的中国形象。
以博尔赫斯等作家为代表的拉美先锋派文学,着重于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博尔赫斯的创作通过迷宫叙事阐述自己独特的时空观念,以此表达对动荡社会的不满和疏离。博尔赫斯接受英式教育,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哲学等多方面著作,接受西方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我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我对世界始终感到诧异”[3]48。在阿根廷动荡的社会局势下,博尔赫斯对庇隆政府持抗拒态度,最终疏离政治及所嫌恶的一切,栽进文字的迷宫中以求寄寓,具有哲学意蕴的东方文化成为他艺术梦境中的主要意象。他收藏有伯顿和安托万·加朗不同版本的《一千零一夜》,并为加朗版的《一千零一夜》作序,赞叹“此书由一连串精心幻想出的梦所组成”[16]。庄周梦蝶的故事被反复运用演绎,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形象在作家笔下愈加奇幻瑰丽。
美国学者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指出,“西方人探讨并创造性地阐释他们半知半不知的中国社会及其价值。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 出现的”[17]。对于博尔赫斯而言,中国是一个符码化的信息,成为象征和文化形象的集合体。博尔赫斯阅读与中国相关的书籍,都是源于翻译或第三国家学者的介绍。他敬佩柯勒律治由梦中启示而写就的神奇诗篇《忽必烈汗》。博尔赫斯读过威廉·菲尔希纳编译的德文版《中国民间故事》,也读过沃尔弗拉姆·埃伯哈特的英语译本《中国神话故事与民间故事》,特别喜欢《西王母》《龟仙的儿子》《魔箱》《铜币》《神画》和《演员和魔鬼》等故事[10]395。作品的翻译介绍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还会受到国别文化、时代环境、译者情感等多方面的影响。西方语言翻译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形象成为遥远神秘的想象物,是西方文化自我反思与自我书写的一种投射。
(二)文学思想的融通
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他的创作基本上都来自于书籍,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和认知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拉美文化的魔幻与东方文化的神秘相互呼应,促进作家营造迷宫式氛围,达到时空移置变形的玄幻效果。他通过想象性创作去描述中国文化,更大意义上是寻求中西幻想文学思想的融通。
长期的图书馆环境使博尔赫斯与那些圆形回廊中密集而无限的书籍结下不解之缘。他大量阅读哲学、神话、历史等多学科的书籍,汇合成为写作的无尽灵感,在《关于天赐的诗》中喟叹:“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昏昏然缓缓将空幽勘察,凭借着那迟疑无定的手杖。”[18]博尔赫斯在56岁左右近乎失明,此后他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更多依赖母亲及朋友的描述,博闻强记的作家也是依赖于口述来进行创作,坚忍不拔地书写着虚无与永恒交错的迷宫世界。
在《聊斋志异选》的西班牙语选本序言中,博尔赫斯对《聊斋志异》的虚实奇幻世界进行高度评价,“使人依稀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同时也看到一种与荒诞的虚构的异乎寻常的接近”[12]92。博尔赫斯的小说具有幻想性,往往借助匪夷所思的惊险飞跃,反复探究有形无形、有限无限、瞬间永恒等哲学命题,差不多每一篇都是在描绘一个眩惑的微型宇宙。在《阿莱夫》中,世界微缩为一个闪烁的小圆球“阿莱夫”,但其中的万物景象并没有按比例缩小。正如“道生一,一生万物”,它体现着“一”与多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作家哲学理念的象征。《沙之书》同样展示了由真实堆积起来的虚幻,无穷尽的书页是玄幻思想的载体。
博尔赫斯改写中国君王权杖的传说,权杖传给新君时会缩短一半,再传又减一半,引发出无限分割但永不消失的哲思。他后来在纽约唐人街买了一根黑漆手杖,形影不离。晚年创作著名诗篇《漆手杖》,“我看着那根手杖,觉得它是那个筑起了长城、开创了一片神奇天地的无限古老的帝国的一部分。”[19]296接着提到梦蝶的庄周,想起工匠“信奉道家还是佛教,是否翻查六十四式的卦书?”[19]296由此感叹世界无不存在着神秘联系,表现作家对丰富悠久的中国文化的痴迷与神往。
博尔赫斯在《幻想文学精选》中选编了《红楼梦》的两个章节,小说所巧妙运用的梦境和镜子意象特别符合博尔赫斯的偏好。《环形废墟》的梦中造梦打破了虚实界限,《创造者·被蒙的镜子》突显对镜子的恐惧,二者都与《红楼梦》中的意象运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博尔赫斯评价《红楼梦》是“循环往复、生生不已、幻为无限”的迷宫,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的赞赏。博尔赫斯乐于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真实与幻想交织之间,他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创造出了《小径分岔的花园》《皇宫的寓言》那类亦真亦幻的迷宫世界。《阿威罗伊的探索》中的阿威罗伊是12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居然可以和大清帝国的旅行者阿布卡西姆畅谈中国戏曲表演,谈论新卡兰(广州)和长城。博尔赫斯通过打破时空维度的界限,构建了全新的小说叙述体系,中国想象成为作家幻想文学思想的完美诠释。
四、结 语
受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影响,博尔赫斯将宇宙世界看成一个谜,他善于通过迷宫、梦境、镜子的意象来思考永恒、无限、死亡等哲学问题,形成现实与虚构交织的幻想文学思想。博尔赫斯向往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借鉴与描述就是哲理化的文学接受与重写过程,对中国的想象塑造与迷宫叙事巧妙融合,建构出博尔赫斯式神秘奇幻的中国形象,达到了中西幻想文学思想的融通。分析博尔赫斯迷宫叙事中的时空观念,探究作家对中国正面形象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揭示出多元文化融汇下博尔赫斯文学的叙事革新与美学价值。文化交融能冲破文明隔阂,文化和谐共生能冲淡文明固化,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文化共存的非凡意义。
——读《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