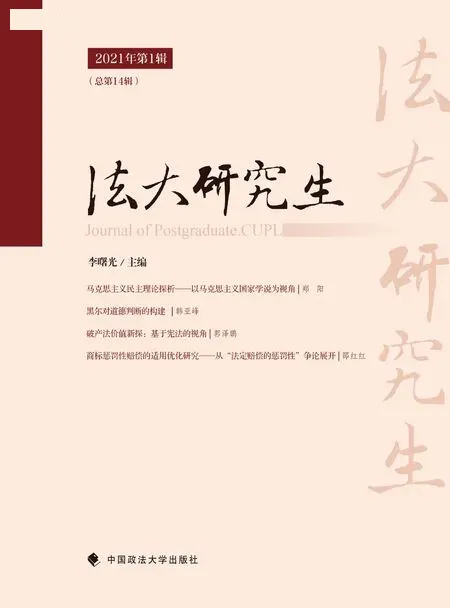黑尔对道德判断的构建
韩亚峰
一个规范在何时可以被称为是公正的呢?逻辑规则是否最终能够在公正与不公正的规范之间作出区分?本文无意于也不可能对这一宏大问题作出探究,而是试图从其中的“逻辑—分析性进路”〔1〕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可以将法律论证理论划分为逻辑—分析性进路、论题—修辞进路和商谈理论发展而来的模式等。对此可参见[德] 乌尔弗里希·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入手,关注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语言能为法律论证贡献什么?但这仍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问题:语句作为语言的构成,几乎所有的理论分析都与之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更是体现在静态的规则建构到动态的解释和推理等过程之中。法律论证以符合逻辑规则的程序为主,逻辑涉及的概念与命题都必须由语言来表达,语言的清晰尤为基础和重要,而作为一种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性语言,清晰和明确又是困难的。本文的研究角度就集中于对语言逻辑的清晰化探讨。这一基础性的问题必然要回溯到元伦理学上对语言的研究。传统的道德推理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直到18 世纪,休谟开始质疑传统的形而上学,包含以严密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事实的可能性。元伦理学(meta-ethics)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产生。不同于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其不关心“一个人应当怎么做”(Should I …?)的问题,而是关注 “应当究竟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the “should”mean?)〔2〕See,Michael Smith,The Moral Problem,Blackwell Publishing,1994,pp.2-3.基于此,元伦理学试图揭示语言本身的规范性,而不去提倡某一个具体的原则进而以鼓励人们追求某种善。
在这个名称下,早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形而上学伦理学和伦理自然主义,或主张以上帝存在来定义伦理术语,或主张伦理术语表达的是某些经验或者自然的性质。而真正从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对元伦理学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则属摩尔(G.E.Moore),他将伦理学从研究行为善恶价值的规范系统延伸到道德语言的分析,从而推动道德论证走向逻辑化的方向。此后,以史蒂文森等人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主张道德的论证不是逻辑关系,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关系,认为道德陈述的情感意义在于有能力从因果关系上对情感态度的变化产生影响——此时的逻辑方法虽然没有像传统伦理学那样被忽视,但已然退居次要。〔3〕更多关于摩尔的直觉主义伦理学可参见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5 章至第8 章。
面对伦理学可能会陷入非理性认识境地的危险,黑尔(R.M.Hare) 等人开始着手建立新的语言分析理论,加强对道德语言(the language of moral) 本身的逻辑研究。“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prescriptive language)”〔1〕[英] 理查德·麦尔文·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5 页。另:以下正文中的引用部分,如无特别说明,均源自本书。——虽然更早时期的摩尔就已经开始倡导对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但真正将其明确为规定语言并加以逻辑化的则集中于黑尔的理论中。黑尔在诸多涉及规范性的关键问题上保持相对严格的逻辑立场,比如面对休谟法则(Hume's Doctrine) 时,黑尔坚持“是”与“应当”在逻辑上的不可混淆,并主张以清晰的逻辑去解决道德争论。这一努力成功与否暂且不论,但其对道德语言较为彻底的分析和论证值得去关注。〔2〕尽管休谟难题(事实是否能够推导出规范) 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甚至在一些情形中成为判断道德观点和方法立场的有力标准,但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一宏大问题进行扩展。黑尔本人所持的严格二分法在下文的论述中会渐进展开,体现在其道德语言理论中。经后文分析后可以看到,黑尔之所以从祈使句的逻辑规则追溯到这一问题,是为了强调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
本文将首先阐明黑尔所采用的主要论证方法及背景,文章主体部分以此为工具对道德语言理论进行分析。分析将以“规定语句—推论规则—价值词”的递进方式进行,意在展现道德判断的规定性及其是如何作出的。应当说明的是,相较于黑尔的观点本身,其在批驳传统伦理学观点中所持有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实践进路反而是更为重要的,这也正是本文欲借此探究其分析力度与不足的初衷。
一、道德判断的性质
元伦理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解决道德分歧的方法,而思考的道德问题本身与传统伦理学并无不同,概括来说都是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一坚实的基础,明确的道德判断才有可能。黑尔首先将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区分,明确这一区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要集中解决的问题在何处。
(一) 从道德问题到狭义伦理学
在黑尔看来,伦理学的问题有三〔3〕See,R.M.Hare,Essays on the Moral Concep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p.39-40.黑尔在后期总结性的Sorting out Ethics 中总结性地将伦理学理论区分为描述主义和非描述主义,此为在整体上对各伦理学研究的划分,与此处所论及的具体研究对象关系相对间接,故不涉及。:①道德问题(moral questions)。我应该做什么?这类问题研究什么应该做,如何确定善恶标准,因为当一个人说他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表示接受了一定的道德观点并在此指导下作出道德判断,以指导其行为。②关于人们道德意见的事实问题(questions of fact about people's moral opinions)。人们对堕胎的意见是什么?这属于陈述关于道德的事实情况。③关于道德词的意义问题(questions about the meanings of moral words)。“善”“正当”等道德词语的意义。
与此三者对应,广义的伦理学科就有了道德、描述伦理学和狭义伦理学。前两类是实质问题,第三类是形式问题。故狭义的伦理学和道德的关系,犹如科学哲学之于科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science),是关于道德语言、语词意义及其所指称的对象本性等问题的逻辑研究。它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搞清楚道德问题的意义是什么;欲清晰道德问题的意义,就要懂得诸如“我应该”之类的道德语言是什么意思;欲懂其意,就是要明确相关道德语言的逻辑性质——只有对表达问题的语言意义和逻辑性质有了共同的理解,人们才可能对之发表意见,进行讨论,这是黑尔“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
(二) 方法:语言分析
道德原则的作用在于指导我们的行为,这种作用是通过道德语言来进行的。要理解道德原则就要理解道德语言,黑尔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道德理论研究的方法,即语义分析方法。此处首先需要理清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 和语义分析(semantic analysis)。〔1〕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有两种:概念分析与语言分析,概念分析是指对语言所表达的概念与命题的内容的分析;语言分析是对语言意义的分析,这两种分析的对象不同。而逻辑分析与语义分析则是两种分析方法,其中逻辑分析既可以针对概念分析也可以用于语言分析,即利用逻辑规则对概念内容与语言意义进行分析。语义分析则主要是指用语言学中的一些语义规则对语言意义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即主要针对语言分析,类似于法律解释中的语义解释。参见江怡:《语言分析与概念分析》,载《外国语文》2011 年第1 期。“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关于我们这些认识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对语言的讨论,对于我们所表达的认识的理解可以归为对我们所说的句子的意义的理解。这样,就从关于世界的探讨转为对语言的探讨。”〔2〕王路:《走进分析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106 页。与之相关的“语言分析”概念是一个上位概念,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 和概念分析。作为本文论证起点的语义分析方法则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进行逻辑分析的内容之一。〔3〕金炳华等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855 页。
欲明了何为语义分析,首先需要明确此处的逻辑分析所指为何。考虑到本文关注的大背景是法律论证的问题,故“逻辑方法所期待的是只要有人主张或意图进行正确的论证,他所实际运用的表达就应当具备可被转译为逻辑形式的意义,并可对其逻辑上的可靠性进行检测”。〔1〕[德] 乌尔里希·克卢格:《法律逻辑》,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译者序。因而本文所涉及的逻辑分析主要是从形式和结构方面分析人工语言和日常语言中的词语、句子及命题的逻辑结构,而较少从逻辑上进行阐明以获得哲学理解。以此为基础,本文所谓的语义分析主要是对语词和句子的所指与意义进行的分析。〔2〕关于概念分析,比克斯在《法律理论词典》一书中指出:“概念分析通过区分观念和范畴的逻辑结构或必然的 (necessary)、本质的 (essential) 属性来探求我们的世界的某些方面的真(truth)。”由此界定可以看出,概念分析的对象是观念和范畴。这说明概念分析是语言层面上的探讨。对概念进行分析仅仅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在于:一是“区分观念和范畴的逻辑结构或必然的、本质的属性”,二是“探求我们的世界的某些方面的真”,而这一目的构成了其与逻辑语义分析的区别。详细可参见[美] 布赖恩·比克斯:《牛津法律理论词典》,邱昭继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
(三) 立场:反对还原论
把规定语言与其他语言进行对照,是理解道德语言性质的切入点。最简单的规定语言的形式即祈使句,那么与之对应的其他语句有什么?在此,黑尔借鉴了语法学者的分类:陈述句、命令句和疑问句。尽管这一区分是不够透彻和严格的,如在祈使句中就有表达请求和说明使用指南的不同类型,但是在宽泛意义上的理解已经足够。〔3〕此处,黑尔用“命令”来概括以祈使语气所表达的所有祈使语句类型,从而试图说明陈述和命令这两种语气的区别和共同特点。
如何在这种比较中理解祈使句(imperative sentences)?黑尔首先清理了前人对此的理解,排除掉不可靠甚至错误的进路。概括而言,以往对祈使句的分析有两种理论形式,黑尔称之为“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在本文看来,这种还原分别为内部还原(心理事实) 和外部还原(物理事实)。内部还原是将祈使句描述为“表达者心灵的陈述”,该理论主张:正如“A 是正当的”意味着“我赞同A”一样,“关上门”同样意味着“我要你去关上门”。但是这里的困难之处在于,“关上门”这一命令似乎是针对关门的事,而不是说话者的心灵状态,正如教室投影仪的使用指南是关于投影仪所需要的步骤而不是上课老师的心灵分析。外部还原则是通过添加假设性后果来实现的,即“如果……那么……”。在这一理论下,“关上门”就意味着“如果你不关上门,那么X 就有可能发生”——此处的X 是一种后果,这也正是此主张者所认为的祈使句的指向:要么实现某种目的,要么防止某种趋于发生的结果。这种还原似乎给予了祈使句以描述性的力量,但是终结句子分析是添加的目的,这种目的通常是一种坏的结果——显然,当对“坏的”进行追问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评价。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还原论的共性在于将规范(祈使句) 还原为事实。这正是摩尔所讲的“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1〕关于摩尔对此的阐述,可参见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5 章至第8 章。,也是黑尔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前必须要排除掉的进路。进一步思考会发现,将祈使句还原为陈述句的努力完全可以理解,其吸引力在于诸多方面,比如陈述句严格的表达,以及证实主义的流行等。但是基于本文的关注立场,这里欲对其所谓的“逻辑优先性”进行探讨。长期以来,人们似乎认为祈使句在逻辑上低于陈述句的地位,进而,如果我们只是把陈述句视为是不可怀疑的,那么自然地就会认为:祈使句并不像陈述句一样陈述事实,而是只表达愿望。这种优先性的主张是否经得起探究呢?下文将从陈述句和祈使句的逻辑结构上予以探究,而这必须要借助黑尔对语句的逻辑分析工具。
(四) 道德判断的逻辑构成及其规定性(prescription)
虽然对两种还原理论进行了批驳,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其主张:其中,祈使句中的陈述(indicative) 部分确实是存在的,分歧只在于这种陈述是否能在某一个标准确定的意义上进行表达;如果能,那么这种标准是否是唯一确定的。黑尔在此对陈述句和祈使句的不同部分进行了技术性的处理:
我将造一些全新的词。我将把两种语气共同的部分叫作指陈(phrastic); 把命令和陈述之不同的部分称之为首肯(neustic)。〔2〕这两个术语源于拉丁语,黑尔借用了这一表达,但并没有给其以明确的定义,这也是反对者对其的一个批评,但本文认为这两个术语的引入是为了揭示出陈述句与命令句的区别,而不试图给以精确的概念界定,后文将会揭示出这一区分功能是可以实现的。
结合陈述句和命令句的实例,“指陈”指的是说话者指出或者指示出他准备去陈述的事实,或者命令的将要成为事实;“首肯”则是表达“这是事实”或者“做吧”的方式。可见,陈述句与祈使句的区别集中在首肯部分:陈述句借助于首肯想表达某事处于何种状态,而祈使句则试图告诉某人去做某事。
陈述句与命令句的这一逻辑结构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这至少能够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就是上面所提及的,即陈述句是否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从指陈上看二者具有一致性,故如果有所谓的优先性,那么也许会表现在首肯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确实能以陈述语气来代替命令语气——但不是所有,这也不能证明前者具有逻辑优先性。原因之一是在有些情况下,命令句同样可以代替陈述句的表述(比如“晓明下午来了办公室”这一陈述语句可以被“ ‘让晓明下午来办公室’这一命令已经被晓明执行”这一语句所代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事实上陈述句能实现更多的代替呢?这要从祈使句本身来考虑:如我们所知,除了极少数祈使句,祈使句多数都是限于将来时,而且多为第二人称,而陈述句则几乎能够涵盖所有时态和人称。其二,祈使句的指陈有其内在功能,比如“赞许”,这在后文会加以细述,其作为价值词“善”的首要功能,其目的是引导行为人的各种选择,因而其具有无法被取代的功能,逻辑上的优先性自然也是无从谈起。
明确祈使句具有指陈和首肯两个部分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澄清人们在批评中可能会犯的“打击错误”〔1〕通过对道德词和道德语句的逻辑分析来澄清争议问题本身是道德语言理论的独特之一,本文将类似于这里的澄清称作“打击错误”。这在后文还有两处体现:①说明规定语句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诉诸心灵驱使,从而澄清其所遭受的不必要非议;②在分析“善”这一价值词时,黑尔主张尽管道德领域的善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更多是基于人之为人的基本情感,并不意味着道德善需要更为特殊的逻辑。。比如,“应该在3 个小时之内跑完马拉松”这一命令对于一个从不跑步的人而言是无意义的,因为其无法理解3 个小时如何完成42 公里的距离,进而他可能会迁怒于命令做出者本人;但对于一个长期坚持长跑训练的人而言,这是可以实现的,并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此时两种理解的不同虽然是针对命令句本身,但根本上是针对其中的陈述部分。
上述内容是针对祈使句逻辑结构的分析,通过将其与陈述语句进行对比,揭示出指陈和首肯两个逻辑构成。作为最简单的规定语句,祈使句仅是研究规定语句的起点。同样作为规定语句的道德语句也是要告诉某人去做某事,问题是,道德语句的这一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对此,情感主义者是这样主张的:“伦理学语词不仅仅是用来表达感情,它们还适用于引发感情,因而也适合于刺激行动。”〔2〕转引自[英] 理查德·麦尔文·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即道德判断语言中的功能是在因果意义上影响听者行为或者情绪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在逻辑上尚需区分这样两种行为:吩咐(telling to) 某人去做某事与促使(getting to) 他去做某事。这两种行为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如同在陈述句中,告诉某人某事是事实不同于令其相信它,命令也不是使某人去做或者说服某人去做,而是先吩咐;若不得,则以别的方式刺激之。
这组区分是有重要意义的。吩咐有告知之意,本身并不存在说服的企图,后者更倾向于是一种引诱、促使或者影响。如果直接以“影响”来发挥道德判断的功能,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试想当某一个人意识到别人正在试图说服自己时,他对这一意识的自然反应便是警惕和保持自由主体性,显然这种对道德判断的反应是不应该鼓励的;反之,若仅仅是告诉或者吩咐,听者则不会有上述反应。我们所支持的做法是让听者知道去做什么或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并且本人不必然因此受到影响,而是自己能够决定是否服从。
不直接将道德判断功能的发挥诉诸“影响力”,一方面能够澄清道德判断的功能不是浮于表面的宣传,也并非直入人心的驱使,而是要告诉某人去做某事——从而能够澄清道德判断的祈使理论所遭受到的不必要的争议,其多是源于对道德判断和命令的误解。更为重要的是,道德判断和命令尽管会有不同,〔1〕二者的不同最大表现在道德判断需要诉诸理由,否则不可能实现普遍化,而祈使句则只需要诉诸命令即可。如果片面强调形式,就容易将二者混淆,此处关注的是二者的相同。但同样作为是对理性主体所为为何的告知,二者都要受到逻辑规则的支配。
二、道德判断的推论规则
(一) 推论规则
概而言之,黑尔把道德判断的推导过程在逻辑上看作是一个建立在全称判断(大前提) 和特殊事实判断(小前提) 基础上的实践三段论(practical syllogism) 的过程。〔2〕关于为何以全称祈使句做大前提的问题,涉及与“全部”有关的“蕴涵”这个强语气词的意义。但是要充分讨论这个词需要大量篇幅,而本文关注的是道德判断中的语气这一难题,复杂的蕴涵关系并不影响这一点。在前文论及祈使句的逻辑结构中可以看到,指陈和首肯这两部分使得祈使句具有“吩咐”行为者去做某事的结论。同样作为规定语言的道德判断,其语气也是诸如“去做”之类的命令语气,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是”与“否”的结论,也就是说,其结论是祈使语气的。对此,黑尔提出关于支配这一推论形式的规则:
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使句,则我们就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地引出任何祈使式结论。〔1〕[英] 理查德·麦尔文·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30 页。
如果回顾伦理学上一些重要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这一规则早已隐约闪现其中。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构建了一个以善(good) 为所有事物欲求的目的论的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不同的等级,在其中,有些是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另一些其自身便是善的,即目的。显然在这个等级中存在着最高等级的善,它能够作为最权威的科学和最大的技艺对象。但是,“最高善显然是某种完善的东西”〔2〕[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18 页。,是自足的。因而要揭示最高善就要弄清楚人的活动,人的善体现在其活动的完善。〔3〕此处的活动专指人的特殊活动,而生命活动等为人和动植物所共有,并不在讨论之列。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是“有逻各斯部分的实践的生命,即实现活动意义的生命”。参见[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19~20 页。从善本身来说,这也就意味着,说某物是善的首先是要引导行为,那么就不可能只是去陈述一种关于世界的事实。与之联系更为密切的另一种伦理学观点当属休谟法则:任何道德判断都不可能是纯粹事实陈述正是休谟法则的基础,即从一系列关于“是”的命题中不可能推出“应当”。〔4〕其他与之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伦理观点,如康德对道德原则之“意志他律”的反对,以及摩尔在提出“自然主义谬误”时的背后理论基础。但是以上这些均未清晰地予以其阐明,其要么作为论点的潜在基础,要么并未在逻辑语言结构上进行细致分析。尽管如此,但它们在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即主张道德判断不可能是纯粹的事实陈述,而应当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这一主张在道德语言进路中意味着什么呢?
(二) 笛卡尔式推论为什么是错的?
同前文的论证方式一样,此处依然是先对不同观点进行厘清。与之前的不同在于,这里的反对意见不独是针对道德情感主义,而是包括其在内的诸多“粗陋的道德体系”,黑尔将其统称为“笛卡尔式的”。笛卡尔式的道德推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从自明的第一原理之演绎推理,达到关于经验事实问题的科学结论,就像对血液循环的推演一般。〔5〕转引自[英] 理查德·麦尔文·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33 页。在进入黑尔的反驳之前,这里首先明确对于笛卡尔式推论的反驳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甚至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坚持从自明的前提中推出不为其所包含的结论。但是细致地分析后会发现,这些反对和黑尔所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通常我们是从演绎推理本身入手,论证其具有分析的性质,演绎推理的功能是将隐含在前提中的东西明确化,故我们在谈论事物时都必须要遵守某些逻辑规则。
与此不同,基于道德语言的反驳着力点不在于演绎推论本身,而在于前提中的初始原则,主张隐含在大前提中的初始原则实际上并非不证自明的。〔1〕伦理学家对实践三段论的普遍认同可以结合法律论证理论来理解:在法律论证的“逻辑—分析”进路中,尽管在诸多方面存在争议,但其至少在核心范围内显示为三段论的结构(对此可参见[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年版,第273~284 页),而处于讨论中心的问题多是围绕三段论在论证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否要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演算得以重构等。具体而言,这一反驳是从几个不同的进路并行推进的:①假设结论必然蕴涵于前提之中,那么要充分了解前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而不需要借助于演绎推理;②前提和结论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既如此,对结论的推理就表示对结论的质疑,那么一般性的前提何以不证自明;③循环推理……在本文看来,以上虽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笛卡尔式推论进行质疑,但最能体现道德语言理论的进路是关于“不证自明”的追问:称某一个命题是自明的,此为何意?
对此,可能存在几种可能性:①从逻辑上看,否认前提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若如此,这一推论就必然是分析性的,也就无法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内容。②从心理上看,否认这种行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何为心理上的不可能,以及这种感觉不可能是一种事实,而且是偶然性的事实,其不足以作为普遍道德原则的坚实基础。③从理性上看,否认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表现。问题在于,何为理性之人?对其的说明恐怕又要回到循环式的证明之中。理性与否的评价是蕴涵着价值判断的,而这些价值词又本是应当在道德判断过程中进行的。
在对以上三种可能性进行的道德质疑中,基于对“理性”的追问而可能陷入的循环推理是最能体现道德语言理论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黑尔在此主张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蕴涵关系(entailment),即纯粹的事实不可能推出道德判断。对此的理解要从道德判断的功能上去着手,即道德判断的主要功能即是调节行为,故唯有命令语句才能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描述不可能是规定的理由。
(三) 新的推论规则
如此严格地坚持事实性前提和道德判断结论的不可推出,客观事实就无法作为大前提,是否意味着任何道德体系都不能再履行其调节我们行为的功能?随之而来的滑坡效应可能会让人质疑道德本身是否还是一项理性活动。此时,许多人要么主张复兴自然法理论,要么主张某种目的论的伦理学,或者同样在语言逻辑框架中主张一种较为松散的(looseness) 蕴涵关系,建构评价性的道德推论。〔1〕从逻辑形式的角度看,以前两种解决方案为代表的进路似乎是把规范性命题是否有真假性的问题与验证描述性命题(或者事实命题) 的真假问题等而论之,以至于其基于自己的前提走向了道德怀疑主义,进而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挑战;第三种解决方案,即图尔敏坚持一种广义逻辑的立场,建构一种评价性推论,给予从事实性陈述到应然性陈述这一步骤的正当性证成,力图维护事实作为价值判断的理由。关于图尔敏与黑尔主张的分歧可参见宋旭光:《道德论证的方法论问题——图尔敏与黑尔之争》,载《法学方法论论丛》(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年版。相较于对上述诸主张的梳理,明确黑尔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是更为必要的:拒绝了粗陋的“不证自明”,大前提就只剩下了价值词,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词能够担此重任?此时的道德判断又是如何推出的?
第二个问题本身不难理解。在有效的实践三段论推理之中,结论中包含祈使命令,当且仅当该命令隐含在所有的前提中,每一个道德推理才是一个前后连贯的逻辑过程。〔2〕对于如何作出一个道德判断的问题,黑尔依然遵从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模式,将行为原则和事实陈述与大小前提相对应。这样决定我们作出判断的要素就在于对所要发生事情的结果的考虑。此处的“结果”并不是庸俗的结果主义,不是与“义务”相对应的,而是表示一种境况的变化。因而,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什么样的前提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变化的相关性大从而影响结果,即集中关注大前提。而在每一个道德推理之初,即大前提的部分,必然是包含祈使命令或者同属于规范语言的价值判断。同传统的伦理学理论一样,这一推理过程面临的难题同样是:作为大前提的规范语句,其内容上的道德原则如何论证。与以往伦理学理论的不同在于,对这些道德原则的把握一是依靠对价值词的全新理解,二要依靠方法上的实践——前者涉及黑尔对价值词的解读,后者则需要探究其所使用的方法论。
三、价值语词(value-words)〔3〕文中反复出现“价值词”与“道德词”,这与黑尔一贯的论证方式有关:无论是对规定语句还是价值词的分析,黑尔都使用一种从非道德语境到道德语境的进路,故会有这样对应性的概念出现,另有“祈使句—价值判断—道德判断”。
按照一般论证思路,接下来应该首先关注价值词的逻辑结构,然后探究方法论的问题——但在道德语言的理论中,价值词的作用不止于此:价值词并非如传统伦理学所理解的那样,以道德概念的意义,作为一个对象存在,而是有其实践面向的。这一独特性在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s) 的建立上得以显示,故有必要先揭示出其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为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价值词的独特性;同时,道德原则的建立问题是道德推理的关键性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探究黑尔所持的方法论立场。
(一) 实践中的道德原则
正如前一部分所指出的,尽管道德语言理论摒弃了纯粹的事实陈述作为大前提,但并未放弃对一个稳固前提的追求。对这一前提的分析起点始于生活中的行为实践,这里以驾驶为例,讨论什么样的司机是好司机?一方面,好司机能够以已经成为其习惯的那些原则非常准确地支配其行动,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不需要去想怎么做的问题;另一方面,当面对千变万化的马路情况时,一个好的司机还要时刻留意其开车习惯是否需要加以改进,不停学习。这样一个好司机的形象是为我们所倡导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形象,而这种形象却不太为人们鼓励。生活中,很多人做一个行为可能是知其所为,甚至知其所以然,却讲不出是怎么获得的,甚至讲不出为什么这样做——但实际上,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讲不出所以然的后者,并不意味着其依靠的是神秘的直觉或者偶尔的运气,而是因为其遵守的是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不是通过灌输和言传,而是通过实践手段和点滴积累。当这种原则和我们日常的道德判断相互联系以后,其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原则决定”(decisions of principles)。
当然,以日常中的行为实践所推导出的上述结论也许是不可靠的,其中很大的质疑可能就在于:驾驶原则本身和行为原则是不同的,后者涉及价值判断。相较于一般的行为原则,涉及道德的行为原则多少会更重要一些,道德分歧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而应当遵从不一样的逻辑。〔1〕应当说,针对上述从一般的语境过渡到道德语境的质疑不止一处:无论是在由祈使句推出道德判断的逻辑结构,还是在亚氏三段论中,作为大前提的祈使句到道德语句之间的形式跳跃,抑或是下面将要提及的对价值词的逻辑分析,都会面临这样一种质疑。尽管看起来都是从一般语境到道德语境的过渡,但由于针对的对象不同,如此过渡的原因也不同。首先,针对道德语句逻辑结构的过渡,前已述及,基础在于祈使句和道德语句都为行为人所为为何提供说明或者吩咐,即使前者不需要理由,但二者在语气上是一致的,因而能够做指陈与首肯之区分。其次,针对亚氏三段论的推理,道德原则作为大前提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对大前提进行限定,这也恰恰是道德推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而本部分的“道德原则”才显得尤为重要。至于一般价值词如“善”到过渡至道德价值词如“道德善”的原因,将在结合价值词的内在构成中予以说明。
对此,需要结合道德语言理论在此处所采用的方法论:不追求原则本身的指向和意义,不去探究这些原则究竟是什么,而是直接把握其用法,在行为中规定之。具体来说,就要分析驾驶规则的获得:要么是先了解基本的驾驶原理和目的等,然后教授基本的驾驶规则;要么是先从基本的驾驶规则开始,慢慢教授目的和原理。但不论何种方式,都是针对驾驶员本人的实际状况,都是以假言祈使句的命令形式。与此不同,我们在生活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却是多从经验法则中获取的。当了解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法则,当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现实情况后,就需要对这些经验法则进行反思——但反思的原因不是为了该法则本身,而是更好地去行为,去生活,问题实际就变成了:如何证明一个道德判断的作出是正当的?
(二) 道德原则的形成
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又退回到问题的开始,而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不去执着于支撑道德判断的唯一真理的道德原则是什么,而是在实践中把握影响道德判断的因素。对此问题的妥善回答,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语言理论,而是要通盘考虑其在后面的道德论证中的分析。〔1〕黑尔在Freedom and Reason 一书中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进行道德推理的“规定性”与“可普遍化”原则,并在后期构建出进行道德论证的两个层次。而这属于另一个问题,与本文所探究的道德语言理论本身并无直接性关系。但本文一以贯之的关注点在道德语言本身,在此框架下,道德原则的问题就集中在:如何使得在某些情况下做什么成为一个普遍的原则?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两个进路:一是面向实践,以观察的视角来看原则的形成和演化;二是从细微着手,分析原则的逻辑构成。
首先,我们必须要作出自己的原则决定。表面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主张,康德早在强调人的意志自律时就已经表达过此主张,但黑尔的不同之处在于,自我决定是一个渐进且不断稳固的过程,这直接关系到道德原则的确立。何以如此?此处可以借用两个不同身份的行为者来展现这一过程。其中一个是非道德领域的科学家:科学家必须依赖于自己的观察;我们普通人在学习做实验时,如果出错,倾向于怀疑自己,并进而发现自己的实验错误,故而科学不是我们的职业,而是科学家的职业。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原则是如何形成的:通常我们小时候接受基本的道德教育,或者别人告诉我们,或者自己去做,我们一般会听从那些给我们提供的后来慢慢明白是好的的忠告。两种情形对比之下可以看到,科学家不会去重复书本上已有的全部东西,而是将其作为理所当然的,并执着于他自己的特殊研究;道德行动者也是如此,接受好的忠告,并结合自己情况具体采用,使之不时地适合于自己的情况。
(三) 道德原则的“学与教”
道德原则如此形成,也开启了道德教育的可能性:道德原则是可以被教授的,通过道德教育,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客观道德力量。此时不妨回顾一下亚氏伦理学中论“善”之获得: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未丧失接近德性的能力的人都能够通过某种学习或者努力获得幸福。〔1〕但并不是说要“看到最后”,并不是意味着人只有到最后才能获得善——倘若如此,一个人只有到死后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样既荒谬又无意义。而是说一个人只有死去才最终不再遭受恶或者不幸,因而可以可靠地说是至福之人。对此的论述详见[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25~29 页。
但是以这种方式获得“善”还需要两点特别说明。一是从人的主观上来看:人有资质之分,良好的品质和明智的能力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取得某种教育并不一定会获得这种能力。但亚氏主张明智即实践智慧的核心存在于每个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在“理智”上对“中道”的选取,故仍然有正确的理性和“真”之如何寻求的问题。二是从客观,即道德原则本身来看:教什么?这与前文提及的驾驶技术的学习有相似之处,但又更进一步,这里可以以两种极端呈现:只接受原则教育的,在行为之时会表现为直觉主义;只接受具体的规则教育,适用于具体的情景则缺乏可以反复适用的规定性,在行为之时往往表现为机会主义。〔2〕这里的“规则—原则”仅是在不严格意义上所说,与法哲学意义上较为严格的区别不同。
这样一种两端化的模式在伦理学的论证中并不罕见,在传统学者对两种观点进行或哲学上的解释,或结果上的衡量时,黑尔是如此解决的:
要在道德上臻于成熟,也就是通过学习去做原则决定,使两种表面上相互冲突的观点达到和谐一致,亦即学习运用“应当”语句,认识到这些语句只有通过诉诸一种标准或者一组原则,才能得到证实,而我们正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接受这种标准或这些原则,并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标准和原则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如此痛苦地努力去做的事情。〔1〕[英] 理查德·麦尔文·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76、188页。
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道德语言理论框架下道德原则决定的作出,甚至道德原则的建立,开始与价值词联系起来。
(四) 价值词的内在构成逻辑
依照道德语言理论的论证方式,对“价值词”的追问不去诉诸哲学解释,而是试图在实践中去发现:当我们在表达一个价值词时,这意味着什么?如黑尔一贯的论证进路,这里首先在非道德语境中展开,并对之前伦理学的观点进行分析。
以“善(好的)”为例,当我们说“A 是好草莓”时意味着什么?自然主义者认为这里存在使得草莓为好的特征,并着力予以探查,得到诸如“甜蜜、硕大、多汁”的特点。摩尔认为这会犯下自然主义谬误:即选择形而上学或者超越感觉的特征来定义善,试图从事实陈述中推导价值判断,而忽略了价值判断中的规定因素或赞许因素。
黑尔对自然主义谬误的立场是赞同的,但在论证说理的部分有所不同,而是依托于其语言逻辑立场:A 是一种好草莓;A 的特点是B:甜蜜、硕大、多汁。若依自然主义者的主张,“A 是好草莓”的意思等同于“A 是好草莓,并且A 是B”。那么,当我们想说“某种草莓之所以是好草莓是因为它甜蜜、硕大、多汁”时,提出的定义使得我们说成:某种草莓是甜蜜、硕大、多汁的,是因为它是甜蜜、硕大、多汁的。如此,便使得我们“无法说出某种我们在日常谈话中能有意义地谈论的事情”。
对此批评,自然主义做出了修正,他们认为,当我们提出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定义项和被定义项的含义完全一样,而是说两者指称相同的对象。例如,我们常常说“水是H2O”。显然,这两个语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所指称的东西是相同的,都指向一种具有无色无味、可饮用等一系列性质的东西。类似的观点可以用在对“善”的分析上。普特南认为,当把“善”定义为某一种特定的“N”时(正如此处的A 是好草莓,并且A 是B),并不是说二者的含义相同,而是在这种情形下,二者指称的性质相同。这一自然主义的定义并不意味着其拒绝对“善”的开放性。〔1〕[美]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8~219 页。
应当说,这一回应是有一定力度的——但主要是针对摩尔的批评而言。因为摩尔反对自然主义的主要根据就是其“开放—问题的论述”〔2〕对此批评详见[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 页。,但这对黑尔的反对并不切要害。因为黑尔强调的不是词语的多义和指向问题,而是含有“善”这些价值词语句的功能问题。前已提及,自然主义对“善”的定义使得我们“无法说出某种我们在日常谈话中能有意义地谈论的事情”——那么,我们借助含有价值词的语句想要如何有意义地谈论事情?
(五) 价值词的赞许(commending) 功能
使用“善”这个语词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在黑尔这里可以肯定一点,即当我们说“善”(好的) 时,往往是在表达一种价值判断:我们在评价什么,或者称赞什么,等等。换言之,这里的“赞许”和自然主义作为定义的语言活动不是一回事,“善”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事实描述。如上面的例子所揭示的,如果我们说“A 是好草莓,并且A 是B”,这样将无法表达对B的赞许,而变成无意义的重复。
毫无疑问,“善”这个词必然有描述事实以外的功能,而“赞许”就是在评价意义这个层面上的。赞许功能的本义是要引导人们的选择,即我们自己或他人的、现在或者将来的各种选择——这就意味着价值判断和行动联系了起来:以赞许的方式指引人们的选择,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
应当说,作为一种反驳理论,“赞许”功能是充分的〔3〕“善”不能用于赞许的特征来定义并不意味着在被称为“善行”特征与“善”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而只是意味着这种关系不是一种蕴含关系。:以自然特征定义来说明何为“善”忽略了其本应发挥的其他功能,如赞许,而这恰恰是联系价值判断和行为的关键。但作为一种建构理论,即说明“善”的意义,黑尔的理由充分吗?塞尔(J.R.Searle) 对此提出了质疑,并将其称为“言语行为的谬误”(speech act fallacy)。〔4〕J.R.Searle: Speech Acts.转引自[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年版,第77 页。比如还存在一些关于“善”的用法是被黑尔所忽视的,在“这通常是好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的”等语句中,赞许功能是无从推出的。
这一质疑已经不仅仅是关于“赞许”或者“善”本身是什么,双方的争议实质上是这样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以“X 是如何被使用的”来确定“X 的意义是什么”?
这一争议并不罕见。把语言视为工具的质疑也是早已有之,最初级的反省就足以对此产生疑虑,这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呈现为关于“意义”和“使用”的关系问题,简言之,维特根斯坦主张“意义即使用”。〔1〕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5~191 页。但若是仅仅将其理解为口号,理解为只要把意义都改写为使用就能解决语言意义的问题,那就太过草率和轻易了。一方面,“使用”本身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所指十分宽泛,而语言结构却是力求稳定;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也并非简单地将语言视为工具,而倾向于一条“初级反省的思路引导”,把语言视作现实的反映。
对此质疑,黑尔积极予以回应〔2〕R.M.Hare,Meaning and Speech Act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79,No.1 (Jan.,1970),pp.3-24.,曾出现两种批评:一种批评主张语言用力和意义完全不同,另一种则认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联系。黑尔着力回应了前一种批评。他以“承诺”(promise) 为例,指出当一个人说“我承诺”时,对其的完整解释需要指出其语气、时态等,因为“Do you promise…”和“Are you promising…”显然是不同的,承诺的原因不能直接等同于作出承诺这一行为。而“善”作为意涵价值判断的语词,在言语行为中的表现更为复杂:即便我们能确定在说出这个词语时的那些不同于事实断言的语气(mood)或者意向,但是意向具体是什么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同时,从“善”本身来看,其功能的归类也不是可以穷尽的。
可见,黑尔接受了一部分批评,承认价值词的功能是难以列举的,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支持了其在面向实践这一方法的坚持,继续将意义纳入到言语行为之中进行考察。但是应当看到,意义本身是属于本体论上的认知,虽然面向实践的言语行为确实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并且能作出一些更为精确的区分(比如上述关于承诺的分析),但在给出本体的意义说明上,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
黑尔自始至终并没有要给出所谓的本体意义说明,而始终都是致力于建立和完善道德论证,这在其后的著作和努力中或许可以窥得一二。因而其在方法上可能更倾向于“跨出经院式的分析伦理学的栅栏,去感受和正视书斋外活生生的‘现实世界’”〔1〕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2011 年版,第400 页。,相较于道德结论,他更关注道德争论。
即便如此,也不能豁免对道德原则的充分说明。道德论证的形式是从一个道德大前提和一个事实小前提,过渡至一个道德结论。在推理过程中,显然不能将推理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而必须将其终结在某一个行为原则上,而这一行为原则又是无法进一步加以论证的。如此,黑尔认为,通过“选择”(choosing) 使自己为之承担责任。质言之,判断者所采纳的规定,最终只能依凭判断者自己所任意采用的原则,这样,黑尔是不是也遇到了“终极原则”的难题?他认为判断不可能依照论证,而只能诉诸选择,选择便成为道德价值判断行为的最高权威,这样,道德主体通过讲出他自己所规定的“法则”而成为“立法者”——此时的“选择”和“情感”又有何不同呢?
本文在说明论证初衷时就已明确,出于对论证规则的怀疑而迅速转向本体意义的说明也许是太匆忙,因而有必要在具体问题上面向实践,优先进行基本的逻辑分析,澄清问题本身。黑尔在面对基本的道德基础问题(道德判断、道德原则、价值词等) 时,方法论上几乎都是由非道德领域进入道德领域,由批判传统观点到建构新规则,并坚持清晰的逻辑分析,始终保持对实践的面向,因而其规定语言的逻辑分析和推论规则的建立都极具建设性和说服力。但诚如上一部分所揭示的,致力于解决道德争论但不作出道德结论,道德语言分析的理论似乎又陷入了危机之中:相互冲突的道德争论持续不断,在此情形下,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道德分歧也不会得到一个真正合理的解决。
当然,以上评价仅针对方法本身而言,就黑尔自身的理论来说,这样的评价也许是为时尚早的。一方面,其在随后的《自由与理性》中也说明道德哲学的功能“在于阐明我们表达道德想法的语言逻辑结构,进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德问题”;〔2〕See,R.M .Hare,Freedom and Reas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p.1.另一方面,黑尔在后期的努力中更加致力于对论证规则的建构,并重视对结果的考量,转向新功利主义,以道德语言理论为基础建构起规范主义伦理学,而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则属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