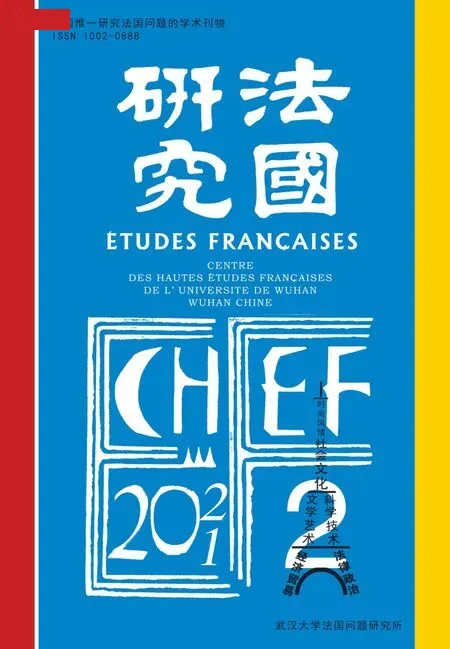掌舵人、牧羊人、经济人
——福柯论治理技艺的三重譬喻
肖炜静
治理(governmentality)是福柯晚期演讲稿的关键概念,也是勾连早期权力谱系学和晚期主体伦理学的中介。福柯一方面将治理术的发展视为政治现代性的关键特征,注重人口与资源整体分配的治理国家与封建领土型司法国家相区别。另一方面又将治理视为所有权力模式的分析框架。从纵向发展看,治理术包括希伯来的牧领权力(pourvoir pastoral),它经由基督教体系得以制度化并逐步渗透到世俗社会中。之后是对内强调无限治安、对外追求国家竞争力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但其无所不包的规章制度又逐步被限制管理的自由主义(libéralisme)所取代。从横向组成看,除了对治理技术历时发展的精致分析之外,晚期福柯还追溯古希腊,探讨伦理主体的形成,涉及直言(parrêsia)、欲望、家政、教育等一系列内容。这属于与外在他者治理相对的自我治理,也是反抗外物强制统治的可能途径。虽然福柯的论述绵密繁复,跨越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等诸学科,但他的阐释又不缺乏文学色彩,例如他对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伊恩》、歌德的《浮士德》的分析。同时,福柯承袭了自柏拉图以来以譬喻阐释政治思想的传统,治理技艺的某些关键特征和思想史渊源在掌舵人、牧羊人、经济人这三个譬喻中得以呈现。由这几个譬喻入手,我们得以一窥晚期福柯治理思想的几个关键内涵。
一、 掌舵人:引领全局与自我修身
在福柯的著作中,航行与船只的譬喻并不少见,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疯癫与文明》中的“愚人船”(Narrenschiff)。它与久远的神话传奇息息相关,勇敢的英雄们通过伟大的航行既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又传递了遥远的真理。与神秘浪漫的探险航行不同,确实存在的愚人船是被理性与世俗生活放逐的存在,它承载着麻风病者、贫苦流民、罪犯和诸种“精神错乱者”。被病毒腐蚀后的身体与心灵不能痊愈,他们无法在城墙下徘徊与禁闭,只能被推往一个遥远而安全的距离,既没有目的地,更无回头路,既是最自由,但也最束缚: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到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一旦下了船,人们不知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之间的不毛之地,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①[法]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3 页。
而承载疯人们的水域,既有神秘莫测的净化作用,也暗示着前途叵测的命运考验。富有意味的是,福柯早期著作中的愚人船与他晚期演讲稿中的航行譬喻完全不同,前者寓意被现实世界排斥的疯癫与非理性,而后者恰恰是与之相对的现实城邦,前者漂向未知的远方,后者则是回到熟悉的家乡,前者还属于福柯极具个人化的奇绝描绘,后者则有着西方海洋文明熏陶之下一以贯之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都曾用过航行譬喻传达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家篇》曾言:“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23 页。漂洋的船舶无疑会经历重重考验,或有礁石风暴,或有迷途难择,或有敌军侵袭。在《荷马史诗》中,大海上的风浪被作为城邦政治危难的隐喻,攻击阿尔戈斯人的特洛伊军队“有如辽阔的海上一个巨浪咆哮着,被强风推动滚涌,凶猛地扑过船舷”①[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卷十五),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行381-383。关于希腊诗歌中的航行隐喻及政治哲学思想,可参考刘晓枫:《城邦航船及其舵手——古希腊早期诗歌中的政治哲学举隅》,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 年第2 期。此时,国王应该像一位优秀的领航员,引领国家这艘大船,避开礁石,扛过巨浪,驶回港口。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中,歌队长劝说俄狄浦斯道:“当我们的城邦驾驶过痛苦的海洋之时,你曾为之掌舵(steer),现在请继续指引我们前进。”②Sophocles, Sophocles:Four Tragedies. Trans. Oliver Tapl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41.
更为典型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虚构的故事。在一艘船上,体型和力量巨大的船长已经耳聋眼瞎,略懂航海术但又早已落伍。而诸多船员为了争夺掌舵之权纠缠不休,或者簇拥在船长身边,游说其放权,或者将其灌醉杀害和抛尸,之后便纵酒摆宴席,任凭喜好与习惯随意驾驶。说服和组织杀害船长的人被吹捧为航海家,而真正掌握诸多技艺的人则被污蔑为“天象的观察者、喋喋不休的智术师、不中用的家伙”。③[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19 页。无疑,柏拉图的故事隐含着对民主制的反思:眼聋耳瞎的“高贵船长”属于古老的王政,它既可以被改良,也可能被暴力革命。诸多民众并无合格公民应有的智慧,掌握权力后不过是为了自我享乐。真正的哲人被抛在一边,善于蛊惑民心的人反而被称为航海家,之后也会转化为僭主。
柏拉图的航行譬喻既有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行使、分配、争夺的探讨,也涉及理想公民与智慧君主应具有的品格与技能,这与福柯强调的现代治理技艺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关键的差异是单个君王权力的行使与整体治理技艺的差别。从古希腊以来,有诸多试图给君主“忠告”的政治哲学著作,涉及君主的道德品行、驭下之道、治国之法等,《理想国》中对护卫者教育和哲人为王的论述也可归于此列,只是关注点是理想城邦下特定人群的素质要求,而非世俗意义上巩固现有权力的技巧。更为典型的文本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提倡君主必须凶猛如狮子,狡猾如狐狸。福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论述还属于传统的主权逻辑,其基础是君主对于君权具有唯一性、外在性与超越性,二者之间无任何本质或自然的联系,因而时刻面临被夺权的危险,因此君主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强化与保护君权,弥补君主与君权间的空隙。这就使得君权的行使成为了一种循环互推,即行使君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君权。
福柯在不同著作中都提及了治理技艺与主权权力的诸多差异。主权权力以法律的颁布与实施为中介,对内强调君权正统,对外关注领土扩张和种族战争。既以契约、分权、民意等方式作为合法性依据,但其效力又唯有在剥夺臣民生命、宣告对外战争之时才能彻底展现。霍布斯《利维坦》中的主权者的权力起源于全体公民为了生命安全而“自愿”让渡,但又成为了可以剥夺任一公民生命的压倒性存在——富有意味的是,作为一种海怪形象的Leviathan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城邦舰船形象的妖魔化与极端化。与之相反,“治理的目的则存在于它治理的事物中,存在于对治理所指导的过程的完善和强化中。”④[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84 页。它不是针对单一人物的统治或命令,而是关注与财富、资源、习俗、思维方式、流行病、死亡率等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人的总体。因此,治理必须通过不同策略相互配合,借助统计学、经济学、人口学等专业知识,试图实现数字化、科学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福柯指出,在讨论这种治理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诉诸这个隐喻,也就是船的隐喻”(福柯,2010: 82),它意味着一种全方位的安排与考量:“你不光要对这些船员负责,同时你还要对船舶及货物负责。照料一艘船还意味着你要认真考虑风向、礁石、风暴和各种坏天气。照料一艘船就是这样,它要在需要保护的船员和船舶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还有需要安全运抵港口的货物,以及所有这一切与各种突发事件(风向、礁石、风暴等)之间建立关系,这就是治理一艘船的特点。”(福柯,2010: 82)
治理对象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无疑要求治理者更广阔的视野、更精心的考量、更专业的知识:“真正的舵手必须集中精力研究一年的日期、季节、天空、星座、气流以及一切和这门技术密切先关的东西。”(柏拉图,2017: 219)对这些技艺的修炼并不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是更好地利用事物本身的规律展开治理。只不过,一个成功的掌舵人,不仅具备治理他人的技艺,更是自我的掌控人,这就是“对自我的治理”,它涉及一整套生存艺术,类似中国古人说的“修身”。富有意味的是,福柯同样用航行譬喻阐释自我修身技艺,此时该譬喻体现出三个内涵。首先,它代表一种变动,即将目光由外在现实转向自身,自我不是通向其他事物的工具,而是必须切实关心的存在。其次,变动朝着特定的目标与方向,转向自身的回归不仅涉及物理位置的转化,更隐含着自我才是最终的庇护之所:“迈向自身,同时是回归自身:就像人回到港口,或者一支军队重新占领城市和保护它的堡垒”①[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6 页。“人在这一港口中找到了他的来源地、他的祖国。走向自身的轨道总会有某种奥德赛似的东西。”(福柯,2005:263-264)最后,这个过程是充满危险的,就如同水手需要掌握诸多技艺一般,对自我的修炼涉及各种理论与实践技能,例如养生法、性爱论、回忆与反思、体能锻炼、节制训练等。晚期福柯对古希腊文献中自我修身的探讨,一方面完善了治理理论由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的过渡,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与早期被权力毛细血管全方位渗透、无任何个体自主性的主体截然不同的面向,这就是有自我掌控力和生存艺术的伦理化主体。
在与西方传统的航行譬喻和与主权权力的对比中,对他人的治理术展现出总体化、精细化、知识化等特征,而对自我的治理则强调通过诸方式达到对自我的掌控和回归。当然,航行譬喻只是福柯庞大的治理理论的一角,治理的心灵方向在牧羊人譬喻中最为典型,而现代国家全方位、数字化、经济化、自由化治理,则在经济人譬喻中得以呈现。
二、 牧羊人:个体化灵魂救赎与制度化权力压抑
据福柯考察,治理最初覆盖的领域非常之广,既指具体事物的推进与转移,如航行譬喻中的回归,也可以是精神领域的指导与带领,这在牧羊人譬喻中得到了完整呈现。后者有几个关键性特征。首先,牧领看护以善意和拯救为唯一理据,并且极度个人化、全方位、事无巨细。其他权力虽然也会有善意、仁慈的要素,但那不过是其战胜敌人、发号施令等关键特征的附属品而已。而宗教经典中的牧羊人不仅不会表现出一般权力的高高在上与咄咄逼人,反而是无止尽的诚意、勤勉、责任、付出。既会亲力亲为地喂养,公平准确地分配好食物,带领羊群前往丰美的草场,安排好路途的休憩时间,又时刻担忧和警惕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牧羊人的全部忧虑都在羊群,一点都不顾及自我,甚至为了羊群宁愿牺牲自己。更独特的是,牧羊人的看护体现出“全体”与“个体”的悖论。既要公平正确地处理羊群内部事务,又必须非常了解每一只羊的习性,任何一只羊都是不能放弃的存在。一方面,合格的牧羊人会按时清点羊群的数量,合理安排羊群整体饮食。例如,当摩西作牧羊人时,来到新草场后,会先让最年轻的母羊吃最嫩的草,然后放出去稍微大一点的母羊,最后才放出最为强壮的母羊,它们才能消化得了最硬的草。另一方面,这种整体的细致安排唯有在每一只羊都健康平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当任何一只羊走失或生病时,牧羊人绝对不能为了羊群整体弃它不顾,因为他必须拯救每一只羊。但每一只羊的不可放弃性,甚至会使牧羊人处于为了一只羊而必须放弃整个羊群的处境。这个主题在圣经文本中反复出现,摩西就曾经为了寻找一只迷途的母羊而暂时离开了整个羊群。但当摩西把迷途的母羊背回来时,那被他抛弃的羊群却也得到了拯救:“正是他同意放弃羊群的行动本身使羊群获得了象征性的获救。这里是牧羊人伦理和宗教悖论的核心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牧羊人悖论:为了全体牺牲一个,为了一个牺牲全体,这绝对是基督教的牧领问题的核心”(福柯,2010:111)
无疑,摩西“为了一个牺牲全体”的做法无法用日常利益考量去阐释,这也是宗教中牧羊人譬喻的特殊之处。和航行譬喻一样,福柯也是在与古希腊牧羊人譬喻的比较中展开论述的。从荷马史诗开始,君主或统治者是人民或城邦的牧羊人的说法就一直存在,它突出地表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中。在《理想国》第一卷中,色拉叙马霍斯为了反驳苏格拉底“统治者所做的总是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的说法,举了牧羊人的例子,认为牧羊人对牲畜的奉献不过是为了自己,因为将羊群养得越好,他能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苏格拉底对此的反驳是色拉叙马霍斯所定义的不是真正的统治者,而是其反面或丑化。虽然专业人士通过专业知识会获得特定报酬,但他在执行任务时考虑的是被照看者的利益,如医生之于病人,牧羊人之于羊群。只不过,福柯发现古希腊的牧羊人譬喻和宗教的牧羊人譬喻在各自领域的内涵、所占据的分量都完全不同。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牧羊人譬喻并不占主导地位,因为它无法精确反映政治家的独特性。牧羊人的工作牵涉诸多琐碎而日常的事,包括生病照顾、准备食物、安排交配等。但是在城邦之中,农夫、面包师、医生等行业才负责民众的身体健康、衣食起居,这就使得本应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的执政者的功能受到了挑战。因此,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牧羊人指代的不过是众多城邦角色的一种,它和治病救人的医生、栽收作物的农夫等比喻处于并列和平等的地位①[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50-351 页。,最多属于公务员序列,而非真正的执政者或立法者。
古希腊政治家并不如牧羊人一样凡事都亲力亲为,而是需要一系列辅助。在法庭上审判、在议会中说服大众、在战场上杀敌都不过是政治运作的诸多条件之一,而“政治的本质,政治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就是联系,如纺织工人把经线和经纬线联系起来。”(福柯,2010:126)政治家不是做日常琐事之人,而是审时度势、纵观全局、周密安排、发布命令的人,这一点和前文所提及的航行譬喻反而具有相似性。在城邦中从事不同岗位的个人就如同每一个船员,既得拥有各自职位的品德与技术,又要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一致。船长并不对单个人负责,而是对整艘船负责,甚至为了整个城邦的安危与发展,可以牺牲船上的个人。柏拉图就提及牧人必须及时发现和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牲口:“任何一个牧人,绝不会在照顾牲口之前不给他特殊的畜群来次清洗、剔除,即是说,他剔出不健康的和质量差的牲口,把它们送到别的畜群里去,只留下良种牲口和健康牲口加以照料。”(柏拉图,2001:145)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古希腊政治中的牧羊人譬喻与宗教中“为了一个而牺牲全体”的牧羊人完全不同。
东方希伯来文化提供了牧羊人譬喻的基本内涵,而基督教则彰显了其制度化后的严苛与精细。福柯同样在与希腊执政官制度的比较中,从拯救、法律、真理这三个方面凸显牧领权力将灵魂疗救与严酷教条相结合的特质。首先是拯救,在希腊执政官制度中,团体和团体负责人间也存在相互责任关系。城邦的灾难与瘟疫、战争与荣耀,都与执政者直接相关。在《俄狄浦斯王》中,破解斯蒂芬斯之谜和导致城邦瘟疫的是同一个君主。但在牧领制度中,规则与责任都更加严苛。福柯将其归纳为四点,一是分析责任原则,即牧羊人必须按时记录和观察每一只羊各方面的状态,精确照管,事无巨细。二是即时转移原则,牧羊人必须为羊的福德感到高兴,为其恶行感到痛苦,对羊所有的行为感同身受。三是牺牲倒转原则,即牧羊人必须准备好以自我死亡为代价保护羊群。最后是转移原则,即羊群和牧羊人之间由于各自的功德与缺陷互相拯救。
受到严格规则束缚的不仅是牧羊人,还有被引导的羊群本身。福柯通过与希腊城邦的服从机制相比较阐明了该特征。在城邦中,公民必须服从的是已经建立起的律法,这是对城邦中无差别个人的强制规定。除此之外,通过修辞术说服也会获得他人的自愿跟随。只是在得到真理后,引导者和被引导者的关系有可能被翻转,例如“我爱吾师,更爱真理”。而基督教的服从则强调不管命令的具体内容,都要无需思考,立即行动,甚至其内容越荒诞,越能考验信徒的心智与忠诚。服从也没有具体的修行目标,只是为了服从本身。至于真理层面,福柯强调的是宗教教育的独特之处,它包括日常行为和灵魂引导两方面。在日常行为方面,牧师不仅传递客观知识,他还必须通过自我榜样的作用进行言传身教,它的作用甚至大过具体的理论知识教育。同时,这种教育并没有严格的课堂限制,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诸方面,包括行为举止的观察和调整,持续细致的指导和纠正。在精神指导层面,一般的精神指导都有原因或环境,如亲人逝去、经历困境,指导也是暂时的、自愿的、有明确目标的。而基督教的精神指导是强制的、长期的、最终导向的不是要成为自我的主人,而是彻底地贬低自我,对指导者更加强烈的依赖和臣服。希腊人虽然也节制欲望和激情,但放弃快感是为了让自我得以掌控欲望,但基督教的节欲恰恰是将自我彻底贬低。希腊人追求的是强壮、健康的身体,而基督教对身体的折磨并不彰显意志,而是视为神对自我的考验,自我只能无条件地臣服于神。
基督教的灵魂引导依托于具体的制度与规则,最后打造了完善精致的从属网络,也实现了希伯来文化中牧羊人譬喻由个人化灵魂引导到制度化权力压抑的转变。福柯在《性史》中就对宗教的忏悔机制作了精彩的技术分析。忏悔必须要有具体的对话对象,它具有督促、强迫、坚定、介入忏悔活动中的作用,并且最后可以评价、惩罚、原谅、安慰忏悔者。在坦白之前,我们是有罪的。在坦白之时,就将罪和盘托出,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罪恶,唯有这样,在坦白之后,才可以获得“宽恕”:“它宣布它是无罪的,它让他赎罪和纯洁了„„它许诺他获得了拯救。”①[法]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 页。福柯在日常生活诸方面都发现了基督教忏悔机制的变形,它遍布于医院、审讯室、法庭、教室,发生在师生、父母与子女、警察与犯人间,形式有拷问、咨询、自传等等。这也意味着宗教对灵魂治理的具体方式,已经被世俗社会吸收和利用。
三、 经济人:从国家理性到自由社会
在将宗教法则与世俗社会相互关联的诸理论中,福柯将圣·托马斯视为典型,称其为“治理的类比”。圣·托马斯认为君主的责任是将上帝的治理挪到人间,最终目的是获得永远的至福和灵魂的救赎。这是一条由一家之父、再到牧师、君主、最后直通上帝的连续性链条,而这也是“一个充满着奇迹、不可思议的事和征兆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类比和代码的世界”。(福柯,2010:207)与之相反,现代国家理性有以下几个区别性特征:从统治目的上看,治理没有任何外在于国家的目的,即使有完善与至福的提法,也与上帝和救赎无关,而是国家本身的完善。从时间观上看,国家理性不会提来源问题,而是执着于永久、保守、当下的时间。也不会有末世帝国的终极幻想,世界上注定会永久地存在具有自己法律和目的的其他国家。因此,对外通过外交条约与常备军队,将国与国间的敌对关系转化为竞争关系。对内进行无限和细微的管理,既注重维持内部治安,也试图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国家力量。管理内容牵涉人口的数量、健康与职业、生产物品的供应与流通、社会资源的生产与分配等诸问题,遍布车间、学校、军队、市场、医疗等诸领域。法律往往处理的是相对固定的事件,而国家理性的治理则表现为更加具体的规章、法令、禁令等,它的特点是无限制、永远更新、越来越详细。同时,国家理性的治理以数字化为工具,统计学的发展也催生了“人口”的概念。那不是直接服从于君主的单个人,而是既具有内部规律,同时又关系一系列变量的整体,是具有发病率和死亡率、地域差异和年龄分布、既提供劳动力又消耗广大资源的人口。
国家理性的治理既要分析和计算人口和资源的诸变量,更要根据最终目的对不同变量施加影响。但这种无所不包的管理模式随后便被两条路径所限制,首先是法国的司法激进主义,其次是英国的功利主义。前者采取司法推演的方式,探讨人的自然权利或原始权利,推定特定条件下的权利与交换。通过在个人、国家、君主这几个层面的理想化规划,试图明确各个要素的边界。这是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其实也是卢梭的道路。后者则是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根据效用原则确定权限范围,“最大的效果与最小的成本”被视为政策制定的关键要素。前者是法律束缚下的契约主体,后者则是自我主动追寻的利益主体。权利主体是否定性的主体,他必须主动放弃自己的某种权利,才能得到另一种权利,二者之间的“否定、放弃以及限制”①[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43 页。的关系,构成了权利主体的辩证法机制。而利益主体不仅不要求个体放弃他的利益,反而唯有在个体主动追逐其利益的过程中,系统的利益才得以最大化,这就导致了治理方式的变革。即对社会资源与人口的调配,不可能通过面面俱到的规章制度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是应该充分利用系统中个体对利益的自主追逐。福柯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合理性的特征:如何调管治理技艺,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福柯,2011: 275)
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将自由主义视为最新的治理模式,而经济人就突出地体现在美国自由主义治理方式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也认为财富的生产取决于土地、资本和劳动。但无论是亚当·斯密、李嘉图还是凯恩斯,都没有直面劳动本身的性质,而是从外部关注劳动分工或劳动时间,将劳动作为整体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它自身是被动的。而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劳动产生的价值,而是劳动本身的规定与变化,以及该变化带来的经济结果。简单说来就是将劳动者的能力培养看成一种投资,工资就是该投资的回报。因此,对劳动者来说,自己就是一个企业,劳动者也从让渡劳动力的主体变成主动追逐利益的主体,这就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概念的内涵。这个概念其实严格说起来并不算是一个譬喻,但它预示着用经济学的理论或术语来分析和解释一个非经济领域,或经济从未涉及过的领域,也意味着用经济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体在系统中的行为模式。每个人既是系统诸要素的组成部分,是被动反应者,更是主动合作者,他们的自由正是他们得以被治理的原因:“经济行为就是我们所赋予个体之行为的一个可知性构架。它同样意味着,通过经济行为这个可知性构架,个体将变得是可被治理的。”(福柯,2011: 224)正因为如此,在系统中,每一个人又都处于“双重的不自主”中,既会偶然地影响他人,也会时刻受他人的影响,经济总体对于单个人而言具有“不可见”性。此刻,面对经济的整体进程,君主可以、也必须是无知的。这体现出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下对君主要求的变化,在牧领制度中,君主必须是上帝的代理人,但是如今的统治者面对市场却不可能拥有居高临下的目光。除此之外,还有诸多转变。例如市场功能的变化,市场最初是一个公正场所,它以合理的交换和流通为特征,应该尽力做到无作弊和不法的行为。而如今,市场变成了一个间接性颁布命令的裁决机制,被统治者可以用市场运行是否良好对政府机关的工作提出质询。
对牧领权力、国家理性和自由主义的分析只是福柯论述治理术的一个侧面。福柯在不同的著作中还“概括、粗糙和不精确”(福柯,2010: 92)地划分了三种统治形式,首先是司法国家(État de justice),对应的是封建领土型政体,以习惯法或成文法管理。其次是行政国家(État administrative),对应的是国家理性的管制和规训。最后是治理国家,关注人口和资源分布等总体。这三种形式在福柯不同时间段对罪行和惩罚的论述中得以典型呈现。在《规训与惩罚》的开头,福柯描述了两种不同类型制度下对待罪犯的方式。一种是公开的刑罚仪式,过分的暴力既是一种伸张正义的方式,也是为了证明君主本身的“过剩权力”。另一种是现代监狱里的惩戒和改造,表现为诸如罪犯的作息时间表、日常思想行为检查等安排,这是一种改过自新、劝恶从善的规训机制。相比于前者,它对由肉体到心灵的监视、训练和矫正无所不在,也更加人道、隐秘、经济。而在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惩罚体系中,罪犯会被“从人类学上抹去”(福柯,2011: 229),也就是说,对个人的心理或行为的矫正已不再重要,关键是通过“犯罪经济学”的分析来减少犯罪。因为“好的刑罚政策根本不是为了消灭犯罪,而是为了达到犯罪供给曲线与负需求曲线的平衡。”(福柯,2011: 227)以对毒品的打击为例,最初打击毒品的方式是减少毒品的供给,但是却会导致部分大卖商以及价格的上涨。同时,无论采取怎样严厉的政策,毒品交易都不可能完全消失。甚至过分严厉的政策反而可能使得毒品价格上涨,进而使毒瘾者的犯罪率增加。为此,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分析了两种类型的“毒品消费者”。一种是尚未成瘾者,会因为价格高而放弃消费,另一种是无论价格如何都会去购买的“刚性消费者”。聪明的贩毒人对于尚未成瘾者,采取的是低价售卖引诱其吸毒,对于沉迷的人员,则高价售卖。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则要采取与之相反的策略,对未成瘾者,通过打击来源使得毒品高价减少其购买,对高度成瘾者,低价则有可能减少其为了集资而发生的一系列杀人、抢劫等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干预的前提是将系统中的个人视为追逐特定自由和利益的“经济人”。治理必须“顺其自然”地利用并允许个人特定的行为取向,营造由差异性要素构成的系统的最优状态,这是一种“环境类型的干预”(福柯,2011: 230)。
可以发现,在选取的三个譬喻里,福柯的精彩论述诞生于喻体的日常鲜活与所论思想的深刻驳杂共同构成的张力场之中。无论是在思想史脉络里,还是在福柯的论述中,航行譬喻、牧羊人譬喻以及经济人的论述都有各自的关键特征。航行譬喻具有传统王权的领袖色彩,而牧羊人譬喻凸显宗教对灵魂的引导,“经济人”则彰显了最为现代的数字化、系统化、自动化管理方式。但也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在福柯的语境中,“治理”既是一种统治技艺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也是一种涵盖所有类型的统治方式的总称,包括从肉体到心灵,从古典到现代,从自我到他人。总体来说,一方面,福柯对特定譬喻所强调的重点十分突出,例如牧羊人譬喻的关键特征是“为了一个而牺牲全体”的悖论,而经济人则强调自由主义对治理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思想史的视野、不同治理模式的纵横交错、福柯本人思想的发展等原因,使得本体与喻体间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静态链接,而是既有特定指向,同时又与其它喻体和所指内容构成彼此关涉的网状结构。而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作为论述的背景,既是福柯论述的基础,也与之处于不断对话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