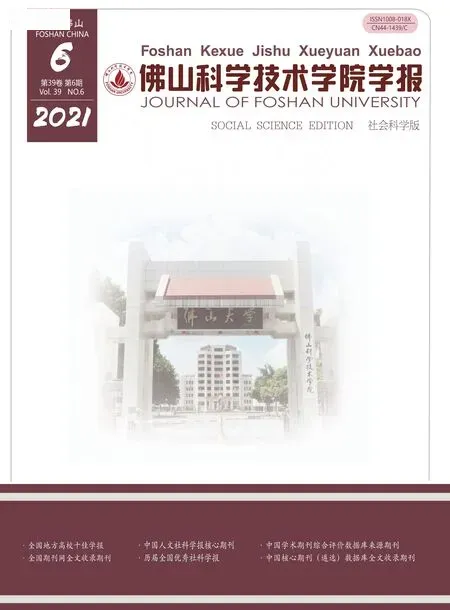囚徒困境:《K 氏零度》中人与科技的非零和博弈
林佳惠,周芸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1)
引言
19 世纪中期,威廉·汤姆森·开尔文男爵定义了热力学的绝对零度:绝对零度是热力学的最低温度,没有物质的温度能低于这一温度,也被称为K 氏零度或开氏零度,等于零下二百七十三点一五摄氏度。从理论上来说,处在这一温度附近的事物将达到宏观运动的最低形式,其组成的原子将在零点的附近做随机的量子涨落运动。基于K 氏零度理论的人体冷冻技术承诺可以保存肉身而不损害生命,让人们躲避疾病、灾难甚至末世而至想复活时再复活,尽管尚未有成功案例,仍凭借巨大的魔力吸引人们去实践它。
每个人都想与世长存(Everyone wants to own the end of the world)。[1]长生的欲望直指世界尽头,末日的幻想亘古不变。人人都害怕生离死别,想尽力延长有限的生命,死亡恐惧笼罩世界。死亡、恐惧与魔力一直是贯穿美国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以下简称德里罗)小说的主题,其最新小说《K 氏零度》(Zero K)延续了作者对后现代社会现状的关注与思考,描绘了一个对抗死亡的科技乌托邦:处于沙漠中的半实验室半陵墓的聚合中心(The Convergence)——人体冷冻基地,人体冷冻基地和前来接受冷冻的人们正是期望运用K 氏零度理论实现长生的愿望,躲过末日的灾难,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再造新的文明。
主人公杰弗里两次进入聚合中心,一次为了告别继母阿缇斯,另一次为了送别父亲罗斯。小说以杰弗里的叙述为线索构成对称的两部分[2],叙述了后现代囚徒困境中面对被技术背叛的风险,人与科技合作与否的两种选择。阿缇斯、小男孩和罗斯都选择合作,而杰弗里拒绝合作。阿缇斯和小男孩是身患疾病选择冷冻自己的一类,为回避最坏的死亡结果,他们选择不确定的技术,冷冻技术获得受试体,人获得健康重生的希望。罗斯是提前冷冻自己、放弃健康生命的一类,冷冻技术获得健康的受试体,人为了不确定的未来失去现有鲜活的生命。杰弗里则是拒绝人体冷冻的这一类,他保有健康生命,拒绝重生,冷冻技术无法获得受试体,他本人也没有超越死亡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与人体冷冻技术的博弈实际上是在死亡恐惧笼罩下个人与永生希望的一次性博弈,风险极大却似乎别无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物面对的是跨越死亡的科技,除了科技的魔力、救赎的希望,还有灾难社会中人与科技的博弈。小说不断思考的是“人如何面对科技?”“人如何确定自身?”“科技的边界及伦理是什么?”等问题。人们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掌控死亡的时代,也是科技对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正如德里罗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技术所能够实现的一切,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去实践的一切。”[2]科技成为除宗教信仰末日拯救之后的又一对抗死亡、对抗恐惧的途径。与宗教为人们勾画一个苍茫空洞的死后世界不同,科技承诺的是生命可以一直延续而永生。只不过自然的死亡是肉体的消失,科技的永生是抹去历史的新生。
国内学界对《K 氏零度》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身体、死亡等后现代因素的关注,着力分析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本文主要从囚徒困境得以形成的原因、科技社会对人的塑造、人的反思与选择三个方面分析人在死亡阴影中的存在可能,理解人身处科技漩涡中的焦虑与恐惧,以期为科技时代人的自处提供一定启示。
一、聚合中心:人类困境的诺亚方舟
非零和博弈通常发生在博弈双方合作中,双方得失相加是一个变数,一方的获得未必会造成另一方的损失,双方可能因为合作而一起获利,形成“双赢”局面。而在背叛中这种可能性更为复杂:背叛合作的一方可能会获得最大利益,所得大过“双赢”局面;被合作方单方面背叛的则面临最大的损失;互相背叛则是双方损失。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囚徒困境模式: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人是理性的动物,想为自身谋取利益降低风险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囚徒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让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又不至于被背叛。如果说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模式可以让双方基于害怕背叛所带来的报复而选择合作,那么只有一次的囚徒困境模式则更像是一场无法退避的豪赌。
在《K 氏零度》的实验基地中,人与科技形成的合作关系恰如只有一次的囚徒困境。如果人与科技合作,成为受试体,而人体冷冻技术确实可以实现并且不会割裂人的灵魂与肉体,那么科技被证实是进步的,人也可以获得救赎;如果人体冷冻技术本身无法实现,那么选择接受人体冷冻的“先驱”则会在灵魂和肉体上都承受背叛,永远失去生命,但科技可以证伪,也能取得进步;如果人选择不合作,不相信冷冻技术的价值,不为科技提供受试体,那么人体冷冻技术则无法取得实质上的进步,但人不会提前失去现有的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只是要继续面对末日的恐慌。
在灾难频发、死亡无处不在的社会,当宗教救赎不可期盼,彼岸世界大门已经关闭,人与科技的博弈是一场必然。人不得不从宗教信仰逃往科技信仰,从死亡恐惧奔向新生渴望,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与科技,尽管也承担巨大风险。小说中的半实验室半陵墓的聚合中心(The Convergence)——人体冷冻基地建立在沙漠之中,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到任何最近的城市都是越过边界[1]18。而聚合中心之所以建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秘密之地的原因也是人们必须面对科技、参与博弈、做出选择的原因:彼世不可信,现世不足期。
在“车里雅宾斯克时期”这一部分,作为基地的热忱拥护者,阿缇斯认为:一切都是过渡性的,人们来来往往,在此意义上离开,在彼意义上停留。她本人也总是思考着从浴室帘幕上滴落的水滴,某种意义上阿缇斯的生命和水滴的命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隐喻:冷冻延缓了水滴的坠落,让水滴停止奔赴尘土的路途;冷冻让阿缇斯此刻的生命停留,在地下越过漫长的时间,等待重新回归的希望。传统的宗教信仰已不能切实地承诺彼岸,但科技可以付诸此生的永存。于是,对科技的信仰成为基地存在的合理支撑,也成为每个奔赴此处,留在地下陵墓人体冷冻吊舱中的人的长生期望。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时期”这一部分中,确立基地核心思想的双胞胎兄弟(The stainmark)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Never can a man be more disatrously in death than when death itself shall be deathless.”[1]165阐释现世社会四处弥漫的死亡恐惧,如果死亡是不死的,那人便必然死去。恐怖和战争席卷全球,宗教之间的相互倾轧,战争的残酷杀戮,历史仇恨的宣扬,在未知的村寨里男人被屠杀、妇女被强奸、孩童被绑架……都是事实,不能因为没有记录,这些残酷、野蛮、原始的杀戮就可以被忽略。这个危险的世界与不可信的彼岸世界共同构成人存活于世的巨大阻碍,恐惧弥漫,人们无处可逃,只有寄希望于科技信仰。
可以说,聚合中心就是沙漠中这群聚在一起的人因为现实的残酷和彼岸的不可救赎而造出的诺亚方舟。盲目也好,狂妄也好,在灾难社会所造成的困境中:一半世界在挨饿,另一半世界在重新装修厨房;一些人死去,另一些人活着。[1]46沙漠基地为人们提供一种救赎,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毁灭,身处其中,确信现世和彼岸都不可靠的人必然如囚徒一样,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豪赌。
二、装置与影像:科技对人类困境的强化
在现实的非零和博弈中,期望获得更多利益的一方会向另一方抛出橄榄枝,通过合作实现双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当然,科技并非像人一样具有主观能动的意识,但科技本身的发展确实对人的观念有着巨大影响。在小说《K 氏零度》中,科技对人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人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地中随处可见的装置艺术,二是展现在空旷大厅中巨大屏幕的无声影像。
经过乘坐多种交通工具长时间的奔波,杰弗里来到静默压抑的建立在空旷无垠的沙漠中的聚合中心,“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But I was already feel trapped.[1]12)面对沉默寡言的寥寥几人,住在狭窄低矮没有窗户的房间,带上被监视行踪的腕表,不被允许走出大楼,彳亍在空荡无人的大厅里。在失去自由、手机无法使用、看不到外面的时间里,杰弗里把注意力放在了了解基地有限空间的各种装置上。他注意到:基地入口不远处立在飞扬尘土中的两个长袍女人,走廊角落无脸的裸体女性,微风拂过无一丝波动的没有鲜活花木的精致假花园,花园后的潮湿地窖中散发腐臭气味半身的人形雕塑,白色大理石房间中孤独蜷缩的女孩塑像,陈列在地下陵墓中的一排排装在吊舱中安详的赤裸的无名的人体,宽阔走廊中没有头的也没有储存在冷冻荚中的赤裸的人体……很难说明每一个塑像的含义,但比起阿缇斯和父亲的坦然、领路向导所说的“有趣interesting”,杰弗里从未有过轻松的感觉,像低矮局促的卧室、油漆的墙壁、紧闭的一排排门一样,这些装置让他感觉到的是一种压抑与焦虑、一种寻求意义的强烈渴望。但在基地里,除了未来的永生,名字、意义、面孔、过去都被丢弃或者说无关紧要,正如努力半生的罗斯更愿意为了未来重生而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现代文明的一系列灾难是《K 氏零度》中最大的恐惧,也是反复出现的意象。”[3]建在沙漠中的人体冷冻实验室中有许多大厅,在空荡无人的最后一个大厅尽头有巨大的屏幕从天花板垂落,直接展现在人面前的是一幕幕灾难的影像,杰弗里是唯一的观者。季风雨导致的洪水肆虐、龙卷风对整个城市的破坏、僧人自焚、社会动乱、战争杀戮……穿插在小说的不同部分,构成杰弗里对现代文明灾难的直观感受。声音的消失迫使观者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画面本身,直接放大了这些影像给人的震撼与恐惧。[4]“寺庙被洪水淹没,房屋从山坡上坍塌下来。我看着城市街道上的水不断上升,汽车和司机都在下面。屏幕的尺寸使影响效果远远超过电视新闻。一切难以看清,这个场景延续了很久,远远超过广播的播报……”[1]6在极端的自然灾害中,人们苦苦挣扎却无能为力。视屏将灾难巨大的摧毁力量带到观者的眼前,也将生命的脆弱展现在人们眼前。现世笼罩着巨大的阴影,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不得不努力找寻继续生存的可能。杰弗里没有在大厅里,在自己身旁发现另一个观者,实验室里的人无一不是寄希望用科技消除这种恐惧。
除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报复,人类自身也在不断自我损害和相互损害。在不知名的地方僧人正在痛苦地自焚,人们成群结队、形形色色涌在一起,不停奔走、奔跑的男男女女,图像被放大,从屏幕溢出来。然而,在突然的一刻杰弗里想到影视制作,一致的行动、有序的步伐……“这些都是虚构的视觉影像,野火和燃烧的僧侣,数字节,数字代码,所有的都是电脑生成,没有一个是真实的。”[1]103非真实意味着一种轻松,实验基地以虚构的影像展现想象中的末世,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人因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出对科技的信仰。杰弗里仍旧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对死亡和科技的思考,可是女友艾玛的养子——斯塔克作为儿童兵在战争中血淋淋的死亡却证实了视频中的影像正是真切发生的。如德里罗在访谈中所提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战争的方式正在上演……不同的政体、宗教、个人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到处都如此,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种族暴动,ISIS,许多无辜的人被伤害。这些战争其实是古老的战争,它们早该被制止,却仍在上演着。”[2]
面对巨大屏幕上真实发生的无声影像,杰弗里是渺小无助、焦虑迷茫的。他无法认同也无法相信科技承诺的永生,但在恐惧面前,他也不能否认科技的力量。不时出现在基地中的人偶装置艺术同样让杰弗里陷入一种身份焦虑之中。巨大的死气沉沉的颅骨,被放置在会议室中,令人不安;赤裸的、没有头发的、没有面部特征的人体模型被固定在大厅墙上的凹槽里;地窖中排列起来的半身的人体模型剥蚀严重;被放置在冷冻舱中真正的人体和没有头部的人体……一切都让杰弗里感到难以接受,他却要两次面对这些场景,终有一天父亲也会被冷冻在吊舱中,赤身裸体,与许多同样选择的人一起。杰弗里无法认同这样的方式,却也无法阻止阿缇斯和罗斯选择这样的方式。他不信任人体冷冻技术,认为父亲提前冷冻自己是对生命本身的背叛。但是即使处于最深的怀疑之中,他也不禁希望有一天瘫痪的小男孩可以重新获得健康。
一方面,实验室的装置艺术强调着永生,否定着现实意义,是对科技世界忽视个体性的夸张呈现;另一方面,大厅的影像将灾难聚集在人们眼前,极致显现和刻意放大,直呈现实的丑陋。对科技的怀疑与对生命的热爱是杰弗里无法明确自己观点的重要原因,他始终处于思考的焦虑、身份的焦虑之中。
三、定义与命名:超越困境的体悟与反思
对命名的热忱,对定义的执着,是杰弗里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的把握自身确定性的努力。父母不明原因的分离,父亲独自离开的傍晚,他反复写着、念着有关三角函数的三个素语:正弦余弦正切,以后在别人家做客感到不安时,也是同样的“正弦余弦正切”。可以说生活中父亲身份的缺失加剧了他对确定性的渴望。追寻事物的意义,确定周围的事物,找寻自我的位置……希望过一种与父亲精致积极人生不同的生活,最终却发现父亲竟然改了自己原本的名字,放弃了他世代的历史,也使得渴望定义的杰弗里连追寻生物谱系的可能都化为乌有。“如果以Satterswaite 这个名字,我过去是谁,将成为谁?”(Who would I have been and what would I have become?[1]55)一个人的名字包含着一个人所有的历史、记忆和秘密,但是杰弗里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名字。一直以来,他都处在身份的焦虑之中。而这份焦虑在只关心永生,忽略名字、历史和过去的实验中心被放大了。
在基地中,对死亡的恐惧要么通过宗教信仰的灵魂救赎来抹平,要么通过科技来消除。罗斯选择“基于信仰的技术,另一个神”,这个神让人们“死后复生(life after death)”。[1]4让罗斯花费巨资打造的正是处于吉尔吉斯斯坦沙漠中的人体冷冻室,儿子杰弗里被带到了这里,为了相聚,亦是告别。与罗斯和阿缇斯的亲密关系让杰弗里得以深入地参观这个半实验室半陵墓的基地,然而在这个空间里,杰弗里始终是一个外来者。执着于意义、关系和位置的他与周围一切格格不入,对冷冻技术的怀疑与对整个空间的感觉始终呈现着杰弗里的外来者身份。也正是对基地的环境的排斥和对冷冻技术的怀疑让杰弗里能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和体悟。
通过人体冷冻,可以实现对肉体的保存,在更好的时代醒来,实现生命的长存。罗斯的第二任妻子,杰弗里的继母阿缇斯正是这次实验的实验对象。在这场注定的告别里,杰弗里想到自己的母亲,死亡第一次出现了,两种死亡交织在一起。在阿缇斯的身旁,杰弗里脑海中是母亲死去的场景。在看到父亲上了杂志封面的那个下午,他看着床上等待死亡的玛德琳、门口拄着拐杖的邻居。他能清晰回忆起于母亲一起生活的点滴细节,感到一种真实的刺痛,是死亡确证了曾经的存在。母亲身体的消失恰恰证明着曾经的存在,“不正是我们最终死去这件事,让我们对我们生命中的人来说显得珍贵吗?”[1]46死亡让人们消失在对方的生命中,却又在他人切实的感受中建构了自己。然而当死亡消失时,生命的意义变得难以找寻。这种对死亡的思考不只表现在对母亲的回忆里,也对比着阿缇斯和罗斯的选择,“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已死亡的人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停止你的存在?”[1]70关于“存在”和“是”的问题是思考死亡的核心,“是石头,但它不存在”,“是马,但马不存在”,如果人体冷冻得以实现,那么“是阿缇斯,但她不存在”。存在和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死亡便没有存在,是过去构成生命的真实,如果没有过去的身体是阿缇斯,是罗斯,是任何人,那么他们从真实性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没有过去,便不是那个名字在他者生命中所标记的存在。由此,对死亡的恐惧和因恐惧而做的选择又有何意义?杰弗里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技术怀着一种追问,也注定他首先是一个游离在这个信仰之外的人。
无法认同父亲的价值,与父亲的多年分别和性格差异,对平凡生活的细心感受让杰弗里始终处在基地之中却又徘徊在这一空间之外。“那些死去的人呢?其他人。总会有别人。为什么有些人要活着而另一些人要死?”[1]46他无法理解基地的建筑艺术,更无法理解人们抛弃此生的存在去选择一个不确定的、没有历史的未来。冷冻技术许诺人们在新的时代醒来,拥有新的人生,把过去的经历远远抛在脑后。对杰弗里来说身体的保存不能等于存在,“难道不正是我们所遗忘的那些东西告诉我们自己是谁吗?”[1]117是过去构成了人们此刻的存在,也是我们生命中他人的见证和感受标示出我们的存在。科技带给人们的东西是复杂的,它让人们远离死亡,也让人们无限接近死亡。科技抹掉过去,也让人之间孤立隔绝。无法认同实验基地中人们的思想,也无法对灾难视而不见的杰弗里需要不断思考的其实是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和位置。
通过对自我身份的把握、对死亡与存在的重新认识,杰弗里最终认同了死亡的意义,超越了由死亡恐惧所支撑的囚徒困境。同样面对着世界的灾难、生存的恐惧,与父亲和继母的选择不同,杰弗里没有把自己陷在这场囚徒的困境里,他选择勇敢面对不完美的生活,在冰封的海角找到希望的出口。与母亲是朝夕相处构成了生命的真实感,我知道我是谁。[1]73他渐渐在生活细节里看到了生命的意义来源于人的历史,是细碎点滴的平常构成了生命的价值,是死亡确证了生命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年少时为何要跛脚行走,可是当灾难影像压得他几乎要倒塌时,他发现自己再次跛脚走路,是他自己在主宰着这架复杂的身体机器。当艾玛给身体残障的孩子上课时,他明白要发出一个音是多么困难,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奇迹。当父亲安排工作时,他选择了拒绝,尽管穷困潦倒,但他是他自己,不用顶着“罗斯的儿子”这一身份。他会为了旧公寓里与母亲细碎平常的回忆而放弃搬进父亲豪华的海景别墅……在不知不觉中,渴望确定性的杰弗里已经做了太多选择,而这些选择也让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小说结尾便是杰弗里的选择:我不需要天堂之光,我听见孩子惊奇的呼喊。(I didn’t need heaven’s light.I had the boy’s cries of wonder.)[1]190对杰弗里而言,生命本身就是奇迹,值得期待。杰弗里所畏惧的不是死亡而是无意义,在依靠死亡恐惧所设的囚徒困境之中,他不是囚徒,便无惧困境。
结语
在传统信仰崩溃、灾难无处不在、末日危机浮现的社会里,科技成为人自我救赎的最大希望,但与此同时许诺未来的科技也让人将自身的身份、存在的价值抛入深渊。冷冻的告别掩盖了自我与他者的情感联系,消失的死亡也让自我与他者难以相互确证。科技的发展不只带来对科技力量本身的思考,也让人们面对智能与智慧的选择,冲击着人们对自我的定义。
对彼岸世界失望、对现世世界不抱期望的人沉溺于灾难社会无处不在的恐慌之中,在对科技的妄想式迷恋中抛却自身生命的意义,投身于科技所承诺的不确定的未来之中。基地中的人们如同困境中必须做出选择的一方囚徒,渴望着永生,也承担着长眠的风险。这固然不属于承认当下的杰弗里的选择,他看到死亡与存在与意义的关系,比起死亡,他更害怕的是无意义,也是对意义的追寻让其摆脱困境。渴望拥抱切实生活的人们面对残酷的现实将何去何从?真实的世界是可爱又可怕的世界,自我是人们必须要把握的底线,灾难和恐慌也是人们不可忽视的威胁,没有人能跳出困境之外,对科技及其用途和底线的思考才是人们无法回避的焦虑。小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答案,它启示着人们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