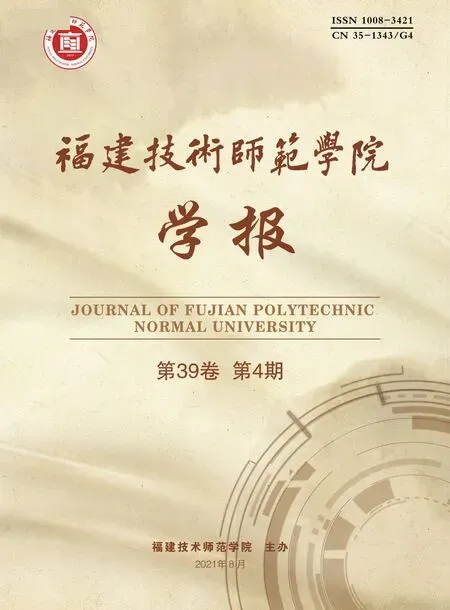论80年代以来女作家自传的个人叙事
雷莹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自传在本质上是身份认同的构造,女性独特的生理、心理特征及社会文化地位影响了女性的自我认定,也影响其自传文本的建构。女作家在自传中坦率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及情感体验,通过对传主应该忏悔的行为的叙述和行为动机的深入剖析,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及精神层面的重生。丁玲、戴厚英、张雅文等女作家在写作自传之前已是成熟的作家,拥有较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和从容的表达才能,这使她们能在自传写作中既呈现出时代语境中自我存在的复杂本相和状态,又不完全依附于宏大事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自传中,茅盾、王蒙等男性作家的自传受到关注较多,而大部分的女作家自传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究其原因是男性作家更多地从历史事件线索中找到了自身的时间感,将个人经历融入社会性的集体记忆中,在自传中提供了更多丰富、详实的资料。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男性作家在自传中以理性化的叙述重构历史与记忆的清单,女作家作为社会格局中的弱势在自传中更多地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的价值,关注社会历史给个体成长提供的意义,记录私人性的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这样的选择使她们的自传写作属于个人叙事。
一、个人化叙事
中国传统自传受史传的影响,关注的重点是传主与社会的关系。“加上篇幅的限制,过往传记只能以记叙传主官职、爵禄、往来、政绩的进退为主要内容。而序传的情形更为不堪,一般四五千字,而议论居之七八,对于个人生活历程的记录,更是简上加简”[1]。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大量男作家自传由于传主的高度社会意识形态化,采用历史叙事的内容和风格,关注自我与社会大局、大事相关的那部分人生经历,更接近中国传统自传。而女作家在自传中采用了自我的个性化叙述,重视自我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符合现代自传关注传主内心冲突和人格复杂性的特征。女作家自传虽然也有关于社会历史的描写,但是这些更多是有传主自我思想感情投射的社会事件,并不一定要包含深刻的社会意识和历史内涵。丁玲、戴厚英、张雅文等女作家都有着传奇的人生,她们坎坷的人生历程与社会变动有着密切关联,但自传中既没有社会历史大事件的详细叙述,也没有历史事件的完整记录。丁玲的《风雪人间》包括《寂居》《悲伤》《何去何从》等短篇,从这些篇名就可以看出自传虽然书写了其在北大荒的生活和遭遇,但重点不是对外部事件的叙述而是呈现个人历经磨难时的精神状态,这是以自传的形式营造起的心灵景观,是一部显影在自我意识中的历史。张雅文在自传的第九章《死神在女儿的哭声中放过了我》中叙述了丈夫被关进牛棚之后自己的悲惨遭遇,但叙述的重点不是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影响整个国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在地狱之门一次次向“我”敞开时,自己从困惑、迷茫、痛苦到要坚定地为了丈夫和孩子活下去的心路历程。戴厚英自传中《反右斗争 惊梦向左》一章主要是由父亲、叔叔的遭遇组成,政治走入自己的生活与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有直接联系。而传主与闻捷的恋情也是《十年沉浮》的主要线索和重要内容。女作家自传往往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互为映照,通过传主一次次选择而人生却总不平顺的情节,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困境中不断探索挣扎的成长过程。张抗抗曾怀抱文学梦想走向北大荒,可是为了实现她的文学梦,她甚至付出了牺牲文学的代价,对文学真诚而执着的追求最终使她走出迷雾回归文学自身,成长为一名以人性为终极关怀的女作家。一个个体的人在历史运转中失语,不仅无法按照个体的心愿去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而且在历史运行中内心一次次失落、生命一点点消耗,这种触目惊心的景观体现出自传关照个人存在状态的深度。自我期许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使这些女性产生过失望、迷茫等情绪,但对信仰的坚守和坚强乐观的个性使她们走出困境不断成长,因此女作家自传关注的是对自我个性或情感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
女作家自传记述了传主所经历的重大人生转折,挖掘每一次转折为个人提供的深刻而复杂的意义。对于真诚而敏感的人来说,这些意外事件的打击足以启动她的思考,追问外部因素的源头和内部因素的力量。戴厚英的父母家人曾因政治经济的双重剥夺,陷入了赤贫的境地,为了帮助父母,她和女儿的生活也一度非常艰苦。但是赤贫生活又成为她灵魂的清洁剂。“我尽力永远不会忘记贫苦的人民,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在人民的苦难面前漠不关心。我不会昧着良心高唱颂歌,更不会甘作鱼肉百姓的败类。我今天摆脱了贫困,但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从贫困走过来的。我对下层人民的真切同情,正是植根于我苦难的过去。我现在仍然不会享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对花天酒地嗤之以鼻,原因也在这里”[2]167。出生在山沟里的张雅文目睹了父辈在命运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目睹了哥哥、姐姐们在环境的限制下无法选择人生道路的悲苦命运,也曾在各种大灾小难中尝尽世态炎凉。“这十年也使我从懵懂与无知中醒来,学会了坚强与思考,懂得了要善以待人,尤其要善待那些无职无权、被命运推向绝境的底层人。即使他是一个囚徒或捡破烂的,我也要尊重他,他也是人,因为我也是从逆境中走过来的。这种深切的人生感受对我的一生,对我后来的创作,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3]211。所有的艰难困苦造就了她不畏艰险、不惧苦难的个性,这些促使她成长为一名为英雄树碑立传、为弱者仗义执言的报告文学作家。女作家在自传中对自己置身于历史洪流中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以及个体心路历程的呈现,间接地表现了生动而复杂的时代历史图景。戴厚英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值得骄人的财富,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的经历。”“与我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的遭遇,我几乎都经历过。与我年龄相仿的中国妇女可能尝到的酸甜苦辣,我差不多也尝遍了。”[2]1对个人处境和遭遇的关注是女作家自传写作的源泉,但它同时触动了一个群体的精神隐痛。个体在时代中的存在状态就是时代状况的隐喻,女作家用个人的经验和语言进行个体存在状态的表达,是自我对存在状态的言说与见证,与时代有着强烈的互显关系。在自传中,女作家释放了自我各种不同层次的原始记忆、情感等,体现了强烈而执着的个人化思维。
二、情感化叙事
许多有一定影响力的男作家期望以撰写自传的方式为历史重构提供史料支持,因此作品以叙事为主,客观性强,而女作家自传采用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在叙事的同时更多融入了抒情性和哲理性文学元素,通过主观体验式的语言呈现作者的人生经历。女作家在自传中投入了强烈的感情,用抒情性的语言建构自传的艺术世界。作者在叙事的同时直接抒发感情,这种表达方式所具有的直达人心的力量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对传主的坦诚相告产生共鸣。丁玲在得知陈明被下放到黑龙江劳动,三天以后就要离开时,情不自禁抒发情感:“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像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呵!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重聚。”[4]4作者通过饱含情感的语言,使读者感受到她坚强乐观的个性,以及面对困境时对信仰对爱情的坚定执着。丁玲在自传中叙述了传主独居农场时对陈明的思念:“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哎,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4]59作者用浓重的抒情彩笔描绘传主热烈美好的爱情,即使在残酷的现实中他们天各一方,但是那种真挚的感情、那种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却是永恒的。
除了用抒情性语言直抒胸臆外,传主还经常用抒情性的语言书写刻骨铭心的场景,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张雅文在自传中叙述自己在孩子刚满月时拖着虚弱的身体冒着大雪去郊区看望被关押的丈夫,可是在十几双眼睛的注视下,朝思暮想的爱人连一句心里话都不能说。“刚生完孩子,又经历了几次生死大难,此刻,有多少话要对亲人说,有多少委屈要向爱人倾诉啊!可是,他站在北门口,我坐在南炕沿上,我们只能透过十几双冷冰冰的眼睛,远远地望着对方……不过没关系,只要他活着就好,只要他活着我们一家三口就有团聚那天!”[3]202这样的描述在具象生动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以真情感染读者。《别离》一文叙述了丁玲在1965年5月被安排到21队劳动时与陈明分别的情景,“门呀然一声开了,他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象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却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4]82。丁玲充满感情地描述了即将与爱人结束这种苦苦依恋的生活走向未知时的情景,用抒情性语言书写别离时的细节,呈现了两人内心深处默默承受着痛苦,却希望给对方以宽慰和鼓舞的复杂心情。
自传是以自我为中心,但必然会涉及与自我相关的人和事。不同于传统史传的纪事写人,女作家在写人记事时明显带有个人好恶的感性投射,这也是自传情感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戴厚英与闻捷相恋期间曾接待过上海某报的两位记者,当时的一些细节后来出现在有关他们恋爱的汇报中,因此戴厚英认为两位记者的来访本就动机不纯,她在自传中写道:“可是那位年轻的记者,以前曾多次与我打过交道,以后却再也不见面了。想必正在哪里得意着。朗朗乾坤的阴影里,堂而皇之的冠戴下,掩蔽着多少可耻的罪恶,隐藏着多少丑陋的灵魂?上帝知道,我是相信报应的。”[2]137女作家在自传中对人事的评价更多建立在个人印象或感受的基础上,这种评价本身可能不够准确或客观,但是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真切的情感倾向。
三、反思的叙事模式
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许多人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认识和信仰,“在群众声威的气氛镇摄之下自谴、自责、自恨、自愧、自悔、自惭形秽,于是,积年学养累成的‘精神武装’完全被解除了,人格尊严完全零化了”[5]。新时期作家们面对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作为最早觉醒的社会群体之一他们都开始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思考和总结。中国现代作家受西方自传的影响,在自传创作中加入反思忏悔意识,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罪责忏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家自传中不缺少反思,但大多数男作家的自传在涉及社会历史时反思极为深刻,而一旦涉及自我行为,反思就大打折扣,有时甚至为了塑造正确的自己而回避自己的罪责,或是极力为自己辩解。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时代的错误应该受到抨击,但人性之恶更应该被揭露和正视。女作家往往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思想情感的重大变化,进而自我反思,写下一部展示自我心路历程的精神自传,再现生命及相关生活的真。“‘忏悔’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活动,企图通过自我检讨和反省,排除恶念,大彻大悟,以期再生”[6]2。如果没有生存危机、内心危机,没有在“恶”的逼迫下不甘沉沦的灵魂,就不会有这些作品出现。韦君宜认为虽然自己有受过苦,但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呈现出来,她在自传中勇敢地将自己曾经做过的违背良心的事暴露出来,作为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逐一叙述。这可以看作是作者与自己所犯之“罪”的对话,是作者对自己的恶进行理解和探索的开始,通过自己亲历的一件件事、一个个场景,为读者开启了理解社会和时代的崭新窗口。回首过往的人生历程,女作家没有被坎坷的命运蒙蔽,而是更加坚定了信念,从个体的经验中索解,承担个体的责任。戴厚英还是一名大四学生时,曾经在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大会上发言,粗暴地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几十年过来了,当我明白什么是人道什么是善良的时候,我为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感到羞愧。我愿以后的年轻人再也不要重复我这样在无知和愚昧的蛊惑下所犯的错误,凡事应该多想想,多听听不同的意见。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要想到自己毕竟所知甚少”[2]71。作者直面自我人性中更深层的真实,在自传中描述了内疚和羞愧这类只有本人才能把握和理解的情绪体验,而这种内疚感、羞愧感就内在地包含了忏悔叙事的动机。1969年初,张抗抗在外婆和舅舅的安排下到德清县洛舍公社陆家湾当插队知青,但出于年轻人对远方的向往,也为了到一个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地方彻底摆脱家庭出身和父母问题造成的歧视和压迫,她在几个月后毅然走向北大荒。这一抉择却成为她最要自责的一件事。“当时,妈妈虚弱的身体,已如游丝奄奄系于千钧;我的远行,在她不可重负的劳累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中,犹如雪上加霜。妈妈的痛苦不在于我下决心去边疆,而在于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时,弃她而去。我本已到陆家湾插队,我是完全可以不去北大荒的,但我却执意要走。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当我离家北上时,我怎么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酷?”[6]37作者在自传中呈现的个人处境代表了一类人的处境,她们因自己深刻的个人经验具备了对人性进行多维透视的能力。在自传创作中任何忏悔都必须有勇气说出事实的真相。而自传的真实性来自于对复杂人性的展示,来自于对传主的生存处境和灵魂处境的展示,让读者真实感受到传主痛苦的个人性,及传主作为一个人的痛苦的普遍性。女作家在回述往事时,那些亲见的、亲历的应当忏悔的事件让她们意识到自我生命的空虚和匮乏,这种空虚和匮乏并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俯瞰人间就可以充实的,而是必须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切体悟来救赎,因此,忏悔叙事挽救了作者自我的存在之思。
每个个体都是自己所在时代与自我人生的承担者,生命随着时间流逝,而自传写作是用语言留住逝去的生命时间。反思是对过去错误的质疑和承担,是个人成长和自我认同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承担的见证,女作家普遍采用了历史加反思的方式书写那些给予自己深刻生命启示的遭遇和事件。在回顾自己苦难的童年经历时,张雅文想到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农民。“苦难给人们带来的绝不是什么财富,更不是什么赞美之词,而是非人的,没有选择的、伤害自尊的痛苦。可是,令我们不得不深思的是,中国有几个农民没有经历过苦难?”[3]136丁玲在自传中刻画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朴实平和的基层干部李主任,作者通过李主任的故事呈现人间的温情,同时也从他的经历中提出了更沉重的思考。她认为李主任在生活和事业上遭遇的挫折主要是因为文化低,“我总觉得我对他,或者是我们对他,都负有咎责似的。这样一群纯朴的农村子弟,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为什么过去不给他们更多一些学习的机会?自然,在战争环境下是很困难的,但至少在建国以后,我们就应该大批大批组织这些同志,进中学,进技术专科学校,进大学,教会他们一些新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4]44女作家在自传中的反思是在个体人生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个性化思考。
自传是对个人生命体验的回溯性叙述,具有主体意识和尊严意识的女作家将生命中的感性体验进行升华,在对往事的追忆中进行反思。反思的前提是觉醒,反思的作用是改变并超越自我,因此,作者对自我生命体验的书写,也是对自我的言说与承担。女作家自传是建立在个体生命经验上的个人叙事,这种疗治切身创痛的文本策略,将具体的人事导入当下的历史,对真实“遭遇”的陈述和展示,使作品具有真诚坦率、自然朴实的特点,既有历史内容又有人性内涵。女作家自传在反思的叙事模式中对经验性事实和生命体验进行叙述,这种个人感性经验的叙述可能存在着更多人性的真实面目,提供了另一种文学生态和精神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