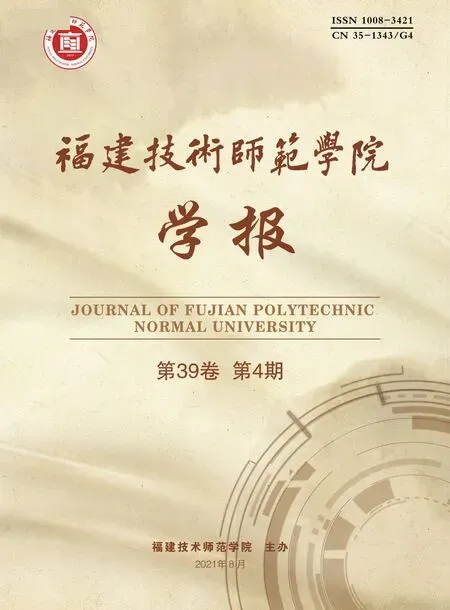黄檗禅僧独立性易的书学与日本书法
温志拔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黄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福建福清 350300)
中日两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宋代开始,逐渐走向繁盛,伴随着经济贸易的发达,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在经历了五代至北宋的短暂沉寂之后,出现了唐代以后的又一次发展期。闽浙两省,地处东南沿海,六朝时期开始,便是中日两国海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起点,宁波、福州、泉州等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自始至终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至明清易代之际,以福清黄檗宗为中心的晚明禅僧遗民东渡日本,在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影响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日本各阶层社会,成为唐代以后两国社会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峰。这其中,福清籍僧人隐元隆琦(1592—1673)更是其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一位,而他与同贯即非如一禅师(1616—1671)年以及晋江禅僧木庵性瑫(1611—1684),因书画艺术成就,在日本并称“黄檗三笔”,对此后日本文人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黄檗流派,对日本‘唐样’书法的振兴贡献颇大”[1]220,学界对此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①。这一时期,同受隐元感召影响,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局势中,别离妻子东渡,并曾侍居隐元左右的,还有浙江杭州籍禅僧独立性易,其晚年虽以医术闻名,但同样以独特的书论主张和书法创作,不仅与“黄檗三笔”书法迥然不同,且同样影响并拓展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书风。
一、独立性易的家世生平与书风取向
独立性易(1596—1672),本名戴观胤,后改名戴笠,字曼公②,号荷鉏、天闲老人,出家后法号独立性易,杭州仁和人。据性易本人所作《有谯别绪自剡分宗》载,戴氏先祖居山阴会稽(今浙江绍兴),乃东晋名士戴逵(字安道)之后。戴逵,《晋书·隐逸传》谓其“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2]2457,《世说新语·方正》篇更有王徽之雪夜访戴的经典故事。性易对这一家世十分感怀,其于自述文字《有谯别绪自剡分宗》中,特别提到了戴逵历经五胡乱华、江左东兴,自谯郡迁居会稽后,门庭优美,传衍不息,“世仰高风,时称郯溪曰‘戴溪’”,自此“江南无二戴”。显然,其中饱含历经女真入关,明室颓败的伤时之感,也体现出作为戴氏后人,对魏晋先祖的追念,两重情愫之中,自然与出身闽地的“黄檗三笔”不同,对两晋书风有更深切的体认和追崇,也就并不奇怪了。
性易的高祖戴彰、曾祖戴文奎、祖父戴德清乃至其父均继承了先祖淡泊清雅之风,“依隐玩世,弢光善晦,争高避世之墙”[3]143-144,坚守耕读凤栖之志。性易本人,史料也称其“不欲以儒术显,乃潜究《素问》《难经》诸书,悬壶濮里”,似乎同样表现出避世隐居,医术见闻乡里的家世传统。不过,与父祖不同的是,性易不仅“天资颖悟,过目成诵,幼肄举子之业,早登黉舍”(东条琴台《戴曼公》)[3]596,也曾用力科举,只是不喜八股时文。因此,性易与先祖辈并不完全相同,仍不失淑世襟怀。明治初期日本儒者东条琴台(1795—1878)称“其学术主于洛闽,文章经艺,固不让朱舜水”(转引自徐兴庆《自序》)[3]6。可见他对宋明理学至少还是用过心的,从性易本人的文章看,他未必主于程朱,而更认同当时显学的阳明之学。其《正心说》一文,开首即言“心者,身之主也”[3]118,此正是王守仁所言之“身之主宰便是心”[4]12,强调本心的生命灵觉对天理落实于人的决定性,生命情感的真相,不是一套知识系统和抽象观念的教条,一切理论,最终必须内化为本心良知的领受,才是真知真行,性易《正心说》又言:“天下国家,不出一心之有地也。”[3]118性易的哲学思想,并不为程朱所限,而是既承认天理的预设,又重视本心良知对天理实现的决定性,可谓程朱和陆王的折中之学。赴日之初,性易即与日本儒学界多有往来,“细析性理之精微”(安东省庵《与独立》)[3]170,不过,与彼时日本儒学普遍重视程朱不同,性易显然更为强调心之主体的作用,这既与晚明以来浙东学风有关,也与其家世近于道禅有关。
同为浙东士人,性易受到晚明学风影响,还体现在其与此时同乡朱舜水的关系。明亡之初,还是戴笠的他,曾参与反清复明,东奔西走,并与朱舜水多有交往。但是彼时国内抗清运动全面受挫,戴笠对时局深感失望,一个多月后,即东渡日本。赴日后,戴、朱二人仍有书信往来,但由于心境思想不同,已渐行渐远。朱舜水东渡主要意在乞师复明,终身不渝,且素不喜释道,曾劝阻戴笠出家,而戴氏虽然在诗作中也不时表达黍离之悲,但其东渡扶桑,侍奉黄檗隐元,并随后剃度,则体现出其冷淡心境。可见,戴笠与“黄檗三笔”的僧人不同,其对儒学的基本价值仍有长期的认同,年近耳顺方出家,既是受家世基因中的隐逸超越之气的影响,也是对于时局悲观绝望的心境写照。不过在隐元周围的闽籍禅僧看来,落发后的性易,仍称不上真正的出家人,其精神气质也与之不同,这或许也是二者不相容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之性易书法理论和创作路向,都与“黄檗三笔”不同,这也造成了其被排除在黄檗书法脉络之外。
二、独立性易的书学理论
明末清兴,在很多当时的士大夫看来,这也是一场传统文化的命运转折,如何保存自身文化精神传统,是深处其中的士人,特别是遗民的自觉选择,从这方面说,这些士人群体的文化活动、艺术创作,就不仅仅是个体聊以自慰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此意义上,黄檗禅僧的东渡和文化交流,也可视为一场文化的迁徙和保存。隐元作为这一文化活动的组织上和精神上的领袖,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宗教的意义。隐元周围聚集了各方人才,而就理论自觉程度和涉及领域广度而言,其中独立禅师都可称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精通诗文、书画、篆刻、医药等,特别在种痘治疗方面,影响深广,把当时中国的种痘技术带给了日本,而且在书法、绘画、文字学等理论研究领域,也有一定建树,对于明清之际的书画艺术史也有自己的判断。
性易的书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其所著《书论》一书中。全书分六章,包括《自叙》《斯文大本》《六义原本》《书法原本》《自跋》与《再跋》等,内容涉及书法起源、书法史、书道精神、技法理论、风格评论以及具体书写要诀等。其作可谓体系完整严密,论述细致周到,是明清之际乃至传统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可惜一般的书法史、书法理论史,均未见论及。
首先,性易和传统书学理论一样,认为书法起源于文字对外在世界的描绘记录,以及随后的文明时期的书写要求的发展进步,其《书论·自叙》云:
字繇一画之始,文成六义之中。一画具而万象出,六义析而变化通。则字者,文之本、理之源、心之声、言之用、义之至也。
汉语文字不仅是对外在世界景象的描绘记录,更是对其中隐含的价值秩序的表达,因而文字书法承载着人对天理的认知,不能仅以小道技巧视之。这既有传统书学的传统精神,也有性易理学、心学思想的底色。更重要的是,这一观点是有所指的,意在批评当时书家“不溯其源、考起本,争向杪杪梢头,摛文掇锦”以为好学能文[3]94,强调书法文字之学,应该是对天道人心的表现,这是书法艺术的灵魂根本。可见,性易不是一般的书家,更具有理论的自觉。在他看来,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承载的是文字形态之上的中华文化根本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精神显然不是禅家的顿悟自性所能涵盖的。书法要传达的不能仅仅是自性了悟之后的主体张狂,而是天道与人心的统一。性易《偶说》一文曰:
天心之合于人心也,密矣。高明之天,虚灵之心,大还之理,可不顺受其正而自弊其天心之无间乎。
禅宗强调心一起念即是发恼,万法之相,莫不因心而起,但性易认为人心之上还有一个天心,“人心之自邪,天心之自正”[3]113,这无疑是对晚明王学左派及狂禅以自心代天心的纠偏。书史上,明末书家多倾向于表达独立的审美追求,表现感性生命、自我个性的尚奇风气甚浓[5]190-205,与性易同时的著名书家,如王铎(1592—1652)、傅山(1607—1684),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铎在《赠汤若望诗册》中云:“书时二稚子戏于前,叽啼声乱,遂落数字,亦可噱也。书画之事,须于深山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安可得耶?”[6]437虽然王铎强调崇尚自由洒落的书法艺术,并非童稚般狂叫妄为,而是深得自然之韵的艺术心灵之外显,但追求童真的书写情态,确实是尚奇书家的自觉追求。傅山亦言:“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鄙陋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7]458尚奇书家正是从学童书写中获得启发,反对过分成熟乖滑的书风,而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著名书学主张(《作字示儿孙》)[8]3。而性易则重提晚唐柳公权的“心正笔正”之说:“得法者,一心御笔,醇正无疵,少有惰心,病随笔见”(《书法原本》)[3]107。
因此,性易书学一方面认可书之为道,“用之挥洒,托之性情,聊自寄以遣兴”(《自跋》)[3]109;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法的重要性,“今人咸好书法,不知书有道在,不求于法,何以尽藏锋善学哉”(《书法原本》)[3]107,认为学书应当严格地从字学开始,从许慎《说文解字》,旁通《字汇》《韵会》,明六书,然后再广泛学习历代篆、隶、真、行草,种种书家名帖,手摹心仿,那些所谓独处手眼、无所依傍的作品,乃“草率乱书,不知自丑”,“岂堪云书、岂堪云法哉”。性易特别指出书法当以秦汉、晋唐为上,面对明代以宋元为尚的书风,其《书论·六义原本》提出批评:
篆隶非秦汉不可法,真草非晋唐不足以学。今并失其所法、所学之原,可无慨哉。其宋元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揭(傒斯)、赵(孟頫)诸君子,明世祝希哲(枝山)、王雅宜(宠)、邢子愿(侗),虽曰席上之珍,风貌藐矣。况今日之董(其昌)、文(文征明),尤不足以誇前[3]103。
在性易看来,宋元明书家,均无法与汉唐书家,特别是二王、智永、颜真卿、怀素、张旭相提并论。实际上性易的这一书学主张,正应和了明末清初开始的由尊崇宋元尚意向晋唐重法的书法转变思潮,这也是其所处地域文化和自身家世渊源的结果。同时,这一书学主张,与黄檗禅僧为主的尚意、怪奇书风,大异其趣。禅僧书法,历来主张大开大合的狮吼用墨,表达黄檗棒喝门风之下,自性顿悟的机锋,而性易则更强调书法渊源和技法的严谨。
三、独立性易的书法与中日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派出大批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当时的文化,其深广程度,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宋元明以后,中日之间更多的是开展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渐趋平淡,以至于此后相当长时间里,日本文化都保持着唐代文化的样态。至于宋末元初,也就是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年),受到蒙元入主中原的影响,南宋部分禅僧、士人东渡,临济、曹洞各派以及程朱理学文化相继传入日本,形成一次高潮。此后到了室町时代(1338—1573年)后期到江户时代(1603—1868年),亦即中国明朝后期至清前期,随着日本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中日两国贸易的中断,文化交流反倒开始繁盛开来,其中包括朱熹理学、阳明心学先后在日本达到鼎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隐元东渡为中心的闽浙禅僧所展开的文化交流,带去了宋元以来的文人生活方式、艺术旨趣。频繁的交流,最终形成了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文化最为繁华的一段时期。
隐元、木庵、即非等“黄檗三笔”的书画艺术,是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艺术的典型代表,他们崇尚宋元风格,具有明显的文人书法尚意特征[9],意境风格大体以宋元苏轼、黄庭坚、赵孟頫等文人书法、文人画为圭臬,又重视明代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南派宗师。例木庵小字行楷秀逸纵容,都颇具董其昌的优雅流畅,如隐元、木庵的大字草书舒展俊朗,则近于苏黄。“黄檗三笔”的文人艺术特性,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书画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日本学者对宋元文人书画艺术的浓烈兴趣。与此不同,性易的书法,受其复古重法的书学观念影响,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晋唐之风。
性易赴日之前,熟谙篆书、隶书、楷书和行书,楷书直取魏晋六朝的钟繇、智永以及唐初虞世南之法,气韵端庄秀美,结构严谨平实,运笔简易不张扬,同时又具有隶书的蝉头燕尾痕迹,多用枯淡墨法,在晋唐风格之中更添古拙自然之气,完全不同于宋人楷法的飘逸奔放。性易的小楷,特别受到楷书钟繇楷书的影响,楷书的自如秀美中透露着隶书的古朴典重。例如独立性易《西湖志题词》,其中的字体结构和运笔特征,均明显有继承钟繇《力命表》的书法风格之处。
性易的小楷,与明中期“吴门书派”之一的王宠书风,十分接近。王宠(1494—1533),初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精于楷书、草书,尤其以小楷见长,具有俊逸儒雅的气息,时人评之曰:“衡山(文征明)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10]183王宠的小楷同样出于钟繇、二王、智永以及虞世南等晋唐诸名家,具有高古典雅、拙巧并见,结构扁宽,隐含隶意,体现出质朴圆润之感。而从性易现存的小楷作品来开,其书风与王宠的代表性小楷作品,如《竹林七贤》等,更为接近,或许性易确实是从学习王宠楷法,而上溯晋唐的,只是资料缺乏,尚待考实。日本儒者东条琴台评之曰:“曼公书法,出于长州王宠履吉,正锋逼古。”不过,就二人的草法而言,则王宠近于王羲之而有明人古拙尚奇的个性,而性易则是学习晋唐二王、怀素而保持其圆润流畅之秀美。关于这一点,只需对比王宠《千字文》与独立性易《致吉川广正离别诗》、怀素《论书帖》即可见出,后二者与前者书风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
性易书法,相较王宠,更保持着晋唐书法的谨严之法,较少明清之际的创新个性和同时期禅僧书法的文人狂放意趣。东渡后,“传之于北岛雪山及高天漪。雪山传之于细井广泽,天漪传之男颐斋,颐斋传之于泽田东江。而后广泽、东江虽有异论,至其执管五法、把笔三腕、拨镫等说,皆渊源于曼公之所接受”[3]597。正如学者指出,日本书法史上,同样是“唐样书法”,不同的师承渊源,“都是可以以此标明是另立门户的,其间并不会太多混淆”[11]407。虽然性易书法与“黄檗三笔”同出黄檗派,但其师承渊源既不同,经日本几代书家的传布之后,便逐渐分流,自成一派,特别是到了泽田东江(1732—1796)一代,性易所推重的晋唐书法理论和书风精神,形成了更为自觉的理论表述和书法实践,最终发展出“东江流”一派的日本江户书道流派。其门人桥圭橘曾编录东江有关书法评论语录,成《东江先生书话》一书,并在书跋中总结:
东江先生居恒有谓,凡学书,不据魏晋者妄矣。唐人祖述为家,宋已后以其意耳,弗取也。……而吾东方有晋唐书法,实从先生始。[12]
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深远持久,尽管自镰仓时代(1192—1333年)以后,日本思想文化就日益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但是在生活和艺术领域,唐代文化艺术的影响仍随处可见。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祖述唐人不失为一种文化坚守,而其根源,恰是同出黄檗派的独立性易的独特人生及其书学追求,其中所揭示的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影响的持续性,仍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学术命题。
注释:
① 例如解小青:《明末黄檗禅僧与日本书法——以黄檗三笔隐元、木庵、即非为中心》,《中国书法》2011年第9期,第63-66页;马旭明:《黄檗派高僧隐元书法及其用印》,《中国书法》2018年第10期,第126-128页。
② 一说字子辰,号曼公,清初文献,如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四十七《隐逸·戴笠》、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四《书家传·戴笠》,以及独立圆寂六年后成书的《桐乡县志》卷四均作“字曼公”。更重要的是,性易本人所作《由绪书》亦称:“贱名笠,字曼公,别号荷鉏,志为农也。”可见当以“曼公”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