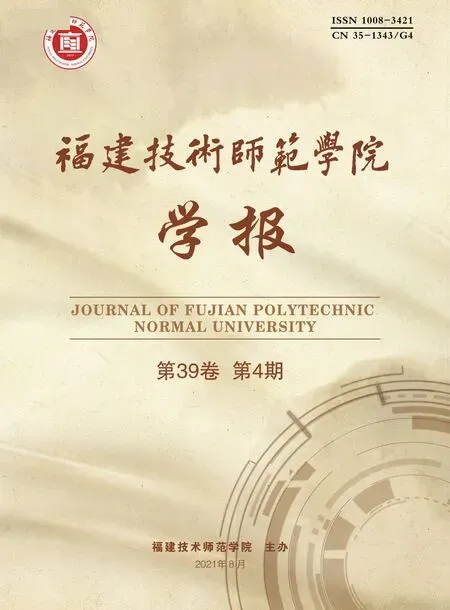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全球化理论的多维解读
陈旺,陈文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当前,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国内经济渐趋复苏,但世界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全球经济未见向好,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方面也给出了“疫情将常态化”的判断。有说法称,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范围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或可将其称作“后疫情时代”。在这个“后疫情时代”中,特别是伴随着疫情的强烈冲击、西方右翼政党的强势干涉、意识形态偏见等多种因素影响,使得排外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极端主义等全球化进程中的负面思潮在国际社会暗流涌动。而近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种种行径的背后逻辑,透露出“新冷战”思维,其甚至大有“逆全球化”的趋势。因此,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重谈全球化及其理论思想,既有利于破除“逆全球化”思潮拥护者的荒谬叙事,也有益于粉碎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全球化理论的逻辑理路,这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学说及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语境:“全球化”概念及其理论的出场
近年来,“全球化”一词在国内业已是一个见诸于报刊、家喻户晓的大众词汇。且从学界来看,“全球化”亦是一个学术热词。要将全球化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进行具体讨论,首先要对“全球化”概念及其理论的出场过程作出一定的梳理。
从“全球化”概念的出场来看,“全球化”概念对应的英文译词是“globalization”——一个具有名词属性的组合词汇,其是由动词“globalise”演化而来的名词形式,从语源上看,最早可追溯至拉丁文。而“globalise”又可拆解为连续词缀“al-”和“se-”及词根“glob”,其中词根“glob”源于拉丁文的构词元素“glob-”。由“glob-”派生而出的如“globus”“globo”“globi”“global” 等词汇,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如“球体”“球状”“球”“全世界的”等语义。尽管前述“global”等词汇在西方语境中的历史可长跨400多年,但真正具有“全球化”语义的,如“globalization”“globalize”“golbalizing”等词汇,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还未出现在西方论著中。据考据,1959年4月4日出版的英国杂志《Economist》首次应用了“globalise”一词,1961年版的We-bater字典或是首个将“globalism”和“globalization”收入在内的字典[1]。但值得强调的是,一个词汇通常出现一段时间被社会认可后才会进入字典。因此,如若仅从“全球化”概念本身的出场时间来看,大致可得出国际学界对“全球化”概念及其理论的讨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
从全球化理论的出场来看,根据学界一般讨论的结果,通常认为全球化理论最早出场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西方学界之语境中,流行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降的“后冷战时代”。从“全球化”概念在彼时学界的应用情况来看,其是一个学界、政界人士用于阐述“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概念范畴。如前所述,根据“globalization”一词被收录进字典的时间,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已有人公开讨论全球化有关问题。但就其热度而言,因受此时“冷战”、美苏两极对抗的影响,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并未进到国际学界的视野范围。也就是说,学界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比较迟的。但对其讨论却是来势如潮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被认为是对全球化理论的开源之作,特别是麦克卢汉在书中对“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的提出和界定,是对全球化的形象比喻;而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对“全球化”概念的初步界定,是将其引进学界的重要一着。再到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概念及其理论叙事才作为一个新时期的理论范式为学界所普遍接纳。
而国内学界对全球化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国际学界。文章以“计量可视化”作为分析工具,在CNKI数据库中以“全球化”为主题关键词进行全网文献跨库检索,CNKI数据库内可供参阅的有关全球化主题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1984年。因此,基本可得出国内学界对全球化理论的讨论之时间起始,与学界普遍认可的全球化理论由国内学者从西方引进国内的时间大致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说法基本相符。但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环境和政策的相对转向,为适应全球化趋势下的全球市场,国内学界对全球化相关理论的研究可谓是满腔热忱,仅在CNKI内以“全球化”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的文献总数多达145606篇。但不论是国内学界还是国外学界,特别是在经济学派的主流研究中,在全球化理论的出场探源上,都将其归结为是一门出自西方语境的理论研究。尽管,近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学者,从文本研究和思想研究的视维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想作出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就其影响力而言,还远未能及其前者,并广受质疑。
二、质疑与回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是否存在全球化思想的问题
如前所述,国内外主流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化理论是出自西方语境的一项研究成果。目前在学界中有两类颇为流行的全球化理论,一类是西方左翼的,另一类是新自由主义的。尽管从这些流行的全球化理论的逻辑理路来看,其理论观点都有所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都具有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某些西方主流学派,基本都持有“全球化=西化=美国化/欧洲化”范式的观点立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全球化思想的出场时间,远早于现代西方主流学派对全球化理论的讨论时间,且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如毕希纳奖获得者、德国大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就曾明确言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大概可算作对一个在当代世界上造成大劫难的过程,即不可抗拒的全球化压力的最简洁也最具震撼性的描述”[2]。也有学者开始尝试提炼归纳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化思想的组成元素,如陈光泉认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思想可概括为:“一、生产力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二、落后国家必须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三、世界将全面整合为城市—乡村(中心—外围)的结构;四、全球化造成了各种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五、全世界无产者将会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国家,整个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3]但是,从当前国际学界在全球化理论领域的研究热点来看,似乎并未有多少学者提及或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从国内来看,尽管鲜有学者会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但对其整理还远不能说得上系统和完整。
国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是否存在全球化思想”的问题持否定态度者,大多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论著中未曾出现过“全球化”等字眼为其质疑的主要依据,并认为全球化是近来才出现的现象。另一部分学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或对全球化的研究有所涉猎,但同时,他们亦认为当今时代已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因此,在今天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已无意义。从上述二类意见的逻辑基点来看,似乎很是站得住脚跟,但须知一个论断是否为真理并非是单由逻辑的严密性来决定的。文章姑且将上述两种观点归结为“不存在论”和“过时论”或“破产论”并予以回应。
对于第一种“不存在论”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论著中未曾出现过‘全球化’的字眼”的观点,仅从“全球化”概念的出场时间来看,这一观点似乎并无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确实也无“全球化”这一词汇。但是,要认定某个理论体系是否存在全球化思想,似乎并不应由该理论体系是否提及“全球化”一词来决定。对这一说法,只需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段话,便可对其不攻而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404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文本中,虽无直接提及带有“全球化”字眼的理论观点,但他们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判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以及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趋于全球化的演变趋势。就其逻辑进路而言,前述所及的马克思恩格斯之言断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
至于“全球化是近来才有的现象”的说法,戴维·赫尔徳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提出:“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在广义上可以追源到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进而提出了全球化“四阶段”的划分法,即“前现代、现代早期(1500—1850年)、现代(1850—1945年)以及当代(1945年以来)四个阶段”[5]。对此,全球化理论研究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也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历史阶段划分的观点,从这些观点来看,尽管前述学者对全球化的历史阶段界分之区间和依据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大多都认为全球化并非是新近才有的现象。
对于第二种“过时论”又或是“破产论”的观点,要承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并非全知全能的“预言家”,但需知马克思主义给予后人的决非某种对标入座的教义,而是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仅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确是无法“预言”到21世纪全球化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自然也不能无视当代全球化进程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时代的全球化进程的极大差异性。但如所谓“现在的全球化已非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全球化,因而再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的全球化思想已无意义”等言断中,以当代作为尺度来衡量过去的方法尺度是不科学的。正如20世纪以前,由于运输技术和跨国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运输成本的消减、贸易壁垒的减少,进而引发的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家为避免本国经济受创纷纷树起贸易壁垒,21世纪的前20年的全球化的进程轨迹不正是对20世纪以前的历史图景的“复刻”和“重现”吗?因此,笔者完全有理由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从狭义上的全球化的维度来看,是全球化进程运动轨迹的“起点”,其广度、深度及影响的范围等自然不能同当代的全球化进程相提并论。但是,全球化现象发生的原理及其运动轨迹,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的讨论范畴之内。因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展开系统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且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区别于当代全球化理论的地方不仅在于其终极指称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化思想的终极指称在于“人的解放”),而且还在于他们更注重原理分析。因此,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归结为全球化理论的“原理学”。
三、重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全球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未曾使用过“全球化”这样时髦的词汇,但其思想宝库存在全球化思想的论断已是不容置疑。虽无直接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全球化现象时,多使用的是与“狭窄的”“民族的”“地方性的”相对立的如“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世界市场”“全球的”等具有“全球化”内涵的词汇,并以此来体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下的世界历史的新变化、新趋势——即全球化的趋势。文章拟在该部分,重新解构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并在生产力、生产方式、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运动等四个不同维度上对其全球化思想进行重新建构。但又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巨大张力,两两之间关系紧密。因此,文章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置于同一维度进行讨论。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维度
用适当的抽象来讨论现实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区别于过往旧哲学家们的最大不同。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诸多现实问题时,往往是将其落脚点置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范畴之上来进行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现象的观察和讨论始于对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揭示。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全球化现象研究的着力点和出发点。而在生产方式中又有着一对重要的对子,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从生产力的维度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生产力运动是全球化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生产力运动及其引发效应的具体过程来说,生产力运动首先引发的是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扩大,随之带动的是各民族和各地区间的普遍交往,而交往的普遍深入直接带来的是贸易的普遍繁荣,世界市场和为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生存的各国大工业体系及其承载者也在这一图式下最终形成。这一运动图式刻画的也正是全球化进程的光景。由此,就不难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制度的革新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确立同样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伴随资本主义共同出现的是具有强烈扩张性的资本。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6]714可推之,马克思在那时就已察觉到资本的扩张本性及其诱发全球化的逻辑演绎。
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极大区别于过往的原始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是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同过去以追求“直接使用价值”的原始生产不同的是,前者追求的是更多的剩余价值。且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逐,因此,这种生产存在“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和“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6]714的趋势。不仅如此,资本还表现出了对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要求,马克思将其归结为三点:“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6]714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特别在生产和消费的两极张力中,一定意义上催动了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向全球范围扩大的趋势。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彩的生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生产效率的极大飞跃,这使得过去需要使用1个单位的生产力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变得仅需0.5个单位,这直接造成0.5个单位的生产力和相应的劳动力不得不从旧的生产部门中分离。资本力量就建立起专门为这0.5个单位的剩余生产力和剩余劳动力而存在的新的生产部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运动在这一过程也得到了生动演绎,因为新的生产部门呼唤新的消费,而新的消费也在促进新的生产。如此反复不断。但是,一个民族的市场始终是有限度的,当这个市场不再能满足资本的本性时,资本就会“突破”这一界限,寻求更大的市场——即世界市场。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在资本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二)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维度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指代全球化现象的重要概念范畴。从世界历史理论提出的逻辑来看,它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概念范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过去的历史观——唯心史观进行清算、颠倒,从而实现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的研究,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研究,探究其逻辑演绎可以发现,二者对全球化的研究开始于对世界历史形成的描绘,而终结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希冀。
从世界历史的维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世界历史”所指的并非现在语境中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世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更趋于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向的一种哲学概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诸多原著中首次系统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文本,在文本中他们如是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184而对于“世界历史”,即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问题,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本中有所分析外,《共产党宣言》是较早地正面作出回应的文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执行者,由于受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本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的驱动,驱使他们“奔走于全球各地”,因而资产阶级“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404。世界历史便是在这种联系中逐渐形成的,置换到当代语境中,全球化进程亦是这样开始的。总结前述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至少包含三层内涵:第一,世界历史是指人类总体史的过程;第二,世界历史是指十八九世纪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间普遍交往、互相影响,且世界逐渐进入一体化状态的历史过程;第三,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共产主义运动且共产主义的历史过程。因此,在世界历史的维度上,或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视为其全球化思想的生动外显。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的终极指涉在于共产主义运动及其运动结果——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区别于现代的、西方的全球化理论的最大不同。
从共产主义运动的维度来看,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全球化思想的终极指称,他们认为进行式中的全球化为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终结、共产运动的开始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前置条件。关于全球化是如何对共产主义运动起作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详细论述:“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16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在全球化的构图中,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4]166,对于这样孤立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断然是无法忍受的,因而他们提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动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4]166,而这恰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为基本前提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共产主义是全球化视野下的共产主义。
综上,从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维度来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想同其他流派的现代理论思想存在何种不同。其中最大不同也许就在于“境界”的不同。诚然,不能否定的是专门从事全球化理论研究的现代学术大家,他们对全球化现象描述的细致程度已远超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源于他们对全球化理论研究的专精,也源于21世纪现代化进程的新变化。然而现这些学术大家对全球化的研究却仅局限于现象的描述或是基于描述的对策提出,始终脱离不开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图式。而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时空对他们的指责也正在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的研究开始于对资本原罪的批判,而在他们对全球化现象描述背后“藏匿”的正是共产主义。
四、余论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者对其或是忽视或是质疑。文章分别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世界历史、共产主义运动等不同维度中重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这不仅是对这些忽视和质疑的回应,亦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需求。
同时,笔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文本中寻觅二人关于全球化思想的论述,其主要目的是想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全球化理论。而这种重新建构的目的却不仅限于此。在新时代,我们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全球化理论告诉我们:全球化不可逆。尽管从1999年反全球化标志事件“西雅图风暴”①到以美国政府肆意挑起贸易争端、“任性退群”等为代表的反全球化事件,无不在提醒我们“逆全球化”思潮始终与全球化进程相伴而行。甚者有部分学者提出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逆全球化趋势的主流之中。
不可置否的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化在为世界经济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对全球化提出反对声音,甚至有不少国家将本国经济的衰弱不振简单归结于全球化,致使“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总体来看,“全球化大潮不可挡,融合大趋势未变”[7]。因为资本为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未曾改变,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主导的全球化,到现如今仍是由其主导的“逆全球化”,归根到底都是为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逆全球化”仅是资产阶级为应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一种暂时性政策。在这种悖论的背后,实则体现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周期,而资本的本性在这当中未曾改变。
所以,在一段时期“逆全球化”浪潮后,必然迎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在这种大趋势中,不能忘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告诫: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存在,以普遍交往为前提,如此其才有可能成为经验上的事实。换言之,即只有全球化,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要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中充分把握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
注释:
① 1999年11月30日于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全球谈判无疾而终,原因在于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反全球化者举行大规模游行,甚至喊出‘关闭世贸组织’的口号,这场大规模游行活动被称之为“西雅图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