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尔历史剧《崇祯》:17世纪欧洲天主教视野下的明清鼎革
施晔 李亦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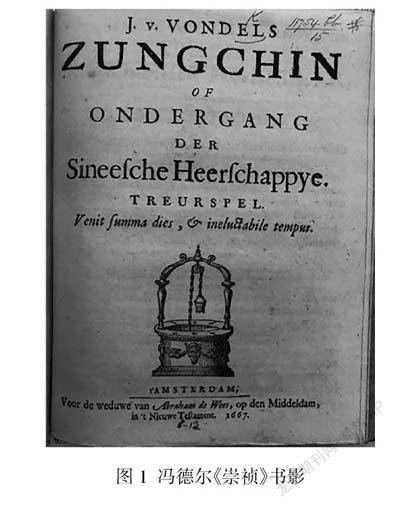
摘 要: 《崇祯》是17世纪荷兰伟大诗人及剧作家冯德尔唯一取材于中国的戏剧,因真实且及时地反映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破家亡国悲剧而被称为欧洲第一部“中国风”文学作品。但由于资料匮乏、语言壁垒等原因,国内学界迄今鲜有学者关注到此人、此剧。细读剧本,结合冯德尔的人际交往及宗教信仰,不难发现卫匡国《鞑靼战纪》及东印度公司涉华报告是其主要素材来源。冯氏以古典主义悲剧的创作手法想象与演绎崇祯之死和明朝覆灭,尽管带有浓重的天主教神学观,却形象地彰显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及这部戏剧在荷兰产生的时代必然性。
关键词: 冯德尔;崇祯;明清鼎革;天主教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6-0060-(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6.007
崇祯十七年(1644),由于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白热化,李自成义军攻陷北京,清人入关继而占领中原,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明政权轰然倒下。同时代的欧洲旁观者,也以各种文体记载着发生在遥远东方的这一声势浩大的政治事件。17世纪荷兰著名诗人及剧作家冯德尔的五幕剧《崇祯》便是其中之翘楚。1 然而,该剧一直未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足够关注,语言障碍使国内学界知之者甚少;西方学者则着眼于冯德尔著名诗人及剧作家的身份,更倾向于对其生平、宗教信仰及文学成就做综合性研究,2 对《崇祯》一剧的检讨便被湮没其间,偶尔还夹杂在对17—18世纪荷兰戏剧或鞑靼征服汉人书写的论述中。3 本文拟另辟蹊径,从时代背景、素材来源、宗教情怀等角度为该剧做一专论。
一、冯德尔及其历史剧《崇祯》述略
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出生于科隆一商人家庭,幼年随父母迁居阿姆斯特丹。1608年接替亡父经营袜店,与此同时开始学习拉丁语,投身于诗歌创作,加入了阿姆斯特丹文學会,成为“白色薰衣草”组织的成员,1 并与罗默·维斯切(Roemer P. Visscher,1547—1620)等文学界精英交游。冯德尔一生创作颇丰,被公认为17世纪荷兰共和国最伟大的诗人及剧作家。作为诗人,其叙事诗《施洗者约翰之一生》(Joannes de Boetgezant,1662)被誉为荷兰最伟大的史诗。作为剧作家,他一生创作及翻译剧本32部,第一部《逾越节》(Het Pascha,ofte de Verlossinge Isra?ls uyt Egypten)1612年上演,再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脱埃及奴役的历史。他的《吉士布雷特·范·阿姆斯特尔》(Gijsbrecht van Aemstel,1637)一剧写成后,每年新年在荷兰上演,从1638年一直持续到1968年。因此,19世纪英国作家乔治·巴罗(George Henry Borrow,1803—1881)甚至称冯德尔为“迄今为止荷兰出现的最伟大的人”。2
图1 冯德尔《崇祯》书影
《崇祯》166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图1),是冯氏创作生涯中最后两部戏剧之一(另一部为《诺亚》)。此剧演绎了发生于1644年的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煤山自缢事件,被西方学界视为欧洲首部“中国风”(Chinoiserie)文学作品。3 其剧本全名“崇祯或明王朝的覆灭”,正文前有作家呈现给诺贝勒爵爷(Cornelis Nobelaer)的致辞、4 剧情概要(inhoudt)及人物表。全剧共五幕,铺陈了崇祯政权灭亡前夜发生于京城皇宫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主要戏剧人物有崇祯、都督(US)、阁老、皇后、太子、公主及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
此剧付梓时间距“甲申之变”仅23年,属典型的时事剧。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中国朝代鼎革对于荷兰受众来讲是极其新异之事,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东方异域还有这么一个古老帝国。为此,首次尝试使用中国题材的冯德尔,在第一幕中安排都督向汤若望讲述明王朝历史及其积重难返的政治、社会危机,并且道出了崇祯的心头大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及关外女真族的侵犯已严重威胁到王朝统治及国土安全。作为一个剧场经验丰富的作家,冯德尔十分注重剧情的布局,努力使情节紧凑严密而富于节奏。该戏剧从李自成兵临城下起始,引导观众尽快入戏,将战争漫长复杂的背景以对话的方式呈现,从而使观众初步了解这一战争的历史语境。在第二幕,甫一开场,叛匪已在猛烈攻城,心急如焚的崇祯开始怀疑皇城是否真如阁老、都督所说的固若金汤,他已不再信任朝中大臣及宫中太监,计划连夜出逃南京,但遭到阁老的竭力反对。为了进一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第三幕情节紧凑,环环相扣:皇后召见汤若望禳解凶兆;崇祯与太子辨奸,共读匿名警告信;都督主张谈判,以财宝及皇位换取李自成退兵;崇祯否决都督之计,派太子出宫打探敌情,了解京城现状。这一悲剧的高潮被安排在血雨腥风的第四幕:崇祯出逃受阻,随后父子诀别,血书遗诏,剑斫公主,自缢殉国,所有史书中记载的真实事件接踵而至,令读者触目惊心,魂飞魄荡。在皇宫惊心动魄的生离死别之后,冯氏有意放缓第五幕的节奏,以追述的方式交代帝、后、公主之死,都督奉旨将崇祯血书交给甫登皇位的李自成,而李忌惮重兵在握的辽东总兵吴三桂,令都督下书劝诱其子率部投诚。全剧最后以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幽魂的形式交代自成败亡、清兵入关、诛杀崇祯三子等史实,并预言基督教在鞑靼新王朝的命运。其剧前的剧情概要、演说式台词和充满宗教色彩的剧诗,使《崇祯》具有古罗马剧作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式“书斋剧”的特质,似更适合案头阅读而非剧场表演。
西方古典戏剧孕育自古希腊罗马史诗及悲剧,冯德尔在戏剧创作上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和悲剧之父塞涅卡为师。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s)以生动的情节、凝练的语言及哀伤的情绪书写罗马帝国历史,被冯氏奉为经典,《崇祯》标题页上因此醒目地题写了维吉尔的著名诗句:“大限将至,厄运难逃。”(Venit summa dies, & ineluctabile tempus.)1 而塞涅卡的《特洛伊女人》(Troades),则被冯氏直接模仿创作了《耶路撒冷的毁灭》(Hierusalem verwoest,1620)。塞涅卡以特洛伊城的陷落表现尘世伟迹或人间英雄的短暂易逝,冯德尔则以耶路撒冷的毁灭呈现上帝对人类恶行的惩罚。以帝国兴亡、城邦毁灭等宏大题材昭示上帝“神意”,是冯德尔最为青睐的戏剧主题,其《崇祯》也不例外。在冯德尔看来,除了特洛伊城的失陷,没有什么事件能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革命相提并论。然而,冯德尔既没细写大明与李自成或鞑靼间的战争,亦未描绘京城陷落、百姓流离的惨状,却将目光聚焦于沦陷前夜的皇宫,以丝丝入扣的剧情展现崇祯所遭遇的家破、人亡、国灭的巨大灾难,同时把改朝换代的许多其他事件以追述或穿插的方式展现。其布局巧妙,结构简约,矛盾冲突高度集中,充分体现出古典主义悲剧的艺术特征。
具体来讲,《崇祯》在主题、语言、结构、人物塑造各方面均汲取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养分。在戏剧主题上,冯德尔承继了古希腊罗马悲剧反映人与神、人与命运关系的宏大命题,采用崇祯灭亡、若望传教的双线结构,以异教徒王权的兴衰更迭来弘扬主宰世界的上帝至高无上的伟力,具有极强的宗教寓意。在戏剧语言上,《崇祯》中人物独白、对白和歌队合唱平分秋色,双行押韵、富于内涵的台词充分表现了人物个性及复杂心理,2唱词则交互押韵、典雅整饬,成为与前者交相辉映的剧诗。全剧每幕均终结于两组合唱剧诗,其中第二幕组诗除首节(strophe)、次节(antistrophe)外,还有末节(epode),第五幕大结局则由教士歌队及沙勿略幽魂的轮唱替代组诗。悲怆的合唱、忧郁的独白与极具末日悲悯的剧情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西方古典戏剧诗、剧合一,也即抒情、叙事合一的特点。在戏剧结构上,冯德尔严格遵循古典戏剧三一律准则,强调时间、地点及行动的整一性,将剧情压缩在崇祯自杀前一晚日落到次日日出前十余个小时内,将场景设置于皇宫外朝大殿,所有戏剧行动均服从于主要情节:崇祯及大明王朝的灭亡。剧本的结构方式及鬼魂、巫术等超自然情节皆显现出对塞涅卡《特洛伊女人》的模仿。在戏剧主人公崇祯形象的塑造上,冯德尔毫不隐晦其个性缺陷,在剧情简介的首句便评价崇祯说:“崇祯,中国大明最后一位皇帝,被无厌的贪婪所攫取,官员憎恨,子民厌恶,因而在国都北京受到匪首李自成出其不意的攻击时只得将皇位拱手让人。”3 此外,作家还以去留北京一事凸显崇祯优柔寡断的个性。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本有机会出逃南京,但臣僚、太监的一致反对和瞒报军情使其错失良机。当断未断,终受其乱。总之,《崇祯》与冯氏的《玛丽亚·斯圖亚特》(Maria Stuart,of Gemartelde Majesteit,1646)、《耶弗他》(Jeptha,1659)、《流亡的大卫王》(Koning David in Ballingschap,1660)等剧一样,是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生动诠释。各剧皆有高贵而并不完美的主角,由于性格缺陷或某些过失遭受不幸,从他们的痛苦、彷徨甚至死亡中,受众顿悟命运的无常及人生的虚无。“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 怜悯是由上帝弃民崇祯及其家人遭受的厄运而生发的共情;恐惧出于戏剧的移情作用,也即剧中人遭遇的无妄之灾会随时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同理心;而“陶冶”一词在亚氏原文中为katharsis,此为一宗教及医学术语,原义为“净化”,也即借助主人公的苦难涤荡情感中的不洁,从而使受众的心灵得到宣泄和净化。这便使《崇祯》具备了异乎寻常的悲剧力量。
二、《崇祯》素材来源考
那么,远在西欧低地小国的冯德尔如何能在明清易代战争发生不久,即以戏剧的形式演绎远东异国这一重大政治变革?他从何处得来相关素材?
事实上,在1667年《崇祯》付梓前不久,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1654)及《中国新图志》(1655)、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1617?—1672)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纪实》(1665)、汤若望的《历史故事:传教团在中国的开始与发展》(1665)、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国图志》(1667)等书相继在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等地出版。这些涉及明清史的著述皆有可能对冯德尔产生过影响,从而使《崇祯》全剧显现出对中国山川地理、历史朝代、天灾人祸各方面情况的熟稔。2
但从剧本的结构、行文及情节看,卫匡国的《鞑靼战纪》是《崇祯》的主要素材源。而此书在低地国家的首先面世,又不能不归功于17世纪上半叶崛起为远东海上贸易霸主的荷属东印度公司。
1651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日巴拉(Japara)劫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发现有一耶稣会士搭乘该船返欧,此人便是卫匡国。卫匡国为意大利籍传教士,崇祯十六年(1643)夏抵达澳门,后在浙、闽、粤等地传教。卫氏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战争,并于顺治七年(1650)春到达北京,同年被耶稣会中国传教团派赴罗马教廷陈述“中国礼仪之争”相关事宜,却在半途被劫获并逗留于巴达维亚荷兰人定居点近一年,从而成为东印度公司有关中国朝代鼎革最为直接可靠的消息源。卫匡国用对该公司极具商业价值的信息换取相应回报,1652年7月16日由荷兰人安排搭乘商船返欧。3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信息传递相当快捷,1652年12月,明清易代、鞑靼人已在中国建立稳固政权并准备开放广州为自由贸易港的简报已摆在该公司董事会面前。4十七绅士从中看到了与中国开展直接贸易的曙光,立即于1653年策划派遣访华使团与清政府接洽。这一中西交流史上著名的使团1654年7月从巴达维亚出发前往北京,5 公司董事会为使团配备了专职画家,而且明确指示两位大使侯叶尔(Pieter de Goyer)及凯塞尔(Jacob Keyzer)关注卫匡国的著述:
配属给你们的管事是一专业素描家,你们可以让他把沿途可能见到的所有城市、乡村、宫殿、河流、城堡和其他奇异的建筑物以它们本来的形象描绘下来。你们应当带上耶稣会士马丁尼所写的中国旅行记和所作的中国地图,它们可能在你们的行程中或其他情况下发挥作用。6
荷属东印度公司指派的素描家正是撰写《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纪实》的尼霍夫,由此可见,该公司董事会早在卫氏著述公开出版之前就掌握了其中的重要信息,并将其用作公司对华外交活动的指南。卫匡国最早给欧洲带去了明清鼎革的详细信息,而东印度公司实为此信息的传递者。正因为荷兰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强烈兴趣,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及《中国新图志》相继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出版,并迅速传播至欧洲各国。冯德尔、范·胡斯(Antonides van der Goes,1647—1684)、塞特尔(Elkanah Settle,1648—1724)等剧作家也才能取得可靠翔实的素材来叙写鞑靼人征服中国的故事。1
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后文简称《战纪》)2 以中国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也即西人所谓的“鞑靼”为主要书写对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两百余年间女真族鞑靼与明朝的关系,万历年间的辽东战事,以及天启、崇祯朝的政治社会危机;并较为客观地总结了导致明亡的三大要素:鞑靼辽东侵略战争,李自成等流民起义,以及宦官魏忠贤专权。除鞑靼征服中国这一主线外,《战纪》还铺设副线真实记录明末清初中国基督教发展简况及战乱中各地教堂、教士的遭遇。因此,《战纪》是欧洲关于中国明清易代历史的最早记载之一,“盖为欧洲第一部中国政治史也”。3 它不仅对西方学界,即便对中国明清史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补充,犹以作者亲历所记最为翔实,可补正史之阙略。并且,耶稣会士的身份使卫匡国能以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记录这一天翻地覆的革命,从而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故1666年率团访华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使节范·胡伦(Pieter van Hoorn,1619—1682)在其出使报告中专门“致敬卫匡国”,感谢其给公司传递的中国信息。他认为自己的访华经历完全印证了卫氏对中国翔实可靠的观察。4 而冯德尔正是借用《战纪》的相关记载营构起《崇祯》一剧,该剧的主题思想及时间、地点、角色、情节设置均受到了《战纪》的极大影响。
首先,《崇祯》与《战纪》具有相同的双重主题:帝国灭亡与福音传播。卫氏为双重主题设置了两条宏大主线,一是鞑靼征服中国史,一是1654年前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5 冯德尔的双线设计则更为具象,崇祯自缢、明朝覆灭是其一,耶稣会士在宫内致力传教是其二,前者比重无疑大于后者,应为全剧主线。正因为天主教主题的影响,卫、冯二人皆以相对超脱的叙事立场看待明清易代。作为一个耶稣会士,无论是朱明还是大清,在卫匡国眼中皆为上帝子民,而政权更替实为全能上帝的旨意。对于崇祯与顺治,卫氏亦以较为客观的态度评价他们。尽管崇祯善待汤若望等传教士,但《战纪》并不避讳对其政治弊端的诟病:“崇祯帝的贪婪也使暴乱大大加剧,他增加赋税,榨取百姓血汗。”6 与此相对,他对顺治的卓越见识、宽厚仁慈不乏赞赏:“中国人开始明白,鞑靼王不仅庇护他们,还以善意相待,于是许多大员为了避免受到中国皇帝凶暴之害,托庇于鞑靼卵翼之下。”7在卫匡国眼中,残忍而又笃信异教的皇帝最终将成为上帝的弃民,“当他们不顾基督的和平时,上帝就在中国发动激烈战争,同时允许这些鞑靼人扎根中国,乃至发展到消灭大明王室及国家”。8受卫匡国影响,冯德尔的《崇祯》同样选择这种立场,对崇祯国破家亡的悲剧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而剧中“钦保天学”的汤若望神父可谓这种心态的代言人,他超脱地对待皇后的种种忧虑恐惧,劝导她放弃迷信及对佛教的盲目崇拜,建议她“只敬畏能预示祸福的上帝”,9 并暗示崇祯是被上帝抛弃的以色列王扫罗(Saul)。10 这种无关痛痒的劝导泄露了传教士们的共识:明清易代是无可改变的上帝神意,他们无力回天,只能在竭力尽忠后作壁上观。
其次,《崇祯》根据《战纪》的记录安排戏剧的时间及地点。在《战纪》中,卫氏如此描写京城及皇宫的陷落:“流寇没有受到什么阻击,于1644年的某一天,太阳升起前,从一座打开的城门进入中国的京城,忠于皇上的人也未能长时抵抗。潜伏城内的贼兵制造混乱,没有人知道跟谁打仗。在这场大屠杀中,李自成趁乱胜利入城,直抵皇宫。”1 冯德尔根据这段文字将戏剧的时间限定在崇祯自杀前一晚日落到次日日出前十多个小时之内,地点设定于皇宫外朝大殿,然后按时间顺序次第展开京城陷落、崇祯自杀、招降三桂等重要情节。卫氏的“某一天”即《明史》所载都城沦陷的“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暝”,2 “乙巳,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3 又,“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4因此,《崇祯》的时间、地点设置基本符合史实。
再次,《崇祯》依据《战纪》设置戏剧人物。《崇祯》的十个角色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如崇祯、周皇后(Jasmine)、太子朱慈烺(Fungiang)、长平公主(Pao)、李自成、汤若望等。另外都督、阁老(Kolaus)、宫女(Xaianga)等亦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人物,耶稣会先驱沙勿略则以幽魂面目出现。
都督是贯穿全剧始终的重要角色,从第一幕简述明史到最后一幕呈献遗诏,他见证了悲剧始终,被作者塑造成一个深得崇祯信任的忠臣。从剧终李自成威逼利诱都督劝降其子吴三桂这一情节看,此角色应以吴三桂之父吴襄(?—1644)为原型。吴襄天启二年(1622)中武进士,沉浮官场二十余载,崇祯十六年被起用为正一品中军府都督,实为明廷挟制封疆大吏吴三桂的一枚棋子。李自成占领京城后,吴襄被迫下书劝降吴三桂,后吴三桂与多尔衮部击溃大顺军,吴襄被李自成斩首。冯德尔当然无从得知这位重臣的坎坷一生,他对吴襄形象的塑造,仅凭想象及卫匡国《战纪》中的两句话:“有个姓吴的贵人,其子吴三桂统率中国军队在辽东防御鞑靼人。暴君李自成用酷刑胁迫这个老人,要他用孝道之名叫他的儿子及其部属归降;还答应,如他用为父之权威(中国人认为这是神圣的)命其子投诚,那么可以授予父子重赏和高位。”5 卫氏所记基本符合史实,故《崇祯》中的都督并非凭空虚构的人物。此外,剧中还有两个角色“阁老”及宫女,应为《战纪》中忠于皇室的一众大臣、太监、宫女的合体。如剧中的“阁老”似为《战纪》提及的大元帅李阁老(Colaus Lius),也即东阁大学士李建泰(?—1649)。6 当《战纪》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载出现讹误时,冯德尔亦以讹传讹。如崇祯十六年任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李建泰确如《战纪》所云因保定城陷“害怕受辱而自尽”,7 但其“自刎不殊”,又被“大清召為内院大学士。未几,罢归。姜瓖反大同,建泰遥应之。兵败被擒,伏诛”。8 兵荒马乱之际,流言纷起、信息壅蔽,《战纪》里出现错讹亦情有可原。而正是受到“阁老自尽”说的影响,《崇祯》剧中的阁老效仿其主自缢于梅树。然而,《明史》记载,崇祯死时只有提督城守的太监“王承恩从死”。9 但若参照史书“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10 的记载,冯德尔的虚构亦不算离谱,毕竟当时以各种方式从死的明臣不在少数。
最后,《崇祯》基于《战纪》编撰情节。《崇祯》中的主要情节皆来自《战纪》,但《战纪》简练的记载经冯氏艺术加工后,被注入了充沛的情感及丰富的想象。如卫匡国仅以三句话记载崇祯去世前的行止:“据说,他被告知所有出路都被封锁,便留下一封血书,其中向后人悲痛诉说官员的不忠、背叛,声称他可怜的百姓是无辜的,祈求李自成,既然天授予王权,当替他向叛徒报仇。然后,他想起已届结婚年龄的女儿,落入恶人之手会受辱,就当场亲手用剑把她杀死。接著他走进一个果园,用袜带套在一株树上吊死。”1 而冯德尔将此三句话演绎成第四、五幕中的三个主干情节:血书遗诏、剑斫公主、袜带自缢。并且,他通过教士悲伤的合唱、宫女惊恐的回忆以及充斥着血与泪的恐怖氛围构建起悲剧的高潮:享国270余年的王朝毁于一旦,含苞待放的青春之花不幸凋谢。冯德尔以此凸现了社会、民族矛盾恶化所导致的人生最苦痛和残酷的一面,带给受众极大的震撼,从而让人感受到悲剧崇高及宏大的力量。而卫氏所记、冯氏所本的这三个情节,皆有史实依据,如“血书遗诏”见于《明史》之《本纪第二十四》:“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2 但某些细节,戏剧与史书有出入,崇祯血书并非写于纸上而是写于衣襟上,亦并未托人转交给李自成。另外,崇祯以袜带自缢于树亦不同于《明史》“以帛自缢于山亭”的记载。当然,这些细枝末节无妨历史的真实性及《崇祯》的悲剧性。
而《战纪》中提及的其余相关历史事件则被冯氏安排在首尾两幕。第一幕都督与汤若望的对话完全是《战纪》中明史的缩写。如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驱除鞑靼后于应天府称帝、万历四十七年(1619)清兵攻克铁岭后直抵京城、太监魏忠贤弄权被崇祯赐死、李自成及张献忠叛军壮大等《战纪》中提及的史实,均通过两人对白做了简述。而崇祯自缢后发生的史实则集中于第五幕。为呼应“都督+汤若望”的起始,冯德尔以“都督+沙勿略”作结,次第交代李自成逼迫都督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献关降清、大顺王朝崩塌、崇祯三子被杀、南明各小朝廷相继灭亡等史事。因此,《崇祯》完全依循《战纪》的记录展开戏剧冲突,是浓缩化、戏剧化的《战纪》。
然而,冯德尔尽管倚重《战纪》,但也并非亦步亦趋。比如我们在《崇祯》中找不到卫氏对鞑靼人的诸多赞美之辞,反而在致辞中出现“鞑靼凶徒”及“血腥入侵”等词语。这可能与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在多瑙河两岸屠城的原始恐怖记忆有关,因而冯德尔每每在戏剧中呈现出对鞑靼人的负面想象。除《崇祯》外,其《撒旦》(Lucifer,1654)和《玛丽亚·斯图亚特》中均有残暴的可汗形象。
三、上帝“神意”的显著在场
如果说卫匡国的传教士身份使《战纪》难免宗教内容的记述,那么《崇祯》浓重的天主教色彩又因何而起呢?这就必须对冯氏的宗教信仰做一简要回顾。
冯德尔幼年受洗,并于1606年成为新教沃特兰门诺团体(Waterland Mennonite Community)的一员,3 其早期诗歌充满了宗教激情,曾写下“爱战胜一切”的座右铭,意欲把生命呈献给上帝,用宗教之爱战胜一切邪恶。一直到17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皆以模仿基督、表现严肃的宗教及道德主题为主。1641年前后,冯氏改信天主教,在当地教徒中引发较大震动,因为当时共和国的主流宗教是新教加尔文宗,天主教、再洗礼派(Anabaptism)、阿米纽派(Arminianism)皆因被官方禁止4 而成为地下秘密教派。冯氏改变信仰之因无考,有人认为他在发妻亡故后与一位女天主教徒的恋爱或许起了关键作用。5 自此,冯德尔创作了诸多批评加尔文派的讽刺文学,且与长驻阿姆斯特丹的耶稣会士泰灵恩(Augustine van Teylingen)成为密友。6 信仰的改变使他开始关注天主教题材。
冯氏诗歌和戏剧创作有一贯用技巧,即创造一个极具象征性及时代性的形象,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开展宗教及道德教化。其《崇祯》亦不例外。他以传教士汤若望开启全剧,并将其作为剧本政治、宗教双重主题的汇合点着意塑造,又以沙勿略收结全剧,具现作者虔诚的宗教情怀,这种安排彰显了揄扬上帝“神意”的创作意图。
作为帝国毁灭的见证者和致力于传教“天职”的传教士,汤若望无疑具有独特的象征性及时代性。汤氏在华传教47年、历经明清两朝,甚受崇祯、顺治器重,并于顺治七年被委任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主掌钦天监的洋监正。这一身份使汤若望多有机会接触天潢贵胄及太监、宫女。他常利用入宫的机会举行弥撒,施行圣事,在各阶层中发展奉教者两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冯德尔与汤若望皆出生于科隆,可能相识。有学者基于对冯、汤二氏密切家族关系的研究,甚至认为《崇祯》是部颂扬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的宗教剧(missie-spel)。1本文认为,尽管该剧宗教色彩浓重,但崇祯王朝的灭亡仍是戏剧的主线。冯氏选择汤若望入剧,起因可能是后者恰于《崇祯》出版前一年离世,而其在华传教的坎坷经历和卓越功绩又给教徒们留下较深印象。冯德尔因而浓缩其毕生功业于一剧,对其颂扬有加。此外,汤氏是该剧宗教主题、上帝“神意”的主要呈现者,冯德尔将其塑造成剧中祈求天主护佑、宽慰落难皇族的重要角色,为自己的宗教思想代言。更重要的,汤氏这一角色是戏剧主、副双线的汇合点,因而也是剧情的有力推动者。冯德尔首先安排汤氏在戏剧起始以宫廷御用顾问的身份出场,通过他与都督的对话展现悲剧的历史大背景;在此后的第三、四幕中,汤氏连续出场,皇后视其为禳解凶兆、祈请上帝护佑的“最信任的顾问”,汤氏因而在宫内举行弥撒圣祭仪式,并以《圣经》中求神问卜、悖逆耶和华的以色列王扫罗的败亡故事劝导皇后不要将希望寄托于迷信与占星,要耐心等待上主的启示及自己的宿命。在某种意义上,汤若望这一角色是全能上帝及全知叙事视角的合体。当然,若从史实角度考量,汤若望作为皇家顾问在危难时刻进入后宫的情节设计明显违背历史真实,因为崇祯十七年时的汤若望仅是钦天监中的一名洋司历,根本无缘谒见皇后,这种安排显然是出于作者对汤若望及宗教主题的偏爱。
除汤若望外,《崇祯》一剧还提及了沙勿略、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耶稣会士,且以汤若望开启全剧、以沙勿略作结。沙勿略作为第一位抵达马六甲、日本及中国的耶稣会士,倡导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工具传播基督教义,坚持本土化传教策略,是耶教东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冯德尔对沙勿略的颂扬贯穿《崇祯》全剧始终:在剧前致辞、剧情简介及第二幕颂诗中即已褒扬了沙勿略为东亚传教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及至第五幕戏剧终结前,沙勿略以幽魂的形象出现,祈求万能之主的仁慈,并预言李自成大顺朝的败亡、清人将一统帝国、耶稣会士虽得顺治优待但又难逃康熙初年的严酷教案等史事。与第一幕以汤若望追叙明史一样,沙勿略出现于此是为了交待《崇祯》创作时的最新中国政治及传教形势。这种具有明显“反叙事性”的设计为戏剧营造出一种历史纵深感,且能体现出时事剧的即时性特征。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历史人物在剧中实为上帝“神意”的代言者。很显然,中古基督教神意史观仍主导着冯德尔的创作,在他看来,历史便是基督神意的展现,上帝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他以沙勿略的预言映带出未在戏剧中呈现的上帝“神迹”,如备受顺治恩宠的汤若望至康熙初年却遭弹劾下狱,甚至被四辅臣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等罪名判凌迟处死,却又在行刑前因京城突发地震而获得赦免。2 此事普遍被天主教徒视为上帝神迹。3 上帝既能以神力拯救汤若望,亦必能以神力毁灭大明,故戏剧尽管题名为“崇祯”,但其真正的主角却是全能上帝。上帝因扫罗违背圣意、听信卜者之言,最终让其“失去王位,跨过三个儿子的尸体,被剑砍死”,4 冯德尔以扫罗之典预言了崇祯及大明的宿命。崇祯在其眼中就是中国版的扫罗,崇祯之死代表了异教徒的共同命运。冯德尔以这一惨痛历史昭示人类永远无法抵抗的“神意”:“帝王们尽其所能想要延续稳定恒久的统治,但他们永远不能如愿……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罗马帝国如何在三四百年后令人震惊地崩溃,继而逐渐变成荒漠,除了光辉历史的遗响和死亡的阴影,其显赫声名现已荡然无存。永恒、持久及万世只属于上帝,上帝给俗世之力设置了恒定的限制,正如先知丹尼尔所云,季节及年岁的更替、政权及皇朝的兴亡教会我们除了上帝,不去相信任何易变之物。”1 在冯德尔等基督徒的观念中,上帝支配着人类历史、主宰着人类命运,当最终审判来临时,上帝的信众将安居天国,追随撒旦者则永遭地狱折磨,世俗之城如罗马就因罪孽深重而难逃毁灭厄运。当然,上帝是理性的,必依人事善恶来支配历史,而非随心所欲地操纵历史,明王朝的腐朽黑暗、统治者的残暴贪婪使其难逃覆灭之宿命,此即上帝神意在中土的彰显。
但冯德尔毕竟不是耶稣会士,因此其宗教书写中或多或少地掺入了世俗情怀,最为突出的便是对崇祯身上的父性的表现。他把崇祯塑造成一个慈父,担忧出城打探敌情的太子的安危,安排王子们在城陷之前逃出生天;将长公主比喻为“神圣王冠谷中最美丽的凤凰花”,2 为她凋谢于14岁豆蔻年华的生命而扼腕伤怀。这些都是同理心对作者的潜移默化。在现实生活中,冯德尔的发妻梅根(Maaike de Wolff,?—1635)早逝,四个孩子夭折其半,他将自己的舐犊之情移注于崇祯,从而使这一形象闪耀着父性的光辉。这种父性同样出现在为一个誓言而将女儿献为燔祭的耶弗他身上:“这句话先割断我的心脉,然后是女儿的喉咙!哀哉,一个誓言变成一把剑,由复仇的阿蒙神铸就!哀哉,无可挽回的誓言!”3 耶弗他的哀号与崇祯剑斫公主时的悲泣如出一辙。而这种移情及神入断不会出现在卫匡国、杜赫德这些天主教神父的笔端。4
此外,冯德尔的宗教书写一以贯之地具有市场意识,从最早的《逾越节》到最后的《崇祯》,他的戏剧致力于营构迎合受众欣赏趣味的故事,既贴合俗世现实,又不乏宗教诠释,将道德说教及圣经隐喻巧妙编织于世俗纷扰中。比如,《逾越节》将带领低地国家摆脱西班牙奴役的奥兰治王子(Willem van Oranje,1533—1584)比喻成第二个摩西,以基督救赎论为当时正如火如荼的独立战争提供神意支持。这部戏剧处女作因符合时代之需、彰显爱国情怀而一炮走红,大受欢迎。冯氏文学创作的市场意识得益于荷兰的重商社会。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冯德尔出生于商人家庭,除了诗人及戏剧家的身份外,他还是一个店主。在他眼中一部作品也是一件商品,《崇祯》的卖点显然在于其突出的时效性及鲜明的异域性,这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当然,统御剧中一切的依然是永恒的“神意”。
四、余论:好奇的时代与难以抗拒的“中國风”
冯德尔的《崇祯》一向被视为欧洲文学领域最早的“中国风”作品,付梓时明清易代的战火甚至尚未完全熄灭。这样一部时事剧在荷兰的出现绝非偶然。地理大发现及方兴未艾的远东贸易使欧洲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心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在荷兰表现得尤其突出。17世纪中叶,尤其是1640—1660年的20年间,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地图。正如卫匡国在《鞑靼战纪》前言中所云:“我希望本书将满足我们这个好奇时代的胃口。”5 正是时代及大众的好奇催生出《崇祯》和《自成:中国的覆灭》等演绎明朝覆灭题材的戏剧。一方面,远东异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荷兰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们经过“八十年战争”(1568—1648),刚刚挣脱西班牙统治建立联省共和国,《崇祯》尽现帝国覆灭的悲壮,不仅唤起了荷兰人遭受西班牙奴役的惨痛记忆,更促使他们正视当时英荷战争(1652—1674)可能给荷兰共和国带来的危难,激发起他们维护国家独立富强的强烈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伴随着17世纪荷兰开疆拓土的殖民扩张,海难、死亡、战争频发,因而《崇祯》体现了荷兰人对本土与全球各种天灾人祸的敏感。正如冯氏所云:“(悲剧)会唤起观众的同情心及恐怖感,如要达到其创作目标和初衷,就应节制观众的这种激情以净化他们的缺陷,引导他们更好地、温厚及平静地承受世界的灾难。”1《崇祯》正是以宗教宿命论稀释悲剧引发的同情及恐惧,并利用受众的好奇心润物细无声地宣扬基督福音。此外,荷兰是个重商的国度,明清易代对这个迅速崛起的海上贸易强国尤为重要,因为觊觎已久的对华直接贸易终于出现了转机。更何况,他们还看到了联合鞑靼人从郑成功(Coxinga)手中夺回台湾岛的一线希望。2
相较于冯德尔,胡斯的《自成:中国的覆灭》一剧则以李自成篡夺皇位随即覆灭的悲剧为主体,将崇祯自缢到满人入主北京之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压缩在一天之内,演绎了李自成推翻大明、君临天下,旋即沦为鞑靼人俘虏的戏剧人生。胡斯撰写该剧时年仅18岁,3 他虽是冯德尔的崇拜者,却并未亦步亦趋于前辈,亦未渲染汉、满两个民族间文明及道德上的差异,更未评判基督教与异教的高下,反而在其剧的第三幕中以儒士之口传导出中国人对耶稣会士来华意图的质疑:
你东来中土,怀揣虚伪可憎的嫉妒及仇恨,
在民众中传播妖法、蛊惑百姓,
好让他们向你的天主俯首称臣。
但你镀金面具下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圣人孔子,荣耀无上,
立言不朽,垂教无疆,奠定儒教,
纯粹睿哲,无关若邦天主,
他是政治迷局中的俗世先知。4
胡斯不仅没有冯氏对耶稣会士的溢美之词,反而委婉表达了对天主教信仰及以神启为中心的基督教史学观的质疑。并且,他进一步指出16世纪耶稣会士在日本及南美各地的传教并不成功,甚至造成诸多土著的伤亡。胡斯对中国圣哲孔子的赞颂,也体现出其不为基督教所缚的开放心态。更为可贵的是胡斯宽广的全球视域,他惋惜早期荷兰航行家开辟北冰洋直通亚洲航道的壮志未酬,以中美洲阿兹特克君主蒙特祖玛二世(Monctesuma II,约1475—1520)遥相呼应自我封闭、轻信佞臣的崇祯,希望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华能打开国门,以无尽的财富向荷兰贸易王国及英勇水手致敬。5 与之相应,胡斯还将统御《崇祯》的“神意”世俗化,把崇祯、李自成的生死沉浮描述成个人运气的好坏,由此可见胡斯与基督教信仰的疏离。他比冯德尔更善于激发受众的好奇心和全球意识,引导他们透过中国易代战争来一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相关历史事件,并以俗世视角观照帝王将相的坎坷人生,这折射出17世纪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及近代进步史学观的日趋成熟。
而引发这种好奇的始作俑者是自达·伽马开辟印度洋新航线后在亚洲迅速扩张的两个庞大机构:耶稣会及东印度公司。尽管两者分别关注宗教及贸易领域的利益,但都成为17世纪中国信息的主要输送者。由于两者入华的目的及其程度不同,因而各自的中国想象也有差异。如卫匡国在瓷塔中看到了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尼霍夫却在瓷塔中领略到了中国辉煌的建筑艺术;明朝灭亡被卫匡国归因为上主神意,而在尼霍夫眼中只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盛衰变迁,与上帝无关。但是,对一些需要深入了解、多方考察的事物,如中国的政体、民俗、文学、教育等,东印度公司只能顺从于传教士的观点,因为当时公司尚未与中国展开直接贸易,缺乏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民风的机缘。除了前往台湾岛、马六甲等地的华商外,再无可靠的信息源,故东印度公司更多依赖于遍布帝国各地乃至朝廷的耶稣会士,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中国认知。比如,关于中国政府采用开明专制政治(benevolent despotism)、鞑靼文明远逊于中原文明等观念。有意思的是,冯德尔与这两个机构皆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推动了《崇祯》的问世。冯德尔与耶稣会士的关系上文已提及,此不赘述。而他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并不逊于耶稣会:“作为一个阿姆斯特丹人及该城最具名望的作家,冯氏与共和国最著名的社团皆有联系,包括东印度公司,其诸多作品是公司及其亚洲职员的编年史。当其子荡尽家财深陷债务危机时,冯氏甚至安排儿子进入公司当差。他与公司的关系使其全部作品皆体现出熟悉亚洲的特质,他对中华帝国的了解并不仅仅源自其所依赖的出版物,正如某些学者已指出的,耶稣会士仅是冯氏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1 因此,耶稣会为《崇祯》提供了文本素材及角色原型,东印度公司的远东信息及尼霍夫使团报告则给《崇祯》输送了鲜活的养分,从而使该作品更丰满、立体、真实。
总之,正因为时代对中国的好奇,一个宣扬天主教神学观的陈旧主题被套上了新颖别致的中国华袍。冯氏的诸多剧本皆为弘扬上帝“神意”而作,且在主人公命运的剧变上也有相似性。冯氏欲以新颖的中国历史题材掩饰其主题重复及创造力贫乏的用意不言而喻,他对神意的过度强调使《崇祯》这一中国题材被圣经典故、神意说教抢占了戏份,因而脱不了宗教剧之嫌疑。但是,能从一个明清鼎革的旁观者变身为再现者,这种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创作无疑极具示范性及创新性。
Vondels Historical Play Zungch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17th-Century European Catholicism
SHI Ye,LI Yiting
Abstract: Among all the works of Vondel, the 17th-century great Dutch poet and playwright, Zungchin is the only play based on China. Because of its truthful and timely representation of Emperor Zungchin, the last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and his tragic downfall, it is viewed as the first Chinoiserie literary work in Europ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material as well as the language barrier, few scholars in China have paid attention to Vondel or Zungchin. Through reading the playscript carefully, with combination of Vondel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his religious belief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artino Martinis Bullum Tartaricum of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hina-related reports are the main material sources of Zungchin. Vondel imagined and interpreted the death of Zungchin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with a classically tragic creative approach. Despite its strong Catholic theology, the play vividly demonstrated the curiosity of the Western world towards China and its inevitability produced in the Netherlands.
Key words: Vondel; Zungchin; Ming-Qing transition; Catholicism
(責任编辑:陈 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