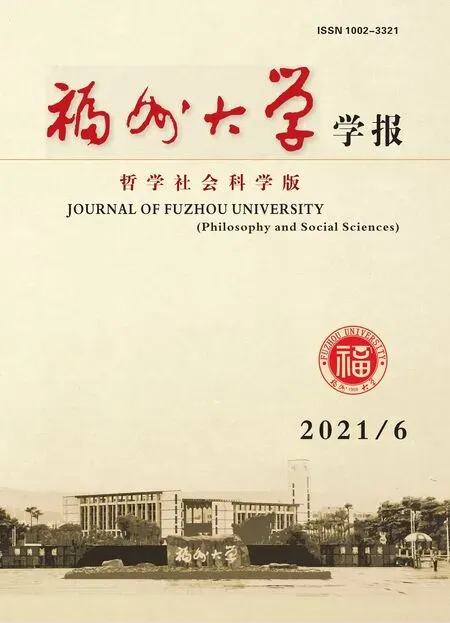北宋理学论争探析
——以章望之与李觏、欧阳修的论争为中心
胡 悦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漳州 363000)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浦城章氏是当时的地方望族。《挥麈录》载:“浦城章氏,尽有诸元。至今放榜,必有居上列者。”[1]自开宝至宣和百五十余年间,浦城章氏一门得有两位状元,两朝宰相,三十四进士,盛极一时。其兄章拱之,曾知晋江。伯父章得象为仁宗朝宰相。望之少孤,得伯父章得象教养。章望之一生未仕,却以理学成就显于当时。《宋元学案》载:“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2]
章望之以倡道为己任,著有理学文章《救性》七篇、《明统》三篇、《礼论》一篇,另有歌诗、杂文数百篇,集为30卷,惜多亡佚,被后世誉为“浦城理学十三子”之首。
一、理学初兴的时代背景
宋自“陈桥兵变”而来,“安史之乱”后的藩镇之祸乃至五代十国的割据政权犹在目前,宋朝廷吸取教训,试图分割权力、集中兵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政治上,实行“崇文抑武”的策略,大幅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并推行恩荫、荐辟制度,大量吸纳文士,以文官代替武将,将中央行政权力管控于文官手中。这样一来,虽避免了武将权倾朝野、压迫皇权的可能,但也造成了官僚队伍的庞大;军事上,迫于辽和西夏的威胁,为维护宋的封建统治,宋王朝大量招募士兵,“庆历年间,宋兵的数量已由宋初的22万增至125万。”[3]然而士兵数量上的庞大并没有切实提升宋朝的军事实力,反而造成了军费的巨大消耗;思想上,宋王朝虽提倡儒学,但也采取佛教保护政策,与道教并重,各地佛寺道观几不胜数,遑论僧道人数。佛、道的繁荣一方面消耗着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另一方面“佛老空虚”的价值观若长期浸染士大夫一族,朝廷就有陷入腐朽不作为的危险的可能性,进而影响社稷。“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4]冗官、冗兵、冗费终使宋朝百年之积,唯存空簿。面对这样积贫积弱的社会局势,天下有志儒士欲起而救之。他们不再满足于笺注训诂,而是渴望从佛教与道教思想中汲取养分,将传统儒学发展成具有哲学思辨的经世实学,重新树立儒学在宋朝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正统地位,以“明体达用”的理学与虚空佛老相抗衡,重振社会之风气。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家,极力推行庆历新政的同时大倡兴学。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家,发起诗文革新运动,倡导“文道并重”,宣扬儒学道统。与之相呼应者,有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和胡瑗,他们先后任太学主讲,发扬“明体达用”之学,视儒家所传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治国平天下的依据。江西学派先驱李觏、河南先生尹洙,闽学先驱蔡襄、章望之、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以及“北宋五子”等人也奋起而争鸣,形成“学统四起”的繁盛局面。
二、“礼论”之辩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早期创立盱江书院,门下学生数十百人,故世称“盱江先生”,晚年任太学直讲。他以“礼”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康国济民”的思想体系,是北宋早期理学代表人物之一。天圣十年(1032),李觏著《礼论》七篇阐述自己的礼论主张。庆历七年(1047)章望之专门写了一篇《礼论》来反驳李觏的观点,李觏看了章望之的文章后,又撰一篇《礼论后语》与之辩论,这次论争是北宋理学界的大事。
章望之之所以要撰文反驳李觏,是因为他与李觏在对“礼”的定义以及对“性善”论的看法上存在差异。李觏在《礼论》中是这样定义礼的:
曰: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
曰:尝闻之,礼、乐、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并用;传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于礼,无乃不可乎?
曰:是皆礼也。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日仁,曰义,日智,日信,礼之别名也,是七者盖皆礼矣。[5]
李觏认为礼是为人治世的根本准则,是统摄礼、乐、刑、政与仁、义、智、信的最高范畴;并将传统儒家君子提倡的修身美德归结于外在的“礼”,认为仁、义、智、信都是礼的别称。章望之反对李觏这种将仁、义、礼、智、信都归结于礼的主张,他反驳称:
率天下之人为礼不求诸内,而竞诸外。人之内不充而惟外之饰焉,终亦必乱而已矣。[6]
章望之不认同李觏将内在的仁、义、礼、智、信修为同外在的礼乐行政制度都归结为礼,并将礼作为他整个“康国济民”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的观点。章望之说:“学乎圣人者,何必易其言?”[7]在他看来,孔子谈及仁、义、礼、智、信时更为强调的是仁与礼,最为注重的是仁,故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8]仁是礼的内在价值。孟子亦强调仁,他将仁政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准则,并将仁义礼智信并举,认为它们发源于人的内心。章望之是孟子思想的捍卫者,他主张实现大道应求诸内,而非外,天下之人若皆像李觏所说将礼奉为根本准则而放弃充实内在的品德修养,那么不仅不能实现尧舜之治世的政治理想还会致世乱。面对章望之“不求诸内求诸外”的批评,李觏辩说:
夫章子以仁、义、礼、智、信为内,犹饥而求食,渴而求饮,饮食非自外来也,发于吾心而已矣。礼、乐、刑、政为外,犹冠弁之在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内出也。[9]
李觏的话,可看作是对传统儒家思想重视内而忽视外的突破,他主张以外在的礼制伦常来统摄约束内在心性。李觏的这种主张具有特定的时代思想背景,当时的社会思潮向佛之风盛行,而国家却积贫积弱,李觏正是为了反驳这样的“佛老空虚”的社会风气,避谈心性,甚至是隐藏主体内在心性的价值,强调“礼”的经世致用、强调“尊王”、强调“霸者不易”、强调“谈利”,力求用这种极具“功利性”的论说来改变社会向佛的风气,一振国家局势。而章望之与李觏对立的根本点在于:章望之是正统儒学的捍卫者,他始终秉持着道德的理想主义,认为君子修仁义道德方是强国济民的大道。他的理学思想具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他认为:“善在我思必有,不善在我思必无。”[10]强调君子要以“五德四失”来规范自身。
章望之与李觏的思想差异,除了体现在对“礼论”问题上,还体现在对“性善论”的接受上。章望之撰文反驳李觏《礼论》的原因,除不认同他的礼论观外,还因为李觏弃孟子“性善”之学而取韩愈、扬雄之说。李觏在《礼论第六》中道:
孟子以为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谓之皆善,荀卿谓之皆恶,扬雄谓之善恶混,韩退之谓性之三品:上焉都善也,中焉者善恶者混也,下焉者恶而已矣。今观退之之辩,诚为得也,孟子岂能专之?[11]
李觏不赞同孟子的“性善论”,并吸收扬雄和韩愈的人性观,将人性分为五类:
贤人之性,中也。扬雄所谓“善恶混”者也。安有仁义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学而自能者也,圣人也。下愚,虽学而不能者也,具人之体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为三焉:学而得其本者,为贤人,与上智同。学而失其本者,为迷惑,守于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学者,为固陋,与下愚同。是则性之品三,而人之五类也。(《礼论第四》)[12]
章望之则以孟子学说为宗,他曾著《救性》七篇阐发孟子的“性善论”学说,排斥荀子“性恶论”、扬雄“性善恶混”说、韩愈“三品”说和李翱“性善情恶”说。
章望之与李觏虽在“礼论”和“性论”观方面存在思想差异,但二人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渴望复兴儒学强国安邦,不同的只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途经的选择上。李觏求诸外,而章望之求诸内:李觏希望通过外在的法制约束来实现社会的安宁秩序,而章望之始终坚守儒家君子可以凭借内在的经典学问和道德修养而非外在的政治法律来重建社会秩序。
章望之与李觏的论争从根本上来说,是北宋理学内部不同思潮的论争。他们虽然都是北宋理学的先驱,都重义理不重训诂,且都渴望在佛老虚空思潮的冲击下重振儒学,重振社会风气以兴邦。但涉及具体的学说理论和兴国设想时,二人的思想就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二人身上。“章李论争”只是北宋理学初兴时期各学派蜂起争鸣的一个缩影,如今回过头来看待这些论争时,比起议论孰是孰非更为重要的是,应当看到正是这些坚守自己的理论学说同其他学派争鸣的志士扩大了新儒学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为理学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基础。
三、“正统”之争
“正统论”开始作为一种史学理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在魏晋“正统之辩”时期,但正统作为一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深入人心,它的核心主题是讨论历代王朝的递传秩序与合法性。以宗法制为权力分配制度的封建王朝最为看重“名正言顺”。于是乎,历代君王都将正统论视为政治舆论工具,以标榜自身为正统来统摄臣民、建立威望、为其统治的合理性辩护;史家以正统王朝更迭的年份作为纪年线索来编撰事迹;文士亦以正统朝纲所建立的社会秩序为基础来发扬风教。关于孰为正统的实际论争历朝不废,但正统的系统理论则是在宋朝形成的,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13]两宋时期,史书编撰的盛行与史学思想的发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宋朝史学的繁荣。作为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正统史观亦于这一时期趋于系统化、理论化,并对当时及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欧阳修是宋代正统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于康定年间撰“正统七论”:《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秦论》《魏论》《东晋论》《后魏论》《梁论》,晚年删改为《正统论序论》《正统论上》《正统论下》三篇。关于写作的背景和缘由,欧阳修于《正统论序论》言:
伏见太宗皇帝时,尝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晋、汉、周事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为伪。梁为伪,则史不宜为帝纪,而亦无曰五代者,于理不安。今又司天所用崇天历,承后唐,书天佑至十九年,而尽黜梁所建号。援之于古,惟张轨不用东晋太兴而虚称建兴,非可以为后世法。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历家不识古义,但用有司之传,遂不复改。至于昉等,初非著书,第采次前世名号,以备有司之求,因旧之失,不专是正,乃与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14]
据此可知,欧阳修撰写《正统论》是出于史书编撰的现实诉求问题。宋太宗时,薛居正承旨编撰《五代史》,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事,李昉等人奉命编次前世年号。然而,李昉等人将梁国政权视为僭伪,朝廷司天监所用《崇天历》也“尽黜梁所建号”,认为后唐(923-936)才是承继大唐的正统政权,在唐朝灭亡之后舍弃梁朝年号而继续沿用唐哀帝的天佑年号(904- 923)。史学家往往以朝代更迭的顺序来作为编史的纪年线索,这样一来,薛居正等史官撰写的《五代史》中所涉梁的编年就与李昉等人编的前世年号以及《崇天历》使用的年号不符。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世人在看待正统问题时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欧阳修看到了这一根本矛盾,所以撰文阐发自己的正统观,希望能通过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评判正统的理论体系以供世人参考,以此来达成正统论上的共识。
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以《春秋公羊传》为滥觞,由“君子大居正”和“王者大一统”衍生出自己的正统理论。与偏向从道德层面出发评价政权的传统正统观相比,欧阳修在评价一个朝代的正闰时更为注重政权的功业。在判断一个政权是否能够被称为正统时,欧阳修认为取得“一统”的功业是很关键的要素,他在《魏论》中言:
自秦以来,兴者以力,故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而已。彼汉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灵而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故豪杰并起而争,而强者得之。此直较其迹尔。故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15]
欧阳修认为魏取得了汉的天下正如汉继承秦的天下一样,是“强者得之”,面对历来颇具争议的曹魏政权是否为正统的问题,他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肯定了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同时,他在《正统论上》说:“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16]古往今来称王的人,有的是因为有美好的德行,有的是因为施恩于百姓,有的是因为世代的累积成就了帝王基业,所以不应当仅从德的角度去评价一个政权。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他从功业的角度出发黜蜀而取魏为正统。欧阳修这种将政权的实际功业凌驾于道德之上的评价引发了士人对正统问题的激烈讨论。
章望之并不赞同欧阳修将取得功业的强者政权同那些在道德层面居“正位”的政权一起归为正统的观点,于是撰写《明统论》发表自己的正统观,同欧阳修论辩。《明统论》曰:
欧阳永叔《正统论》与夺异于旧说者四焉:以前世谓秦为闰,今较其功业之初,宜得正统;以陈寿列叙《三国志》均为之传,而魏不立纪以统二方;以朱梁得唐,而后唐以降,皆绌为伪梁,故今并以王统进之。[17]
章望之不同意欧阳修将曹魏与后梁归为正统的观点,但他并没有直言不满,而是先说欧阳修的观点同自己的旧说自相矛盾,这里的旧说是指欧阳修在《原正统论》中阐述的观点:“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8]章望之从欧阳修以“大居正”“大一统”作为衡量政权是否为正统的标准入手,然后以此标准分析各政权的“正”“统”情况:一是秦国虽达成一统中国的霸业,取得“统”的地位,但秦朝以暴政统天下并无功德可言,所以难居“正”位;二是曹魏政权以篡逆起家,政权得之既不正,又没能一统天下;三是后梁开国皇帝朱温挟力欺君,凭武力强盛篡唐称帝,非处“正”位,亦无一统之功。所以他认为欧阳修《正统论》“进秦得矣,而未善也,进魏、梁非也”[19]。像曹魏和朱梁这样靠武力谋得帝位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偶尔现象,这些政权难以称其为正统,但又不能忽略它们确实存在的这一现实。面对这样的历史问题,章望之也深刻思考过,他不赞成欧阳修将它们归为正统的做法,并在《明统》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正统”与“霸统”说:
予今分统为二名:曰正统、霸统。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尧、舜、夏、商、周、汉、唐、我宋其君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秦、晋、隋其君也。[20]
章子认为,看待政权更迭问题时,既不能放弃儒家的“正统”观,亦不能忽视那些以武力取得帝位却无功德的政权,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将皇统分为“正统”和“霸统”。“正统”即是尧、禹、汉之类以功德得天下的政权,“霸统”是指像秦、晋这些虽成就王业却难归入“正”位的政权,既坚持了儒家正统观,又肯定了霸统政权所取得的功绩。章望之的正统、霸统说与“王道”和“霸道”一脉相承。他的理学思想以孟子思想为基石,在探讨正统问题时,继承了孟子的“王道”观,坚持实施仁政方是王道的政治思想,同时,他也吸纳了荀子的“霸道”理论,以解决政权更迭的历史实际问题。可以看出,章子虽以孟子为尊,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他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博学纳广,善于从思辨角度解决实际问题。也正是这种不会陷入固步自封的思想僵局的思辨精神促使章子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物之一。
章望之与欧阳修的“正统论”之辩广为当时名士所关注,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就此事发表了议论。
苏轼见章望之著《明统论》反驳欧阳修的正统观,于至和二年(1055)撰写《正统论》三篇同章子辩争。苏轼在文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
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辩,以全欧阳子。[21]
苏轼不得不与章子辩的原因有二,一为全欧阳子:《正统论》作于苏轼二十岁时,虽然苏轼是在写就这篇文章的两年后才在科举中被欧阳修亲点为第二名,写《正统论》时也未与欧阳修有亦师亦友的交往,但早在这之前,苏轼就已经把欧阳修看作是自己的老师了,他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追溯:“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22]苏轼自童子时起便将欧阳修奉为自己的老师,他的政治抱负和文学理想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欧阳修文章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欧阳修是苏轼人生前行道路上的灯塔,他受人辩驳,苏轼不可能无动于衷;二为论学术:“《春秋》学”大盛于当时,刚刚从五代纷乱中走出来的北宋学者们,在当时国家政治问题以及儒学式微的现实面前,亟于从《春秋》中寻求理想的政治宪纲,有关正统问题的讨论大为炙热。苏轼年少时就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新政人杰为追慕的对象,关注政治民生和社会改革的他不可能对“正统论”毫无见解和看法,撰写《正统论》既是为全欧阳修之说,亦是表达自己的正统观。他在《正统论》总论中说:
不幸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是二人者立于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统之论决矣。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实也,夫何议。[23]
在苏轼看来,正统之争的实质是名实之争,“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是名,“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是实。他从名与实的角度批评章望之不把曹魏归为正统,说:“是章子未知夫名实之所在也。”[24]接着解释说:“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夫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25]曹魏是当时的强者,于魏之外无有其他政权同他相抗衡,苏轼认为曹魏有正统之“实”,章望之不应把它排除在正统的行列之外。但实际上章望之不把曹魏归入正统的原因并不全在于它没有一统天下,更多的是因为他认为曹魏篡刘汉政权称帝,难居“正”位。苏轼辩说:“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26],力图从曹魏政权有天子之位的实际功业出发反驳章子。
苏轼与章望之论争的接续者是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宋神宗命蔡延庆、孙觉修起居注,欲诏苏轼同修。时任参知政事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上谏说:“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岂可便令修注!”[27]
王安石说这段话或是出于其个人政治立场的考量,重点也并非是苏轼和章望之的正统之辩。但自那场论争至熙宁二年已隔十余年,王安石在向神宗上谏的场合仍提到这件事,而且以“苏轼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来作为自己反对起用苏轼的论据之一,可见这次“正统”之辩的影响持续之久,也足见章望之《明统》的观点深入人心,若章望之的观点不为人们所接受,多数文人学者都支持欧阳修与苏轼的话,想来王安石也不会拿此事同神宗谏说,由此可以推论章望之的学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对这场论争发表意见的还有司马光,他在《答郭纯长官书》中说:“夫正闰之论诚为难晓,近世欧阳公作《正统论》七篇以断之,自谓无以易矣。有章表明(民)者,作《明统论》三篇以难之,则欧阳公之论似或有所未尽也。欧阳公谓正统不必常相继,有时而绝,斯则善矣。然谓秦得天下,无异禹汤,又谓始皇如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又以魏居汉、晋之间,推其本末,进而正之。此则有以来章子之疑矣。章子补欧阳公思虑之所未至,谓秦、晋、隋不得与二帝三王并为正统,魏不能兼天下,当为无统,斯则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与魏同,乃独不绝而进之,使与秦、晋、隋皆为霸统亦误矣。”[28]司马光具有史学家的理性批判的精神,他在看待历史正闰问题时强调应依功业而作客观的评价。[29]他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分别评说了欧阳修和章望之的理论中的益和弊。对章望之反驳欧阳修将秦、魏、晋、隋与二帝三王并为正统的观点表示赞同,同时也对章望之将魏与秦、晋、隋都列为霸统的做法加以批评。
要言之,欧阳修为解决当时官修《五代史》选取年号的现实问题,以“大居正”和“大一统”为衡量标准,构建自己的“正统”理论,由此引发了宋代士人对“正统论”的激烈讨论。先是章望之站在传统“王道”思想的角度,不认同欧阳修将魏梁归为正统的做法,于是构建“正统”和“霸统”思想理论同他争辩;后有苏轼为全欧阳修之说,著《正统论》三篇反驳章望之。再有王安石认为苏轼为批评章望之所作《正统论》是无理之谈,反映出章子的理论为传统儒士所接受;最后,司马光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总结了欧阳修与章望之理论的得失。但由这场论争引发的宋人对正统的讨论并没有就此落幕,“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亦撰有《正统论》;宋室南渡后,张拭、朱熹等人在三国正闰问题上持正蜀而闰魏、吴的观点;直至宋末,仍有学者探讨正统问题,如周密著有《正闰》表达自己支持蜀汉承东汉正统的主张。
在这场论争中,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是,章望之将儒家思想中的“王道”和“霸道”概念与历史的皇统继承问题相联系,把“统”分为“正统”和“霸统”,在讨论朝代更迭出现的有的政权以强权获取帝位而无功德的问题时,既坚持了传统的儒学“正统”观,又很好兼顾到了存在“霸统”政权的历史现实。他强调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和政治思想的继承,并善于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体系,具有义理思辨的特征。他的“正统”和“霸统”论从道德和功业两个方面看待政权更迭问题,坚守传统仁政思想的同时也肯定了那些统而不正的政权的实际功业,体现了理学“内圣外王”的思想。且他主张曹魏不应归为入正统的思想也为后世多数士人所接受。章望之的“霸统”思想促进了宋代系统正统理论的形成,他与欧阳修的论争也促使更多士人关注理学思潮,为宋代学术繁荣以及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章望之与李觏、欧阳修的论争中,我们可以有这两点重要认识:一则,章望之是构建“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繁盛格局的重要理学家之一。他在与李觏、欧阳修的论争中提出的理论学说,为后世“礼论”“性论”以及“义利王霸”说的理论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对宋代义理之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闽学的萌芽要比杨时、游酢洛学求道早约半个世纪。元祐八年(1093)杨时拜入程颢门下,同游酢一起研习理学。世人多将杨时与游酢立雪程门、载道南归视为闽学的开端。但庆历年间,闽地已有章望之致力理学,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不计。
注释:
[1] [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2] [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第2页。
[3] 杨永亮:《近世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变革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年,第111页。
[4][10] 曾枣庄、刘 琳主编:《全宋文》第1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上,第354页。
[5][6][7][9][11][12] [宋]李 觏撰,王国轩校:《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第5页,第24页中,第24页中,第24页下,第18页,第11页。
[8] [清]纪晓岚总撰,林之满主编:《四库全书精华 经部》,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
[14][17][20][21][23][24][25][26] 郭预衡、郭英德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第4403页上,第4403页上,第4403页中,第4403页中,第4403页下,第4403下。
[15][16][18][19] 李之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四册),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6,34,37,34页。
[22] 张春林编:《苏轼全集》(下册),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332页。
[27] [宋]杨仲良: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110页。
[28] 仇正伟、李肇翔编:《唐宋十大家书信全集》(上册),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年,第737页。
[29] 陈庆元:《中国散文研究》,见《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