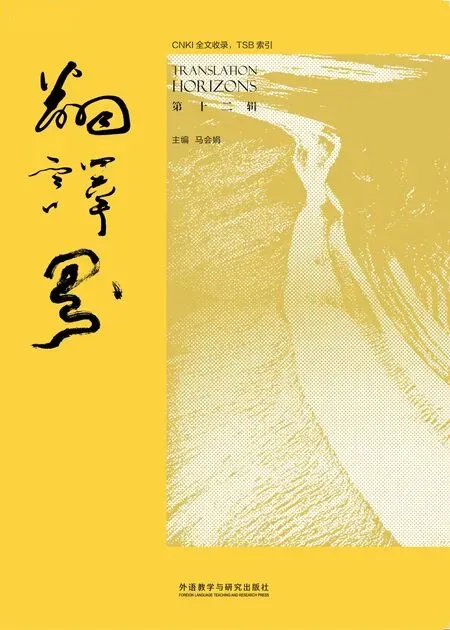翻译价值:中国文学外译的“无形之手” *
罗迪江
郑州大学/广西科技大学
1 引言
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与深入推进,目前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它的问题与实质(谢天振,2014)、滤写策略思考(陈伟,2014)、学科范式(陈伟,2016)、影响因素(许多,2017)、成就与反思(胡安江,2018)、路径探索(戴文静、焦鹏帅,2019)、评价(刘云虹,2019a)、译者主体视角(张汨,2019)、困境与出路(张丹丹,2020)等,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需要正视的是,中国读者对于本土文学的漠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空白、英语世界对于翻译作品的先天歧视,以及翻译策略的决策偏失与本土传媒的缺席使得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依然长路漫漫(许钧,2018a)。这些症结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与始终贯穿和“操纵”中国文学外译过程的“无形之手”——翻译价值——密切相关。
翻译价值,一方面制约着中国文学外译的进程,另一方面也隐含着解决上述问题的神秘力量,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中的关键论域。但就目前研究而言,翻译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翻译事实的遮蔽之下,对其研究相对沉寂,这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实践的一大遗憾。翻译价值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翻译策略、翻译评价、翻译主体甚至困境出路,犹如一只“无形之手”始终贯穿中国文学外译的整个历程。本文试图从这只“无形之手”来审视中国文学外译的实践与研究,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整体省察,有效反拨此过程中对翻译价值之维的忽视,同时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偏向性与合法性进行深入阐释,从而推动当前中国文学外译之价值理论的深入研究。
2 中国文学外译的隐秘力量
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张柏然、许钧,2002)。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量案例分析揭示了中国文学外译并不是价值无涉(value-free)的,而是价值负载(value-laden)与价值关联(value-relevant)的。进一步来说,中国文学外译本质上是一个由“价值驱动”(value-driven)的文学外译过程,其过程总是由翻译价值这个隐秘力量驱动并渗透着相关翻译主体的价值观。“价值驱动”的中国文学外译,核心在于确立关于中国文学外译的基本认知价值及其相关认识价值理论,为中国文学外译的症结性问题寻求新的理论资源,从而揭示中国文学外译固有的价值形态。中国文学外译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指向的是翻译价值偏向性的反思,是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模式等所做的有益探讨,要求的是一种合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价值分析;另一方面,它指向的是对翻译价值合法性的反思与审视,关注中国文学外译之中运用的翻译策略、方法、模式等方面的论证,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有效的批判进而做出合法性地推进。如此定位的翻译价值理论,使得这只“无形之手”始终贯穿于中国文学外译之中,并使之具有了价值负载、价值关联与价值驱动的本真形态。
2.1 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偏向性
作为价值负载与价值驱动的中国文学外译,体现了中外文学之间的“视域融合”关系,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其中必然涉及翻译价值观问题,因其蕴含翻译价值所以其外译的内容就存在着价值偏向性,即要么以符合西方文化主流翻译规范为标准,要么以准确传播中国文化思想的真实形态为己任。由于价值具有偏向性,翻译策略也具有相应的偏向性。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偏向性,决定了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而不同的策略选择就是一种基于归化与异化的逻辑选择。不管是作为方法、策略抑或伦理,归化和异化基本上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并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在语篇层面(冯全功,2019)。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历程,或聚焦于归化,或选择异化,或两者兼顾。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它们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外译的整个进程。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承载着价值意向并驱动着翻译策略要么归化要么异化的选择史。
纵观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历程,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前期,主要是选择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强调中国文学外译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潜在地凸显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偏向性。在该时期,符合西方文化价值观被视为文学翻译的价值根据,“归化式”翻译策略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它同时更多地渗透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痕迹与影子。以《道德经》英译为例,综观《道德经》英译的历程,从1859年耶鲁大学英译本手稿到1868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版本,从189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版本到1898年卡鲁斯(Paul Carus)版本,再到21 世纪诸如罗慕士(Moss Roberts)、韩禄伯(Robert.G.Henrick)、安乐哲(Roger T.Ames)、戴尔(Wayne W.Dyner)、闵福德(John Minford)、 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 汉密尔(Sam Hamill) 等英译版本,《道德经》英译的大部分历程是由外国传教士与外国译者主导的,这些译者翻译时遵循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对核心关键词“道”的翻译也渗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思维,由音译的Tao 到直译的the Way、the Path、the Road,再到意译的primal、cosmic、existence、infinity、infinite、spirit、atheism、ineffable、guide、nature等皆是如此。然而,也正是在“归化”翻译策略的操纵下,“这一庞大而又神圣的文化翻译事业中,华夏文明的精神格局、智慧知性体系建构未能形成自觉意识,皆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认识范式、问题框架裁剪、肢解之”(包通法,2018:127)。如此而来,中国文学外译也就相应地变成了一种由西方文化价值观支配的实践行为,因而这种归化策略使中国文学的本真形态难以接受“异的考验”,无法在异域中获得“持续的生命”。由于西方译者所处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和立场等因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其中不排除有误读、误释、误译、误导的成分,甚至有过于西方意识形态化的成分,从而影响着读者的价值取向(杨琍玲,2014)。翻译策略的偏向性将中外文学关系中的西方价值偏向性推向西方读者,也“异化”了中国文学的价值形态,中国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也随之“异化”,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深入推进,中国文学外译逐渐转向选择与遵循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异化”策略,旨在强调中国文学外译的文化形态与真实面貌。王向远(2015:59)指出,“民国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由晚清的‘归化’转变为‘异化’,可以说是对晚清以林纾为代表的‘窜译’的一种反拨”。这种反拨就是对“异化”策略的回归与关注,尽可能地保持中国文学内在的文学性与价值观。当然,回归“异化”,并非是用“异化”替代“归化”,而是加大“异化”策略的选择以凸显中国文学外译的焦点,让世界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学,领悟中国文学的价值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学真正融入世界文学。就翻译价值偏向性而言,由“异化”驱动的中国文学外译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一种新翻译视角,在这一新视角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价值问题无疑需要被重新审视,并在中国文化价值化的背景下获得新的说明与解释。回到《道德经》的英译历程,自20 世纪30年代开始,华裔学者逐步加入英译《道德经》的队伍之中,先后诞生了四川大学胡子霖英译版本、英语语言学家初大告英译版本、法学家吴经熊英译版本、文学家林语堂英译版本、陈荣捷英译版本、赵彦春英译版本等。其中,“陈荣捷的译介工作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西方《道德经》英译中的神秘化和宗教化倾向,凸显了《道德经》的哲学意蕴”(刘玲娣,2016:136);“外文出版社版英译《道德经》采用基于可拓逻辑的类比法,再现了原典独特的语言形式、修辞手法以及思想文风,从而再现了原典的文学性”(赵彦春、吕丽荣,2019:84)。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主要由西方学者主导《道德经》英译的局面,“异化”策略的偏向性从西方文化价值观转向了中国文化价值观。换言之,“因其特定的文化身份及向外国读者阐释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使然,这类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汪宝荣,2017:118)。目前,推进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就是要让中国文学在异域中获得“来世生命”,在寻求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强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向异域文学展示中国文学外译固有的文学性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独特的文化价值,形成一种寻求中国文学荣耀的译者姿态与寻求中国文化荣耀的精神姿态。
2.2 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合法性
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合法性是从中国文学外译“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中引发的价值思考,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化自觉,对推进中国文学外译的深入发展颇为重要。就中国文学外译而言,翻译合法性一般是指人们对翻译实践活动的伦理信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翻译价值的合理性。它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观,通过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分析,剖析当代中国文学外译的翻译策略选择隐含的价值观念,从而对“归化”与“异化”策略做出价值评价与判断,进而审视中国文学外译蕴含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价值体系,中国文学外译的内容虽然丰富多样,但却存在着一种隐秘力量——翻译价值。蓝红军(2016:98)指出:“衡量我们一个时代的翻译成就如何,最终要看翻译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文化引领和精神提升的作用,要看我们的翻译是否向世界讲述好了中国故事,传递出中国情怀之美和中华文化价值观之高尚,要看我们的翻译是否无愧于我们民族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因此,中国文学外译的合法性最终要通过翻译价值来体现,它既是对自身文学性的根本保障,也是对自身价值观的具体确证与文化彰显。
许均(2017:2)指出:“建立翻译价值观,一方面要以对翻译之‘用’的理论探讨与历史思考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超越对翻译的实际之用的描述与分析,对翻译之‘用’进行价值的是非评判”。对翻译之“用”的价值评判,实质上涉及翻译活动的合法性问题。“翻译活动的合法性指向什么?我认为是指向伦理。例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尊重原文,这样的翻译是合法的吗?对原文不断地修改、修订甚至是改编,这样的翻译是合法的吗”(许均,2019:2)?进而论之,翻译活动的合法性问题本质上就是翻译价值的合法性问题,也可以说是翻译活动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问题。它所涉及的是翻译“应当”还是“不应当”的问题,是一种关于中国文学外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判断,凸显文学外译的价值理性与价值信念。因此,它需要我们亟待思考、关注与解决如下根本性问题:“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中国文学、文化怎样能够在‘走出去’过程中得到真实而有效的传播?如何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平等交流、共同发展这个开放的视野下来认识与理解翻译?如何促使翻译在社会发展、文化建构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凸显其应有的价值”(刘云虹、许钧,2017:59)?就此而言,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是价值判断所指导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结果的一种性质,而其价值合法性就是要求中国文学“走出去”需确立一种合理性的价值观,通过对翻译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建构力量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进行价值论分析,从翻译策略的西方价值观转向批判性地审视西方价值观的策略选择,回归到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上来,切入中国文学的现实土壤,深入并扎根于中国文化思想,领会、译介与传播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思想,确定中国文化外译的合理性,从而彰显翻译的语言符号、社会功能、历史传承与精神文化的共享。
3 中国文学外译价值论建构的途径
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论建构是利用价值论的观点对整个文学外译的过程进行重新解读,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价值化,建构一种合理化与合法化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形态。它既不是在追问“何谓翻译”的本质问题,也不是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语言性描述,尽管这种描述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而是以“翻译应当成为什么”“应当如何翻译”为出发点,来探讨并确定翻译价值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意义。运用翻译价值的隐秘力量来分析中国文学外译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就是进入中国文学外译范畴的问题终究能够被“还原”为一种价值的问题或解释。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学外译是负载着不同的价值,或者说被价值化了而显露出翻译价值的光环,其深入发展就是要重新挖掘中国文学外译本身业已存在的“价值力量”,是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行价值化与合法化的更深层次的说明与解释,其建构路径可通过祛除功利性价值思维之“魅”、去除译者身份之“伪”与解除主体性价值观之“蔽”等方式来实现。
3.1 祛除功利性价值思维之“魅”
价值思维展现的是翻译价值研究一个独特的视角,包含了主体的价值观念、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策略、价值操控等多方面内容(刘晓晖、朱源,2017)。从价值思维出发可以发现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导向与动因。翻译研究的后现代性发展,使中国文学外译前所未有地遭遇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之间的冲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功利性价值思维风靡盛行,成为翻译实践的主导思想。中国文学外译最大问题就在于功利性价值思维的操纵,导致中国文学外译“只从市场角度评价翻译作为一种工程项目的即期效益,而未从精神建构的角度来衡量翻译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的事业所产生的长远的历史影响,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翻译焦躁症和市场决定论”(许钧,2017:2)。这使得翻译在各界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中往往被与诸如“象征性文本”“影子”“包装”“欺骗”等颇具负面色彩的用语以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误解和曲解联系在一起(刘云虹、许钧,2016a:100)。因此,祛除功利性价值思维之“魅”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如果单纯从功利性价值思维来对待中国文学外译,那么翻译就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的工具性活动,它与“象征性文本”“影子”“包装”“欺骗”等翻译隐喻彼此契合,形成了翻译价值观之“魅”。如此之“魅”赋予中国文学外译以一种市场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追求即期效益的价值行为将不断腐蚀翻译本身的价值信念,从而“遮蔽”了其真正的文学性与价值观。事实上,功利性价值思维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文学外译的内在价值在异域中被“异化”,遮蔽了其自身应具有的文学性与文化性,造成读者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误读、误解、曲解,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中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祛除功利性思维价值之“魅”,就是要寻回与彰显出中国文学“走出去”应具有的文学性。诚如许钧(2018b:7)所说:“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翻译学者更应自觉地从文化交流、思想驱动的高度来认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崇高历史使命,促进世界文明的互学互鉴,共同丰富和提高”。可以说,祛除功利性思维价值之“魅”就是保留中国文学自身文学性最重要且最紧迫的问题。
祛除功利性思维价值之“魅”,就是要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彰显出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学性,并以此进入翻译活动的价值化谋划。这种谋划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如何处理好翻译之“异”的问题、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就“异”而言,中国文学外译的本质要求就是既要维护中国文学的独特文学性,又要尊重异域文学的异质性,做到求同存异、异中存同,因而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转换,而是渗透着自我价值与他者价值相互博弈的复杂性活动。在自我与他者对立的视域下,由于对自我价值的误解以及对自我价值与他者价值关系的误解,中国文学外译必定会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缺失本身应有的文学性与价值观。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统一的视域下,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观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翻译沟通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它应建立并实现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对话。无论何种沟通与对话,翻译都意味着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联系,并促成各种关系的发生”(刘云虹,2018:98)。因此,祛除功利性思维价值之“魅”,就是警惕与避免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价值思维,强调中国文学外译是一种价值化的实践活动,做到对他者的尊重与对异质性的保留,维护中外文化的多样性,有效地彰显自身独特的文学性与价值观。
3.2 去除译者身份之“伪”
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各种翻译理念往往抓住译者概念的某个点(如主观性、主体性、能动性)而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译者不再隐身于文本而显形于翻译之中,呈现出一种主体性价值论难题。这种难题表明,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造成中国文学价值观的“异化”,翻译价值与翻译事实由此分道扬镳。翻译主体手持利剑,对中国文学随意删减增补,既可为翻译市场决定论所“操纵”,也可成为功利性翻译的“同谋”,其本身应该彰显的文学性遭遇“遮蔽”,从而造成文化误读。归根结底,翻译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化误读或文化过滤的同谋,那就完全背离了翻译在其跨文化交流本质下的根本目标(刘云虹、许钧,2016b:75)。因此,要去除译者身份之“伪”,就是要摒弃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使译者以“生态人”的身份出场。译者作为“生态人”,与文本是互生共存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任何一方被改写、被主宰、被操纵的绝对关系;译者与翻译群落彼此之间是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彼此适应的和谐关系(罗迪江,2020:18)。在“生态人”的作用下,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论建构就是追求翻译价值与翻译实践的统一,避免将中国文学外译功利化与市场化,促使翻译价值朝向合法性前行。在此,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合法性,“不是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文化,而是既要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灵魂,又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以创造出与时代相适应的独特的中国新文化”(许钧、沈珂,2013:66)。
翻译价值论的建构既要强调翻译主体的重要性,又要去除译者身份之“伪”。译者身份之“伪”就是在中国文学外译中一味地凸显与彰显译者主体性而无视各种翻译生态环境的限制,其后果就是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观被“遮蔽”。强调合理的价值观就是回归本真的翻译实践活动以去除某种超越主体性的“权力”与“地位”,因而预设了译者在中国文学外译中应该以“生态人”的身份出场。译者作为“生态人”出场,是一种生态化生存的出场,是一种以价值主体的方式出场,是对操纵者、改写者、吞噬者、背叛者的扬弃。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译者不仅被翻译活动赋予具有主导作用的翻译能力,将译前、译中、译后内在地联系起来并建构一种稳定的翻译生态系统,而且还被赋予协调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的关系、履行生态理性、保持生态平衡与维护生态和谐的特殊使命(罗迪江,2019)。因此,译者唯有以“生态人”的方式出场,才能去除译者身份之“伪”,将自身作为价值主体来建构中国文学外译应有的价值理论。如果审视中国文学所蕴含的文学性,立足于中国文学所体现的价值维度,那么它们都蕴含着译者要作为“生态人”出场、要促使中国文学外译凸显自身的价值的理念,而除去译者身份之“伪”的认识旨趣就是来源于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合法性及其价值论建构的敏锐洞察。
3.3 解除主体性价值观之“蔽”
不论是祛除功利性价值思维之“魅”,还是去除译者身份之“伪”,两者都与主体性价值观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最终将会汇聚并落脚于解除主体性价值观之“蔽”。中国文学外译实质上就是一种面向异域文化的译介活动,而且是一种承载翻译价值的合法化过程。简而言之,翻译价值作为中国文学外译所承载的属性,既要附着于中国文学外译之上,又要达到翻译主体需要的效应。当然,这种效应离不开中国文学外译的性质和功能,需要借用翻译主体的活动作为中介,并表现为翻译主体的价值判断。主体性价值观就是在翻译主体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判断之中产生的,它是翻译主体从自身的翻译活动出发来考察翻译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其目标在于超越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体现并确证翻译主体在中国文学外译的过程中自我发展的生存方式。那么,主体性价值观的“蔽”何在呢?那就是翻译价值与翻译事实的二元分离。事实上,翻译价值与翻译事实是相互依存的,“翻译事实是翻译价值认识的基础,翻译价值应该反映翻译事实”(高雷,2016:15-16)。主体性价值观不仅从翻译客体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学外译,而且也要强调从翻译主体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学外译。这样,翻译事实性与翻译价值性就被区分开来,否定了从中国文学外译这个翻译事实的陈述中直接推导出翻译价值及其价值评价,而是认定价值评价是从翻译主体的需要出发做出的;同时,翻译价值也并非只是翻译主体的自我追求而与翻译事实无关,而是在与翻译事实交互耦合的过程中体现翻译价值的优先性。作为一种翻译活动的事实,中国文学外译被纳入翻译主体的活动之中而承载了价值属性,从而被翻译主体做出肯定的评价。在此意义上,翻译价值虽然不是中国文学外译这个翻译事实的本身,却是翻译事实向翻译主体呈现出的价值属性。
解除主体性价值观之“蔽”,还在于约束翻译主体的主观性,回归翻译实践的合法性与翻译活动的“理性”。对于翻译主体来说,中国文学外译的翻译价值是主观的,但是翻译价值与翻译事实、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是互生共存的。翻译价值存在于翻译事实之中,翻译主体离不开翻译客体,彼此构成的依存关系为主体性价值观起到了直接的奠基作用。因此,中国文学外译不仅要关注翻译价值,也要将理性作为翻译价值评价的相关条件,并且承认理性在价值评价中的辅助作用。翻译是一个渗透着译者主观选择的能动过程,而任何选择都不应是盲目的,翻译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译者必须自觉地遵循一定的原则、合理地运用一定的方法(刘云虹,2019b)。因此,翻译活动不仅要强调中国文学外译(外在尺度)对翻译主体的约束,也要强调翻译主体(内在尺度)对其价值属性的定位。翻译理性与主体性、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的统一,从根本上促使中国文学外译回归并嵌入价值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之中,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翻译理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除主体性价值观之“蔽”,超越翻译主体的主观意愿,发现并指出翻译主体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判断是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从而让人们对中国文学外译的评价尽可能地符合翻译价值性事实。另一方面,翻译理性并非主体性价值观的基础,因而它对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评价较为客观,充分发挥分析与引导作用并深入地思考中国文学外译的长远规划,寻求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的统一,从而避免翻译行为陷入市场决定论与功利主义倾向。换而言之,当以合法性作为价值追求,这种追求所体现的主体性,就不再是一种主观性,而是一种合乎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形态,它既摒弃了翻译主体性之单纯的主观性,也让中国文学外译本身的事实性得到呈现,并且与翻译主体不断地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达到“视域融合”,让彼此的价值意义合乎其本性地呈现出来。翻译价值的主体性、合法性与理性在中国文学外译的活动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4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价值犹如一只“无形之手”贯穿中国文学外译的整个过程,它既体现了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偏向性,又要求中国文学外译回归价值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建构中国文学外译的价值论就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迫切要求,它是通过祛除功利性价值思维之“魅”、去除译者身份之“伪”与解除主体性价值观之“蔽”的途径来实现的。当我们从价值论来审视中国文学外译时,我们就不再像原来那样紧紧抓住“翻译事实”这个“金科玉律”而忽视贯穿与操纵中国文学外译的“无形之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文学外译的深入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新思考与新思路。以此为视域审视中国文学外译,翻译价值的偏向性与合法性、自我价值与他者价值、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翻译主观性与理性等相关话题将会进一步涌现,并在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中得以延伸与拓展,而这些话题将构成当代中国文学外译价值论研究的新风向。